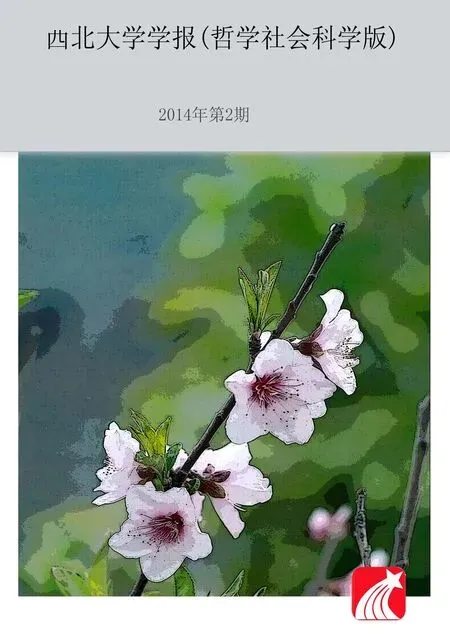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制度研究
唐欣瑜
(吉林大学 法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收益权是指利用财产并获取一定经济利益的权利[1](P402)。收益权是所有权的一项重要权能,它可以基于所有权人的意志和利益,与所有权人发生分离,所有权人为他人设立用益物权以后,用益物权人就享有收益权[1](P404)。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是指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利主体依据自己享有的相应权能而获得一定收益的权利。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集体土地收益权的权利来源,我国目前的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不可能直接并完全地行使对集体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而必须将其中的部分权能分离出去由他人行使,农村集体土地之上便产生了相应的权利如用益物权等。各项权利在转移和行使过程中能够带来不同的土地收益,相应的收益又分属于不同的权能所有者。所以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是在农村集体土地这一客体之上存在的一组权利,各项权利的主体依据自己享有的相应权能而获得一定收益。由于各权利主体在行使各自权利的动态过程中相对分离,或者二者合一甚至多者重叠,集体土地收益权的存在往往以其他权利为依附主体,体现在其他的权利之中。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是构建农民权利体系的基础,集体土地产生的收益是我国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有必要对农村集体土地之上的收益权主体进行归整,进一步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制度,最终有效实现我国农民的集体土地收益权。
一、问题的缘起:分散的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
我国目前并无自成体系的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在行使收益权的动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权利界定关系,因而零散地见于以下几个权利主体中:
第一,基于所有权而获得农村集体土地收益的主体,即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物权法》第39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我国《宪法》与《物权法》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客体——土地规定为集体所有,这里的集体虽然没有明确其含义,但集体当指一定成员组成的集合体,相对于农村集体土地而言,当指一定农民组成的农民集体。改革开放前,“农民集体”被认为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三类经济组织[2](P64),而现行法律规范提出的三类农民集体形态包括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以及村内农民集体。但迄今为止尚无私法规范明确界定农民集体的法律地位,学界也存在各种争议。有学者认为“农民集体”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种能够按照章程或规则行使权利的组织形式[3];也有学者认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一定社区范围内的全体农民组成的集体,只是“农民集体”既非自然人,也非法人或其他组织[4]。立法对农民集体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权利主体的制度抉择采取搁置争议的态度,以致现在很多学者批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性[5],但也并不能否定“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在我国法律中被多处提及,并在实践中享有相关的权利。因此,“农民集体”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享有集体土地收益权,是为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
第二,基于用益物权而获得农村集体土地收益的主体。用益物权是由所有权派生的权利,同时也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权。由于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本身的特点,所有权主体在集体土地上设置用益物权,用益物权主体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的方式实际占有、使用集体土地。由于宅基地使用权的用途受到国家的严格限制,只能用于建造住宅和附属设施,不得用作生产性的经营活动,它仅代表着国家对农民居住的保障,并不是收益的来源。尽管我国实践中存在着宅基地私下流转的现象,并产生了一定的收益由一定的主体享有,但该主体并不受立法认可和保护。我国《物权法》第125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由此可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对其承包经营的土地享有收益权,也是集体土地收益权的主体。《土地承包法》将农村土地承包分为家庭承包和其他形式的承包,家庭承包的主体是本集体的农户,其他形式的承包主体除了集体成员以外,可以是集体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可以流转,法律对于流转中受让的主体并没有限于是本集体的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包括特定的本集体农户,还包括不特定的其他主体。换言之,用益物权中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是确定的农户和不特定的其他主体。
第三,以征地补偿费的形式获得农村集体土地收益的主体。征地补偿费是指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时,对土地所有者在土地上的投入和收益造成损失的补偿,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被征地单位的各项补偿费用。征地补偿费以农地收益来计算,具体指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的总和。能够获得征地补偿费的主体也应当成为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具体而言,征地补偿费中的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所有,农村集体象征性拥有所属成员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在转让其所有权时依照法理应当获得与所有权相称的经济收益。安置补助费是对具有劳动能力而失去劳动对象的农民的生活安置,由失地农民获得。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即指被征用土地的承包经营者、已转包经营者,既如前述,包括特定的农户和不特定的其他主体。因此,在国家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农村集体、农民、农户还有不特定的其他主体都可以以征地补偿费的形式获得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成为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
综上所述,农民集体(农村集体)、农民、农户以及其他一些不特定的主体都可以是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主体,他们分散在集体土地所有权、用益物权的行使过程与集体土地的征收过程中,未成体系,只是作为其他的权利主体而享有收益权,很难得到完整意义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通过民事法律关系的分析和民事主体相关制度的构建,理顺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各个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明确收益权主体的法律地位,确保有效实现各权利主体在集体土地上的收益权。
二、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在私法关系中的应然定位
(一)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是私法规范调整的民事主体
民事权利的设定大多体现了主体一定的利益目的,即主体为了追求一定的利益而从事一定的民事活动而取得权利,没有利益,民事权利的设定就失去了意义[6](P204)。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集体土地收益权的权利来源。不论是所有权主体,还是享有所有权人分离后的收益权的用益物权主体,其作为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享有收益权的目的,就是实现基于收益权产生的各种利益,故由所有权与用益物权的私权属性所决定,其主体当然应具有私法性,由私法规范所调整。
如前所述,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包括农民集体(农村集体)、农民、农户和其他不特定的主体。农民个人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是毋庸置疑的,其他不特定的主体本身就需要具有民事主体的资格才能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用益物权的法律关系。而我国法律多处提及农村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农民以“户”为单位取得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但是私法规范并未明确此二者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尤其是“农民集体”的民事主体性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作为民事权利享有者和民事义务承担者的农民集体,同时也作为村民自治的主体出现,容易导致自治权与民事权利混同,使其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事权利主体[7]。从民事主体角度而言,除自然人之外,其他的主体均是拟制主体,拟制主体的意志是自然人意志通过一定的程序形成的集体意志。但在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管理经营主体的意思表示在很多时候理所当然替代了农民集体的意思表示,这必然会给人们造成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到底是农民集体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的困惑。一些学者自然就会认为农民集体不是民事主体,因为作为民事主体的“集体”及其代表主体的民事权利竟与农村自治组织的自治权力存在混同可能。成为私法的主体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存在,其二是国家法律的确认[8](P63)。无论是《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还是《物权法》,都承认了农民集体的民事主体地位,尤其是在《物权法》颁行后,从规范意义而言,农民集体已经确定无疑被赋予了民事权利主体地位。完整意义上的民事主体要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立法赋予农民集体的民事权利能力源自对农民集体是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的明确规定。农民集体还必须具备行为能力,即其要有自身的意思形成与表达机制的方式,而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点上我国的立法并没有就农民集体的意思形成与表达作出规定,多数农民集体欠缺凝聚成员意志、反映成员利益的成熟机制,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的实际能力尚不完备。但农民集体作为民事主体在法律上是不存在任何障碍的,农民集体在立法和所有权登记中固定使用,能独立享受民事权利,独立承担民事义务,还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谈判与诉讼。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以及《物权法》的相关表述,农户也可以作为与农村集体直接相对应的享有成员权的民事主体,在农村相关法律中拥有主体地位。例如,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中,农户在承包经营合同中是签约方,是承包经营权的享有者,也对外独立承担着相应的义务。
(二)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直接参与收益权的外部与内部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必须具有外在的独立性,能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具有一定的意志自由[9](P364)。在财产法意义上,农民集体作为群体主体的抽象而享有土地所有权,实质意义是将特定的土地资源归属于特定范围内的村民。也就是说,农民集体的存在,直接的私法意义是排他功能,排除其他民事主体对农村集体财产利益的分享。农民集体作为一个私法主体,对外是一个独立的自由意志单位,代表农民集体成员以集体的名义行使收益权,发生对外法律关系的法律行为,获得基于土地所有权而产生的经济利益即收益。而农民与其他不特定的主体作为收益权的主体,对外可以作为独立的自由意志主体,以个人或单位名义与第三人发生外部法律关系。因此,不管是农民集体、农民、农户还是其他不确定的主体,都直接参与到收益权的外部法律关系中,即收益权主体与其他权利主体的法律关系。
各个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在集体土地收益权内部也发生对内法律关系的法律行为,体现内部法律关系,此类内部法律关系是指在收益权内部存在的农民集体、农户、农民个人以及其他不特定的收益权主体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农民集体、农户、农民个人以及其他不特定的收益权主体尤其是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在对外行使了收益权之后,在收益权内部享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参与集体土地的收益分配,反映出内部收益分配的法律关系。究其原因,中国农民集体存在的法理基础在于为其成员提供与他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公共产品[2](P64)。而此类公共产品的提供必须要使集体拥有一定的经济来源,集体土地所产生的收益理应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集体享有一定的收益分配权,再以公共产品或其他方式由所有的集体成员共同享有。因此,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参与的收益权外部法律关系发生在收益权主体与外部民事主体之间,直接参与的收益权内部法律关系则发生在各个收益权主体之间。
(三)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具有不变的内核
对于法律权利而言,其要寻找的是能够依归的主体,这一主体必须具有边缘清晰的特性,以提供实践操作上的可能性[2](P54)。首先应在民法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界定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的收益权主体,但由于我国农村情况复杂,务农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在农民集体成员中的比例逐年下降,农民集体所占有的土地也不再作为耕地使用,而是大量用于创造集体收益。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本身具有复杂性以及发展变动性,任何一种静态视角观察到的往往是特定时期的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而不能反映全部。与其利用民法基本理论牵强附会地描述某一时期的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不如以发展的视角去观察,于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发展变动中将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不变的内核描述出来,并结合民法基本理论抽象出农村集体收益权主体的概念,还原其私法之本来面目。因此,从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发展变动来看,并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有以下几点不变的内核:第一,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主体有一定的表现形式,或是个人,或是集体,甚或是其他不特定的法人。其中个人表现为个体权利,集体或法人则表现为群体权利。第二,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中特定的主体集体是依照特定范围确定的,特定范围可以是乡(镇)、村、村民小组等农民进行生产生活的区域,特定范围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动而有所改变,例如有的农村集体已经撤村,不复存在,有的农民加入城市户口,不再是集体成员等。第三,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中不特定的主体是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农民集体以外的个人或其他组织,是变动的无法确定的因素,因而无法进行具体的权利主体构建。
三、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制度之构建
在法学当中,我们把那种对既已存在的、艺术上尚且零散的部分从整体上进行再创造的活动称为构造[10](P171)。在通过民事法律关系分析了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地位之后,以民事主体的基本原理构建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制度是必然选择。
(一)农村集体是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群体性主体
“集体”是建立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后的法律伴生现象,但在经历数十年的发展之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在我国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11]。如果继续使用“农民集体”这个与“国家”一样抽象的概念,集体土地收益权同样存在行使上的困难。但如果仍要以“集体”作为民事权利主体,那么就必须首先对集体与其成员之间的法律关系按照民法的基本规则加以规定。笔者认为,应该使用“农村集体”来代替“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收益权的主体,使权利与主体资格对号入座。
农民集体是传统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上的表述,目前大部分法律文件采用的依然是“农民集体”的概念,并不能体现农村集体的动态性与发展性。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农民集体”中的“农民”意指村、村民小组和乡(镇)范围内的农民,但具体落实到那一层范围的农民,就有所指而无所确指了。立法逃避了对农民集体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权利主体的制度抉择,只静态地规定了“农民集体”。“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的概念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农民集体”是农民个人所组成的集合体,它更多的重点是落在“个人”上,甚至可以拆分理解为“农民的集体”。而“农村集体”是一个整体的概念,由特定农民成员构成的集体整体,重点是以“农村”为“供体”,而不是被拆分理解为“农村的集体”,不管作为“供体”的“农村”里的“农民”如何变动,它都作为一个动态性的群体主体。也就是说,它的“农民”构成不是固定不变的前后对应一致的关系,从某种角度而言,不仅包含当前农民集体成员的权利,还包含将来成为农民集体的人的权利。因此,“农村集体”是最为适合被重塑为农民集体组织形态的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表述为:“这块土地是某某村集体的”“这是某某村集体的土地”,而不会表述为:“这块土地是某某村农民集体的”“这是某某村农民集体的土地”,可见,采用“农村集体”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的形式也符合我们的语义逻辑和习惯表达方式。
法律之所以要赋予农村集体主体地位,因为需要通过农村集体的主体地位负载特定的功能。农村集体作为主体,在特定的土地资源和特定规模的农民的基础上划定了一个界限,设定了一个私法自治单位,在这个自治单位内,“这些权利的主体并不是有组织的集体,而是某一类人。与一般的个人权利也不同,这些权利的主体不是所有的个人,而是某一种、每一时期或处于某一状态下的个人[12](P1)。”农村集体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它以一种群体性主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它的群体是与农民个人相对应的,介于组织和自然个人之间的人群混合体,不是抽象于个体之外的组织,而是个体结合的本身自在整体。因此,农村集体是一种群体性的集合主体,作为集体土地收益权的主体,对于集体因土地产生的经济利益具有收益权。而作为一个私法主体,对外是一个独立的自由意志单位,对内通过民主程序、代理和代表机制,在全体农民成员意志表达的基础上形成共同意志。只是现有的私法规范对于农村集体的性质、法律地位、机关构成、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等问题的规定不甚明确,应予改进。
(二)农民、农户是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个体性主体
在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法律关系中,集体的权利和义务与农民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有所区分,集体代表集体成员对外发生法律关系,享有收益权,对内则由农村集体与农民享有集体收益分配权。但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民应当是基于土地所有权所产生利益的最终享有者,即在集体土地收益权法律关系中,作为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的农村集体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但集体土地收益权存在的最终目的应是实现其成员的利益。笔者认为,自然人(农民)及农户是适格主体,农民与农户是与农村集体相对的权利义务主体,虽然农村集体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但是农民与农户通过法律制度赋予和保障的成员权方式将农村集体利益转化为农民利益。
农民个体是指在一定的农村集体场域内生产生活、被农村集体认可为集体成员的自然人。自然人在私法上是当然适格的民事主体,无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以取得农村集体的成员资格为依据而获得一定收益,是为集体土地收益权的权利主体。农户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作为农村集体场域内自然人联合的较为固定的形式,在相关法律中拥有主体地位。农民与农户作为集体土地收益权的主体,它们都表现为一种与群体性主体相对应的个体性主体。农民是作为个体形式存在于农村集体中的基本主体,在集体经济活动中,个体农民是最终意义上的利益当事人,相对于农民个体,农户、集体、社会、国家均是其生存的环境和手段,这些组织的存在和运行,最终服务于农民个人的生存发展利益。在收益权的法律关系中,每个农民均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收益权,而个人也是农户中的构成要素,在家庭中同样享有因家庭成员权而获得的收益。农户作为农民个体行动单位,它最大的体现是成员的个体性,而不是群体性主体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性。也就是说,它与群体性主体是有区别的,作为群体性的权利主体,农村集体的存在意义表现在“并不是说要将集体土地划分成各个份额归每个农民所有,但法律应当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利益应由全体成员共同享有。”[13](P530)而农户的存在意义是能够作为一定条件下的利益获得单位而使利益最终安然落置在农民个体手中。因此,农户虽然是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一定自然人联合,但它在权利上的表现还是个体性的,依然属于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个体性主体。
(三)国家不应成为隐性的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
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当中,国家通过强制性征收将农村集体土地由农村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国家享有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收益权,国家给农村集体以及农民一定的征地补偿。但凡是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为国家建设用地,同样特定位置特定的地块,身价翻十几倍甚至升值更多,但按照中国当前的土地制度安排,农民所获得的征地补偿是相对农民之前的务农损失的补偿,而不是农地非农化之后土地市场价值的补偿,即高额的土地增值收益。为获取巨额的土地出让金,我国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低价向农民征地而在市场高价卖地。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才5 587亿元,2007年猛增至9 933亿元,2009年为15 900亿元,2011年达到历史性的31 500亿元[14](P99)。而在农村集体土地向城市国有土地转化的这一过程涉及的土地收益分配主体主要包括国家、用地单位、农村集体以及农民。据有关测算与学者的统计,征地收益分配的比例大致为:农民5%~10%,农村集体25%~30%,各级政府及其机构60%~70%[15]。我国从1989年5月至2008年,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为城市建设用地后的土地增值收益均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法分享土地增值[16]。政府的这部分收益并不是基于国有土地的所有权而享有由此而产生的收益,而是在农村集体土地向城市国有土地转化的过程中,因为土地的农用和非农用的使用用途不同产生的截然不同的收益,实为农村集体土地本身就蕴含了这部分增值收益。实质上,国家真正享有的这些土地的收益是从农村集体、农民应得的收益那里转移过来的,国家、农村集体和农民之间,国家是土地最大的收益者,农村集体和农民无法分享自身所有的集体土地在征收过程中因用途改变而产生的增值收益,自然就无法成为高额增值收益的收益权主体。而国家,明面上是基于已经转移为国家所有的土地所有权而享有土地的收益权,实则是隐性的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主体。
国家是土地的管理者,在基础设施等公共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从而使土地得以升值,国家理应是土地受益者之一,但国家不应利用公权力以土地征收的方式成为隐性的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对于政府收益,应区别政府行为的公法与私法关系。政府对土地的公益性投入,如基础水利、交通设施等,即使土地升值,也仅体现为公法关系,政府不能享有私法上的集体土地收益权,只能按公法关系以土地的税收方式获得集体土地收益。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国目前尚不认可农村集体作为市场交易主体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农村集体不能代表其成员独立参与市场交易活动,土地市场化的经济利益相对中国的农村集体而言是得不到保障的。只有理顺集体土地之上各收益权主体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其私法权利主体之法律品格,还其以私权面目,使其依据民事法律制度的法理与规则,防御国家公权力的不当干预,以期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之有效实现。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 侯德斌.农民集体成员权利研究[D].吉林大学,2011.
[3] 肖方扬.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缺陷与完善对策[J].中外法学,1999,(4).
[4] 丁关良.“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之客观界定[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5] 蔡立东,侯德斌.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缺省主体[J].当代法学,2009,(6).
[6] 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 李国英,刘旺洪.论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权利制度变革——兼评《物权法》的相关规定[J].法律科学,2007,(4).
[8] 佟柔.中国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9] 孙国华,朱景文.法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0]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11] 孙宪忠.确定我国物权种类以及内容的难点[J].法学研究,2001,(1).
[12] 常建.人权的理想·悖论·现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13] 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4] 贺雪峰.地权的逻辑Ⅱ:地权变革的真相与谬误[M].东方出版社,2013.
[15] 宋敏.城镇化与土地收益分配[J].安徽农业科学,2009,(2).
[16] 赵秀清,赵秀丽.农村土地收益分配“兼顾公农”模式成因探析[J].开放导报,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