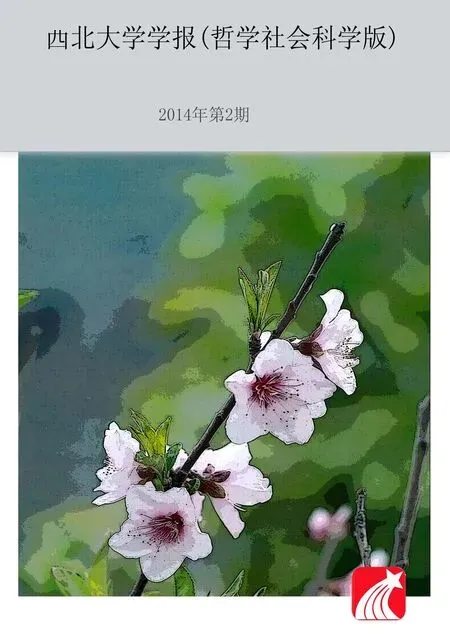小说类型演替略论
张永禄
(1.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2.上海政法学院 文学院,上海 201701)
韦勒克与沃伦在那本广为流传的《文学理论》中乐观写道:“文学类型史无疑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领域”[1](P301)。这一论断自然也包含了对小说类型史的期待与乐观。 但是,小说史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描述为小说类型史?小说类型史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概括为小说的发展史?这决定了小说类型学的解释效力,一个没有解释效力的理论是没有价值的理论。我们说,“小说类型”是一种事实,是历史和现实存在;与此同时,在研究者的理论概括和审美批评实践中,“小说类型”也是一种理论假设,将小说界定为类型来研究,意味着为这种小说的研究和批评假设了理论前提,这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相对的理论、思想指导。
小说的世界好比流动的海,无边无际,深不可测且变幻不拘,任何小说理论都无法涵盖其生动性与复杂性。这就客观上要求对小说类型理论要用发展的眼光、动态的模态和现象学方式描绘它,尽可能贴近小说世界本体。换言之,当我们解读特定小说及小说现象时,需要保持开放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尽可能把特定对象置于小说的海洋中观测与比较,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否则,我们推开了一扇窗,却关闭了大门。但是,反过来,我们也得说,小说理论水平高低的较量,基本判定准则不外乎是看谁能更准确地描述小说本身,谁更能及时发现并恰切阐释隐藏在小说世界中的独特性。小说类型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能接受小说现实与历史的检验,能够解释小说史上的基本的现象和难题,并能像元素周期表般预测一定的未来。本文试图从小说类型发展的视角,用类型学理论对小说类型的演替状态,影响小说类型演替的因素,以及小说类型演替与小说活力关系等三个方面做初步探讨。
一、小说类型演替描述
把“类型”历史化是非常困难的。类型更多的是共时性概念,用来解释小说发展的共时现象更有效力。事实上,小说史的发展极其复杂,我们很难找到纯粹而透明的“类型晶体“(理想的类型模态),小说类型的发展是在其内在规律和外在干扰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变异过程。宏观地看,的确存在一些历史类型,它们和小说史几乎是对应的,似乎能完整解释小说史,尽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这样做过。但是,通过简单的观察我们就可以发现,小说在口耳相传时代、纸面文学时代、网络文学时代,都呈现出某一种或者几种类型主导的特征。比如在口耳相传时代,小说的主导类型是演义(中间当然也夹杂文人笔记小说等,但不是主流类型),到了小说的纸面文学时代,印刷小说呈现出更多的文人单独创作倾向,表现为文人个人案头小说的特征, “文人小说” 因此成了某种主导类型,代表这个阶段的小说的主要成就,比如《红楼梦》以诗词文韵为表征的雅文学特质。到了网络数码时代,小说又重新表现为某种大众化、世俗化特征,新大众体小说特别流行,比如起点中文网上的盗墓小说等,其点击率超过千万人次。这种小说是在和读者网络互动的过程中创作出来的,文体风格和审美倾向是充分的世俗化和大众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小说的大历史似乎可以用小说类型的某种“历史标志性形态”来解释。当然,这种工作,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这种设想也许是可行的,提出这样的设想,并没有离开小说类型学的理论框架范围。
从小说类型学的本体上讲,具体的小说类型应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逻辑统一,共时性表现在其表层的基本叙事语法和深层的语义结构,历时性则表现在这些基本语法与深层结构的生成过程和阶段性的历史特征乃至合理变形,它们共同构成了小说类型研究的基础。研究小说类型的基本叙事语法时,一个重要的、也是奠基性工作就是要从追踪特定类型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而厘清小说类型演进的基本规律。我们粗略考察汉语小说类型演进的历史轮廓,可以分这样几个方向来讨论:
(一)单一类型的艺术进化
和发现自然界的很多规律一样,类型成规的获得需要漫长的历史积累过程,它是多位甚至数代小说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以经典作家的伟大创造及其杰作为根本表征。类型的理论指认首先依赖某些作者的写作风格的定型和成熟,其次要依赖一群作者对该种风格的认可、发展和推升。有的时候,甚至表现在一部小说的漫长成熟过程上。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是很常见的,比如英雄传奇《水浒传》跨越了从北宋末年至元末明初的二三百年历史。期间,无数作者参与了“水浒”故事的创作,比如《东都事略》《三朝北盟会编》《宋史》《醉翁谈录》《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大宋宣和遗事》中都载有“水浒”故事,这些故事内容和表述形式在不同阶段都有一定的发展变化,只有到了施耐庵、罗贯中,他们将这些民间传说和原始早期作品作了最后的艺术加工及创作,使民间作品升格为不朽的文学巨著,同时也奠定了中国英雄传奇的基本范式。成熟的小说类型既要在艺术内部形成自己相对稳定的形式法则和独特的审美风貌,还要经受住来自外部的方方面面的考量。这里以颇具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小说类型之一的武侠小说为例。武侠小说在中国至少有一千年的历史。它的上限可以追溯到唐代豪侠传奇,而后是明清侠义小说,接着是清末民初的旧武侠小说,最后到上个世纪50年代在港台风起云涌的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今天的武侠小说和以往时代的任何一部武侠小说相比,整体上非常成熟,但是,若没有唐代豪侠传奇、明清的侠义小说和民国的旧武侠,就没有今天的新派武侠小说。何以如此断言呢?这是因为武侠小说的基本叙事语法和艺术规范就是从它们那里慢慢沉淀下来,逐步形成了今天的成熟的武侠范式。比如唐代的豪侠传宣扬的是“报恩”和“仗义”的主题,到了清代的侠义小说在继承和发展打斗场景的同时,还从风月传奇中偷来了“情”,把单纯的狭义精神丰富为“侠骨柔情”,并从公案小说那里找到了长篇的结构艺术,有了如上因素有机磨合,武侠小说的艺术形式才大体成熟,作为独立类型才最终站住脚。在考察各种小说类型具体形成和成熟的历史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小说类型的历史大致经历了类型倾向—初具模型—模型成熟—类型变体—反类型等”[2](P74)。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须要树立对于小说类型的历史主义态度,对于很多今天看起来并不算成熟的小说保持足够的尊重和重视,因为在小说类型的源头,那些今天看起来很幼稚的小说,它很可能是特定类型的开端。这是我们研究单一小说类型发展演进的基本意义所在和态度要求。以托多·洛夫(Todorov)为首的西方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叙事研究过于关注共时性的叙事公式和语法,而疏忽叙事成规、语法的历史形成过程,我们今天研究小说类型学不能重蹈西方的旧辙。
(二)小说的类型变体
在小说的实际发展过程中,类型化趋势并不是直线性的,而是有着曲折与反复。也就是说,作为类型的小说集合体中并不存在自然客观的模式或范型等待研究者去发掘。否则,小说研究就如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旦找到类型模态,就可以按照模态复制,创作就可以进入工程流水作业,作家不过是流水线上的码字工人。作为理论的小说类型学,和所有的理论一样,存在把研究对象理想化的倾向,不同程度地把对象纯净化和突出化,这就有了技术上的去杂质和简化处理。但在实际的小说中,那些杂质和被简化的成分依然存在。这些杂质时时刻刻对基本叙事语法和核心元素等构成危险。另外,基本语义结构模态也会因为核心元素的性质变化出现结构变形,而基本叙事的语序组合关系也处在发展之中,以及作家的艺术个性等因素导致了实际的创作情况往往是,作家在创作上大致采用某一基本语义结构或叙事语法乃至叙事模态和行动元关系,但对一些亚元素作了改动,在行动元矩阵上调整关系构成,在基本语法中增补或删减一些质态。表面看,我们仍能判定它的类型归属,仔细深入研究却又发现了很多“违规”,这就是类型之变体。类型之变体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也是类型小说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过去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小说变体现象,遗憾的是,由于缺少小说类型理论的指导,不能更加科学简明地解释这种小说类型的历史变化现象,习惯性地采用创作手法的创新,或者叙事模式变迁等说法来概括,并固执地认为这种现象恰恰是类型研究不能观照到的。这是错误的见解,是对类型研究和类型理论的倭化。
类型有一定的叙事成规、叙事语法,有相应的语言和知识特征,研究者正是依照这些既定法则作为参照来判定变体的。比如中国本土的言情小说是从唐代传奇开始,经过几百年的历史演变,逐渐发展为“才子佳人”的正体模态,最后凝固为“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成婚大团圆”[2](P175)的程式,但这个程式很快被《红楼梦》打破。鲁迅把《红楼梦》称为“世情小说”,认为它一方面保留了一定的言情气,少不了才子佳人小说和《金瓶梅》的影子;另一方面该小说大大突破了儿女之情,百科全书式地融进了社会、历史、政治、伦理和儒道佛,具有复杂的社会科学和哲学气质。《红楼梦》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统伦理预警下,热情讴歌性情至上的“爱情主义”的同时,也把婚姻生活同反映社会、揭露世态结合,把批判现实和理想探索结合起来,成为后来难以为继的高峰,这是一变。到了晚清,“原有的主题和模式已经丧失消费再生能力,需要再一次深化和综合使它完成跨时代的转折”[3](P191-192),在儿女和英雄的比例上做足文章,重视英雄轻视儿女,成了“无情的情场”;或者在“情”上下功夫,要么走出儿女私情,要么深化儿女私情。
(三)旧类型消亡和新类型催生
小说类型家族本身充满斗争,各种力量此消彼长,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台”,或者“各领风骚三五年”,于是类型的产生和消亡也就稀松平常。先看小说类型的消亡情况:一是那些市场定位不准,反应不明的类型首遭淘汰。晚清讽刺小说发展到官场谴责小说很受读者欢迎,但旋即堕落为黑幕小说,终因“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故而“旋生旋灭”[4](P236)。而梁启超鼓吹的晚清政治小说也因作者急于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拿小说舞台做政治演说的大众广场而导致艺术上过于粗糙而昙花一现。二是旧有的小说类型被新的类型取代。作为清官“虚张正义”的公案小说流行于明清,但到了讲民主和科学的时代就明显不合时宜,那种“辨色断案”和“凭智办案”的方式不得不被获取物证为表征的侦探小说取代。明人时遇安的《包公案》和今人罗云的《少年包青天》就是同一题材不同类型的小说,前者是传统的公案小说,后者是现代侦探小说。三是随着时代进步而失去存在必要的小说类型自行消失。那些在特定时代产生并风行一时的小说会随着时代进步而失去存在合理性,比如西班牙的骑士小说和美国的西部小说,还有我国的反特小说,莫不如此。时间是最苛刻和最公正的审判师,那些被历史淘汰的小说类型终究是因为其艺术上的粗糙等原因出局。相反,那些由于人为原因而被迫“禁毁”的小说类型会随着压制环境的消除而成为“重放的鲜花”,比如神魔小说(《西游记》除外)在五四以来作为封建“毒草”一度消亡多年,这几年随着文化市场的繁荣重新获得活力,属于这样的小说类型还有惊悚小说等。
小说新类型诞生。新出现的小说类型大致有如下四种情况:一、新类型的引进,这是小说发展最快捷的途径。从异域民族和文化里拿来新的小说品种,少走很多弯路,晚清小说界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从日本引进了科学小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等类型小说,除了政治小说外,另外两种小说不仅在我国生根开花,还对我国现代小说的发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引进新的小说关键要看水土服不服,比如西方的骑士小说和哥特小说就和中国文化差异比较大,不易进入汉语小说的文化语境,侦探小说进入中国有传统的公案小说作为底子而作为接受基础,但又因为“中国的现实社会科学和法制都不健全,缺乏一个侦探活动的公共空间,……中国作家的侦探故事大都不是来自现实生活,而是来自外国作品的启发”[5](P15),西方的侦探小说在引进本土过程中发生了两处大的置换,一处是把推理的科学性改为侦探者的个人智慧,忽视了科学的侦查手段和用证据说话;二处是过于重视情节的曲折与趣味,忽视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比如看不到“侦探”身上的民族性和时代感。二、本土小说类型的融合创新。在小说跨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融合出新,成为新小说类型。新世纪出现的奇幻小说,就是西方的科幻小说与本土的神魔小说融合;穿越小说则是幻化小说与历史小说的结合等,当然这些小说类型的最终确立要经过历史的考验。三、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原有的类型不能涵盖新的内容和思想,需要新的类型形式与之相适应。比如现代科学的兴起催生了科幻小说,而现代理性对个体的关注,启蒙思想的兴起对现代人的塑形,英雄小说或者传记小说则不能承担此重任,因此引发了成长小说的产生。四、随着技术进步,交流和传播小说的媒介变化,在形式上可能锻造出新的小说类型,比如网络、游戏的流行和风靡催生了网游小说等。
(四)主流类型因时更替
随着“自然力的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恩格斯语)。弗莱(Northrop Frye)在《批评的解剖》中详细考察了西方文学从神话到浪漫传奇,到高模仿,再到低级模仿,进而反讽或讽刺的规律及其必然性,中国古代文学也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体裁演进之概说。不独文学的体裁如此,小说的类型也不例外。新兴的小说类型要萌芽、成长,有的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有的不过昙花一现。随着新类型的加盟,类型家族格局变化,促使原有的类型观念改变,到了一定程度,既定类型序列被打破,就会重新排列秩序形成新的格局。没有谁能在类型的舞台做永恒的“主角”。但是,在主导社会等级和主流意识形态里,总是因时存在一些小说类型占据前沿和醒目位置,不同程度遮蔽了其他类型的光芒,成为一时的类型宠儿——主流类型。这里仅以现当代小说的主流类型演替为例来浮光掠影地印证此现象:晚清时代主要以谴责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等新旧小说杂呈,反应了过渡时期的暖昧与包容;五四在清理鸳鸯蝴蝶小说后,乡土小说、自我小说和问题小说粉墨登场*问题小说和海派小说、京派小说、新写实小说、新潮小说等严格说是小说思潮或流派类型,但鉴于习惯说法,这里不妨姑且用之,这也不经意透露了现代小说类型命名的混乱。。1930年代的革命小说、社会剖析小说、新感觉派小说和京派小说以及这一时期的武侠、言情、侦探等小说类型也有了长足发展;1950年代的革命英雄传奇、成长小说、乡土小说等独占鳌头;1980年代以来的则是伤痕小说、改革小说、反思小说、政治小说、新写实小说、新潮小说占主流位置等。从以上主流类型的演替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文学和政治的特殊关系,政治对文学影响巨大,使得我们了解的主流性文学都是带有特殊政治色彩和鲜明时代特色。而在意识形态宽松时期,精英心态、政治意识形态和市场法则三种力量则相互作用,小说发展更是呈现万花筒般的类型化趋向,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类型化发展。总体上,我们认为政治宽松,文艺相对多元化发展的时代,小说类型会百花齐放,比如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就有了《暗算》这样的类型作品获奖。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提倡各个历史时期应该有几个主导性的小说类型成为文坛寡头,而是认为,对于历史上出现的寡头小说类型我们要反思,对于未来的文坛我们还是希望多元化小说类型格局。
(五)跨类、兼类与反类
跨类小说是兼具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小说的特质,其中任何类型都不占主导地位而形成的一种类型小说变体,如武侠言情类型,武侠和言情并举,从而形成跨类特点;兼类是以一种小说类型特征为主导,兼具另一种小说类型的部分特征,本质上还是属该种小说类型,例如目前流行的职场言情小说,如果主导叙事是职场小说类型,只是里面增加了一些言情元素乃至叙事构型,整体上我们还是把这部小说指认为职场小说的类型,如职场小说作家李可的《杜拉拉升职记》尽管增加了不少主人公杜拉拉和王伟的爱情叙事成分,但读者和评论家还是把该小说定位为职场小说;反类则是某种小说类型发展到成熟阶段,该类小说内部出现自我革命(叛逆出新)或者几种小说类型有机融合(综合出新),逸出原有类型的边界,原来的基本叙事语法和语义结构已不能涵盖或解释其艺术特征,即所谓的“反类型化”走向。“反类型” 小说的出现往往是艺术创新的重要标志,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对传统纪传体小说的“反叛”。鉴于跨类、兼类、反类现象极其复杂,需另撰文来论述*相关论述可参看葛红兵的《小说类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三、小说活力与类型替演
好的理论既要简单化,又要对复杂的文学现象具有阐释力,还要有周延历史的能力。对汉语小说类型演变的描述和归化,目的是谨防研究者把类型理论当成小说DIY工坊里的陶泥,捏造为随心所欲的样品,而是倡导研究者们深入小说鲜活的世界,把小说类型理论催化为小说发展的有效驱力。具体来说,体现如下:
(一)类型演化理论紧贴小说实存地图
无论是对小说发展之树作历史的纵向剖析,还是作横断面鸟瞰,小说类型在时间上的演化形态和空间上的分布格局是非常复杂的,实际上并不存在古典主义者所鼓吹的“纯粹类型”,即便因人为原因使得某个时段和特定地域会暂时出现高度提纯的小说类型(比如文革期间的革命历史小说),但终究不过是昙花一现,时局一变,被压抑的小说类型就会变成“重放的鲜花”。小说类型学应该适度历史化,以应对错综复杂的小说史内在的演变逻辑,通过对小说类型的演变来追溯并找到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作家个性特色,形成历时的与共时的,创新的与传统的,集体的和个体的,内部与外部的,所指和能指相统一的表述模式,描绘出既复杂又清晰的小说史地图,这是小说类型学理论需要面对的艰巨任务。
(二)解放小说类型活力,促进小说创新
“类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术语,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机体,它和正常人一般,有诞生、有成长、有斗争、有传承、有变形,有坚守与自反、还有跨越……。 承认类型的存在,重视类型自身的规律所在,并不是像有些敌视或者轻视类型的学者所说的类型化就是模式化、机械化或雷同化,恰恰相反,研究类型成规的意义在于它的全部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是艺术创新,既定的成规是考察艺术创新的基本参照系,离开了成规这个参照系,我们将无法判定具体小说的创新所在。反思今天小说批评的困境,我们认为最大的障碍不在于缺少理论的支撑,而恰恰在于缺少批评的科学性,这个科学性很大程度依赖于类型成规这把尺子。大胆承认艺术成规并不会使得艺术形式规律固化,而是在促进创造者在尊重成规基础上,有目的和有分寸地破坏这个成规,促进艺术的自我更新。从运动视角看,类型在其诞生之日起就把既是自我又不是自我作为自己存在的规约。在漫长的小说历史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固定不变的类型,更看不到能让作家机械复制、自我复制的创作类型。真正的小说类型,既向不同的小说类型敞开,又向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开放,自觉调适艺术模态与语义结构,努力承担时代和社会赋予的使命,才能真正获得小说史的认可。也就是说,小说类型常常拥抱开放性,常常允许自己接纳或者被纳入其他类型,出现跨类、兼类现象,允许出现反类现象,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永葆“青春的活力”。
(三)树立小说类型平等理念,反对小说等级观
小说演进的事实清楚地展示了不仅特定小说类型的内部在不断地衍化和变体,不同小说类型之间也在时时进行渗透、兼容、跨越等,乃至杂化出新的类型。这既让我们在清醒地认识到小说类型的复杂性事实外,又提醒我们应该树立平等的小说类型理念,不厚此薄彼,承认并尊重每种小说类型的艺术法权:在审美上有独特的艺术表达和魅力构成;在认识论上有其认知世界的特定视角和解释模式;在价值论上有其相应的情感诉求和精神取向。在小说的百花园里,让各种类型的小说之花自由开放,竞相绽放,鼓励不同的小说类型相互交处,相互激发。作为小说花园的花工——研究者和批评家们——的任务就是提供它们必要的阳光、雨露和养料,这是小说花园繁荣的前提。如果无视这一基本前提,人为地排座次、分等级,最终难免会搞出自相矛盾的闹剧。比如很多研究者瞧不起言情小说,认为它仅仅停留在“儿女私情”和“家庭琐细”里,不能登高雅之堂。其实,晚清以来的很多言情小说也发生了现代性的质变,除了塑造具有自由、平等、爱国精神等现代意识的主人公外,还把人物活动的背景扩展到广阔的社会,乃至战争层面上,在爱与情的内涵与诉求上都有了很大改观,我们能说它比同时期的主流的乡土小说、问题小说和革命小说低级吗?反过来说,其时大力提倡的社会分析小说,如矛盾的《子夜》不也非常多地借鉴了言情的成分吗?坚持类型平等,并不意味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的“一视同仁”。在人类历史的某些特殊时刻,根据需要提倡某些小说类型和适当压制某些类型,是艺术史上常有的现象,如建国初期,对革命历史小说和成长小说的重视和提倡等,但是,为了突出这些类型打击其他类型则是不妥当的。
另外,我们还要提倡对类型的评价要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即对历史小说类型苛刻,对当代类型宽容。对待发展历史跨度长,很多问题相对定型的类型,看得相对比较分明,我们的尺度不妨紧一些,而对于当下正在兴起的新的类型,其艺术机制和模式正处在形成过程中,还充满变数,我们不妨把尺度放得宽一些,给它们更多的发展空间,促进自由创造。
参考文献:
[1]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4.
[2] 张永禄.现代小说类型批评实践检视与类型学建构[D].上海大学,2009.
[3] 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小说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鲁 迅.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M].济南:齐鲁书社,2004.
[5] 孔庆东. 抗战时期的侦探滑稽等小说[J].涪陵师专学报,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