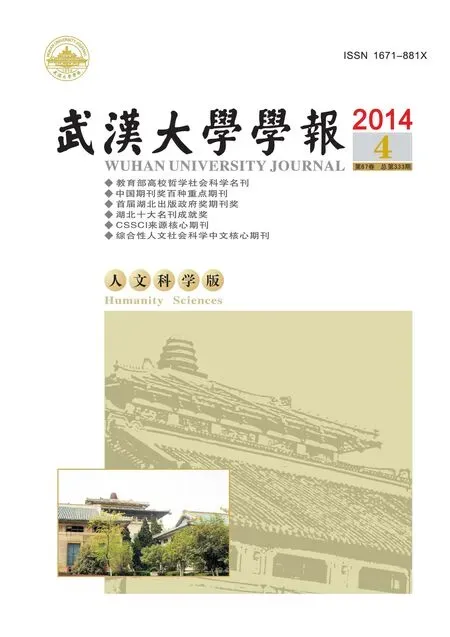从联合托管到南北分立:美国与朝鲜半岛冷战对抗局面的形成(1944-1948)
梁 志
自二战后期直至后冷战时代,美国一直是影响朝鲜半岛内外部关系演变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众多史学家才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讨论的起点便是美国在朝鲜半岛分裂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同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朝鲜半岛冷战起源的其它因素*笔者认为,朝鲜半岛分裂问题研究与朝鲜半岛冷战起源问题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表现为在观察对象方面二者的时间跨度和主要事件大体重合,均重点考察美国、苏联和朝鲜左右翼三国四方互动关系。区别表现为在观察视角方面前者更多强调的是外部大国势力范围之争和一国内部派系争斗,探究的是导致朝韩分立的责任问题;后者更多强调的是外部大国和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及其引发的争端,探究的是在朝鲜半岛缘何会产生美苏之间的体制之争和当地左右翼之间不同的民族国家建构路线。——却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且既有研究多从1945年开始叙述,忽略了美国国务院战争末期对朝鲜政策的分析及其影响*近来有关朝鲜半岛分裂问题的研究可参见小此木政夫:《美国进驻南朝鲜: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早稻田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五届冷战史工作坊会议论文,2013年3月3日;Mark P.Barry.“The U.S.and the 1945 Division of Korea:Mismanaging the ‘Big Decis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2012,29(4),pp.37~59;Kim Bong-jin.“Paramilitary Politics under the USAMGIK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Korea Journal,2003,43(2),pp.289~321;Bonnie B.C.Oh(eds.).Korea under the American Military Government,1945-1948.London:Praeger,2002; 董洁:《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形成:从不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到托管政策的提出》,载《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51~158页。有关朝鲜半岛冷战起源问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下:Charles K.Armstrong.“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Korea,1945-1950”,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03,62(1),pp.71~99; Park Myung-lim.“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Cold War in Korea:Entangling the Domestic Politics with the Global Cold War in 1946”,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2001,2,pp.309~350; Kim Kyun.“The American Struggle for Korean Minds:U.S.Cultural Policy and Occupied Kore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95; Charles M.Dobbs.The Unwanted Symbol: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Cold War and Korea,1945-1950.Ohio: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1。,更很少有学者将朝鲜半岛作为个案探讨更为宏大的冷战起源研究方法论问题。鉴于此,本文拟主要依据《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以二战后半期为观察起点,以美国、苏联和朝鲜左右翼三国四方互动关系为宏观背景,着重辨析朝鲜半岛冷战格局形成中的美国因素,并就冷战起源研究的视角提出自己的认识。
一、 “国际托管”构想:由大国合作向遏制苏联的转变
二战期间美国提出托管朝鲜的政策设想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对日宣战,但美国并未立即将解放朝鲜列为政策目标,原因是朝鲜解放与早日打败日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Susan Chung.“Disparity of Power:The U.S.Engagement with Korea”,MA thesis,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2004,p.11.。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迟疑,出于顺应欠发达国家民族解放潮流、控制日本殖民地和委托统治地以及维持战后东亚地区稳定等考虑,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终于提出对朝鲜实施国际托管的设想。1943年3月27日,罗斯福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外务大臣安东尼·艾登时首次明白无误地指出,战后朝鲜应被置于国际托管之下,托管国包括中国、美国和“其他一两个国家”*Kyun Kim.“The American Struggle for Korean Minds:U.S.Cultural Policy and Occupied Korea”,pp.63~64.。
在美国提议对朝鲜实施国际托管前后,国务院的相关分析判断十分值得关注。早在1942年2月20日,负责远东事务的国务院官员威廉·兰登(William R.Langdon)便在一份有关美国对朝鲜政策基本原则的重要备忘录中指出,大约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让朝鲜人具备自治能力和自主国防意识。此间,外部大国的保护、指导和帮助必不可少*转引自James I.Matray.“An End to Indifference:America’s Korean Policy during World War II”,Diplomatic History,1978,2(April),Issue2,p.182。。1943年下半年,国务院开始明确地将朝鲜问题与战后苏联在远东的地位联系在一起:日本败降后,苏联将趁机填补朝鲜半岛出现的权力真空。苏联很可能会以朝鲜为例鼓吹其在处理殖民地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借此攫取更多的当地资源,获得不冻港,谋求比中日两国更有利的战略地位。苏联的所作所为“不但会严重挫伤中国对战后和平的信心,还会挑动中国在东北亚或其他地区采取类似的单边行动”*刘晓原:《东亚冷战的序幕:中美战时外交中的朝鲜问题》,载《史学月刊》2009年第7期,第73~74页。。1944年3月29日,国务院远东地区司际委员会(Inter-Divisional Area Committee on the Far East)在一份关于对朝鲜实施军事占领的备忘录中论证道,假使苏联对日宣战,它最有可能从朝鲜半岛北部向日本人发动进攻,并因此占领相当一部分朝鲜领土。朝鲜海外军队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苏联红军训练出来的那批朝鲜人。他们完全接受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府管理模式,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一旦时机成熟,这些人便会立即参加到解放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去。鉴于此,务必防止苏联单独对朝鲜实施军事占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RUS),1944,Vol.5,The Near East,South Asia,and Africa,The Far East,pp.1225~1227.。5月4日,该委员会在论述朝鲜临时政府问题时进一步指出,为防止一国在朝鲜事务上独断专行,应对朝鲜实施多国托管。托管国可能包括美国、中国、苏联和英国。反之,倘若由苏联单独监管朝鲜,朝鲜的苏化(sovietized)*根据前文述及的国务院1944年3月29日备忘录对有关苏联训练朝鲜人的描述,此处的“苏化”应指“共产主义化”。会令中国忧心忡忡,美国也将因此认为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安全受到了威胁*FRUS,1944,Vol.5,The Near East,South Asia,and Africa,The Far East,pp.1239~1241.。
概括地讲,二战后期美国国务院在对朝鲜实施国际托管方面的关注点大体历经了三个阶段:1942年,重点讨论战后初期国际社会监护朝鲜的必要性;1943年,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苏联将朝鲜纳入自身势力范围的意图,继而提出防止苏联单独占领朝鲜的政策建议;1944年,进一步强调苏联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可能对朝鲜产生的不良影响,并以此为依据力主对朝鲜实施联合托管。由是观之,战争尚未结束,国务院已开始从美苏意识形态对立的视角观察朝鲜问题。
罗斯福接受了兰登1942年2月的论断,但国务院随后对苏联朝鲜政策的分析框架却似乎并未打动他,原因是这位美国总统对战后东北亚格局的设计渗透着大国合作的理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多次表示:“在诸如朝鲜独立这一类问题上排斥苏联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受欢迎的。”考虑到中苏两国过去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的斗争,只有各大国达成对朝鲜半岛实施国际托管的协议,才能切实保证该地区的稳定。然而,国务院的主张并没有被一直束之高阁。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突然去世,在此前后美苏关系在欧洲明显恶化,苏联参战对亚洲局势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印证了国务院对苏联战略意图判断的正确性,这一切促使美国对朝鲜政策的出发点在战争即将结束之时迅速由四强合作转变为美英中三国联合抗衡苏联*James I.Matray.“An End to Indifference:America’s Korean Policy during World War II”,pp.182,195~196; 刘晓原:《东亚冷战的序幕:中美战时外交中的朝鲜问题》,第71、78页。。9月底10月初,美国占领南部朝鲜还不到一个月,驻朝鲜政治顾问梅里尔·本宁霍夫便向国务卿汇报说,苏联正在北方组建一党制政府,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共产主义,目的是全力促使朝鲜走向共产化。用不了多久,南部就会出现大批共产党追随者*FRUS,1945,Vol.6,The British Commonwealth,the Far East,pp.1061~1066.。及至1946年年中,杜鲁门总统已明确接受国务院提出的将朝鲜半岛视为美苏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的看法:“美国对亚洲政策能否得到全面落实可能取决于(朝鲜这个)意识形态战场”。苏式民主的主要标志是大众福利,美式民主的主要标志是言论自由。在朝鲜,美国一定要以民主竞争机制击败日益强大的共产主义制度*FRUS,1946,Vol.8,The Far East,pp.706~707,713~71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苏联之所以接受对朝鲜实施国际托管的建议,是因为苏联希望通过这一制度参与战后朝鲜事务,将朝鲜变成苏联的安全缓冲带,并以在朝鲜托管问题上的合作从美国那里换取更多的政治利益*董洁:《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54~655、679~680页。。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在朝鲜独立问题上,虽然美苏两国赞同的是同一种方式,但希望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局。这一切似乎预示着国际托管方案最终难免夭折。
二、 防苏反苏:从占领南部朝鲜到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的召开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很快在朝鲜半岛北部登陆并迅速向南推进。为了防止苏联占领整个朝鲜,10日晚美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时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等人提议把半岛中部的三十八度线作为美苏军队对日作战和受降的分界线。虽然美国决策者提出了这一建议,但他们认为苏联很可能会讨价还价,谋求将分界线南移。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竟然接受了美方的主张*FRUS,1945,Vol.6,The British Commonwealth,the Far East,p.1039.。9月8日,美国陆军中将约翰·霍奇率领第八集团军第二十四军在仁川和釜山登陆。
与半岛外部美苏两国领导人彼此间日渐猜疑相呼应,朝鲜内部左右翼之间也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展开了较量。9月6日,中左派政治领导人吕运亨组织成立朝鲜人民共和国,并很快颁布了施政纲领:废除日殖时期的法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无偿向农民分配日本殖民者和亲日分子的土地并将他们的其他财产收归国有等*余伟民、周娜:《1945-1948年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政治变动》,载《史林》2003年第4期,第106页;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2页;Hakjoon Kim.Korea’s Relations with Her Neighbors in a Changing World.New Jersey:Hollym Press,1993,p.163.。这一切立即引起了右翼的警觉甚至敌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信仰基督教的地主和富商,曾有过亲日行为,因而担心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会危及自身的财产安全和政治地位*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第23~24页;Donald Stone Macdonald.U.S.-Korean Relations from Liberation to Self-Reliance:The Twenty-Year Record.Oxford:Westview Press,1992,p.143; “Analysis of Current Political Economic,and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U.S.and Soviet Zones”,March 18,1948,i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CK3100250486.。得知美国即将占领朝鲜,右翼势力十分振奋,很快便公开拒绝与吕运亨合作,甚至大肆叫嚷着要推翻朝鲜人民共和国*Hyesook Lee.“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 Society under American Occupation:The Case of South Korea”,Korea Journal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1997,26(2),p.21; Hakjoon Kim.Korea’s Relations with Her Neighbors in a Changing World,p.164.。
美国人并没有让朝鲜右翼失望,占领军总司令霍奇等人迅速开始认真考虑遏制北方苏联和南方“颠覆者”问题*Bruce Cumings.“Introduction:The Course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1943-1953”,in Bruce Cumings(eds.).Child of Conflict:The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hip,1943-1953.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3,p.15.。美国军政府对朝鲜政局的基本判断如下:朝鲜人民的革命要求非常有害,代表这种革命要求的激进派(或共产党)一贯无视法律法规,时常采用恐怖和压制手段,是苏联的傀儡和维护当地秩序的首要障碍*Chan-pyo Park.“The American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the Framework for Democracy in South Korea,” in Bonnie B.C.Oh(eds.).Korea under the American Military Government,1945-1948,pp.125~126; FRUS,1945,Vol.6,The British Commonwealth,the Far East,pp.1070,1106,1144~1146.;右翼保守势力是朝鲜主流思想的代表,愿意与美国军政府合作,持有反苏观念,与他们结盟有利于维持社会现状,建立反苏堡垒*Adrian Buzo.The Making of Modern Korea.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2,p.58; Bong-jin Kim.“Paramilitary Politics under the USAMGIK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Korea Journal,2003,43(2),pp.291~292; FRUS,1945,Vol.6,The British Commonwealth,the Far East,p.1050.;苏联人竭力在北部朝鲜宣传共产主义,推动当地共产化,甚至屡次提及同美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FRUS,1945,Vol.6,The British Commonwealth,the Far East,pp.1065~1066,1147.。基于以上认识,霍奇等人着力在南部朝鲜推行“扶右抑左”的政策。
1945年12月16-26日,美苏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朝鲜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经协商,三方最终签署了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协定”确定了苏、美、中、英四周联合托管的框架。
“莫斯科协定”公布之初,热切盼望独立自主的朝鲜人民异常愤怒,南部朝鲜左右翼一道起而反对国际托管。1946年1月1日,朝鲜共产党领导人朴宪永访问平壤归来,旋即公开表示支持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决定。此后,左右翼互相指责对方是“卖国奴”和“反动势力”*赵虎吉:《揭开韩国神秘的面纱——现代化与权威主义:韩国现代政治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5页;FRUS,1945,Vol.6,The British Commonwealth,the Far East,p.1154; FRUS,1946,Vol.8,The Far East,pp.615~616.。没过多久,在以李承晚和朝鲜民主党为代表的右翼分子的煽动下,“反托管”变成了反苏反共的代名词。如此一来,围绕国际托管问题,战后南部朝鲜的政治力量格局第一次出现明显的两极化趋势*Myung-lim Park.“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Cold War in Korea:Entangling the Domestic Politics with Global Cold War in 1946”,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2001,2(December),pp.322~323,326.。
1946年3月20日,协商朝鲜托管问题的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正式召开。不久,双方就在究竟哪些朝鲜政治组织有资格参与协商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苏方主张协商对象严格限于“莫斯科协定”支持者。美方则认为,不能剥夺朝鲜人民的言论自由,一切政治团体皆可参与协商。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执,为了打破僵局,苏联做出让步:同意联合委员会可以与所有政党和组织协商,其中包括曾反对“莫斯科协定”者,条件是它们的领导机构在报纸上公开声明支持“莫斯科协定”。然而,两国的分歧并未就此消除:苏联代表团坚持认为,各政党和组织应派“未因积极反对莫斯科决议和盟国而名声不好的党员或组织成员”参与协商。美国代表团拒绝接受该立场,理由是这样做无异于党派清洗,有违政治活动民主化原则。5月6日,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FRUS,1946,Vol.8,The Far East,pp.657,659,661~662,665~667,749.。
与此同时,美国驻朝军政府不断加强打压左翼的力度*FRUS,1946,Vol.8,The Far East,pp.649,658,662~663,705; 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第35~36页。。面对占领者咄咄逼人的攻势,朝鲜共产党决定放弃以往不与霍奇发生正面冲突的温和路线,转而领导广大民众举行罢工甚至发动武装起义*Bong-jin Kim.“Paramilitary Politics under the USAMGIK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p.302.。表面看来,左翼反对的是美国军政府;实际上,由于美国军政府的军警力量主要由极右分子组成,镇压罢工和武装起义的恰恰就是这些人,因此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左翼领导的民众与隶属军政府的右翼分子之间的较量,标志着左右翼之间的斗争形式由互相指斥升级为武装冲突*FRUS,1946,Vol.8,The Far East,p.774.。
1947年5月21日,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第二次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召开*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16,Part2,number405-417,April-June,1947,pp.716~717,812~813,947,995~996.。6月7日,联合委员会第一分委会决定,凡签署声明支持“莫斯科协定”并承诺与联合委员会合作的政党和组织均有资格成为协商对象*FRUS,1947,Vol.6,The Far East,pp.668~671,673~674.。但问题并未因此获得解决。在27日的会议上,苏方拒绝允许作为反托管委员会*1947年1月21日,赵素昂、金俊渊和梁又正等九人在金九寓所组建反托管独立斗争委员会,共有35个右翼政党和社会团体加入其中。详见董洁:《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第677页。成员的约35个右翼政党和组织参与协商。美方认为,同意苏联的立场意味着大多数右翼将拒绝与联合委员会合作,结局必然是仅与左翼协商,这正是苏联希望看到的。美国的观点是反托管委员会成员的身份与坚决反对托管绝非同一概念,不能以此作为拒不给予协商资格的理由。7月上旬,联合委员会会议再度走向死胡同*FRUS,1947,Vol.6,The Far East,pp.680~682,687~689,693~695,697~700,798.。
美苏联合委员会缘何始终未能达成协议?据美国人统计,朝鲜半岛右翼与左翼的比例是3∶2*FRUS,1947,Vol.6,The Far East,p.688.,只要尽可能地允许所有政党和组织参与协商,便基本上可以实现协助右翼主导未来朝鲜政坛、阻止苏联吞并朝鲜半岛的目标。唯是如此,美国才千方百计地要将反托管的右翼政党和组织纳入协商对象之列,而确保朝鲜人民言论自由只不过是这一做法的托词而已。相对美国而言,苏联的意图更为明显。1946年3月20日,在联合委员会会议开场白中,苏联代表团团长什特科夫宣称:“苏联热切盼望朝鲜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独立国家,并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目的是确保未来朝鲜不会成为攻击苏联的基地。”5月8日什特科夫在离开汉城之前再次强调:苏联之所以反对某些人参与协商,主要是因为作为朝鲜近邻的苏联希望在朝鲜建立一个“忠诚”的政府。当地右翼诽谤苏联,如果他们组成未来的政府,必将组织人民对苏联发起敌对行动*William Stueck.Rethinking the Korean War:A New Diplomatic and Strategic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pp.34~36; Hyun Woong Hoog.“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Korea,1945-1950”,PhD. dissertation,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2007,p.163; FRUS,1946,Vol.8,The Far East,p.653.。也就是说,苏联排斥右翼的根本动因并非是他们反对“莫斯科协定”,而是担心这些人将来占据朝鲜政治舞台,使朝鲜成为美国的反苏根据地。既然美苏两国的政策设想完全相左且均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组建临时朝鲜民主政府事宜,双方难以在协商对象问题上实现妥协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 南北分立:必然的结局
1947年8月4日,美国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制定了第176/30号文件。文件认为,美国此时不能撤出朝鲜,否则共产党势必统治整个半岛。共产党在朝鲜进行的政治压制会严重损害美国在远东乃至全球的信誉,使依赖美国抵制共产党压力的小国失望。同时,美国又必须在尽可能阻止苏联统治朝鲜的前提下努力消除或减少在朝鲜的人力与财力投入。因此,美国将考虑放弃双边讨论,把朝鲜问题交由美苏英中四国联合解决。若四国依旧不能就此达成协议,则应求助联合国。假使联合国方案失败,单独赋予南部朝鲜独立地位也是政策选择之一*FRUS,1947,Vol.6,The Far East,pp.738~741.。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对朝鲜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单独建立南部朝鲜分立政府的可能性。
依据上述文件,8月26日美国代理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致函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声称联合委员会会议的僵持状态充分表明美苏双边协商已无法取得进展,建议将朝鲜问题提交美苏英中四国会议讨论。9月4日,莫洛托夫复函表示:联合委员会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且“莫斯科协定”也没有规定要由四国共同讨论朝鲜问题,因此苏联拒绝接受美国的建议*FRUS,1947,Vol.6,The Far East,pp.771~774,779~781; James I.Matray.The Reluctant Crusad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Kore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pp.122~123; F.C.琼斯、休·博顿、B.R.皮尔恩:《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1942-1946年的远东》,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701~702页。。17日,洛维特在回信中断言联合委员会已不可能在组建临时朝鲜民主政府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而苏联又拒不参加四国会议,华盛顿只得将朝鲜独立问题提交联合国裁定*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17,Part1,number418~430,July-September,1947,p.624.。
9月17日,美国向第二届联合国大会提出朝鲜独立问题。11月14日,联大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主要内容包括:决定设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职责为监督朝鲜议会选举;建议朝鲜在1948年3月31日前举行议会选举。选举完成后,尽早召开国民议会,组建全国政府;由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与朝鲜政府协商组建安全部队及美苏两国撤出占领军等相关事宜。然而,由于朝鲜人民普遍反对联大决议、苏联认定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为“非法组织”和北朝鲜人民委员会拒绝允许联合国人员入境,临时委员会不得不派分管托管问题的副秘书长胡世泽回纽约请示。联合国召开“小型联大”会议讨论此事。2月26日,根据美国的提议“小型联大”通过了关于在南部朝鲜单独举行选举的决议*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17,Part2,number431~443,October-December,1947,pp.867~868; 彼得·卡尔沃克雷西、希拉·哈登:《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418~422页;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第66~67页。。
“小型联大”决议通过后,未经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开会商讨,美国军政府就自行宣布在5月9日举行选举,后又改为5月10日。选举准备及实施过程中,右翼警察和准军事青年组织的舞弊行为随处可见,相当多的朝鲜人被迫参与了此次不得人心的选举*James I.Matray.The Reluctant Crusad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Korea,1941-1950,p.148.。但美国依旧对整个选举表示称赞*FRUS,1948,Vol.6,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1195.。不但如此,华盛顿还试图劝说各相关国家认可南部朝鲜的选举结果,承认即将建立的南部朝鲜政府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FRUS,1948,Vol.6,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p.1235~1237.。长时间犹豫迟疑后,7月22日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公布监督报告。报告认为:南部朝鲜选举的准备过程中和选举当天存在相当程度的自由气氛,人民享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权利;驻朝美军和朝鲜临时政府对选举活动的安排与委员会选举程序建议一致,符合选举法要求;考虑到朝鲜人民的政治文化传统及以往经历,选举结果可以被认为是南部朝鲜人民自由意志的有效表达*FRUS,1948,Vol.6,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p.1260~1261.。虽然报告的内容不完全符合事实,措辞又隐含勉强的成分,但美国毕竟初步实现了推动联合国承认南部朝鲜选举的目的。在部分美国官员看来,此举的意义在于通过联合国对韩国的政治和道义支持,将韩国的生存和发展与联合国的信誉联系在一起,借此对“一直企图统治南部朝鲜”的苏联构成“政治威慑”,使美国可以更加安全地撤出朝鲜。
7月28日,第一届南朝鲜国会以间接选举的方式推举李承晚为大韩民国总统。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成立,美国终于在南部朝鲜建立起了一个由右翼势力掌控的反共堡垒,朝鲜半岛走向分裂。
1944-1948年美国对朝鲜政策大体历经了提出“国际托管”设想、实施“莫斯科协定”、通过联合国推动南部朝鲜单独建国等几个阶段。对于这段历史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说最晚到1946年中,美国政府高层已开始从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视角看待朝鲜问题,那么这种政策思想的渊源则是国务院1944年提出的对苏联朝鲜战略的认识框架。考虑到在二战后期苏联似乎更多地只是从传统大国之争出发应对美国托管朝鲜的提议,1944年美国国务院有关美苏在朝鲜半岛体制之争的认知模式与政策建议可以被视为朝鲜半岛冷战对抗格局形成的萌芽;朝鲜战争爆发前,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倾向于由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入手看待朝鲜在东西方冷战中的价值,而军方则更多地从全面战争爆发的角度考虑驻朝美军、朝鲜军事基地以及整个朝鲜半岛在美国全球军事战略中的功用。结果,二者分别将朝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界定为趋于无限高和无限低两个极端*FRUS,1947,Vol.6,The Far East,pp.817~818; 梁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1945-198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5~129页。。换句话说,1946-1950年间在美国政府眼中朝鲜半岛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为展现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橱窗;冷战在朝鲜半岛的兴起既是美苏关系由战时合作向战后敌对转变的产物,又是朝鲜当地左右翼相互斗争的结局。早在日殖时期,围绕“反日”和“亲日”问题,朝鲜人就已分化为极端对立的两派势力——由左翼构成的“反日派”和以右翼为主体的“亲日派”。光复后,根据彼此间的意识形态分野,朝鲜左右两翼力量各自找到了苏联和美国作为外部靠山。结果,一方面,左右翼在“国际托管”、南北朝鲜建立分立政府、国家统一方式等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当地政治格局进一步分极化;另一方面,美苏两国不断指责对方操纵当地政治盟友进行反对自己的宣传和敌对活动,难以就实施“莫斯科协定”的具体细则达成妥协。最终,朝鲜半岛冷战爆发。
这一阶段的朝鲜半岛内外部关系还告诉我们:冷战起源问题研究不应仅仅关注宏观的全球层面,还应留意中观的地区层面和微观的国别层面。换句话说,虽然冷战史学界一般认为全球冷战开启于1947年,但各地区、各国家冷战起始的时间却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二战末期;冷战之所以爆发,主要是由于东西方之间存在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不能将冷战发生的责任仅仅归咎于美国或苏联一方,而应将其视为美苏双方相互防范和敌视的结果,此过程有时还掺杂着当地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内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