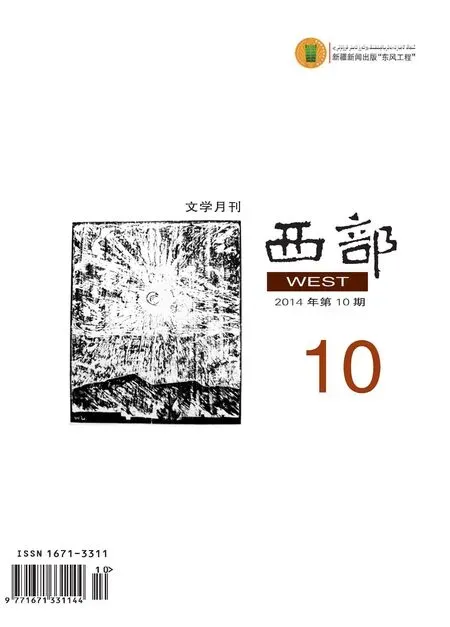德国琐记
黄梵
作家漫游
施益坚还在台湾就提出,六月初我一到哥廷根,他就从马堡来看我。他的“看”显得有些隆重,他当天往返一趟,路途需五个多小时,只为了在哥廷根尽四小时的地主之谊——请我吃大餐,带我见识哥廷根的德国文化。据说他来前还做了功课,向他在哥廷根大学读过书的妹妹打听哪家咖啡好,哪家餐食有特色,哪里有博物馆……
我去车站月台接他时,只见他一身学生打扮,T恤加牛仔裤,肩上斜挎着一只棕色方包。待两人感慨地拍完背,并不觉得已有两年未见,仿佛两年前就在昨天,一见面就续上了昨天的话题。两年前他从台湾来南京,见面就抱怨南京比台湾干燥,逼得他用保湿霜。这次他抱怨的是德国,自嘲地说德国气候把他弄得像个女人,成天往脸上洒水抹霜,只为了给皮肤保湿。我睁大眼睛打量他,的确,那张英俊的脸有点油光发亮。作为男人,如此关心皮肤,说明他内心藏有很多的敏感,这颇符合他那本当红小说《边境节》呈现出的细腻之功。这类敏感同样也表现在他的调皮捣蛋上。哥廷根城虽小,红绿灯却不少。两人前往古城的路上,每每遇到红灯,哪怕马路上没有车,我也会本能地停下脚步。每当此时,他就快活地嘲笑我:“你怎么像个德国佬?没有车干吗不走?”他毅然领着我迈步闯过红灯,然后露出一脸轻松的坏笑,仿佛他早已是个中国佬。记得慕尼黑的汉学家樊克曾告诉我,德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东方的意大利人,同样重视美食和家庭,同样不愿遵守规则和法律……这里条规森严,他却宁愿按中国方式行事,令我想起巴尔扎克的看法:“在指定的时间里喝水、吃饭、睡觉”“我就算完了”,施益坚不愿在“指定的时间”过马路,说明作家们尊崇的东西都差不多,只愿尊崇肆意的想象和自由……
古城人头攒动。听说我还没有哥廷根地图,他立刻带我到处找游客中心,没多久,就发现它设在市政厅一楼。游客中心为什么不像台湾那样设在火车站?记得游魏玛时,我也发现游客中心同样是设在市中心。施益坚开始为德国辩护,说火车站有游客问讯处,只是游客中心还可以提供租车等服务。我有点不依不饶:“游客要先走到市中心,然后才能租到车?”我顺势调侃起德国的火车,说不敢想象德国火车经常迟到、变更停靠的站台、取消车次、同一车次每天发车时间都不一样,令初来乍到者不知所措。没想到他听罢居然更加开心:“你对德国人的想象有误,既然是人,就不可能像机器那样精确,但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你们的火车很准时,每天发车时间都一样,除非你们……”接下来的路上,两人就这样不停靠“抬杠”寻开心。
大概决意要帮我找到德国文化,他手执哥廷根地图,领我穿街走巷,结果与城市博物馆不期而遇。见门头上刻着勃拉姆斯的名字,我兴致陡增。我和女儿都是勃拉姆斯迷,曾有数年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听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施益坚马上用德语帮我一探究竟,原来墙上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勃拉姆斯曾在这间楼里演奏过。我踩着博物馆的木地板,它像老人的关节发出响声,这声音真的令我内心滋生出历史感。二楼摆放着不少十九世纪的钢琴,述说着那段辉煌——哥廷根曾是德国的钢琴制造中心。墙上早已褪色的绘画都与中国有关,描绘了德国人曾对中国的想象,那是十八世纪中国风黄金时代的遗物。这种风潮的遗物,我后来在法兰克福和慕尼黑都见识过。法兰克福的歌德故居有一尊取暖器,不是典型的德国铁铸样式,它的表面覆盖着一层中国青花瓷。那时的德国人拥有青花瓷,如同魏晋时期的中国人拥有罗马琉璃杯一样,都象征着财富和品位。慕尼黑的汉学家樊克甚至把慕尼黑的中国塔视为一种历史担保,只要看过中国塔,担保你就了解了慕尼黑作为封地时的历史。
两人无意间逛进了一家建于1735年的书店,没想到老板竟是施益坚的粉丝,书架上赫然摆着施益坚的两本书,其中一本还标着“最佳畅销书”的字样。老板对施益坚表示恭敬的方式,几乎与中国人一样,双手合十,向施益坚微微鞠躬。施益坚生怕冷落了我,竭力向老板介绍我的情况,我听不懂,但知道这样做没有意义,毕竟我只有几个短篇译成了德文。离开时,我记住了老板的笑,他的笑在德国人脸上很少见,是一种恭敬谦和的笑。刚出书店,施益坚又把我随口的抱怨当了真,我抱怨德国书店跟中国书店一样,少有英文书,他马上又显出愚公移山的劲头,决意要带我逛遍哥廷根的书店。虽然最终找到的几本英文书不值一提,却让我见识了哥廷根书店的数量,以全城三万学生来衡量,书店已经算很多,光很像样的书店就有十来家,且家家有施益坚的小说。一个书店能卖这种严肃小说,其趣味还能不专精吗?
接下来两人在哥廷根的吃喝几乎没有变数,一切如他所愿,吃完大餐,两人手执冰淇淋,顺利找到了他妹妹推荐的一家咖啡馆。去那里喝咖啡的人以中老年妇女居多。按照施益坚的解释,德国中老年妇女多有闲暇,与友人喝咖啡消磨时光,成了她们唯一的乐趣。如同中国中老年妇女,乐此不疲地跳广场舞一样。
我那天还有一种“恶毒”的心理,希望能在哥廷根找到一幢丑陋的房子,如同我在中国可以找到大量丑陋的房子一样,但是没有成功。不仅哥廷根找不到,魏玛找不到,后来在汉堡、法兰克福、科隆、慕尼黑等地也找不到。顾彬的朋友海娆是法兰克福的作家,嫁给了一个德国人,她的德国丈夫认为法兰克福是德国最丑陋的城市,因为它有大量的现代建筑。可是以我的眼光,那些现代建筑根本算不上丑陋,相反,它们显得既时尚又漂亮,与传统建筑相处融洽。
施益坚尽地主之谊的那天,令我有了一种新的嗜好,即任何德国的事物,我都要从正反两面嚼一嚼,不大信任已有的结论。送走施益坚的第二天,我就怀着这样的矛盾心态,开始了在德国境内的漫游……
简-玛利亚夫妇
慕尼黑的汉学家樊克陪我北上柏林,火车路过克罗纳赫小城时,上来了他朝思暮想的女友戴安娜。她没忘樊克最喜欢吃牛角面包,给樊克和我各捎了一只。更没想到,为了我能在两天内游完柏林,她煞费苦心,精心规划了我的游览路线。到柏林已是傍晚,她替我预订的旅店离柏林火车总站不远,刚把我安顿下来,她的柏林好友简-玛利亚就开车寻踪而来。简-玛利亚是法国人,个头不高,见我们三人在捣鼓我的电脑,为无法上网着急,他自告奋勇来帮忙。望着满屏汉字,他完全像个巫师,通过猜测汉字的意思告诉我该如何操作。他差点成功了,电脑顺利连上了无线网络,只因信号太弱,最终只好放弃。
简-玛利亚开车像所有德国人一样,疾驰如飞,拐弯、倒车等动作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他替戴安娜挑选了一家地中海餐厅,请我吃饭。邻桌是四个俄国年轻女郎,彼此用俄语说说笑笑。简-玛利亚朝邻桌瞥了一眼,告诉我柏林有个不小的俄国街区。一开始,为了迁就我,我们这桌都用英语交谈。几口德国啤酒下肚,简·玛利亚就变回法国人,英语在他激情澎湃的演说中变成了法语。好在戴安娜是法语教师,我和樊克尚能通过她零星的翻译,得知一鳞半爪的内容。简-玛利亚是品酒师和酒商,曾来上海呆过一个月。不知为什么,他的个头、手势、神情和澎湃的精力,令我想起一部旧电影中的拿破仑。我端详着眼前的“拿破仑”,觉得他的每颗牙齿都在说话。
第三天早晨,他邀请我去他家共进早餐。去他家的路上,戴安娜说他的房子是抢占来的,这陡然激起我的兴致。原来柏林墙倒塌前,柏林尚有许多没人住的空房,简-玛利亚当时和许多穷困的年轻人一样,与另一家共同“瓜分”了一套公寓。即使只有半套,也大大超出我的想象,连卫生间一共有七间。早餐安排在宽大的阳台上,五个人吃喝说笑间,我渐渐看出了端倪:这幢公寓原本没有阳台。这宽大的钢结构阳台,其实是各家共同出钱建造的。餐毕,简-玛利亚和妻子领着我们上上下下一探究竟。一楼有间门房,被布置成楼内居民议事的会议室,楼前空地被建成花园和幼儿园的露天游乐场,通向大街的露天走道一侧,盖了三间存放自行车和用具的板房,楼顶阁楼被改造成桑拿房和健身房,楼顶平台经过精心装饰,摇身一变,成了能远眺城市的露天咖啡吧……这些很棒的主意当然都诞生于那间门房,一旦谈妥,各家就爽快地出资兴建。我很诧异,这些普通的德国市民会有如此完备的公共意识和自治精神。这事要是搁在南京,一说要出钱,估计各家就没兴致了,大家都指盼着别人出钱。记得五年前,我家楼下车棚塌了,有人动念想成立业主委员会,好用维修基金来修车棚,可是至今业主委员会都没成立起来,数百万元的维修基金一直闲置在政府账号上,原因很简单,大家达不成共识。说实话,走在他们“抢占”来的公寓楼梯上,我一时感到脸红,他们不仅在水泥台阶上钉上防滑金属条,还铺上一层防滑地毯。我和我的邻居们对自己花钱买的水泥楼道,从未有过如此深厚的爱心……这爱心还体现在公寓的墙面上,他们特意请来愿意涂鸦的画家,在公寓立面画上巨幅人物肖像,在通道墙面绘上花卉和动物。这对夫妇在介绍绘画和画家情况时的那种深情和自豪,差点令我动容。简-玛利亚指着墙上一只数厘米大的蚕虫说,你瞧,画得多好,多好的画家啊!他们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有绘画的角落,仿佛正领着我参观卢浮宫……

魏玛市政厅及广场花市 黄梵摄
路过他家冰箱时,我对冰箱门上用来压纸条的小钢柱产生了兴趣。它们只有半厘米高,吸力却超强,不使大劲别想拔下来。想到我给母亲留纸条的冰箱吸铁石,吸力孱弱,纸条常被风刮落,我连忙打听哪儿有卖。他妻子提醒我,今天是周日,所有商店关门,但她马上提议,改日由她购买,寄往我在哥廷根的地址。就在我准备给她留地址时,她突然眼睛一亮,问我需要多少。“十个就够了。”我话音刚落,她如阿基米德找到答案一般,转身就跑,不一会就找来十二个,塞进了我手心。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她把冰箱门上的小钢珠都拔下来给了我。任凭我怎么想付钱,她都不答应,那情景颇似三十年前乡下亲戚给我家送青菜,打死不肯收钱。
参观完他们“抢占”的房子,简-玛利亚夫妇与戴安娜、樊克站在衣帽间,开始商讨如何让我在离开柏林前的四小时尽可能游览更多有趣的地方。他们一丝不苟讨论的劲头,完全不亚于一场商业谈判。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什么是德国精神。不管事情大小,一视同仁,全力以赴,这大概就是德国精神的威力所在。经过二十分钟的“商业谈判”,大家最终同意了简-玛利亚的方案。他换了一辆能坐七人的商务车,驱车带我参观同性恋市场、柏林墙、卡尔·马克思大街等。他觉得我会对卡尔·马克思大街感兴趣,说那条街以前叫列宁大街,德国统一后换回成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大街真的很像中国一些大街的景观,笔直,宽敞,两侧全是包豪斯式样的公寓大楼。车行至某处,我会产生置身于南京或北京的幻觉。我想他朴素的目的已经达到,他希望我看到一个混搭的柏林,文化多元的柏林,不只是看过很德国的哥廷根、慕尼黑、魏玛等。其实简-玛利亚的家,就是法国和德国的混搭,他的妻子是德国人,连他们早餐烤的面包也混合了法国面包的硬和德国面包的黑。甚至简-玛利亚名字本身,也混搭着女性气息。我曾不止一次开玩笑,直接称呼他“玛利亚”,引得大家会心地大笑……
与他们精心的安排相比,告别显得有点简短、草率,我依旧说着那些套话:“非常感谢”、“再见”、“欢迎来南京”等等。我知道这些话都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我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来看看这对夫妇“抢占”的半套公寓,再来享受我叫他玛利亚时他那无地自容的脸红,再来分享他家面包里的法国硬和德国黑……
生活的轻与重
我从法兰克福车站登车去慕尼黑前,着实虚惊了一场。前一天晚上,作家海娆开着外形浪漫的跑车,带我到美茵河一带兜风。路上为了真正“兜到风”,她降下了车篷,一边开一边问我速度够不够快?她说由于这边高速公路没有限速,常有国内的飙车族来这里飙车。兜完风,她带我去美茵河边一家小镇咖啡吧闲坐,满目是驱车来闲坐的德国人。美茵河只有长江的夹江那么宽,却不时有游船驶过,游船的大小和模样,令我想起小时常在江边看到的那些渡轮。离咖啡吧五米远的河边,就有一处停靠小船的木码头。那晚,倒没有小船往来停靠,但见一群肥硕的野鸭一直霸占着码头,搔首弄姿。这样的野趣我已有三十年没见,不敢相信会出现在工业化的德国城郊。
闲坐近尾声,远处天空响起了一声闷雷,雷声刚落,海娆就惊慌起来,说要下雨了,赶快走。按照过去的天气经验,我觉得海娆的反应有些过激,天并没有下雨,到处和风习习。当我跟她回到跑车上,只见她没了来时的轻松,神色异常紧张,加足马力往市中心狂奔。车行不到二十分钟,果真下起了雨,雨大得有点离谱,每滴雨砸在挡风玻璃上足有土豆那么大。我开玩笑说,德国的雨也像德国人一样,比中国的壮硕。海娆瞥着挡风玻璃,疑惑地问我会不会是冰雹?没看见满地乱蹦着白球,我肯定地说不是冰雹,不过是壮硕的德国大雨而已……
翌日清晨,我在法兰克福车站到处找那趟去慕尼黑的火车时,海娆打来了电话,话筒里传来的消息令我震惊。昨晚,当她把我送回旅馆,继续驱车往家里赶,因雨太大迷了路,折腾到深夜才到家。接着她纠正我说,昨晚下的真是冰雹,这场冰雹覆盖了德国好几座城市,还砸死了好几人。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一听到雷声她就惊慌,她着实了解德国天神的坏脾气!正是昨晚那场冰雹,让我再也找不到那趟火车了。冰雹砸断了许多输电线,令许多车次停开。绝望之余,我加入了问讯处前面的冗长队伍,打听还有没有火车去慕尼黑。算我走运,半小时后就有一趟,我连忙给将去车站接我的樊克发短信。大概总担心他接不到我(这是在不识德国字的环境里常有的心态),我反复给他发短信,他便调侃我,叫我放心,说一定会到车站把我给捡走的……
我与樊克已有五年没见。见到他时,才知道他没有给我预定旅店,执意要我去他那里住。他住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小区,房东家只有一人,是个聋老太,但她能读懂樊克的唇语。只是樊克与她说话时,得将脸正对着她,同时要减慢语速。她当然读不懂我的唇语,但我喜欢她背微驼时的慈祥笑容,令我想起已经故去的奶奶。樊克说完冰雹的事,也说我走运,恰好他最近不忙,可以领着我到处闲逛。白天看完慕尼黑的老街、英国花园、中国茶塔、城堡、青少年在伊萨河小溪里的冲浪等,晚上我跟他去了一家有名的酒吧“B先生的”——他的朋友吉奥黑姆夫妇邀请我一起去听爵士乐。此B先生是来自美国的黑人爵士乐手,他白天有一份正式工作,晚上则经营自己的小酒吧。酒吧不大,可以坐三四十人,常有乐队来演出。我十分诧异,整个酒吧只有他一人,他既是老板、调酒师、收银员,又是服务生、洗碗工、清洁工,件件事情做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脸上永远挂着微笑,令我感慨德国环境里的效率之高。在国内,常见类似的小酒吧,至少需要三人打理。
两人刚刚坐定,吉奥黑姆夫妇就探头进了酒吧。吉奥黑姆个头很高,和我一说英语就有点结巴,但和老婆、樊克说德语就十分顺畅,我猜测他是对自己的英文没有把握。他读过我小说的德译文本,所以一直问我还有什么作品译成了德语。海阔天空闲聊了一会儿,我对他们的生活渐渐产生了兴趣。吉奥黑姆夫妇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有精神疾患,都正在上学,但夫妻俩常晚上或假日撇开孩子,外出听音乐,与朋友聚会,参加各种活动。我把话题聚焦在他们与孩子的关系上,问他们把孩子丢在家里放心吗?这本是困扰中国父母的问题,一般有了孩子,中国夫妻就很少单独外出找寻浪漫的情调。没想到他们夫妻各给了我一个答案。妻子说,孩子哪怕有疾患,也需要独立成长的空间,不独立孩子不会成人。吉奥黑姆说,如果夫妻一直只和孩子们纠缠在一起,一旦孩子大了,夫妻就很难适应两人世界,如果没有两人世界,婚姻的意义又在哪里?婚姻只是为了繁衍?一说到繁衍,我立刻想到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话题:中国不少家庭已经出现了无性生活,原因不外乎是,太忙、太累,令人打不起精神、提不起兴致。我问他们如何看待?他们说,德国也有个别家庭有此问题,但原因不是太忙、太累,多是丈夫酗酒,彻夜不归造成。他们不敢相信一对正常的夫妻,会坦然接受无性生活,如同有了孩子,就不再经营夫妻感情。此话不假。我在德国境内漫游时,满目皆是德国夫妻经营感情的证据。也许年轻男女当众接吻,在中国也不算稀罕。可德国中老年夫妻的表现,一点不逊色于年轻人,满目皆是表达感情的举动:除了接吻,不忘抚一抚对方的背,牵着对方的手,不时搂抱一下。如果是夫妻重逢,他们在车站或机场的搂抱,简直感人至深……一次我坐火车去法兰克福,身边一对已入耄耋之年的夫妻,平均每半小时就彼此吻一下,吻完会朝我微微一笑,仿佛是感谢我理解他们情深意笃的举动。有人可能会说,中国人的所有情感表达,都不会放到马路上,只会在家里完成。但依我所见,只要过了热恋期,尤其有了孩子,中国夫妻在家里几乎不再有性以外的情感表达举动。若说中国人重视家庭,我看主要集中在重视孩子身上,夫妻感情倒成了家庭中并不重要的部分。吉奥黑姆告诉我,他妻子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代表着德国人的共识:正是这些零零碎碎的情感表达,让夫妻关系能超越血亲,不同于与其他所有人的关系,由于性的表达无法像这些情感举动一样频繁、及时,所以,它们是维系夫妻关系的重要手段……
B先生的酒吧演出中间常插入一刻钟的休息,我们就不时走出燠热的酒吧,把话题搬到门外街边。我打量着满街酒吧门前诸多的中年夫妻,蓦地有所醒悟:中国夫妻一旦有了孩子,两人不再单独外出,恰恰与他们没有养成情感表达习惯有关。这种不表达的“冷漠”习惯,渐渐异化了他们的关系,使他们不在乎有没有两人世界,甚至有没有性生活……他们能忍受的婚姻其实质量很低,任何事都能堂而皇之地挤占两人世界,孩子、父母、工作、挣外快等……仿佛夫妻情感只有为这一切让路,夫妻才能最终获得幸福。这么奇怪的悖论,当然经不起德国人的理性分析,但可以被中国人非理性地接受……
那天晚上,我、樊克和他们分手时,吉奥黑姆说了一句祝愿:希望中国的夫妻能更亲密。他说时用的是英语,表达得结结巴巴,不经意成了中国夫妻情感表达不顺畅的一个象征。我至今记得他表达时的挣扎神情,与其说那是祝愿,不如说是对中国情感的真切描绘——是啊,中国夫妻什么时候能真正摆脱这种挣扎,其情感被孩子、工作、父母等彻底淹没的挣扎?
德国的“雷锋”
我拖着发虚的身子摇摇晃晃走进“依蝶”时,已经拉了三天肚子。“依蝶”是哥廷根唯一的中国餐馆,老板娘姓萧,来自台湾,在德国打拼了三十年。也许是对德国人过分讲究细节感触太深,言谈中她流露出不满,说她宁愿房子空着也不想出租,“那些德国人可讲究啦,一会儿马桶要修,一会儿洗衣机要修,一会儿吸尘器要修……反正会不停折腾你。”发完牢骚,老板娘才注意到我脸色不好,嘘寒问暖之下,我只好道出苦衷:骤冷的德国六月天令我猝不及防,寒气侵身,狂泻不止。老板娘立刻表现出对同胞的关爱,索性抛开墙上贴的菜单,直接问我想吃什么,可以让厨师单独做。我用双肘在柜台上支着微颤的身躯,开始与她一同畅想各种组合:豆腐面条、面条煮饭、汤煮米饭、炒饭和面、青菜稀饭……我几乎两天没进食,想到晚上歌德学院有一场我的作品朗读会和演讲,我觉得必须吃点清淡又有营养的中国餐。当老板娘冷不丁报出“小馄饨煮米饭”时,我本能地觉得就是它了!老板娘颇有“雷锋精神”,只收了我米饭钱。当我端着“营养餐”,一屁股坐在面对大街的橱窗前,桌上一沓传单映入了眼帘——上面印着我的头像、朗读会与演讲的时间地点等。面对我好奇的询问,老板娘不得已道出事情原委。原来哥廷根大学派出一些研究生,到哥廷根一些有特色的餐馆,为我演讲那天观众们也参加的酒会“化缘”,依蝶答应届时免费提供中餐,传单是学生委托依蝶散发的。当我感谢她慷慨支持活动时,她平静地告诉我,哥廷根的餐馆为文化活动提供免费餐食,是本地微不足道的常态,“我们不支持哥廷根的文化活动,谁来支持?……”不觉间,她的身份已由台湾人转回成哥廷根人,大有中国铁肩担德国道义的国际风范……
慢吞吞吃了半碗饭,身边坐下来一个中国人。我和他虽然都望着车水马龙的大街,但各想着各自的心事。突然,我注意到一辆小轿车停在了马路中央。通常德国人不会干这种缺德事,除非出了什么状况。果真是车上的电瓶没电了,司机沮丧地把车缓缓推到路边。与此同时,只见另一辆小轿车悄悄跟了过去,也停在路边。两个司机打招呼时,能看出他们不是熟人。热心帮忙的司机,把车挪到车头对车头的位置,然后找出导线,连接两辆车的电瓶开始充电。我忍不住掏出相机,拍下了那感人的一幕。我的举动令身边的中国人很诧异,他连忙朝外打量,可惜他漏掉了“故事”的前半截,左看右看没看出要领。充完电,两个司机各自开车上路,分别加入了不同的车流。没想到这类令我感慨的事,当天晚上也落到了我头上。朗读会和演讲结束时,已经过了十点,但去哥大访学的南大舒也教授意犹未尽,力邀我去老街喝咖啡闲聊。他相中的一家咖啡馆小巧玲珑,空间逼仄,一行四人围着很小的圆桌坐下。小店已经坐进二十多人,只有老板娘一人打理,忙碌程度可想而知。我手上一直捧着哥大师生献的一束鲜花,进了小店,只得把花搁到座位上。点的咖啡还没上齐,就见老板娘捧着一只装着水的玻璃容器来到身边。我以为她要给我们倒水,没想到她指着挤在座位里的鲜花说,你可以把它先放到这里面,这样花就不会枯萎……天啦,她这么忙碌居然还有一份闲心想到我的花!她小心把花放进容器,然后搁到圆桌上,但见花束太大,妨碍我们喝咖啡,又把花挪到柜台上,同时提醒我走时别忘了它。数年前,我在国内也有过捧着鲜花去咖啡馆的经历。记得那次是给南师大研究生作演讲,结束后同样是捧着鲜花和朋友去了半坡咖啡馆。花束比歌德学院送我的还要大,我们围坐的长桌几乎就靠着柜台,但自始至终,没见老板或店员为那束挤在椅子里“昏睡”的鲜花操过心……
近年我养成了一到陌生之地就浏览当地报纸的习惯。到了德国,我当然只能浏览中文报纸,但一样可以了解当地人的情态。反正浏览了一个月,从没见报纸提倡或号召过什么公益善举,但身边的“公益善举”却比比皆是。哥大有个叫阿林娜的研究生,繁重的学业之余,她不惜耗费时间和精力,组织德国学生制作咖啡和蛋糕出售,将赚来的钱捐给墨西哥印第安农民。我曾问过哥大一些中国学生,他们是否也参与这样的公益活动,但得到的回答几乎完全一样:学业太忙,没有时间参加。这样的回答会让人以为,德国学生都不务正业。其实阿林娜能流利地说九种语言(不包括正在学的汉语),作为跨文化专业的研究生,她跨文化的能力可以说强得邪乎。短短一个月,德国人“公益善举”的画面,在我脑海里越积越多……记得有天早晨,我和巴巴拉、崔丽娜闲坐在汉堡旅店门口,一个德国送货员骑车闪过时,一小瓶白兰地不慎落地,啪一声,酒和玻璃碎片散在三人脚下。就在我和崔丽娜不知所措时,巴巴拉已经起身安慰送货员,叫他只管走,她会来收拾地面。巴巴拉马上找来扫帚和簸箕,一边和我们说说笑笑,一边把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我没有忘掉自己的“记录员”身份(我习惯用相机拍下异地一切有助于回忆的东西),一边拿相机给巴巴拉拍照,一边用英语开玩笑:Barbara is working……巴巴拉的反应如此迅速,说明“公益善举”早已是德国人血液里的东西,根本用不着提倡。记得坎帕斯组织研究生举办我的朗读和交流会时,曾有个很小的举动也令我万分感慨。朗读和交流会开始前,有半小时的酒会,那天因肚子不好,我没有加入吃喝的人群,一人坐在隔壁教室等酒会结束。不时有德国和中国学生拿着酒和食物进来,陪我说说话。不知什么时候,坎帕斯也进来了,只见他蹲在地上用纸一点点擦拭地上的地砖。原来他发现地上有不知哪个学生泼出来的酒。那一小摊泼在地上的酒,我其实早已看见,只是没当回事。他擦地砖的认真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人擦自家的木地板。他起身离开时,我内心顿时涌出一丝羞愧。作为一个来自几乎天天提倡“学雷锋”国度的人,坎帕斯只用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证明了我们提倡的失败。是的,如果公益善举不能真正成为血液,那么任何所谓的提倡都只会沦为装饰门面的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