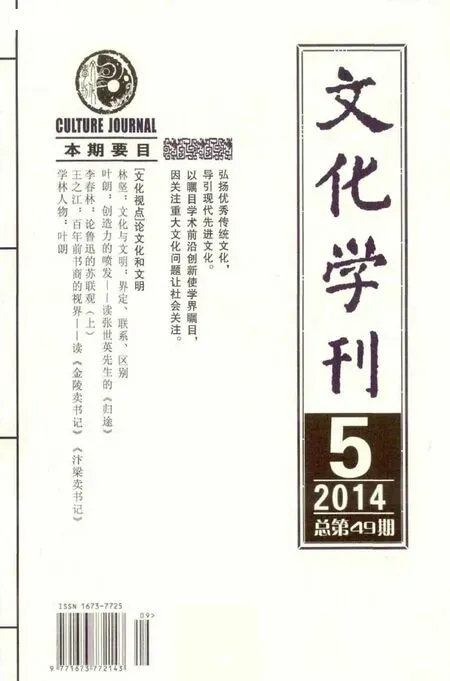文化语言学论纲
杨 琳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文化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是中国学者1985年正式提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兴起一股文化热,形形色色的学术论著都喜欢打着文化的旗号登台亮相,诸如“文化研究”“文化概论”“文化内涵”“文化阐释”“比较文化”“旅游文化”“民俗文化”之类的名目触目皆是,俨然是学术界百“化”齐放的春天。一向以人文科学带头学科自许的语言学面对“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而不为其他学科问津的局面,也树起了文化语言学的大旗,开始“寻寻觅觅”,主动向其他学科靠拢,成为一门出入百家又不失自己独立价值的边缘学科,但对文化语言学的内涵,学者们至今仍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文化语言学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学科,属于语言学的分支,因而将其名称理解为“文化/语言学”(cultural linguistics /linguistics from culture)。另一种意见认为,文化语言学是研究文化和语言之间关系的学科,既包括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也包括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化,是一种双向交叉学科,因而将其名称理解为“文化语言/学”(study of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culture)。从实际操作来看,在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的过程中,难以排除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在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化的过程中,难以排除对语言问题的探讨,两者常常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古代文献中常把刑具统称为“三木”,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这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但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历史上刑具的使用状况,而这又是一个文化问题,因此,将文化语言学的内涵确定为研究文化和语言相互关系的学科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而且这种界定也使该学科与其他学科联系更加密切,有更广阔的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目前国际学术发展的趋势表明,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是解决疑难问题和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途径。据对1976—2000年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统计,不同学科的交叉成果占47.37%,这充分显示了学科渗透、多角审视的研究价值。
文化语言学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就是“文化”和“语言”,对这两个概念也必须作出界定。中外学者对“文化”下的定义有上百种,可以归纳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所有精神产品,如思想意识、规章制度、风俗习惯等。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及物质产品的总和。文化语言学所说的文化指广义的文化,这是由语言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语言不仅反映精神文化,也反映物质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不可能局限于研究反映精神文化的语言现象,而将反映物质文化的语言现象置之不理。“语言”也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语言指口头语言及书面语言 (文字记载),更狭义的语言仅指口头语言。广义的语言不仅包括口头语言及书面语言,还包括具有表义功能的副语言,如肢体语言、各种图符等。文化语言学所说的语言是指广义的语言,但其中最主要的是狭义的语言。
除了文化语言学的概念外,还有民俗语言学 (folkloric linguistics)、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人类语言学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等概念,文化语言学跟这些概念是什么关系呢?民俗语言学以民俗语言和民俗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由于民俗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民俗语言学应该是文化语言学的一部分,文化语言学可以涵盖民俗语言学的内容。社会语言学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语言,侧重研究当代的语言现象。与社会语言学刚好相反,人类语言学主要关注没有文字的文明前社会的语言。文化语言学则既关注古代,也不割弃现代。所以就范围而言,文化语言学要比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广泛,文化语言学的概念可以统领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我们可以把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看成是文化语言学的两个研究方向。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信息载体,文化则是语言记载的对象,二者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互相依存,互相作用,密不可分。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 (L.R.Palmer)在《现代语言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1936)中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互相提供证据和解释。”[1]美国哲学家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指出:“脱离了它所植根于其中的传统习俗,语言便是不可能被理解的;脱离了界定它并且构成其组成部分的语言,传统习俗也同样不可理解。”[2]中国语言学家罗常培也说:“语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面联系的……所以,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要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3]可见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是中外学者的共识。事实表明,许多语言问题如果局限于语言学内部是无法解决的,需要结合文化现象来解析阐释。
拿语音来说,语音系统发生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我们知道远古时期语言的数量是很少的,目前语言谱系研究的结果是世界上有十几种语系,按照这一观点,后世的三四千种语言大都是由远古时期的十几种语言分化而成的。分化的主要原因则是社群部分成员的迁移疏远或中断了与原社群的联系,使得两个社群中出现的语言变化难以为对方所吸收,两个社群的语言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经过漫长的演变,便形成两种不同的语言。语言分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语音系统的改变。
就同一种语言而言,其语音系统演变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文化,在于人的心理和生理需求,而不在语言自身。法国功能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丁内 (Andre Martinet)提出语言运转的基本原理是“语言经济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他认为交际和表达的需要始终在发展变化,促使人们采用更多、更新、更复杂、更具有特定作用的语言单位,而人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惰性则要求在言语活动中尽可能减少力量的消耗,使用比较少的省力的或者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语言单位。这两方面的因素相互冲突的结果使语言处在经常发展的状态之中,并且总能在成功地完成交际功能的前提下,达到相对平衡和稳定。经济原则是支配人们言语活动的规律,它使人们能够在保证语言完成交际功能的前提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言语活动中力量的消耗作出合乎经济要求的安排。语言经济原则能对语言结构演变的特点和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4]例如,英语原本是综合型语言,有丰富的词形变化,如名词有主格、所有格、与格 (the dative case)、宾格四种格,这些格跟名词的数和性密切关联;形容词有主格、所有格、与格、宾格和工具格 (the instrumental case)五种格,要与被修饰的名词在数、性、格上保持一致。[5]但现代英语已经演变成为分析型语言,复杂的词形变化大都消失了。俄语现在虽然仍然是综合性语言,但也有向分析型靠拢的趋势,如某些名词在过去必须变格的场合现在可以不变。[6]推动综合型语言向分析型演变的动力不在语言内部,而在于语言使用者的省力需求。
汉语的雅言系统从中古到近代发生了音系的简化,其主要标志是全浊声母清化,声母的清浊对立消失;入声韵尾脱落,韵母阴阳入对立的格局变成阴阳两分;韵尾-m合并到-n。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简化?动力主要来自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对发音省力的追求。当人们感到把“今”(kǐem)读成“巾”(kǐen)而不影响交际时,就会忽略-m和-n的区别,把发音比较费力的-m发成-n,这样就造成了-m、-n的合并。汉语的轻声也是发音省力的结果。王福堂在谈到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时说:“汉语方言语音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出于发音上省力和方便的要求,引起发音动作的改变。”[7]语音变化最先发生在个别的常用词身上,然后通过类推机制逐渐扩散到其他词汇,最终造成语音系统的改变。
语言除了分化,也有融合的情况,融合的动力更是来自文化。一般情况下弱势文化的语言或方言向强势文化的语言或方言靠拢,最终采用强势文化的语言或方言作为共同的交际语言。如我国历史上北魏时期的鲜卑族、西夏时期的党项族、清代的满族等,都因汉族强势文化的影响而放弃自己的民族语言转用汉语。在汉语方言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词的读音老年人跟年轻人的读法不一样,老年人的读法是方言固有的读法,年轻人的读法则接近普通话,这是普通话对方言区的人们施加影响的结果。
语音演变的规律性是很强的,但有时也会出现个别例外,这些例外往往是文化原因造成的。例如,汉语中的“贞、祯、桢”等字《广韵》中读陟盈切,今天应该读zhēng,但事实上却读 zhēn,这是为了避宋仁宗赵祯的讳而造成的。
语音对文化也有影响,如民俗画及雕塑艺术中常有一只猴子爬在枫树上挂印的造型,寓“封侯挂印”之意;还有一只猴子骑在马背上的造型,寓“马上封侯”之意;[8]有小猴骑在大猴背上的造型,寓“辈辈封侯”之意。正月里塑造出三只羊的形象,表示“三阳开泰”。“三阳开泰”的说法来自《易经》的泰卦,泰卦的卦象是乾下坤上 (),表示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交合,万物通泰。传统易学中泰卦被认为是正月的象征。由于三阳在下,故以“三阳开泰”称颂一年的开始。阴阳之气是不好表现的,所以在绘画及雕塑中取谐音“羊”,用三只羊来表示三阳。其他如在婚俗中,新娘身上散麦麸,取富贵之意;新房中放上枣和花生,取早生孩子、男女花插着生。
语法与文化也有密切关系。汉语是孤立语,没有词形变化,句子比较简短,理解时需要较多的预设信息 (presupposition)。例如,《左传·隐公元年》中说:“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完”是修葺的意思,“聚”是聚集,但修葺什么、聚集什么,文中没说,需要理解者用当时战争的背景知识加以补充。古汉语中大量使用的“使动”“意动”“名词活用为动词”等也是追求表达简洁的结果。“左右欲兵之” (《史记·伯夷列传》)显然要比“左右欲以兵杀之”简洁。

(天津天后宫的“马上封侯”石雕)

(天津石家大院房屋上的砖雕,小猴骑在大猴背上,身上有蜜蜂叮咬,寓辈辈封侯之意)
现代汉语中如:“她的眼睛像妈妈,嘴巴像爸爸。”这是很正常的句子,如果说成“她的眼睛像妈妈的眼睛,她的嘴巴像爸爸的嘴巴”,那么反而叫人觉得罗嗦,但在英语中必须说成“Her eyes are like that of her mother,her mouth is like that of her father”。汉语语法的这种风格是由汉民族崇尚简洁的文化心理所决定的。汉民族讲求简单实用,不搞烦琐哲学。这种民族心理体现在语言上,就形成了句子简短的特点。表现在书面上,不采用分词连写的形式。
词汇与文化的联系最为密切。黄金贵将词汇分为文化词语和通义词语两类,有文化义蕴的词语为文化词语,无文化义蕴的词语为通义词语。他通过统计,指出语言中文化词语的数量是通义词语的两倍。[9]文化词语不光数量庞大,而且由于它们所反映的事物生灭演变的速度很快,这就决定了文化词语具有易变性,更需要我们去研究,所以文化语言学在词汇领域有很广阔的天地。例如,殷墟卜辞中凤鸟的凤和风雨的风都写作“凤”()。《甲》3112:“隻 (获)凤。”这是凤鸟义。《合》28556:“今日辛,王其田,不遘大凤。”这是风雨义。传世典籍中有“凤”“风”通用的情况。《初学记》卷二八引《山海经》:“凤伯之山、熊山、真陵之山,木多柳。”传本《山海经·中山经》作“风伯之山”。很多人认为这是借“凤”为“风”,这是从今人的思维出发作出的判断。事实上在古人的观念中,风是由凤鸟掌管着的。甲骨文中有“于帝史凤二犬”(《合》14225)的记载,说明凤在古人眼中是天帝的使者。《说文》:“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虎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崘,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文选》卷五十四刘孝标《辩命论》李善注引许慎曰:“风穴,风所从出。”风穴是风的来源,而凤鸟暮宿风穴,可知在前逻辑思维中风被想像成是由凤鸟掌管着的,凤是风神。凤“出于东方君子之国”,而《素问·五运行大论》中说“东方生风”,唐王冰注:“东者日之初,风者教之始,天之使也,所以发号施令,故生自东方也。”这也表明“凤”和“风”在古代文化观念中是有密切联系的,两个词具有同源关系,但谁源谁流,不好判断。甲骨文中的“凤”是为凤鸟而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先有凤神义,后有风雨义。从事理上来推断,可能是先有风雨的观念,后有凤神的观念,“凤”因“风”而得名。不管怎样,“风”古代写作“凤”应该是源于二者有词义引申关系,而非文字的假借。风字最早见于睡虎地秦简,大约是战国晚期才造出来的,是凤的后出分别文。传世战国晚期以前典籍中的风字应该是后人改凤为风的结果,上引《山海经》的例子就表明了这一点。
如所周知,词义演变的基本方式是引申,引申的重要诱发因素是使用者的联想,而联想则往往基于文化因素。如“玉”本义是一种有光泽的石头,由于中国文化中崇尚玉石,所以当人们想形容美好的事物时常常联想到玉石,于是“玉”就引申出了“美好”的义位,如“玉食”“玉女”“玉体”“玉音”等。西方文化中人们对玉并没有多大兴趣,不大可能把美好的事物跟玉联想到一起,所以英语中的jade词义只限于“玉石”和“绿玉色的”两个。
现代语言中词义的演变尤能显示文化的力量。《现代汉语词典》对“孩”的解释是“儿童”,“儿童”虽然在年龄上没有明确的上限,但一般应该在十三四岁以下。由于现代社会的成年人都喜欢装嫩,不喜欢别人说自己年纪大,于是那些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也被称为“男孩”“女孩”。众人的愿望使“孩”的义域发生了变化。
文字跟文化也关系密切。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极富文化蕴涵。解析古文字字形,把握字形所反映的本义,正确理解古人的用字现象,往往需要古代文化背景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古文字字形,我们可以了解古人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状况等。例如,古人认为玄鸟是主司孕育的神鸟,所以在春天玄鸟飞来之时他们要举行祈子活动。《礼记·月令》:“是月也 (指仲春二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郑玄注:“玄鸟,燕也。燕以施生时来,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为候。”“带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乃礼天子所御”之御指幸御。据此可知,玄鸟飞来之日天子幸御后妃于高禖之前,以祈后嗣。宋罗愿《尔雅翼》卷十五《释鸟·燕》云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燕)以春风来,秋风去,开生之候。其来主为孚乳蕃滋,故古者以其至之日祀高禖以请子。契因是而生,故《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或曰契母简翟吞乙 (按:即燕)卵而生契,故契号玄王,赐姓子氏。成汤绍其祖而字天乙。后代以子加乙为孔氏,乙至得子,则名嘉而字子孔。又人及鸟生子谓之乳,亦从乙从孚。荆楚之俗,燕始来睇,有入室者,以双箸掷之,令人有子。皆燕乙为生子之验。
上巳节的原始动机在于祈求生殖,所以上巳节期间民间有迎玄鸟的习俗。《昌黎县志》载:“三月三日曰‘蟠桃会’。……男女俱簪柏叶,若门前插柳,以迎玄鸟,今则不然。”《滦州志》三月条载:“旧志谓男女簪柳为饰,做面燕插檐,以迎玄鸟。”宋葛天民《迎燕》诗云:“咫尺春三月,寻常百姓家,为迎新燕入,不下旧帘遮”。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提到鲁国人“展喜”,《国语·鲁语》作“乙喜”。清张澍《春秋时人名字释》(《养素堂文集》卷三十二)云:“展喜字乙,《鲁语》称乙喜者,先字后名。乙,玄鸟,请子之候鸟。乙至而得子,故可喜。《楚辞》:‘简狄在台嚳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是已。”这是乙鸟赐子观念在古人名字中的反映。
有了这样的文化背景知识,我们就可以对小篆 (乳) (孔)二字的构造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文》在“乳”下解释说:“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产。从孚乙。乙者,乙鸟。《明堂》《月令》:‘乙鸟至之日,祀于高禖以请子。’故乳从乙。请子必以乙至之日者,乙春风来秋风去,开生之候鸟。”《说文》:“孔,通也。从乙从子。乙,请子之候鸟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乳”甲骨文作 ,象女子给孩子哺乳之形,本义是哺乳,小篆已发生讹变。“孔”西周金文作 ,也不从乙。因此,学者们大都认为许慎的解释不可信。就甲文金文而言,许慎的解释固然是错误的,但就小篆字形而言,许慎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这两个字在演变中都变成从乙,并不是任意的,恐怕还是受了乙鸟赐子传说的影响。
甲骨文中妇女的妇都写作帚,如“帚好”(《粹》1230)“帚汝”(《福》35)“多帚”(《佚》321)等,这种现象令学者们感到困惑。唐兰认为这是音同假借。他说:“今音帚妇侵迥异,在甲骨则相通叚,可知商时此三字音尚未甚变,其距离不甚远也。”[10]这只是一种猜测,并没有古音相同的证据。根据一般的古音研究的结论,帚上古读章母幽部 (*ȶǐəu),妇读并母之部 (*bǐwə),两字古音差别较大,没有假借的可能性。黄树先(1992)认为彗星古代也叫孛星,孛上古读*buət,与妇字读音接近。古有义同换读的现象,孛的理据是扫帚,与帚义同,故帚也读作孛,所以假借为妇。[11]这一解释也比较勉强。理据义与现实词义属于不同的词义范畴。孛的理据即便是扫帚,实际上并没有扫帚的意思[12],而帚虽然是扫帚,但殷商时期却没有指称彗星的用法,两个字不符合义同换读的条件,说殷商时期帚换读作孛,根据不足。
文字的借用并非只有音同假借一种情况,意义相同相关也可以假借,如甲骨文中“女”也借用作“母”,“月”借用作“夕”,“言”借用作“音”,都跟读音无关,而是由于意义相关。“帚”借用作“妇”就属于这种情况。考查古人生活习俗,我们看到打扫卫生是妇女的日常事务,因此扫帚就是妇女最常使用的工具。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卷十三“世妇”条:“王昭禹曰:执箕帚以事人者谓之妇。”早在《诗经》中就有妇女打扫卫生的记述。《豳风·东山》:“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即使贵为公主皇后,也仍以洒扫为天职。《汉书·东方朔传》:“上往临疾,问所欲,主辞谢曰: ‘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遗德,奉朝请之礼,备臣妾之仪,列为公主,赏赐邑入,隆天重地,死无以塞责。一日卒有不胜洒扫之职,先狗马填沟壑。’”《隋书·后妃传·炀帝萧皇后传》:“时后见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为《述志赋》以自寄。其词曰:‘承积善之余庆,备箕帚于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将负累于先灵。’”尽管公主皇后未必亲自打扫,但她们的这种说法却是体现了一种社会上普遍认同的观念。正因如此,古人提到妇女时往往也提及箕帚这两种清扫用具。《国语·吴语》:“勾践请盟,一介嫡女执箕箒以晐姓于王宫。”《战国策·楚策一》:“臣请秦太子入质于楚,楚太子入质于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箒之妾。”《古列女传》卷二《楚於陵妻》:“楚王闻於陵子终贤,欲以为相,使使者持金百镒往聘迎之。於陵子终曰:‘仆有箕箒之妾,请入与计之。’”《史记·高祖本纪》:“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晋代的庾衮在他的侄女庾芳出嫁的时候,还专门送了箕帚二物作为陪嫁。《晋书·孝友传·庚衮传》中记载说:“衮乃刈荆苕为箕帚,召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适人,将事舅姑,洒扫庭内,妇之道也,故赐汝此。匪器之为美,欲温恭朝夕,虽休勿休也。’”由于扫帚与妇女有如此密切的联系,所以人们借用扫帚义的帚表示妇女之义。《说文》:“婦,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婦是帚的后出分别文。
再就语言的理解而言,也离不开文化的参与。如《诗经·卫风·氓》中说,一个小伙子到外乡“抱布贸丝”。“布”在古汉语中有布匹和货币的意思,这里应该怎样理解才符合诗意呢?这是一个语言学问题,但从语言学本身是得不到答案的,因为这牵扯到我国商品交换发展的历史,我们得弄清布币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又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抱布贸丝”的正确理解有赖于这两个文化问题的明了。又如《战国策·韩策二》中记载,楚国围攻韩国,韩国派尚靳到秦国求援。秦宣太后对尚靳说:“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话虽很好懂,但我们不免对宣太后的“大胆”感到吃惊。她居然将自己的闺房隐私堂而皇之地用于外交谈判,真所谓不知天下有羞耻事。清代学者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卷二十一《谈异》中就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难道堂堂一国太后真是这样的厚颜无耻吗?要消除这一疑惑,需要联系当时的文化背景来考虑。先秦时期的人们对合理的两性关系有着十分坦然的态度,并没有后来人们讳莫如深的心理。战国时期的孟子曾劝说齐宣王实行仁政,齐宣王不愿采纳,便找了个借口予以推脱,他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梁惠王下》)。公开承认自己好色,这跟秦宣太后公开隐私的心理基础是一样的,属于见惯不惊的谈话内容,跟道德的沦丧并无联系。
宋代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把莲花描绘成一位高洁端庄的正人君子。人们一般把“出淤泥而不染”理解为莲花没有受到污泥的沾染,如果是这样,那所有的花都是生长于泥土,都没有受到泥土的沾染,何独赞美莲花?其实,莲花的这种意象源自佛经。例如:
道人心一如石在地,日炙不消,雨渍不释,风吹不动,出其凡俗,得成至道,心意已冷,无复热淫。譬如莲华出于污泥,根叶常冷,尘水不着。(三国吴支谦译《佛开解梵志阿颰经》)
其身清净,尘垢不着,犹如莲华不着尘水。 (西晋竺法护译《贤劫经》卷三《三十二相品第十一》)
已断于恩爱,远离于欲网;断除于一切,有爱之结缚。如水生莲花,尘水不染着;如日停虚空,清净无云翳。(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四十四)
如来所着衣,自覆身形体,莲华不着垢,此衣亦如是。(苻秦僧伽跋澄等译《僧伽罗剎所集经》卷中)
佛身微妙如融金聚,舌相广长如莲华叶,无有垢秽,清净鲜洁。(后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卷十四)
譬如莲华生长水中,淤泥浊水而不能染。(宋施护译《佛说大迦叶问大宝积正法经》卷二)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演变历程及其启示——基于对历届党代会报告的分析 ………………………………………………………… 李 聪(5.33)
从佛经的描述我们知道,“不染”说的是莲叶,而非花朵。古代印度人很早就发现莲叶有自我清洁的功能,尘垢很难附着在莲叶表面,所以莲叶总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莲叶的自洁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呢?长期以来,人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直到20世纪70年代,莲叶的这一秘密才被德国的两位科学家揭开。德国植物学家巴特洛特 (Barthlott Wilhelm)和艾勒 (Ehler N.)发现,在高分辨率的电子扫描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莲叶表面有许多微小的乳突,乳突的平均大小约为10微米,平均间距约12微米。而每个乳突由许多直径为200纳米左右的突起组成,使莲叶表面布满了一个个的“小山包”,“山包”间的凹陷部分充满空气,在莲叶表面形成一层只有纳米级厚的空气层,这就使得在尺寸上远大于这种结构的灰尘、雨水等降落到叶面后,只能同叶面“山包”的凸顶形成很小的接触点。雨点在自身表面张力的作用下形成珠状,只要叶面稍微倾斜,水珠就会滚离叶面。水珠在滚动中吸附灰尘,从而清洁了叶子表面。莲叶的这种自洁功能被称为“莲花效应”或“荷叶效应”(lotus effect)。科学家们模拟莲叶的自洁特性,发明了纳米自清洁的衣料和建筑涂料,只需一点水形成水滴,就可以自动清洁衣物和建筑表面。
由此可见,如果不熟悉与词语相关的文化知识,那么理解词语时很容易造成似是而非的错误。
总之,语言的各个方面都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加以研究,这可以弥补从形式角度研究语言的不足和缺陷,从而使我们对语言现象有更为全面的认识。19世纪末期欧洲出现的青年语法学派对语言演变的动力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语言不是游离于人们之外、凌驾于人们之上、为自身而存在的现象。语言实际只存在于个人之中,因而语言生命中的一切变化,只能来源于说这种语言的人。”[13]美国学者拉波夫 (William Labov)是社会语言学的创始人,但他并不喜欢使用“社会语言学”这个名称,因为在他看来,语言学的任何理论和活动都离不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天下不存在脱离社会的所谓语言学。[14]这一观点尽管有忽视语言可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的缺点,但它强调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自然现象,这一认识对语言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告诉我们,语言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之中,语言的变化来源于使用它的人,亦即来源于社会文化。
另一方面,语言既然是文化的载体,那么一些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文化习俗或观念就可以通过对语言记载或词语的分析爬梳而重新发掘出来。就拿我们熟悉的照明来说,“点灯”的说法反映的是用油照明的文化,“拉灯”的说法反映的是电灯开关有拉绳的现实,而“开灯”的说法意味着电灯开关拉绳的消失。英国学者泰勒在探讨早期人类精灵观念的形成问题时,就借助于语言中的词汇进行求证:
为了理解关于人类灵魂或精灵的流行观念,注意那些被认为适于表现这些观念的单词将是有益的。精灵,或者被昏睡的或有幻觉的人看见的幽灵,是一种虚幻的形态,如同一个阴影,因此同样的词shade(阴影)就用来表现灵魂。例如,在塔斯马尼亚人那里,表示灵魂和阴影的是同一个词。阿尔衮琴部族的印第安人称灵魂为“奥塔赫朱克”,意思是“他的阴影”。基切人的语言中,“纳图勃”这个词的意思既是“阴影”,又是“灵魂”。阿拉瓦克人的“乌耶哈”意思是“阴影” “灵魂”和“形象”。阿比彭人用“洛阿卡尔”这个词来表示阴影、灵魂、回声和形象。祖鲁人不只把“吞吉”这个词用作“阴影”“精灵”和“灵魂”,而且他们认为,在死的时候,人的阴影就会以某种途径离开人的肉体,从而成为祖先的精灵。巴苏陀人不只称死后留下的灵魂为“谢利其”或“阴影”,而且他们认为,当一个人沿着河岸行走的时候,鳄鱼能够在水中捉住他的阴影,于是把他拖入水中。在旧卡拉巴尔,精灵跟“乌克彭”或阴影同样混为一谈,假如失掉它,人就死了。[15]
许多古代文化习俗并没有专门而详细地记载,它们像雪泥鸿爪一样,只在茫茫书海中不时留下一鳞半爪,这就需要我们将零散的鳞爪拼集起来,将其本相予以复原。
《史记·外戚世家》记载,汉武帝到平阳公主家作客,“既饮,讴者进,上望见,独说 (悦)卫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 (上)衣轩中,得幸。”“更衣”是上厕所的委婉语。这几句话似乎给我们透露了这样的消息:古代富贵人家可能有在厕所里换衣的习俗,而且还有侍女伺候。但仅凭这一条记载还不能遽下断言,因为“轩”在古汉语中除了厕所的意义外,还有车子、长廊等含义,从后世的眼光来看,理解为“车子”或“长廊”好像更近情理,厕所中换衣则是不可思议的。唐代的张守节、颜师古及清代的何焯、周寿昌等正是这么理解的,然而如果我们再找一些类似的记载加以对照分析,就会相信古人确有在厕所里换衣的现象。《论衡·四讳》:“夫更衣之室,可谓臭矣;鲍鱼之肉,可谓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为忌;肴食腐鱼之肉,不以为讳。”“更衣之室”而曰臭,分明就是厕所。《世说新语·汰侈》载:“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箸(着)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梁刘孝标注引《语林》云:“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可知富贵人家的厕所有床有帐,石崇不过是比别人搞得奢侈一些罢了。《世说新语·纰漏》载:“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王敦就是那位在石崇家上厕所时“神色傲然”的王大将军,这回在舞阳公主家上厕所时却出尽了丑。他把厕所里塞鼻用的干枣当零嘴给吃了,又把婢女送来的洗手用的澡豆当干饭给吃了。这从侧面反映了富贵人家厕所的奢华。《后汉书·党锢·李膺传》载:“时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北海郡,臧 (脏)罪狼藉。郡舍溷轩 (厕所)有奇巧,乃载之以归。”将珍宝奇玩摆在厕所里,其厕所之豪华想来不让石崇。《史记·汲郑列传》:“大将军 (卫)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汉武帝在厕所里召见大将军,也说明厕所如同宫室。在这样的厕所里发生武帝幸卫子夫的事就没什么可诧异的了。《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四》文帝仁寿四年载:“陈夫人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这虽是一起未遂事件,但发生的场所也是在厕所。综合上面的材料来看,说古代富贵人家有在厕所里换衣的习惯是可以成立的。富贵人家之所以在厕所里换衣服,一方面是因为古代的堂室构造私密性不好,厕所则很隐秘;另一方面,古代有地位的人士穿的外衣非常宽大,“不脱长衣,则大溲不能办,亦犹清时服大礼服之难以大遗也。”[16]唐佚名《玉泉子》:“(杨希古)性又洁浄,内逼如厕,必撤衣无所有,然后高履以往。”宋雷庵正受编《嘉泰普灯录》卷七:“闻有悟侍者,见所掷爨余,有省,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丧志,自经于延寿堂厕后,出没无时,众惮之。师闻,中夜特往登溷。方脱衣,悟即提净水至。师曰:‘待我脱衣。’脱罢,悟复至。未几,悟供筹子。师涤净已,召接净桶去。”这两个例子表明古代大解之时要脱去宽大的外衣,便后再穿上,这种事在厕所里完成最为方便。正因换脱衣服在厕所里进行,所以人们就用“更衣”委婉地表示解手。清黄生《义府》卷下“溷轩”条云:“盖贵者入厕,出必更衣,如王敦在石崇家入厕之事,可证当时即谓入厕曰更衣。”“贵者入厕,出必更衣”只是石崇炫富的做法,黄生却当成了古来普遍存在的习俗,普遍存在的习俗则是在厕所更衣及如厕脱衣,出厕穿衣。
正因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所以语言和文化互相引证、互相发明的研究路子是中国学术的一个传统。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有时就借助于语言学方面的知识。《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是用“政”的得名之由要求统治者持身治国要奉公守法,做到名实相副。《韩非子·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这是借文字构造说明公私利益从来就存在着矛盾的观点。这种语言知识的印证有时虽有牵强附会的毛病,但它说明古人早就意识到了语言和文化的密切联系。到了汉代,语言研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不可避免地也就出现了通过文化研究语言的现象。《说文》:“外,远也。卜尚平旦,今若夕卜,于事外矣。”用占卜讲究清早的习俗解释“外”的构形①“外”可能是形声字。甲骨文中“外”字写作“卜”,与占卜之卜同字,如殷人先王“卜丙”“卜壬”就是“外丙”“外壬”。后加声符“夕”(实即“月”字,“夕”“月”原本一字),成为形声字。。《释名·释首饰》:“黛,代也,灭眉毛去之,以此画代其处也。”这是说古代女子用黛画眉时要拔去眉毛,用黛代替,故谓之黛。语言是文化最主要的载体,这就决定了研究语言必然要牵涉到文化,研究文化也往往要以语言记载为依托。研究佛教词语而不懂佛教文化,犹如扪烛扣盘,难明真谛。研究佛教文化而不由佛典,犹如矮人看戏,随人短长。所以,自有学术研究以来语言和文化相互结合的路子未曾中断过,也不可能中断。
西方语言学界虽然没有提出过“文化语言学”这样的名目,但从事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也还是有的。17世纪欧洲的唯理语法学派认为,语言形式是由人的理性决定的。19世纪下半叶,西方有一个以德国学者库恩 (Adalbert Kuhn 1812-1881)为代表的语言古生物学(linguistic palaeontology)学派,该学派把词语当作特殊的历史文献来进行研究,认为根据词和词义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判断各民族古代的生活和文化。20世纪初期,西方有一个以奥地利著名语言学家舒哈尔德 (Hugo Schuchardt,1842-1927)为代表的“词与物” (Wörter und Sachen)学派,该学派认为语言是由词组成的,因此要研究语言的历史必须研究词的历史,而研究词的历史单纯以语言分析为依据而忽视与它有密切关系的文化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他们主张研究词语时不要局限于分析它们的语言形式,而要研究这些词所表示的事物以及能在某一方面阐明的语言事实的全部文化材料,他们甚至认为语言学家所研究的主要就是这类词与物。[17]
自本世纪初以来,注重形式的结构主义语言研究异军突起,并很快成了语言研究的正宗,而以语义为中心的传统语言研究遭到冷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说:“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18]胡明扬指出:“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在一段时间内力求割断和传统语言学的联系,并且一再宣称语言科学只是从他们才开始建立起来的,在他们以前根本没有科学的语言学。他们还只承认研究语言结构的语言学是语言学,根本不承认研究语言跟社会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语言学是语言学。这当然是一种偏见,可是却在一个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很多人对研究社会跟语言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语言学的看法。结果,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语言学就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划了等号,语言就不再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社会理论就不再是语言学理论。”[19]在这一语言观的影响下,语言研究的独立性虽然大大增强了,但同时也走上了一条孤立的道路,语言研究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语言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工具,研究语言的目的就是“利其器”,而“利其器”是为了“善其事”。传统语言学“善其事”的功利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它是为经学、史学、文学、宗教等学科的学习与研究服务的,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现代语言学对语言“善其事”的作用不大关心,认为那样的语言学是其他学科的附庸,是语文学,不是真正的语言学。他们追求语言研究体系的自我完善,讲究形式标记,看重口语材料,结果是研究出来的东西不但难以引起其他学科人员的兴趣,同行中也找不到多少知音。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可以说是向传统的回归,或者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传统语言学发扬光大,把语言研究纳入整个文化研究的广阔天地,使语言研究更具民族特色,更有应用价值,因而也就更有活力,更有吸引力。可以相信,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对改变语言学在学术界孤立的现状,对繁荣祖国的语言文化事业,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那么,是不是重形式的现代语言研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呢?当然不是。语言毕竟有它的形式,为什么不能从形式的角度进行研究呢?事实上现代语言学对语言结构的分析、对语言单位功用的探讨以及对语言事实的仔细描写,是其他名目的语言研究不可替代的。拿对外汉语教学来说,外国留学生缺乏汉语言环境的长期熏染,很难把握一些词 (尤其是虚词)的用法及细微含义,如果没有对语言事实的认真描写和归纳,我们是说不明白的。某院校有位外国留学生在作文中写了这么一个句子:“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老师批改时在末尾给加了个“的”字,并告诉学生“是……的”是习惯的搭配格式,没有“的”句子就煞不住。后来在一次作文中这位留学生写了这样一个句子:“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的。”这回老师却把那个“的”字给删去了,学生感到疑惑,就去问老师:“您上次不是说前面用了‘是’,后面要用‘的’相配吗?怎么在这个句子里前面用了‘是’后面又不能用‘的’?”老师被问得答不上话来。[20]面对这样切实的问题,“汉语注重意会”“不搞形式主义”之类的概论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老老实实地去搜集实例,寻找规律。可见试图用文化语言学取代现代语言学的想法是片面的,也是行不通的。
其实,文化语言学和重形式的现代语言学并不是不能相容的。由于它们各自的研究方法及侧重点不同,刚好可以互相补充,使我们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认识更为全面、更为深刻。比如汉语词汇的复音化现象,那么如果从形式着眼,我们可以统计出复音词在各个时代的词汇系统中所占的比例,可以去摸清复音词当中各种不同的结构方式在历史发展中的消长情况,可以探讨复音化跟语音、语义的关系等等。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复音化现象,那么我们可以探讨复音化跟民族文化心理有什么联系,何以有些结构方式十分能产,有些则未能充分发展,复音词的发展规律对其他学科有何借鉴意义等等。如果没有具体事实的描写,文化角度的阐释则未免空疏。如果没有文化角度的加工,对语言现象的认识就有可能是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形式的描写就不能升华,难以融进其他文化领域,其价值也就得不到充分的体现。这样看来,文化语言学完全可以和重形式的现代语言学携起手来,共同为繁荣语言文化事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