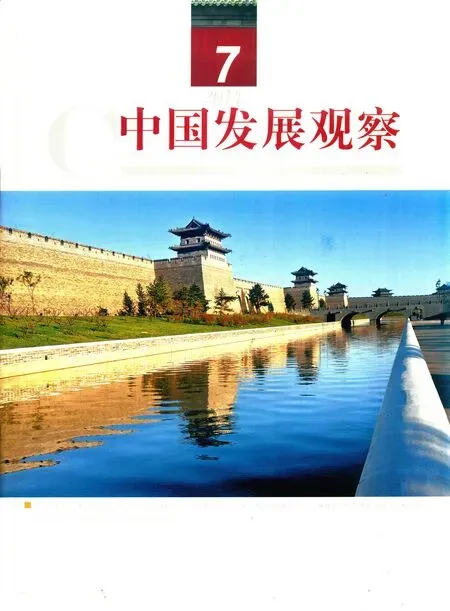迈向高收入国家:从金字塔社会向网络型社会的转变
——“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中的现代化转型研究”之十六
◎宣晓伟
迈向高收入国家:从金字塔社会向网络型社会的转变
——“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中的现代化转型研究”之十六
◎宣晓伟

人物绘像:罗雪村
宣晓伟,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有人从西珥不住地大声问:“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
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
守望的人回答:“黎明到来了,可是黑夜却还没有过去!
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
——《以赛亚书》,(21章11~12节)
对以前系列文章的简单综述
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per capita)在2010年达到4270美元(当年价美元,来源:世界发展指标2012),已经迈入了世界银行所设定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行2010年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区间内)。“中国是否能够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并最终进入高收入国家”由此成为了社会热议的话题,本系列文章试图从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的角度对“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一宏伟命题进行一番探讨。
从主流的观点来看,更多是将“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与“发展方式转变”结合在一起。站在“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中国能否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并最终迈向高收入国家,关键在于能否转变目前已经难以持续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根据官方文件的表述,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也有一些研究者侧重从“现代性”的视角来考察中国迈向高收入的过程,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应只局限在物质层面,“现代性是指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现代文明秩序”。在他们看来,“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就是要“建立一个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为最终目标。(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第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本系列文章认为,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不仅仅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再上台阶的过程,也是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应将“中国迈向高收入”放到中国现代化整体进程中来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外来冲击,被迫从几千年朝代循环的旧轨道中跃出,在器物、制度和思想观念的不同层面实现了巨大的转变,个人、社会和民族经历了根本的变迁,以逐步实现从一个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目前这个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尚未根本完成。
人类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变迁,是一个划时代、全方位的巨变。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爆发,伴随着“现代经济增长现象”的出现,为什么现代社会的生产力能摆脱传统的桎梏,并臻于无限增长的境地?经济学家们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经历了从资本到技术再到制度的演变。而马克思和韦伯站在社会变迁的更宽广视角,分别认为物质或观念的因素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扮演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侧重于物质因素的“马克思典范”和侧重于观念因素的“韦伯典范”。不同的理论均有各自的解释力,只有将它们综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了解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一复杂过程。
本系列文章从侧重“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的“斯密—涂尔干典范”来理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在斯密那里,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在于分工的深化。设备的投资、技术的进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乃至有效率经济组织的出现,既是带来分工的原因,更是分工导致的结果。现代经济增长伴随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分工的无限深化,而正是这种分工的深化,带来了对资本投入、技术进步、相应组织形式乃至制度环境改变的需要,推动着资本积累、技术创新、社会组织和整体制度的变迁。
既然分工的无限深化是现代经济增长出现的重要原因,也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根本动力,那么为什么有的社会可以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有的社会却不能呢?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分工程度要受到其社会结构的制约,不同社会所具有的器物、制度和观念等各种因素衍生出不同的社会结构,也决定着不同的分工水平。由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基于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视角的社会变迁分析框架,探讨器物、制度和观念层面的因素与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在此框架下,原始社会是由家庭、部落等小型社会单位自我复制而形成的“分支式结构”。传统社会是由不同层级、且层级之间有明确等级关系构成的“层级式结构”。现代社会则是由不同功能的社会领域、且各个领域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和规则构成的“功能式结构”。
在原始社会中,基于血缘的“生物基因”和基于习俗的“文化基因”在推动人们开展合作和群体扩张中起着根本性作用,但在由自给自足的基本社会单位所组成“分支式”的社会结构下,社会关系和社会功能都较为简单,社会分工水平也极其有限,很难有不断拓展的空间。
在传统社会中,轴心时期超越突破所产生的几大终极价值诉求,为传统社会的制度构建提供了支撑,以家族、庄园、教区、行会或种姓等基本社会单位为依托,产生了集中的社会管理和复杂的社会统治体系,建立了传统意义上不同类型的国家机器。与原始社会相比,传统社会的分工水平有根本性的提高,由此也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明显攀升和社会财富的大量集聚。然而,在传统社会的“层级式”结构中,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处于底层,处于社会上层的一小部分人支配着社会的主要权力和财富。在功能泛化的条件下,这些处于社会等级上层的小群体,常常集社会权力和社会资源于一身,凭借自己的特权地位,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畅行无阻。所以,在一元化价值信仰、血缘亲缘社会关系主导和社会功能泛化的束缚下,传统社会的分工水平难以无限扩展和深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受到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限制,不得不停滞下来,无法带来社会生产力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
在现代社会中,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次系统,它们基于与整体系统间的功能关联而彼此区分开来,例如区分为经济、政治、法律、科学、宗教、教育等等领域。传统社会虽然也存在着上述领域,然而不同领域的界限模糊且常常被整合在一起,一个团体、组织或个人往往身兼社会的多种功能,呈现的是一种功能泛化的状态。而现代社会中各个领域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和规则,社会不同领域的等级不能混淆。正是现代社会由功能分化而形成的各种自由进出、界限清晰、规则明确、独立自治的不同社会领域,破除了社会分工无限深化的樊篱,真正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现代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局面。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功能分化式的社会结构、推动社会分工不断拓展,是与其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个人权利的正当化、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和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密不可分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就是一个由金字塔型层级式结构的社会,向着网络型功能式结构社会逐渐转变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于三类社会的概括和划分只是一种“理想型”的理论建构,现实历史过程中的社会演进远为复杂,也不可能呈现出如此泾渭分明的区别。此外,尽管在物质层面,不同社会类型的演进呈现出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的状态,由此具有一种“进步”的特征。然而在观念层面,我们很难对不同社会拥有的价值诉求加以简单判断,例如将原始社会或传统社会的理念斥之为“野蛮”或“愚昧”,而将现代人具有的看法理解为“科学”或“高明”,人类的心灵和信仰的演变,事实上远较物质层面的因素更为复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拒绝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即在讨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时,并不认为现代社会样样都好,在价值上是可欲而且是必须追求的。
西方社会是第一个由传统迈向现代的人类社会,它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相互作用、机缘巧合的结果。正如麦克法兰将西方进入到现代社会比喻成用一把钥匙去开一扇门,他强调:“头等重要的是,开启现代性大门的钥匙必须丝丝入扣,这不仅是要把每一个零件都弄正确,而且是要把每一个零件和其余零件的关系摆正确;所以,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家庭与经济的关系,等等,都必须恰到好处。这种契合得以首次出现的概率是几千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 201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页)。
为什么西方世界能率先进入到现代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列出无数的答案。从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西方独特的政教关系有助于形成一个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天主教会制度在对西方传统社会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首先引进法治和理性传统,形成了一个相对自治、制度严密的大一统组织,从而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的母体。政教的相对分离也为西方现代法治传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就像伯尔曼所言:教皇革命(1075年~1122年)所带来的“宗教管辖权和世俗管辖权的分离、并存和相互作用,是西方法律传统的一个主要渊源”(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2010年,法律出版社,第95页)。
在推动社会分工的分化和整合方面,西方传统社会中权力的高度分散化和统一的宗教意识制约事实上并不利于分工的展开,但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乃至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等一系列因素的带动下,英国首先探索出了一条君主立宪、议会政治的道路,率先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英国的带动和影响下,西方各国逐渐都迈入了现代社会的行列,由此马上凭借着船坚炮利对世界其他文明下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为了应对冲击、救亡图存,各个传统国家不得不展开艰苦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但囿于传统价值观念转变困难等多种因素,绝大多数国家的转型之路并不成功。
回到中国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终极价值关怀是由己及人、依靠自身力量去逐步构建人间的美好社会。儒家传统通过“家国同构、忠孝同构”的方式将基于血缘和家族的伦理规范从个人、家庭放大至国家。大一统国家的实际治理遵循的是“儒法互补”的方式,依赖“读书人做官”的官僚体系。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社会同样是金字塔型的层级式结构,但“士大夫政治”的推行使得整个社会具有更强的流动性,保证了王朝治理的弹性和稳定性。而且大一统的王朝在“整合”方面也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开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然而传统帝国整体大而不强,陷于周期性的朝代循环中。在西方冲击下,中国依靠新意识形态、全能主义政治和超级行政体系完成了救亡图存、展开现代化初步建设等一系列任务。改革开放使得原有一元化体制日益碎片化,在充分调动个体积极性、使得社会爆发巨大活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带来社会终极价值观念缺失,社会失范、腐败加剧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如何从金字塔型社会迈向网络型社会
回到上述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我们从观念、制度和器物三个层面来看中国社会在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迈向高收入的过程中所需的进一步变化。
在观念层面,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一元化体制碎片化后,社会共识和社会规范的缺失,其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共识就是社会的终极价值观念。自人类文明迈向轴心时代,产生各种终极价值关怀以来,无论是在漫长岁月的传统社会,还是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终极价值关怀始终对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意义提供答案,规范着每个人的行为,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基石。中国目前在终极价值关怀层面所遇到的困境,从本质上来看,是中国文明传统遭受西方文明传统冲击后,还难以有效真正应对、吸收和融合西方文明的结果。现在的暂时状态更多呈现出丢弃了自身传承数千年的文明传统、却又迟迟难以转变为他人传统的尴尬。从几百年来中国历经磨难、千转百回以应对西方挑战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现在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更新的起点,更为理性、包容、谨慎、全面地分析中西文明的差异,以真正将中国自身的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包括西方主流的资本主义文明传统、和对此加以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等传统)融合起来。具体而言,中国目前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思想文化资源,一种是自身的几千年传统文化、一种是受西方冲击后引进的社会主义思潮、一种是改革开放以后兴起的现代资本主义传统。中国未来文明演进的任务是要发挥出中国文化善于融通的特点,将这三者较好地融合起来。在终极价值观念层面,中国人应回到几千年的文明传统中寻求安身立命的真正之本。正如钱穆所言,“家庭是中国人的教堂”,我们需要重新构建由己推人、依靠自身努力去构建人间美好社会的传统。当然这个回去也并非简单地重复过去,而是要汲取西方传统中的营养,将其对个人权利和观念的尊重、对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明确区分纳入中国传统价值关怀的框架内。在现代社会管理和运行方面,需要更多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成功做法和经验;而在具体的政策指向上,则需要引入更注重公平和平等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源。
在制度层面,中国则需要改变其全能主义政治传统,调整从中央一直到地方的超级行政体系。全能主义政治是中国为了应对西方冲击下的全面社会危机而产生的一个自然结果,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全能主义政治也必须做出改变。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生必须要有一个功能分化、界限清晰、规则明确的不同社会领域划分,而在全能主义政治下,难以产生上述的功能分化式社会,也无法真正不断展开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中国一元化体制的碎片化导致了社会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分化,但如何再整合和规范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已经很难再依靠全能主义政治传统下的政治权威,必须转向更为明确、规范和公正的法治传统(即契约关系)。同样,改革开放打破了中央政府指导一切的计划经济,赋予了地方更多的自主权。然而如何进一步明确规范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当前中央地方关系不顺,在经济层面导致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原有的从中央一直管到乡村的超级行政体系,同样已经难以适应环境的变化,需要做出调整。
在器物层面,中国文明传统中具有高度入世、实用主义的世俗理性精神,它在赋予中国文化很强包容性和灵活性的同时,也对真正的求知和科学精神缺乏应有的关注。因此,如何真正学习借鉴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树立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自足自主的求知求真传统,也是中国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中国要在已有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并迈入高收入社会,在分化的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确保“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实现对政治权力的有效约束;同时要推动界限清晰、规则明确的不同社会领域的功能分化;在整合的方面则需要重塑社会共识、重建社会规范,使得法治(契约)成为支配社会运行、调节社会主体关系的真正基石。
概而言之,中国要迈向高收入国家,需要从目前碎片化的金字塔型社会进一步转变为网络型社会,推动社会结构和功能的调整、社会主体间关系的重塑和规范,实现由社会运行由“关系型支配”向“契约型支配”的转换,真正建立一个不同领域界限清晰、功能分化、权责对等的多元化社会。
至此,我们采取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的视角(斯密—涂尔干典范),利用系统演化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迈入高收入这样一个宏伟的命题,做了一番微不足道的探索。目前的研究更多只是给出了一个视角,提出了相应的简单分析框架,因此是一个导论。研究的结论还非常粗疏,仍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展开分析。然而正如顾准所言“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年,第229页)。我们会对“中国迈入高收入”这一宏伟命题继续进行研究,在下一系列文章中将会围绕“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主题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