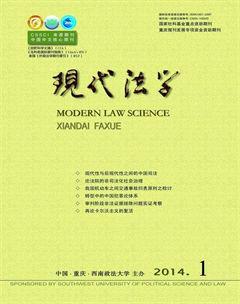再论卡尔沃主义的复活
摘要:晚近,一些国家为应对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修改宪法、法律和合同,限制或放弃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条款,甚至终止双边投资条约和退出《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这一系列现象是卡尔沃主义不同程度复活的表现。卡尔沃主义复活的原因在于经济危机引发的对新自由主义的质疑、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为代表的国际投资仲裁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各国对保留规制权的诉求。在这种国际潮流和背景下,中国应支持和提倡改革现行国际投资仲裁体制,在签订国际投资协定时,应审慎设计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条款。
关键词:卡尔沃主义;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条款;新自由主义;规制权
中图分类号:DF96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4.01.12
引 言单文华教授曾发文对卡尔沃主义的死亡和再生进行了深刻论述。其核心观点是:“卡尔沃主义”的真正精髓在于“反超国民待遇”;否定“卡尔沃主义已经死亡”或者“卡尔沃主义行将就木”的流行观点,指出它并不是死了,而只是暂时搁浅,且有复苏的迹象[1]。在2006年于《国际经济法学刊》上发表的这篇论文中,囿于现实发展的客观限制,单文华教授使用了不太确定的措辞——“卡尔沃主义似乎正在再生”,而且,其考察的对象也仅限于拉美国家。在2007年于《西北国际法与商务学刊》发表的另一篇英文论文中,单文华教授则明确指出卡尔沃主义正在复活,其标志着国际投资法发展方向的变化,并指出国际投资法的主题已从南北对立转为公私分野,然而,他并未对中国的政策取向问题给出建议[2]。另一位外国学者在2006年也对卡尔沃主义在拉美的复活进行了论述,并给出了政策建议:在支持投资者—国家仲裁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改革以增强透明度,且仲裁员要增加对东道国政策的考虑,以更好地平衡两种利益[3]。如今,卡尔沃主义已经从有复活迹象走向真正的复活,而且,续写这一新篇章的不再仅仅是拉美发展中国家,还包括其他大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所有这些现象再次引发了作者对卡尔沃主义的反思:卡尔沃主义不但在拉美复活,而且在其他国家得到实践,卡尔沃主义不同程度的复活必有其原因,对国际投资法的未来走向必将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在国际投资协定缔约实践中应如何对待这种国际潮流?中国在签订国际投资协定时是否应接受包括国际投资仲裁在内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条款(ISDS条款),以及应如何设计ISDS条款?这是中国国际投资法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卡尔沃主义内含的进一步厘清 学界公认卡尔沃主义由阿根廷外交家及法学家卡洛斯·卡尔沃于1868年提出由于卡尔沃主义由卡尔沃提出已得到国际法学界公认,因此,本文也采用通说。然而,有学者认为,实际上,卡尔沃主义的产生早于卡尔沃的第一部著作,其出现于1832年的第一部拉美国际法著作中,因此,卡尔沃主义应被称为贝约/卡尔沃主义。该学者甚至还主张,贝约/卡尔沃主义的初衷是为了刺激和鼓励投资,而不是反对外国投资,所以强调给予外国投资者全面的民法上的平等待遇,但除非有拒绝司法的情况,外国投资者不能享受超过平等的待遇。关于这一主张,请参见:Santiago Montt. Wha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Latin America Can and Should Demand from Each Other,Updating the Bello/Calvo Doctrine in the BIT Generation[J].Res Rublica Argentina,2007,(3):300-301.在笔者看来,卡尔沃主义产生的时间和初衷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贝约主义和卡尔沃主义都主张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反对给予外国投资者以超国民待遇。,然而,对于卡尔沃主义的确切含义,学者们则是见仁见智,因此,为了本文的进一步展开,还需要对其进一步厘清。
在我国,国际法前辈们概括地认为,卡尔沃主义主张“在一国定居的外国人,肯定应该享有和该国国民相同的受保护的权利,但他们不能要求更多的保护。”[4]显然,这里强调的是国民待遇,但否认超国民待遇。唐纳德·谢伊在其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中则将卡尔沃主义描述为包含两个主要原则:自由和独立的主权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享有免于其他国家任何武力或外交干涉的自由权利;外国人无权享有本国国民所不享有的权利和特权,对其申诉,他们只可以在当地寻求救济。所以,唐纳德·谢伊认为卡尔沃主义基本上主张“不干预及外国人与本国人的绝对平等”这两个概念[5]。罗杰·C·韦斯利进一步认为,卡尔沃条款包含五个要素:服从当地管辖权;当地法的适用;在当地合同安排上对外国人一视同仁;放弃外国人母国的外交保护权;放弃国际法上的权利[6]。佩德罗·罗夫则将卡尔沃条款缩小为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本国国民与外国国民的平等待遇;东道国的排他管辖权;对外交保护的限制[7]。肯尼斯·J·范德维德教授颇有见地地从实体与程序的角度,概括地将卡尔沃主义分为两个关键要素:在实体意义上,卡尔沃主义强调东道国没有义务授予外国人比本国人更大的权利或利益;在程序意义上,卡尔沃主义强调外国人无权获得东道国国民无法得到的救济,包括外交保护或军事干预的外国或国际救济及非当地法即外国法或国际法的适用[8]。其他对卡尔沃主义的解读或者强调外国投资者不能强硬要求享有超国民待遇,或者强调外国政府不应违反主权国家的法律以强制执行其本国人的求偿。此处不再赘述。
现代法学韩秀丽:再论卡尔沃主义的复活——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视角 综上,笔者认为,对卡尔沃主义更全面的理解包括实体意义上和程序意义上两种含义,但得到强调的往往是程序意义上的卡尔沃主义。所谓反超国民待遇,实际上是为排除外交保护提供理论依据,或者说作为排除外交保护的预设前提,因为可以推理,如果外国投资者可以诉诸母国外交保护,而国内投资者没有这种权利,这就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从而违反了卡尔沃主义。可以说,卡尔沃主义的核心是非干涉和拒绝外交保护,卡尔沃主义只是国民待遇原则的附带原则。作为对付投资者母国滥用外交保护的具体程序方法,卡尔沃主义主张用尽当地救济,排除强国利用外交保护进行任意干涉。卡尔沃主义的实质精神是外国投资者不能享有高于国内投资者的待遇,所以,其推理必然是拒绝将投资争端交由母国司法机构或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审理,也拒绝受母国法或国际法的支配。
卡尔沃主义通过卡尔沃条款的方式得到拉美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宪法、制定法、条约及特许协议的普遍采用,从而从理论变为现实。总体上,在20世纪60-70年代,卡尔沃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努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法律文件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这些文件包括《联合国跨国公司行动守则(草案)》、《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等,但由于发达国家的异议,这些法律文件的性质一直是有争议的。
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对待外资态度方面的对立和分歧,导致缺少私人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入,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困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吸引外资,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改弦易辙,强化对外资的国际法律保护,接受ISDS条款,以至于卡尔沃主义被宣称死亡。
总之,笔者的考察表明,卡尔沃主义更多的是在程序意义上使用,从其产生也可见原因之一斑。卡尔沃主义主张“僵硬”的国民待遇,不允许任何超国民待遇的存在,即使考虑到其产生的背景,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在国民待遇原则的基础上,卡尔沃主义旨在用当地救济取代母国的外交保护和武装干涉,当然也排斥外国投资者享有内国投资者所不能享有的诉诸国际投资仲裁的权利,从而使外国投资者处于东道国的立法和司法体制之下,排斥母国法及国际法的支配。归根结底,如果说国际投资法中卡尔沃主义的死亡主要表现为对用尽东道国救济的放弃和对投资者—国家仲裁的接受,则卡尔沃主义复活的主要表现是对ISDS机制的不信任和敌视,及限制外国投资者诉诸国际投资仲裁的权利。
二、卡尔沃主义复活的不同表现 作为投资者提起国际投资仲裁的依据,ISDS条款主要规定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包括双边投资条约(BIT)、包含投资章节的自由贸易协定及其他国际投资协定。此外,也可能体现在东道国的投资法以及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合同中。这种条款授权一国的投资者对另一国政府在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采取法律行动,主张另一国政府的措施侵害其权益而要求赔偿。程序意义上的卡尔沃主义复活即表现在对投资协定中ISDS条款的剔除和一些相应的措施,这一趋势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各大洲,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
(一)激进的拉美国家
在拉美,卡尔沃主义的复活表现为非常激进的方式,其中,代表性的国家包括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
1.玻利维亚
2007年4月,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一致同意退出《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以下简称《ICSID公约》),以建立美洲的“区域经济新秩序”[9]。2007年5月2日,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秘书处收到了玻利维亚正式退出《ICSID公约》的声明,退出声明自ICSID秘书处收到通知之日起6个月即于2007年11月3日生效[10]。通知退出《ICSID公约》之后,玻利维亚就宣布重新谈判和修改BIT。在国内法方面,2009年,玻利维亚通过一部公投宪法,该宪法特别强调了玻利维亚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绝对司法主权,并在其第366条明确禁止将特定行业的投资争议提交至国际仲裁。玻利维亚无疑是复活“卡尔沃主义”的先行者。
2.厄瓜多尔
2007年10月,厄瓜多尔政府对国内的外国石油公司开征99%的石油暴利税,这一行为引起了其与石油公司的争端。面对这些争端,厄瓜多尔最初试图利用《ICSID公约》关于管辖权的灵活条款,即第25(4)条,限制ICSID管辖石油、天然气和矿产投资争端的权利。根据该条,任何缔约国可以在批准、接受或认可《ICSID公约》时,或在此后任何时候,把它将考虑或不考虑提交给“中心”管辖的一类或几类争端通知“中心”。2007年12月4日,ICSID秘书处收到了厄瓜多尔的通知,就涉及石油、天然气、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开发活动的争端,厄瓜多尔收回管辖权。
在国内法层面,厄瓜多尔全民公决通过的新宪法于2008年10月20日生效。该新宪法对国际仲裁施加了限制,其第422条规定禁止厄瓜多尔缔结那种在与私人的合同争端或商事争端中,将管辖权转移给国际仲裁机构的条约或国际法律文件。但此条有一个例外,即如果厄瓜多尔与拉美居民将争端提交至区域性的拉美仲裁机构或司法机构,则宪法并不禁止签订此类条约或国际法律文件。所以,新宪法旨在要求政府不缔结服从ICSID仲裁的条约或国际法律文件,而不是不缔结服从拉美仲裁机构的条约或国际法律文件,意在以拉美区域仲裁取代ICSID仲裁。
如果说一开始厄瓜多尔采取的还是稍微缓和的限制ICSID管辖权的方法,但最终还是采取了激进的退出政策。2009年7月2日,厄瓜多尔总统颁布了第1823号行政法令,宣布退出《ICSID公约》。2009年7月6日,ICSID秘书处收到了厄瓜多尔退出《ICSID公约》的声明,声明于2010年1月7日生效[11]。
3.委内瑞拉
2007年4月,委内瑞拉与玻利维亚、尼加拉瓜一致同意退出ICSID,自此,委内瑞拉为配合退出ICSID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废除包含投资者—国家仲裁条款的BIT。由于委内瑞拉与荷兰的BIT成为众多投资者滥用的工具,委内瑞拉于2008年4月30日正式通知荷兰政府,因彼此的BIT与委内瑞拉的“国家政策”不符,委内瑞拉决定废除其与荷兰的BIT。另外,由于委内瑞拉的外国投资法也成为投资者提出国际仲裁的依据,委内瑞拉最高法院于2008年10月17日做出第1541号判决,该项判决指出委内瑞拉的《促进和保护投资法》第22条不构成对ICSID管辖权的承认。2008年2月13日,委内瑞拉国民议会通过了批准委内瑞拉退出ICSID的决议,从而完成了委内瑞拉退出ICSID的国内法程序。2012年1月24日,ICSID秘书处收到了委内瑞拉退出《ICSID公约》的书面通知,据此,委内瑞拉于2012年7月24日正式退出了《ICSID公约》。
4.阿根廷
虽然阿根廷在ICSID官司缠身,又是卡尔沃主义的故乡,且阿根廷政府和议员都对ICSID仲裁制度表达了强烈不满,但阿根廷却久久没有提出退出《ICSID公约》。为了应对在ICSID的如潮官司,其采取的是较为缓和的措施,主要有:与原告进行协商谈判以便达成撤销或者中止ICSID仲裁程序的协议,或诉诸《ICSID公约》第52条寻求撤销仲裁裁决。但是,阿根廷无力履行任何败诉的裁决,以致遭到美国取消普惠制待遇的报复[12]。阿根廷再也无法忍受,终于在2013年1月24日宣布打算退出《ICSID公约》。
此外,尼加拉瓜也早于2007年表达了退出《ICSID公约》的意向,尼加拉瓜此后已经停止签订包含同意ICSID仲裁的国际投资协定,而代之以国际仲裁院仲裁。2008年4月14日,尼加拉瓜司法部长进一步重申其正在考虑废除《ICSID公约》,并再次表达了不再签署任何包含ICSID管辖权的国际投资协定的政策定向。
对于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国的激进行为,有学者指出其只是拉美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出现剧烈变革的前奏,如果其他国家也效仿它们采取激烈行动,退出《ICSID公约》,创立区域争端解决机构,则ICSID在拉美前途未卜。笔者认为,否定国际投资仲裁是拉美的主旋律,但不仅要看到这几个国家采取了激进的退出政策,还要看到有些拉美国家从未放弃卡尔沃主义,如墨西哥和古巴未签署《ICSID公约》,多米尼加共和国虽于2000年3月20日签署了《ICSID公约》,但至今没有批准。巴西从未加入《ICSID公约》,在反对派的掣肘下,也从未有任何生效的国际投资协定。
(二)仅仅排除ISDS条款的澳大利亚
与拉美国家相比,卡尔沃主义在发达国家澳大利亚的复活主要体现为面向未来的措施。在2011年4月12日发布的《贸易政策声明》的“投资者—国家”章节,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其未来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将排除ISDS条款。笔者将其主要内容概括为四点[13]:(1)澳大利亚政府支持国民待遇原则,但并不支持会给予外国企业比本国企业更大权利的条款,所以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者有权得到和国内企业相同的法律保护,但不能通过ISDS条款得到比本国企业更大的权利;(2)在不会造成歧视的情况下,不支持会限制澳大利亚政府制定关于社会、环境和经济事项法律之能力的条款;(3)没有也不会接受限制其对烟草产品做出健康警告或“素包装”要求的条款;(4)没有也不会接受限制其继续实施《药物福利计划》的条款。
第1点的用语几乎是卡尔沃主义的原义重复。第2点至第4点的性质实际上一致,即强调澳大利亚政府在各方面的规制权。澳大利亚政府对ISDS条款的排除及对规制权的彰显无疑是卡尔沃主义的复活。在过去,澳大利亚政府采取的是明显相反的政策,主要表现在:在澳大利亚企业的请求下,澳大利亚政府曾寻求在与发展中国家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订入ISDS条款。但是《贸易政策声明》表明,澳大利亚政府将不再延续这一实践。
有学者不希望将澳大利亚政府的《贸易政策声明》解释为在未来的所有国际投资协定中完全排除ISDS条款,而试图将其解释为澳大利亚政府将在逐案基础上来决定[14]。虽然这种解读为澳大利亚保留了政策灵活性,以使其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但笔者从《贸易政策声明》本身的措辞无法看出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一意图。从实践方面看,在2011年2月16日签订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议定书》中根本就不包含ISDS条款。在2012年5月22日澳大利亚与马来西亚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同样不见ISDS条款。澳大利亚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正在磋商的自由贸易协定皆不包含ISDS条款。可见,新贸易政策的正式出台无疑会导致澳大利亚在将来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普遍地排除ISDS条款。对于澳大利亚政府采取的新贸易投资政策,有学者间接指出,没有包含ISDS机制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但会增加澳大利亚的海外投资者和投资的风险和保险成本,而且会增加在澳大利亚的外资的风险和保险成本,从而使其转投其他投资条约机制更好的国家。
(三)官方态度并不完全明朗的南非和印度
1.南非
虽然南非在ICSID只有一起根据《ICSID附加便利规则》的仲裁案件,且以投资者申请终止仲裁程序、南非得到40万欧元的仲裁成本补偿而告终,但由于该案触动了南非敏感的公共政策领域,即“黑人经济授权法”,使其开始了为期三年的BIT审查,而审查的结论是否定BIT对吸引外资的作用,认为BIT严重制约了东道国的政策空间。根据南非贸易和产业部部长罗布·戴维斯2012年7月26日的演讲,南非政府对待BIT的态度和立场可具体概括为[15]:在南非第一代BIT中,南非政府以牺牲规制权为代价,使其投资体制自由化以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某些投资利益不能自动实现,国家必须为此起重要作用;BIT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关系含糊不清,并且,BIT对政府追求其以宪法为依据的转型议程之能力施加了风险和限制;南非怀疑和否定现有的国际投资仲裁体制;对于和南非没有BIT关系的国家,南非在将来会避免与这些国家缔结BIT,除非在令人信服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需要签订BIT;对于与南非存在第一代BIT关系的国家,南非应当对这些条约进行评审,以终止这些BIT,在可能的情况下,基于南非将来制订的BIT范本进行重新磋商;应当在国内法中规定两种典型的BIT条款:保护投资者以及基于公共政策考虑的正当例外;南非的追求是“实现投资者的权利与义务间的适当平衡”,“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依据以上思想,南非已经首先终止了和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及德国的BIT,南非打算逐步淘汰与欧盟各国的BIT。如前所述,南非现任政府计划以终止BIT为目的,评审1994年民主转型后签订的所有第一代BIT(1994年至1998年)。毫无疑问,根据条约签订的年代,中国—南非BIT(1997年签订)正属于这一类条约,但并不明确南非官方所说的逐步废除是否包括其和中国的BIT。另外,并不清楚南非政府到底是想通过国内法,还是通过制订新的条约范本,并依其缔结的条约来实现对外资的管理。
2.印度
据报道,在印度与欧盟进行的贸易协定磋商中,印度拒绝了ISDS条款。印度产业政策和促进部的官员表示,国家不应当被“拖入”私人争端,原则上,双边协定要排除ISDS条款,或者说不允许外国投资者将与印度政府的争端诉诸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现在,印度政府正在逐个审查与其他国家签订的BIT,以甄别出容易在将来引发争端的条款,尤其是ISDS条款。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也在试图起草新的条约范本。印度政府的这一举动是由于2011年末印度在投资者根据印度—澳大利亚BIT提出的仲裁案中失败,而2012年,印度面临着一系列投资者的挑战,尤其是英国电信的经营者“沃达丰”向印度政府送达了通知,通知指出印度税法的拟议变化及撤销电信许可证违反了印度与荷兰的BIT。与南非一样,印度不是《ICSID公约》的缔约方,这也表明印度对国际投资仲裁向来持谨慎态度。最近,印度政府通知议会,印度已搁置BIT的谈判。但到目前为止,印度在将来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是否包含ISDS条款,官方的态度并不完全明朗。
(四)对ISDS条款进行改革的美国和欧盟
1.美国
2007年6月28日,美国与巴拿马签订了贸易促进协定。在该协定中,包含ISDS条款,巴拿马于2007年7月11日就批准了该协定,但美国国会到2011年10月13日才批准该协定。美国国会此前为此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作为国会专门研究机构的美国国会研究部的报告曾提出要修改该自由贸易协定,其中之一就是关于ISDS条款的用语,主张应澄清以下观点:对于该协定下的投资争端解决,外国投资者并没有比美国国内投资者更大的权利。之所以要作此修改是因为,虽然在美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普遍包括ISDS条款,美国投资者为保护其投资利益也长期支持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包括ISDS条款,但是,美国过去之所以缔结这样的条款是因为缔约对象通常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美国鲜有投资,所以,也只有美国投资者可以利用这些条款。然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仲裁实践表明情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的众多州政府因环境和其他规制措施而被外国投资者提起国际仲裁,这为美国敲响了警钟。
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开始审查美国2004年BIT范本,经过三年多的审查,最终于2012年4月20日结束了内部争论,并发布了2012年BIT范本。尽管面临各种批评,该范本还是保留了ISDS条款,但将投资者与东道国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议的程序规定得极为详尽,用12页之多的篇幅对投资者的适格性、各方同意的条件及限制、仲裁员的选择、仲裁程序的进行和透明度、准据法等问题给予了详细规定。该范本基于的现实是:美国越来越兼具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双重身份,甚至美国也在采取各种措施吸引海外投资者到美国投资,极力解决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2.欧盟
2010年12月1日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将对外投资政策统一划入欧盟的职权范围,提出在欧盟层面实行统一的外资政策。2011年5月7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今后欧盟将作为一个整体与第三国缔结投资协定。在讨论制定欧盟国际投资政策的欧洲议会注意到美国和加拿大修改了BIT范本以限制国际仲裁庭的解释范围,确保更好地保护其规制权。欧洲议会于2011年4月6日通过的决议也表明其对ISDS的关切,强调未来订立的国际投资协定将保护国家的规制权。该决议还对ISDS机制提出了更大透明度、上诉机制及法庭之友诉讼摘要等方面的改革建议。
以上笔者对卡尔沃主义复活现象的国别考察未必是全面的。例如,2009年8月20日,俄罗斯正式通知《能源宪章条约》保管处,它不打算成为《能源宪章条约》和《能源效率与有关环境问题议定书》的缔约方。根据该条约第45(3)(a)条,临时适用的终止自保管处收到书面通知60天后生效,也就是说,从2009年10月18日起,《能源宪章条约》终止对俄罗斯的临时适用。俄罗斯与印度、巴西和南非这三个金砖国家一样,也不是《ICSID公约》的缔约国。韩国司法界也存在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中ISDS条款的强烈反对,担心其会损害韩国的司法主权。2006年,韩国最高法院曾向韩国政府提交了题为“对韩美自由贸易协定ISDS程序的审查意见”。韩国政府宣布其会在2012年3月15日条约生效后90天内就该协定中与投资有关的条款重新磋商。
综上,鉴于加入《ICSID公约》以及国际投资协定、国内立法或合同中包含ISDS条款是启动投资者—国家仲裁的前提条件,所以,卡尔沃主义的复活主要表现为:退出《ICSID公约》、终止国际投资协定或投资者—国家合同、修改国内立法或仅仅排除投资者—国家仲裁条款。另外,许多国家都进一步完善了其国际投资协定中的ISDS条款,以减少受投资者求偿的风险、增加争端解决程序的效率和透明度。虽然使用“卡尔沃主义复活”这一表达,但需要明确的是,今日之卡尔沃主义已经与最初不同,因为最初的卡尔沃主义是针对强国的外交保护和炮舰索债,而现在的卡尔沃主义针对的则是国际投资仲裁对东道国主权和政策空间的侵犯。此外,需要注意以上所列各国复活卡尔沃主义的程度是不同的。
三、卡尔沃主义何以复活 表面看来,卡尔沃主义在拉美国家、澳大利亚及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复活的原因并不相同。在拉美,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危机的发生将东道国拉入投资者—国家仲裁的深渊,惹怒了这些国家,而这种仲裁本身又存在诸多不正当性和不合理性。在澳大利亚及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主要是因为国家的规制权受到国际投资仲裁的威胁和挑战。但实质上,卡尔沃主义复活的共同原因仅在于各国要在新自由主义受到质疑的背景下维护国家的规制权及国际投资仲裁本身存在诸多问题。
(一)经济危机背景下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以拉美国家为例回溯往事,当初拉美国家放弃卡尔沃主义、接受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管辖权并非心甘情愿,这为卡尔沃主义复活埋下了“伏笔”。在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国家反对设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一个拉美国家签署《ICSID公约》,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纷纷签署《ICSID公约》和签订包含ICSID仲裁的BITs。其实这并非出于自愿,而完全是债务危机逼迫的结果。由于发达国家债主开出的条件是债务国接受私有化的安排,签订保护外国投资者的BIT,同时将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提交到ICSID这样的中立机构来解决,作为债务国的拉美国家也不得不顺从,所以,接受发达国家根据“华盛顿共识”开出的“新自由主义”药方,完全放弃卡尔沃主义是被迫的。
自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以来,当外国公司在拉美地区赚取丰厚利润的时候,拉美国家却并没有得到太多好处,外国公司几乎将全部利益盘剥殆尽。越来越贫穷的国家无法实施满足社会需要、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政策,甚至陷入经济危机。因此,到了21世纪初期,南美各国政府又纷纷实施一系列反私有化和反自由化的国有化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根廷政府。截至2013年3月21日,ICSID共受理369起仲裁案件,其中约有36%是针对拉美国家的。总之,拉美国家发现无法自由实施自己的国家政策,即使是为了应对国家危机的政策、为了公共利益的政策。面对也许未曾料想到的不利后果,拉美国家开始“悔不该当初”,试图重新捡回“救命稻草”,即卡尔沃主义。所以,无论是放弃卡尔沃主义,还是卡尔沃主义的复活,新自由主义、债务危机或经济危机似乎都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国际仲裁机制本身的缺陷
卡尔沃主义复活的直接原因是被指责为不公正的ICSID仲裁机制。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多次得到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详细阐述,其认为这些问题已经使国际投资仲裁受到了体制性挑战[16]。
举例来说,在玻利维亚退出《ICSID公约》时,玻利维亚政府对ICSID提出了以下批评:其裁决即终裁,没有上诉程序;缺乏中立性;ICSID的管辖违背了玻利维亚宪法(第135条),其宪法法院已宣布ICSID没有管辖权;只受理由外国投资者提交的仲裁;ICSID的方法不明确,并且是武断的;ICSID不接受公众的外部申诉,仲裁程序不公开;国家的抗辩费用高昂,据统计,每起仲裁需花费400万美元。玻利维亚政府还认为ICSID偏袒跨国公司,若跨国公司没有遵守协定,ICSID没有给予过任何惩罚。归根结底,世界银行促进私有化的职能与其争端解决的职能是格格不入的。在一个仲裁程序中,玻利维亚甚至对全体仲裁员提出了质疑,并指出其将不遵守支持投资者的仲裁裁决[17]。厄瓜多尔总统则公开表示对ICSID没有信心,对ICSID做出公正裁决的能力表示怀疑。这些批评虽有过激之处,但也切中要害。
有学者指出,ISDS条款多规定投资者有权在国内争端解决机构和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间行选择,一旦选择了一种争端解决方式就不能选择另一种,这就是所谓的“岔路口条款”,但投资者去当地化的倾向使他们普遍选择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选择却使国家政策的制定落入几个国际仲裁员的手中,从而导致这一机制缺乏政治上的正当性[18]。一些学者认为,ICSID对发展中国家持有偏见[19]。还有学者指出,投资仲裁是一个“不公平、不独立且不平衡的方法”,因此不应当信赖这一方法,“政府有强有力的道德和政策理由退出投资条约和反对投资者—国家仲裁,包括拒绝支付不利于他们的仲裁裁决”[20]。有学者还针对苏珊·弗兰克通过数量研究方法为ICSID公正性进行的辩护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关于Susan Franck的主要观点,请参见:S. D. Franck. Development and Outcomes of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J].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09,(50):435-489.,该批评指出,研究ICSID的独立和公正,从而证明国际投资仲裁不存在偏见,数量方法虽有重要贡献但却是不充分的,因为ICSID裁决的公开性本身就不充分,因此,这种实证研究在证明有或没有实际偏见方面有严重的局限性,而事实是,发展中国家的确比发达国家更多地受到投资者的国际求偿[21]。最近,律师事务所、仲裁员和金融家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逐利行为更受到了揭露和批判[22]。
出于ISDS的影响和正当性问题,各国正在促进解决投资争端的预防机制和替代机制。完全排斥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国家还试图以区域争端解决机制或国内司法加以取代。在笔者看来,来自国家及学者们的这些批评也许有些过激,区域仲裁设计未必能成功,东道国的国内司法未必完全可以信赖,但它们无疑证明了现有的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谨慎对待。
(三)保留规制权的现实要求
不可否认,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国家争端涉及国家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措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包含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的确会授“投资者”以柄,可能导致国家的规制权无法正常实现,如何保留政府的规制空间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而且,由于国际投资协定中对投资者及其投资的过分保护,投资仲裁启动门槛过低,导致国际投资条约仲裁被滥用。
在笔者看来,卡尔沃主义在澳大利亚复活不但是因为受到拉美等国家“遭遇”的启示,更是因为“治理困境”引起的对国家规制自主权的重视。目前,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资本输出兼输入国。根据《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自2006年至2011年,澳大利亚外资流入量甚至远远超过流出量[12]169。归根结底,在成为资本输出兼输入国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外资政策也将发生相应改变,以便维护自己的主权,预防可能发生威胁到自己主权的争端。以多国已经和将要实行的保护公共健康的控烟政策为例,澳大利亚由于采取控烟政策而被投资者根据澳大利亚—香港BIT提出了求偿。虽然这一试验性案件尚未有结果,但对于澳大利亚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实际上,在投资者提起仲裁之前,澳大利亚政府面临着来自投资者、美国国会议员、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以及美国商会等方方面面的压力。澳大利亚政府无疑希望自己有更大的政策空间来采取规制措施,所以,其《贸易政策声明》第3点明确提出,澳大利亚政府没有也不会接受限制其对烟草产品做出健康警告或“素包装”要求的条款。吉拉德政府采取的在新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去投资者—国家仲裁条款的政策无疑与类似于控烟的规制措施直接有关。归根结底,面对跨国公司和烟草出口国的压力,竭力想为国家保留更大的政策空间。
有的国家虽然并没有表明在其国际投资协定中排除ISDS条款,但是通过对投资者更大的透明度和问责要求,已明显表现出保护国家规制权的倾向。在欧洲议会关于欧盟与加拿大贸易关系的决议中也强调:“要求投资章节尊重缔约双方的规制权,尤其是在国家安全、环境、公共健康、工人及消费者的权利、产业政策和文化多样性等领域;呼吁从投资协定中排除文化、教育、国防和公共健康等敏感部门。”
实际上,对于广大拉美国家,由于大多数案件涉及的也是其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如汇率控制或油气产业的国有化,投资者挑战的也是这些国家的规制权。这些国家之所以决定退出《ICSID公约》,是因为其认为ICSID仲裁侵犯了各国的主权。所以,各国普遍提高对政策空间和规制权的重视程度,为卡尔沃主义的复活创造了主观条件。
以上是卡尔沃主义复活的主要原因,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卡尔沃主义的复活并不意味着强调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彻底失败,更不意味着在现阶段要废除现有的国际投资法体制,我们还应该看到仍有国家在积极地加入《ICSID公约》,很多国家仍在踊跃地签订各种国际投资协定,黑山、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加拿大分别于2013年批准《ICSID公约》,就是典型的例证,但对国际投资协定的内容进行调整无疑是必然趋势。卡尔沃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同时复活也表明,南北矛盾已经不能解释所有现象,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缔结BIT,但其实质仍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缔结的BIT,资本输入国与输出国地位的变化更能说明现实问题。
四、卡尔沃主义复活对中国缔约实践的启示 卡尔沃主义的复活并非空穴来风。为了回避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一些国家取消或完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ISDS条款,修改宪法、法律和合同,甚至退出《ICSID公约》,终止BITs,寻求替代争端解决的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当今国际投资仲裁存在的正当性问题。确实,在已裁决的案件中,存在过于偏袒投资者利益、过分侵犯国家主权的问题。然而,是否因此就退出国际投资体制,而完全回归到国内法或区域法体制?中国的国际投资协定缔约实践应向何处去?说到底,中国该如何对待国际投资法中的这股潮流?
(一)完全回归国内法之不可行
首先,对于那些选择退出《ICSID公约》和/或终止BIT,试图回归到国内法的国家,这种政策并不可取。因为各国政府做出这种选择的目的是解决现实的政策实施问题或者解决因过去的政策在ICSID成为被告的问题。然而,纵观这些国家缔结的各种BIT,大多规定对在该条约终止之日前发生的投资,在条约终止后,该条约将继续保护一段特定的时期,通常为10年或15年。有学者主张,各个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各种限制或取消投资者权利的措施至少在短期内无法产生预期结果,因为BIT包括许多自卫机制,尤其是最惠国待遇义务、默认续订及存留条款,因此,他们主张最好的办法是重新谈判BIT。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倒是合理的,退出《ICSID公约》和/或BIT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仅仅查询委内瑞拉于2012年退出《ICSID公约》声明生效后至今在ICSID的案件就会发现,2012年委内瑞拉被提起了8个案件,是当年被诉最多的国家,而2013年又有一起新案件发生。所以,退出《ICSID公约》并不能保证不在ICSID被诉。拉美国家试图通过退出《ICSID公约》、终止BIT及其他国际投资协定来实现排除ICSID管辖的目的,但这一目的暂时无法实现。
对于完全采用国内法的做法,有许多现实问题无法解决。巴西是采用国内法的典范,其确实仅通过国内法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但因有庞大的消费者市场、高经济增长率和自然资源禀赋,2011年巴西依然是外国投资者在南美投资的最大目的国,其中外国投资的流量增长了37%,达到670亿美元,占整个南美外国直接投资的55%[12]53,171。因此,“巴西模式”被一些学者所称道,并因此主张国内保护可以替代国际保护。然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具有资源或市场优势来吸引外资,即使有资源或市场优势吸引外资,安全保障永远是外资的第一需要。而且,不容否认的是,巴西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2011年下降了10.29亿美元,巴西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整体趋势也是下降的[12]171。相比之下,巴西仍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所以,笔者认为,在巴西主要还是一个资本输入国时,其可以依靠其他优势来吸引外资。但是,巴西并不能保障国外投资地也具有巴西的各种条件,因此,没有保护其海外投资者的国际投资协定,可能会阻碍其海外投资的发展,这可能也是巴西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整体上呈下降趋势的重要原因。
在完全回归国内法的情况下,有人主张通过将习惯国际投资法并入国内法的方法来实现国际投资法的保护功能,但是,对于何谓习惯国际投资法,并不存在一致的看法。其次,即使国内法的规定与国际投资协定的保护完全一致,或者说将国际投资法的规定纳入国内法,但司法与立法并不一定能保持一致,完美的立法却可能缺乏公正及时的执法和司法保障。为促进和保护海外投资,有人建议在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合同中约定仲裁方法,但鉴于投资者与东道国实力的不对等,东道国未必会接受这种约定。还有人主张通过由投资者进行“条约选购”或“国籍设计”的方法来利用其他国家间的国际投资协定,然而,为了避免第三国投资者“免费搭车”,现代的国际投资协定大多已经增加了“拒绝授惠”条款,即规定如果一个企业是由非缔约方的国民或企业拥有或控制,且如果该企业在缔约另一方境内未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则缔约一方可拒绝给予缔约另一方的企业及其投资以该条约项下的利益。因此,“条约选购”或“国籍设计”的方法已很难行得通,“条约选购”或“国籍设计”不但增加了投资者的成本,而且代替不了国家层面的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完全回归国内法不利于一个国家保护其海外投资者,从而不利于扩大其海外投资。
(二)完全依赖区域司法或仲裁中心之不可取
各国所可能选择的所谓区域组织司法或仲裁中心,其效率并不高,甚至前途未卜。如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法庭,于1992年根据《SADC条约》第9条设立,正式建立于2005年,于2007年开始审理案件。在SADC法庭审理的Mike Campbell案中,法庭于2008年裁决津巴布韦政府征收原告农业用地违法,其应该给予原告公平的补偿。参见:Mike Campbell (Pvt) Ltd and Others v. the Republic of Zimbabwe,SADC(T) Case No 2/2007.该案曾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津巴布韦政府却以裁决违反其宪法和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只有SADC峰会有权对津巴布韦进行制裁,但其却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制裁措施。虽然SADC法庭曾有权受理SADC内的自然人或法人与SADC成员国间的争端,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其效率低下,且无法得到执行。在针对津巴布韦政府做出几个裁决后,法庭事实上在2010年的SADC峰会上被解散。2012年8月17日,SADC峰会做出决定,认为应当经磋商形成一个新的法庭,而其得到的授权应当限于国家间有关《SADC条约》和议定书解释的争端。
再如,2009年7月,在美洲国家组织第39届大会上,厄瓜多尔外交部部长提议在南美国家联盟(UNASUR)建立新的投资仲裁中心来取代ICSID,以使拉美国家摆脱外国势力的干涉。2010年12月1日,南美国家联盟成员国外交部部长一致决定由厄瓜多尔负责组织争议解决中心的工作。之后,厄瓜多尔向联盟递交了组建区域性调解和仲裁中心的草案,根据该草案,仲裁中心的受案范围不仅包括投资争议还包括任何需要中心帮助的纠纷。中心受理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中心设置前置调解程序,根据法理或判例仲裁。中心仲裁并不排斥主权国家所主张的公共政策原则,仲裁裁决将创立先例制度。咨询委员会将提供法律指导、技术支持和研究,特别是投资纠纷的研究和法律支持。仲裁中心在初期只受理UNASUR成员国间的争议,在中期可以受理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争议,最后将向所有愿意适用该仲裁中心的国家开放。在管辖权的范围方面,首先,除非有关条约或合同中有明确的相反规定,草案的第3(2)条限制了中心的管辖权,排除了涉及健康、教育、税收、能源、环境的争端;其次,草案的第3(3)条规定,根据中心规则设立的仲裁庭对涉及UNASUR成员国内法的争端没有管辖权;最后,草案的第3(4)条和第6(1)条还规定,各国可以要求将用尽国内司法和行政救济作为同意仲裁的前置条件。
可以说,草案表明,UNASUR仲裁中心意在克服ICSID的各种缺陷,而且,为了不对各国的主权构成过大冒犯,中心对自己的管辖权进行了极大的自限,这使仲裁中心对投资者的有用性非常有限。而且,在笔者看来,其设计虽然完美,试图克服ICSID的一切问题,但过于理想化,实施起来绝非易事。时至今日,UNASUR的各成员国尚未批准UNASUR仲裁草案。一个裁决制度的形成和完善并非朝夕之功,建立一个全新的区域仲裁中心,更是任重道远。
总之,保守的国家主义方法及不成熟的区域主义方法并不能完全取代现有的国际投资仲裁方法,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三)排除投资者—国家争端条款方法适用之有限性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于2011年2月16日签订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议定书》不包含ISDS条款。对于其没有包含这种条款的原因,新西兰的议会委员会指出,当事方之间的争端更有可能通过磋商而不是仲裁的方式得到满意的解决,同样,没有强制性的ISDS条款也反映了更紧密关系的独特性和长期性,以及两国对彼此完善的司法制度的高度认可。
同样,欧盟与加拿大之间投资协定的新近动态与走向也以“各方都有健全的法律体系”或对司法独立的相互信任为基础。在欧洲议会关于欧盟与加拿大贸易关系的决议中明确提出:“……鉴于加拿大和欧盟高度发达的司法制度,国家和国家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及使用当地司法救济是更合适的处理投资争端方法。”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n EU-Canada Trade Relations,B7 0000/2011,RE\8639 27EN.doc,PE460. 791v02-00.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放弃ISDS条款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其适用范围有限。所以,UNCTAD在其《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IPFSD)中建议在缔结国际投资协定时,要清楚地区分两种情况:“根据东道国行政和司法体制的质量,选择‘不包含ISDS条款或选择设计争端解决条款以使ISDS条款成为最后救济手段。”[23]
(四)中国的政策选择
对于现行国际投资仲裁中存在的问题,如案件增长过快、仲裁员倾向于进行扩张性解释、裁决赔偿金额过高、缺乏透明度、法律推理不具有说服力、裁决前后矛盾、仲裁员不能秉持公正等问题,中国不应视而不见,而应该积极提倡改革。实际上,面对各种指责和非难,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也在进行各种改革。例如,因为求偿人在发起国际仲裁之前没有充分寻求当地救济,几个仲裁庭据此拒绝了他们的求偿。
积极提倡改革不公正的国际投资仲裁体制,即意味着中国应支持ISDS条款。尤其是对于那些国际声誉欠佳、不尊重投资者权利或政治不稳定的国家,与其签订包含ISDS条款的国际投资协定更有必要。例如,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东道国有征收的权力,但要辅之以补偿等合法性要件,但在津巴布韦2005年的宪法修订中却允许政府没收或征收私人农业用地而不予以补偿,并且禁止法院裁决投资者提出的任何法律挑战。
笔者的政策主张是有现实依据的,根据《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从2006年到2011年,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分别为:211.6亿美元、265.1亿美元、559.1亿美元、565.3亿美元、688.1亿美元和746.5亿美元[24]。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正在逐步演变为一个重要的直接投资输出经济体。而且,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的海外投资将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期望在中国缔约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排除ISDS条款,是不现实的。
对于一个资本输出国而言,在投资条约中完全排除ISDS条款并不是一个理性选择,因为ISDS机制毕竟能为一国保护其海外投资起到理论上的震慑作用或现实中的保护作用。举例来说,在2007年10月厄瓜多尔政府对外国石油企业征收暴利税时,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因在厄瓜多尔有重大投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它们曾打算提请国际投资仲裁,但如果没有ISDS机制可以利用,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利益就很难通过法律途径得到维护。再例如,澳大利亚是中国重要投资目标国,从单个国家来看,澳大利亚是中国海外投资者最感兴趣的国家。然而,如果现在有中国投资者和澳大利亚政府发生投资争端,鉴于中澳BIT的规定,只能将涉及征收补偿额的争议提交ICSID仲裁,而无法将所有的投资争端都提交ICSID仲裁。在中国与澳大利亚磋商修订1988年签订的BIT时,中国强烈要求保留ISDS条款,而澳大利亚的态度则截然相反,所以,将来在澳大利亚投资的中国海外投资者甚至不能将任何投资争端提交国际投资仲裁。还有,秘鲁取消了所有的私人开矿许可证,中国—秘鲁BIT无疑会对中国在秘鲁的投资起到保护作用。所以,完全接受卡尔沃条款,尤其是在与发展中国家签订国际投资协定时,并不是明智之举。现行的国际投资法体制无疑有利于目前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另一方面,实践表明,BITs由有到无会严重影响外资的流入。以南非为例:南非逐步取消第一代BITs的现实后果是2011年其外资流量的负增长。对此,《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直言:南非在2011年吸收到的外国直接投资比预期要少,根据其经济因素,其应该吸引到更多的投资,原因或者在于南非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了封闭的态度,或者在于其维持着一种对外国投资者没有吸引力的政策氛围[12]31-32,161-162。所以,不能否认,取消BIT传达的负面信息会影响外资的流入。回顾历史,只有“与征收的补偿额有关的争端”才可提交国际投资仲裁庭是1984年中国BIT范本、1989年中国BIT范本及中国签订的第一代(1982年至1989年)和第二代(1990年至1997年)BIT中采用的典型规定方法[25],体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对国际投资仲裁的保守态度。在20世纪80-90年代末中国与外国签订的BIT中,有关ISDS的条款对ICSID仲裁的程序也有严格限制,即保留“逐案审批同意权”和“当地救济优先权”。
中国的第三代BIT,即约1998年后签订和修改的BIT普遍包含投资者可以无条件地将其与国家间的一切争端提交国际投资仲裁,尤其是ICSID仲裁的条款,几乎没有附加条件限制。第三代BIT与中国1997年BIT范本是一致的。首先是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任何争端均应通过友好磋商加以解决,如不能在6个月的友好磋商期内解决争端,则投资者可选择东道国法院或ICSID,东道国可要求投资者用尽当地行政救济。在东道国国内法院与ICSID之间,投资者只能选择其一,此即岔路口条款。准据法为东道国的国内法律,该BIT以及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并无先后顺序之分。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为吸引外资表现出的一种重要姿态,这与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也是高度一致的,无疑会起到保护中国海外投资的作用。但就此类ISDS条款而言,无论是“任何争端”,还是投资者必然选择诉诸ICSID的岔路口条款,显然放权过大,也遭到了中国权威学者的批评[26]。
2010年中国BIT范本是中国缔结新一代(第四代)BITs的依据,其第13条对投资者—国家投资争端解决增加了一些限制:对仲裁庭的管辖范围进行了限制,排除了对拒绝授惠条款和税收条款引发的争端管辖权,此外,还增加了3年诉讼时效的限制;在准据法方面,强调争端方的意思自治,如争端方没有选择法律,则仲裁庭应适用作为争端缔约方的法律(包括冲突规范),以及可适用的国际法规范,尤其是BIT;在费用方面,对轻率的申诉或异议规定了惩罚机制。此外,根据该范本第4条,投资者不得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援引其他协定中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相比之下,该范本的规定对投资者的权利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
笔者认为,无论是国内法律制度还是国际法律制度都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当其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时应该接受,但当其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时,从理性的角度看,可以对其予以修改或放弃。鉴于退约的重大负面影响,尤其是退出公约会被多国视为敌对行为,引起较广泛的后果,退约行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显然并不是明智选择,中国的经济现实决定了中国也没有必要做出此种消极选择,恰恰相反,中国应该是现行国际投资法体制的支持者和改良者。
但是,笔者建议在缔结条约之时要全面审慎考虑,要重视所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的每一个条款。非常清楚,国际投资协定限制了政府的行为,政府不得不承担国际投资协定下“强制的争端解决程序”可能产生的不利裁决,并支付巨额赔偿。而且,最重要的也许并不是因为要支付赔偿,而是国家的公共利益和重要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因为中国兼具资本输入国与输出国身份,而且目前仍以前一种身份为主,所以,ISDS条款对中国政府无疑也会起到约束作用。目前已经有了第一起外国投资者针对中国政府的ICSID案件参见:Ekran Berhad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CSID Case No. ARB/11/15.,虽然这起案件由于原告的情况而不具有典型性,然而,笔者担心,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如同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一样,中国政府的规制措施在国际投资仲裁机构也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在未来的国际投资协定中,除了缔约对象是那些明确表示全面放弃ISDS条款的国家以外,普遍包含ISDS条款是中国的必然选择。现行国际投资法的“牙齿”即在于ISDS机制。但笔者主张应该在“逐案的基础上”进行国别考虑,仅仅区分两类国家是不够的,还应在此基础上区别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的身份。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虑,不同的国际投资协定毕竟是特殊利益的体现,是国家间政治与经济实力较量的结果,所以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举例来说,在与主要作为我国自然资源投资地的国家签订国际投资协定时,涉及自然资源的争端应尽量不被排除在ISDS之外,否则,我国与其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将没有实质意义。反之,在与那些主要对我国进行自然资源投资的国家签订国际投资协定时,应该尽量将此类争端的管辖权保留在自己手中。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和第266条的规定,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引起的纠纷应当专属于中国法院管辖。然而,中国签订的很多国际投资协定同意将所有投资争端交由ICSID管辖,这不但会产生管辖冲突的危险,还会使国家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即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受到损害,因此,应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将关于履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引起的纠纷排除在国际仲裁之外。
笔者主张针对中国和缔约对象彼此投资的现实情况来考虑ISDS条款和排除条款的具体设计。如果在“逐案的基础上”考虑如何在国际投资协定中设计ISDS条款,明确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适用于程序事项将具有重大意义。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涵盖程序事项与本论文的关联在于:如果最惠国待遇原则涵盖程序事项,则即使母国与东道国的投资条约中不含有或包含不同的ISDS条款,投资者仍然可能援引母国与东道国的投资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和东道国与第三国的投资条约中包含的“更有利”的ISDS条款而将争端诉诸国际仲裁。自赞成最惠国待遇条款涵盖程序事项的Maffezini案开始参见:Emilio Agustin Maffezini v. Kingdom of Spain,ICSID Case No. ARB/97/7.,由于ICSID本身的判例前后矛盾,最惠国待遇是否适用于程序事项就成为备受争议的问题。因此,依赖司法或仲裁实践来结论性地解决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适用于程序事项,在目前看来是不可取的。因此,笔者建议,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明确规定其最惠国待遇条款不允许输入其他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是最可行的,即将最惠国待遇条款仅仅限于实体保护,排除将其适用于争端解决程序。这种规定在立法层面澄清了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简洁明了地切断了有关条约与东道国签订的其他投资协定的联系,可避免投资者规避东道国国内管辖、挑选争端解决条款,从而违背东道国意志的情况。
总体上,对于ISDS条款,应该有较详细的规定。首先,最主要的是应当对仲裁范围设限,只将某些条款项下的义务划入可授权国际仲裁庭裁决的范畴,至于环境与劳工保护、拒绝授惠和根本安全例外等内容,则不应当允许外国投资者寻求国际仲裁救济,从而限制外国投资者可诉诸国际仲裁的范围。实际上,现代化的国际投资协定还通过澄清条约范围,引入一般例外条款、自裁决条款、传统国际收支例外条款及金融例外条款,澄清特定责任,如公平公正待遇和间接征收的范围,来限制国际仲裁机构的管辖权。其次,对于岔路口条款,为避免外国投资者滥用平行程序,可借鉴美国2012年BIT范本第26(2)(b)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只有当其和其在东道国所投资或控制的企业皆书面表示放弃在东道国寻求当地救济后,方可寻求国际仲裁,这是控制滥诉的一种非常简洁的办法。再次,为防止投资者滥用其他国际投资协定中“更优惠”的争端解决条款,还应明确最惠国待遇条款不适用于争端解决程序。最后,保证仲裁程序有一定程度的透明度以及仲裁员的选择等内容,都应予以规定。
结论 ISDS条款已经成为国际投资协定中最有争议的条款之一,也是国际投资协定遭到反对的原因之一。在程序意义上,卡尔沃主义归根结底旨在排除或限制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权。晚近在拉美国家、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及美国等国家出现的对ISDS机制不同程度的排斥和反思,正是卡尔沃主义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复活的表现。这必将对中国的海外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重要目标国既有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厄瓜多尔和秘鲁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有南非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卡尔沃主义不同程度复活的情况下,中国应反思自己的国际投资法律政策,因为中国同样面临着一个正当性受到质疑的国际仲裁机制,中国也存在保留规制权的现实要求,同时,中国的海外投资又需要中国政府通过国际投资协定加以保护。
卡尔沃主义不同程度的复活虽然对现行国际投资法体制提出了挑战,但并不是主流。完全否定现行国际投资法体制并不可取,中国没有不支持现行国际投资法体制的理由,因为这种体制总体上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决定着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即总体上接受并主张改良现行国际投资法体制。作为国际投资协定中最重要的程序条款,投资者—国家仲裁使国际投资法有了“牙齿”,并成为实现其他实体权利的保障。如果没有这一“牙齿”,再好的国际投资法也可能无法得到真正实施。当然,对于国际投资仲裁体制,要积极推动其变革,包括限制投资者滥诉、限制仲裁庭进行扩张性解释、提高裁决的推理水平和解释水平,限制对投资者的巨额补偿、增加仲裁透明度、要求仲裁员秉持平衡投资者与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保护投资利益的观念,等等。
现实的形势是:很多国家都在对以保护投资者为基本目的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重新审查和修订,这些审查和修订寻求在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尤其包括预防赋予投资者特权的投资者—国家仲裁对国家主权的不利影响。如果说卡尔沃主义的复活标志着国际投资法发展方向的调整,尤其是发达国家对自己发明创造的ISDS机制亦有所怀疑和顾忌,中国亦应认真对待这种变化。ML
参考文献:
[1] 单文华.卡尔沃主义的“死亡”与“再生”——晚近拉美国家对国际投资立法的态度转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经济法学刊,2006,13(1):183.
[2] Wenhua Shan.From North-South Divide to Private-Public Debate: Revival of the Calvo Doctrine and the Changing Landscap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J].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2006-2007,27(3):631-664.
[3] Bernardo M. Cremades.Resurgence of the Calvo Doctrine in Latin America[J].Business Law International,2006,(7):53-72.
[4] 王铁崖.中华法学大辞典(国际法学卷)[K].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329.
[5] Donald Shea.The Calvo Clause: A Problem of Inter-American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55:19-20.
[6] Roger C. Wesley.The Procedural Mala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Disputes in Latin America: From Local Tribunals to Fact Finding[J].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1975,(7):818.
[7] Pedro Roffe. Calvo y su Vigencia en América Latina[M].Revista del Derecho Industrial,1984:356-357.
[8] Kenneth J. Vandevelde.Sustainable Liber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J].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8,(19):379.
[9] JD Mortenson.The Meaning of “Investment”: ICSIDs Travaux and the Domai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J].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10,(15):313.
[10] ICSID.Bolivia Submits a Notice under Article 71 of the ICSID Convention[N].Press Release,2007-05-16.
[11] Denunciation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and BITs: Impact on Investor-State Claims[R].IIA Issues Note,No. 2,2010.
[12]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2: Towards a New Generation of Investment Policies[R].New York and Geneva,2012:87.
[13]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Gillard Government Trade Policy Statement: Trading Our Way to More Jobs and Prosperity,Investor-State Dispute Resolution[EB/OL].[2013-04-01].http://pdf.aigroup.asn.au/trade/Gillard%20Trade%20Policy%20Statement.pdf.
[14] Luke R. Nottage.The Rise and Possible Fall of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in Asia: A Skeptics View of Australias “Gillard Government Trade Policy Statement”[R].University of Sydney - Faculty of Law,University of Sydney - Australian Network for Japanese Law,2011.
[15]Speech Delivered by the Minister of Trade and Industry Dr Rob Davies at the South African Launch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EB/OL].(2012-07-26)[2013-04-01].http://unctad.org/meetings/en/Miscellaneous%20Documents/South-Africa-Investment-statement_Rob_Davies.pdf.
[16]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0: Investing in a Low-Carbon Economy[R].New York and Geneva,2010.
[17] Sebastian Perry.Bolivia Ramps up Anti-ICSID Rhetoric[EB/OL].(2010-07-14)[2011-06-07].http://tinyurl.com/6hf5cja.
[18] Gus Van Harten.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Public Law[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9] Christian Tietie,et al.Once and Forever? The Legal Effects of a Denunciation of ICSID[J].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2008,(6):5.
[20] Gus Van Harten,et al.Public Statem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EB/OL].(2010-08-31)[2011-07-02].http://tinyurl.com/37b2ktl.
[21] Kevin P. Gallapher,Elen Shrestha.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Appraisal,Glob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R].Working Paper No. 11-01,Tufts University Medford MA 02155,2011.
[22] Helen Burley.Profiting from Injustice: How Law Firms,Arbitrators and Financiers Are Fuelling a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Boom[R].Brussels/Amsterdam: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and th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2012.
[23] UNCTAD.Investment Policy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B/OL].[2013-06-11].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Views/Public/IndexIPFSD.aspx .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5.
[25] Norah Gallagher,Wenhua Shan.Chinese Investment Treaties: Policies and Practic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35-40(Appendices).
[26] 陈安.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四大“安全阀”不宜贸然拆除[J].国际经济法学刊,2006,13(1): 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