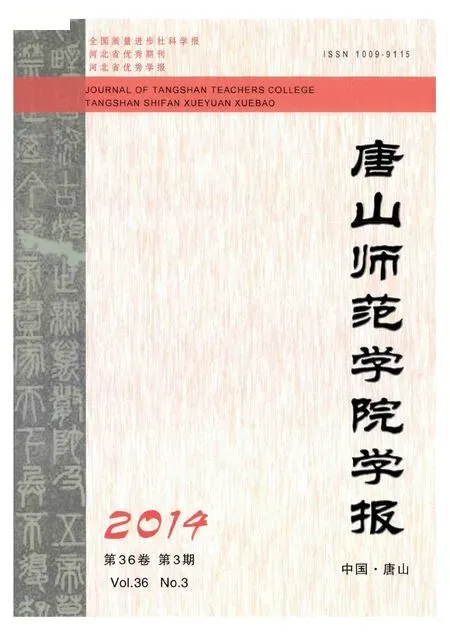国共两党敌后抗战的差异
黎世红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重庆 400065)
国共两党敌后抗战的差异
黎世红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重庆 400065)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都在抗战中起到积极作用,但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导致两党敌后抗战的结果迥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两党阶级本质的不同。
抗日战争;共产党;国民党;敌后游击战
近年来,学术界有关国民党敌后抗战的研究取得积极进展。国民党在沦陷区组织敌后游击战的问题逐渐得到公认。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共两党敌后抗战的差异也逐渐显现出来。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导致两党敌后抗战的作用和结果大相径庭。共产党在敌后抗战中依靠民众的支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力量得到发展和壮大。国民党在敌后抗战中脱离民众,依靠正规军,实行错误的游击战术,导致敌后游击战的失败。国共两党在敌后抗战中的差异反映了两党阶级本质的不同。
一、认识上的差异
国共两党对敌后游击战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差异。共产党较早认识到游击战在抗战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游击战理论要比国民党成熟得多。共产党军队在十年内战中长期以弱对强,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在抗战开始前,中共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中日战争的特点和游击战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游击战争应在全国发展起来”,“一切游击队应以民族战争的面目而出现”,“要使游击战争在反日反卖国贼的战争中担负起战略上的伟大作用”[1]。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迅速确定了敌后游击战的指导方针。1937年8月1日,毛泽东、洛甫《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要求红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2,p297]。8月下旬,洛川会议确立了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9月25日,毛泽东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2,p339]。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对敌后游击战的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为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提供了理论指导。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游击战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性。他说: “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3,p552]
国民党军事当局虽然在抗战爆发前也曾提出:“作战时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4]但这只是从正规战与游击战不能截然分开的角度提出了以游击战牵制敌人,并没有认识到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地位。国民党的军事理论来自西方正规战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国民党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主力部队与日军的正规战,寄托于国际干预。因此,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主要依靠主力部队在正面与日军拼消耗,淞沪会战、忻口会战都是这样的战例。但这恰恰让敌人的优势得以发挥,结果是防御失败,丧师失地,主力损失惨重。长此下去,对中国军队无疑是很不利的。随着正面战场的不断失利,国民党才认识到中日双方的差距,“以劣势的装备,光是同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争胜负,一定得不到很好的结果”[5]。1937年11月,蒋介石认识到:“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6]这说明淞沪会战和忻口会战的教训促使国民党重视游击战。12月13日,军委会在武汉拟定新的作战计划:“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7]在汉口军事会议上,白崇禧提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8,p352]。会议第一次决定把敌后游击战作为一种抗战策略。从徐州会战开始,国民党已经注意发挥游击战的作用。1938年4月15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指示速派正式军队到大岘山附近与新泰、莱芜建立根据地并实施游击。”[9]在徐州会战期间,第五战区在山东和江苏都部署了游击战以配合正规战。第一次南岳会议决定在沦陷区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设立敌后游击战区,把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一部署在沦陷区。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之训示”[10]。会议对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作出相应的部署。
由此可见,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早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地位。共产党在抗战开始前就认识到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作用”。洛川会议从战略高度作出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决策。国民党在1937年11月以后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在汉口会议上作出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决策。由于国民党对游击战的理论认识落后于共产党,国民党开展游击战的时间也晚于共产党。共产党军队开赴前线后就开始实行游击战,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而国民党军队在徐州会战中才开始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在武汉会战中继续实施游击战,均取得积极效果。第一次南岳会议后,国民党从全局上部署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
在敌后游击战与正面战场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主张敌后游击战与正面战场在战略上是统一的相互配合的关系,但在战役和战术上是相对独立的。毛泽东强调敌后游击战在战役和战术上独立自主,灵活自如,不受正面战场的约束。1937年8月1日,毛泽东、洛甫《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明确要求红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2,p297]。
而国民党强调敌后游击战对正面战场的配合作用。在抗战初期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相持阶段的多次战役中,国民党军事当局都强调敌后游击战与正面战场配合作战。虽然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强调敌后游击战与正面战场的统一,不无道理,但这样也会导致敌后游击战处于正面战场的从属地位。从全国战略布局来看,在第一次南岳会议后,国民党把敌后游击战放在了全国战略总体布局中。山西、河北、山东、江苏、鄂豫皖、湘鄂赣、浙西的敌后根据地在全国的战略部署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战略角度讲,敌后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组成全国一盘棋,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国民党要求敌后游击战与正面战场不仅在战略上配合,而且在战役和战术上配合。白崇禧在汉口会议也是“于战术上”提出“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8,p352]。因此,国民党敌后军队不能独立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仍然没有把敌后游击战放到共产党那样的战略高度。
二、实践上的差异
认识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党敌后游击战在实践上的差异。首先,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的依靠力量不同。共产党开展敌后游击战依靠军队和民众相结合。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沦陷区后,分兵到各地农村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逐步建立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体系。自卫队和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武装组织。共产党通过建立自卫队和民兵组织实现对群众的武装。地方军和庞大的人民武装为主力部队的补充提供了保障。主力军“遇有损失应加补充时,须由自卫队、民兵、地方三方面酌量动员抽补,以维持相互间应有之比率为原则”[11]。因此,共产党军队即使在战斗中遭受较大的损失,也不至于溃散,甚至能较快恢复战斗力。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主要依靠正规军,集中主力作战,忽视群众的力量。正规军是主力部队撤退时留在敌后或者派到敌后的。何应钦说:“担负游击战之主要部队,仍为开入沦陷区之正规军,并非依赖民众组合之游击队”[12]。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从正面战场撤退时,在沦陷区留下正规军开展游击战。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冀察战区的正规军有第97军(朱怀冰)、第69军(石友三)、新5军(孙殿英),苏鲁战区的正规军有第51军(牟中珩)、第57军(缪澂流)、第89军(韩德勤)。在山西,国民党正规军共15个军在抗战初期太原失守后即全部转入游击战。武汉失守后,廖磊率第21集团军进入大别山区开展游击战。正规军在沦陷区并未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虽然黄绍竑在浙西根据地建立了民众自卫团,廖磊在大别山根据地仿效广西建立民团,河北、苏鲁等地建立了保安部队、游击队,但都没有大规模武装群众,而且国民党害怕群众被武装起来后难以控制。由于正规军没有与当地群众相结合,缺乏补充力量,一旦主力被日军打垮,就意味着敌后游击战遭到失败。
其次,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不同。共产党军队与民众关系良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确立了全面抗战路线。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p511]朱德说:“如果抗日游击队不能团结群众、维护群众利益,不能使群众成为游击队的良好依托,那么,这样的游击队将会没有出路。抗日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在水中才能生存和长大,抗日游击队有了群众依托才能生存和长大。”[13]郭化若在《游击战争战术上的基本方针》一文中说:“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特殊形式的战争,因此,它需要广泛地发动群众。”[14]而国民党军队脱离民众,掠夺老百姓。国民党当局也曾要求“游击队应爱护民众,并组织而训练之,使由亲近而信仰而合作,积极的参加作战,消极的不为敌用,俾可争取民众,而发动全面战争”[15,p2],但国民党在沦陷区的政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地方官贪污腐化。李品仙在大别山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阎锡山在山西发行“晋钞”。沈鸿烈在山东发行印刷质量很差的纸币“大花脸”。沈鸿烈、秦启荣纵兵抢掠,“游安全之区,击无辜之民”,甚至“勾结日寇,鱼肉百姓”[16]。国民党军队掠夺老百姓的本性暴露后,逐渐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再次,国共军队在游击战术上存在差异。共产党军队在红军时期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掌握了比较成熟的游击战术。共产党军队按照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善于实施内线中的外线作战,防御战中的进攻作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把握战斗中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避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避免陷入阵地战,避免于我不利的决战。
国民党军队接受正规战的战术教育和训练,游击战术水平低,战术不够灵活。在敌后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以阵地战和运动战为主,没有发挥游击战的优势。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开始学习共产党的游击战术。白崇禧、胡宗南、关麟征等都提出向共产党军队学习游击战术。1939年2月,国民党在湖南南岳成立游击干部培训班,蒋介石兼任主任,共产党派出30多人在培训班担任教官等工作,叶剑英担任副教育长。在一些战区和部队中,也有学习共产党军队游击战术的培训班。在山西开展游击战的第47军军长李家钰曾派人到八路军中学习游击战术,并在平陆县槐树庄举办游击干部培训班。为了加强对游击战的战术指导,白崇禧主持军训部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军事学校作为教材。《游击战纲要》也曾提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攻虚,乘敌不意,出奇制胜之妙诀”[15,p33],但国民党军队在实战中不能摆脱正规战的束缚。国民党军队在与日军主力交战时,照搬正面战场的战法,过于强调固守阵地,不善于化整为零,不善于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摆脱敌人,不善于“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3,415],游击战变成阵地战,失去了游击战的本意。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鲁南、河北的失败都与战术上的错误有关。
最后,国共两党敌后根据地建设存在差异。共产党从国共内战时期的经验出发,特别注重根据地建设。毛泽东指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3,p418]共产党军队深入沦陷区后,分散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政权,包括代表民意的参议会。共产党军队依托根据地,贯彻人民战争的思想,与日军开展游击战。“以根据地为依托向外渗透和扩张,这是中共在关内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17]共产党注重根据地的保守和坚持,决不轻易放弃根据地。对共产党军队来说,没有大后方,根据地就是后方。无论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多么残酷,八路军、新四军都会坚守根据地。在形势不利时,共产党军队可以避开与强敌的交锋,即使暂时撤出阵地,也会重新打回来,而共产党的武装体系也有利于根据地的坚守。
国民党军队缺乏根据地建设理论,没有把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更谈不上武装群众。《游击战纲要》提出:“游击队根据地,为机动战之策源,持久战之堡垒。”[15,p15]但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政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地方官甚至贪污腐化,掠夺老百姓。没有民众的支持,就不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在保卫根据地时,比较注重与强敌的阵地战。卫立煌部、庞炳勋部、于学忠部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都没有依靠人民的支持。国民党主力缺少补充力量,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遭到惨重损失后,根据地就会丧失。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失去后,多数没有夺回来,如山东、河北、中条山等。只有大别山根据地在主力尚存的情况下,一度失去后又重新夺回来。
三、结局上的差异
国共军队在敌后抗战中的结局完全不同。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抗战初期,共产党军队仅4万多人。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发展到15万余人。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50万人,建立了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10多块。经过8年抗战,共产党军队发展到120万人和200万民兵,根据地人口近1亿。
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抗战中不断遭到失败。抗战初期,在沦陷区的国民党军队达到60万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沦陷区的军队最多时达到100万人,但多数遭到失败。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抗战中的结局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坚持敌后游击战,直到抗战胜利。黄绍竑领导的第三战区浙西根据地,廖磊和后来的李品仙领导的第五战区大别山根据地,阎锡山领导的第二战区吕梁山根据地等坚持到抗战结束。第二,被日军打败,或撤退,或投敌。第二战区中条山根据地卫立煌部被打垮后,有的溃散,有的撤退。冀察战区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战败后投敌,充当伪军。中央军刘进第27军战败后退出河北。战区仅高树勋部保存下来,但战败后退到皖北涡阳,战区名存实亡。苏鲁战区鲁南根据地于学忠部被日军打垮后,撤出山东。苏鲁战区被撤销。第三,在国共磨擦中被打垮。在沦陷区的国共磨擦中,冀察战区石友三部损失惨重,苏鲁战区韩德勤部、冀察战区朱怀冰部损失殆尽。由于国民党在沦陷区的游击战不断遭到失败,而蒋介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美国援助,也不再重视敌后游击战,因而不断缩编敌后游击武装。到1944年4月,国民党在沦陷区的军队仅剩27万人[12]。
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在抗战中的作用不同。共产党军队最初人数较少,但随着根据地的创建和队伍的壮大,在敌后抗战中逐渐起到主要作用。到1940年春,在华北战场上,“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18]。 1943年8月24日,《解放日报》公布材料证明:共产党军队抗击全部日军的58%,全部伪军的90%[19]。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在抗战初期对于配合正面战场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一度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鄂豫皖等地部署重兵,从战略上牵制日军,但从1941年5月到1943年8月,山西、河北、山东沦陷区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扫荡”下损失惨重,先后失去中条山、太岳山、太行山、鲁南等重要抗日根据地。
在1943年8月以前的相持阶段,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对于配合正面战场依然起到积极的战略作用,但已经不能与共产党军队相提并论。到1943年8月以后,国民党军队仅剩下吕梁山、大别山、天目山等少数敌后根据地,在敌后抗战中的作用已经不能产生全局性的影响。
[1]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41.
[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6-1938) [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上)[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34.
[5] 黄绍竑.五十回忆(下册)[M].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89:626.
[6]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6册)[M].台北:中央日报社编印,1986:60.
[7] 张宪文.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131.
[8] 贾廷诗,等.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9]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第2册)[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258.
[10]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268.
[1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9-1941) [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755.
[12] 唐利国.关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几个问题[J].抗日战争研究,1997(1):189-199.
[13] 朱德.朱德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1.
[14] 陶剑青.游击战术纲要[M].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238.
[15] 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编译处.游击战纲要[M].1939.
[16] 赵万钧.国共两党领导的两种敌后抗日游击战[J].党史文汇,1994(10):19-22.
[17] 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J].抗日战争研究,2006(2):1-32.
[1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216.
[19] 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575.
(责任编辑、校对:郭 静)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Kuomingdang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LI Shi-hong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065,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CPC and the KMT both developed guerrilla war in the Japanese-occupied areas. The guerrilla war of the CPC and the KMT in the Japanese-occupied areas both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b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ed to totally difference in result of the guerrilla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behind enemy lines. The difference reflected clas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parties.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CPC; the KMT; guerrilla war behind enemy lines
K265
A
1009-9115(2014)03-0085-04
10.3969/j.issn.1009-9115.2014.03.022
2013-10-02
黎世红(1966-),男,重庆潼南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