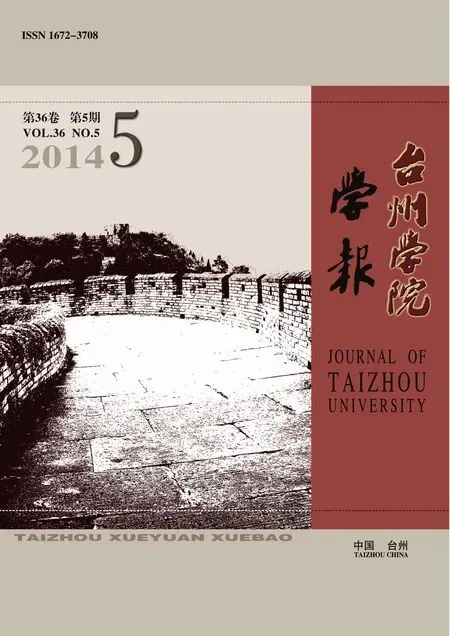花开花谢 情深几许
——《我漂亮的玫瑰树》、《一朵枯萎的紫罗兰》和《水仙》对比解析
李菁菁
(通化师范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部,吉林 通化 134002)
花开花谢 情深几许
——《我漂亮的玫瑰树》、《一朵枯萎的紫罗兰》和《水仙》对比解析
李菁菁
(通化师范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部,吉林 通化 134002)
英国浪漫派诗人长于借自然之象诉内心之情。《我漂亮的玫瑰树》、《一朵枯萎的紫罗兰》与《水仙》分别是浪漫派的起点诗人布莱克、“浪漫骑士”雪莱以及“湖畔派”代表华兹华斯的咏花诗。诗人在诗作中借花言情,借三朵“花”吐露出三种不同的爱情观。玫瑰树诉说了布莱克对爱情的忠贞信仰,他的情感世界是纯真的;紫罗兰寄托了雪莱对亡妻的缅怀,他的情感世界是浪漫的;水仙慨叹的是华兹华斯与爱人相思不得见的孤独,他的情感世界纯真的浪漫与浪漫的纯真兼而有之。
浪漫派诗人;咏花诗;爱情观;情感世界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和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分别代表英国19世纪浪漫派诗歌发展的不同阶段。布莱克是浪漫派的起点诗人[1]1,他将自然之象中蕴含的天真之美写于字里行间,绘于视觉图象之中,令诗中有画境,画中含诗意,开创了“诗”、“画”合一的先河;华兹华斯作为“湖畔派”的重要代表,他将真情实感和自我反思寓于自然风光和平民事物中,用“抒情歌谣”向古典主义诗歌创作法则进行了“浪漫的反抗”,创立了英国浪漫派诗歌理论;新一代浪漫派诗歌领袖雪莱则在自然界的生命之象中预言了革命终将胜利的结局,为诗坛注入了勃勃生机。虽然这三位英国浪漫派诗人诗歌创作的理念不同、诗风各异,但他们游历山水的类似经历使他们在诗作中都长于借自然之象诉内心之情。他们创造性的想像引领着读者穿越有限的客观世界的表象去探寻复杂的情感世界中的真意。
本文选取英国浪漫派诗人咏花诗的代表作——布莱克的《我漂亮的玫瑰树》[1]、雪莱的《一朵枯萎的紫罗兰》[2]与华兹华斯的《水仙》[3]——为语料,以诗歌的创作背景为依据,反溯“三朵花”吐露的三种情感世界。
三首诗的主题同为花朵,但三朵花反照出的“伊人”以及“伊人”各自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布莱克在《我漂亮的玫瑰树》中,表达了他愿与“玫瑰伊人”相伴一生的爱情观。诗中的“玫瑰伊人”就是布莱克的结发妻子,也是他一生惟一的爱人。雪莱在《一朵枯萎的紫罗兰》中,倾诉了他对“紫罗兰伊人”的思念。诗中的“紫罗兰伊人”是雪莱的第一任妻子,雪莱婚后的移情别恋造成了“紫罗兰”过早的枯萎。有别于“玫瑰树”(惟一的爱人)和“紫罗兰”(已故的爱人),那一丛摇曳在湖畔的“水仙花”并不是特指华兹华斯情感世界中某一位具体的女性,而是一位“仙子”。这位“水仙伊人”是华兹华斯的精神伴侣,是抚慰诗人孤独心境的使者。
基于对三首咏花诗的主题及主题关联的宏观把握,下文将进一步对三首诗展开相对独立的微观解读,逐一展现“三朵花”反映的“三个世界”。
一、相守一生的玫瑰树
布莱克《我漂亮的玫瑰树》一诗收录于他的诗
画集《天真与经验之歌》。这首诗并非诗人的经典诗作,但却是反映其情感世界的代表作。诗人以平白的语调讲述了一个看似简单的爱情故事——“有人送给我一朵花,/五月里从没有这样的花。/但我说我有一棵漂亮的玫瑰树,/我就把这朵可爱的花还给他。//然后我去看我漂亮的玫瑰树:/白天黑夜把她好好照应。/但我的玫瑰却嫉妒得掉头不顾;/而她的刺却成了我唯一的欢欣。”[4]100
在这首八行体诗(Octet)中,诗人讲述了自己真实的情感经历。诗中的“我”(作者)已经拥有了“漂亮的玫瑰树”(妻子),然而此时,有人送给我“一朵花”。“我”与“玫瑰树”之间的情感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五月里的那朵花新鲜可爱、唾手可得;玫瑰树虽美,却浑身带刺,需要日夜守护。已经拥有了漂亮的“玫瑰树”就一定要拒绝五月里一朵可爱的花吗?“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我”对“一朵花”和“玫瑰树”截然不同的态度折射出的是布莱克的爱情观——对于爱情应该忠诚不渝、对于爱人应该相守一生。
对布莱克爱情观的深入解读需循迹于诗人独特的个人经历,特别是诗人的情感经历。布莱克生于伦敦的一个小商人家庭,自幼喜欢诗歌。然而迫于贫寒的家境,他的青少年时光是在学习绘画与雕刻中度过的。1772年,15岁的少年布莱克结束了他于绘画学校四年的学习时光,踏上了雕刻学徒的道路。历经七年,22岁的青年布莱克学会了雕版、蚀刻、点刻以及临摹的所有技艺。更重要的是,学徒生涯使他得到人生的历练,使他深入地接触了底层民众的情感。他学会了雕刻,社会的风雨也把他“雕刻”成了一位脚踏实地有鲜明个性的画家诗人。此时,他认识了一位乡村姑娘凯瑟琳·布歇尔(Catherine Boucher,1762-1831),并与她在1782年结婚。纯朴的布歇尔没有读过书,布莱克教她读书写字,并指导她为版画涂色。布莱克的首部诗画集《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1789)与第二部诗画集《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1794)的印刷工作就是他们夫妇二人共同完成的。这期间的种种困苦不仅没有拆散他们,反而使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加坚固。然而,布歇尔只能成为布莱克生活的忠诚伴侣与事业的忠实助手,却无法为布莱克家族绵延子嗣。曾有人建议布莱克:为了绵延子嗣,重建家庭。但布莱克拒绝了这样的建议。
自1782年布莱克与布歇尔结为夫妻至1827年(布莱克逝世)的45年中,布莱克夫妇经历了战争与贫困带来的数不尽的困难,但他们始终同甘共苦、相伴相守一生。“玫瑰树”成了他们忠诚爱情的象征。
二、缅怀昨日的紫罗兰
如果说布莱克情感世界的特点是“纯真”,那么雪莱情感世界的特点就是“浪漫”,这与雪莱“浪漫骑士”的称谓相符。他的情感经历与情感世界的形成,都与他贵族的出身有着密切的关联。雪莱于1792年出生于英国苏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富裕的家境,使他青少年时代的光阴能在萨昂学校、伊顿公学与牛津大学度过。这也促成了他与“紫罗兰”相恋的一个机会。
1810年,年仅18岁的雪莱爱上了还在中学读书的15岁的哈莉特,并向哈莉特表达了倾慕之情——“啊!那拱廊般的绿树浓荫下,/静卧在泉水上的月光恬美,/低声飘拂着的和风使人陶醉,/隐约可见的远山景色妩媚。//而更美的是你含情的话语声,/在夜静时刻仿佛尚未消失,/那时间虽已过去!亲切记忆,/必将永存在你珀西的心里”。“他爱你,如此真诚的一颗心/对你的爱,哦,永无尽期”(《歌——致哈莉特:“啊!那拱廊般的绿树浓荫下”》,1810,8)。[2]时至1811年,雪莱因刊行《论无神论的必然性》一文而遭牛津大学开除,他与哈莉特的相爱也受到家庭的反对。为了爱情,19岁的雪莱与16岁的哈莉特私奔了。婚后的雪莱曾向他的妻子深情地倾吐衷肠——“永远像现在这样闪耀着爱和美德,/愿你不会枯萎的灵魂不停地燃烧,/愿你的心永远泛溢着那些纯洁的/使我不得不及时热烈响应的思想”(《十四行片段:致哈莉特》,1812,8)[2]626。181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初为人夫又初为人父的雪莱是那样兴奋——“我爱你,宝贝!因为你实在可爱,/浅浅的酒窝,蔚蓝色的眼睛,/你温柔的躯体,软弱得动人,/能在最冷酷的心里把爱唤醒;/但是,当你睡熟你母亲俯下身来/把你抱进她时时警觉的胸怀,/目光中既有怜悯又有慈爱”,“她曾把你怀在她无瑕的腹中,/你就更加可爱,哦,娇嫩的花朵;/而你最可爱的时候是当你的/形象最充分体现出了她的美”(《致艾恩丝》,1813,9)[2]649。
从1810年至1813年,雪莱与哈莉特的恋爱是充满诗意的,婚姻是充满幸福的。然而充满诗意的幸福并没有天长地久。一年后,当才貌双全的玛丽走进诗人的视线后,他发现自己理想的爱人应该是玛丽而不是哈莉特。他爱上了玛丽(玛丽也爱上
了他),并试图与哈莉特分手,与玛丽组成新的家庭。他甚至还希望得到哈莉特的宽容——“即使在一个充满恨的世界,/你也只该温良而且正直:/请稍许再用些微一点忍耐/成全一个同伴恒久的欢快”。“哦,请听一次不谬的规劝,/快让那冷酷的感情离去;/那是怨懑、报复,是傲慢,/是别的一切而不该是你;/请为一种高尚的骄傲证明:/当你不能爱时,还能怜悯”(《致哈莉特:“你含情的目光”》,1814,5)[2]22。哈莉特没有接受雪莱的诉求——当时,他们的宝贝艾恩丝还不满一岁,难道一个完整的家庭就这样解体吗?哈莉特依然爱着雪莱,并为他孕育着又一个生命①于1814年11月出生,取名查尔斯·比希。。而雪莱却于1814年7月携玛丽私奔,并使玛丽怀孕。哈莉特难以忍受由此产生的来自各方面的沉重的精神压力,于1816年12月初投河自尽,年仅21岁。不会写诗的她,用这样的方式回应了诗人写给她的《致哈莉特:“你含情的目光”》一诗中的诉求,“成全了”一个伴侣“恒久的欢快”——同年12月20日,雪莱和玛丽在圣·米尔德里德教堂举行了婚礼。但欢快的外表掩不住雪莱伤痕累累的内心,在此后的多首诗歌中,我们听到了他的哭泣和叹息——“开启泪泉的银钥匙,/灵魂痛饮这泉能至疯癫”(《断章:致音乐》,1817)[2]79。特别是那“一朵枯萎的紫罗兰”,寄托了他对亡妻哈莉特的思念——“这朵花的芬芳已经消隐,/象你的吻对我吐露过的气味;/这朵花的颜色已经凋殒,/她曾使我想起你独有的光辉。//一个萎缩、僵死、空虚的形体,/搁置在我被冷落的胸襟,/以它冷漠、寂静、无声的安息/嘲弄我依旧热烈的痴心。//我哭泣,泪水不能使它复生;/我叹息,你不再向我吐露气息;/它静默无声,无所怨尤的命运,/正和我所应得的那种无异”(《一朵枯萎的紫罗兰》,1818)[2]113。
造成“紫罗兰”枯萎的原因是什么?是诗人的移情别恋?亦或是哈莉特的迷情苦恋?我们没有理由去谴责哈莉特。但诗人并不认为他自己有什么过错——他有自己的“爱的哲学”:“灿烂的阳光抚抱着大地,明丽月华亲吻海波,那甜蜜的作为有何价值,如果你,不亲吻我?”(《爱的哲学》,1819)[2]206。雪莱认为,他对爱的追求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在布莱克的情感世界里找不到雪莱式的“爱的哲学”,因此,也不会有“紫罗兰”枯萎的悲伤。
三、抚慰孤独的水仙花
布莱克的情感世界“纯真”,雪莱的情感世界“浪漫”,透过哥拉斯米尔湖那一丛金黄的水仙,能看到华兹华斯怎样的“爱的哲学”呢?
华兹华斯的童年是在坎伯兰郡的湖区度过的。湖区生活赋予了他亲近大自然的天性,以至于“湖畔情思”成为解读其情感世界的关键词,他的《水仙》一诗,就是在哥拉斯米尔湖畔写成的咏物抒怀的名篇。——那是1802年4月15日,隐居湖区的华兹华斯与妹妹多萝西去湖边散步,他们看到了大片的水仙[5]141,水仙灿烂的笑容与优美的舞姿在诗人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两年后的1804年,诗人忆起当年的情景,继而写就了这首咏花诗《水仙》。——“我独自漫游!像山谷上空/悠悠飘过的一朵云霓/蓦然举目,我望见一丛/金黄的水仙,缤纷茂密;/在湖水之滨,树荫之下,/在随风摇弋,舞姿潇洒。”(《水仙》,第一节)[3]85。华兹华斯在诗中将自己比作一朵孤独的云,这似乎与诗人当年与妹妹相伴漫步湖边的情景并不相符,但却与他当时孤独的心境十分契合。
诗人的孤独是心灵的孤独。1790年及1791年,华兹华斯为了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理想曾两次赴法。法国之行未能实现他最初的理想,却令他结识了最初的恋人——法国姑娘安奈特。后因英法开战,诗人被迫于1792年末回国。回国后,他“纯真浪漫”的故事遭遇家人的指责,掌管他经济命脉的舅父坚决反对他与安奈特成婚,加之战争的阻隔,诗人与安奈特天各一方无法相见。时至1802年春,十年的时光已经过去,安奈特依然是诗人心中的牵挂。尽管有心仪于诗人的姑娘——玛丽·赫金逊的追求,但他依旧孑然一身,依旧苦守孤独。1802年3月25日,英法两国签订停战协定,使诗人产生了再次赴法的想法。诗人《水仙》的腹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成的。不仅诗人的孤独,而且诗人的无奈,不都像随风飘荡的云朵吗?但有幸的是,诗人在孤独的漫游中,遇到了“随风摇曳,舞姿潇洒”的水仙。——“连绵密布,似繁星万点/在银河上下闪烁明灭,/这一片水仙,沿着湖湾/排成延续无尽的行列;/一眼便瞥见万朵千株,/摇颤着花冠,轻盈飘舞。//湖面的涟漪也迎风起舞,/水仙的欢悦却胜似涟漪;/有了这样愉快的伴侣,/诗人怎能不心旷神怡!/我凝望多时,却未曾想到/这美景给了我怎样的珍宝”(《水仙》,第二至三节)[3]85。水仙已成为诗人的精神伴侣,伴随着缕缕
轻风,驱散着他心中的孤寂。
所以,华兹华斯的情感世界里,“纯真”与“浪漫”兼而有之。《水仙》充满了“纯真”,纯真源于诗人对自然的虔敬,也源于诗人对童心的依恋;《水仙》充满了“浪漫”,浪漫源于诗人对自然的热爱,也源于诗人对未来的向往。纯真的浪漫与浪漫的纯真是华兹华斯情感世界的本质属性。
作为大自然的歌者,诗人的爱情观相融于他的自然观。他认为,人的肉身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灵魂则脱胎于无形的永生世界。人在儿童时期,具有在自然界中感知永生世界的独特能力。华兹华斯有感于此,故将弥尔顿《复乐园》中“儿童引导成人,像晨光引导白昼”[6]92的名句化作这三行诗句:“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我可以指望:我一世光阴;/自始至终贯穿着对自然的虔敬”[3]——这是《华兹华斯诗选》中第一首诗《无题·虹》的结尾,也是《华兹华斯诗选》中最后一首诗《永生的信息》的题引。诗人认为大自然平等对待所有的生命,我们的赖以生存的社会也应该如此——“我们的欢情豪兴里,万万不可羼入任何微贱生灵的不幸”[3]2。
大自然关爱着每一个她所造就的生命,她造就了水仙去抚慰诗人孤独的心灵。诗人能否像水仙一样去抚慰那些远在天边的孤独的心灵呢?1802年夏,诗人踏上了他的第三次赴法之旅。8月1日他回到阔别十年的法国,见到了昔日恋人安奈特与已经十岁的女儿凯洛琳,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没有战争的安恬时光,但他们无法预料战争还会在什么时候打响,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本国平和地生活。此次法国之行,诗人与法国姑娘安奈特都了却了一份心事,他们都将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诗人于8月30日结束第三次法国之旅——抚慰孤独之旅。但舞姿潇洒的水仙却依然常常闪现在他的情感世界中——“从此,每当我倚榻而卧/或情怀抑郁,或心境茫然,/水仙呵,便在心目中闪烁/那是我孤寂时分的乐园;/我的心灵便欢情洋溢,/和水仙一道舞踊不息”(《水仙》,第4节)[3]85。心灵与水仙共舞——这是纯真的现实,还是浪漫的童话?是自然的歌者融于自然的情感世界。
四、结 语
本文选取《我漂亮的玫瑰树》、《一朵枯萎的紫罗兰》和《水仙》为语料,以布莱克、雪莱与华兹华斯创作诗歌的背景为依据,解读了诗中蕴含的以爱情为主线的情感世界。三首诗歌,三种不同的花,蕴含了三个不同的情感世界。
布莱克是一个不戴面具的人,他的情感世界充满着“纯真”。他纯真的爱情观在“玫瑰树”一诗中得以诠释。他的“玫瑰树”即象征着爱情也象征着生命,诗人借“玫瑰树”之象,主张要像呵护生命那样去呵护爱情。只要有真情,即使玫瑰有“刺”也能乐观面对。布莱克一生坚守他的“纯真”——坚持真爱,守护真情。
较之布莱克的“纯真”,雪莱的情感世界中充满“浪漫”。他认为,阳光、大地、月华、海波等世间万象都透露着自然的爱的行为,人也应该如此——“灿烂的阳光抚抱着大地,明丽月华亲吻海波,那甜蜜的作为有何价值,如果你,不亲吻我?”(《爱的哲学》,1819)[2]206。雪莱的浪漫,与他的贵族家庭出身有关,他的童年与少年都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度过。成年后,尽管他在政治观点上叛逆了家族,但他却仍然可以得到来自贵族家庭的经济资助。在他的充满浪漫的情感世界中,缺少布莱克的对平民的理解;也缺少华兹华斯的对大自然的虔敬。——在他爱情的花园里,看不到“漂亮的玫瑰树”,也看不到“舞姿潇洒的水仙”,却可以看到“枯萎的紫罗兰”。
在华兹华斯的情感世界中,纯真与浪漫兼而有之。两度赴法、邂逅初恋是浪漫的经历,以诗(露西组诗)传情,是浪漫的情怀。另一方面,十余年的湖山隐居,使诗人对大自然有了深刻的感受;以大自然为师,使诗人的心灵得到净化——“我可以指望:我一世光阴/自始至终贯穿着对自然的虔敬”《无题·虹》(1802,3,26)[3]2。他写出了大量寄意自然物象的诗篇与怀念童年生活的诗篇,足见其纯真心灵的回归。他的《水仙》就是将浪漫和纯真寄于自然景物的杰作,在他的情感世界里,水仙是抚慰孤独的使者,而他也愿意化作水仙,去抚慰那些依然孤独的心灵。
一花一世界。玫瑰树、紫罗兰和水仙吐露了诗人不同的情感世界;不同的情感世界却有着共同的期待:让世界多一点真情。
[1]William Blake.Complete Writings[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2]雪莱.雪莱抒情诗全集[M].江枫,译.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3]华兹华斯.华兹华斯诗选[M].杨德豫,楚至大,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
[4]威廉·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M].杨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5]多萝西·华兹华斯.格拉斯米尔日记[M].倪庆凯,译.广东:花城出版社,2011.
[6]蓝仁哲.解读命题“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从《我心欢跳》的惊喜到《永生颂》的人生感悟[J].国外文学.2005(04):91-96.
Flowers Bloom and Whither,Could I Love Thee longer?——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My Pretty Rose Tree”,“On a Faded Violet”and“I Wo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Li Jingjing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Tonghua City,134002)
English Romantic poets are masters of transmitting natural images into displaying their emotional imag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undertaken to decipher the emotional world embodied in poems of flowers—“My Pretty Rose Tree”,“On a Faded Violet”and“I Wondered Lonely as a Cloud”respectively.Blake,as one pioneer of the English Romanticism,injected his belief in eternal love into the flower image“rose”.Shelley,as the Romantic Knight,reminisced the death of his first-love by the flower image“violet”.Wordsworth,the“Lake Poet”,voiced his lovesickness and loneliness to the flower image“narcissus”.
Romantic poets;poems of flowers;view of love;the emotional world
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14.05.011
2013-10-26
李菁菁(1982- ),女,吉林通化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