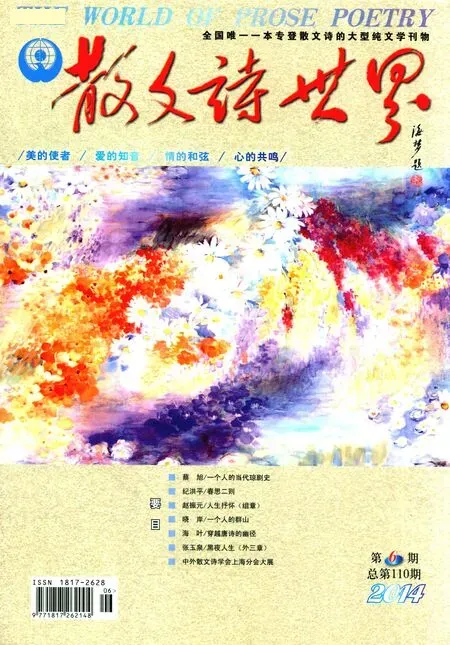外滩,或者路
语 伞
外滩,或者路
语 伞

语伞,本名巫春玉,生于四川,现居上海,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诗刊》《十月》等数十种期刊,入选多种选本。著有散文诗集《假如庄子重返人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1
打开门,向前,瞄准晨光。
路的镜头晃动出沧桑的形态。
各种影像在它凹凸有致的身体上汇集,构成喜剧,或者悲剧的模样。
另一个天空悬浮的,是可能的昨日。
窗外年轻的草木,又站出了新的信仰。我咽下黎明前的断梦,在母亲的叮嘱声中提取早餐的营养和意义,感受一个词语携带拼音和偏旁,走出字典。
感受行路——
无非是目光请远处与近处对饮,无非是双腿绕过障碍物,手指辨别岔道,无非是沉默带着石头的重量,站在一条路上说,足迹只是时间的偶遇。
2
当路以外滩的身份出现,俗事就密集了紧急的气笛。
谁也不能独自停下,必须以浪潮的姿势完美配合。
满街的鞋子似乎深谙音律,每日打着专业的节拍翻唱水泥地面,我迎上去,在内心
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一个在问,一个在答。理想国路过我秘密的心脏,我的血管,已被这个城市灌注了太多高贵的谎言。
我探出头去,通向龙之梦购物中心的花园路抢夺了我的眼球。我看得更多的,是人们的手指在计算器的花园里跳舞。
他们的心在某些时候与花朵毗邻而居。
他们的须发和手臂,翻唱熟悉的小区和楼群。很快就在我眼睛里长出枯黄的叶子。
城市幻化为人的森林。彼此推移。自由组合。瞬间消失。仿佛是大自然以生命的权利所奉献的天衣无缝的魔术表演。
3
往来通行,岔道很多。
沿着四川北路向前,即见外滩。四川与上海的距离,只隔着几个省份的方言。我伸长手臂,试着涂改舌根的图形,尽力与方言们亲如一家,以便凝聚它们头顶的祥云,来压低乡愁。
我并无借尸还魂术,仍然身披蜀人的赤诚,在人性的河流中,坚持仰泳。但我常常看见蝉、螳螂、黄雀在水中谈判,成群的鱼与鲲鹏守在庄子的门口,它们是在等待七月的风扶摇直上?
献出捷径的方向,难以预测今天与明天的距离,常常死在白日梦的忧伤里。
哦,对路客气一些——
人们立即转过身来,穿好恰当的鞋子重新出发。
背负十字架行走,是非恩怨像灶台上积攒了多年的油污,我始终没有找到一张真正的万能抹布。
4
一个装满顾虑的苍穹,无法同时盛放暴雨和太阳。
我不确定外滩深刻的召唤,我只能在风吹草动时跟随眼睛和耳朵,认真收录某条路的神秘显像。
踩着人行横道的腹部穿行,绿灯在上,步伐不是一本超越时差的巧书。
人们站在合适的位置,在途中等待神秘的机缘。
我等待十字路口那个朴素的城管,用黝黑的面孔贴出暗示的布告。他重复多年的表情和手语,再一次毫无新意地重复出他的性格特征。他偶尔抛出一堆粗鲁的词语,还是无法阻止闯红灯的人在车流的夹缝里练习冒险。
这个城市,到底住着多少心存侥幸的人?
公园一角的宁静尘封了鲁迅的呐喊,只有石库门还在痛诉脏空气要如何为上海的繁华还债。
5
脚印在自己的外套上寻找答案。
我在道路的袖口捕获了另一个我的存在。
大梦吞食毒蛇,我吞食整个夜晚。佛经里的生字太多,没有读懂的人都以高僧的姿势盘坐。
善良的人开始揣度道路的心地,我在幻觉里切割时间,陪迷途的羔羊走路。
紫色的喇叭花开了,一个城市的美被它们的芳香喊出。而一群身患忧郁症的病号,正在黑暗中试图将破碎的灵魂抛弃。
我在冥想中醒来。
我想掐住一条路的七寸。
我在赫尔曼·黑塞的文字里复制了悉达多的影子——那个永远自我否定的“逻辑”。
6
多年以后,我亲手割断的风筝,还能不能找到故乡的软肋?
亲人仍不能常常相聚,不是距离捏造的借口。路,早已不是千山万水。路在不断繁衍,只是我和许多行路的人一样,越来越分不清,自己应该先走哪一条,再走哪一条。
上海在历史的回音壁上镌刻记忆,英雄的脸上淌过血泪,名嫒的旗袍上写过悲剧。今日的酒吧里,仍有人身陷迷雾,在酒精里曲解方向。
于是,尘埃倒立,横山路和新天地重建了人们的内心。
法国梧桐还在为这个城市撰写日志,多少花朵的隐私还来不及忏悔就已凋零,多少枝条的秘密并未发芽就被修葺,多少根的思想不曾被理解就形同枯槁。
长路漫漫,我的目的地,在有和无之间徘徊。
我一直在寻找身背指南针的人。
7
分不清是路在挥手还是外滩在挥手。
我向前迈出一百年,虚构自己的坟墓。
一本书,正在为一首诗,守灵。
卧室多像躲在这个城市里的甲壳虫。我在甲壳虫的体内放逐不安的臆想,无数条想动又动弹不得的细腿,在时间的乐园里生锈。
现在,稠密的晚餐闭上了眼睛,酒杯已精疲力竭。我翻开书,返回商周,流浪在“小雅”与“大雅”之间。我的马匹,瞬时奔驰于云朵之上。
天空与大地对应,我走遍自己,无数的影子在太阳下复活。
一个城市的心脏,被理想的喧嚣攻破。
丢下《诗经》,我说,归哉,归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