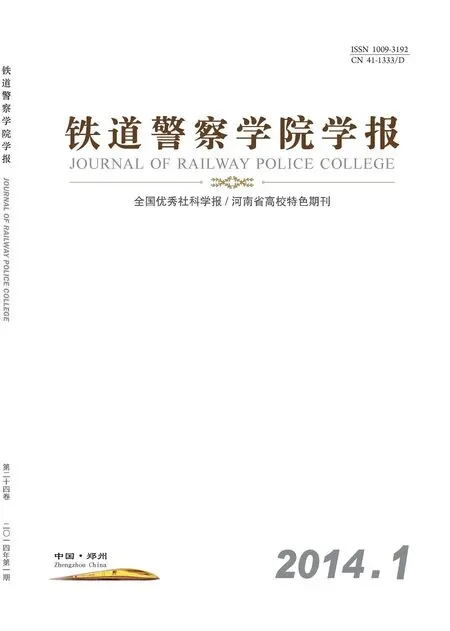刑法法益保护内容的新思考— —以社会共同情感为视角
韩瑞丽,陈庆安
(华东政法大学 科学研究院,上海 201620;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上海 200050)
如果说犯罪的本质在于法益侵害,那么,法益保护就成为刑法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意味着刑法所干预的只能是侵犯法益的行为。问题在于,尽管“法益是整个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根基”,但是具体到法益的内容究竟是状态、利益、价值抑或其他,则“几乎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法益定义”。这样就导致同样使用法益概念,但各自所指的内容并不相同。大体上看,物质的法益概念论者持“利益说”,认为法益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能填充“精神的东西”;精神的法益概念论者持“价值说”,认为“法益存在于规范背后的精神领域”,与人类共同生活密切相关,并根据社会的评价形成。奥本海姆(Oppenheim)提出:“所有的法益要么是权利、要么是义务、要么是状态、要么是感情。”[1]凯斯勒(Kessler)甚至主张,“利益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人的感觉,即只有人的感觉、感情,才能受到保护”[2]。
也就是说,基于精神的法益概念立场,情感可以成为刑法法益的保护内容。当然,这里的“情感”要作“社会共同情感”来理解。社会共同情感,是指“一般人都具有的”社会平均道德情感。它不要求在较高级和较优良的层次上,而仅要求在全社会都具有的平常程度上,而这种程度无论是对于个人适应社会还是基于保护“符合人的生活”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一、“情感”成为刑法法益保护内容的可行性
(一)价值源于情感
休谟曾以具体的犯罪为例阐明价值的情感来源。他说:“以公认为罪恶的故意杀人为例。你可以在一切观点下考虑它,看看你能否发现出你所谓恶的任何事实或实际存在来。不论你在哪个观点下观察它,你只发现一些情感、动机、意志和思想。这里再没有其他事实。你如果只是继续考究对象,你就完全看不到恶。除非等到你反省自己内心,感到自己心中对那种行为发生一种谴责的情绪,你永远也不能发现恶。”[3]
基于同样的主张,霍布斯提出:“任何人所欲求的对象,就他本人说的,他都称之为善,而他所仇恨及憎避的对象,他则称之为恶。”[4]洛克则进一步指出,事物之有价值,只是由于人们对之有苦乐感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对象没有产生快乐或不快乐的情绪,从而去赞成或谴责对象,对象自身就不会有任何价值。正所谓“价值是感情的对象,不是理性的对象。它就在你的心中,而不在对象之内”[5]。
(二)法益的具体内容是价值
通说认为,刑法法益是受刑法规范保护的利益和价值。其中,持“价值说”的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法益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探讨[6]。
其一,法益是价值类属。耶林认为,刑罚法规的目的和其他法律目的一样,都是为了确保社会生活条件,社会生活条件不仅包括社会及其成员的物质存在和自我继续,而且还包括所有那些被国民判断为能够给予生活以真正价值的善的美的和愉快的东西。基于同样的主张,有学者提出,法益不是物质主义的,而是作为生命、健康、自由、财产、名誉等的不可侵犯性来理解,它内存着社会伦理的价值要素;是以共同社会的原来存在的安全、幸福及尊严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理念的诸价值。
其二,法益以文化价值为基础。逻辑思路大多如下:社会伦理的“价值”构成了社会的文化财,文化财由于法的保护而成为“法益”。如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法益是指法的财,即被某种文化共同体的各重要阶层的一般价值感情所承认的,并由该文化共同体的妥当意志即法规范秩序所实现的财。
其三,法益与共同体价值有关。一方面,浸透于共同体意识中的对某种行为的无价值判断,是立法者作出禁止性规定的动机。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将共同体价值作为刑罚法规的目的客体纳入视野时,法益才获得生命。正如一些德国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法益产生于共同体所承认的生活价值或文化价值之中,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共同体的价值。判断什么是法益,即判断什么对共同体特别有价值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该共同体的指导阶级的价值意识。
二、“情感”成为刑法法益保护内容的妥当性
(一)情感的自然妥当性
情感是自然禀赋。作为“自然授给人类精神的一种特殊种类的能力”,情感并非纯粹的个人心灵状态,而是具有独特的主观体验形式和外部表现形式,具有可描述性。关于它的起源,达尔文将其归因于对我们同类本能的同情。斯宾塞将其归因于某种精神过程,这种过程迫使我们的祖先必须服从特定的行为戒律,以至于成为世代相传的思维习惯并转化为道德直觉本能。即对于正确和错误行为所持的特定情感、憎与恶都是遗传的反应本能,它是我们祖先愉快与痛苦的经历的反映[7]。
(二)情感的社会妥当性
情感还是社会建构的。即人们的感受是文化社会化以及参与社会结构所导致的结果,情感的用语把人们联结在共同的或社会性的行为之中[8]。就犯罪而言,它是社会成员共同谴责的行为。“而社会成员之所以共同谴责这一行为,就在于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9]。上升至法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某种生活要素要成为法益必须通过“社会的承认”。即便是某个社会成员强烈地希望保护某一生活要素,也会存在其他社会成员不承认、不接受的情况。为了使该生活要素成为法益,就必须通过法的保护性的“社会的承认”这道关卡[10]。也就是说,法益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而所谓得到“社会的承认”,就是要求根据平均市民对保护对象的价值理解能力,来确定该保护对象是否属于在客观上具有社会的重要性的利益[11]。
(三)情感的法律妥当性
其一,犯罪本身就是情感侵害。“不能直截了当地拒绝承认把单纯的感受或者一般的价值观念当成法益,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缺乏法益内容状态的确定的道德观,因为刑法典对单纯的侵犯孝敬的情感或者激起公愤的惩罚,直至现在仍然没有产生争议,尽管在这里,损害仅仅存在于感情世界和举止是否得体的领域之中”[12]。
其二,将情感与道德分开。“道德不是刑法目的意义上的法益,因为某种行为不损害任何人的自由空间,而且仅潜在于行为人的私人领域里,对存在于外部的人感情不可能直接产生不愉快的作用时,对之进行处罚并不具有上述意义的目的”[13]。也就是说,至少要在他人情感“被侵犯”的意义上,法益保护才被激活。
其三,寻求关于犯罪的矫治方法。按照加罗法洛的观点,犯罪是一种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且根据个人情况而变化的社会疾病,“如果不采取这种(犯罪是情感侵害)途径,没有一个内科医生会作出他的判断。但是这一点并未被立法者所遵循。任何特定刑罚的种类、期限以及它与犯罪性质或犯罪人本性的关系对于社会防卫或犯罪人的改造究竟有多少作用,这一点我们全然不了解”[14]。
三、“情感”成为刑法法益保护内容的限定性
有人会提出,情感喜好因人而异,上升为法益保护内容,势必会造成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导致刑法干预国民生活的一切领域的状况发生。
这种担心一方面反映出对情感以及对情感上升为法益的途径存在着误解。因为,任何一部现代刑法都不会完全依据特殊利益主体的观念来决定什么是利益或何种价值优先,只有立法者根据一般人的观念所确定和保护的利益和价值才是法益。就其中的情感而言,“我们根据这种情感不是作为私人的情感,而是作为一种共同的情感”[15]。就进一步上升为法保护而言,“法所保护的利益的概念,也不问为其保护目的的各个人主观感情之认为有利益与否,如果在社会一般的认识上,认其有价值,那纵使受其保护的个人,主观上不感其价值,而在法的见地上,仍作为其人的利益而被保护”[16]。不过,另一方面,这种担心也充分说明要对情感填充刑法法益进行适当的限定。
本文认为,“情感”对刑法法益具体内容的填充,要立足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守成法益的立法批判机能。法益具有限制刑罚处罚范围的机能。然而,“随着法益内涵不断丰富,法益却有成为政策化工具的倾向,致使其限制刑罚处罚范围的功能也日益弱化”[17]。鉴于此,本文提出情感填充刑法法益的命题,目的就在于强调法益论对于立法的批判和刑罚处罚范围的限制作用。一方面,“立法者没有权力把公众舆论认为是值得赞扬的甚至是中性的行为确认为无耻的行为”,“仅靠刑罚去证明那些公众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具有犯罪特征,这种做法从未成功过”[18]。另一方面,“对大量无关紧要的行为加以禁止,防止不了可能由此产生的犯罪。相反,是在制造新的犯罪,是在随意解释那些被宣传为永恒不变的美德和邪恶”[19]。正所谓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一个社会体系不应根据社会自身的意愿来维系,而是应该根据生活在各自社会的人们的意愿来支持”[20]。
二是发挥法益实质解释的“出罪”机能。一般而言,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必须使符合这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规定该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从而使刑法规定该犯罪、设立该条文的目的得以实现。然而,在法律的运用和解释过程中,价值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这种状况下,解释者的姿态,即坚持什么样的解释理念,既决定着法律解释的结果,又影响到法治的实现程度。以人为本、尊重人性、反映人性要求的精神日益成为现代法律解释的原则和指导思想。以三个以上的成年人,基于同意所秘密共同实施的性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为例,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行为不属于《刑法》第301条规定的聚众淫乱行为,理由是:立法者规定聚众淫乱罪“是为了保护公众对性的正常感情”,故在公众不可能发觉之处实施这种淫乱行为的,根据法益侵害说,不应以犯罪论处。相反,如果采规范违反说,则会认为由于成人间完全私密的淫乱行为也违反了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故也应认定为犯罪[21]。显然,在价值日益多元的当下,坚持一种以人为本的法益侵害理论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实质解释理念,可以最大化地将对人的利益和价值的关注作为法的价值追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公众对法律的尊重和认同。
[1]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45.
[2]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44.
[3][英]休谟.人性论(下)[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08.
[4]洪汉鼎.斯宾诺莎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24.
[5][英]休谟.人性论(下)[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09.
[6]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06.
[7][意]加罗法洛.犯罪学[M].耿伟,王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22.
[8][美]乔纳森·特纳.情感社会学[M].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3.
[9][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36-42.
[10][日]関哲夫.法益概念与多元的保护法益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4).
[11]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18.
[12][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总论[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4.
[13]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16.
[14][意]加罗法洛.犯罪学[M].耿伟,王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5.
[15][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78.
[16]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70.
[17]舒洪水,张晶.法益在现代刑法中的困境与发展——以德、日刑法的立法动态为视角[J].政治与法律,2009,(7).
[18][意]加罗法洛.犯罪学[M].耿伟,王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56.
[19][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91.
[20][德]克劳斯·罗克信.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A].樊文,译.陈兴良.刑事法评论(19)[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7.
[21]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