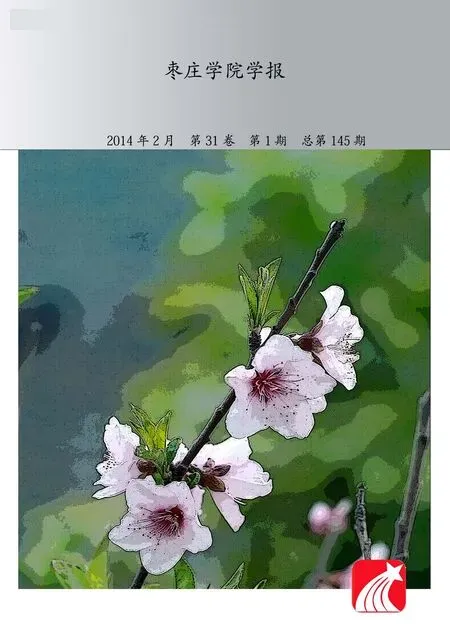论“荒诞”
——简析加缪《西绪弗斯神话》的哲理观
欧婧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一、“荒诞”的定义与产生
法国作家与思想家阿尔贝·加缪发表于1942年的哲学著作《西绪福斯神话》,讨论了“荒诞”这一哲学命题在人生意义上得以呈现的多种面貌。加缪将“人和生活的分离感,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感”称为“荒诞感”,他指出“在一个突然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他表示当人开始对眼前世界产生“陌生感”的认知的时候,“荒诞”便足以开始成立了。加缪所处的20世纪上半叶,正是科学技术与理性主义逐渐促进人类社会工业经济飞速发展,自发摆脱封建政治体系的重要环节,此时应当是启蒙话语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却使得加缪本人在这个先进的新时代里,萌发了与世界的认知有所隔绝、陌生,无可依凭的“荒诞感”。
加缪指出宇宙被剥夺了“幻觉”与“光明”,从一个可以被熟悉被感知的世界变为了一个无法用人类之力进行理解的世界,人与世界看似理所应当的密切联系被阻断,人类无法再通过直观的感知把握世界的形态,用尼采的“日神精神”进行理解,则是人类无法再运用“梦”一般的造型能力,通过塑造事物的形态来感受世界的诸多现象,从而获得感性冲动的主体满足,这种幻觉化的生命本能在启蒙主义的理性萌芽之时,就已经逐渐丧失它对于人类理解世界的主要影响,加缪时代的人类早已不能满足于一个独特个体的自我感知,去把握并承认世界的本质。与之相对的,尼采还提出了以“醉”为代表的“酒神精神”,通过陷入迷狂的精神状态来消解个体与世界的隔膜,当日神精神在当代受到理性主义思潮的挑战的同时,酒神精神的存在应当说可以使得人类在激情的迸发中忘却个体之间的樊笼,从而通过沉醉的战栗获得与世界的充分融合。然而,这一理想化的精神状态远远不能缓解整个社会群体的陌生感,尤其是在这一现代性发展日益深入,理性主义思潮逐渐完备的时代。唯美主义与浪漫主义正是力图在用直观感知维持生命意识的基础上,借助于个体在自然万物、情感等层面无所为的精神放纵,来坚持对启蒙理性催化下的功利人生的抗争,这样通过生命体验的瞬间饱和来完成自我救赎,与酒神精神的追求有着一定程度的谋和,然后在现代性推动世界这一主体对象日益多元的背景之下,理性主义威胁着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的瓦解,科学技术的正统知识体系挑战了希腊酒神式的精神沉醉与物我两忘,并不能成为使人类与世界重塑亲缘关系的良方。
自始至终,人类对于眼前世界始终报以强烈的探求欲望,对于绝对可靠认识的强烈愿望与呼唤从未消退,然后在并不理想的认识方法之上,世界对人类回报以不可理喻、神秘的沉默,在加缪的认识中二者处于永恒的对立产物,这种对立状态的产物,即是产生于人与世界关系之间的荒诞感,这种精神形态的陌生感使得个体产生了“局外人”的困惑,并在从属于社会群体的现实生活中逐渐植根,由此产生了诸多具体的精神面貌与人生形态。
二、“荒诞”的标志与延续
由于启蒙理性推动时代发展,摈弃感性冲动的重要地位,使得新时代的人类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时代里,越来越被约束于特定的社会位置之上,作为现代化社会进程中的一枚齿轮,个体的价值理念逐渐被某种定式的社会理念所主宰,个体的意识消亡成为了现代性的一大危机。加缪表示,意识到“荒诞感”的人群会首先会意识到生活的重复节奏,由于自我思想价值的受限,对于枯燥、反复的日常生活与工作步调,产生惶恐、忧虑、无可救药的茫然与绝望。人们会逐渐意识到自己身处于一个同样无法把握与感知的世界中,人与世界的隔绝开始形成,人类将觉察到面对世界这一感知对象时,所拥有的,无法穿透的“厚度”。
正如加缪小说《局外人》中的主人公莫尔索一样,他始终对生活的种种对象,如亲情、爱情、甚至于生死观念拥有着隔膜感,他无法感知到世俗社会价值体系中的种种概念,最终却在被执行死刑的前夜,突然意识到了自身与眼前这个世界的距离感。“一种阴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从遥远的未来向我扑来,这股气息所过之处,使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以往的生活更真实。他人的死,对母亲的爱,与我何干?”他面对死亡,也拒绝接受牧师提供的忏悔告解,因为在他眼中,世界的荒诞感业已形成,当整个世界的时间空间都产生了陌生的触感,而无法与之建立联系的时候,例行的临终忏悔也不过是这个陌生世界的一部分,对于人心毫无益处。对于个体生活如何在现代社会主体中合理运行,赛亚·柏林曾设定了两种自由原则,一是积极自由这一“去做什么”的自由,即社会个体的自我导向与自我控制,柏林希望社会个体的行为出于自我的意识与准确动机,并能通过自我意识设定目标与决策,从而实现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不希望社会环境中的人类受到奴役而成为一件毫无自我意识的物品。积极自由的实现不仅要依靠社会环境与政治制度的约束要求,还应当依靠于个人主体意识的能动,然而在“荒诞感”的产生过程之中,人类会从对于世界的“厚”的陌生感知之中,逐渐领悟到自己,即具有主体意识与能动性的个体,也呈现出了“厚”的陌生感。柏林不希望在某一种不合理的经验与制度引导下,人类会变成无法呈现人性主体性的物品,然而在脱离了理想化色彩的现实社会中,这种人对于自我存在的陌生感,会随着荒诞感的逐渐加深而应运而生。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人类自身也是属于认识对象的一部分,随着人类逐渐意识到自身的种种机械面貌,终将会对自我主体性带来的种种毫无意义的行为感到厌恶,当人从镜子中审视自己的时候,会发现镜中人形所映照出的,不过是同样机械化的行为叠加。
在荒诞感的层层叠加中丧失了自我主体的控制与引导欲望之后,人类必然会导向对于自身存在以及种种行为的质疑,主体意识在受到一定程度的消磨之后,还有消极自由这一“免于做什么”的自由可以保障人类依存于社会的这一固有模式。然而消极自由只是一个极低的限度,即通过被免于种种超出人性界限的要求,而呈现出最为基本的社会生活形态,当拒绝自我意识的个体对生活趋同于麻木无感的时候,他的存在要求也就被降低到了这一最为底线的位置上,在“免于……”的同时,由于不再具有“去做……”的主动自由,社会个体将为成为某种形态下的社会,最易掌握的棋子。这时,伴随着荒诞感在主体意识中的逐渐清晰,权威的政治统治将社会人群控制为一个符合某种既定规章的群体,通过最基本的人权底线与阶级划分等统治方法,保障人们在社会范围内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在这样的制度运行中的社会,极有可能因为荒诞造成的对积极自由的抗拒,而最终安于某种程度极低的生存理念。由于加缪强调,荒谬是无法自我消解的,即使通过自杀这样的消亡肉体的方式,也无法使得人与世界的陌生感得以消失,而通过权力进行生活方式划分的政治体系一旦出现,也会为了维持自身的有效运行,最终使得人类在这一过程中继续重复叠加的生活步调,体会到自身与外部世界愈来愈深厚的距离感与陌生感,由此而来,荒诞是一个永远持续的人生困境。
而这种高度统一的社会的可能形态,正是未来题材的小说中极权主义所带来的的隐忧。随着启蒙话语的思想地位日益主导,难免在话语体系中呈现出了一定的极权主义倾向,当其愈试图接近真理时,愈需要利用社会群体的价值认同来推进这一过程。如福柯所言,启蒙话语超越了原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把握这一动机之后,开始达成与权力的联盟,从而为极权主义倾向的政治阶层服务。《一九八四》与《美丽新世界》中奥威尔与赫胥黎都用绝对权威的阶级差异制度,将人类划分为各个阶层,并人为地确定这一阶层的属性,而隶属于自己阶层的个体将会受到这一阶层属性的种种保护,保护他们享有“免于做……”的消极自由,但这重保护同样也是约束,个体不能逾越自身阶级而去享有“想做……”的积极自由,除了极少数的集权制顶端的统治阶层享有这一权利之外。
此时正是荒诞感的循环效应发挥了它的效力。极权主义统治阶层通过严密精细的阶层划分,为各个阶级的人群划定了一定范围的行为轨迹与精神空间。《一九八四》中的统治阶层通过高压强权的政治统治,禁止自由思想的传播与交流,通过统一的渠道限定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将人们的精神世界禁锢为一片荒芜的文化沙漠,将人们麻木地安置于某一固定的社会地位之中;《美丽新世界》则阐释了从出生起便被划分阶级的人群,受到以温和形态御下的极权主义的包围,最终在感官娱乐之中丧失对自身主体性存在的思考。然后,这两种社会形态都导向了一种不可避免的主体性精神的消亡,在意识到世界荒诞感的同时,又遭受了主体性认识的消磨,极权主义背景下的荒诞感的延续,所带来的现实意义,远远超过了1942年加缪对于这一概念的设想。
三、如何直面“荒诞”
因为丧失了自身与世界联系而应运而生的茫然、忧虑的陌生感、荒诞感,使得认识到这一点的社会个体产生了边缘于主流价值之外的“局外”意识。《局外人》中,浑浑噩噩、麻木无感的莫尔索则是在无自知、无所谓的状态下犯下了杀人的罪行,直到临死前夜,他突然感受到了“土地的气味、海盐的气味……沉睡的夏夜的奇妙安静,像潮水一样浸透我的全身”,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心扉”。同样地,伊朗电影《樱桃的滋味》中老人巴格里在将上吊的绳索挂在树上的时候,感受到了黎明的阳光与青草的芳香,从感官的体验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可贵与幸福,而同样对生活厌倦的巴迪,躺在为自己挖掘的坟墓中凝望着宁静浩瀚的星空,镜头传递了他眼中有别于麻木、厌恶的崭新的光彩。
莫尔索、巴格里与巴迪,这三个离死亡如此接近的人物形象,他们原本置身在陌生感浓烈的社会中,洋溢着对生命主体性的厌弃,却都在某一时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气息。他们完成了哲学意义上的新生,他们重新建立起了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此时他们面对“荒诞”所最终迎来的是瞬间的生命感的爆发,在这种有如天灵感应的生命意识,将重新消褪他们与世界之间的隔膜感,他们从消极、困难的生命形态上,瞬间完成了一定程度的生命意识的向上提升,在这个充斥着无限可能性的瞬间中,他们幸运地找回了曾经牵引过自己也在同时牵引大多数人群的特定意识,他们能够在意识到了与社会、他人的隔离之后重新回到主流社会的价值框架中。
然而,这毕竟是戏剧性的文学作品所描摹的一种理想状态,即使是加缪本人,也很难承认这种生命意识的瞬间回归能够适用于每一个“局外人”。与此同时,很难承认这种理想化的“跳跃”就真的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荒诞感”带给人类的苦闷。即使重新建立起了与世界的联系,加缪更加推崇的是“西绪弗斯式”的应对方式。西绪弗斯作为被希腊众神所惩罚的罪人,要不断地将会从山顶滚落的巨石,重新推上山顶,从而周而复始的进行着这种徒劳、机械、毫无意义的生命行为。西绪弗斯的这一虚无、绝望的行为所昭示的,正是具有集体性特征的现代人的悲剧,神明强迫他进行“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正如同昭示了意识到“荒诞感”的个体生命,乃至于昭示了整个人类无法抗拒的命运。
在诸多前辈哲人中,加缪最为肯定克尔凯郭尔在“荒诞”上的发现,他指出他甚至还经历与认识到了“荒诞”。面对现代性的发展带来的危机,他清醒地认识到自我意识价值丧失所带来的不安,他虽然通过清醒的自我意识来凸显了荒诞感的存在,却未能在多种哲学认识的尝试之后,达成一种较为明确而现实的反抗的荒诞人生的方法。然而,加缪肯定了他对于重新建立信仰维度的追求,并将这种通过宗教式的神圣感,重建安身立命的信仰的特点,继承与发展到了“西绪弗斯”的身上。在此基础之上,加缪为西绪弗斯安排了更为宏大的人道主义赞誉。他作为“荒诞”中的英雄,被充分地剥夺与世界的联系,注定在机械的劳作中走向永恒的失败。西绪弗斯的可贵在于他对于悲惨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知,虽然他无能为力改变命运却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反抗。反反复复的推石过程,“造成他的痛苦观察力的同时,也完成了他的胜利,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他对于加诸于自身上那看似绝望的命运保持着轻蔑,在形体受到机械化的奴役的同时,他宁愿保持着精神的独立。这种加缪式的反抗真是来自于对于个体内心价值空间的肯定,与生俱来、不应忽视的主体意识表明了个体远非麻木不仁,如西绪弗斯相同困境中的人类并不匮乏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这种执着、积极的主体意识始终引导着虚无主义困境中的,诸多个体生命意识的向上提升。能否改变命运的困境已经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面对“荒诞”的个体,应当建立起自我意识的独立与强大,一种向上的意识提升虽不能改变现实世界的作用力,却将“西绪弗斯”们的立场视野凌驾于苦劳、机械、绝望的人生命运之上。就如加缪所说“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弗斯是幸福的”,面对现代性对于人类命运所施加的无法摆脱“荒诞感”,我们所要坚持的便是重拾那在启蒙话语与现代性发展下,被忽视的自我意识与被消泯的个体意义。面对“荒诞”的失败与胜利,都将注定是永恒的。
通过对于“荒诞”的产生、定义、标志、应对以及可能性的发展的思考,不仅探求到了“西绪弗斯”式的反抗对于人类主体意识价值的成功彰显,还从前人的种种思想成果中寻觅到了至今仍有着重要意义的,面对永恒的“荒诞”困境的有力良方。
[1][法]加缪著,郭宏安译.加缪文集·局外人[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2][法]加缪著,郭宏安译.加缪文集·西绪福斯神话[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3][德]尼采著,周孙兴译.悲剧的诞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英]赛亚·柏林著,胡传胜译.自由论[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
[5][丹麦]克尔凯郭尔著,刘继译.恐惧与战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6][德]霍克海默、阿多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