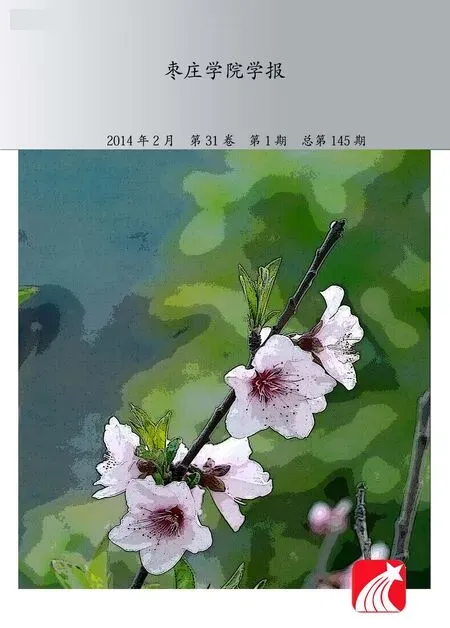论鲁迅的宋元话本研究
朱祥竟,刘相雨
(1.曲阜师范大学 图书馆,山东 曲阜 273165;2.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一、鲁迅宋元话本研究的贡献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关于宋元话本的论述,主要在第十二篇“宋之话本”、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两章,第十四篇、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下)也有一部分内容与此有关。鲁迅对于宋元话本研究的贡献,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鲁迅揭示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另一条线索——白话小说的发展线索。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发轫较早,《汉书·艺文志》即已著录了“小说家”十五家,作品1380多篇;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出现了大量的志怪、志人小说集,如《搜神记》《世说新语》等;唐传奇就更是“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成就斐然。而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发展线索在宋代才开始显现。
鲁迅在论述宋代话本前,在第十一篇先论述了宋代的文言小说——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在两者的比较中,他认为:“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古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①在与文言小说的比较中,鲁迅突出了宋代话本的成就②。宋代以后,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发展就呈现出“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态势,白话小说逐渐呈现出与文言小说分庭抗礼的局面。
第二,鲁迅在论述宋代话本时,将话本的源头向上追溯到了唐代。鲁迅不但引述了敦煌变文中《唐太宗入冥记》的部分内容以说明唐代说话的情况,而且注意到了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提到的的“市人小说”以及李商隐《娇儿诗》中关于“说话”的相关记载③。这种追本溯源的研究方式,对以后话本小说史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萧相恺《宋元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张兵《宋元话本》(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萧欣桥、刘福元《话本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后来的话本小说史对唐代“说话”资料的梳理、介绍更加全面,特别是对敦煌文献中的相关篇目的论述更加细致、深入了。
第三,鲁迅首次明确了“话本”的定义。“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依凭,是为话本”。宋代的说话伎艺是非常繁荣的,这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周密的《武林旧事》等书中都有记载,但是说话艺术毕竟是一种口头表演艺术,在没有现代录音、摄像技术的时代,这一艺术的具体情形如何,人们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弄清楚。例如,宋元时代的说话人在从事艺术表演时,有没有供其参考的底本?如果有底本,这些底本的情形如何?如果没有底本,说话人是如何记住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宋元说话人说话时是有底本的,这些底本就是今存的宋元话本,也就是宋元的白话小说。
鲁迅先生这一观点提出后,得到了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响应。胡适、谭正璧、叶德均、陈汝衡、赵景深等学者,均支持或赞同这一观点。不过,事情到1965年发生了变化。日本学者增田涉在日本的《人文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话本”一词的定义》,该文从《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刊小说四种》以及“三言二拍”中找了几十则含有“话本”一词的例句,经过认真的考证,他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话本显然是故事的意思,说什么也没有‘说话(人)的底本’的意思。”这一观点提出后,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促使国内的学者重新思考“话本”一词的定义。有一部分学者接受了这一观点,如卢世华认为:“今人所称的宋元话本小说就是宋元白话小说,是经过口头创作之后改编出来的小说,并非说话人底本。”④王庆华也认为:“‘话本’一词在古典文献中有‘说话人的底本’之义,但古人却从未在‘底本’的意义上指称今天称为‘话本小说’的作品。”⑤周兆新、胡莲玉等也都在论文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⑥。有的学者认为,宋元时代的说书人即使有说话的底本,也应该是《绿窗新话》一类的书,与今天所谓的宋元白话小说无涉。另外一部分学者则对增田涉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或修正,如程毅中认为:“话本指说话人的底本,这只是一种比较概括的说法。如果对具体作品作一些分析,至少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提纲式的简本,是说话人准备自己使用的资料摘抄,有的非常简略,现代的说书艺人称之为‘梁子’。另一种是语录式的繁本,比较接近场上演出的格式,基本上使用口语,大体上可以说是新型的短篇白话小说。”⑦刘兴汉、萧欣桥也都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⑧。那么,“话本”一词到底有没有“说话人的底本”的意思,现在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争议。不过,无论我们怎么评价鲁迅的观点,不管是赞扬还是反对,我们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这恰恰说明了鲁迅在宋元话本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
第四,鲁迅论述了宋代的“说话”四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了吴自牧的《梦粱录》,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周密的《武林旧事》等对于“说话”四家的不同记载,对于“四家”到底应该是哪“四家”,鲁迅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对于《梦粱录》中的材料引述得较为详细。1924年7月鲁迅到西安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时,则明确地指出,“说话有四科:一、讲史;二、说经诨经;三、小说;四、合生”。这种分类法大体上采用了吴自牧《梦粱录》中的说法。而“说话”四家到底是哪四家,成为以后较长时期内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胡适、孙楷第、谭正璧、陈汝衡、李啸仓、王古鲁、赵景深、胡士莹等学者,都对这一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从总体上来看,大部分学者认为,说话四家中应该包括小说、说经、讲史三家,至于第四家是谁,学者们的分歧很大,有的认为是合生,有的认为是说参请,有的认为是说铁骑儿……面对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解决方式,如程毅中先生认为:“说话有四家可能只是耐得翁的一家之言,未必是当时公认的说法”⑨。萧相恺先生也认为:“根据现存宋元市人小说的实际,综合上引各书的有关记载,将宋人的‘说话’分为三家更符合当时的实际,也更为科学。”⑩不管宋元的说话当时有几家,都反映出时期宋元说话艺术是十分繁荣的。而说话艺术的繁荣,直接催生了宋元的话本小说。
第五,鲁迅对宋元话本的重要作品进行了评介。鲁迅论及的作品,以讲史家话本为主,如《梁公九谏》、《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三国志平话》等。鲁迅在论述这类作品时,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作品的成书时间、作品内容、主要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如对于《新编五代史平话》,鲁迅评价说:“全书叙述,繁简颇不同,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俪,证以诗歌,又杂诨词,以博笑噱”。鲁迅认为《全相三国志平话》,“观其简率之处,颇足疑为说话人所用之本,由此推演,大加波澜,即可以愉悦听者,然页必有图,则仍亦供人阅览之书也。”鲁迅论及的小说家话本较少,仅提到了《京本通俗小说》中的七篇作品。对于小说家话本,鲁迅特别注意到了这类作品体制上的特点,“什九先以闲话或他事,后乃缀合,以入正文”,“大抵诗词之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小说家话本的前半部分,鲁迅称之为“得胜头回”,他认为“头回犹云前回,听说话者多军民,故冠以吉语曰得胜,非因进讲宫中,因有此名也。”他还以《西山一窟鬼》为例,认为其“描写委曲琐细,则虽明清演义亦无以过之”。鲁迅论及的说经话本,只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他认为“今所见小说分章回者始此;每章必有诗,故曰诗话”。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小说史略》经常大段大段的引用宋元话本的作品,可谓不厌其烦,而他对宋元话本作品的评价则十分简洁,可谓惜墨如金。鲁迅先生的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是由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宋元话本的作品还不够普及,一般的读者难以接触到。鲁迅大量的引用作品,既可以省去读者的翻检之劳,又可以让读者了解某一小说的主要内容和基本风格。另一方面,鲁迅的治学方式受到乾嘉学派的某些影响,讲究以事实说话,以证据说话,不发空言,言必有据。《中国小说史略》大量引用作品,就是想通过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判断;同时,鲁迅又避免了乾嘉学派繁琐考证的毛病,对于作品的断语十分简洁。
此外,鲁迅对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高度评价。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称宋元话本的出现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视为与唐传奇的出现同等重要的大事。他还认为“后来的小说,十分之九是本于话本的。如一、后之小说如《今古奇观》等片段的叙述,即仿宋之‘小说’。二、后之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其中讲史之影响更大,并且从明清到现在,《二十四史》都演完了”。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情况来看,确实如此。宋元说话的“小说”一家直接影响了明代“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
二、时代风气与鲁迅宋元话本研究
从《中国小说史略》章节安排来看,鲁迅用一章的篇幅来讲述宋代的文言小说,用两章多的篇幅来讲述宋元的话本,其篇幅是宋代文言小说的两三倍。这固然是由于鲁迅认为宋代文言小说的创作成就要低于宋代的白话小说,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提倡有一定的关系。
1917年,胡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从八个方面对当时的文学进行改良,即所谓的“八不主义”,他并且认为“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胡适对白话小说的评价甚高,称之为“文学正宗”,“世界第一流文学”,而白话小说的源头正在于宋元话本。
陈独秀响应胡适的主张,在《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甚至认为当时的文学不够繁荣,是由于受到了“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等十八妖魔的迫害,“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而流产”。因此,他提出要“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与当时流行的文言文宣战。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胡适、陈独秀的主张均有某些偏颇之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的鲁迅未必完全同意胡适、陈独秀的上述主张,但是对于他们提倡白话文学的主张还是肯定的,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就于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可以说,鲁迅以实际的创作行动支持了胡适、陈独秀的文学主张。在文学研究领域,鲁迅致力于“不登大雅之堂”古代小说的研究,与这一时期人们对小说的重视,特别是对于白话小说的重视,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另外,鲁迅对于宋元话本的论述也有某些不够准确之处。如他认为宋代说话艺术属于杂剧中的一种,并随着杂剧的消歇而衰亡,“然据现存宋人通俗小说观之,则与唐末之主劝惩者稍殊,而实出于杂剧中之‘说话’”;“南宋亡,杂剧消歇,说话遂不复行”(注:下划线为笔者所加,非原书所有)。其实,宋代的说话与杂剧属于不同的艺术类别,说话是口头表演艺术,杂剧是戏剧的一种,“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两者之间的兴盛与衰亡没有必然的联系。另外,鲁迅认为《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和《大宋宣和遗事》都属于宋元的拟话本,因为二书“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宣和遗事》是由作者“掇拾故书,益以小说,补缀联属,勉成一书,故形式仅存,而精彩遂逊”。而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和《大宋宣和遗事》都属于宋元话本,前者属于说经类,后者属于讲史类。
注释
①本文所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下同,不另注.
②欧阳健在其专著《〈中国小说史略〉批判》(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9-173页)中认为鲁迅有意贬低宋代小说,特别是宋代文言小说,他认为宋人比唐人更看重小说,宋文言小说地位甚至高于唐代。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
③赵宽熙先生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于现在意义和重要性已得到新的认识的敦煌民间文学资料,丝毫都未曾提到”(赵宽熙《对鲁迅中国小说史学的批判性研究——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5期),不知赵先生依据的是何种版本?
④卢世华《元代平话研究——原生态的通俗小说》,中华书局2009年,第41页.
⑤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⑥周兆新《“话本”释义》,《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胡莲玉《再辨“话本”非“说话人底本”》,《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9期.
⑦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2000年,第3-4页.
⑧刘兴汉《对“话本”理论的再审视——兼评增田涉〈论“话本”的定义〉》,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4期;萧欣桥《关于“话本”定义的思考——评增田涉〈论“话本”的定义〉》,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Z1期.
⑨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6页.
⑩萧相恺《宋元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