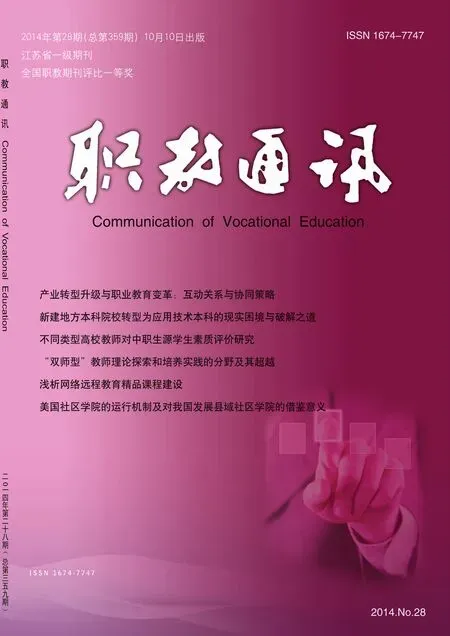教育中的争论、调和与迷失
刘 虎
肖思汉在美国的中小学课堂进行了随堂观察,其观察时间之长、观察内容之仔细都令人感到佩服。肖思汉还将其印象深刻的一节科学素养课和我们做了分享。在一堂关于“生命体特征”的课堂上,教师设计了一个科学问题,即“火是活的吗?”,随后教师精心设计了各种类型的活动和对话,让学生在互动、讨论以及积极主动的检索过程中养成科学素养,并逐渐掌握了一项项具体的技能,学生学会了检索信息,学会了判断信息的准确性。肖思汉进一步分析了美国科学教育的历史演进,他指出,美国科学教育最初强调知识掌握的多寡,强调知识本身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后来,美国教育界出现了日常实践学派,呼吁教育要回归真实的日常生活,要从普通人的视角教育孩子与科学打交道。在肖思汉看来,美国科学教育中的这种将“知识、技能与思维方式围绕‘日常生活’组织在一起的科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学徒制有相吻合之处”,同时,他也看到,传统的学徒制虽然能够较好地传授“特定的技能”,但是这种方式却忽视了一些“默会知识”,而“认知学徒制”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学徒制的不足,更好地促进学生科学素养的养成。
肖思汉对美国课堂的描述可能会让我国的老师们感到诧异,课堂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不是冲淡主题吗?学生最后学到了什么啊?如果要教授学生搜索信息和判断信息的技能,直接告诉他们不就行了吗?从中国教师和美国教师对待课堂教学的不同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国家教育理念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否有优劣之分,我们不敢妄下定论。然而,我们却可以从差异的背后看到教育发展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争论:知识与能力的关系,这个争论表现在学术层面,就是“形式教育”与“实质教育”之争,这场争论贯穿了教育发展的始终,支持两种观点的力量此消彼长,有对立、有调和、也有否定之否定,世界各国也基于对这种观点的不同认识形成了各自的教育形态。从各自的基本立场来看,“形式教育”者主张教育要发展学生的能力,而“实质教育”的支持者则认为教育要使学生获得知识。
“形式教育”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形式教育”思想的萌芽,昆体良最早对其进行了明确的表述,而裴斯泰洛奇被称为“形式教育之父”。形式教育思想纵贯人类早期的教育,在教育理论演进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美国《教育百科全书》中对“形式教育”这样界定:“形式教育主张通过学生学习的方法,而不是其学习的内容,来培养学生的能力”;《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指出,“形式教育”者的主要观点是:教育的任务在于训练心灵的官能,教育中灌输知识远不如训练官能来的重要,这是因为,如果人们的官能经过教育而发展,那么任何知识随时都可以吸收,即使知识被遗忘了,却依然留下了一种永久的、更有价值的效果,在具体的形式上,可以使用拉丁文法的教材训练学生的记忆力、使用数学教材训练学生的思考力。
19世纪初期,世界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要求学生培养掌握了一定实用知识的人才。这时,一些教育学家开始认识到,形式教育论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主张教育要能够使学生获得与实际生活和工作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这种主张被称为“实质教育”。一般认为,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泛智论和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是实质教育思想的缘起。在夸美纽斯看来,以往的学校始终存在一种倾向——完全割裂学校生活与校外生活的联系,学生看上去好像掌握了全部的知识,但是实质上并没有形成什么能力。我国《辞海》中对“实质教育”这样界定:“实质教育认为教育应当使学生学习有‘实际用处’的知识,学生获得这种知识的本身就包含着能力训练的作用。”我国教育学家施良方指出,实质教育的主张可以概括为:教育应该重视课程、教材的具体内容及其实用价值,从而使学生获得丰富的知识,同时必须重视课程和教材的组织,这是因为课程和教材的组织化程度及其呈现次序,直接影响学生的心灵的组织和程序。
形式教育与实质教育作为人类教育思想的两个极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然而,这两种思想也受到了人们的反思与批判,许多教育研究者试图对这两种思想进行“调和”、“否定”或者“否定之否定”。德国教育学家第多斯惠认为,形式教育和实质教育应该在教育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他认为,在初等教育阶段,形式教育应该占支配地位,因为小学生不需要学习大量的知识,而各种形式的能力训练则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好处,基于此,他讲出了这句教育名言“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而在中学教育阶段,则应该逐渐提出实质教育的目的,应多方面的高深的科学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也有学者认为知识和能力只是学生认知发展的不同阶段,但知识在前,能力形成在后。例如,加涅在其《学习的条件》一书中就说:“教育不应该仅仅关注知识的获得,而更重要的是关注知识在新的情境里的使用和泛化。但事实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掌握知识本身,知识迁移是不可能发生的。”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则试图消弭形式教育和实质教育之间的纷争,他认为,经验是最重要的东西,经验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也就是活动的过程,因为在杜威看来,学生学习知识和养成能力并不矛盾,它们可以统一在完整的活动过程之中。
虽然教育理论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然而,教育实践的发展却不能够被某一种教育思想所全盘把握,教育实践的改革与发展受到众多的诸如社会发展水平、知识形态、学生、教师等矛盾要素的相互作用与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改革都是一定的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在众多的矛盾要素中不断地寻找新的突破口和平衡点。特别是20世纪以来,受到社会发展和各种教育思潮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林林总总的教育改革运动,但透过现象的表面,人们也发展一个规律,即教育改革总是在两个极端摇摆或者转向。比如美国,在20世纪初期,主张适应生活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要求以儿童中心和活动中心课程取代传统的成人中心和学科中心的课程;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反实用主义思想抬头,教育领域又出现了“回归基础”运动。我们可以从各个时期“适应生活”、“学业优异”、“切合需要”、“高质量教育”等标志性口号中可以看到教育改革钟摆的不同摆向。
当前,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中,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鉴于我国传统教育过于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而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养成,因此,教育改革者们在极力呼吁教育要回归生活,要为学生能力的养成而服务。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教育研究者们关注到了建构主义、情境主义、认知学徒制等新的学习理论,希望借用这些理论为改革提供支持。这也导致在我国的教育理论话语体系中,言必称“建构主义”、“学徒制”等,似乎这些理论才是教育事业中的普遍真理,而传统的所谓“行为主义”、“学校教育”等则是没落和落后的代表,应该完全将其抛弃。人们在借用这些理论的时候,却很少关注这些理论是如何被提出。殊不知,现代流行的情境主义理论是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的方法通过观察学徒制中师傅和徒弟的学习以及观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学习活动而提出。建构主义理论提出了“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是自我建构”的论断,而这一论断的提出其意义仅仅在于让教育者更加关注儿童的主动性,因为任何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下,学生的知识和能力都必须自我建构,而不可能由别人替代,但在教育理论研究中,人们却将建构主义的作用和功能无限放大,以致教育研究似乎都成为了关于建构主义的研究。
无论是形式教育思想还是实质教育思想,我们都无法证明其正确性,反过来讲,我们也无法证明其错误性,对这种思想的折中与调和,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根据实际需要而进行,任何一种改革仅仅是课程改革钟摆向某一个方向的摆动。认识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无需将各种理论置于过高的位置,反而是过于纷繁复杂的理论,往往会造成人们的无所适从甚至迷失。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借用胡适先生的一句话,“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当我们真正关注教育实践的时候,随着实践中问题的一个一个地解决,相信我们的理论大厦也会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