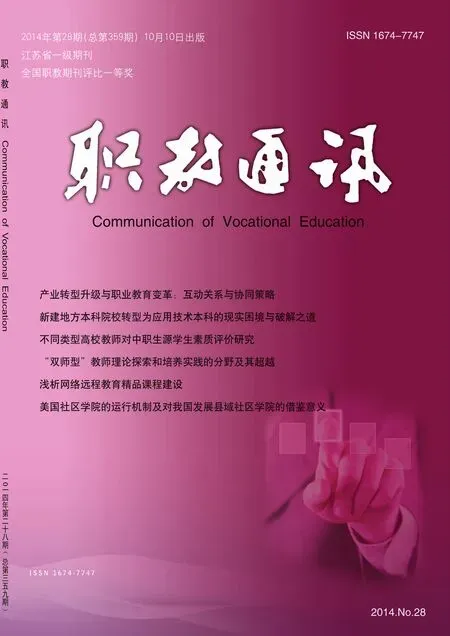“现代职业教育”思辨(三):作为社会治理节点的职业教育
臧志军
通过前两个月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工业化之前的职业教育是一种分布式的个体化教育,学习的方式是个人体验,教育的内容是上一辈人的经验;而工业化时代的职业教育则是集中式的学校教育,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标准化的知识与技术成为教学的中心。我们还知道,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力量对职业教育的介入——国家越来越多地成为职业学校的举办者或资助者、越来越多的国家制订了统一的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了对职业学校的统一管理、越来越多的国家设立了全国统一的职业标准……
以上的表述,会让人以为职业教育的现代化伴随着职业教育的国家化。事实上,德国等大陆国家的现代职业教育早期发展确实存在国家化倾向,所以,我们才会提出“国家的学徒”的说法。不过伴随着绝对国家的解体,职业教育已经从国家化走向了社会化或公共化。这个问题100年前在杜威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解释。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写到:“(在18世纪的德国)国家不仅提出公共教育的工具,而且提供公共教育的目的。在教育实施方面,从小学的各个年级到大学的各个学院,整个学校都是培养爱国的公民、士兵和未来的国家官吏,并提供军事、工业、政治防御和扩张的手段,在理论方面,就不可能不强调社会效率的目的……教育过程被看作纪律训练的过程,而不是个人发展的过程。”紧接着,他引用康德的话说:“一切文化,都是从私人开始,然后从他们向外传播。只有通过具有博大的胸怀,能领会未来更好社会理想的人们的努力,才能使人类天性逐步地接近它的目的”。在讨论过两种教育哲学之后,杜威提出一个问题:一种教育制度能否由民族国家实施,而教育过程的全部社会目的又不受限制、不被约束、不被腐蚀呢?显然,杜威采用了一个二分法:国家的教育与社会的教育。在这个天平上,杜威明确地站在了社会的教育这一端。
在另一本名著《明日的学校》中,杜威使用了一个可以视为许多教育家理想的用语:作为社会改良机构的学校。他把瓦伦丁先生的学校作为例证,这个学校位于城市中一个贫穷和有色人种众多的地区,学生也全部是黑人。学校认识到这个贫穷的社区公共资源非常稀少,就向社会提供各种专门的课程和娱乐活动,“学校确实成为地区人民的财产,他们感到他们对学校里做的事情多少该负些责任。在某种程度上学校举办的范围较广的活动,就是当地人民自己的活动:他们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利用了学校的设备罢了”。
杜威之所以赞赏瓦伦丁先生的学校,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这个学校已经与社会改良机构结合起来,或者是这个学校已经成了社会改良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他的心中,教育不仅是一种公共的产品,更应是一种公共的事务,所以学校应该成为一个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节点。在杜威等人的推动下,美国的学校具有较强的社会性,无论是学校向当地社会的融入,还是学校向当地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都有一些特色。相比而言,中国的学校则习惯于筑起高墙、锁上大门,学校仿佛是社会里的一个个孤岛。所以,我们才不怕繁赘引用杜威,想告诉中国的教育者们我们已经落后于这个世界百年。
当然,中国有它特殊的情况,与强势的国家相比,社会本身发育就不健全,这种情况下,学校融入社会的难度很大。但我在吉林省抚松一所县级职教中心的见闻却说明事情并非不可为。这个县位于长白山脚下,全县多山地。学校经常组织教师开展大规模家访,发现有些学生家庭非常贫穷,用学校校长的话来讲是“穷到了无法想像的地步”,学校就在有限的资金中拿出一部分给这些家庭送去一些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学校承担了一些政府的农民培训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山区的地理和经济特点,送教下乡——背上培训设备,爬进山沟里,为农民上课。据说,有老师在送教下乡时因为大雪封山而困在山里长达一个多月时间。这所学校与杜威欣赏的瓦伦丁先生的学校都没有把自己仅看作圈养学生的农场,而是大大拓展了学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两所学校的不同点在于:瓦伦丁先生的学校更倾向于一种草根的做法——学校在当地招生、学校资金来自当地社区、学校为当地社区服务;与之相比,这所学校则借助了较多的行政资源——资金由政府提供、培训项目由政府发起。这可能就是中国特定情境下学校的社会化道路——依托政府、服务政府、服务社会。正因为此,我们认为,职业院校应积极融入整个社会治理体系,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节点之一。就像抚松那所学校校长所说:我们了解了一些县长、民政局长都不知道的农民的真实情况,我们只做了一点点工作就让农民感受到温暖,让青年走上了正路。
三个月来,我们试图说明职业教育已经从师傅——学徒的纯粹私人关系走了出来,尽管国家曾一度试图掌控职业教育,但实际上只能以有限介入而结束,目前的职业教育发展的主流是职业教育的社会化而不是国家化。如果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那我们只会把以前走过的老路再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