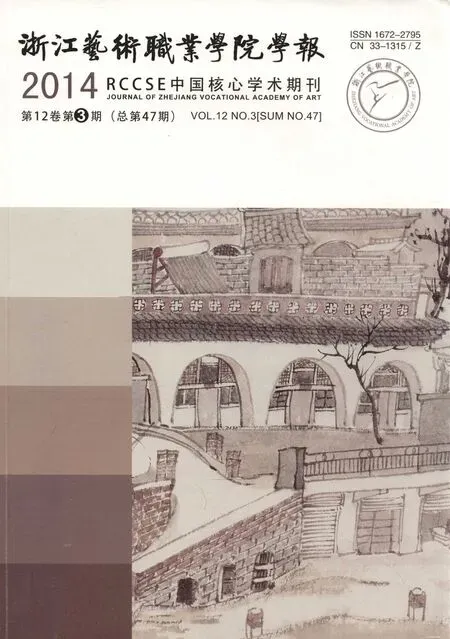对中国戏曲跨学科研究的思考
李 玲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了第四版学科专业目录。在这份目录中, “艺术学” 由一级学科升格为学科门类, “戏剧戏曲学” 二级学科也由此成为“艺术学” 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并改名为“戏剧与影视学”。虽然学术界对于艺术学的升格、学科设置及其研究建设的方法有诸多争论,①具体可参考张道一: 《艺术学研究的经纬关系》,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2004年第2 期, 第1-7 页。刘道广: 《艺术学, 莫后退——论艺术学研究的学科框架》,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 期, 第71-76 页。凌继尧, 付强: 《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 《艺术百家》, 2009年第4 期, 第47-52 页。徐子方: 《当代中国艺术学学科错位及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出路——兼论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问题》, 《艺术百家》, 2010年第3 期, 第54-58 页。刘道广: 《关于当前艺术学学科设置的三个思考》,《艺术百家》, 2010年第3 期, 第59-62 页。刘道广: 《学科升级背景下艺术学的“名” 与“实” 》, 《艺术百家》, 2010年第6 期, 第33-36 页, 等。但艺术学门类下各学科在理论研究和应用上的繁荣与进步是毋庸置疑的, 这同时也标志着21世纪中国戏曲学研究获得了进一步的环境优化。
回顾20 世纪至今的一百多年里, 中国传统戏曲研究历史中涵盖了戏曲的近代和现当代, 社会形态和理论思潮的变动及演进非常剧烈, 戏曲之场上演出与学术研究亦是如此。如果说近代西方学术思潮的流入及“五四” 前后对旧戏的争论刺激了中国戏曲的学术研究向科学化、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期戏曲学术研究更呈现出多元化、细致化的特点, 其中戏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是其学科发展的助力之一。
一、“跨什么” 与“如何跨”
戏曲的跨学科研究到底可以“跨什么学科”,又应该“如何跨” 呢? 根据已有对20 世纪中国艺术学的跨学科研究总结, 有学者主张中国艺术学历史演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五大分支: 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符号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人类学。②主张五大分支的代表性研究参见张晓刚: 《跨学科研究——20 世纪中国艺术学》, 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戏曲研究作为艺术学研究下属一级学科, 似乎应该同样存在着与之相对应的分类。但中国戏曲研究学者的总结则更为全面和开阔。郭汉城先生在1993年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八五” 计划重点项目中的《戏曲史论丛书》 所做的序言中提道: “中国戏曲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必须重视戏曲交叉学科的研究。因为有些理论上的重大问题, 不是在本学科的范围以内能够解决的。……其他如戏剧人类学、戏曲生态学、戏曲社会学、戏曲经济学、戏曲观众学、戏曲民俗学、戏曲宗教学等等, 都有广阔天地有待我们去开拓探索。”[1]刘祯、张静在总结中国戏曲发展历史的长文《百年之蜕: 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戏曲研究》 中提出: “新时期戏曲研究使20 世纪戏曲学体系更为完备, 不断向纵深拓展。戏曲研究传统的历史学、文学学、艺术学外, 又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新型学科方向开掘, 这包括戏曲文化研究、戏曲人类学、戏曲社会学、戏曲生态学、戏曲民俗学、戏曲宗教学、戏曲观众学、戏曲心理学、比较戏剧研究等等。”[2]
有学者提出: “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一方面, 学科愈来愈多, 分工愈来愈细, 研究愈来愈深入; 另一方面, 各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 愈来愈朝‘跨学科’、‘交叉学科’ 方向发展。”[3]由于分工的细化, 形成了“戏剧音乐是戏剧学与音乐学的交叉学科”[4]的现象, 造成戏剧学与音乐学分为两个学科的现象带有一些人为因素, 因为传统曲学包含文学与音乐学,但由于曲学分化导致中文系只教授曲的文辞, 而音乐院校只教曲谱却很少涉及古代文学, 所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学科细化与研究高度分工的发展导致了众多“跨学科” 的出现, 但是, 如果连戏曲音乐研究也成为“跨学科” 研究的话, 那么戏曲学本体研究究竟缩小到什么范围了呢? 戏曲是否只要与任何一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结合, 就能立即产生出一项新的学问?
如果回到跨学科研究本身来看, 学界一般认为应该定位为一种研究方法和手段, 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 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跨学科研究的结果有可能出现新的交叉学科, “但它集中突出的是问题, 更注重行动本身及其与社会联结的深广程度, 而不以成立学科为目的, 因而天然地蕴涵有吸收和集中学科之外非学科因素的意味, 这就不仅比交叉学科突出了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活动的群体性, 而且明显地具有实践效果的放大性”[5]。在前人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本文中所理解的戏曲跨学科研究, 主要是以围绕戏曲研究为中心, 从方法交叉、理论借鉴、问题拉动、文化交融四个层次出发, 展开与其他学科的横向渗透或交错叠合, 通过拓宽研究视野与途径, 以期实现对戏曲进行更为宏观与深入的整合性研究的目标。戏曲跨学科研究的具体研究领域包括戏曲文化研究、戏曲宗教学、戏曲符号学、戏曲生态学、戏曲心理学、戏曲人类学、戏曲社会学、戏曲民俗学、戏曲观众学、戏曲经济学、比较戏剧研究等等。
二、戏曲跨学科研究构建历程
众所周知, 中国跨学科研究的概念得到全面重视是在20 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事实上戏曲研究被纳入现代的学术研究范畴之后, 单纯依靠传统本学科的知识无法适应时代发展与学术进步的要求, 或多或少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或方法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因此也可以说, 早期中国戏曲跨学科研究之存在是远远早于“跨学科” 概念本身以及其方法的提出与普及的。当然, 在当时未有“跨学科” 研究理论体系指导的情况下, 大多数戏曲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主动意识来源于构建中国“剧学” 体系时的高瞻远瞩。
20 世纪前30年, 潜心于中国戏曲学建构的理论研究者们, 例如齐如山、冯叔鸾、宗天风、王梦生、徐凌霄等, 他们不仅解析戏曲本质论的根本问题, 更尝试在学术范式上提出科学性和体系性的要求。1932年徐凌霄在《剧学月刊述概》 提出一是要以“科学精神对于新旧彷徨中西糅杂之剧界病象, 疑难问题, 谋适当之解决”。二是要以“科学方法, 研究本国原有之剧艺, 整理而改进之, 俾成一专门之学, 立足于世界之林”。同时“剧学” 的主要内容有二, “ (一) 是关于戏剧的组织及技术方面, 剧本之结构, 剧班之管理, 剧场之设备, 剧艺之支配, 演员之技术, 乐队之组织, 及服装、道具、歌曲、舞蹈之应用等俱是”。相对于20 世纪初期之前以感性剧谈杂录为主要内容的戏曲理论来说, 这一学科体系建设的设想已经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另外, 他还提出“剧学” 内容之二是“关于戏剧所涵容之学问, 如心理、历史、哲学、宗教、音乐等皆是”[6]。可见在20 世纪30年代, 研究者们已经意识到戏曲作为一门新兴学问所具有的跨学科性, 这当然离不开“西学东渐” 体系架构的影响以及研究者们自身对近代科学的耳濡目染。因此, 如果说王国维在“戏曲史” 的研究上引入现代学术理念, 那么, 齐如山、徐凌霄等人则在“戏曲学” 上引入了现代学术理念。[7]
20 世纪前半叶的戏曲研究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开拓, 并且随着不断积累, 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范式与传统。1949年之后, 历史唯物主义的戏曲研究范式逐渐成为新的学术潮流, 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和介入, 戏曲研究范式变得单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逐渐非学术化, 加之话剧研究思维、成熟戏曲观以及历史研究中的线性发展观,戏曲研究的视野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不能否认的是, 中国戏曲跨学科研究真正的大发展是在20 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种大发展与中国戏曲研究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期间的极度萧条之后呈现出一种井喷式的大发展有关, 也与深刻影响到跨学科研究的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大背景有关, 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比较文学等学科迅速与国际接轨, 客观上为戏曲的跨学科研究发展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
三、戏曲跨学科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宗教祭祀戏剧——目连戏相关研究可以视为百年来戏曲跨学科研究的缩影。早在20 世纪20年代初, 周作人等学者已经注意到目连戏研究的重要性。在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研究的刺激之下, 钱南扬等学者开始对古老的目连戏进行了最初的系统学术研究, 但从研究的人员、方法、出版的成果来看, 影响都不大。①从这个领域研究成果的统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特点,参见茆耕茹: 《民俗曲艺丛书·目连资料编目概略》, 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 1993年, 第193 页。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62年期间, 虽然有一些目连戏的研究和整理, 但十年浩劫使这项重要研究几乎绝迹。改革开放之后, 特别是1983年国家开始编辑出版《中国戏曲志》, 极大推动了目连戏研究的发展。除了传统戏曲研究所强调的剧本整理之外, 杜建华的目连戏研究重点在戏曲文化的挖掘, 朱恒夫则更注重目连的宗教性与民俗性, 刘祯则体现出综合性的特点。除传统戏曲研究方法的广泛涉猎外, 还涉及民俗学、生态学、宗教学、中外戏剧比较等领域和方法, 真正实现了全面地、跨学科地审视目连戏的目的。而近年来, 目连戏研究中的戏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得到重视,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如徐宏图对浙江东阳、田仲一成对新加坡和广东乡村、胡天成对重庆、王馗对广东梅州等地目连戏的田野调查工作都取得了累累硕果; 在中国学者不断深入挖掘的同时, 也吸引了日本、美国等世界各地学者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参与。1984年湖南祁阳目连戏座谈会、198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组织的目连戏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郑之珍目连戏学术讨论会则吸引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新西兰等地40 多名学者。②对中国20 世纪目连戏总体研究的总结, 参见刘祯: 《20世纪中国宗教祭祀戏剧的研究》, 《戏剧文学》, 1997年第9 期,第29-33 页。关于建国以后目连戏研究特点的总结, 参见王馗:《鬼节超度与劝善目连》, 2010年版, 第15-51 页。无疑, 这种全方位、跨学科的发展趋势不仅仅限于目连戏研究, 而是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戏曲研究的基本特征。
比较戏剧研究应该是中国戏曲跨学科研究中产生比较早、成果比较多的领域。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 陈独秀(三爱) 在1904年的《论戏曲》 中,对比中西演员的社会地位, 提到“我中国以演戏为贱业, 不许与常人平等, 泰西各国则反是, 以优伶与文人学士同等, 盖以为演戏事, 与一国之风俗教化极有关系, 绝非可以等闲而轻视优伶也”[8]。由此提出戏曲不善者改弦更张的改良方法。在比较戏剧研究的早期, 多是简单的评论意见, 或者是“睁眼看世界” 的感慨, 这些言论及比较未必确凿, 或者也存在臆测的成分, 但从简单的中西戏剧特征罗列中找到了他者与自我比照的切入点, 这为后来出现的较规范的比较戏剧研究论文奠定了基础。在20 世纪早期, 余上沅《旧戏评价》 这篇文章归纳出西方戏剧写实, 东方戏剧写意的特点, 认为中国戏剧是纯粹的艺术[9]。在今天看来也许这样的结论并不深奥, 但在以西方戏剧为理想楷模、以戏剧的社会功能为准绳的文化激荡时期, 余上沅对西方戏剧较为全面的认识帮助他从世界戏剧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戏曲艺术,[10]这一认知是难能可贵的。王国维运用比较戏剧学的方法对中西悲剧做出的研究, 可以被视为早期戏剧比较研究的代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印戏剧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热点, 许地山 《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李满桂《沙贡特拉和赵贞女型的戏剧》 等都是代表之作, 此外, 林培志、朱维之、潘家洵、赵景深等人的研究也都产生了影响, 事实上, 学者们对梵剧与中国戏曲之关系的关注一直延伸到了下一个世纪。与学者案头的学理阐扬与引经据典的考证不同, 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 (下部) 则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中国传统戏曲演员, 在实地考察和全面交流基础上对中西戏剧比较的宝贵记录, 具有独特的价值①20 世纪前期中国戏曲比较研究的总结参见苏国荣: 《戏曲比较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概貌》, 《戏剧杂志》, 1986年第3 期。。1987年夏写时、陆润棠先生组织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比较戏剧学术研讨会, 次年在北京出版了《比较戏剧论文集》 一书,这次活动被视为比较戏剧学作为一门新学科诞生的标志[11], 其中夏写时《论中国演剧观的形成——兼论中西演剧观的主要差异》、陆润棠《中西戏剧的起源比较》、胡妙胜《中国传统戏曲舞台与现代西方舞台设计》、徐朔方《汤显祖与利玛窦》、刘若愚《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与元杂剧——两种戏剧中某种程式的比较》 等是这一时期比较戏剧研究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另外, 1989年暨南大学中文系出版的《中西戏剧比较教程》 里, 专门附录了从1926—1988年间发表的中外戏剧比较研究的目录。当这一研究被固定为大学课程并编辑出版了教科书时,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比较戏剧的复兴及学科意识的强化”[12]这样的评价是恰当的。随着比较戏剧研究的发展, 运用悲喜剧理论来比较中外戏剧的差别, 以及从中外某个剧目的比较来寻找各自戏剧体系的异同的文章较为多见, 另外, 其研究角度也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趋势, 逐渐开始从整体、宏观式的比较向更加具体、微观的方向发展,例如蓝凡《中西喜剧人物比较研究》、德国学者布海歌《中国戏曲传统与印度kerala 地方的梵剧的比较》、季羡林《吐火罗文A (焉耆文) 〈弥勒会见记剧本〉 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孙玫《 “中国戏曲源于印度梵剧说” 考辨》, 问题意识与许地山的研究一脉相承, 在中印戏曲比较的讨论中审视中国戏曲的起源; 苏国荣《日神与酒神——戏曲的文化模式》 一文则是戏曲文化比较领域的深入探索;张哲俊《日本能乐的形式与宋元戏曲》 体现中外戏曲国别比较, 特别是东方戏曲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
戏曲心理学方面的代表学者骆正先生研究文艺心理学和戏曲审美心理学, 他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传统戏曲的表演和人物塑造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 1991年的 《从现代心理学看传统戏曲文化——论〈贵妃醉酒〉 的艺术魅力》 是其代表作。符号学作为20 世纪80年代新引进的概念也被尝试着结合到戏曲研究中来, 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戏曲程式、脸谱与符号的相关性上来, 虽然仍然处于“引进” 和“尝试” 的阶段, 但也有不少新的思考,例如丁和根的《戏曲演出的符号化特征》、张生筠的《中国戏曲与符号学》 等。其他领域如戏曲文物学、戏曲观众学、戏曲民俗学、戏曲经济学等都涌现了许多代表性文章, 建立了各自的学术体系,有的甚至有专项研究所, 例如成立于20 世纪80年代的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
正如美国俄亥俄大学比较艺术教授罗伯特·沃特曼博士在跨学科研究时曾谈道: “如果跨文化研究能发挥其功能, 那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从广泛联系中审视专业性知识的机会, 因为它提供了思考这种知识的另一些途径。最重要的是, 它提供了一个以非正统方式进行实践的机会。如果这种情况真能发生, 知识的可用性就可能大大增加。”[13]中国戏曲跨学科研究植根于中国戏曲研究的深厚土壤,通过相关学科崭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角, 为中国戏曲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
四、戏曲跨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戏曲跨学科研究, 打破了传统学科划分形成的学术研究壁垒, 以开放的学术视野进行学术研究,这无疑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但是, 认真审视近年来中国戏曲的跨学科研究成果, 有一些动向和特征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是在全局化的“跨学科研究” 潮流中出现了对戏曲研究具有导向性的弊端, 产生了所谓“跨学科化转向” 的压力, 甚至出现了“不做跨学科研究就没有学术出路” 的倾向。于是, 将戏曲与各种学科相结合的努力纷纷出现, 令人眼花缭乱, 至于研究者本人是否具有扎实的传统戏曲研究功底,是否真正了解和把握了被借鉴学科的本质, 试图结合的两个或者多个学科之间是否存在有机联系, 新方法是否能真正拓展对于戏曲的深层次认识等问题, 则不在考虑之列。换句话说, 就是为“跨学科” 而跨学科, 这种方法很值得商榷。例如有年轻学者尝试利用2004年美国人提出的经营管理学中的“长尾理论” 来研究戏曲市场的开发[14], 这种努力固然值得称道, 但无论是对长尾理论的理解,还是对戏曲市场的把握, 对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说明都有待提高, 特别是结论, 新的学科或者观点的介入, 并没有给人们提供崭新的视角或者结论, 也没有对既有的研究提供更有力的佐证。因此可以说, 跨学科的研究是有前提和限度的, 我们应该秉承更谨慎的姿态。
另外一种现象是跨学科研究的全面发展, 可能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基础学科的重心位移, 使传统基础学科为其“新兴” 付出自我泛化的代价, 甚至面临自我消解的危机[15]。苏联艺术学家齐斯在论及艺术学的跨学科交流时曾强调类似这种观点, 一方面是艺术学借鉴其他科学的原则和材料作为分析工具, 另一方面, 还应该根据艺术学本身的传统把这些原则、材料和工具加以提炼。更准确地说,“各种方法、各种科学的工具消融在艺术学中, 艺术学是使研究艺术的各门科学形成系统的核心。”[16]近年来中国的戏曲跨学科交流出现过不少论争,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著名法学家朱苏力发表的《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一文, 引起了戏曲界和法学界诸多的批评①原文参看苏力: 《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第2 期, 第96-108 页; 评论文章参见康保成: 《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与苏力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科学》, 2006年第3 期, 第149-159 页; 康保成在上引书《中国戏剧史研究入门·开展跨学科的中国戏剧史研究》中也有评论, 参见同书第107 页; 陈建华: 《一次失败的跨学科研究——从苏力的〈窦娥的悲剧〉 说开去》, 《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3 期, 第13-18 页; 张建伟: 《窦娥的“二度被害”:读朱苏力〈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 》, 《清华法治论衡》, 2008年第1 期, 第15-59 页。。对于这次“失败的跨学科研究”, 戏曲研究学者更多是从文章中对戏曲知识与版本等理解的硬伤, 以及混淆文学与史学界限等视角进行批评。其实, 如果认真去看朱苏力这一文章的背景可以发现, 他的主旨是借戏曲个案来研究中国传统司法制度问题②朱苏力类似的研究还很多, 如苏力: 《复仇与法律——以〈赵氏孤儿〉 为例》, 《法学研究》, 2005年第1 期, 第53-69页; 苏力: 《传统司法中“人治” 模式: 从元杂剧中透视》,《政法论坛》, 2005年第1 期, 第49-62 页; 苏力: 《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以元杂剧为材料》, 《法商研究》, 2005年第2 期,第73-86 页., 从本质上说, 与其将其视为戏曲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所谓戏曲法学, 不如将其视为法学跨学科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当然, 那些对其进行批评的文章, 是真正戏曲学跨学科研究的范畴。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的话, 对于戏曲跨学科的各个领域研究是否都需要进行一定的界定。如部分戏曲民俗研究学者强调这样的观点, “戏曲民俗研究既可是戏曲学者借助民俗角度去研究戏曲, 也可是民俗学者借助戏曲角度去研究民俗, 还可是戏曲和民俗双管齐下的整体性研究。”[17]借助民俗学研究戏曲毫无疑问是戏曲跨学科研究的范畴, 那么借助戏曲研究民俗呢? 我们是否应该确认, 在戏曲跨学科研究中, 戏曲学的本体地位和基本关切仍然是根本, “以围绕戏曲研究为中心” 这一前提条件不能抛弃, 其他不同学科借鉴过来的方法只能是辅助, 而不能喧宾夺主。
从百年来中国戏曲跨学科研究论文的数量统计来看, 20 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领域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这种发展趋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下去, 戏曲研究学者吸收借鉴的学科数量会进一步增加, 不同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追踪吸收会更准确及时, 不同学科与戏曲研究有机结合的力度会不断深入, 也肯定会取得更多优秀的研究成果; 同样我们也期待着, 更多学者在推动戏曲跨学科各个具体领域研究的同时, 也要高度关注对戏曲跨学科研究方法与范畴本身进行更高层次的总结和规范。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推动戏曲跨学科研究的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
[1]郭汉城. 序[M]/ /马也. 戏剧人类学论稿.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3: 3.
[2]刘祯, 张静. 百年之蜕: 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戏曲研究[J].戏曲研究, 2002 (58): 38-39.
[3]康保成. 中国戏剧史研究入门·开展跨学科的中国戏剧史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105.
[4]康保成. 中国戏剧史研究入门·开展跨学科的中国戏剧史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106.
[5]刘啸霆. 当代跨学科性科学研究的“式” 与“法” [N].光明日报, 2006-04-06.
[6]徐凌霄. 剧学月刊述概[J]. 剧学月刊, 1932 (1): 5-7.
[7]黄霖, 陈维昭.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戏曲卷·20世纪前30年的戏曲建构 [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06: 266-269.
[8]三爱. 论戏曲[M]/ /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53.
[9]余上沅. 旧戏评价[M]/ /余上沅. 戏剧论集. 北新书局,1927: 18.
[10]单跃进. 失而复得的“写意” 演剧观——余上沅旧戏观二题议[J]. 上海戏剧, 2006 (2): 31-35.
[11]夏写时. 前言[M]/ /夏写时, 陆润棠. 比较戏剧论文集.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
[12]乐黛云, 王向远. 比较文学研究[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441.
[13]罗伯特·沃特曼. 美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现状[M]. / /郑雪来. 当代外国艺术.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105.
[14]王小梅. 长尾理论引发的当下戏曲市场思考[J]. 福建艺术, 2007 (6): 10-13.
[15]肖鹰. 美学跨学科研究的初步检讨[J]. 光明日报, 2006-03-28.
[16]齐斯. 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M]. 北京: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231.
[17]李祥林. 民俗学与中国戏曲研究[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 114-119.
——弋阳腔艺术保护中心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