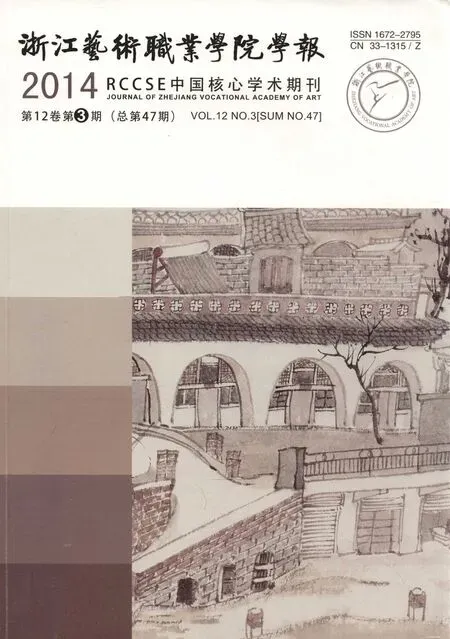关于大众化与程式化——1978年王传淞与王朝闻的一次谈话①
按 语:王传淞(1906—1987), 昆剧表演艺术家, 戏曲教育家, 昆剧副丑的代表人物。他在《十五贯》 中成功塑造了娄阿鼠形象, 深入人心。1960年后, 王传淞曾执教于浙江艺术学校首届昆剧班。王传淞十分注重昆剧人才的培养, 王世瑶、林继凡、刘异龙、范继信、陶波等都曾得到过王传淞的教诲。本期专题推出5 篇文章, 对王传淞的昆剧表演艺术做全面的研究。
王朝闻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
王传淞你出题目。
王朝闻我有一点不明白: 为什么昆曲这样优美而丰富的艺术, 观众总是不多?
王传淞因为昆曲生了毛病。记得1978年春天,在南京召开的昆曲座谈会上我已经讲过:粉碎“四人帮”, 昆曲得解放。但光是“解放” 了, 不等于原来的毛病都医好了。依我看, 新病已经产生, 旧病也可能复发, 弄不好病势还会蔓延; 最讨厌的是“并发症”。
王朝闻你说说有哪些是新病? 哪些是旧病?
王传淞曲高和寡——因为太讲究典雅, 并且硬充风雅, 变得深奥、冷僻, 写怪字, 用怪典, 弄得一般有文化的人都看不明白, 听不懂, 这是昆曲长期来患的慢性病。
王朝闻这类戏大概写才子佳人的居多。
王传淞不错。昆曲和古代传奇的作者, 常常借戏里的才子佳人的吟诗作对来卖弄自己的才华, 舞文弄墨, 咬文嚼字, 雕凿牵强, 为了要炫耀自己样样懂, 就只好叫大家不懂。一般在写才子佳人和名臣高士的时候, 用典特别冷僻。甚至有几出付副行当的戏, 作者也是舞文弄墨, 让戏里那些挑葱卖菜、揩桌抹凳的“下等人”, 居然嘴里都是《诗经》 《论语》。
王朝闻你演的那一类丑角和副角的戏, 很多都是下层人物, 他们不应该咬文嚼字。
王传淞但是作者偏偏要咬文嚼字。《水浒记》 里的张文远, 不过是一名刑房帮办的书记,现在讲起来, 是个抄写员之类的小人物、小知识分子, 或者小市民。他在《借茶》这出戏里, 借口讨茶吃去兜搭阎婆惜, 完全是市井无赖勾引妇女的行为, 从思想到行动都是极其庸俗的。这出折子戏, 刻划人物非常深刻, 表演也极细致, 但是作者硬是要用许多文绉绉、酸溜溜的句子让他来唱。一出戏不到20 分钟, 用了30 多个典故, 有时一句唱词六七个字, 竟连用三个典故。有些字在字典上也没有。譬如“螮蝀” 这两个字, 我从15 岁学戏开始,一直记不住它的字音, 等到记住了, 也不知啥意思。老先生自己也解勿出。老实说, 后来还是想了个自己易认易记的同音字注在旁边, 才总算记住了。一出 《借茶》, 竟让我当了半辈子文盲!
王朝闻当初昆曲老前辈里, 不是也有不少很有学问的老先生吗?
王传淞那时候, 大文学家我们攀不上话, 连一般文人自己也勿认识。直到1962年祖安来昆剧团写本子, 同时帮我和传瑛整理表演的心得, 我就请他把《借茶》 翻译成白话, 总算彻底弄明白了。螮蝀原来是天上彩虹的别名。据《山海经》 上说: 虹是一种动物, 还有一雌一雄, 雄的叫螮, 雌的叫蝀。我们中午在虎跑喷水池看见的虹, 不知是雌的还是雄的?
王朝闻真好笑, 都是庸人自扰! 过去文人卖弄笔墨, 倒给唱戏的找了好多麻烦。
王传淞昆曲老本子里有不少这种洋相。《牡丹亭》 《西厢记》 《长生殿》 里也有。最好笑的是《虎囊弹》 中《醉打山门》 一出,鲁智深吃醉了酒后有一段唱, 里面竟用了“济癫僧” 的典故。鲁智深是北宋人, 同徽宗道君皇帝同一代, 济癫僧是南宋小康王这一代, 阿爹用孙子手里的典故, 好像讲勿通。
王朝闻对! 虽然都是传说中的人物, 但是既然有个时代的界限, 不应该再混淆了。
王传淞是啊! 如果认为传说里的人物都好颠倒,让穆桂英嫁给了杨老令公, 这总不行吧?哦, 我说远了。我是说老戏里乱用典, 像《借茶》 这样一出折子戏, 为了查到出典在哪里, 得把《诗经》 《离骚》 《庄子》《山海经》 几十种冷僻的古书都翻遍, 才晓得其中意思, 叫演员和观众怎么吃得消? 据我晓得, 就连从前的吴梅、俞粟庐、徐凌云教昆曲本子, 也读过白字。而像赵景深、吴白匋、俞振飞和陆兼之, 这些都是当代昆曲界有学问的先生, 他们也有勿认识的字, 如不打幻灯同样也听不懂。我没有得罪他们的意思。振飞就亲口对我说过: “古本上有的字, 恐怕《康熙字典》 上也寻不到!”
王朝闻对。昆曲曲文的深奥、冷僻, 加上曲牌的繁复, 何况演员也不能每一句都真正领会, 自然不能准确地表达, 这就苦了观众。
王传淞演员只能大致上表达这个意思, 有的是瞎猫拖死老鼠——撞着算数的; 有的是黑铁墨塔——认不清楚, 就像瞎猫把酱瓜当老鼠来捉。这样, 就会造成表演上的形式主义。
王朝闻对。古老剧种有一套比较规范的表演程式, 如果运用不当, 不从人物出发, 不根据人物的性格、感情和情绪来表达, 程式化就会出现, 也就是你所讲的形式主义。
王传淞这也就是我们昆曲衰落的缘故吧。
王朝闻《十五贯》 应该是推陈出新的一种典范。它含义很深刻, 但是不生僻, 很大众化。应该说, 这是昆曲改革的一个重要开端。
王传淞是的。《十五贯》 是昆曲走向通俗化的一个重要的尝试。周总理也说过: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新中国成立后, 昆曲是枯木逢春, 又抽了芽。这表明它还没有完全枯死。
王朝闻新中国成立后, 昆曲得到政府的关怀, 有了阳光, 又活过来了, 但是关键还是自己仍有生命力, 所以才能抽出芽来, “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十五贯》 这出戏,从剧本到舞台艺术, 都体现了昆曲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的。
王传淞光有生命力, 不等于它能很健康地活下来。因为它身上有好几种病没有根治。“救活了”, 又不等于万事大吉。60年代,我们改编了古装戏《西园记》, 从内容到舞台艺术都有所改革; 后来创作和改编了现代戏《血泪塘》 及《红灯传》, 又在昆曲走向大众化中迈出了一大步。当时从省委到文化部门, 都很支持。《浙江日报》还就昆剧编演现代戏的问题, 讨论了一个多月。大家认为, 昆曲也可以跟上时代。这些年来, 昆曲又出现了一些老毛病。从1978年到1982年, 先后在苏州、南京开了四次会议, 大家讨论的还是一个老问题: 昆曲要争取观众, 它面临一个往哪里去的问题。因为太守旧, 能看懂的人太少, 这样, 观众的圈子也越来越小。有人说, 昆曲应向电影靠拢, 向话剧和京剧靠拢, 我看也不行。还有人提出干脆关门不公演, 专门作为一个研究文化遗产的团体, 这样行不行? 我看同样不行。因为昆曲毕竟还是一个活着的剧种, 并非出土文物, 不能单为了几个考古的人欣赏的需要, 像一本旧皇历一样锁在抽屉里, 每逢黄道吉日才翻一次。
王朝闻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之所以喜爱昆曲, 是因为感到这门传统艺术确实精彩和丰富,但并没有对它作过更多的研究。我认为,作为我们民族历史悠久的一种传统艺术,它既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又能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传统的演法——如果它不是深奥到使人费解的话, 可以作为一种古典艺术存在。像日本歌舞伎那样, 成为一种艺术上的国宝。中国那么大, 历史那么久,也应该有一些优秀的古老艺术继承下来,流传下去。但是, 你是一位艺术家, 一个共产党员, 一个社会主义的戏剧工作者,又是昆曲艺术的老前辈, 你所关心的, 你所忧虑的, 主要是昆曲如何能在今天立足于人民之间, 如何能为现实服务, 这也是很重要的。我理解你的心情。我觉得, 你对昆曲的意见, 恐怕还不仅在剧本的文字上。
王传淞对。我还对现在昆曲的演唱有些看法。这里关系到一个剧种究竟有多少人喜欢看的问题。观众的多少, 决定剧种的生存。
王朝闻这是对的。一个剧种, 不能光为了让少数几个专家看, 要使更多一些的观众也喜欢看, 尤其是戏曲团体。对广大观众来说,唱得好听不好听, 这一点很重要。
王传淞昆曲在表演上的长处, 大家是公认的。现在的问题是它的唱要使更多的人喜欢听。但是不少观众认为昆曲唱起来不好听。据说老先生传下来的昆曲有上千种曲牌, 现在能用的还有几百种, 常用的也有上百种。但是观众却说: “听起来都是依—咦—吁—哦”, 差不多。
王朝闻对, 我听起来也好像大同小异。但是我想, 如果都是差不多, 怎么会有上千个曲牌呢?
王传淞因此观众到了剧场里, 常会传染一种“病”。这个毛病大约是近几十年来才生的。
王朝闻什么病?
王传淞叫做“瞌睡病”。有些演员嗓子条件不算差, 但是都照一种谱子哼, 既不讲究韵味, 也不追求风格特色; 既唱不出味道,也唱不出感情, 总 是 “依—咦—吁—哦”。你说唱得不对, 倒是有板有眼, 而且都是定了曲谱的, 何况简谱、五线谱比你工尺谱要科学, 可是却唱得连自己快要睏熟, 观众都想瞌睡。所以有些原先对昆曲并不了解又只偶尔听过一次的新观众,就把昆曲叫做“睏曲”。
王朝闻你太夸张了一点。我听过许多老年和中年演员的演唱, 都不是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的吗? 俞振飞唱得多好!
王传教当然, 唱得好的也有。尤其是有些较有名气的, 演唱上确有功夫。俞振飞不但熟悉音乐, 也熟悉唱法, 更熟悉昆曲演唱的特点, 所以他的唱格外好听, 有橄榄味道。
王朝闻什么叫橄榄味道?
王传淞这有两种意思。一是昆腔的发声和收声,先尖中圆, 后面又尖, 由于中间大、两头小, 像橄榄形状, 所以就叫“橄榄腔”;二是因为橄榄吃起来, 味道不是马上品得出的, 起先有点涩口, 有点苦, 但是回味却特别好。有人形容第一次吃橄榄, 觉得味道苦, 将它丢到草房顶上去了。后来回味越来越好, 就爬到草房顶上去找, 把草房也爬坍了。昆曲的腔调, 应该是像橄榄那样, 要使听的人感到回味无穷。俞振飞就是这样。上海、浙江、江苏的有些中年演员唱得也有这么一点味道。可惜现在昆曲演员中唱起来有这种味道的还是太少。
王朝闻我看这是由于后来分批招考进来的青年演员, 对老一辈演员的艺术特色, 对传统的艺术特点知道得太少的缘故。一个剧种,尤其像昆曲那样古老剧种的昆山腔, 它的特色应该是很强烈也很吸引人的。
王传淞确实如此。明朝万历年间魏良辅和梁辰鱼创造了“水磨腔”, 使昆山腔有了进一步发展。好像水碓里磨糯米粉那样, 又糯,又软, 很好听, 所以叫“水磨腔”。
王朝闻这种“水磨腔” 流传下来, 随着历代优秀演员的不断创造, 特点一定越来越鲜明。
王传淞不错。听说从明代到清代都有不少好演员, 有不同的唱腔, 但我都没有听见过。又听说自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 还有不少流派。1962年我们在苏州听几位全福班的老人回忆说, 当年全福班和鸿福班里都有不少好唱腔。俞振飞、顾传玠和白云生都是小生, 他们的唱腔各具特色, 而且又都很好听。
王朝闻其实这就是流派唱腔。
王传淞对。任何一个古老剧种, 都是靠历代优秀演员的演技和流派唱腔丰富及发展起来的。中国古典戏曲, 声腔是主要的, 声腔和语言的特点最要紧。可惜近几十年来,昆曲的流派唱腔不但没有很好的发展, 连一种唱腔——就是根据一个曲牌照样地唱, 也唱不好。我当然不是讲全部, 是讲相当一部分。
王朝闻照理说, 现在青年演员有文化, 有乐理知识, 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王传淞可惜他们偏偏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考进来时不少已有初中文化程度, 等到毕业至少高中水平。他们懂乐理, 自己会哼谱子, 但是拍曲子唱戏时却像唱歌, 好像中国人学唱外国歌。正因为唱不出特点来,所以没有橄榄味道, 也就对昆曲失去了信心。还有一些青年演员热衷于学京剧, 学越剧, 学唱歌, 可就是不热心学好自己所从事的昆曲。“十年动乱” 中昆曲又被当做垃圾, 还差一点给扫掉。现在应该是爱好自己昆曲的时候了。然而有些青年演员并不安心学昆曲, 觉得昆曲观众少, 票房价值又不高, 因此缺乏信心, 即使自身条件很好的也千方百计想改行, 更谈不上自豪感。这样长期下去, 昆曲的观众自然会越来越少, 干这一行的信心也更加不足了。
王朝闻看来还是要有一批爱好昆曲的人努力把昆曲振兴起来。实际上, 唱腔、语言和表演都是一种形式, 是一个剧种形成自己特点的标志。
王传淞不错, 就是形式问题。我看, 如果对一种艺术的形式都不掌握, 还谈什么继承和发展呢? 现在犯的一个主要毛病, 还是形式主义。
王朝闻对。中国戏曲艺术很讲究形式美。形式要讲究, 但是又要反对形式主义, 因为它要破坏艺术的形式美。
王传淞对。你肚里墨水多, 讲得清楚。为啥会有这个毛病呢?
王朝闻这还是不懂得自己剧种艺术形式的特点在哪里的缘故, 因此就往往会产生形式主义。这和戏曲讲究程式又反对程式化的道理一样。你认为对不对?
王传淞有道理。对症就好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