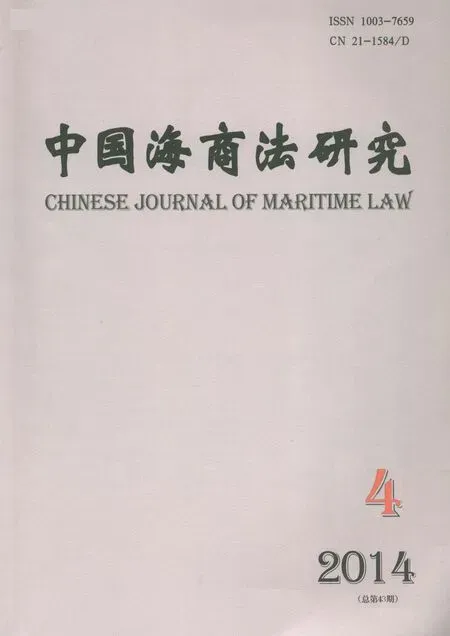南极生物勘探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
刘 茜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南极一直被视为人类的最后一片净土,因其丰富的生物资源,一直被世界各国争抢与觊觎。南极生物勘探被世界各国提上日程,通过对南极生物的勘探以及对生物资源的后续开发利用,获得巨大的产业价值与经济利益。世界各国打着科学考察的名号,对南极生物资源无秩序的勘探活动不仅破坏了南极生态环境,也出现了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目前,国际上并无专门的法律规制南极生物勘探,《南极条约》体系下现有的国际法律制度对此均有所涉及,但在适用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基于这样的背景,笔者从南极生物资源勘探引发的国际争端的实质、历史演变及焦点入手,论述现有法律制度对南极生物勘探的规制现状:《南极条约》体系没有涉及如何规制南极的生物勘探商业应用研究;《生物多样性公约》惠益分享原则无法适用于南极生物勘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未明确管理和养护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底区域生物资源保护的相关制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一般性原则、程序性规定阻碍南极生物勘探产品的专利权的归属,而后笔者创新性地提出对未来南极生物勘探法律规制的突破建议,倡导以科学研究而非纯商业利益的目的进行南极生物勘探;建立一套独立、综合、权威的南极生物勘探管理、监督、救济法律制度;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为视角,构建完善的南极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在国际法和南极条约体系的协调和融合下寻求解决的方法,以求对构建南极生物勘探管理制度有所裨益。
一、南极生物勘探引发各国纠纷
南极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具有巨大的经济、商业、医用价值。《南极条约》冻结了南极的领土主权,导致了现有的南极生物资源权属不明。近年来,因南极生物资源潜在的可观利益,导致了南极生物勘探问题纠纷不断,引发了一系列南极生物资源勘探国际争端事件的发生。
(一)南极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
南极生物资源具有巨大的经济、商业、医用价值,因此成为国际社会广泛争夺的焦点。南极生物勘探依赖于南极生物的多样性,南极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仅鱼类就达到200余种。其中,最具开发价值的为磷虾,开发价值高,储量丰富,可供人类对水产品的需求。[1]除此之外,南极大陆边缘有藻类、苔鲜、地衣等低等植物分布,在维系地球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目前的南极生物勘探中,最具应用价值的是南极微生物。细菌、酵母和丝状真菌等微生物具备独特的生物学适应机制和生理生化特性,如耐冷、耐盐、抗辐射等,被作为重要的潜在生物技术应用资源。[2]近年来,南极生物勘探资源已经被广泛用于制药、食品、化工、生物技术等工业应用领域,成为各国开发战略资源的重点之一。
(二)南极生物勘探的历史演变
南极生物勘探的发展历程跟当时的世界形势与科学技术息息相关,其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起始阶段(18世纪初末—20世纪60年代):这一阶段,南极因为没有法律规制的管制,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只有阿根廷、智利等少数国家在南极建立科学考察站。直到20世纪40年代,英国、新西兰、德国等国纷纷宣告各自对南极的领土主权范围,导致南极被卷入了各种国际争端。但这一阶段南极的各种国家争端并没有涉及南极生物资源勘探方面的内容。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大多数国家没有足够的技术实力与雄厚的经济力量作支撑,对南极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下的生物资源勘探技术掌握得不够充分。
缓慢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20世纪末期):世界大战后,各个国家内外政治环境稳定下来,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能力关注资源丰富的南极,开始出现各种资源纷争。为约束各个国家的行为,《南极条约》《保护南极动植物议定措施》《南极海洋生物保护公约》《海豹保护公约》《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等应运而生。一些国家在《南极条约》体系所确立的宗旨下,修建了南极科学考察站,为下一阶段的南极生物勘探顺利进行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依据。
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末—目前):这一阶段,多数国家在南极建立的科学考察站有了科技成果,南极生物勘探的种类、地理范围都在随着各国技术水平与经济实力的提高而与时剧增。世界主要国家都以“国际极地年”为契机,设立“南极特别保护区”,潜在的南极生物资源勘探争端始终存在,同时也越来越白热化、复杂化、隐蔽化,但表现却更加科学与合法,各国对生物勘探成果的保护力度也在不断增强。
综上所述,南极生物勘探的每个阶段发展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南极生物勘探也从简单的科学考察演变为直接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国际争端的解决除了需要依据政治层面的较量,最终还需上升至法律层面寻求法律途径的解决。如何在保护环境、资源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国际法律规制,成为当前南极生物资源保护的核心和最终目的。
(三) 南极生物勘探纠纷的焦点
《南极条约》冻结了领土主权,导致了现有的南极生物资源权属不明,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关于南极生物勘探的纠纷极具特殊性、复杂性、急迫性。具体分述如下。
1.南极生物勘探破坏了南极生物多样性
从南极生物勘探活动现状来看,大多数国家并不局限于对南极原始生物遗传物质的勘探,而是将其扩展到了微生物等具有遗传性的生物化学物质。南极的自然条件与众不同,也就导致了在其自然环境下生长的生物往往集中在南极的某个区域,这一区域也就成为世界各国争相追逐生物勘探的区域,直接引起南极这一区域内独特生物数量的减少。[3]不合理的勘探活动,过度利用某一种或某几种生物资源,都导致了南极生物生存环境的破坏甚至消失,影响物种的正常生存,有相当数量的物种在人类尚未察觉的情况下便已悄然灭绝。
2.南极生物勘探已经对南极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
人类进入南极进行生物勘探,势必因排放废弃物等原因引起南极环境的变化,从而直接影响南极特有物种的繁殖和种群规模,使得南极的生态系统进入恶性循环。[4]将整个南极大陆视为一个特别保护区,动植物栖息和繁殖聚集特性、生态系统保护的科学价值等,应得到相关国政府的特别保护,以保存它们独特的自然生态系统。[5]由于南极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规范南极生物勘探环境的条约不仅能够对生物勘探活动进行一定的约束,而且有助于对南极环境及依附于它的生态系统的保护。
3.南极生物勘探结果的商业用途界定不明
南极生物勘探的利益共享包括商业利益、科研利益、科学考察成果信息利益等问题,但是这些利益在国际法范畴内很难在各个条约缔约国之间达成共识,也无法形成统一有效的利益共享的规则。南极生物物质的商业化利用并没有被南极条约体系所禁止,并且也没有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成员国提倡禁止南极生物的商业化利用。如何从一个平等、客观、合理的视角解决勘探结果的利益共享,实现人类共同的进步与文明,也是目前的国际争端焦点之一。[6]
4.南极生物勘探专利申请的争执不断
世界各国对南极生物勘探获取的科技成果都会想方设法地给予合法的保护,申请专利权是多数国家的做法。但是,南极作为一个无主权领土,任何国家都无法对其主张领土主权,那么从其领土上获取的生物资源专利权的申请如何界定,成为当前争论的一个焦点。在实践中,一些国家将从勘探活动中获取的成果申请了专利,并获得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认可。这对其他国家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影响。考虑到对于南极领土的利益共享原则与互惠互利原则,有必要制定相应的规则,对南极生物勘探的专利申请要求进行有效的限制和有序的引导。
二、国际现行南极生物勘探法律制度的适用与局限
当前,国际上对南极生物勘探的相关法律规制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南极条约》体系、《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法律制度对南极生物勘探有少许涉及条款,但是在适用上明显具有局限性,在有关南极海洋区域的问题方面存在诸多冲突。现分述如下。
(一)无相关条文规制生物勘探商业应用研究
《南极条约》体系在南极生物勘探法律规制中占据了“第一把交椅”,引领着其他国际法律规制的运行。《南极条约》冻结了所有南极主权的要求,使想强占南极领土的国家心如死灰。并且,《南极条约》确立了和平开发、科学考察自由和国际合作三大原则,将世界各国在南极领域的活动定位为南极科学考察。条约提到生物资源的仅有一处,即第9条规定各缔约国代表应制定与“南极生物资源的保护和保存”的有关的措施,但没有具体内容。随后,《保护南极动植物议定措施》《南极海豹公约》相继出台。依照这两个文件,除非是根据许可证采取的两个规定中的动植物或者海豹,其余商业目的的南极生物勘探活动均被禁止。《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规定了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提供长期的高标准的保护,要求《南极条约》非缔约方的本公约缔约方承认并适宜地遵守《南极条约》协商国推荐的措施去保护南极环境。随后,《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及六个附件限制了南极活动对南极环境的不利影响,制定了维护南极现有生态环境的一般原则,并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地区保护和基金赔偿等制度,从各个方面保护南极生态环境的良好运行。[7]
综上所述,《南极条约》体系下的几个文件的出台,形成了以《南极条约》为核心的南极生物勘探保护体系,从不同的层面约束了各个国家的南极生物勘探活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各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科学技术都得到了飞跃的提升,对南极生物的勘探也从肉眼能勘探的领域发展到了需要更高科学技术的微生物等生物遗传资源的勘探领域,显然,此时的《南极条约》体系无法再圆满地完成它之前对于生物资源勘探的规制作用。尤其是《南极条约》体系在规制生物勘探的商业应用研究方面完全没有涉及,导致了生物勘探商业、专利申请等纠纷的出现,成为国际法律规制的一个盲点。
(二)惠益分享原则无法适用于生物勘探
1993年12月29日生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明确保护生物多样性,规定了三个原则:遗传资源国家主权原则、事先知情同意原则和惠益分享原则,防止过度的开采利用,以期达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各国合作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在生物勘探方面明确了两个内容:第一,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下,合理开采生物资源;第二,必须严格控制生物开采过程中的不利影响的扩散范围。各国在勘探生物资源的同时,必须保证权责一致,确保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活动,不得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虽然,《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出台给予了各个国家在南极生物勘探的明确依据,但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首先调整的是属于一国管辖范围内的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关系,《南极条约》已经将南极领土冻结,南极的生物资源也就无法纳入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那么《生物多样性公约》在调整南极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时,也就不那么具有强制的效力,可以说,《生物多样性公约》对南极生物勘探存在极大的阻碍作用。
(三)未明确管理和养护生物资源保护的相关制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一步明确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利用的管辖权,为不同方式迁徙的物种制定特殊的制度,对公海上渔业资源的管理给予规定,明确赋予了各个国家在公海上的捕鱼权利与自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关于公海上渔业资源的管理规定都可以作为南极海洋生物勘探的法律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海底区域制度,强调该区域及其资源属于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并统归国际海底管理局进行管理,但是,公约还未有管理和养护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底区域生物资源保护的具体法律规定。目前就海底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属性还存在定性上的争议。
(四)相关规定严重阻碍生物勘探产品的专利权归属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主要条款有:一般规定和基本原则,关于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及使用标准,知识产权的执法,知识产权的获得、维护及相关程序,争端的防止和解决,过渡安排,机构安排,最后条款等。其中一般性原则、程序性规定普遍适用于有关南极生物勘探的知识产权。但是,《南极条约》已经将南极领土冻结,南极的生物资源的产权问题也就成为一个极大的难题。南极生物资源不能完全适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一般性原则、程序性规定,其对专利权的要求具有其独特性。从另外一方面考虑,我们如果对南极生物资源设置了专利权的归属,授予给那些前商业的或者上游的研究产品,那么对该生物资源专利权的下游使用者与其他各国的互惠互利原则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微生物和基因序列,遏制了其他国家的利用,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有些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生物勘探成果,会利用保密协定加以保护,那么这种恶劣的影响更会加剧,极大地损坏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在保护南极生物勘探者的专利权的基础上,如何去保护其他国家的权利自由,以平等的地位去获取已经设置了专利权的物种资源,成为当前争议的一个焦点。
三、对未来南极生物勘探法律规制的突破建议
《南极条约》冻结了南极地区的领土主权,在没有领土主权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如何解释南极生物勘探活动在法律上的合法性,且如何合法界定本国正在进行的南极生物勘探活动,都需要明确的规则予以指引。对未来南极生物勘探法律规制的突破建议如下。
(一) 倡导以科学研究而非纯商业利益为目的进行南极生物勘探
南极生物勘探从应用目的来分,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勘探、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勘探。其中,以商业化应用为目的的生物勘探从南极生物资源的商业化应用出发,试图寻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破坏了南极生物的多样性。近年来,南极基因资源已经被广泛用于各个工业应用领域,对南极生物多样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绝大多数的生物勘探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有关搜索和检验生物资源的功能,已经被用于商业开发价值。由于目前对生物勘探的法律监管还不完善,南极生物勘探的商业化勘探处于混战状态。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各国国内展开的各项科学研究,其意图均是将科学研究的成果运用并造福于人类,而任何成果对人类的普及过程都是以商业化为手段进行的。从“生物勘探”到“科学研究”,再到“成果的商业化”,这是一个线型的过程,而非几个并列概念的比较。针对当前的南极生物勘探现状,我们应该提倡以科学研究而非纯商业利益为目的进行南极生物勘探。无论是在南极大陆,还是在南大洋的公海区域,生物勘探可依据《南极条约》和国际公约中“科学研究”的规定开展,而随后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的过程就不是规制生物勘探活动时应当考虑的问题了。[8]
(二)建立一套独立、综合、权威的南极生物勘探管理、监督、救济法律制度
虽然,《南极条约》体系、《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法律制度对南极生物勘探有一定的规制作用,但是这些法律只是从一个或几个单一的方面去规制南极生物勘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并没有一部完整的、独立的、综合的、权威的南极生物勘探管理制度出台。以南极生物勘探的现状为依据,结合各相关国际组织以及各缔约国的具体实践,建立一套专门针对南极生物勘探的管理与监督法律制度有着一定的紧迫性。
首先,从保护南极生态环境以及减少人类在南极活动的原则出发,对南极生物资源的勘探应采取特殊许可制度。对于进入南极领域进行生物勘探的国家,应该有专门的许可组织去授权与管制。对该管制组织的机构设置与权力进行明确规定。而对于许可进入南极生物勘探的主体及其行为也要有明确的管制内容。同时,设置相应的许可程序,对活动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管。
其次,为预防进入南极生物勘探的国家作出不适格的行为,对南极造成不良的环境影响,应该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现有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及六个附件规定了保护环境的一般原则和环境影响评价、地区保护和基金赔偿等制度,从而限制南极活动对南极环境的不利影响。南极生物勘探开发活动适用“预先防范、保护环境”的理念,确定生物勘探活动是否会对特定物种或栖息地产生负面影响,在生物勘探开展前应对活动的目的、地点、期限和强度予以说明,对进入南极进行生物勘探的国家应优先考虑该国的科学研究的价值,限制其后续无理由地扩大生物勘探商业化活动的申请;将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各缔约方保护生态系统义务的一部分,所有相关行为都应遵循原先设定的评估程序;一旦发现相关缔约国作出破坏南极环境的不适格行为,需立即作出相关反应,考虑可替代的方法和防范措施,阻止其进一步破坏,并承担相应的环境赔偿责任,从而预防对南极环境造成的影响和风险,保护南极生态资源的健康发展。
最后,南极生物勘探需要强力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与南极生物勘探有关活动的管理。可以将联合国作为监督机制的主体,毕竟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在协调国际经济关系,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科学、文化的合作与交流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另外,南极生物勘探需要强力有效的救济机制。通过分析目前南极生物勘探的现状,由于受到国际政治等相关因素的影响,某些国家的生物勘探活动或许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压迫,导致出现不公平的局面,所以,建立有效的救济机制,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自己应有的权益。
(三)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为视角,构建完善的南极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南极生物勘探的生物资源毕竟还是有限的,过量的生物勘探活动超过容量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实际上就是不断消耗生态资源。在南极地区的环境和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的情况下,秉承可持续发展原则去实施合理的生物勘探是十分必要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人类针对当前南极环境危机必须秉承的。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在未来南极生态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上,运用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保护南极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必经之路,不致因当代人类的欲求而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通过法律手段的运用来保护南极生态环境,制定对应的规范,做到有法可依,保持南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总之,在构建当前的南极生物勘探相关法律制度时,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原则,确保人类在南极的生物勘探活动不致损害南极原有的生态资源多样性,使其可以支撑后续的人类的活动。
四、结语
南极孕育了奇特且丰富的生物资源,被认为是地球上仅剩的“资源宝库”。《南极条约》冻结了南极的领土主权,但南极生物资源所带来的利益纷争仍然不断地在世界各国之间火热地进行着。在南极生物勘探问题上,世界各国首先应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和平地维护南极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稳定,倡导以科学研究而非纯商业利益为目的进行南极生物勘探,基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积极开展对南极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其次,建立一套独立、综合、权威的南极生物勘探管理、监督、救济法律制度,从国际法律层面,保护南极生物资源的合理开发、有序开展,同时维护国际社会秩序。最后,世界各国应以南极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为出发点,严格限制生物勘探活动无节制的开发利用,秉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保护南极环境与生态。综上所述,世界各国开展南极生物勘探活动必须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制,合理约束南极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人类共同财产共同维护和利用,这是人类共同的义务和责任。
纵观现在的南极生物勘探活动,大多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进行的。在南极地区进行的一切活动也都强调人类共同的利益,实现各个国家在南极地区的利益共享。站在中国的立场而言,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在中国实施以来,中国作为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成员国,严格执行委员会各项措施和决议,认真履行成员国义务,国际履约能力日益提高。随着其他国家越来越注重南极生物勘探的立法保护,加快中国南极活动管理立法步伐也成为大势所趋。将已经生效的《南极条约》及其议定书、“措施”及中国承诺的国际南极管理规则转化为国内法规,对中国在南极的生物资源利用开发活动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既可以保障中国在南极现有的生物资源利用活动——南极科学考察活动,实现对南极科学资源的有效利用,也可以提高中国在南极事务方面的国际地位,增强中国参与制定国际南极“游戏”规则的话语权,从而切实维护好中国在南极所享有的生物资源利益。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孙雷,周德庆,盛晓风.南极磷虾营养评价与安全性研究[J].海洋水产研究,2008(2):57-64.
SUN Lei,ZHOU De-qing,SHENG Xiao-feng.Nutrition safety evaluation of Antarctic krill[J].Marine Fisheries Research,2008(2):57-64.(in Chinese)
[2]李田,刘光琇,安黎哲.低温微生物的适冷特性研究进展及其应用前景[J].冰川冻土,2006(3):450-455.
LI Tian,LIU Guang-xiu,AN Li-zhe.Properties of cold-adapted microorganism their application prospects[J].Journal of Glaciology and Geocryology,2006(3):450-455.(in Chinese)
[3]GEORGE F,KELLY D.Bioprospecting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what happens when discoveries are made?[J].Arizona Law Review Summer,2008(2):545.
[4]BIERMANN F.Concern of humankind:the emergence of a new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J].Archivödes Völkerrechts,1996(4):426.
[5]刘秀.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南极资源的法律研究及中国的战略选择[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10-115.
LIU Xiu.Research on the laws concerning the sustainable use and protection of the Antarctic resources and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China[J].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2013(1):110-115.(in Chinese)
[6]LOHAN D,JOHNSTON S.Bioprospecting in Antarctica[EB/OL].[2014-10-22].https://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BsQFjAA&url=%68%74%74%70%3a%2f%2f%77%77%77%2e%75%6d%61%67%2e%63%6c%2f%67%61%69%61%61%6e%74%61%72%74%69%63%61%2f%3f%77%70%64%6d%61%63%74%3d%70%72%6f%63%65%73%73%26%64%69%64%3d%4d%6a%51%75%61%47%39%30%62%47%6c%75%61%77%3d%3d&ei=1NGHVIGKO4LZmAXPzYLABg&usg=AFQjCNF7poAdRI-Ljt4TBsTtVMvwtbu9Kg&bvm=bv.81456516,d.dGY&cad=rjt.
[7]胡德坤,唐静瑶.南极领土争端与《南极条约》的缔结[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1):64-69.
HU De-kun,TANG Jing-yao.The conclusion of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with theAntarcticTreatyin the Antarctic[J].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2010(1):64-69.(in Chinese)
[8]刘惠荣,刘秀.国际法体系下南极生物勘探的法律规制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9-14.
LIU hui-rong,LIU Xiu.A study on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Antarctic bioprospecting under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law[J].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2(4):9-14.(in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