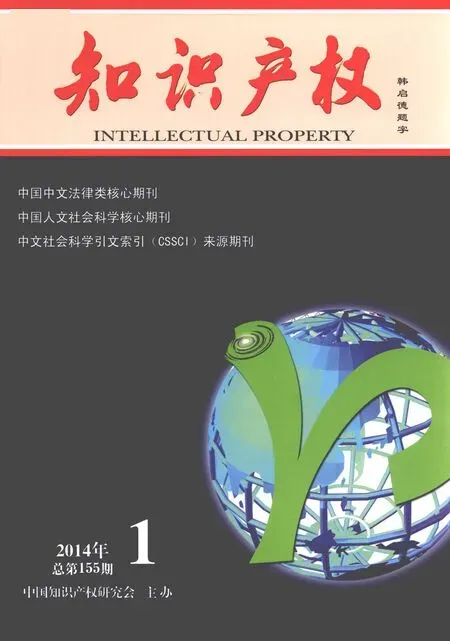后现代主义对著作权法的冲击及理论新读
任俊琳 王晓玲
后现代主义对著作权法的冲击及理论新读
任俊琳 王晓玲
著作权制度的产生和演进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文化思潮的影响,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社科领域内日渐重要,它独特的解构理念必然会对著作权法产生冲击。其对“主体”与“符号”的解构,颠覆了传统著作权法中的两大基本理论:“作者—作品”和“思想—表达”二分法。因此,与其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走传统的立法补充的老路,不如转换思路重新解读著作权制度。如取消著作人格权以及以“表达的形式”与“表达的实质”的概念重读之前的“思想—表达”二分法。这样既能保护作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不至于压缩公众的权利空间。
后现代主义 著作权法 著作人格权
引 言
后现代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发端,是在二战结束,现代哲学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后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它独特的解构理念,对历史的重新认知,吸引了无数学者的目光。在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一个全面反叛,而这必然也会对建立在现代哲学之上的法学造成一定的冲击,首当其冲的则是著作权法,它本就是人为建立起来的权利体系,受人文与科学技术的影响颇深,在此次思潮中必然会遭遇不小的正当性危机。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迥异于现代主义的话语逻辑——解构,又势必会对著作权法造成一定的挑战,本文将一一梳理之,以期给出一个恰当的回应。
一、后现代主义对著作权法影响之正当性
(一)文化思潮对著作权法之影响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作品的存在显然要先于著作权法的存在。在中世纪,经济状况以及思想的禁锢都在压抑人的自我意识,直至14世纪开始的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才一改蒙昧主义,强调个人价值和尊严,它所带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对近代著作权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17~18世纪,洛克提出的劳动财产权为著作权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a[英]洛克:《政府论》,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9页。作品被视为智力劳动成果,理应被确定为财产。始此,著作权在英国被首先建立起来。
18世纪末19世纪初,先验唯心主义盛行。康德首先提出了“自由意志”的理论,提出作者权利是内在的人格权利,紧接着,黑格尔对“财产人格理论”的阐述,将人格要素无限扩大化。b吴汉东等:《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97页。同时期,浪漫主义在法国盛行,人的主体性被提出,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它强调主观、主体性、创作个性,由此奠定了著作权体系中人格权的理论基础。
18世纪末,以边沁为鼻祖的功利主义哲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思潮。它强调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关注社会整体福利。个人权利受到保护,但并不是因为个人权利本身的价值,而是保护个人权利将整体推进社会福利。c王清:《著作权限制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204页。由此著作权便设定了一系列合理使用制度作为个人权利的例外情况。
传统哲学摆脱了神学、工具论的影响,依托于理性而建立,单一的指涉关系以及人类中心主义最终确立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著作权理论,现代著作权法的一系列制度即在此基础上逐渐构建起来。可见,著作权不是从来就有,而是伴随着社会发展确立起来的,并且会随着社会思潮的更迭而做出相应的调适。那么,当前在社科领域内日渐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必会为著作权法的嬗变增加可能性。
(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目标
物极必反。一定的理论发展到极致必定会走向它的对立面,神学发展到最后变成了人学,而人学现在也在面临着一次解构。可以说,现代哲学是在对神学的批判上建立起来的,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在对现代哲学的批判上发展起来的。
要准确定义后现代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盖因后现代主义反对的就是标签化、中心化,甚至极端的,后现代主义也与传统的语言系统相对立,转而提倡不断更新、不拘于形式的精神,追求一种无限可能性的道路。与其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毋宁说它是一种“反哲学思潮”,将自启蒙主义以来所建立起的现代哲学“再启蒙”。这种反传统的研究进路一开始便吸引了很多思想家的关注。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现代哲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20世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过度膨胀的理性主义,现代的规训机制使思想家对现有的哲学体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现代哲学是以16世纪到18世纪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为依托,又借工业革命为经济助力而建立起来的,其最终目的是将人类从自然和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科学世界。而接近20世纪末期,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达到了现代想象的极限。现代性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的威胁而告终。d[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雷蒙德·威廉姆斯在《公元2000年》中的一句话,“一旦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受到了挑战,我们就当聚集我们的资源,准备进行新的希望之旅。”后现代主义即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是后现代主义追求令人向往的高度自由。无限的自由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而现代哲学的理性主义与中心主义却在禁锢这无限的可能性。后现代主义者继承了尼采的相对视角,不承认统一,对理性、真理、绝对概念持怀疑态度。他们通过其核心理念——“解构”对传统做了一番割裂。“解构”一词最先源自海德格尔的“分解”一词,但将它系统地运用并真正变成一种工具和原则的,却是德里达。在德里达处,所谓“解构”,就是把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文化通过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而确立的概念和思想体系加以模糊化,使文本和一切符号表达含糊化,破除其原有的“符号—意义”二元对立固定结构和二元对立指涉关系,最终促使原本独立封闭的论述单位转变成多元开放的可能表达结构,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显然,德里达所言的“解构”,就是一种破除文本结构而进行自由诠释的创造性活动,体现了对创造的无限追求,同时也开辟了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所需要的条件。e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406页。
二、后现代主义对著作权法的解构
现在随处可见的后现代作品,无论建筑还是电影作品等都在表明,后现代已不仅仅只是存在于形而上的思辨中,它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多个领域。法学领域同样不可避免。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真正价值,不是已经造出的文化产品的解构或其中的意义,而是文化创造活动的不断更新的生命力本身。”f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0页。而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却是文化的固定产物。二者着重点的差异,姑且不论对错,有一点至少是肯定的,以“生命力”为目标的后现代主义必会对以保护“现有存在”为宗旨的著作权法造成一定的影响。
(一)对“作者—作品”理论的解构
“作者—作品”的理论,载明了作者基于创作对作品享有所有权,并且这种创作具有独创性,体现了作者的人格要素。作品中所包含的情感、信念等都属作者的人格再现,作者与作品之间有天然的精神纽带。该理论是作者人格权理论的基础。
而后现代主义者却对这种以人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作者中心主义充满了怀疑。在他们看来,任何实体都无法自证其存在,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并非是确凿无疑的。在此基础上,罗兰·巴特进一步指出作者的虚妄性。在他的经典著作《作者之死》中,首先从历史的沿革中论证了“作者”的诞生,而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赋予文本一位作者,便是强加给文本以后卡槽,……这是在关闭写作。”他推崇一种互动式的阅读,即由读者来阐释作品的意义,文章发表出来即脱离作者。他从文本阅读的角度解构了“作者”,将作者从作品中抹去。此处,罗兰·巴特的真实意图并非认为作者的创作无关紧要,而是认为作者的“精神幽灵”不应该把控文本,这是对文本的一种亵渎,而应该充分尊重文本,赋予它最高限度的自由,由读者来将其复活。意即文本的意义,是作者与读者互动共鸣的结果。
“作者死了”的观点必然会导致“作者—作品”的理论出现裂痕。作者对作品不再有绝对的权威,作品自产生之日起,就有了独立的意义。在此处,有的学者混淆了精神上的权威与财产上的权威,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潮所言的“作者死了”单纯只是一件文坛盛事,而法律上的“作者”更多强调的是一种财产上的归属关系,二者所指并不同一。前者之死不会造成后者的消亡。g参见郑媛媛:《作者死了,著作权何存》,载《法学论丛》2011年第4期,第64~65页。本文承认该学者对著作权中“作者”财产意义的认识,但却认为这样的理解太过狭隘。“作者”除了是一个财产上的概念外,还是一个“人格”上的概念,这也符合大陆法系一贯所持的著作权乃“人格—财产”的理论认同。那么,从人格权的意义上来理解,“作者死了”,并不是说作者对作品的财产权利不存在,而是指“作者”对作品的精神权利掌控不再,这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含义也相同。
著作人格权属于作者的精神权利,捍卫着作者凝结在作品中的创造性活动和个性精神。但著作人格权的确立,并非一个生来就有的权利,而是在一系列社会变革中固定下来的。在这个权利的背后有一个理念假定,将作品看成是作者个性的体现,看作人格的化身。h郑成思:《版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而后现代主义者高呼“作者死了”的口号,则是从精神上切断了作者与作品的纽带,作品并不必然体现作者的人格,“作者”只是一个事后的概念,是同现代著作权一起创立的概念。后现代主义从起源处动摇了著作人格权确立的正当性。
(二)对“思想—表达”二分法的解构
“思想—表达”二分法是著作权法的基本理论,是为了指明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思想的特定表达,而非思想本身,其功能在于界定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平衡著作权法激励创造与保留接触的利益关系,从而保障作者权利和创作实践的需求。“思想—表达”二分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并且也在多国的著作权法中得到确立,但无论学界还是实务界,对该理论的质疑却从未停止。最重要的原因是,作品的思想是不易确定的,在实务中这条理论形同虚设,只能起到事后诸葛亮的作用。而后现代主义对该理论的挑战却与实务关系不大,毋宁说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是其最稳定的“表达”,以及二者的联系。
著作权保护的表达,是由特定的文字、图像等符号所构成,这些符号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被固定下来,人们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也相差不大。亦即,人们的交流、实践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运用约定俗成的语言、文字等符号来进行,使得表达与思想是勾连的,通过表达大体可确定其背后的思想,著作权法保护的正是这种思想的特定表达。
任何作品最后的生成都免不了通过“表达”来展现,但传统理论却把“表达”固定化。这种固定扼杀了符号的潜在可能性,不但阻止了新表达的形成,而且也在无形中确认了“表达”的中心地位。后现代主义者正是看到了这其中隐含的霸权与不自由,转而通过解构语言的反传统策略,破除了语言的绝对性和二元对立,打破了传统语言体系中的“意义指涉系统”,寻求语言的多元性、含糊性、不可捉摸性,否认“表达”的单一性。在后现代主义处,“表达”是不具有稳定性的,更不可能因此而获得保护。
在二者的联系方面,后现代主义者也有不同看法。19世纪,英国美学家贝尔提出了一个命题:“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也就是说,这种“意味”是形式本身的意味,与它背后的思想呈现无必然关系,表达本身就有其独立的价值。i牛宏宝:《西方现代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这无异于撕裂了“思想—表达”之间的联系。
如此,著作权法的两大基本理论,“作者—作品”、“思想—表达”就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被轻易解构了。虽然它的解构之路并不周延,但在它强大的语境下,著作权法却有必要重新考量自己的自洽性。
三、对著作权法的理论新读
后现代主义对著作权法的冲击并非全是坏事,著作权法的本质是鼓励创作,但传统的语音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却扼杀了文化及其产品的生命运动过程,这显然不利于创作。反而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下,创作有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故此,我们不应对后现代主义的来袭围追堵截,顺势而为对理论进行新的解读并赋予新的意义,方为上策。
(一)还原著作权的财产本性
著作人格权制度就其本质而言,是为了赋予作者保护其人格尊严不受侵害的权利,它与对象不可分离,同时也不可转让、不可放弃、不可继承。由于受限于著作人格权的存在,很多作品的利用并不充分。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深受大陆法系影响,一贯将作品视为财产权与人格权的一体两权,二者之所以被视为一个整体,是因为它们指向同一个保护对象——作品。j参见潘天怡、谭琪瑶:《著作权中的“人格权、财产权”二元分立论》,载《知识产权》2012年第8期,第36页。但著作人格权的指向对象实则并非作品,作品只是“物”,不会有任何的精神权利,著作人格权保护的其实是作品与作者之间的联系。k参见熊文聪:《作者人格权:内在本质与功能构建的法理抉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6期,第86页。所以,著作权的一体两权体系本来就不甚周密,这也造成了如今著作权体系的混乱。其次,著作人格权的确立,是在假定了“作品体现作者人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作品体现作者人格”本就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当社会话语发生转变时,作为第二性的法律也应该随之改变。l有学者认为,现今网络对作品的大肆侵权,更加彰显了人格权的重要性,人格权亦由此获得重生的希望。笔者不敢苟同,从法的第二性原理来说,法只有顺时之为,万无倒行逆施之理。参见曹博:《著作人格权的兴起与衰落》,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102页。
而且,除去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变化,经济领域内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科技高速发展,创作生态已发生重大改变,技术的提升以及分工越来越精细,使得很多作品需要集体共同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很难高效及时地止纷划界,为了适应这一现状,立法者便将投资商拟制为著作权人。例如,我国将电影著作权人拟定为制片人,显然就是出于这一方面的考虑。但是,这里的投资商又绝非作品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者,此时如果再坚持将人格权或曰精神权利赋予著作权人,难免不合情理。学界对此的诟病也常见于专著论文中,而如若采纳学者的建议:“著作权精神权利归属于创作作品的自然人作者,并不得转让。”将精神权利赋予创作作品的自然人,其他著作权人只享有经济权利。mm 参见李明德等:《〈著作权法〉专家建议稿说明》,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页。但接踵而来的就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主持或者投资,代表法人或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享有发表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那么法人或其他组织基于投资而来的作品,其权利行使必然会大打折扣。造成此项困顿的正是源于学界一直将发表权、署名权等一系列权利视为人格权,而法人并无自然意义上的人格。n参见谭启平、蒋拯:《论著作人身权的可转让性》,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2期,第75~76页。这个悖论的存在o《著作权法》中仍有其他悖论。如:发表权可由作者的继承人行使,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除署名权外可由原件所有人行使等著作人格权与作者人身分离的现象。正是由于我们一直以来都将上述权利视为人格权,如果我们正视这些权利的财产性质,那么也就不会出现上述不合理的状况。
我国传统的著作人格权包含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其中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一个权利的正反两面,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中已删除修改权,所以本文只论述其余三种权利的财产性质。就发表权而言,是将作品是否公之于众并以何种方式公之于众的权利。该权利是一次性权利,这显然与人格权的特征不符。而且发表作品是获得其后一系列财产权利的先决条件,其财产性质明显要高于人身性质。就署名权而言,是作者表明自己身份的权利。这直接构成了“作者—作品”之间联系的纽带。但从实践中看,并不是所有作者都有此希望,大量存在的“匿名”或“代笔”即可为证。正如钱钟书先生对一位求见的英国书迷所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所以客观地讲,署名权更多体现的是作者的一种艺术商誉,是消费者选择购买时看重的价值比较。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更是说明了这一点。2013年4月,曾创作了《哈利·波特》系列畅销书的英国作家J.K.罗琳化名为罗伯特·加尔布雷斯出版了一本小说《布谷鸟的呼唤》,虽然评价很高,但只销售了449册。而在被媒体披露该书的真正作者后,这本小说的销售排名从5076名陡升至畅销榜第一名,销量陡增5000多倍。所以,后现代主义者才认为,“除证明商业交易规则要求外,署名之加插背后毫无物事。”p拉罗歇尔(Larochelle):《从 康德 至福柯:作者余 下什么?》,叶 长良 译,转引自李琛 :《质疑知识产 权之 “人格财产一体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74页。就保护作品完整权而言,立法初衷是通过维护作品的完整性来保护作者的情感、思想一致性等精神权利。但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这个立论点并不必然成立。而且在实践中,更多的情况是,作者为了出版作品,明示或默认了出版商、编辑对作品的修改,也就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放弃或转让了著作人格权。q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中,立法者将第34条“图书出版者、报社、期刊社对作品的修改权”整个拿去,也就是,今后在理论上,出版商或编辑对作品再无修改的权利,但在实务的图书出版中又必然会遭遇更大的不便利。并且,转换一种更实用的角度,保护作品完整权同时也是为了维护作者的艺术商誉,防止修改后的作品降低作者的声誉,从而影响销量,r参见何炼红:《著作人身权转让至合理性研究》,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第54页。这个权利本身就包含了很强的财产性质。
无论从反面的悖论说起,还是从正面的论证而言,著作人格权与人身的紧密程度远远小于与财产的紧密程度。作品对于作者来说更像一个产品,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享有完整的所有权,但著作人格权的确立却让作者的权能受损。精神权利的神圣性要求使用者在利用作品时必须小心翼翼,否则有侵犯作品完整性之嫌,而精神权利的绝对性又使得原作者不能通过转让、许可使权利最大化,徒然造成资源浪费,进而限制了权利的利用效率,同时也不符合私权自治的理念。故此,还原著作权的财产本性,在扩张了公众自由利用作品范围的同时,又没有减损著作权人的利益,而且更促进了信息的传播与创新,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共赢之策。
(二)重读“思想—表达”二分法
一般而言,一种思想可以用不同的表达加以体现,并且每一种表达都可以获得独立的著作权保护。但在后现代主义独特的解构模式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一理论。
既求解决良方,就须对症下药。如上所述,“思想—表达”二分法并非毫无用处,只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它的符号形式被模糊差异化了,失去了以往固定的形态,使得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表达”受到正当性质疑。故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重塑权利的指向对象。
考察“表达”,可以发现其有两个层面:一是“表达的实质”,属于“思想中的表达”;二是“表达的形式”,属于“符号化的表达”。前者是著作权保护的实质,后者是著作权保护的对象。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最初阶段,作者头脑中形成的仅仅是抽象的思想,随着创作的推进,作者日益将自己的个性选择与感情融入思想中,在抽象的思想中不断加入作者个性的取舍、判断、组合,最终形成一个创作的产物,它是具象的,只不过没有将它诉诸一定的符号,外人无法单纯探知而已。这一阶段的表达实乃著作权法保护的实质。s参见卢海君:《表达的实质与表达的形式——对版权客体的重新解读》,载《知识产权》2010年第4期,第68~69页。
如此剖析,即可发现被后现代主义解构的并非是“表达的实质”,而是被符号固定下来的“表达的形式”,而后者却一直被视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是在未颠覆“思想—表达”二分法理论的基础上,将保护确定到“形式”之前的“实质”上,不是说“表达的形式”不需保护,而是指在后现代语境下,由于其极力破除形式的统一性与束缚性,使得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表达的形式”失去了以往稳定的表达能力,但“表达的实质”却并无根本变化。过去的著作权法中将保护对象限缩在“表达的形式”上,实际就是把“形式”当作艺术创作活动成果的终结,从而使艺术创作成果的“形式”从整个艺术创作生命活动中脱离出来,也同艺术创作的未来割裂。
“表达的实质”与“表达的形式”这一概念的提出,既具有最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从理论层面上讲,有助于我们对著作权的客体做进一步的认识,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些作品要素辨析上;从实践方面来看,“表达的实质”与“表达的形式”的区分有助于确定两部作品或多部作品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从而帮助正确地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以轰动一时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为例。陈凯歌导演的《无极》试图表现“爱与命运”的宏大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一个抽象的思想,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倾城、昆仑、光明等人之间在特定情境下发生的种种具体故事就是此处的“表达的实质”。只不过陈凯歌拍的是电影,所以他头脑中的思想所形成的客观存在就是影像;如果他是一个小说家,那么他的思想所形成的客观存在就是一段段的文字。由电影到小说,就是一个演绎的过程,它们“表达的实质”具有同一性,应由法律予以规制。著作权法中的演绎权即由此而来。而胡戈仅仅借用《无极》的一些“表达的形式”,再经重新编排之后有了与原作完全不同的“表达的实质”,那么就不算侵权。
结 语
后现代主义的确对著作权法造成了危机,但危机同时也意味着另一个可能。现代的著作权法把维护作者权益作为其核心的立法原则,是在权利的增值和绝对化为特征的“权利本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系。著作权的悖论在于,对著作权保护不足,原创的诱因就会减少,从而妨碍文化发展;反过来,对著作权太过保护,又会阻碍信息的交流,从而抑制文化的鲜活度。t季卫东:《网络化社会的戏仿与公平竞争——关于著作权制度设计的比较分析》,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第21页。而后现代主义推崇的多元与对话机制可以促使我们转换思路,将“权利本位”变更为“权利保障”,既保护了作者的合法权益,又不至于挤压公众的权利空间。取消著作人格权的提法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放开作者对作品的绝对权威,有助于公众对作品的全面利用,而“思想—表达”二分法的重新解读,又有效防止了“搭便车”的行为。
我们处在一个知识霸权时代,包括学者在内的所有人越来越注重经济分析而忽略伦理性。似乎只要经济最大化便是最好,便是至善。这种倾向非常危险,尤其对著作权领域。著作权直接规制文化领域,如果一味地强调效益,只能使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商业化”。所以对于著作权的探讨应适当地抽离经济分析,而多做些文化上的分析,更多地鼓励“思想”上的创作。这正是本文从后现代主义来重新审视著作权法的旨趣所在。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copyright system are largely infl uenced by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trends. With the postmodernism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 its unique deconstruction philosophy will affect copyright law a lot. Specifi cally,it deconstructs“subject” and “symbol” and subverts two basic theories -“author-work” and “idea-expression dichotomy”-in copyright law. Therefore, it is better to reinterpret the copyright system rather than amend the law, such as abolish moral rights as well as the concept of “form of expression” and “substance of expression” to reinterpret the idea-expression dichotomy. It will not only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author, but will not compress the right space of the public.
postmodernism; copyright law; moral right
任俊琳,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晓玲,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