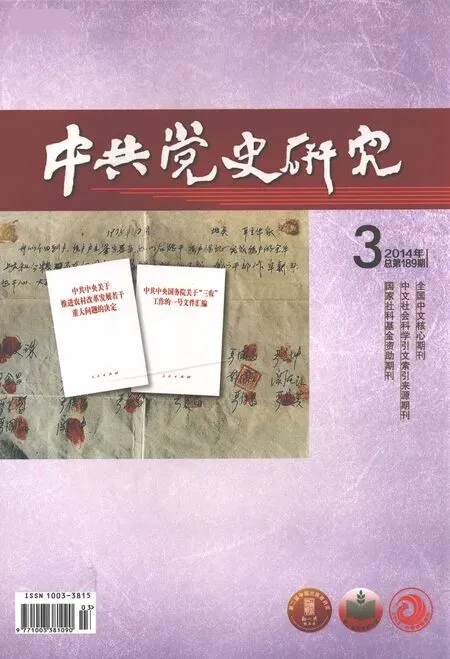从画家到战士:回忆我的父亲
张北英
2013年是中央美术学院建院95周年,也是父亲张启仁诞辰100周年,美院举办了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父亲逝世30年了,他越走越远,与他同时代的那些革命者大都离我们而去,知道父亲的人越来越少,了解父亲的人就更少了。我写文章回忆父亲,是为了纪念他们那一代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战士。
父亲生前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了整整20年,他两次被任命为副院长,第一次是在1963年,第二次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央美院,有父亲青年学生时代的老师王森然大师、李苦禅大师,父亲有幸结识了吴作人、刘开渠、李可染、蒋兆和、罗工柳等一大批当代中国的美术大师,还有靳尚谊、侯一民、伍必端、钱绍武等一大批当年中国美术界的中年领军画家。父亲说过:在美院工作,能与这么多当代中国最有成就的美术大师一起办学,一起研究和探讨美术教学、美术创作中的问题,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父亲去世的时候,中央美术学院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张启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人民的忠诚干部,是人民美术的一位前辈,是国家美术教育事业的一位勤恳的组织者。他后半生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上。他自己放下了画笔,却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造就一批一批的美术新生力量而不知疲倦地工作。中央美术学院二十年来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凝聚着他默默的劳绩”。的确,父亲放下了画笔,这是终生的遗憾;然而,作为一名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战士,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在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侯一民院长说:“启仁一向低调,同他一起工作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他是学画的,而且还画得那样好”。
其实,父亲迷恋上绘画是在幼年,学习绘画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先后考入辽宁省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华北美术专门学校油画系学习油画。在华北美专学油画的同时,父亲还跟随李苦禅先生学习国画,他喜爱苦禅先生的大写意。当时,王森然先生也在华北美专教书,他爱惜父亲是个人才,不仅让父亲住到家里,而且还管吃饭。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大学校长特聘王森然创办艺术教育专修科并请他任主任。王森然先生让父亲转到华北大学艺术专修科继续学习。父亲把森然老视作恩师。王森然先生倡导革命文艺思想,他明确提出“文艺为大众”、“文艺为工农兵”的主张,这些思想对父亲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之际,王森然号召学生们站在救亡的前线“打头阵”。在一二·九运动中,王森然、李苦禅、父亲和黄奇南走在华北大学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他们手挽手、肩并肩,带领师生高呼“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段历史,王森然、李苦禅和父亲一直刻骨铭心。
1937年7月3日至7日,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华北的前夕,父亲参加了由著名漫画家孙之俊发起、在北平中山公园举办的全国漫画展。父亲展出的作品《打回老家去》是画展中引人注目的一幅,画的是一名红军战士拿着刺刀枪跨过长城追击日本鬼子。父亲画的那个战士其实就是他自己。画展结束后,父亲离开北平经山西奔向延安,参加八路军,拿起枪杆子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战期间他在抗日军政大学教学,深入敌后到太行山办学。在抗大期间,父亲画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马恩列斯的大幅领袖像。在抗大成立五周年的大会上,父亲因此受到抗大总校的通令表彰。从画家到战士,父亲不仅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也完成了思想的转变。
父亲一生敬重李苦禅、王森然两位老师,他们不仅是他学习绘画的指导者,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支持者。特别是父亲到中央美院任职后,我就亲眼看到过他在苦禅先生作画时,亲自手举墨盘以方便苦禅老画笔沾墨。我还曾经陪同父亲雨夜送王森然先生回家,父亲怕雨夜路滑老师摔倒,一手为森然老撑伞,一手扶着他。我要代父亲送森然老,他不让,非要亲自送老师回家。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练和延安革命摇篮的熏陶,父亲养成了甘当人民马前卒的平和心态,从不以官自居、自傲。父亲出任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他的心和学生贴得很近。在鲁迅美术学院,学生们可以自由地到父亲办公室或家里向他提出问题并一起讨论。父亲乐于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为了解学生,他亲自到学生家家访。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学校长亲自做家访都是少见的。父亲的心很细,他能叫出许多学生的名字,并且知道星期天不休息到图书馆看书的学生名字。当时范曾是中央美院的学生,我就听父亲说过:国画系有个范曾,星期天在图书馆看书一看就是一天,中午饭是开水、馒头就咸菜。图书馆老师出去吃饭,范曾就被锁在图书馆里看书。范曾研读历史文学,背诵中国古典诗词。父亲说:范曾凭着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今后在艺术创作上一定会有大的成就。艾轩现在是当代中国油画写实主义画派的领军人物,当年他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军区创作室工作,长年深入藏区写生创作。艾轩在藏区写生创作,风餐露宿,饮食无规律,患了严重的胃病。一次他在藏区创作时,胃穿孔大出血,差一点死在藏区。美院恢复研究生制度招生时,父亲亲自动员艾轩报考研究生。父亲对范曾的刻苦学习,对艾轩的不要命也要创作的精神总是赞不绝口,他为中央美院有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和自豪。李林琢在美院读书时到首钢实习不慎被钢水烫伤,父亲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医院,要求医院尽全力抢救。李林琢出院后,父亲关心他的后续治疗和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多次找李林琢谈心,鼓励他尽快走出人生低谷,做一个生命的强者。现在他是中央美院壁画系有成就的教师。
在王森然先生办学思想的影响下,父亲心胸开阔,博釆众长。他在鲁迅美术学院当院长5年,邀请了潘天寿、古元、艾中信、秦仲文等全国著名的美术大师到鲁迅美术学院讲学。他给了潘天寿极高的礼遇,讲完学后,与全校教师合影。潘天寿深为感动,送父亲一幅指墨画,题字:启仁同志法家指正。父亲提倡学术交流,互教互学、教学相长、共同提高。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严重影响美术教学时期,父亲是坚持和倡导在教学中使用裸体模特的美术学院院长之一。他不认为使用裸体模特是资产阶级教学方法,他认为使用裸体模特是按美术教育规律办学。父亲在教学安排中提倡国画系安排素描课。他说:素描课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掌握人体比例结构,有利于学生下笔准确。在素描与白描的关系上,他用辩证的方法看问题。他说:白描不等于素描,素描不能代替白描,白描也不要排斥素描。在中国画的教学中,长期存在安排和不安排素描课的两种意见。父亲坚持国画系的学生要上素描课,但在教学时间与方法上要与对油画、雕塑专业的学生的要求有所区别。父亲提倡画派技法传承,但他反对门户之见。他说破除门户之见,美术界要向戏剧界学习。他特别赞赏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父亲是喝延安的延河水成长起来的干部,的确有着战士般的政治觉悟和抗压能力,他柔韧的性格,更是我们这一代难以企及的。郭小川在《团泊洼的秋天》中赞美战士的性格时说“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诬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诗人想以此来彰显在“文化大革命”逆境中坚守理想主义无畏的精神境界。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靠边站,不能组织领导学院正常的教学工作,他就看传达室、帮厨、打扫卫生、修理桌椅,做力所能及的事。美院一位系主任贴大字报,让父亲交代“包庇历史反革命王森然”的问题,他只能以沉默回应。在当时,沉默也是一种政治立场。父亲在自身难保的困境下,尽可能给正在受迫害的同事以温暖。陈沛、朱丹等住“牛棚”被批斗,父亲见到他们仍然热情地打招呼,从不避讳。朱丹叔叔对我说:我住“牛棚”被批斗,你父亲见到我还叫我朱丹同志,我听了后心里暖呼呼的。你不知“同志”两个字在我心中有多重。启仁叫我同志,他就是没把我当“黑帮”看,我内心是很激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张仃的儿子、中央美院美术史系教员张朗朗因为讲了一些江青30年代在上海电影界的活动情况和对中央文革的不满言论,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判处死刑。张朗朗在《我和易先生的故事》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我们学院‘文革’前的副院长张启仁先生,在全院讨论的时候,全场只有他一个人表示,不同意判我死刑。尽管他态度和蔼,用词谨慎,人们都明白这个老人胆子太大了,居然敢说真话。”“他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人。”许多美院的老人现在回忆起这件事情都觉得不可思议,“张启仁胆小怕事”,当时怎么就敢于对死刑判决说“不”呢?!
1970年5月,在防范苏联可能发生突然进攻而战备疏散的大背景下,中央美院在校学生全部疏散到河北宣化部队农场劳动等待分配,教师和职工到河北磁县中国人民解放军27军所属部队接受再教育,吴作人、刘开渠、陈沛、李苦禅、叶浅予、黄永玉、罗工柳、艾中信、古元、侯一民等被下放到磁县。父亲因患有严重心脏病而留守学校,并被委任为留守组长,后来又加封为艺术院校留守组长 ,也就是戏剧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戏曲学院、电影学院、舞蹈学院留守组的召集人。在留守京城的日子里,父亲经常骑自行车从东城到西城,从南城到北城,到美术学院老师家里家访,了解他们有什么困难,并尽最大努力帮助解决。
1971年底,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领导通知父亲开会,传达周总理关于接待外宾和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宾馆要重新布置的指示。作为留守组长的父亲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中央美院在京的老画家并通知在磁县的一些老画家回京,接受为北京的一些涉外宾馆作画的任务,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美术学院第一次接受国务院交办的任务。没想到其中的一部分画被诬蔑为攻击社会主义的“黑画”而受到批判。全国范围的“批黑画”运动起源于上海,结束于北京,历时半年。北京“黑画展”展出的有宗其香的《虎》、黄永玉的《猫头鹰》、李苦禅的《残荷图》、黄胄的《群驴图》、许麟庐的《三世清白图》等。这几位著名画家,父亲都认识,认识的时间长的有40多年,短的也有20多年。父亲曾经问黄永玉:你画的猫头鹰怎么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黄永玉告诉父亲:“猫头鹰夜里活动,白天睡觉;它白天睡觉时就是睁只眼闭只眼。”父亲感慨地说:“原来这是猫头鹰的生活习惯,你观察得真细呀,我都没有注意过。”父亲知道,画家笔下的画源于生活,把生活中的花鸟山水、动物植物做政治解释,完全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所以,他拒绝了对所谓“黑画”的批判,再一次保持了沉默。1974年3月29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评为某些饭店宾馆创作的绘画》,把批判“黑画”看成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文章批判宗其香的《虎》寄托着炮制者“仇恨共产党,仇恨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批判黄永玉的《猫头鹰》是作者“射向社会主义、射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毒箭”。作为中央美院的留守组长,父亲当时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他做好了因此被罢官的准备,并写信给正在部队的我:“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一旦我出了问题,部队让你复员你就复员。”在顶着“四人帮”在美术界代理人的政治压力下,他亲自到李苦禅、王森然、黄永玉、蒋兆和、宗其香等人家中去看望,安慰这些画家,缓解画家们因被批判而产生的精神压力。父亲坚信,他的老师在战乱年代敢于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呐喊,他们对祖国的挚爱是不会蜕变的。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蒋兆和的夫人肖琼带着儿子到我家里,把宾馆给的笔墨费上缴学校,父亲对肖琼说:“你回去告诉蒋先生,给宾馆作画,他们付给笔墨费是应该的,这点钱不多,也不是稿酬,按稿酬给钱,蒋先生的画不止这么点钱,你们别怕,别担心有什么问题,钱你们收下,有什么事我顶着!”后来李苦禅先生在同父亲的谈话中说: “批黑画你抵制了,这就不容易,你要是再硬点,反过来跟他们斗争就更好了。”这是一位性格刚烈的老师对学生的希望。
其实,我非常理解父亲的为人和处境。他身处敏感的教育界和文化艺术界,既要贯彻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又要尊重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的规律,并且还要保护老画家,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国宝”。父亲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和复杂的心路历程,外人无从揣摩。但是,从他的坚持、抵制和沉默中,已经看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因为“文化大革命”砸烂的是他们那一辈人用鲜血和生命创造出来的新世界。因此,他的抵制和沉默,又彰显出性格中“韧”的一面,这个“韧”既来自于觉悟,也发端于良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的多少个日日夜夜,都是在“跑”中度过的,他希望把损失的宝贵时光夺回来。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百废待兴,父亲为改善美院办学条件、解决改善老师住房条件,四处奔走呼吁以取得上级领导的同情和支持。父亲组织领导了中央美院王府井教学办公楼的建设,改善了美院的教学办公条件。为解决刘开渠院长房屋被占问题、吴作人院长两间小平房不能接待外国友人访问的难题、古元院长住房问题,父亲亲自找国管局领导解决。为江丰家早日安装上电话,父亲亲自跑电话局。“跑”过多少地方,父亲也记不得了。他说:我去跑,人家会给面子,会尽快将问题解决。
1984年5月9日,习仲勋发表了《纪念王森然同志》的文章,称赞:王森然“从事教育事业70年,为中华民族培育了几代优秀人才,刘志丹、谢子长、曹力如、王子宜、李培之、安蛾、李广田、赵望云、张启仁等同志,就都是他的学生。”①《习仲勋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70页。作为一名走上革命道路的战士,父亲没有辜负王森然先生;作为画家,父亲把自己的专长深埋起来,但他对绘画的要求还是那样精益求精,这也正是秉承了王森然先生的绘画遗风。记得有一次我陪他到美术馆看画展,好像是钟函先生的一幅画。画面是毛主席背着手与一位农民在延河边散步。画中的毛主席是背面不是正面。父亲对钟函先生说:应画主席的正面,脸部表情可以表现内心世界。你不画正面是不是怕画不好主席的脸?画不好,你就多观察多画,坚持画下去你一定能够画好。作者对父亲说:是怕画不好正面才画了背面。还有一次我陪父亲去看黄胄,黄胄先生对父亲说:“牵几头驴走吧”。黄胄的意思是让父亲在他画好的几幅画中挑一张,他好送给父亲。父亲看完画说:你的驴腿画得不准确,有点儿问题。于是两个人就讨论起驴腿的问题。父亲逝世多年后,吴小昌教授约我去看望黄胄先生,那时他中风刚好还在恢复之中。黄胄先生对我和吴小昌说:沒有人当我的面说我的驴画得不好,驴腿画得有点问题,就你父亲当我面说驴腿画得有问题。人家看画是看热闹,你父亲看画是看门道。你父亲评画很客观、很公道。
父亲虽然走远了,但他留存的精神却从未离我们远去。在我的眼里,父亲是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爱党、爱国、爱民,他爱美术、爱美院、爱老师、爱学生。为了爱,他可以做出自我牺牲;为了爱,他可以忍辱负重;为了爱,他可以无私奉献。这就是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