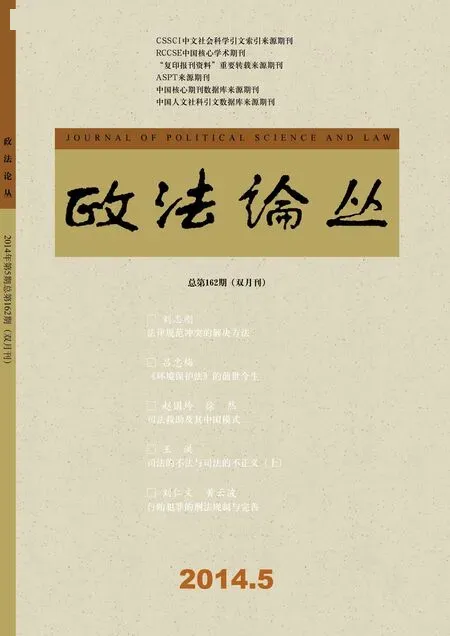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研究
佟连发
(辽宁大学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证明责任就是诉讼当事方在诉讼中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之案件事实的责任。[1]P290证明责任的分配对于诉讼程序意义重大。随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高度司法化,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已经到了无案不涉的地步,几乎每个专家组报告/上诉机构报告都会涉及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由于DSU对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尚付之阙如,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争端解决实践中逐渐形成一套分配证明责任的“判例法”规则。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WTO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可以归纳为:申诉方承担被诉方违反WTO规则的证明责任,被诉方对例外或肯定性抗辩负证明责任。国内外的研究普遍认为这些规则的问题主要在于例外识别问题上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实践存在前后不一的情况。①一些学者质疑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例外区分问题上采用的“语言标准”、“重要性等级标准”和“积极规则标准”的合理性,甚至尝试引入法律经济学的方法来重新建构WTO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②但是国内外的研究普遍忽视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分配证明责任时的一些特殊规则,如“提出事实的一方负责证明”、“合作提供证据”等。而这些特殊规则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问题。因此,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研究,不仅要注意到一般性的规则,还应当注意这些特殊规则在证明责任分配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GATT时期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
GATT时期的专家组报告大多并无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论述。但是如果细细梳理,仍然可以发现专家组分配证明责任的一些规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援引例外的缔约方对例外所规定的条件负证明责任。这是被GATT时期的专家组报告明确指出的一条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在美国关税法337条款案中,专家组指出第20条(d)款是总协定的一个例外,因此应由援引该例外的缔约方证明该款规定的条件。④在加拿大关于冰激凌和酸奶进口限制案中,专家组认为第11.2(c)(i)条属于“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例外,因此应当由援引该例外的缔约方负担已符合例外条款所规定条件的证明责任。⑤除了第20条(d)款和第11.2(c)(i)条,也有判例认为GATT第2.2(c)条和第8.1(a)项也属于证据法意义上的例外条款。⑥不过在GATT时期,判例中确认的例外条款范围和数量是相当有限的。
第二,申诉方对违反GATT的事实负证明责任。虽然整个GATT时期,专家组没有在任何一个案件中相对明确地指出应当由申诉方对被诉方违反GATT的事实负证明责任,但是仍然能够从一些案件中推断出专家组是按照这一规则来分配证明责任的。最早在1950年的澳大利亚对硫酸铵化肥补贴案中,专家组对总协定相关条款进行审查后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证明澳大利亚政府未能履行总协定下的义务。⑦在1952年的德国沙丁鱼案中专家组在检查收到的证据后得出结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德国政府未履行其在总协定 第1.1和第3.1 条下的义务。⑧1978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对动物饲料蛋白质的措施案中,专家组指出: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购买义务、安全保证金或者对缔约国进口的同类产品歧视的蛋白质证书的证据,因此欧共体的措施没有违反第1.1条下的义务。⑨在这些案件中,申诉方指控被诉方违反GATT的事实因证据不足而未能得到证明时,专家组最终都判定申诉方败诉。因此,客观上专家组就是按照“申诉方对违反GATT的事实负证明责任”这一规则进行裁决的。
总体而言,由于GATT的争端解决机制尚属于较多应用外交手段的权力导向型的争端解决机制,[2]并且在GATT时期当事方常常向专家组递交它们相互同意的一系列事实,[3]大多数时候专家组能够在事实无争议的基础上作出裁决。因此,证明责任问题在GATT时期的争端解决实践中并未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二、WTO争端解决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WTO成立后,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数量庞大且极为详细的WTO规则体系出现了。缔约方之间更多地依靠WTO解决它们之间的贸易争端,其中不乏一些事实极为复杂的案件,因此证明责任问题的重要性越发显现出来。[3]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不仅在实践中明确了上述两条规则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而且还发展出一些特殊性的规则。
1.申诉方承担被诉方违反WTO规则的证明责任。在WTO成立初期的两个重要案例,美国汽油标准案和日本酒类税案中,专家组用描述性的语言表达了应当由申诉方承担被诉方违反WTO规则的证明责任。
在美国汽油标准案中,申诉方指控被诉方美国的汽油规则违反GATT 第3.4条。按照GATT第3.4条:任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进口至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时,在有关影响其国内销售、标价出售、购买、运输、分销或使用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规定方面,所享受的待遇不得低于同类国产品所享受的待遇。专家组认为申诉方应当负责证明下列两点:(1)法律、法规或规定影响了国内销售、标价出售、购买、运输、分销或者进口产品的使用;(2)这些法律、法规或规定给予进口产品的待遇低于同类国产品。⑩该案专家组要求申诉方证明的两点违法事实完全是根据第3.4条的义务性规定而导出的。
在日本酒类税案中,申诉方指控日本对烧酒征税低于威士忌、白兰地和白酒,违反了GATT第3.2条的规定。按照GATT第3.2条:任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进口至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时,不得对其直接或间接征收超过对同类国产品直接或间接征收的任何种类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此外,缔约方不得以违反第1款所列原则的方式,对进口产品或国产品实施国内税和其他国内费用。专家组认为该案的证明责任应当这样分配:涉及到违反GATT第3条第2款第1句的指控,应由申诉方负责证明两个问题,即产品为相似产品并且外国产品征收了超过国内产品的税;涉及到违反GATT第3条第2款第2句的指控,应由申诉方负责证明两个问题,即相关产品是直接竞争或者可替代的并且被诉方以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的方式对外国产品征税。就申诉方指控的GATT第3条第2款的违反,专家组指出了申诉方应当承担哪些事实的证明责任,而概括起来可以发现,专家组将证明违反GATT第3.2条事实责任分配给了申诉方。因此在上述两案中,可以看出专家组是按照“申诉方承担被诉方违反WTO规则的证明责任”的原则在分配证明责任。
在美国羊毛衬衫和罩衫案中,专家组指出:因为印度是启动争端解决程序的一方,因此应当由印度来提出证据来证明美国的措施不符ATC第2条和第6条。上诉机构指出:尽管专家组的这点论述并不能算非常清楚,但是法律上是正确的。应当由申诉方印度来负责证明美国对ATC协议的违反。上诉机构还援引了GATT时期的很多案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至此,“申诉方承担被诉方违反WTO规则的证明责任”得以明确确立,在后来的争端解决实践中,这一规则被广泛适用,成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分配证明责任的主要规则之一。
2.被诉方对例外或者肯定性抗辩负证明责任。GATT时期的专家组报告曾经明确提出应当由援引例外的当事方负责证明例外所规定条件。WTO成立后,专家组沿袭了这一做法,同样是在上述美国汽油案中,当被诉方美国援引第20条一般例外之(b)、(g)等款为其不符合第3.4条的措施进行辩解时,专家组指出:应当由援引例外的当事方,即美国承担证明争议措施符合例外规定的条件的证明责任。
在美国羊毛衬衫和罩衫案上诉机构报告中,上诉机构引入了“肯定性抗辩”的概念。该案上诉机构指出:一些GATT和WTO专家组要求对违反GATT义务的指控,例如第1.1条、第2.1条、第3条或者第11.1条,进行按照如第20条或者第11.2(c)(i)条进行抗辩的当事方负责证明。第20条和第11.2(c)(i)条是GATT1994某些条款下的义务的有限例外,而不是本身设立义务的积极规则。他们本质上是肯定性抗辩。这种抗辩的证明责任由提出的一方承担是合理的。对于“肯定性抗辩”的引入,赵维田教授认为这是对“规则例外”说的一种取而代之的新模式。不仅如此,赵维田教授还认为这种模式下用“肯定性抗辩”的思路,把什么“规则例外”原本勉强凑合的概念一笔勾销,免却了多少尴尬与喋喋不休的争论。因而解决了哪些规定算“例外”的难题。[4]P153-154对此,笔者认为,对于“肯定性抗辩”概念的出现及其对WTO证明责任分配合理性之影响,实在不必高估。
“肯定性抗辩”最初为英美法上的概念,按照《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解释,肯定性抗辩是指被告并不否认原告所主张之事实的真实性,而是提出其他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自己不应承担责任的答辩。因此,它并不反驳原告诉求之真实性,而只是否认原告在法律上有起诉的权利。[5]P48按照《布莱克法律词典》:肯定性抗辩是被告对事实和意见的主张,如果该主张为真将击败原告或者控方,即使他们的主张为真。[6]P128因此可以看出,肯定性抗辩有别于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主张的否认,而是提出新的主张来击败原告的主张。在WTO诉讼中,被诉方针对申诉方对其的指控,提出新的主张,例如符合例外条款从而为自己辩解应当属于作出肯定性抗辩的一种情形。但反过来,作出肯定性抗辩未必仅限于援引例外条款,例如基于诉讼程序而提出的,主张原告诉讼要件欠缺等也应属于肯定性抗辩,但却并未涉及例外条款。尽管从理论上讲,作出肯定性抗辩的依据要比“例外”的范围更为广泛,肯定性抗辩与例外并非相同概念。在多米尼加香烟案中,专家组也曾指出,尽管例外与肯定性抗辩这两者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援引例外可以作为一项肯定性抗辩。但是从这十多年的争端解决实践来看,虽然“肯定性抗辩”经常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分配证明责任时被提到,但在绝大多数案件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并未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而是将两者混为一谈。可以认为在WTO争端解决的语境下,“肯定性抗辩”已沦为例外的同义词。因此“肯定性抗辩”的引入,不可能解决“例外”的范围问题。根据WTO的实践,这一条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可以表述为:被诉方对例外或者肯定性抗辩负证明责任。
3.WTO争端解决中证明责任分配一般规则的问题分析。上述两条规则已经成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进行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在WTO争端解决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实践中它们也存在如下问题:
(1)“申诉方承担被诉方违反WTO规则的证明责任”有可能被滥用。“违反WTO规则”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某些违反WTO的行为可能同时违反几个WTO规则,申诉方有可能在其中进行选择,从而利用这个规则指向的模糊性以及WTO规则之间的相互关系逃避本应承担的证明责任,破坏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应有的统一性和可预测性。
我们以已失效的《纺织品与服装协定》(ATC)为例。ATC第2.4条规定:成员方除根据本协定规定或GATT1994的有关规定外,不得针对产品或成员采取新的限制。而ATC第6条则规定了缔约方实施“过渡性保障措施”必须遵守的纪律。如果缔约方采取过渡性保障措施违反了第6条的规定,则必然导致对第2条的违反,因为此举肯定属于针对产品或成员采取了新的限制,而这又不符合ATC第6条。如果申诉方指控被诉方采取过渡性保障措施违反了第6条某一具体规定,那么必须由申诉方负责证明被诉方对这一具体规定的违反。如果申诉方利用“申诉方负责证明违反WTO规则的事实”这一规则,仅指控被诉方违反了ATC第2.4条关于禁止对产品或成员采取任何新的限制的规定,那么只需对被诉方违反ATC第2.4条负担证明责任,也即只需要证明被诉方采取新的限制的事实即可。再如,一方违反《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征收反补贴税将构成对SCM某些条款的违反,同时也会违反GATT第1条最惠国待遇原则、第2条关税减让表和第3条国民待遇原则等。因此,违反WTO规则可能表现为同时违反不同层级的规范,如果申诉方利用这条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仅仅主张被诉方违反了GATT第1条、第2条或第3条,而不主张对方违反SCM的某些规定,那么申诉方只需要证明被诉方违反第1条、第2条或第3条的事实的证明责任,而逃避本应承担的证明违反SCM某些具体规定的证明责任。
笔者的这一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印度附加税案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且与笔者所举的第二个例子高度相关。该案中,印度针对某些酒类饮料在进口环节征收附加税和额外附加税,美国以印度征收附加税和额外附加税违反GATT第2.1条(a)、(b)项为由启动争端解决程序。该案中主要围绕GATT第2.1条(a)、(b)项和第2.2条(a)项展开。第2.1条(a)、(b)项要求缔约方给予其他缔约方的贸易待遇不低于减让表中所规定的待遇,并且应当免征超过减让表所规定的普通关税的部分。第2.2条规定:本条的任何规定不得阻止任何缔约方对任何产品的进口随时征收下列关税或费用:(a)对于同类国产品或对于用于制造或生产进口产品的全部或部分的产品所征收的、与第3条第2款的规定相一致且等于一国内税的费用;(b)以与第6条的规定相一致的方式实施的任何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c)与所提供服务的成本相当的规费或其他费用。第2.2条规定了成员方可以超过关税减让表约束税率征收关税或费用的三类情形。美国仅主张印度对某些酒类饮料征收附加税和额外附加税违反GATT第2.1条(a)、(b)项,而从该争议措施的形式和实质稍加分析,可以发现其与第2.2条(a)项,即对同类国产品征收国内税高度相关。但是美国没有进一步提出印度的措施不符合第2.2条(a)项,而是逼迫印度提出争议措施符合第2.2(a)项的规定,由此美国只需证明印度征收附加税和额外附加税违反GATT第2.1条(a)、(b)项,而印度必须证明措施符合第2.2条(a)项。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双方争议的焦点实为第2.2条(a)项,而美国为了回避在该项规定下的证明责任,转而指控印度违反第2.1条(a)、(b)项,就这一指控的证明而言,相对容易。因此,这一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存在被申诉方滥用的可能性。
(2)例外条款的辨别存在难度。按照上述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应当由被诉方对例外或肯定性抗辩负证明责任。从一般意义上讲,WTO例外条款是指在WTO协议中准许各成员方在特定情况下撤销或者停止履行其协议规定的正常义务,以保护某种更重要的利益。它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国际收支平衡、保护幼稚工业、保障措施、一般豁免、一般例外、安全例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相关条款。[7]P159-237但在WTO的司法实践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并不认为上述这些条款都属于例外条款。
例如在美国羊毛衬衫和罩衫案中,专家组对于ATC第6条下证明责任的分配,模糊地指出双方都有一定的证明责任。该案上诉机构首先承认:诸如第20条和第11.2(c)(i)条是对某些GATT1994条款下义务的有限例外,不是本身确立义务的积极规则,应当由援引它的被诉方承担证明责任。但是ATC第6条并不属于这种情况,因为ATC第6条是具有临时性质的ATC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经小心得出的成员方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这种平衡必须被尊重。它是“WTO成员权利和义务的一个重要部分”。该案中上诉机构否认了ATC第6条是例外。但是这些理由并不具有说服力。该条是“经小心得出的成员方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很难成为否认ATC第6条是例外的理由。可以毫不夸张地讲,WTO每一个条款,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都是关乎成员方的主权和国家利益,都是权利和义务小心平衡的结果。ATC协定的临时性质似乎也与第6条是否是例外之间无必然联系。
再例如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专家组认为SPS协定第3.1条与第3.3条之间存在“规则与例外”的关系,第3.3条的证明责任应当由被诉方欧共体承担。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错误认定了第3.1条与第3.3条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在性质上与第1条、第3条和第20条之间的关系不一样。第3.1条仅仅从它的适用范围中排除了第3.3条的情况,也就是,成员方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比基于国际水平的措施能够取得更高保护水平的卫生措施。只要成员方遵守某些条件,第3.3条承认成员方进行更高水平保护的自治权。不能因为仅仅将第3.3条识别为例外,就要求被诉方承担证明责任,或者要求按照比条约用语、上下文及目的更为严格的解释。该案上诉机构否认了第3.3条属于例外条款,认为第3.3条具有排除第3.1条适用的效果,并且认为应当按照条约用语、上下文及目的,换句话说也就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解释之通则”来进行解释。尽管如此,上诉机构没有进一步解释清楚为什么第3.3条不是第3.1条的例外以及为什么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进行解释就能得出第3.3条并非例外的结论。
在上述两个案件中,上诉机构反对将争议条款认定为例外条款,但是上诉机构的解释缺乏说服力。在欧共体关税优惠案中,关于授权条款是否属于例外,当事方之间发生争议,最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都认为授权条款是例外。该案专家组认定授权条款属于例外时,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这在同类案件中是很罕见的。
该案专家组首先认为:例外是相对于确立条约义务的主要规则——积极规则而言的。回忆上诉机构在美国羊毛衬衫和罩衫案中所述:第20条和第11.2(c)(i)条是在GATT1994某些条款下义务的有限例外,不是本身确立义务的积极规则。因此本专家组认为,许可从积极规则有限背离的法律功能是使第20条和第11(2)(c)(i)成为例外的决定性因素。在美国羊毛衬衫和罩衫案中,上诉机构有效地建立了确定例外的两个标准:第一,它必须不是本身确立法律义务的规则;第二,它必须具备从一个或更多设定义务的积极规则有限背离的功能。专家组认为与GATT1994第2条、第3条和第11.1条相似的是,第1.1条明显是一个确立义务的积极规则,它要求缔约方给予其他缔约方以最惠国待遇。相似的是GATT1994第2条,第3条和第11.1条都是确立义务的积极规则。作为对比的,较为公认的是第20条一般例外、第21条国家安全例外和第24条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就不是这样一个建立积极义务的规则。GATT1994下没有法律义务要求成员方采取一般例外措施、国家安全措施或者和其他成员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成员方可以自由选择是否采取这样的措施。专家组考虑到授权条款的法律功能主要是设置义务的积极规则,这种理解是对第1.1条最惠国待遇条款背离,该条款通常被理解为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普惠制(GSP)待遇。但是,该授权条款本身并没有要求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GSP的法律义务。授权条款第1段“可以”使得给予GSP明显是一个选择而不是一个义务,因此这是一个对背离的许可。最终专家组认为授权条款符合上述确定例外的两个标准,因此在性质上属于GATT1994第1.1条下的例外。
从上述专家组的观点可以看出,对例外的判断应坚持两个标准:(1)本身不是确立义务的积极规则;(2)许可对积极规则的有限背离。如果我们紧扣专家组的这两个标准,会发现我们上述两个案件中被上诉机构认为不是例外的ATC第6条和SPS第3.3条,均完全符合这两个标准。ATC第6条授权成员方在一定条件下采取紧急保障措施,维持进口的某些限制,而SPS第3.3条许可成员方背离采用国际标准的义务,允许采取高于国际标准的动植物卫生保护措施,这两条本身都不是确立义务的积极规则,同时它们都许可对积极规则的有限背离。因此看来,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识别例外时存在着矛盾之处,尤其是认定某些条款不属于例外时没有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无论是关贸总协定,还是各项乌拉圭回合协议,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每个法律文件均含有大量的例外条款,其数量和种类之多,是其他国际条约所罕见的。”[8]如果证明责任完全按照上述技术性的标准建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因例外条款太多,而被诉方需要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形大大增加的结果,而这显然是上诉机构不愿看到的。
三、WTO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
如上文分析,“申诉方负责证明违反WTO规则的事实”和“援引例外或者肯定性抗辩的负责证明”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并不能解决证明责任分配的所有问题,因此,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实践中逐渐发展出下列两条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上述规则,从而尽力达到实质公平的证明责任分配结果。
1.主张事实的一方应提供证明。在美国羊毛衬衫和罩衫案中,上诉机构首次提出:主张某一事实的一方,不管它是申诉方还是被申诉方,应当负责证明。在阿根廷纺织服装案中,专家组对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进行总结,将“主张事实的一方提供证明”与上述两条规则并列,作为WTO证明责任分配的三条规则。这段关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表述,后来被大量的案件所援引。但是从其适用来看,“主张事实的一方提供证明”这一规则仅仅是在少数案件中被实际运用以解决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因此,它只是作为WTO争端解决中分配证明责任的辅助性规则而存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实践中主要在以下两种情况下适用该规则:
第一,解决某些具体争点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主张事实的一方应提供证明”是一条较为灵活的规定,常常可以帮助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解决某些具体争点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在中美出版社市场准入案中,对于《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第8.4条的理解,当事方之间存在争议:按照这条的规定,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必须符合这样的条件,即,中国合作者在合作企业中所拥有的“权益”不得低于51%。对于“权益”翻译成为“rights and interests”,当事方并无异议,但是对于“权益”,也即“rights and interests”应如何理解,美国认为应理解为“equity”,也就是“资产”,那么中国立法的这种限制就违反了GATS第16.2条(f)项“以限制外国股权最高百分比或限制单个或总体外国投资总额的方式限制外国资本的参与”。而中国则认为“权益”一词,对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而言,不能意味着资产投入而只能代表利润和损失的分配比例。对此,专家组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证明责任,应当由对一成员方某一措施提出特定法律解释的一方负责证明它的解释是正确的。因为美国提出应将“equity”解释为“资产”,因此应由美国负责证明这种解释。
在泰国香烟关税和财政措施案中,菲律宾指出:泰国关于消费税、健康税、电视税的担保豁免权的一般规则未能充分公布,违反GATT第10.1条;未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管理这些法律和法规,违反GATT第10.3条。专家组首先援引了上诉机构在美国羊毛衬衫和罩衫案中提出的“主张事实的一方,无论是申诉方还是被诉方,应负责证明”的观点,然后指出:菲律宾认为泰国确实存在关于担保豁免权的一般适用规则,因此,菲律宾作为主张某一特定事实的一方,必须证明泰国针对担保豁免权适用的未公开的规则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案中专家组以“主张事实的一方提供证明”为由,将具体争点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到具体当事方的结果,与按照“申诉方负责证明被诉方违反WTO规则的事实”这一规则进行证明责任分配,其结果并无二致。专家组这么做的更多是出于证实其证明责任分配结果的考虑。
第二,克服证明责任分配一般规则存在的问题。上述证明责任分配一般规则,主要建立在规范分类的基础上,将规范分为规则与例外,在此基础上进行证明责任的分配。因为WTO规范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以及WTO争端涉及利益的重要性,上述规则并不能解决证明责任分配的所有问题。在日本苹果案中,再次涉及SPS协定下争议措施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该案中,美国指控日本对美国出口的苹果实施检疫限制措施违反了SPS协定第2.2条。按照第2.2条,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要有“科学依据”。如果按照证明标准的一般分配规则,应当由申诉方美国负责证明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没有科学依据。这样的证明责任分配结果与欧共体荷尔蒙案中的证明责任分配结果较为相似,即申诉方必须证明争议措施的科学依据问题。由于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与国家主权的牵涉显然要比一般的关税制度要深,因此上诉机构进行这样的证明责任分配显然更容易得到成员方的赞同。但是这客观上造成了申诉方证明责任过重的结果,[9]P299-300因此上诉机构按照这条规则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上诉机构认为:证明措施不符合第2.2条的责任在申诉方美国。但是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从上诉机构所阐述的观点来看,并不意味着在认定某一措施是否符合协定某一条文规定时的所有事实均应当由申诉方来证明。换言之,尽管申诉方应证明它提出的事实,被诉方也必须证明它作为回应而提出的事实。例如在本案中日本提出若干事实来反驳美国,如:日本必须保护自己,防止出口国控制机制的失灵导致引入苹果而不是成熟和无病害的苹果;苹果而非成熟、无症状的苹果可能被火疫病传染;被传染的苹果可能成为火疫病的传播途径等。因此日本应当对这些事实主张负责证明。在这个案件中,上诉机构借助“主张事实的一方应提供证明”这一规则,调整了按照一般规则分配证明责任的结果。
在上述印度附加税案中,美国有意利用“申诉方证明被诉方违反WTO规则”,指控印度对某些酒类饮料征收附加税和额外附加税违反GATT第2.1条(a)、(b)项,逼迫印度按照第2.2条(a)项进行抗辩,进而承担第2.2条(a)项下的证明责任。对此,上诉机构也是利用这条规则干预了证明责任的分配。上诉机构认为:尽管申诉方必须就其申诉负证明责任,被诉方也要承担它主张的事实的证明责任。在这个争端中,从争议措施的表面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第2.2(a)项适用的潜在可能性,同时因为第2.1条(b)项和第2.2(a)项是紧密联系的条款,应将两者放在一起解读。因此美国必须证明附加税和额外附加税不能在第2.2(a)项下被证明是正当的。因此本案中双方都有责任提供关于第2.1条(b)项和第2.2(a)项的证据,任何一方不能证明它主张的事实都将面临败诉的风险。
“主张事实的一方负责证明”作为一条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严格来说是存在缺陷的。因为“事实”一词比较模糊,包含的范围过于广泛,仅凭此条规则很难在当事方之间分配证明责任。但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实践中相当“克制”地适用该规则,并不轻易打破按照一般规则分配证明责任的结果,无论是适用的频率还是适用的情形,均相当有限。在实践中,这一规则确实可以克服证明责任分配一般规则存在的一些问题。
2.当事方应合作提供证据。当事方应合作提供证据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分配证明责任时又一重要的辅助性规则。国际裁决程序是建立在当事方合作的前提之上,当事方应在程序的不同阶段以及许多的问题上进行合作,[10]这当然也包括证明责任问题。这一点得到了国际立法和判例的支持。
在国际立法层面,1899年以及1907年的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均有关于当事方合作向国际调查委员会提供证据的表述。1899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第12条规定:争端各国承允在他们认为可能广泛的范围内,向国际调查委员会提供对全面了解和正确估计有关事实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和便利。1907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第23条规定:当事各方应尽可能充分向调查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和便利,以使该委员会对有关事实获得完全的了解和正确的估计。国际法委员会制定的《关于仲裁程序公约草案(1953年)》第15条规定:当事方应当在证据的提交方面与仲裁庭合作,同时应当遵守仲裁庭为此目的指定的措施。
在国际判例方面,国际仲裁机构在印度/巴基斯坦卡奇沼泽地仲裁案中,明确提到了当事方合作提供证据的问题。在该案中,两国在证据提供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合作。如为了检查和获取地图以及其他文件的复印件,两国代表团曾互邀到对方收集此类证据,而且两国还保持联系,经常要求彼此提供地图和其他相关书面证据,帮助对方收集和提供此类证据。对此,仲裁庭指出,该案的判决归于当事方合作的精神和两国的礼让。他们以特有的方式协助仲裁庭,以及在收集复杂的书面证据方面保持相互合作。
从国际立法和判例可以看出,国际司法程序案情之复杂以及涉及利益之极端重要性,仅仅依靠技术性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显然不能完全解决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问题,这就决定了当事方应合作提供证据规则存在着较大的适用空间。WTO争端解决实践中,这条规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阿根廷纺织服装案中,专家组明确表示:另一个关于证明责任的辅助性的规则是要求当事方合作提供事实和证据给专家组,尤其是被诉方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常提到的在国际法庭面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当事方合作的前提上。在这个背景下,合作规则最重要的结果似乎是对方当事人有义务将其独有的相关文件提供给法庭。这个义务直到申诉方已经尽其最大努力取得证据并且已经实际上提供了支持其案件的表面证据才产生。然而,应当强调的是,普通法中“发现”证据的程序在国际程序中不存在。因此,我们将遵循这些规则来处理美国要求阿根廷提供文件而阿根廷没有这么做的事实。在土耳其大米进口案中,专家组援引了阿根廷纺织服装案专家组关于合作原则的论断来强调被诉方提供证据的责任。
WTO争端所涉及的主要是辩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因此辩方政府最有能力提供证据材料来澄清有关案件事实的疑问。强调当事方合作提供证据,尤其是被诉方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对于WTO争端解决而言具有很现实的意义。所以,“当事方应合作提供证据”也成为WTO分配证明责任时的一条辅助性规则。
四、结语
综观WTO的争端解决实践,可以发现,“申诉方负责证明被诉方的违反”和“被诉方对其援引的例外或肯定性抗辩负证明责任”已成为基础性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这种证明责任分配方法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国内法上的“法规分类说”,[11]P38侧重于从WTO规则本身的结构出发,将WTO规范分为“规则”与“例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证明责任的分配。在WTO的规范体系内,这种方法具有较高的合理性。WTO规范可以分为“义务性”规范与“例外”规范,前者保护的是贸易自由化的总体利益,而后者保护的是各缔约方的主权利益。在起诉之前,双方之间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而一方起诉另一方违反WTO义务,则必须在“义务性”规范的引导下证明对方违反的事实。对于被诉方而言,如援引“例外”规范进行抗辩,则必须证明符合“例外”规定的条件。但是,由于国际诉讼所涉利益之重大以及案件事实之复杂,仅仅依靠技术性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显然不能完全解决WTO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因此,“主张事实的一方提供证明”和“当事方合作提供证据”这两条辅助性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又应运而生了。其中“主张事实的一方提供证明”属于一条相当灵活的规则,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该规则下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上述证明责任分配结果进行调整,以实现特殊案件下的“实质公平”。而“当事方合作提供证据”强调当事方在合作的基础上提供证据,尤其是被诉方在其中的责任和义务。
近年来,我国已经继美国、欧盟之后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第三位的参与者。证明责任的分配对于争端解决的结果而言至关重要。有学者指出:截至2009年底已经通过的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中,申诉方败诉的案件有13个,而其中就有8个是由于败诉方未能证明自己提出的诉请而败诉的。[12]我国在这方面已有一定的教训,如在中美轮胎特保案中,专家组指出,在因果关系标准、救济措施所采用的限度和时限、是否超过入世议定书第16条的“所必需”的范围等方面应由中国承担证明责任,而我国既没有紧扣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反驳这种证明责任分配结果,也未能举出证据证明我们的观点,这直接导致了我国败诉的结果。在DSU对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付之阙如的背景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实践中逐渐发展出上述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体系,这些判例法中体现出来的规则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例如“例外”的识别问题就始终未能解决。我国应当在充分熟悉这些规则的前提下,运用这些规则来追求对我国有利的证明责任分配结果,最终赢得WTO诉讼。
注释:
① 相关文献可参见Michelle T. Grando,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in WTO Disputes: A Cri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9, no. 3, 2006, pp.619-629;John Barceló III, Burden of Proof, Prima Facie Case and Presumption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42, No. 1,2008.朱榄叶:《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证据问题》,《当代法学》2007年第1期;韩立余:《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任》,《现代法学》2007年第3期;姜作利:《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举证责任分配标准的合理性分析》,《现代法学》2008年第5期;赵维田:《举证责任——WTO司法机制的证据规则》,《国际贸易》2004年第7期。
② 相关文献可参见Michelle T. Grando,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in WTO Disputes: A Cri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9, no. 3, 2006, pp.646-656;Ho Cheol Kim, Burden of Proof and the Prima Facie Case: The Evolving Hist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the WTO Jurisprudence, Richmond Journal of Global Law and Business, vol.6, 2007;David Unterhalter,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edings,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42, 2009.姜作利、武轶尘:《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举证责任分配标准的经济分析》,《东岳论丛》2009年第10期;高田甜:《WTO争端解决机制证明负担规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③ 这里所指的“特殊规则”与高田甜所指的“特殊规则”,即特殊协定下特别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所指的对象完全不同。参见:高田甜:《WTO争端解决机制证明负担规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5-49页。
④ USA-Section 337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 BISD 36S/345, adopted on 7 November 1989, para. 5.27.
⑤ Canada-Import Restrictions on Ice Cream and Yoghurt, BISD 36S/68, adopted on 5 December 1989, para. 59.
⑥ USA-Customs User Fee, adopted on 2 February 1988, BISD 35S/245, para. 98.
⑦ The Australian Subsidy on Ammonium Sulphate, BISD II/188, adopted on 3 April 1950, para.11.
⑧ Treatment by Germany of Imports of Sardine, BISD 1S/53, adopted on 31 October 1952, para.15.
⑨ EEC-Measures on Animal Feed Proteins, BISD 25/49, adopted on 14 March 1978, para.4.21.
⑩ US-Gasoline, Panel Report, WT/DS2/R, adopted on 20 May 1996, para. 6.5.
参考文献:
[1] 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 赵海峰,高立忠.WTO争端解决机制——迈向世界贸易法院的准司法机制[J].人民司法,2005,6.
[3] Joost Pauwelyn. Evidence, Proof and Persuasion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Who Bears the Burden?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1, no. 2, 1998.
[4] 赵维田.WTO的司法机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 薛波.元照英美法词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 Bryan A. 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Eighth Edition) [M]. London: Thomson West, 2007.
[7] [英]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 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M].刘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8] 姜建明,陈立虎.WTO例外条款及其法理基础[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9] James C Hartigan. Trade Disputes and the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WTO: an Interdisciplinary Assessment [M]. 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2009.
[10] Dr. Mojtaba Kazazi. Burden of Proof and Related Issues[J].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6:119.
[11] 毕玉谦.民事证明责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2] 朱榄叶.赢多输少还是输多赢少?——WTO争端解决机制申诉方败诉案件解析[J].现代法学, 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