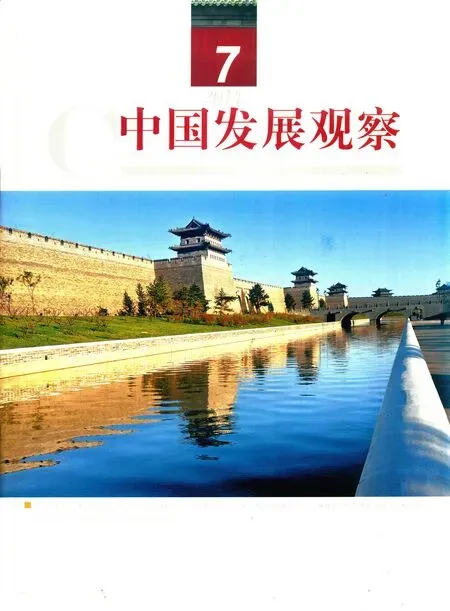九愁一脉问城乡
——读刘奇《“乡愁”九脉》
◎杜永伟
九愁一脉问城乡
——读刘奇《“乡愁”九脉》
◎杜永伟
2014年第2期《中国发展观察》刊登了刘奇《“乡愁”九脉》文章。这篇文章深刻剖析了中国人的乡愁情结,以九愁发问,开解天脉的智慧为我们阐释了乡愁之源,并由乡愁生发开去,在严谨治学、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以及怎样建设小城镇,文章透出的真情、理性,充满睿智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感作者言实由衷、真情表达现实问题。《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作为君子,关注众生民计,这样才不会有失人道、地道和天道。作者对游子思乡和社会面临着的城镇化问题,倍感责任,千思万虑,实言表达,真有兮兮社会、切切众生的士大夫忧国忧民之豪情。中国历代文人学者都传承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的爱国报国之志。刘奇《“乡愁”九脉》是发自内心的厚德情意真言。对城市一元文化洗礼下的结果,作者用“家家包铁栏,户户装猫眼,电话聊千户,不与邻家言”,来描述呆板的、单调的、生硬的、冰冷的人情关系代替了多元的、自由的、和谐的、温情自然的人情关系,感叹“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对有些地方盲目发展城镇化现象,作者说,赶农民上楼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农村脱农的谋划一地比一地现代。批评一些人不懂得什么是历史文明的传承,把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城镇文明对立起来,在做着“灭村运动”的事。如果作者没有立仁贞正的美德,是不会从内心深处说出这等“大不敬”的实话的。对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作者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数据,客观分析了中国近十年平均每天在减少300个村庄。他说:“祖先为我们留下的极珍贵的物质遗产,本该很好地继承保护,这才是有价值的文明产物。但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一切都该推倒重来建新的,这样才能展示自己的才华和业绩。”如果作者没有正义求真的品格,是不会说出这等有人认为是“找闲事”的话的。针对农村非物质文化缺乏有生力量来继承时,作者警醒大家,“美国以高新技术胜,中国以数量居首位,日本则以历代传承的精巧工匠胜。”如果大家只从农村索取食物、不从乡村吸取非物质文化的精神食粮,那么人人追求的现代文明将是空中楼阁。真是警世醒言!
对故乡人的追梦,作者情真意切,希望他们梦想成真,希望故乡的面貌如同故乡人一样能够实现改观,殷切盼望着故乡就是故乡人追梦共建的天堂。对用城市“化”农村,是否就是农村唯一登上天堂之路呢?作者说,这样会“打破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打破了沿袭几千年的道德纲常。”熟人社会和谐亲睦关系遭到破坏,人纲为义、物纲为生、政纲为民的传统伦理规范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城市化不能以传统美德的丧失为代价。对城镇化意义的阐释,作者指出是人人公平享受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搞城镇化不是大量地消灭村庄,乡村与城镇的关系就像一对夫妻,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谁也不能取代谁。用什么方式来建设城镇化,作者用真实的事例引证用“田园组团”和“建筑组团”交叉的方式来发展小城镇。用城镇文化生态来避免城镇一体化对农村传统文化的裹挟,建设多数中下层社会群体的精神栖居。现在中国农村是时代的前线,而农民却退到了城市,农业文明建立起来的社会生态在退化,城市建设得越来越漂亮,乡村越来越凋敝,人要在城里找口饭吃却越来越困难。他以饱含真情的笔触,表达了真实的现实,在对城镇化这个真命题的探讨中,以敢于言真的精神贞卦城镇化的利弊,对问题的分析真可谓真知灼见。
二感理性反思问题、发出哲理启示。哲人明智善反思,对问题的分析和看法要比一般人有深度和深远,角度和高度要比普通人新颖和理性中正。现在社会的乡愁实质上是离开故乡的人在遭遇城镇文化洗礼时,对家乡远离不舍,追念故土生活方式的美好期盼。文中“乡愁”说白了就是愁故乡传统文化和文明的退落,愁故乡人没能守住和建设好自己的幸福生活。因为城镇是把来自不同村落的人集聚在一起进行一体化和格式化改造的场所,把农耕文明生产力低下所形成的熟人社会,通过工商文明把只能进行平等交换而非亲非故的人转化为陌生人的社会。在城镇这个活动场里,为了生活、生产和交流,大家必须使用标准化的语言和行为举止,遵守大家约定俗成的规矩,否则永远要以原生文化的碰撞为代价,以特色乡村文化的减少,农村风景的面目全非为代价。就这样,城镇化渐渐地把我们从以前熟悉的场景、文化和文明中抽丝出来,改造为没有依附感、身在城市里却未觉有主人翁地位的从容自如的人。城镇化是中国治政一项重要内容,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诸内容面临的一个发展课题,是探索中国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作者把这么一个沉重而又关涉政治和社会焦点问题放在一个学术研究的范畴,以游子士子哲人兼有的品质认真反思,用饱满乡愁之念一泄千里,用灵活而又不失学术风格的自由文体进行酣畅表达,足见其睿智,实乃难能可贵。
他的《“乡愁”九脉》句句反思见哲理。一愁城镇化太宠爱一元文化,希冀用多元文明来丰富和消解这太单调的城镇文明。要让传统文明不灭,现代文明不俗,要让平民文化与精英文化并存发展,要让社会存在着“农业文明是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的文明形态。”二愁经农耕文明改造而来的山川河流面目全非,思索要留住记忆中的青山绿水、故乡美景。否则灭村运动灭掉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村庄,而是祖先创造的农业文明。如果我们的现代文明将不能传承历史,文明的传承之源将成为一潭死水。三愁城镇化莫要让几千年的物质文明饱受摧残,对现代建筑破坏传统建筑和反人文的反思,提出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农耕村落。四愁城镇一体化把几千年的非物质文化格式化标准化,让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明渐渐退出我们的人生历程。五愁以城镇为依托的文化,把从农村村落走出来的人改造成不伦不类、角色不自然的一类异味人。“人间的许多悲剧往往就是发生在为了建造一个个完美天堂而抛弃了自己的故乡。”让人失去了做本真的道德人,一个入潮流而不现代的失真人。让人在城镇酒绿灯红下记不清我来自哪,我的生活该怎样才幸福。六愁农业文明建立起来的道德体系受到冲击,甚至是天翻地覆地被破坏。传统的道德礼仪廉耻在物欲横行、人性施放不羁下泛滥成灾。城乡一体化并没有促成和树立起道德体系的一元性。七愁“赶农民上楼”,农民生活条件提高了,但生产条件却下降了,担忧农民即使在城市里也享受不到公平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八愁如何建设小城镇,打造农家田园与城镇建筑交叉互映的格局,使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共生共荣,同步发展。九愁小城镇文化和社会生态的定位,是建构“草灌乔”多元文化,还是精英文化,是以失去农民的精神文明换取高楼物质文明,还是关注中下层社会群体精神栖身之所的建设。他的九脉愁思成了对社会问题的理性反思,成了对现实问题的哲理思考,启发我们去寻找城镇化建设的合理办法,去构建人的本质所需要的兼容生产、生活与生态“三生”和谐发展的幸福城镇化。
三感为城镇化献言献策、立意高远。在文中作者提出了未来城市如何建设这一关乎农业文明生存发展的崭新课题,分析了目前城市化带给传统文化和人文关系的不足之处,反思了“灭村运动”是急功近利割裂农业文明与城市和工业文明遥相辉映的不妥做法。在层层分析中,找出了如何建设城镇化这一民生和社会发展问题不可绕行的出路和办法。他既有士子之忧,政论家的社会责任感,平常百姓人家的思乡之愁,也有仿九章九歌以言志,行高山流水之高雅,吐高屋建瓴之见解。对城镇化建设问题,他的合理建设是:
(1)城镇化是理性城镇化。理性是最佳、适合、兼顾、多元共存之意。要让城镇化楔入“生活更美好、文化更美好、生态更美好”的理念,必须以理性的思维,来建设城市。他指出,理性城镇化不是灭村运动化,不是赶农民上楼,不是任由城市去“化”农村的城市化,不是用城镇里负面的冰冷的一元文化来“化”来自农村带着正能量温情脉脉的人的城镇化,不是把绿树青山、明月清泉、神童牧歌歼灭在城市海洋里的城镇化,不是以祖先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被破坏殆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遗忘殆尽为代价换来的城镇化,不是诚信、和谐、尊亲、守礼等传统伦理美德还没被传承下来,新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现代伦理规范还没有形成之时,那些物欲、兽欲、恶欲、权欲等丑恶现象,在高楼大厦酷似水泥森林的城市环境里泛滥成灾。理性城镇化,作者认为是一种多元文化、灿烂文明发展的城镇化,是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也是看得到物质文化遗产、欣赏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城镇化,更是传统美德传承,新型文明健康生长的城镇化。任何独一灭二的思维和发展理念都是不对的。城镇化建设不应成为使游子愁、农民忧的一项社会建设,应该围绕农民能够享受到如城市一样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来搞好城镇化建设。
(2)城镇化是城镇农村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他指出,在中国,城镇化还远远不够,“但是,推进城镇化不是建立在一刀切地消灭村庄的基础上。只要人类还需要粮食,就必须有一定的村庄保有量。”他把农村与城市协调发展关系比喻成一对夫妻关系。针对中国农村人口多,要改变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让农村人也能享受到城市一样的公共资源,他借鉴欧洲诸国城镇化建设的经验,提出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最佳小城镇建设实施方案,主张中国搞有城市功能又能带动提升农业生产条件的一个个小型城镇建设。在具体小城镇建设实施中,应该把农业作为城市生态有机组成部分,如同城市绿化,用“田园组团”和“建筑组团”交叉展开,做到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协调,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共存,实现把中国几亿农民的生活提高得了,传统农业文明破坏的少,构建一个个让农业作为城镇生态良好建设的宜居大花园。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文明建设中的一个典型而又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社会工程建设。
(3)城镇化是社会生态的城镇化。小城镇建设是农村现在面临着的除了农业生产建设之外,遇到的前沿阵地堡垒,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工程的主攻方向。用田园与建筑交叉发展解决了城镇化的自然生态问题,而社会生态问题如何解决,作者提出了“草灌乔”文化生态建设主张。小城镇建设应该让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草根文化“草灌乔”地结合。要让人的幸福指数提高,不仅体现在住上高楼大厦,生活过得舒服,吃穿住行无忧,更应该让人在内心精神世界方面感到幸福。如果让农民生活攻进了城里,而精神生活却退到了城里,他们精神生活展示和释放的舞台被城镇化遮蔽,那么这样的城镇化对中国八亿农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要让农民融入小城镇,必须发展城市生态文化。让每个刚走进城镇里的居民都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栖所。由于发展小城镇,“我们不能阻挡乡村的变化,但是我们必须留住乡村的文化。”真是高远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