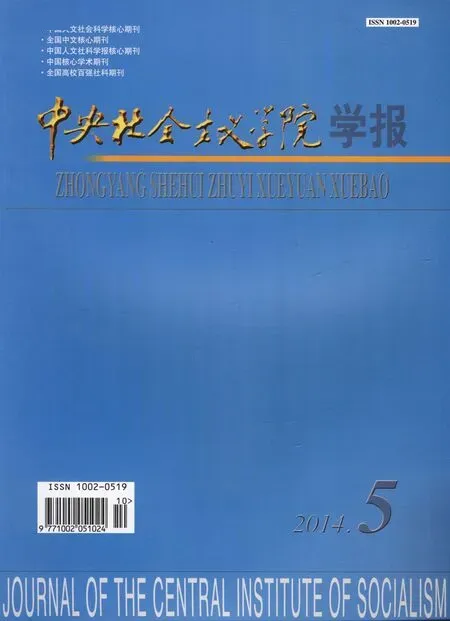关于“回儒”和“西儒”比较研究的思考
金 刚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山东 济南 250100)
·宗教问题研究·
关于“回儒”和“西儒”比较研究的思考
金 刚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山东 济南 250100)
明末清初,在伊斯兰教、基督教与儒家思想文化的对话、交流、调适和融合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回儒”和“西儒”两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回儒”和“西儒”的共同产生,真正开启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全方位的对话和融合,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在华发展传播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回儒”和“西儒”在思想、活动、影响等方面的异同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对当今促进宗教和谐、文化和谐、民族关系和谐、中外文化交流和谐,乃至我国的文化强国战略,都有着十分有益的借鉴作用。
伊斯兰教;基督教;儒家思想;“回儒”;“西儒”
一、“回儒”和“西儒”推动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实现质的飞跃,两者在多方面的异同得失及启示值得深入研究
明末清初是中国封建社会剧烈动荡和深刻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此间,多种政治势力激烈对峙和角逐,多种思想文化广泛交流和碰撞,封建专制主义在空前强大的同时也正在走向僵化、自闭和衰落,西方殖民主义在梦想征服和掠夺中国的同时又不具备真正的实力,中国的主导思想理学在更加成熟的同时也遭遇到有力挑战,中外文化交流在进入崭新阶段的同时也遭遇到重大挫折,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这种状况之下,伴随着伊斯兰教宗教意识的增强和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兴起,在伊斯兰教、基督教与儒家思想文化的对话、交流、调适和融合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回儒”和“西儒”两个引人注目的群体。他们著书立说,共同活跃于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舞台上,在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乃至中外交流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在“回儒”和“西儒”产生之前,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早已传入中国。伊斯兰教自唐朝入华以来,不公开传教,不主动发展信徒,信徒的增加主要依靠群体内部的不断繁衍、其他人口的自然融入、西方穆斯林的持续东来和一些民族群体的主动皈依。基督教曾经两次入华,唐朝时期的景教和元代的也里可温教虽然大力发展传播自身宗教,也曾拥有众多信徒,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湮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在明末清初之前,与同属外来宗教的佛教相比,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没有在思想文化方面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长期、持续、深刻、全方位的交流、对话、碰撞和融合,更没有像佛教一样拥有浩如烟海的中文著作作为传播宗教进而影响中国的载体,其教义教规不为外界所熟知,更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实现深刻的融合。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回儒”和“西儒”并没有产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思想文化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当然也不可能像儒释道三教一样被中国封建政权所倚重。
明末清初“回儒”和“西儒”的共同产生,真正开启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全方位的对话和融合,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华发展传播的转折点,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尽管时至今日,相比之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儒家思想文化的融合仍然远没有佛教广泛和深入,还带有更多的“异质”文化的特点,但是“回儒”和“西儒”的出现,使伊斯兰教、基督教与儒家思想文化的融合发生了质的转变,也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中国化进程实现了质的飞跃。同时,“回儒”和“西儒”在产生背景、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之贡献、本宗教与儒家学说之会通、与中国上层社会之交往、与佛道两教之论争乃至对清末民初“回儒”和“西儒”的影响等很多方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异同得失都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对当今促进宗教和谐、文化和谐、民族关系和谐、中外文化交流和谐,进而促进社会和谐乃至我国的文化强国战略,都有十分有益的借鉴作用。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对“回儒”和“西儒”进行综合考察和对比分析更显得非常重要。
二、对“回儒”和“西儒”进行对比分析,首先应当对“回儒”和“西儒”这两个概念进行梳理和界定
“回儒”一词的出现,跟伊斯兰教在中国又被称为回教密不可分。“回儒”大致有两种意思:一是指伊斯兰教文明(回教)与中华文明(儒教)两大文明体系,与“伊儒”、“经儒”、“经汉”等词含义相近,在这种意义上翻译成英文就是“Islam and Confucianism”。比如,先后在哈佛大学、马来西亚等地召开的一系列“回儒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指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文明对话”研讨会。“回儒”一词较早见于马注的著作《清真指南》,书中说:“若岱舆王先生,回儒博学,墨翰精通,释杖玄丹,应身垂教,虽未及见其人,而《真诠》一集,神游海宇,功在万世,非其文吾不知其人也。”[1]“释氏之学,杂于回儒,若甘草甘遂,共之必反。玄门道在一天,为神者师,而不能复命归真。三教之理,各执一偏。”[1]蓝煦在《天方正学·自序》中讲道:“世人与回儒,往往分视之,而未能参观,良由不明天方经意,以致见少多怪”,“回儒经书,文字虽殊而道无不共,语言虽异而义无不同”,“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以上引文中的“回儒”就是指回教与儒教两种文化。二是指明末清初从事汉文译著活动的回族知识分子和穆斯林学者,在这种意义上翻译成英文就是“Hui Confucian”或者“Chinese Islamic Confucian”或者“Confucian Muslim”。“回儒”一词明确用于指穆斯林学者和回族知识分子首见于日本学者桑田六郎(1894-1987)的《明末清初之回儒》一文,文中说:“中国本部之回回,则迄明末尚颇沉默,不见活动。直至明清鼎革之际以及康熙年间,彼等间乃起一种自觉。于是多数回回学者辈出,翻译回教经典及仪律之举甚盛。此确为中国回回史之一划时代的时期,余算此时期为中国回回史上之文艺复兴时期。盖鼎革之事极有影响,于人心之变动,而明末耶稣教在中国传道之态度与方法,及清朝以塞外民族入主中原后之尊重汉文化,奖励学术,一志明代因循固陋之风习,皆与此复兴时期之现有莫大关系。余所注目者即此一点,可惜先辈研究未能及此也。兹将当时回儒略传及其著述之一列举如次,以为回回研究之一助。”[2]
本文所谓的“回儒”,主要是指从小生长在中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宣扬伊斯兰教为己任,从事伊斯兰教经典、教义的翻译和阐述即“以儒诠经”工作的明末清初的中国回族知识分子或穆斯林学者。这些“回儒”也可称为儒家型穆斯林或儒学化穆斯林,他们因伊斯兰教的儒学化而带有深刻的儒家特质。其主要代表有:王岱舆(约1570-1660)、张中(约1584-1670)、伍遵契(约1598-1698)、马注(1640-1711)、刘智(约1655-1745)、金天柱(约1690-1765)等。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末清初,“回儒”作为一个群体,既非自称亦非他称,而是后来的研究者因其从事“以儒诠经”或“以儒解回”活动而带有回、儒双重文化气质所给与的一个称谓。在民国以前的文献里,“回儒”较少出现,仅指两个文化体系,而非专指一个群体。这也说明明末清初的“回儒”并没有刻意强调自己是“儒”。
“西儒”一词的出现,与以往我国习惯上将欧洲称为西洋或泰西(极西)关系密切。“西儒”大致有三种意思:一是指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两大文明体系,与“耶儒”、“基儒”、“天儒”等词相近,在这种意义上翻译成英文就是“Christianism and Confucianism”。比如,西儒会融、西儒对立、西儒关系演变、西儒和合等都是这种意思。二是指旧时欧美的学者或知识分子,在这种意义上翻译成英文就是“Western Scholar orWestern literati”。比如,梁启超在1902年的《论公德》中写道:“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此西儒亚里士多德之言)”。再如,孙中山在1894年给李鸿章的上书中写道:“窃以我国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肄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3]其中的“西儒”就是欧美的学者或知识分子之谓。包括爱因斯坦、达尔文等西方科学家也被称为西儒。三是指明末至民国来华的传教士。
“西”与“儒”的连用,在明末清初的论著中常常出现,比如,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北京出版的著作《天主实义》,利用儒家思想解释天主教教义,书中多次用“西儒”、“西士”、“西哲”等称呼来代表基督教神学家和西方哲学家。《天主实义》中说:“西儒说人,云是乃生觉者,能推论理也。曰生,以别于金石。曰觉,以异于草木。曰能推论理,以殊乎鸟兽。曰推论不直曰明达,又以分之乎鬼神。”[4]“异端伪经,虚词诞言,难以胜数,悉非由天主出者。如曰‘日轮夜藏须弥山之背’;曰‘天下有四大部州,皆浮海中,半见半浸’;曰‘阿函以左右手掩日月,为日月之蚀’。此乃天文地理之事,身毒国原所未达,吾西儒笑之而不屑辩焉。”[4]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于1626年在杭州出版中文著作《西儒耳目资》(“An aid for the ears and eyes ofWestern scholars”),用来帮助来华传教士认读汉字,并让中国人了解西文。明末的徐光启在《景教堂碑记》中说:“我中国之知有天主也,自利君玛窦来宾始也……其言曰‘西儒所持论,古昔未闻也!’”明末王徵在家乡建立天主教平信徒慈善救助团体“仁会”。在《仁会约》中,王徵交代立会宗旨:“西儒所传天主之教,理超意实,大旨总是一仁。仁之爱用有二:一爱天主万物之上,一爱人如己。真知畏天命者,自然爱天主。真能爱天主者,自然能爱人。”明末的金声著有《金忠节公文集》,认为实学与西学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称自己“敬服西儒,嗜其实学”。清初方以智在著作《膝寓信笔》中说:“西儒利玛窦泛重溟入中国,读中国之书,最服孔子。其国有六种书,事天主,通历算,多奇器,智巧过人。著书曰《天学初函》,余读之,多所不解。”[5]
本文所谓的“西儒”,主要是指明末清初长期生活在中国,研习儒家经典,介绍西方知识和科技,以传播基督教为己任,遵守“利玛窦规矩”,致力于“合儒”、“补儒”、“超儒”和以基督教归化中国人的工作,会通儒家思想文化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这些“西儒”也可称为儒家型基督徒或儒学化的基督徒,他们因基督教的儒学化而带有明显的儒家特质。其主要代表有: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艾儒略(Julio Aleni,1582-1649)、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马约瑟(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1665-1741)。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末清初,“西儒”作为一个群体,既是自称亦是他称,并非后来的研究者提出的一个称谓。这也说明“西儒”为了传教之目的刻意将自己打造成“儒”,这一点与“回儒”迥然不同。自明末以来至民国期间的文献中,“西儒”一词大量出现。鉴于“西儒”在明末清初就专指若干群体,为了便于理解,且不与西方的汉学家或汉学派乃至旧时欧美的学者或知识分子混淆,本文所谓的“西儒”翻译成英文就是“Western Confucian”或者“Christian Confucian in China”或者“Confucian Christian in China”。
三、对“回儒”和“西儒”进行对比分析,关键是着力研究促使他们成为“儒”的关键——会通儒学活动
“回儒”和“西儒”的产生,与儒家思想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对话和融合,尤其是他们会通儒学的思想和活动。综观中国宗教发展史,外来宗教(主要指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有一种特别明显的倾向,即尽力靠拢、比附、融会、贯通、接受、吸收乃至改造、补正儒家学说,尤其是通过阐明佛儒、伊儒、耶儒相通甚至同源,以调和与儒家思想文化的关系。这种现象一般分别被称为佛教“援儒入佛”现象、伊斯兰教“附儒、补儒、包儒”现象和基督教“合儒、补儒、超儒”现象,本文综合这三种现象的共同特点统称之为“会通儒学”现象。正是在会通儒学的过程中,一部分穆斯林学者和天主教传教士才具有了双重文化气质,成为“回儒”和“西儒”。
外来宗教“会通儒学”现象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认同现象,其突出特点是求大同存小异,“和而不同,不同而和”。从历史上看,这种文化认同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碰撞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是各种文化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普遍规律,它有利于不同文化之间增进理解和尊重,减少隔阂与冲突,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团结统一。就中国而言,文化认同无时无处不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外来宗教对在中国处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外来宗教“会通儒学”活动的历史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会通儒学”是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催化剂。中国化是外来宗教在中国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基本规律。中国化既是外来宗教对本土文化的施予和吸收,也是本土文化对外来宗教的施予和吸收,从而产生既不完全同于原来的宗教,又完全不同于本土文化的新的文化形态。从历史上看,宗教不进行本土化就很难适应中国社会,不适应所处社会就会阻碍宗教的发展及社会的和谐稳定。而文化认同是宗教本土化并进而适应所处社会的首要和关键一环。就中国而言,外来宗教的中国化正是随着“会通儒学”活动这一文化认同现象的发展而逐渐深化的。“会通儒学”活动有助于外来文化由“文化披戴”发展为“文化融入”,不断催化外来宗教的中国化进程。
第二,“会通儒学”是中外文化顺利交流的润滑油。外来宗教文化若想与中国文化顺利对话和沟通,就必须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切实寻求与中国文化的认同与融合。外来宗教“会通儒学”活动的最直接的作用是使人们对其宗教教义有了一定的了解,减少了误解,尤其是使佛儒、耶儒、伊儒相通或同源渐入人心。这就减少了人们的排斥心理,增加了人们尤其是士大夫和皇权的认同感,这对宗教在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外来宗教不进行“会通儒学”活动,而是竭力排斥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化,就必然难以在中国生存和发展,文化交流就会受到重大挫折甚至中断。“礼仪之争”导致清政府禁绝天主教就是活生生的事例。
第三,“会通儒学”是外来宗教受到冲击时的减震器。外来宗教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冲击,此时,外来宗教“会通儒学”的活动就显示了作用。当“礼仪之争”造成清政府禁教时,不少认为基督教教义“多与孔孟相合”能“补益王化”因而受洗入教的士大夫,在危机时刻起而护教,尤其突出的是被称为“教门中坚”的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名公巨卿,利用自身的影响尽力减少禁教政策对天主教的冲击。
第四,“会通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丰产素。“会通儒学”现象以佛教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因而佛教的儒学化或者说中国化最为明显,又因为儒佛之间总体上是一种相互融合和吸收的关系,所以,佛教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上说,外来宗教为发展而适应,为适应而“会通儒学”的活动在总体上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四、对“回儒”和“西儒”进行综合考察和对比分析,应紧紧抓住最能体现他们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的重要内容
“回儒”和“西儒”都被称为“儒”,表明他们必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区别。相反,他们又分别被称为“回儒”和“西儒”,本身就表明了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可以说,“回儒”和“西儒”存在不少异同之处。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面面俱到,而要紧紧抓住最能体现他们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的重要内容。
第一,“回儒”和“西儒”的产生背景。明末清初之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早已传播到中国,因此,我们不能绝对地说此前没有出现过儒家型穆斯林和儒家型基督徒,但真正意义上的儒家型穆斯林和儒家型基督徒即“回儒”和“西儒”应是产生于明末清初。因为,没有有意识的文化对话和融合,真正意义上的“回儒”和“西儒”无法产生。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学者和天主教传教士虽然宗教背景不同,但他们共同怀有振兴和发展各自宗教的愿望和使命,共同面对而且必须适应在中国处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文化,这促使他们在有意识地与中国社会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对话和融合过程中,分别成为带有各自鲜明宗教特质的“回儒”和“西儒”。“回儒”和“西儒”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这其中既有促使他们称为“儒”的共同原因,也有造成他们分别被称为“回儒”和“西儒”的各自不同的因素。这种不同根源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宗教文化特质。“回儒”和“西儒”的产生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文化背景不同:“回儒”自幼受伊斯兰教和儒家文化的双重影响,而“西儒”深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和洗礼;二是依附对象不同:“回儒”没有依附某种力量或者说没有后盾可言,而“西儒”有天主教和欧洲列强为后盾依托;三是心理动因不同:“回儒”侧重于实现文化自救和宗教复兴愿望,而“西儒”侧重于完成文化扩张和宗教传播使命。
第二,“回儒”和“西儒”与儒家学说之会通。“回儒”之所以被称为“回儒”,“西儒”之所以被称为“西儒”,除了表明了他们各自的异质文化特点外,更深刻地体现了“回儒”和“西儒”与儒家思想文化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对儒家思想文化的适应、接受甚至践行,使“回儒”和“西儒”都被共同归于儒者行列,而在宗教特质方面的明显区别,又使他们分别被称为“回儒”和“西儒”。伊斯兰教学者和天主教传教士在对儒家学说有了比较深入的把握的基础上,在保持自身特质和核心教义的前提下,着力会通儒学,以会通来求得与儒家思想文化的有机交融。综观中国宗教史,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都不约而同地去调和与儒家思想文化的关系,尤其是在教义上“会通儒学”,“会通儒学”成为各外来宗教适应封建中国的共同选择。“回儒”和“西儒”的“会通儒学”活动既有很大的相似性,也有明显的区别。“回儒”和“西儒”与儒家学说之会通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核心目的不同:“回儒”“会通儒学”的目的侧重于宣扬伊斯兰教教义,致力于适应儒家学说,以消除误解和隔阂,使教内教外了解和认识伊斯兰教的真谛,而“西儒”“会通儒学”的目的侧重于传播天主教,意在通过“合儒”、“补儒”、“超儒”,改造儒家学说,以天主教归化中国人;二是涉及范围不同:“回儒”对历代儒家学说一概予以会通,而“西儒”则“容古儒”、“斥新儒”;三是教内外回应不同:“回儒”面临的阻碍很小,并且赢得了教内外的普遍赞美,而“西儒”除了得到教内外的赞赏外,更受到强烈的批评、诋毁和牵制。
第三,“回儒”和“西儒”与上层社会之交往。“回儒”和“西儒”在开展“会通儒学”活动的同时,与中国上层社会的交往也尤为密切。“回儒”和“西儒”都充分认识到,在中国,若想实现宣扬和传播宗教的理想,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获得中国上层社会的认可和支持。综观中国的宗教历史,各种宗教的兴衰成败和社会地位的高低,无不取决于中国上层社会尤其是皇权对其态度,皇权推崇则宗教兴盛,皇权压制则宗教衰落甚至湮灭。因此,尽力接触士大夫乃至皇权是“回儒”和“西儒”振兴和发展各自宗教的主要方式。其中,首先取得士大夫的支持和推崇是第一步,也是进而获得皇权支持和推崇的“跳板”。可以说,在整个“会通儒学”活动的过程中,“回儒”和“西儒”得到了中国上层社会尤其是一些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真诚理解、充分肯定和宝贵支持,这使得他们的“会通儒学”工作更富成效。尤其是“西儒”殚精竭虑通过各种方式成功地踏上“跳板”,在明末清初的中国皇权内部争得了一席之地,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影响。“回儒”和“西儒”在与中国上层社会交往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一是交往方式不同:“回儒”与中国上层社会交往方式主要是学术交流,而“西儒”与中国上层社会交往方式是学术和科学并重;二是实际作用不同:“回儒”与中国上层社会的交往作用比较单一,而“西儒”与中国上层社会的交往产生了多种作用;三是社会影响不同:“回儒”的社会影响仅限于很小的范围内,且与封建政权的最高层没有直接的联系,而“西儒”的社会影响不仅范围很大,而且与皇权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
第四,“回儒”和“西儒”与佛道两教之论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西亚地区产生的一神教,后来都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明末清初,正是由于强大的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的阻隔,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才不得不取道海路。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具有十分紧密的关联性,因而,持天方学的“回儒”和持天学的“西儒”的一神教的背景和特质,使得他们在对待中国的多神教佛教和道教方面表现出态度方面的极大一致性,“回儒”和“西儒”在着力实现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为宗教的儒学的会通的同时,不约而同地与佛道两教“划清界限”。他们都认为佛道两教均为异端,并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掀起了又一次宗教的论争。如果说“回儒”和“西儒”着力会通儒学、积极与中国上层社会交往是在正面体现了他们“儒”的特色,那么,对于佛道两教的大力批判和排斥又在另一个角度反衬出“回儒”和“西儒”的“儒”的倾向。“回儒”和“西儒”对佛道两教大力批判的区别在于:前者几乎没有受到佛道的回应,而后者却遭到了佛道的猛烈还击。
此外,明末清初“回儒”和“西儒”的思想和活动对清末民国的“回儒”和“西儒”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清末民国,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冲开中国的大门,西方传教士再一次来到中国,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角不再是天主教,而是基督教新教。尽管很多传教士因成为列强的急先锋和同流合污者而犯下滔滔罪行,为中国人民所不齿,但也有很多称得上“西儒”的传教士,延续和继承明末清初“西儒”的思想和活动,着力实现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融合。与此同时,在回族人民顽强反抗清政府民族压迫的背景下,新一代的“回儒”也活跃在激烈动荡的中国舞台。毋庸置疑,清末民国的“回儒”和“西儒”都曾受到明末清初的“回儒”和“西儒”的深刻影响,尽管世易时移,他们与先人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其核心理念确实一脉相承,即传播基督教或振兴伊斯兰教。从这一角度来看,对清末民国的“回儒”和“西儒”进行比较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当今,人们充满了对世界和谐的期待,文明对话和宗教交流蔚然成风,蓬勃发展。而如何化误解、偏见、对抗和冲突为理解、宽容、对话和和谐,进一步实现普惠、共赢和共进,“回儒”和“西儒”的思想和活动以及异同得失能给我们不少借鉴和启迪。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回儒”和“西儒”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中国封建社会对话、交流、冲突、融合过程中的表现、作用、影响的异同得失,在理论上探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生存、发展、传播的基本规律以及中外文化交流所应当和必然遵循的重要原则,对于促进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平等交流、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意义重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明末清初的“回儒”和“西儒”进行比较研究,目的不在于区分出“回儒”和“西儒”及其宗教的高低优劣,也不在于阐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多少误读和偏见,而在于彰显他们勇于促进人类文明交流和融合的可贵精神。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所有对人类文明交流做出贡献的人都需要和值得我们尊重,所以,不苛求于古人在某些方面存在的缺憾,而是将古人的优良之处发扬光大,始终应该成为当今人们认真遵循的原则。
[1]马注.清真指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2]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3]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张晓林.天主实义与中国学统[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杨 东
Thoughts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Muslim Confucian”and“Western Confucian”
JIN Gang
(Party School of Jinan Municipal CPC Committee,Jinan,Shandong,250100)
During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Dynasty,in the process of dialog,communication,adjustment and fusion between Islam,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there appeared two noticeable groups,i.e.“Muslim Confucian”and“Western Confucian”.The concurrentappearance of these two groups started up the overall dialog and fusion of Islam,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especially the Confucianism.It was the milestone and epoch-making turning point for Islam and Christianity to develop and spread in China.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Muslim Confucian”and“Western Confucian”could inspired us profoundly and could be useful reference for us to facilitate religious harmony,cultural harmony,harmonious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harmonious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and even for our strategy to build a much powerful country through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lam;Christianity;Confucianism;“Muslim Confucian”;“Western Confucian”
B91
A
1002-0519(2014)05-0084-06
2014-07-07
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J002)
金刚(1973-),男,回族,中共济南市委党校科研部副主任、学报常务副主编,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史党建专业博士后,主要研究民族宗教、党史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