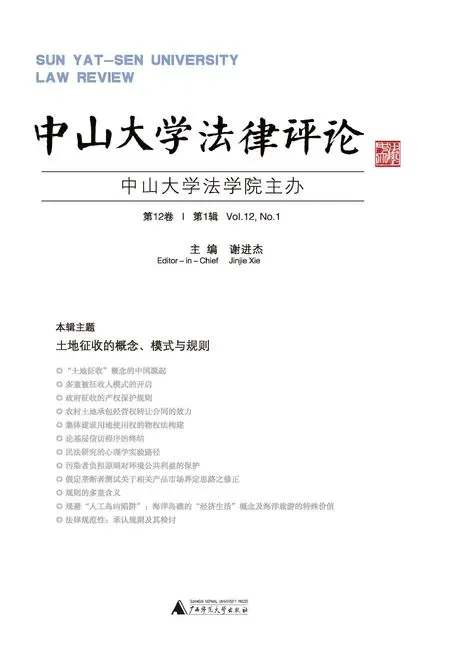民法研究的心理学实验路径
柯振兴
民法研究的心理学实验路径
柯振兴[1]
最近几十年,心理学实验方法被广泛应用到法学研究中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合同法领域,研究人员通过实验来考察禀赋效应对默示条款的影响,也用实验方法研究影响违反合同的几个因素中哪个因素发挥最大的作用。在侵权法领域,实验被用来验证后视偏差和结果偏差等心理因素对侵权法因果关系判断的影响,并且研究人员也提出了一些建议试图消除这些因素的干扰。在决定侵权赔偿数额时,人们也研究了禀赋效应对陪审团确定赔偿数额的影响。最后,实验也被用来研究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影响因素,比如测试案件的伤害程度和被告的财富以及陪审员的个人心理因素是否会影响陪审员的决策。
实验方法;禀赋效应;后视偏差;惩罚性赔偿
一、引言
心理学实验,是指在人为控制或模拟的特定条件下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比较,从而发现事物间的因果联系,或者验证某种理论假设是否正确可行而进行的一系列操作或活动。[1]葛琳:《从理念到技术:在司法领域中运用实验方法的局限性》,《清华法学》2011年第6期,第109页。注意,本文的实验研究是指心理学的实验室实验(laboratory experiments),而不包括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s),即在真实社会场景中进行实验。为了叙述简便,心理学实验常常简称实验。Camerer和Talley发现,在美国法学界过去的几十年,没有一种方法像实验方法那样受到越来越多的瞩目。如今,翻开美国的各种法学期刊,实验研究已经在法学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且应用领域也很广,无论是合同法、侵权法,还是司法制度都有实验研究的身影。[2]Colin Camerer,Eric Talley,Experimental Study of Law,Handbook of Law and Economics,Volume 2,Edited by Mitchell Polinsky and Steven Shavell,Elsevier,2007,p.1621.笔者认为,法学的实验研究在美国得到很好的发展,与实验方法本身的优点以及美国特殊的司法制度有关。首先,实验方法力图还原现实情境,排除偶然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人们的行为和态度,使得实验方法的效度较高。[3]在社会科学领域,信度和效度是评价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指标。效度指研究真实、正确地揭示了所研究的问题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程度,即研究结果符合客观实际的程度。研究的信度是指研究所得事实、数据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程度。并且,实验可以通过施加一些自然状况下没有的自变量,从而观察到自然状况下无法发现的情况,扩大了研究的范围。[4]何挺:《法律实证研究中的实验方法》,《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78页。其次,这也可能和美国特殊的陪审团制度有关。在美国,刑事案件和部分民事案件的审判都会使用陪审团制度,比如在民事诉讼中,陪审团决定被告人是否要赔偿。与此相对应的,在实验研究中,研究人员往往会招募一些具有陪审员资格的公民来参加心理学实验,在给予具体的案件场景后,让这些公民模拟自己担任陪审员时的状态并对案件作出决定。研究人员则通过研究陪审员的决定来判断他们是否受某些特定心理因素的影响。
当下,国内的法学界对美国法学的实验研究已经有了一些介绍,[5]参见朱全景《法学实验论纲》,《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4期;何挺《法律实证研究中的实验方法》,《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葛琳《从理念到技术:在司法领域中运用实验方法的局限性》,《清华法学》2011年第6期。但是这些文章都缺乏对实验方法在部门法的具体应用的介绍和分析。此外,虽然学界也翻译了《行为法律经济学》等著作,但是翻译不等于我们已经消化了这种实验方法,仍然需要加以整理和分析。[6][美]凯斯·R.桑斯坦:《行为法律经济学》,涂永前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而本文希望从民法的实验研究切入,来介绍美国的相关研究现状。鉴于中国当前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此时更重要的是介绍法学实验的过程(而不是结论性的东西),便于从模仿开始进行法学的实验研究。因此,本文会侧重介绍合同法和侵权法的心理学实验过程。
在介绍具体的实验过程之前,笔者先介绍实验这种研究方法的一般路径以帮助理解。
首先,根据实验的目的,实验设计者可以选择不同的实验参加者。如果实验对参加者没有特殊要求,一般就会随机抽取一些人员参加实验,可能是学生,也可能是居民。如果有特殊要求,比如实验想研究陪审员的心理,那就会从符合陪审员资格的公民中抽取。在确定实验参加者后,实验的组织者会提供一些指导(instruction),来告诉他们在实验中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然后是实验的具体过程。接下来就是分析实验结果。有些实验,实验组织者只要分析实验参加者的行为即可;有些实验是在试验后通过让实验调查者填写问卷调查来测试他们的态度,那么就需要通过搜集问卷的数据来分析实验结果。最后是结论部分,对实验结果进行总结,确定实验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以及实验的不足之处。[1]更加系统的介绍请参见Rachel Croson,Why and How to Experiment:Methodologies from Experimental Economics,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2002,pp.921—946。
二、与合同法有关的心理学与法研究
(一)禀赋效应与默示条款
1.禀赋效应的概念和原理
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是指,个体在拥有某物品时对该物品的估价高于没有拥有该物品时的估价的现象。[2]刘腾飞等:《享赋效应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4期,第646页。Kahneman曾经做过一个关于禀赋效应的经典实验:他把实验人员随机分为卖家和买家。每个卖家拿到一个杯子,并被指定从0到8.75美元中选择愿意出售的价格(每次都是以0.5美元上下浮动)。同样,也为买家指定价格区间,并询问他们愿意为购买一个杯子所支付的具体价格。结果显示,卖家报出的卖价的中间值可达到买家报出的买价的两倍多。也就是卖家所接受的出售的价格(willingness to accept,简称 WTA)要高于买家愿意去购买的价格(willingness to purchase,WTP),即WTA>WTP。[1]Daniel Kahneman,Jack L.Knetsch,Richard H.Thaler,Experimental Tests of the Endowment Effect and the Coase Theorem,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1990,p.1330.
禀赋效应是对科斯定理的一种修正。科斯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时候,那么无论初始权利支配给谁,最终的结果都一样,也就是产值最大化或者避免最大的伤害。科斯文中的例子如下:一个糖果店经营多年,但是后来一个医生来到此地并购买了糖果店旁边的土地。之后八年他们都相安无事,直到八年后,医生想开一个咨询室,但是医生认为糖果店的机器太吵,影响他的工作,于是就向法院起诉要求糖果店停止使用机器。接下来科斯分析道,对于医生来说,他所拥有的土地价值200美元,而对于糖果店来说,糖果店只值100美元。那么,如果医生胜诉,则医生继续留在此地;而如果医生败诉,医生则会向糖果店支付100美元(可能多于100美元,但是不会超过200美元)。如果请求糖果店搬走,糖果店也会愿意搬走,因为只要医生支付的价钱多于100美元,糖果店还会获利。因此,无论如何,最后结果都是糖果店搬走,医生继续在此地工作。[2]Ronald Co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2,1959,p. 26但是在禀赋效应下,如果一个人拥有该东西的所有权,那么他的出价可能就会比那些没有拿到所有权的人的出价要高。在科斯的例子里,如果糖果店对自己原来的地方比较有感情,或者出于对失去糖果店的害怕,出价就可能高于200美元,即超过了医生的底线。这个时候,搬走的就是医生了。
2.禀赋效应对默示条款的影响
默示条款(default rule)指在合同中非以语言文字等明示方式表现,但依据明示条款、法律规定、交易习惯或当事人的行为等推论而得出的合同中理应存在的条款。[3]翟云岭、王阳:《默示条款法律问题探析》,《法学论坛》2004年第1期,第28页。关于默示条款在合同中的地位,有人曾经利用科斯定理提出了一个解释,即按照科斯定理,如果交易成本足够低,双方会同意有效率的合同条款,而不管默示条款是哪方持有。[4]Stewart Schwab,A Coasean Experiment on Contract Presumptions,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17,1988,pp.246—249.但是,按照禀赋效应的解释,一旦合同当事人知道了默示条款,会对整个合同有一个重新的评价,即显示出对默示条款的偏爱。
Schwab设计了一个关于集体合同的实验来验证这种偏爱。在实验里,实验参加者随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代表工会,另一部分代表经理。一个工会代表和一个雇主组成一个小组进行谈判。然后全部小组又被分成两组,一组的默示条款是禁止雇主把业务从一个有工会的工厂转移到一个没有工会的工厂。(在一个没有工会的工厂,雇主将获得更大的自主权,这对于雇主有利。反之,有工会的工厂会对雇主的管理权带来限制,对雇主不利。)另一组的默示条款是允许经理转移工厂。每一组都被要求对工资、假期以及雇主转移业务的权利达成协议。同时,每个参加者都得到一张“偏好表”,这张“偏好表”显示集体协议中不同条款的分值。实验的要求是每个人得到的分数要尽可能多。
实验结果表明,和转移工作有关的默示条款会对最后的结果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当转移工作的条款是有效率的而不转移工作的条款是默示条款时,工会代表平均得到1229个点,但是当转移工作也是默示条款时,工会代表平均得到1137个点。原因是,当转移工作的条款是有效率的而不转移工作的条款是默示条款时,双方都会追求转移工作的有效率条款,但是工会代表会坚持要求雇主对放弃默示条款作出赔偿(比如增加其他有利于工会的条款),所以工会得到的点数就比较多。但是当默示条款已经是转移工作的条款时,工会便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卖给雇主,因此得到的点就比较少。[1]Stewart Schwab,A Coasean Experiment on Contract Presumptions,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17,1988,p.255.这个实验结果比较支持禀赋效应,而与科斯定理推导出来的结论不符。
(二)合同违约的心理状态
关于合同违约的心理状态,波斯纳主要是从经济因素来分析的。波斯纳认为,对一方当事人来说,如果违约的效益高于履行的效益,那么违约行为就是值得鼓励的。但是Baumer和Marshal则认为,人们在考虑违约时并未像波斯纳那样只考虑经济因素,反而会受道德的约束。在美国北卡罗纳州,他们调查了119个公司,在回答“如果一个贸易伙伴因为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生意而故意违反契约时,这个行为是非道德的吗”时,有105个被调查者回答是。并且,在119名被调查者的公司中,有86个公司在将来或几乎一直都不会与故意违约的公司做生意。[1]David Baumer,Patricia Marshal:Willful Breach of Contract for the Sale of Good:Can the Bane of Business Be an Economic Bonanza,Temple Law Review,Vol.65,1992,pp.159—186.转引自孙良国、单平基《效率违约理论批判》,《当代法学》2010年第6期,第73页。而Eigen的实验则更加综合,分别从法律、道德、经济以及社会因素出发,考察哪个因素对合同违约的影响力更大。
Eigen设计了一个非常精巧的实验。在实验里,实验参加者被要求填写一个关于工作的问卷调查,而一旦填写完成,就会得到一个DVD的奖励,但是这个问卷本身非常长,一共有480个问题,如果按一个网页上有一个问题来算,参加者要点开480个网页才能完成。因此实验参加者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就会选择退出。而在选择退出时,他们的网页会跳出一个对话框,对话框要求实验参加者返回问卷继续回答。对话框一共分四种,代表了让参加者返回页面继续回答的四种理由:第一是法律原因,既然参加了实验,就要遵守,不然就是违反了法律,所以你必须继续回答问题;第二是道德原因,中途退出回答有违道德,所以必须继续作答;第三是实用或者是经济原因,如果完成问卷会得到DVD,所以还是继续回答吧;最后一个原因是社会原因(社会压力),因为其他人都把问卷做完了,你也赶紧把它做完吧。这四类对话框会随机出现在想退出的实验参加者的页面里。
最后实验组织者统计了每种情况下实验参加者继续答题的答题数量。他们发现,在道德组,人们退回去做题的平均人数最高,其次是社会因素,紧随其后的是经济因素,而法律因素排在最后。法律因素排在最后也好理解,因为这是人们自愿参加的活动,法律实在没有什么约束力。而意外的是经济因素只排在第三位,显示其并没有道德和社会因素重要。实验组织者还统计了实验参加者退回页面至少再回答一题的比例,结果也是类似,道德因素和社会因素依然排在前两名,第三名变成了法律因素,而经济因素是最后一个。不过第三名和第四名在数值上差距不大。实验结果显示,道德因素在推动人们守约的工作上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而经济因素显然作用不大。[1]Zev Eigen,When and Why Individuals Obey Contracts:Experimental Evidence of Consent,Compliance,Promise,and Performance,网址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640245,访问时间:2013年11月19日。
三、与侵权法因果关系有关的心理学实验
(一)后视偏差(hindsight bias)心理对因果关系的影响
1.后视偏差
后视偏差的意思类似老话“事后诸葛亮”,是指个体面临不确定性事件时,往往对先前获得的信息有过高的估价,进而在决策上发生偏差。
心理学有三个理论来解释后视偏差,第一是公平世界理论(just world theory),也就是我们民间所说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即如果一个悲剧是可以预期的,那么人们会更倾向将其归咎于受害人本人的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第二是印象管理理论,即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评价往往会受之前印象的影响。第三则是认知心理学上的解释,按照这个理论,人们本质上会将一个结果和之前发生的事情合并成一个连贯的故事。因此,他们会将结果的发生归结为一些突然发生(precipitating)的情境因素,因此在分析时会特别倚重这些情境因素来解释,从而偏离用先见之明(foresight)的眼光来对待这些因素。[2]Jeffrey Rachlinski,A Positive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Judging in Hindsigh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65,1998,pp.582—585.
2.后视偏差对因果关系的影响
后视偏差对侵权法因果关系的影响是,它会使知道事情结果的人们过高估计发生的情况的可能性,或者扩大结果的可预测性(foreseeability)。
Kamin和Rachlinski就通过实验来验证“事后诸葛亮”在侵权法里的具体体现。实验的情境是一座城市已经造好了一座吊桥,然后需要决定是否设置一个操作员来防范洪水的风险。实验参加者一共分三组,第一组是先见之明组(foresight),组员的职责是监视天气变化,然后当河水威胁吊桥的时候,就把桥面升起来使其不被洪水冲走。其他两组都是后视偏差组(hindsight)。这两组的相同点是,他们遇到的情况都是冬天发生了洪水,洪水破坏了附近的一个面包店,于是面包店的老板起诉市政府,认为市政府应该设置一个操作员去监视大桥,不然就存在管理上的过失。这两组的不同点是,后视偏差组的后一组加入了一个“去后视偏差”的指导,也就是法官会指导实验参加者不要受“事后诸葛亮”这种心理的影响,更多地从先见之明的角度来考虑市政府是否要承担责任。最后,三组实验参加者都需要填写问卷调查,回答的问题是他们认为市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承担责任,以及决定市政府是否需要雇佣一个操作员。
这个实验的假设是,后视偏差组比先见之明组会更倾向于让市政府承担过失责任,但是当后视偏差组受到法官的指导后,后视偏差的影响趋于消失,即受到指导后,先见之明组和后视偏差组的判断应该不会存在显著性差异。实验结果显示,后视偏差组认为市政府应该承担责任的比例明显高于先见之明组,即当人们受后视偏差的心理因素影响时,他们更会认为市政府应该承担责任。但是两个后视偏差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后视偏差在人的判断思维中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而且即使法官给予了指导也很难消除后视偏差的影响。作者也因此得出结论,通过本次试验,本文不能提供后视偏差的解决办法。[1]Kim Kamin and Jeffrey Rachlinski,Ex Post≠Ex Ante:Determining Liability in Hindsight,Law And Human Behavior,Vol.19,pp.94—98.
(二)其他因素对因果关系判断的影响
1.结果偏差(outcome bias)
结果偏差是指如果人们知道一件事情变坏,他们可能更会认为是有人不小心。结果偏差与之前的后视偏差是相互独立的。后视偏差主要是夸大了坏结果的可预测性,而结果偏差主要是通过将坏结果和坏的决定联系起来来干扰人们对因果关系的判断。
Walster发现在生活中,人们对待不同事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事故比较轻,人们会对事故表示同情,会觉得这个人运气不好。但是如果事故比较严重,人们就会觉得,一般人都不会出现的问题发生在他身上,是不是有他本身的因素?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因此,Walster实验的假设是,如果一个人的事故越严重,人们就越会相信事故是这个人本身的原因导致的。
在实验里,人们被随机分成四组。首先,他们会被告知一个实验的情境,即一个叫Lennie的人开车出了事故。第一组和第二组是一对。第一组的情景是,事故前,车辆已经停下来,没有造成实际损失。第二组是车辆没有停下来,车辆损失严重。第三组和第四组是一对,主要的区别是第四组的后果更加严重。即,第三组,车辆已经停下来,损失很轻微,乘客也没受伤。而第四组,车辆撞到杂货店,不仅车辆和杂货店受损,杂货店的一个小孩也因此受伤。实验里每个人在知道情境后都会进行问卷回答,其中主要的问题是,你是否觉得Lennie应该为事故负责任。而问卷的结果发现,在事故严重的情景中,人们更认为Lennie应该为事故负责,而在事故不严重的情景中,认为Lennie应该为事故负责的人要少得多。[1]Elaine Walster, Assignment of Responsibility for an Accid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3,pp.74—75.
2.事件的性质对因果关系判断的影响
Alicke的实验主要是想验证人们对一个事故的价值判断(比如事故的发生原因是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或者是不可接受的)是否会影响人们对责任归属的判断。具体来说,实验一共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两个场景。本文主要介绍与本文相关的第一个部分。[2]其他场景只是增加了新的客观情况,第二部分的场景还是一样,但是比第一部分增加了一个事故的客观原因: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地上有溢出来的油,因此汽车打滑撞到了别的车。第三部分比第一部分增加了一个客观原因:在十字路口,树枝挡住了一个停车标志(stop sign),因此John没看到这个停车标志因此和别的车相撞。第四部分比第一部分也增加了新的因素,即过十字路口时没有能够减速因此撞到了其他的车。第一个场景,John因为超速发生车祸,而他超速的原因是急着回家把他给父母的礼物在父母回家之前藏好,这样可以给父母一个惊喜。第二个场景,同样也是John因为超速发生车祸,但是超速的原因是赶着回家把可卡因在父母回来前藏好,免得被父母发现。然后,每个实验参加者需要填写问卷调查,问题是John多大程度上应该承担责任,以及多大程度上John的行为是发生事故的原因。从实验结果来看,当John回家是为了藏好可卡因时,有更多的人会认为John应该承认责任,而当John回家是为了藏好礼物的时候,认为John应该承担责任的人要少得多。[1]Mark Alicke,Culpable Caus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63,1992,pp.373—375.
(三)对心理偏差的一些弥补措施
既然考虑到这些心理偏差会影响陪审员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学者也会讨论如何消除或者减少偏差,其中,Peters提出的一些建议值得我们考虑[2]Philip Peters,Hindsight Bias and Tort Liability:Avoiding Premature Conclusions,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Vol.31,1999,pp.1300—1303.:
1.法院对陪审团的警告
一些法官已经认识到了这些心理偏差对陪审员的影响,因此他们会使用自己的权力,对陪审团进行一定的指导。但是,正如Kamin和Rachlinski在实验中显示的,仅仅靠法官对陪审员的指导并不能使陪审员去除后视偏差。[3]Kim Kamin and Jeffrey Rachlinski,Ex Post≠Ex Ante:Determining Liability in Hindsight,Law And Human Behavior,Vol.19,1995,p.99.
2.一致同意的判决
有些情况下,法律要求陪审团必须出具陪审员一致的意见,否则如果陪审团里面出现反对意见,陪审团的决定就无效。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员的决定会更加谨慎,陪审员会对证据等因素考虑得更加周全,也会努力克服各种心理偏差。
3.陪审团商议(jury deliberation)
陪审团的集体商议也能减少单独陪审员的心理偏差。通常在商议后,陪审员会更周全地考虑各种事实和证据。
4.责任与损害的分流
这种分流是指法院推迟向陪审员公布伤害情况的证据,而等陪审团先对责任问题作出判决后再公布此类证据。这样的设计可以减小原告伤害程度这一事实对陪审员的心理影响,因为按照后果偏差的原理,伤害的严重性会加剧陪审员的偏见。
四、与侵权损害赔偿有关的心理学实验
(一)损害赔偿额的决定因素
在本文开头,我们就提到了禀赋效应对法学的影响。当学者在研究陪审员决定损害赔偿额的影响因素时,发现禀赋心理也是其中一个。
McCaffery等人做了一个和赔偿额评估有关的实验。实验分为两组,在实验指引里,每一组都假设参与者是原告,需要决定侵权赔偿的合适数额。但是不同点就在于,后一组比前一组多了一个条件,即第二组的原告在受伤前,在某些场合被告曾经提过这种伤(即原告后来经历的伤)要赔偿多少钱。如果我们将第二组里被告曾经提出的对原告的伤赔偿多少钱当作一个参考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考察这个参考点对于损害赔偿额是否有影响。
从实验结果来看,当后一组拥有一个事故发生前的参考点时,所给出的平均赔偿额是第一组的两倍。其实用禀赋效应来解释的话,第二组所得到的被告提供的信息,可以认为是一个禀赋,从结果来看,第二组的赔偿数比第一组高,这也是和禀赋效应的观点相一致的。[1]Edward J.McCaffery et al,Framing the Jury:Cognitive Perspectives on Pain and Suffering Awards,Virginia Law Review,Vol.81,1995,p.1372.
此后,McCaffery等人做了一个关于黄金规则(golden rule)的调查。黄金规则是禁止律师向陪审员主张,在决定判决时想象陪审员处于原告的位置。按照禀赋效应,当陪审团想象自己处于原告位置时,对赔偿数额的评估肯定会产生影响,所以这个规则会禁止律师这样主张或者引导。
他们先是利用网络系统筛选了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和罗德岛的200多个做过人身伤害诉讼的律师(无论原告方或者被告方)。然后将问卷调查寄给他们,最后回收了95份填写完整的问卷。
其中有多数人(95人中的57人)表示,他们在司法实践中从来没有使用或者看到别人使用这种卖方价格视角(selling price perspective)。有一个原告的律师就写得很清楚:当原告律师仅仅在最后陈述(closing statement)建议一个赔偿数额时,会强迫陪审团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案子。[1]Edward J.McCaffery et al,Framing the Jury:Cognitive Perspectives on Pain and Suffering Awards,Virginia Law Review,Vol.81,1995,pp.1375—1383.
(二)惩罚性赔偿的决定因素
惩罚性赔偿一般是指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数额的赔偿。在当代,惩罚性赔偿主要在美国法中采用,兼具补偿、惩罚和遏制等功能。[2]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5期,第1页近些年,在一些惩罚性案件里,陪审团决定的赔偿额都很高,但是过高的惩罚性赔偿数额都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定,[3]比如 BMW of North America,Inc v.Gore,517 u.S.559(1996);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v.Campbell,538 u.S.408(2003)。因此这也让惩罚性赔偿一直备受学者关注。其中,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实验研究主要围绕惩罚性赔偿的决定因素展开。
对于陪审员作出惩罚性赔偿的影响因素,Robbennolt概括了三个,分别是案件因素、个人的心理因素和法律程序因素。[4]Jennifer Robbennolt,Determining Punitive Damages,Buffalo Law Review,Vol.50,2002,p.117.案件因素包括侵权伤害的严重性、被告的行为性质、被告的财富等,个人的心理因素包括人们对民事诉讼的感知、惩罚的直觉因素等,而案件程序的因素包括陪审团评议、法官对陪审团的指导等。本文主要介绍关于前两种因素的相关实验研究。这些实验涉及的话题可能不止惩罚性赔偿,因为补偿性赔偿(compensatory damage)和惩罚性赔偿常常同时出现,但是本文只讨论与惩罚性赔偿有关的内容。
1.案件因素对惩罚性赔偿的影响
Kahneman等人的实验研究的是人身伤害的性质和被告的财富与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关系。[5]Daniel Kahneman et al,Shared Outrage and Erratic Awards:The Psychology of Punitive Damages,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Vol.16,1998,pp.56—58.首先,Kahneman等人从一个县的选举登记中心找到了899名具有陪审员资格的公民来参加实验。在实验里,实验参加者会收到四个信封,从第一个到第三个信封都装着不同的情境说明,而第四个信封则是关于实验程序等情况的说明以及关于人口因素的问卷(比如了解教育等信息)。
在Kahneman的实验设计里,一共有10个场景,分别是:员工因为工作中接触苯而患了贫血症;因为刹车失灵导致摩托车司机受伤;被灌醉的保安用枪击中手臂;汽车的气囊无辜爆炸导致司机受伤;男子因为接受脱发治疗导致皮肤受损;一个老妇人因为使用运动视频而导致背部受伤;一个小孩玩火柴时不小心烧到了睡衣;儿童咽下大量过敏药品需要在医院治疗;轮椅升降故障导致残疾人受伤;最后一个是秘书因为电脑显示器的辐射而患上慢性病。然后,按照Kahneman的安排,前六个案例放在第一和第二个信封,其中第一个信封其实只有六个案例里面的一个,其他五个案例在第二个信封。后面四个案例放在第三个信封。另外,第一个封信和第二个封信的案例里,被告公司被区分为大公司和小公司,而在第三个信封里的案例则增加了伤害程度的区别。比如“一个小孩玩火柴时不小心烧到了睡衣”的案例,第三个封信增加了“他全身被严重烧伤”“他的手被严重烧伤”的区别。每个人都会读到全部10个案例,只不过可能读到案例的具体场景会有所差别。然后参加人员会填写一个问卷,问卷的问题主要是对案件的看法(接受、反对、震惊还是愤怒),对处罚的看法(不需要处罚、轻微处罚、严重处罚还是极端严重处罚)以及心目中的惩罚性赔偿的数额。
而实验表明,原告遭受的伤害程度和被告公司的规模与损害赔偿额有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即伤害程度越严重,被告公司规模越大,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也越大。
Robbennolt也做过一个类似的实验来测试原告的伤害程度与被告财富对于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影响,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在实验参加者里她对法官和陪审员进行了区分。研究的背景是,因为司法实践里陪审员决定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常常很高,有人主张让法官来代替陪审团决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因为法官一般更加理性。而Robbennolt希望通过这个实验来研究法官和陪审员在决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时是否有显著差异。
Robbennolt首先找了陪审员和法官来参加问卷调查。这些陪审员主要指的是找符合陪审团要求的公民来回答问卷。具体来说,在美国的一些州,基本是随机抽取公民电话然后打过去问是否愿意参加调查。在内布拉斯加州,主要是来自社区的公民,然后邮寄材料给他们让他们完成问卷。最后一部分是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生也参加了这个问卷调查。总共加起来有140名。而法官主要是通过邮寄材料让他们完成。他们主要从州和联邦基层法院的名单里随机抽取然后给他们把材料邮寄过去。一共邮寄两次,如果第一次法官没有回复,过段时间还会再邮寄一次,以提高回复率。
在具体内容上,Robbennolt的实验远较Kahneman的实验简单。在问卷的第一部分,Robbennolt设定了一个场景,即原告因为有抑郁症的症状而去某医生那里就诊。某医生有一个针对抑郁症的特殊的医疗方法,但是这个医疗方法有副作用。而原告接受这个治疗后,副作用也暴露出来,严重到送医院治疗。原告律师接受原告委托后开始调查,发现医生本来就应该知道潜在的副作用。关于医生的收入有两个版本,低的版本是1100万,高的版本是6亿多。参加者被告知医生的责任和原告因病产生的经济损失都已确定。然后,参加者要求判定伤害的程度、损害赔偿的数额以及可能有的惩罚性赔偿的数额。
问卷结果显示,首先,人身伤害的严重性对于参加者作出的惩罚性赔偿的决定及数额有显著影响,而被告的财富对于参加者是否作出惩罚性赔偿的决定及数额有微弱的影响。这个结果和Kahneman等人的实验结果基本一致。其次参加者的身份(是陪审员还是法官)对于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决定没有显著差异。[1]Jennifer Robbennolt,Punitive Damage Decision Making:the Decisions of Citizens and Trial Court Judges,Law and Human Behavior,Vol.26,2002,pp.322—324.也就是说,让法官替代陪审员来决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改革意义不大。
2.个人的心理因素对惩罚性赔偿的影响
关于个人的心理因素的影响,我们首先来看Greene等人的实验。他们的实验目的是考察陪审员对赔偿数额的看法是否会影响他们对惩罚性赔偿具体数额的决定。[2]Edith Greene,Jurors’Attitudes About Civil Litigation and the Size of Damage Awards,The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40,1991,pp.810—811.首先,实验组织者找来了西雅图的一个县城的213名有过陪审经验的公民来参加实验。这些陪审员首先都会阅读一个案情梗概,即一个侵权致死案件。然后全部陪审员被分为八组,每个组分到的具体案件会不一样。第一组的情况是产品责任案件,即因为汽车油门(踏板)的故障,一个30岁的男性因车祸而死。第二组的情况是因为过失,一个驾驶员没有及时停下车,因此撞死一个30岁的男性路人。第三组是医疗事故,医务人员给一个30岁的男人注射了一种能让他过敏而死的药物。接下来的四、五、六三组都是把一、二、三组的男性换成女性。第七组将第一组的30岁男性换成60岁男性,而第八组也是在第一组的案例上,对汽车的所有者作了少许变动。然后,陪审员被告知,原告已经证明了被告的责任,而陪审员的任务则是决定一个合适的赔偿数额。在陪审员填完数额后,他们被要求回答“我估计多少比例的原告会受到100万美元以上的赔偿金”。
实验结果表明,如果陪审员觉得几百万的赔偿额是很普通的数字,那么他们作出的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也会更高。也就是说,陪审员本人对赔偿额的态度会影响他们所作出的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决定。
而Robbennolt在另一篇文章里研究了惩罚性赔偿的封顶规定对人们作出的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影响。在美国,比如堪萨斯州就规定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上限,原因是在个别案件里,陪审团决定的惩罚性数额过高,因此有必要设定数额的上限。
在实验里,参加者首先阅读了一个简短的案情介绍,原告在车祸后接受输血但是不幸感染了艾滋病,于是他起诉提供血液的公司要求它为污染的血液负责,因为公司没有对这些血液进行病毒测试,导致他感染了艾滋病。然后参加者一共分为四组。他们被告知被告将承担责任,但是每组的成员所收到的关于赔偿额的指导意见是不同的。第一组是控制组,该小组没有惩罚性赔偿数额的上限,第二组的上限是10万美元,第三组的上限是50万美元,第四组的上限是100万美元。最后参加者要求回答人身损害赔偿的数额以及可能的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这其实也是测试人们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时,是否存在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锚定效应是指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数值作为起始值,起始值像锚一样制约着估测值。而在做决策的时候,人们会不自觉地给予最初获得的信息过多的重视。)
实验结果发现,惩罚性赔偿数额的上限对于实验参加者作出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存在显著影响。首先,在上限比较低的小组,他们确定的数额要明显低于那些在上限比较高的情况下确定的数额。其次,在与控制组比较时,情况又有所不同。上限最高的小组,他们确定的数额要明显高于那些在没有上限规定的情况下确定的数额。但是在上限最低的小组,他们确定的数额要明显低于那些在没有上限规定的情况下确定的数额。通过第一个结果可以认为,数额上限的规定会影响人们的决策,也就是,数额上限的降低会引导陪审团降低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但是通过第二个结果可以认为,如果确定的数额上限过低,以至于低于陪审员内心想要确定的数字,那么数额上限的作用可能就呈现一种反作用,即会增加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或者说,在这个时候,数额上限对于陪审团确定数额不会起约束作用,陪审员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决定。通过这个实验,Robbennolt有力地质疑了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封顶的规定。
五、结语
唐应茂在《法律实证研究的受众问题》[1]唐应茂:《法律实证研究的受众问题》,《法学》2013年第4期,第28页。中指出,法律定量研究者应当关注部门法研究的话题,关注部门法的动态和方向,把自己当作部门法研究中的一个成员,而不是把自己当作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学者进行法律实证研究。笔者深以为然。
本文主要介绍了美国学者在合同法和侵权法领域如何用实验方法来分析问题。在合同法领域,主要考察了禀赋效应对默示条款的影响和合同解除的影响因素,在侵权法领域主要介绍了后视偏差等心理因素对因果关系判断的影响以及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决定因素。笔者认为,虽然中国和美国的法律体系不同,无论是具体的部门法还是诉讼程序,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如中国就缺少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但是美国的这类研究依然有借鉴意义。第一,日光底下无新事,尽管具体制度不同,但是合同法和侵权法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相似的,比如我们的侵权法同样有因果关系和惩罚性赔偿的内容。第二,尽管法学的实验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陪审团制度发展起来的,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涉及法官。如果我们能在理解心理学与法的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对法官进行一些类似的研究,那么对于丰富民法研究也是很好的选择。
比如在惩罚性赔偿中,有学者提出影响惩罚性赔偿数额最大的三个因素是受害人的主观过错、补偿性赔偿数额和企业支付能力,并提出了法官确定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公式。[1]蔡尔津、叶涛:《论侵权责任法中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福建法学》2011年第4期,第52页。笔者认为,对于影响赔偿数额的因素,我们也可以参照美国的研究加以验证。第一,可以更加了解国内法官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机理。第二,如果中国和美国的结论有不一致的地方,挖掘背后可能的文化原因应该会很有意思。又比如,有学者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提出了“上不封顶、下要保底”的建议,希望扭转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征求意见稿》设置上限的规定,有助于提升商家的失信成本和消费者的维权收益。[2]徐海燕:《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西部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第13页。那么,对于是否要对数额封顶,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实验来测试封顶抑或不封顶对于法官判决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影响,以此来为立法提供参考。
(初审:丁建峰)
[1] 作者柯振兴,男,美国伊利诺伊香槟分校法学硕士生(LLM)、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社会学硕士(辅修统计)、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硕士,研究领域为劳动法以及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代表作有《浅谈定量研究方法在公司法研究中的应用》《美国集体合同简介》《与工会利益密切相关的美国不当劳动行为》等,E-mail:chch36@163.com。
——黄咏梅小说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