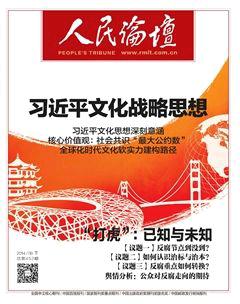电影《蓝色》对“荒诞”的认知与对“自由”的实现
张冲
电影《蓝色》对“荒诞”的认知与对“自由”的实现
张冲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被称为“深紫色的叙事思想家”、“电影诗人”,但他自认为是“朴素的、地方性的”导演。一个导演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个人视野内所关注的事物与独特的角度,在《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中,他说:“生命里很多事都是由当你还是个孩子时在早餐桌上打你手背的那个人决定的,指的就是你父亲、你祖母、你曾祖父、你的家庭背景,那是很重要的。那个在你四岁时因为调皮而打你手背的人,往后几年会在你床前或是圣诞节送礼物的时候,给你第一本书,那些书将塑造你的人格——至少,我的人格就是那么开始形成的。它们教了我一些事,让我对某些事情特别敏感。那些我曾经读过的书,尤其是我在孩提时代读过的书,使我变成了今天的我。”孩提时代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体质虚弱,常常躺在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从那时他便开始阅读加缪、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了。他瘦弱的父亲由于身体缘故要在不同的疗养院之间游走,全家四处搬迁,幼小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敏感、忧郁而又细腻。他日后的电影创作中无论是对意识形态与人的尊严的关注,还是对形而上学的思考,都具有孩提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特征。
基耶斯洛夫斯基曾经说过他宁可看书也不去电影院,生活和文学是他创作的重要灵感,在回答什么人对他影响较大这个问题时,他说出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卡夫卡和加缪四人的名字。加缪作为存在主义哲学思想重镇,他所关注的某些问题对基耶斯洛夫斯基影响颇深,从电影《蓝色》可以略窥豹斑。《蓝色》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色系列之一,三色象征自由、平等、博爱,分别由蓝色、白色和红色代表。基耶斯洛夫斯基说《蓝色》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个人自由的领域,我们离感情能有多远?爱是囚牢还是自由?”在涉及到电影讲述方法时,他说:“有某种知觉或感觉的人,一些有魅力的人。这不一定非通过对比来表现。”他还说在他的电影中“通常是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在幕后,你看不见它。它可能体现在演员的表演中,也可能不在其中;你可能感觉得到,也可能感觉不到。”这些看不见的幕后事情,是指存在于世俗生活现象下的神秘主义、荒诞、自由等。在《蓝色》中诸多元素交织缠绕在一起,基耶斯洛夫斯基运用修辞手段突出神秘、荒诞,以及蓝色“自由”的存在,展示女主人公向“自由”过渡的进程。
通过几种修辞格对“自由”的演绎
修辞学是许多西方导演早年间习得的课程之一,诗歌创作也是一些导演所经历过的事实。基耶斯洛夫斯基进入由当时的先锋艺术家创立的洛兹电影学校前在一家剧院工作,其间进行诗歌创作,这对他日后的电影导演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曾说在他的影片中他“并不直接表述他所要表述的事物,而是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来实现它,……事情很少是直接说出来的”。他在电影中的表述手法与诗歌的表述手法不谋而合,在他所运用的修辞格中,有隐喻、象征、对比、排比、反复等,其中运用得较多的是排比、反复、隐喻与象征。在修辞中,排比具有展示与强调的作用。“三”在电影中是一个比较有用的数字,具有排比或反复的修辞效果。一个人物或道具在第一次出现完成“展示”的作用,第二次出现凸显“强调”,第三次出现时有目的的内容要被陈述,意味着故事的突转或作者的结论即将出现。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中,这种修辞手法随处可见,人物与动作的作用一次比一次更加突出,目的更强烈,对情节以及情节的定位推波助澜,逐渐达到激励事件的顶点。《蓝色》中多个次要人物与道具比较规范地出场(或潜出场)三次,有吹短笛的男人、朱莉母亲、青年安东尼、性表演者露西娅、丈夫的情人、女儿的蓝灯、十字架、床垫等。在每一次“三”中按照展示、强调与结论的顺序完成预设的任务,即主要人物由“不自由”向“自由”的过渡。
吹短笛的男人在影片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导演也将存在主义命题的论述放置到了此角色上。吹短笛的男人第一次出现时是出现在朱莉的关注中,没有台词,只是展示了他的存在,朱莉安静地看着他,这个男人身上曾停留过丈夫的目光,作曲家丈夫也曾经从这个来自民间的流浪艺人身上汲取过灵感,此刻的朱莉虽然拒绝回忆,但她的潜意识却战胜了她的意志,她来到了和丈夫常常光顾的咖啡馆。这一组镜头呈现的不多,但幕后的所指颇多:1、朱莉的拒绝回忆无法真正实现;2、高雅艺术来源于民间艺术;3、人的潜意识无法抗拒等。吹短笛的男人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朱莉发现他病了上前探寻:“生病了?你还好吧?”吹短笛的男人躺在那里露出了羞涩的笑容,并拢了拢自己装短笛的盒子,同时说道:“人总得留着些东西。”这些给了朱莉一定的启示,人不能拒绝所有,势必要留有东西,记忆也好,选择也好,人无法逃避时间留下的痕迹。此时的朱莉正在以逃避与拒绝的方式进行选择,拒绝回忆、拒绝以前、拒绝工作、拒绝肉体上的爱、拒绝宗教的救赎等等。伴随着导演对朱莉承受能力的砝码的加重,朱莉第三次看见了吹短笛的男人,他被好心人从医院送了回来,他的短笛还在,朱莉走上前去问他:“为什么知道这曲子?”吹短笛的人回答:“我创作各种音乐,我喜欢演奏。”这就是他的选择,他的选择证实了他存在的意义,他自为的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向人普遍的自在存在接近,朱莉受到了莫大的启发。在选择过程中,物质上似乎不富有的吹短笛的人实现了自己的自由。朱莉获得启示后决定开始面对残酷而荒谬的世界,并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开始工作,开始创作音乐,向自由、幸福靠近。
《蓝色》从存在的角度讨论了血缘关系。住在疗养院里的母亲作为唯一与朱莉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出现了三次,母亲的三次出场昭示了朱莉从“不自由”向“自由”过渡的进程。母亲第一次潜出场在飞利浦的可视电话中,她参加朱莉丈夫与女儿的葬礼。第二次出场是朱莉有了难题,当朱莉发现了储物间内的母老鼠与一窝小老鼠时,这个荒诞的世界不断地给刚刚失去丈夫、女儿的她增加痛苦的、荒诞的砝码,面对荒诞和痛苦,她是拒绝逃避还是直接面对,导演在完成朱莉这个“西西弗斯”式的英雄的时候,他要朱莉自己选择。影片发展到这个阶段时,不同以前,朱莉面对这窝老鼠,没有像之前那样选择逃避与拒绝,而是选择了到疗养院去寻找母亲、寻求帮助,走出了她之前隔绝的自闭状态,主动地去寻求帮助。可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似是而非的话语让朱莉只能自己选择自己面对——她借邻居的猫来处理那窝老鼠。
在疗养院与母亲对话的这场戏,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场戏,基耶斯洛夫斯基将很多问题展示出来:其一,朱莉身份与伦理的血缘关系问题。朱莉的母亲无法辨认朱莉的身份,朱莉一会儿是她的妹妹、一会儿是她的女儿,身份的混淆,使得她的判断也具有歧义,使得语义产生了多元效果。
母亲:玛莉·凡丝。
朱莉:是我,朱莉。
母亲:啊,朱莉,进来。
母亲:他们告诉我你死了,气色很好,很年轻,总是那么年轻,都三十岁了,小的时候……
朱莉:母亲,我是你女儿,不是你妹妹,我今年三十三岁。
母亲:我知道,我知道,开玩笑的。
朱莉母亲第三次出现是在朱莉与她丈夫已经怀孕的情人见面后,离开那个也还优秀的女人后,朱莉内心汹涌,决定找在疗养院的母亲倾诉,她在窗外俯视着房间里看电视的母亲,这个时候电视画面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高空的钢丝上,象征朱莉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人人都是在人生中独自走钢丝,也意识到了自己存在的荒诞,只能勇敢地独自承担与面对。她离开了,没有进到房间里去向母亲倾诉或求救。此时,她正逐渐向“自由”靠近,她对乐感的控制也随着对自我认知与自由的逐渐显现变得自如。当她无法摆脱“爱”的桎梏、没有意识荒诞的时候,乐感是她想拒绝又无法拒绝掉的潜意识,即使是在游泳池的水中也一样,而当她逐渐变得自由的时候,乐感的出现与否在于她是否自由,这样朱莉在实现自由的过程中,正在以自己的勇敢体会着自由的幸福。
电影中的道具作为诗歌中的“意象”被运用,也充满了隐喻与象征的作用。道具之一是朱莉女儿房间里蓝色的灯,这是女儿留下的唯一的东西,女儿的灯第一次出现的作用要表现朱莉“为了重新获得选择生活的自由,主宰自己的命运和情感,不再被痛苦所支配,朱莉决然地抛弃了与派特里斯有关的一切,她抹去过去的生活痕迹,斩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沈云《<蓝色>漫谈》,《电影评介》1997年第1期,第32页)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要强调朱莉根本无法完全逃避或拒绝这个残酷、荒诞的世界。她“一进新居,第一件事就是将灯饰挂起来。这个细节细腻地流露了朱莉的深层心理,灯饰是昔日生活的浓缩,表达了朱莉对昔日生活的依恋和不舍,是朱莉的情感对她的意志的背叛,她依然是情感的奴隶”(同上)。这个时候她还处于不自由的状态,无法体会自由的幸福。灯第三次出现的时候是脱衣舞女露西娅前来感谢朱莉时提到的,脱衣舞女小时候恰恰也有过同样的灯,冥冥之中将生活本身的神秘主义描绘了出来,这盏灯上延续着贞洁、肉欲正反同体的非理性世界。
影片中的另一道具是床垫。朱莉家中的所有东西都被园丁处理掉了,除了女儿房间里蓝色的灯和自己与丈夫用过的床垫。床垫是欲望与身体的象征,在这张床垫上,朱莉试图用身体的接触来解救自己,和奥利维一夜情之后,内心之痛依旧无法排解。后来这张床垫被奥利维买走,朱莉最后也是在这张象征情与爱的床垫上与奥利维开始了新的爱之旅。床垫作为爱与欲望的道具同样也被使用了三次。
道具之三是丈夫与情人的照片。奥利维整理朱莉丈夫遗物时,其中包括朱莉丈夫与情人的照片,这些照片此时第一次“潜出场”;当奥利维准备送还朱莉这些遗物的时候,恰逢朱莉备受煎熬的逃避与拒绝时期,朱莉拒绝了这些东西,使得遗物中的这些照片在将来的叙事中继续发挥功能;当奥利维把它们展示给电视媒体的时候,击碎了朱莉爱的迷梦。照片三次的出现使我们看到在真相与假象中,朱莉逐渐认清了这是一个荒诞的世界,自己所执著的一切不堪一击,于是她决心自己不再逃避,以自己的肩膀来承担这一切。朱莉的从“不自由”到“自由”的变化也伴随着次要人物的不断出现与道具的不停展示而得以呈现,在这一次又一次的遭遇中她逐渐认清事实,勇敢地面对这个荒诞的事实,从而体察自己存在的尊严、幸福与自由。
朱莉从“不自由”状态到“自由”的转变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谈到《蓝色》时这样诠释:“朱莉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她没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干掉,追随她的家人到另外一个世界;或许她觉得不该这么做——我们永远不知道她的理由——她尝试过另外一种生活。她试图把自己从与过去有关的一切事情中解放出来。……她下决心把它抹去,过去即使重现也只是在音乐中。看起来一个人是不可能完全从过去所有的事情中解放出来的。你做不到,因为某些时候你还是会感到害怕或孤独的,就像朱莉有时体验到的受骗的感觉一样。这种感觉让朱莉改变了那么多,她终于认识到无法按照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就是个人自由的领域。我们离感情能有多远?爱是囚牢还是自由?”这个爱是否“荒诞”?开始之时,朱莉讲“回忆、朋友、爱,这些全是骗人的”,当她用拒绝的方式对待这些,不要回忆,躲避朋友,不要爱等等,她发现她所执著的“爱”本身就具有某种不忠贞的欺骗性以后,她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所具有的荒诞性,爱人的“爱”与亲人的“爱”对她来说,是一种自为的存在,但当她执著的时候,这个“爱”就变成了牢笼,她成了不自由的爱的奴隶。面对荒诞,朱莉以各种方式进行选择,寻找自由。从被动、逃离、拒绝到不得不面对,朱莉意识到只有你迎头赶上去,自由才显现了出来,朱莉像局外人一样打量着、质疑着这个充满所谓主流认同的荒诞世界,作为反叛者,她追求自己的独立存在,也尊重别人的选择与存在方式。
在《蓝色》开始的时候朱莉选择逃避与拒绝,处于被动与不自由的状态,她拒绝活着选择自杀,拒绝奥利维的关怀,拒绝采访,让园丁处理掉家里所有的东西,拒绝回忆,拒绝为爱哭泣,拒绝身体的救赎,拒绝自己的专业与工作,拒绝丈夫的姓名……却来到了和丈夫常常光顾的咖啡馆,这是一个突转点,她意志上进行拒绝,行为却顺从过去的习惯,形成一个悖论,恰如台词所述“人总得给自己留点什么”、“人不能拒绝一切”。在这种情况下,她选择听吹短笛的男人演奏曾经和丈夫共同听过的曲目,情感的非理性战胜了意志的理性。
在新居公寓的第一晚,朱莉拒绝帮助那个被别人追杀的男青年,导致了那个男青年被对方抓走。在她再次遇到同样情况的时候,她选择帮助别人,假以尊重别人的选择、不加干预为借口,由于她拒绝在联合签名上签名,潜意识中帮了露西娅以弥补之前的负疚。签名一事也体现了基耶斯洛夫斯基长久以来关注的民主问题与道德焦虑。同样,她也拒绝收回安东尼送还的十字架,象征着拒绝宗教的救赎以及对过去的爱的回忆。当一窝老鼠出现在房间里的时候,引起了她巨大的厌恶与恐惧,她依旧选择逃避与拒绝,试图寻找新的居所。由于房屋的短缺,加重了对她考验的砝码,在中介公司,她第一次把视野主动投向别人,关心询问中介人脸上的创可贴:“这儿怎么了?”之前的冷漠与决绝开始解冻。随后主动向母亲求救,在求救失败后自己解决厌恶与恐惧的问题,借猫杀鼠,开始独自处理与荒诞世界的对峙与挑战。
狂奔过后,她把自己投入到游泳池里,感情迸发出来,似乎有泪水出现,露西娅问:“你哭了?”她回答:“不,是水。”随后考验的砝码更加重了,无数个小孩子欢呼雀跃着跳进了游泳池,世界的荒谬色彩也更加浓重,她窥视着这些新鲜的生命,面对池壁慢慢俯下身去,思考痛苦与残酷的人生。当天深夜时分露西娅打来电话寻求帮助,朱莉先是拒绝,最后应允去红灯区夜总会帮助露西娅,这是她走出与世隔绝的自我封闭世界,也逐渐在置换选择自由的方法,不再与世隔绝地生活在自我之中。
在夜总会这场戏里,基耶斯洛夫斯基对不同人对自由的选择进行了展示。朱莉问露西娅:“你为什么干这行?”露西娅回答说:“我喜欢,我以为人人都喜欢。”色情表演是一种感官刺激与欲望追求,在露西娅看来,这种感官和欲望上的享受是最自由的选择,但是却存在诸多问题与悖论,她曾经说过:“我就不能一夜没人陪。”孤独是荒诞世界的一种特征,在这世界中,如果无法面对孤独,就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当露西娅的父亲观看色情表演时,露西娅遇到了来自道德与自由的冲突,她无法独自一人解决这个冲突。同露西娅相反,形成鲜明的对比,朱莉试图独自一人承受荒诞的事实。在夜总会,朱莉通过电视媒体得知挚爱的丈夫有一个情人,她主动寻找丈夫的情人,勇敢面对这一事实时,她几乎实现了自己的自由,开始主动同奥利维谈论音乐创作,在对自由有了越来越清晰的意识时,朱莉选择面对荒诞。最后她以宽容和慷慨解决丈夫情人的问题,将丈夫的房子与姓氏赠给丈夫与情人的孩子,并完全投入到作曲的工作中去,在象征情爱的旧床垫上与奥利维开始了新的爱情,实现了自我的绝对自由。
日常生活中的神秘主义所具有的二元对立与偶然性
基耶斯洛夫斯基关注个体的精神世界,倾向于呈现人类的普遍存在状态,包括外在的与内在的存在状态。他称华沙戏剧技术学院是他“上过的最好的学校,……老师很好,而且很智慧,……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种价值观跟我们日常生活中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如何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如何使我们的生活更加舒适、拥有财产、赚钱、谋个好职位等价值观毫无关系。他们向我们展示在那个所谓的更高的世界里,你可以充分体现你自己。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更高,但它确实不同”。基耶斯洛夫斯基所说的更高的世界是指人类的精神世界,它独立于物质的、现象的世界,自在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其神秘性充满了二元对立的悖论与偶然性。
影片中非常吊诡的是,朱莉第一天搬到新公寓的晚上,楼下一个男人被打,当朱莉看到他很危险的时候,过来一辆卡车,被打男人得以逃脱。当逃到楼上敲门求救的时候,朱莉在恐惧与犹豫中,被打男人又被抓了回去,朱莉出来探看,结果那个男人已经被抓走了。当朱莉准备回房间时,却被反锁在外面,引发了后面一系列情节的发生,包括她潜意识中对露西娅的帮助。朱莉这次没有救助那个被打的小伙子,导致那个小伙子再次被一群人抓到。下一次选择的时候,朱莉作为这个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局外人,拒绝了邻居要求的联合签名,邻居们要驱逐性表演者露西娅,朱莉说:“那是她的选择,和我没有关系。”性表演者露西娅由于非全体居民签名而得以留在原来的公寓继续居住,她带着一束象征贞洁的雏菊来答谢朱莉。性表演者/贞洁的雏菊昭示了一个正反同体的世俗世界的表征,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它荒诞而充满了迷人的悖论。紧接着,露西娅发现了朱莉女儿的灯,小时候露西娅也有一只与女儿安娜同样的灯,在这盏灯上面留有了露西娅的目光,某种意义上是女儿安娜的意义延伸,纯洁的女儿与充满肉欲的露西娅联系到了一起,已逝去的和存活的人物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地方,又一个世俗世界的表征,生命中充满了神秘不可知的事物。
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二元悖论现象在《蓝色》中得以呈现。性感的露西娅从夜总会下班回来,打开自家房门前,她挠了挠邻居的门,邻居男人过来与她偷情,后来两个人一同探出脑袋窥视被反锁在外的朱莉,这是非常典型的日常生活写照。当朱莉从邻居处借猫时,这个已婚男人也试图勾引她,他借猫讽喻朱莉的不解风情。不管是露西娅的情欲,还是这个已婚男人的勾引,以及露西娅爸爸在疲惫之下也对色情表演充满好奇,俗世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它不是按照理性、秩序和权威被制造出来的,而是活生生地就在那儿以理性也好或者非理性的姿态存在着。如果以一方的理性来约束和制约,荒诞势必产生,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产生了权威或者极权,判断孰是孰非,显得那么荒诞。露西娅的父亲来到性表演场所观看表演,恰好露西娅提前看到,露西娅震惊了,而她马上要开始表演,这一次她主动求救于朱莉,这一切让露西娅的价值观有所动摇,朱莉问她为何选择这行,她回答说:“我喜欢这个,我认为人人都喜欢。”但是当父亲出现在这里时,声色场所里引发了欲望与伦理道德的悖论。日常秩序中,人人压抑色欲,露西娅喜欢选择、拥有这种欲望,可伦理上的父亲出现在了她要表演的场地的时候,她没有选择必须表演,父亲将要观看自己的性表演,这对露西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对她的选择进行了强烈的质疑。既然人的存在是依靠自己的自由选择来得以证实,那么她选择色情表演职业,是否是绝对的幸福?当伦理秩序对之进行冲击时,露西娅无法感知幸福和自由,只能在痛苦和彷徨中迷失。
影片中,“爱”的二元悖论在十字架这个道具下也有所演绎,十字架往往象征着宗教救赎与代表忠贞的爱情。青年安东尼打算将十字架归还给朱莉,它是朱莉丈夫送给她的礼物,安东尼在车祸现场拾到,朱莉拒绝了这个象征宗教与代表爱情、回忆的物品。十字架第三次出现的时候,略显得荒诞,它出现在了丈夫情人的脖子上。
丈夫的情人问:“想知道他是否爱我?”
朱莉的指尖轻抚那个女人脖子上的十字架,回答:“正是原本想问的问题,但不需要了,他是爱你的。”
十字架道具使得“爱情”这个概念变得二元对立起来,丈夫送给妻子朱莉的爱情信物是为了呈现爱情的忠贞与唯一性,但朱莉看到丈夫情人的脖子上的十字架,爱情的唯一性与纯粹性遭到了质疑,丈夫爱自己这是毋庸置疑的,两个人琴瑟相合,但丈夫也爱这个和他的感性的音乐专业相差十万八千里的理性的法律专业出身的女子,两个女人他都爱,这个事实是存在的。这一存在事实颠覆了理性、道德所确立起来的权威观念——爱情的忠贞性与唯一性,非常荒诞。朱莉感觉到了它的荒诞,也意识到了这一事实的荒诞和悖论,她感到了幸福和解放。在认清了荒诞的本质之后,在选择中,她以宽容与慷慨的姿态将夫姓与房子赠与丈夫情人的孩子。朱莉与奥利维开始了新的爱,她的这次选择为自由的选择,带着自己的尊严加入到这个荒诞世界中来,然后体会自己独立于这个充满主流意识形态的荒诞世界,以自己的选择向绝对精神王国靠近,带着并不仅仅是悲伤的泪水同过去告别。
世俗生活中充满了狂欢的意味,与狂欢有关的是被理性和秩序压抑的事物,比如排泄物。影片在讲述有关排泄物的笑话时,笑声是丈夫派特里斯留给朱莉的最后的声音,丈夫在笑声和调侃声中离开了这个荒诞的世界,但在笑的时候,汽车撞倒了树上。在悲剧与喜剧、生与死、祸与福之间谁是谁的转换体,这并不清晰,二元对立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其间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充满了神秘让人无法感知。
《蓝色》也在荒诞、悖论与偶然性中讨论真实与真相的问题。影片戏剧谢幕式的片尾里,所有的次要人物几乎都出场了。朱莉的妈妈作为伦理血缘关系关注对象,尤为受到关注。朱莉妈妈呈现了三个影像,第一个是焦点略虚的朱莉妈妈的影像出现,随着镜头移动,第二个朱莉妈妈的影像再次出现,我们会以为刚才那个是玻璃中的倒影,这个才是朱莉妈妈本人,可是随着下一个朱莉妈妈影像的出现,它打破了对第二个影像的真实幻想,第二个影像依然是镜像。那么第三个影像是否是朱莉妈妈所指,因为没有第四个影像或者参照物出现而无法得知。朱莉妈妈的三个影像按照顺序映射排列出来,让人无法判断真实与假象,充满神秘。在这里,基耶斯洛夫斯基利用拉康的镜像理论“对什么是真相”的讨论又进行了一次神秘主义之旅,充满歧义与趣味。
在焦点的虚与实中,让观众思考真相、假象的区别,体味着神秘主义中难以被体察的二元对立与偶然性,朱莉母亲最后头一垂意味着死亡,而即将出生的胎儿在B超中象征着出生,死亡、出生之间的转换象征了世俗生活生生不息、不停繁衍的狂欢精神。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充满了神秘的二元悖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二元对立的主题,如:幸运与不幸、爱情与不忠贞、自由与不自由、堕落与纯洁、正与反、非理性存在和所建构的理性秩序等等,基于荒诞的现状,相反相成存在着。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和魅力之所在,到处都隐含着矛盾,体现了复杂的深刻。由于神秘主义、二元对立和偶然性这样一些元素,使得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誉为“当代欧洲最具独创性、最有才华和最无所顾忌的”电影大师。
张冲,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1977年以来中国喜剧电影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