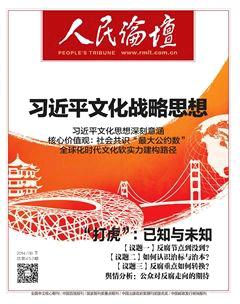大瀛海大自在
陈世旭
大瀛海大自在
陈世旭
一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海南儋州,第一次寻访苏东坡在这里的遗踪。
儋州古名“儋耳”。《汉书》说:“儋耳者,大耳种也。”《山海经·海内南经》注:“锼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儋县志》干脆说:“其人耳长及肩。”这当然是一种夸张。“耳”不过是一个语气助词而已。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海南岛置珠崖、儋耳两郡。这是海南岛上最早同时出现的行政建制。以后的朝代有昌化军、南宁军的变更,到明清仍沿用儋州。古儋州州城所在地中和镇有史一千三百多年。
公元1097年(绍圣四年)七月以后,曾先后担任过翰林学士知制诰、当时摄政的皇太后的秘书以及兵部和礼部尚书的苏东坡,被一步步赶下权力的高峰,最后孤身携着幼子苏过被流放到海南儋县。一直到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获赦北归。
因为没有车道,我在很远的地方就下了车,步行往中和镇。
望不到尽头的白沙地;望不到尽头的桉树、木麻黄、相思树林;望不到尽头的高高低低的土丘,仿佛这条漫长而蜿蜒的黄土路永远也走不到尽头。走了很久,才偶尔看见一个被刺竹和凤尾竹搂抱着的村庄的篱墙。偶尔碰见一个从甘蔗林后面婷婷地走出来的、戴着竹笠或裹着花头巾、上衣紧窄而鲜艳、裤腿又宽又大、挑着水罐或背着柴禾的女人。偶尔听见一阵拖着沉重的木轮车的牛脖子上寂寞的铜铃声。远远的天底下的山坡上,飘着烧荒的青烟。看起来,就像雾里的炊烟一样微弱而淡漠。
更远些的时候,这里的人类的痕迹,肯定比我现在看到的要少得多。史上的海南岛在很长一个时期一直是一个荒岛,相去京城几千里。当时的中原人把这里叫作“蛮荒之地”;把这迢迢路途的尽头看作天之涯,海之角;帝王们则把那些“不合朕意”、又颇固执的人流放到这里来“自省”。
所谓流放,就是将罪犯放逐到边远地区,是肉刑和死刑之外的一种辅刑。
流放文化,大概是以五千年文化沉积自豪的中国文化中人们最不愿意提起的另类文化。
人类在以智慧繁衍自身的同时,也在以智慧折磨自身。千百年来,当权者一直都在穷极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明各种刑罚,来惩处那些违背自己统治意愿的人。
中国最早的流放者据说是尧的儿子丹朱。他出生的时候,全身皆红。红即太阳。正值洪水经年不治,人们渴望大晴天,因名丹朱。但成年以后的丹朱似乎不堪造就,尧后来选择了舜继帝位。为防丹朱作乱,舜把丹朱流放到了鄂西北的房县。那里远离当时的王国政治中心,山林四塞,地势险峻,高湿高温,为“瘴痍之地”。而后又再向南迁徙至二郎岗。清同治版《房县志》记载:“二郎岗,山麓有丹朱冢。”
当权者自己说流放是一种仁慈的刑罚。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大清律例》)。又要表现“仁政”和“慎刑”,又要使流放成为仅次于死刑的重刑,他们创造了丰富的流放形式。对流放地的选择也煞费苦心。西北绝域、西南烟瘴和东北苦寒之地以及一些海岛都先后成为过流放地,形成了历代不同的流放标准,造就了诸多著名的流放者聚居处。其中,有“天涯”之名的海南岛与新疆伊犁当属两个最遥远的地方。
史有记载的第一位到海南的贬官是唐贞观年间的王义芳(615—669),最高的官位是御史台侍御史,最多六七品吧,却是位饱学之士;之后的著名者有唐德宗时当过宰相的杨炎;之后是晚唐时的两位宰相:一为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皆曾是其门徒,被唐宪宗发配到崖州(今琼山县)。一为唐武宗时代的李德裕。唯一一个例外是曾官至户部侍郎、尚书的吴贤秀。他是因为到了致仕之年,唐顺宗特赐铜牌迁居琼山县都化村。至宋代,根据“刑不上大夫”的原则,贬谪官员成为惩罚官吏的一项长期坚持的主要制度。宋代第一位被贬来海南的是宋太祖时的宰相卢多逊,其人因触犯龙颜而被全家发配至崖州古城(今三亚)水南村;另一位是宋仁宗朝的宰相丁谓,以图谋不轨等罪被贬至崖州;之后便是一生数被流放,最后一次贬谪到海南儋州的苏东坡。南宋,有四位抗金主战大臣相继被贬海南:1129年李纲被贬海南,不过六天后就被赦北返;两年后,李光来此,流放时间长达十七年,是五公中居琼时间最长者,后被召返江洲;赵鼎,因力荐岳飞被贬至吉阳军(今三亚崖城),后绝食而死;胡铨,曾作《哭赵鼎》:“以身去国故求死,抗议犯颜今独难”,因上书请斩秦桧而与赵鼎同时被贬至吉阳军。海南后人将此四人与唐李德裕合称“五公”,立“五公祠”祀之。
在海南的流放者中甚至有皇亲国戚。元亲王图贴睦尔卷入宫廷斗争被贬至海南时年方十七岁。一度心灰意冷,修建佛塔寺庙,吃斋念佛,却被元帅陈谦府上一侍女青梅吸引,托人求亲。不料被谢绝,只能羞愧自嘲“自笑当年志气豪,手攀银杏弄金桃,溟南地僻无佳果,问着青梅价也高”。数年后回到元大都并最终成为元文帝。
二
贬官们多为名臣良将巨儒,他们又多诗咏海南风物以抒心中郁结,以至贬官文学成为海南古代文学的一大特色。其中名篇有杨炎在建中二年(781年)被贬崖州司户道中所作《流崖州至鬼门关作》: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鬼门关”在北流、玉林两市间。两峰对峙,其间阔仅三十步,因号鬼门关。谚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古为通钦、廉、雷、琼和交趾的要冲,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经此勒石,残碑尚存。瘴疠尤多,去者罕有生还。唐宋诗人迁谪蛮荒,经此而死者迭相踵接。
杨炎(727—781),唐代政治家,理财家。历任吏部侍郎、道州司马、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等职。建中二年(781)罢相。德宗特加宽宥,贬为崖州司马。流放途经鬼门关,他已预感前景不妙,写了那首诗。离崖州尚有百里,接到德宗赐死诏书。终年五十五岁。
比杨炎稍晚的唐代名相李德裕(787—849)在流放途中写了《贬崖州司户道中作》: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
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
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
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
到达崖州贬所后他又写了《登崖州城作》: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李德裕幼年苦心力学,尤精《汉书》、《左氏春秋》。穆宗即位之初,禁中书诏典册,多出其手。历任翰林学士、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左仆射,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和武宗开成五年(840年)两度为相。在武宗一朝执政六年,外攘回纥,内平泽潞,一转唐王朝积弱不振的局面。宣宗李忱继位,成为“牛李党争”以及宣宗所嫉的打击对象。初贬荆南,次贬潮州,大中二年(848)再贬崖州(今海南省琼山)司户,次年正月抵达,十二月卒于贬所,终年六十三岁。与他同时代的李商隐称他为“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近代梁启超把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之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
五十二岁就死在崖州水南村的卢多逊居崖州期间写有《水南村为黎伯淳题》诗,久为传诵:
珠崖风景水南村,
山下人家林下门。
鹦鹉巢时椰结子,
鹧鸪啼处生竹孙。
鱼盐家给无墟市,
禾黍年登有酒樽。
远客杖藜来往熟,
却疑身世在桃源。
……
卢多逊死后一百一十二年走上贬谪海南之路的苏东坡,更是把海南当作了展示冠盖群伦的天才的舞台。三年流放的日子,一天也没有浪费作为大学者、大诗人的光阴,写下诗词一百四十多首,散文(包括赋、颂、杂记等)一百多篇,书信四十多封;在儿子的协助下收集各种杂记,编成《志林集》;撰写了学术论著《书传》;对《易经》和《论语说》两部学术论著进行了修订,最后完成《五经》的注释。此外,他在这里见识了明月鸟和狗仔花,衷心叹服他在政治上的对头王安石学识的渊博。他严格教导和训练儿子苏过,使之成为出色的诗人和画家。
与前人明显不同的是,我们在苏东坡留下的有关海南的诗文中,难得看到经历同样厄难的落寞惆怅,而更多的是旷达乐观。
这位乐天的、嗜酒的、洒脱俊逸的大文豪、大书法家、大画家、大政治家,一个年逾六旬的老人,在“垂老投荒”的途中写了一首诗给弟弟苏辙,最后两句是:“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作好了“生还无期”的充分心理准备。给朋友王敏仲写信:“某垂老投荒,无复生之望,贻与长子迈决,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视死如归。
九百多年后的那个傍晚,我来到儋县中和镇外这个靠近黎族村庄的院落。即将在苍茫的海那边沉落下去的夕阳,斜照着这片黑灰色的断垣残壁。嘉靖年间来此凭吊的一位诗人所说的“松林山下万松冈”上的“万松”早已荡然无存。只有疏疏落落的几株椰子树,歪歪斜斜地、却显然是不甘心地指天而立;“岁晚空留载酒堂”的载酒堂则穿墙漏壁,堂内遍地杂草瓦砾,残缺不全的石碑狼藉不堪地横陈其间;堂侧“东坡井”,井壁皴裂,水生绿苔。堂后即所谓“东坡书院”,鞍形回廊拱围着小院,甬道两边各有一棵凤凰树。树冠的巨大显示出茂盛期的雍容华贵,枝叶的凋敝则流露出劫后余生的无限怅惘;书院正厅门头的匾上赫然写着“海外奇踪”。匾已被岁月的风尘剥蚀得陈旧残破,但字迹依然醒目,幽怨而又倔强地想要申诉什么。
苏东坡与这座院落的残骸所显示出来的规模和阔气自然毫无关系。当时的海南,潮湿蒸郁,蛇蝎横行,人烟稀少。这是一段相当艰难的日子。他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形: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
……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百余岁者,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甚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也。
有一天苏东坡突然发现自己床上的帷帐已经腐烂,爬满了白蚁,他一面感叹“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一面又“习而安之”,努力让自己的心境平静下来。
物质生命的苏东坡,其健康在海南受到极大损害。《山谷诗集注》说:“东坡自岭海归,鬓发尽脱。”北宋地理学家朱彧在其所著《萍州可谈》中引用了他父亲朱服的见闻,其中有关于苏东坡离开海南时的状况:“余在海南,逢东坡北归……视面,多土色,靨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离开海南后的苏东坡直奔他早已选择的终老之地常州,很快就去世了。
然而,苏东坡的精神生命却是谁也打不倒的。相对于中国历代的无数诗人,他的心灵一直到死都像天真的孩子,而他的性格、情感和智能却又有着无可比拟的灿烂和优异。
一个卓越的人从来不会失去幽默感。苏东坡在日记中写道: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
是啊,“天地”、“九州”、“中国”不都是在“大瀛海”中吗?普天之下有谁不是“岛”上人呢!
在苏东坡看来,一个人活着却没有乐趣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他随遇而安,与黎人欣然为伴:
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
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
借我三亩地,结茅与子邻。
鴃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
(《和陶田舍始春怀古》)
“鴃舌”,黎语戏称:如果能学会黎族话,情愿做黎族老母的子民。
他在槟榔树下同农夫畅谈。面对这位先前的大人物,村民们起先惶然无措,不知该说些什么。于是他笑着请求说,“那你们就讲几个关于鬼怪的故事吧”;他在正直的官吏、风雅向善的和尚和道士、大大小小的读书人中有许多同情者。他初到儋州(时为“昌化军”),军使张中对一代文豪极为敬重,让他和儿子住官房,吃官粮。后来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至雷州时,听说他在海南的待遇,遣使渡海,将他逐出官舍。张中也因此受到处分。他只好暂时在当地学生黎子云家借宿。随后众学子“躬泥水之役”,众乡民“运甓畚土助之”,在中和镇南郊的桄榔林中盖茅屋三间安居,他将茅庵名之为“桄榔庵”,并书题《桄榔庵铭》:“东坡居士谪于儋州,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自贺“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又在庵旁水塘种植莲花:“城南有荒池,琐细谁复采。幽姿小芙蕖,香色独未改”。他得到土著黎人的尊敬,他们送给他黎被、吉贝布(“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大清早,他还在床上睡觉,当地猎人就来敲门,把刚刚猎获的鹿肉分些给他,或者是捧来制好的槟榔(“槟榔代茗饮”)。每年腊月二十三是海南民间祭灶日,邻居拜过神灵送过灶神之后就把祭肉送给他。一位老农妇见他完全像个土人一样地头顶着西瓜走过田野,便跟他开玩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他开心地在诗里叫她“春梦婆”:“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唯逢春梦婆。”(《被酒独行》之三)下次路遇给丈夫送饭的春梦婆,也跟她开玩笑:“云鬓蓬松两腕粗,手携饭钵去寻夫。”春梦婆伶牙俐齿地回敬:“是非只为多开口,记得朝廷贬你乎?”他教他们识字,给他们吟诗,同他们一起饮酒,“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他对黎舞和黎歌给予极高评价:“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
亚热带岛屿,夏天湿热难当,秋多雨,闽粤商船因为气候不好,不再南行。食物短缺,“北船不到米如珠”,苏氏父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面临挨饿危险的老人,甚至写过一篇记述“阳光充饥法”的文章:说一个偶然掉进深坑的洛阳人,模仿坑内蛙、蛇的样子,拼命吞食从洞隙里透进来的阳光,终于不仅止住了饥饿直到获救,而且从此不知道饥饿的滋味。接下来老人写道:“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行此法,故书以授。”好心好意地希望以后跟他一样倒霉的人,能以此获得生机。
美食家的他很快就喜欢上了海鲜,并且颇为自得,煞有介事地教诫儿子保持谨慎,不要随便告诉别人:
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汲江煎茶》)
三
巳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蠔。剖之,肉与浆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又益□煮者。海国食蟹、螺、八足鱼,岂有献□?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路途中忽遇暴雨,狂风撼树,山谷轰响,惊心动魄,他照样有雅兴作诗:“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岛上买不到药,他就自己四处采药并写下大量有关草药的笔记。《苏沈良方》记载他发明的荨麻治风湿、用苍耳润肤等处方,以及经他研究过的蔓菁、苦荠、芦菔等植物的药效。他专门向广州的王敏仲索黑豆,制成辛凉解毒的淡豆豉,当地百姓跟着栽种黑豆,后人称为“东坡黑豆”。找不到好墨,他就自己用松油、牛皮实验烧制。后来有个叫“潘衡”的杭州人自称在海南跟东坡学过制墨,结果店里的墨价倍增。当地民众多取咸滩积水饮用,以致常年患病,他指地凿井,远近乡民一改饮用塘水习惯。那口井遂被命名“东坡井”。在他“指凿”井泉的地方,百姓建亭纪念。后来他遇赦北归时应邀命名为“浮粟泉”。泉台上后人篆刻对联“粟飞藻思,云散清衿”来颂扬这位大诗人。他在《劝和农六首》中,苦口婆心地说服黎族同胞改变“不麦不稷”、“朝射夜逐”的单纯狩猎,重视农耕,以使“其福永久”;他自己采茶、寻找好泉水:
活水还需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流放,对于被流放者,是炼狱。但对于流放地,是福祉。
海南自古被称为“天涯海角”,孤悬偏安于海外边陲蛮荒。因为成了流放地,海南岛得到中原的更多关注,也因此有了更多的传奇色彩。有宋一朝,有关海南的传说成了显贵和名士的话题。来自海南的沉香气息飘散在京城开封府的高屋堂厦里,对海南知之甚少的名流们在诗酒之余,不无夸张地传说着那个孤悬海外的“琼崖”的传闻。诸如“冒白乡风旧,标青社酒酣。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十》)一类,甚至被记载下来,编入文集。
历代流放者以及移民们带来的大陆文化与海南本土的海疆文化相结合,在千年间酿造出了特色独具的文化宝藏。
三亚水南村至今住着从汉到明多位被贬名臣巨儒的后人。不同出处、不同姓氏的民居建筑风格各异。第一个从中原贬到海南来的王义方,他谪居琼西之吉安(今昌江),三十出头,精力旺盛。期间,他召集黎族各洞首领,商议教化“稍选生徒、为开陈经书,行释奠礼,清歌吹笛,登降跽立,从悦顺”,开班讲学,传授礼乐,成为“开创海南儒学教育第一人”、“传播中原礼乐文化第一人”。因而名登《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北宋的《资治通鉴》和《广东通志》、《琼台志》、《琼州府志》等。李德裕在琼期间,著书立说,奖善嫉恶,为海南人所敬仰,他还是中国象棋的发明者。仰仗恩师宰相寇准提携荣登宰相宝座,却又因一桩小事将寇准整得死去活来的丁谓向来为人所诟病,然后来被贬海南后却大彻大悟,做了许多善事。
在所有被贬谪海南的人士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对海南风俗习惯影响最大、最有成就的无疑是苏东坡。
居儋三年,苏东坡以他的巨大影响,化风俗,启人心,对于儋州,对于海南,是一次文化上的开疆拓荒,儋州因而成为全岛文化的中心。史书所说的“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胜实自公启之”,以至“科目自隋莫胜于进士,琼在四榜连破天荒”、“标琼海之先声”云云,就不去说它了。文化的力量和真正影响,其实就在日常生活中。苏东坡在文坛以诗词揽胜,居儋时又喜为诗,儋州诗风因此大盛。中和千年古镇,逢年过节,贺喜迎新,家家户户都有做对联贴对联的习俗。此外,儋州山歌的歌词句式整齐,注意修辞文采,讲究平仄韵律,对歌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敷陈辩驳,声调类似古人诵诗,中原文人诗词歌赋的特色显而易见。中和镇百姓多熟知东坡故事,甚至这里的方言亦称“东坡话”,尾调颇似四川方言等等,皆为东坡流风遗韵。
这位伟大的放逐者给他自己、也给海南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及极为悠远深刻的影响。后人把苏东坡在儋州遗存称作“奇踪”。他在海南的地位相当于孔子在中原。海南人的《东坡居儋歌》唱道:“弦歌海滨垂无疆,儋之人士每叨光。儋人得师喜洋洋,先生当日奔忙忙。饥寒常在身前当,功名常在身后扬。”站在文化的角度,被流放者是胜利者。
四
海南流放岁月,陶渊明是苏东坡的精神楷模。他在海南写作的一百多首诗中,有一百二十四首是“和陶诗”。在给苏辙的信中,他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
他在苏辙写的《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加了一段话:
嗟夫!渊明不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
对自己仕途的反思,让他对陶渊明发生了由衷的推崇。他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对陶渊明的人品、作品推崇备至的人。诗歌经历唐代瑰丽、工整的发展,陶渊明那种天然去雕饰的朴素美学风格重新得到苏东坡的创造性阐发。这就是为什么宋代的张戒会说:“陶渊明、柳子厚之诗,得东坡而后发明。”
等到遇赦北归,他已是早已心志淡泊,宠辱不惊。他在海南澄迈的通潮阁题诗说:
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
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隐约的伤感波澜不惊。
苏东坡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对在磨难中生活过的这个炽热的岛屿充满了深情。离开海南之前,他写诗赠别黎子云:“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走到江苏润州,有人问他:“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他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走到镇江,游金山寺他写《自题金山画像》一诗,题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元符三年庚辰(公元1100年)六月二十日,他在最终北渡的船上写下了著名的《六月二十日渡海》,这样总结了三年的海南流放生涯: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在诗里他把自己比作“乘桴浮于海”的孔子、“九死而犹未悔”的屈原,而海南之旅在他老人家看来竟是一次“冠平生”的“奇绝”漫游。
真是大自在!
杜甫说“文章憎命达”,也许伟大艺术家真就是吃苦的命。恶劣的环境使苏东坡的生存下降到了唯求苟活的程度,却使他的艺术上升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儋州谪居,是他创作的一个转折点,风格趋于平淡清新。黄庭坚曾在信中对友人说:“寄示东坡岭外文字,今日方暇遍读,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朱熹叔祖、南宋诗人朱弁(1085~1144)在他的《风月堂诗话》中说:“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鲁直亦瞠乎其后矣!”
在朱弁看来,苏东坡贬谪黄州之后写的文章就再没有人赶得上了,唯一能跟他有得一比的是黄庭坚的诗。而他被贬谪海南之后,黄庭坚也只能在他身后干瞪眼了。接近人生尽头的海南流放经历,让苏东坡的文学成就远远地走到了同时代人的前面。
这是极精到的见地。
真正可以说,东坡不幸海南幸;诗人不幸诗歌幸。
在对苏东坡的评价中,林语堂的表达最为生动感人: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终其一生他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他没有心计,没有目标,他一路唱歌、作文、评论,只是想表达心中的感受……他把心智用在事件过程中,最先也最后保留替自己说话的权利……永远真挚、诚恳、不自欺欺人。他写作没有别的理由,只是爱写……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他固执、多嘴、妙语如珠,口没遮拦,光明磊落;多才多艺,好奇,有深度,好儿戏,态度浪漫,作品典雅,为人父兄夫君颇有儒家的风范,骨子里却崇尚道家,讨厌一切虚伪和欺骗……向来不喜欢作态……他快快活活,无忧无虑,像旋风般活过一辈子。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尤其他的晚年,不难看出,他是怎样的有着完全独立的人格,他的自我是怎样一个难以攻破的堡垒。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别人的褒或贬,供奉或冷落,在他都是无所谓的事情。这样一个卓尔不凡的人,我们世俗的眼光也许无法理解,但有一点是可以认识到的,那就是:一个人真正的成功是品质的优异和人格的健全。
离上一次三十年后,我再一次得到访问儋州的机会。这一次,车子一直可以沿着平整宽阔的水泥路开到修缮一新的“东坡书院”门前。
我在载酒亭后墙上的明代大画家唐寅所画的《坡仙笠屐图》摹本木版画前端详良久。这幅画的取材甚妙:苏东坡拜访黎子云途中遇雨,从农家借来竹笠戴在头上,穿木屐,微弯着腰,提挽衫脚,笑吟吟地走在泥泞的村道上,路人喧笑,村童嬉随,农家的狗也对着他吠叫。苏东坡也乐了:“笑所怪也,吠所怪也!”
潇洒出尘的精神气质活脱脱再现。
我忽然明白,苏东坡留给后世最大的精神财富应该是他的人格的自尊和优雅,他的人生观念的超脱和优越。
这是庸庸碌碌地沉浮在滚滚红尘中的我最值得记取的。
陈世旭,作家,现居南昌。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梦洲》、《将军镇》等。
人文地理随笔小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