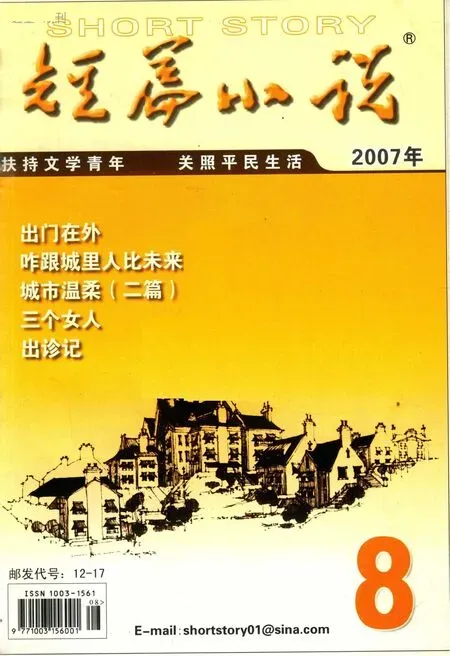《浮士德》的原型批评分析
简 澈
《浮士德》的原型批评分析
简 澈
在文学批评中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几乎成了文学研究的金科玉律。然而,这种似是而非的前提“使得内容本应当很宽广的文化研究中弥漫着一种狭隘的审美主义气氛” 。而真正的艺术欣赏“是一种文化解码行为,它要求解码者先得掌握编码的秘密才行”[1]。原型批评正是从把握各种共时关系、意义和价值的批评,是在历时和共时相互作用中把握人类精神结构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文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深入挖掘《浮士德》中蕴藏的“通过仪式”原型、“死亡与再生”原型和“阿尼玛”原型,以期对《浮士德》这部不朽的作品进行特殊的阐释,使作品背后蕴涵的文化批评得到新的发展和突破。
一、《浮士德》中的“通过仪式”
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指出:“神话中英雄冒险的标准道路乃是成年仪式所代表的公式扩大,即分离——传授奥秘——归来;这种公式可以称之为单一神话的核心单元。”[2]“成年仪式”其实用根纳普的术语表达即“通过仪式”。根纳普在《通过仪式》中指出,“任何社会里的个人生活,都是随着其年龄的增长,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序列”[3]。浮士德的经历正是一种“通过仪式”的原型。
浮士德的人生追求经历了书斋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建功立业五个悲剧阶段,这五个阶段高度浓缩了欧洲资产阶级探索和奋斗的精神历程。在书斋生活中,浮士德不满于书本的束缚,在“返归自然”中挣脱中世纪的精神枷锁而获得新生;在爱情生活中,他通过对爱情、享受的追求,发现低级的吃喝玩乐、对情欲的享受不是美;在政治生活中,通过为封建小朝廷服务,他识破了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不是美;在追求古典美的过程中,浮士德与美女海伦结合,发现只有形式而无灵魂的古典艺术不是美;在事业悲剧中,通过亲身探索,浮士德发现与人民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改造自然才是美。他不断地追寻、实践、不满足、分离、再追寻,在这自强不息的探索真理、追求美的过程中,浮士德经历了种种冒险和分离,通过连续和渐进的形式不断完善自我,最终由上帝派出的天使们抬向了天国,得到了光明。
根据日本学者伊藤清司《难题求婚型故事、成年仪式与尧舜禅让传说》以及荣格《人及其表象》等有关资料,成年仪式即:仪式期间,未成年人首先离家到隐蔽场所,然后接受种种折磨和考验,如一段时期的斋戒、打掉牙齿、文身、割礼、象征性的死亡,此即仪式过渡阶段,仪式结束后再返回原地与社会融合,他们装着变成另一个新人,从此他们开始过一种具有更大权力并承担更多责任的生活。通过仪式即成年仪式理论为文学批评所广泛应用,而《浮士德》中的五个悲剧也蕴藏了“成年仪式”。在《浮士德》的五个悲剧中,浮士德不断面临人生的转折,产生浓烈的心理感慨,不断得到领悟。用哈特曼的话说,“歌德的《浮士德》完全是一个社会化‘通过仪式’在艺术作品中的范例”[4]。
每个人都有人生的转折时期,并产生较为强烈的心理感慨,此即“我们面对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浮士德》的烦恼凝缩了人类普遍遭遇的典型情境,浮士德对理想的追寻、对美的追寻、对情欲的追寻、对外在活动的追寻都可以概括为人生的追寻,而这种追寻本身就是一种“通过仪式”。
二、死亡与再生
从古希腊泊尔塞福涅神话到古东方的借尸还魂,人类对“死而复生”的期望从未止息。“死亡”传递了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的深层思索,死亡的意义何在,人类的归宿究竟在何方等,迄今仍是人类思考的焦点。死亡不可逃避,但“重生”寄托了人类对永恒存在的美好追求,体现出人类对美和生命的向往。
神话学家泰勒曾指出:“古代人认为,为了使一个状态产生变化,首先必须破坏原有的现状,由现状的破坏而产生和引导出另一个新的状态,因此对古代人而言,死亡不是生命的终了,而是到达再生的过渡,在原始宗教原始信仰中常见的是灵魂转生的信仰,死去的灵魂转化为人、动物或者植物而使原来的生命得以继续。”[5]弗雷泽在《不死的观念和对死亡的崇拜》一书中也提到,原始人相信人类原是不会死亡的观念,他用大量篇幅讲述阿杜尼斯神话在世界各地的广泛存在现象,指出了原型批评的一个最基本原型:死而复生。这就如东方文化中的“凤凰涅槃”“置之死地而后生”那样,“重生”建立在“死亡”之上。
伊藤清司认为,“成人仪式”象征着从女性世界向男性世界的转化,意味着年轻人的“死亡与再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浮士德追寻生命境界的提升,展现的正是一种精神再生,这种精神再生历经了三个阶段:旧精神的死亡、成型中的精神在善恶间徘徊、新精神的复活重生。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以学者的形象出现,他学识渊博,却感觉这一生是失败的:年轻时的美好梦想灰飞烟灭,所有基于书本的精神探索都无疾而终。他的内心充满欲望,他渴望上天揽明月、下地享尽人世间欢愉。他决绝地否定旧思想,但对新精神的探寻又无处可循,只剩悲观笼罩左右,“伟大的精灵蔑视我,大自然给我吃闭门羹,思维的线索一经纷乱,我早已厌弃一切学问”,他想“投身于生动的自然”[6],年迈的体质却不允许他这么做。他精神日渐萎靡到想自杀。浮士德评价他:“你的感官关闭了,你的心死了!”[7]这标志了浮士德旧精神的死亡。虽然精神受到折磨,但浮士德内心的光明力量从未消失。在魔鬼梅菲斯特的引领下,他经历了知识、爱情、政治、美等种种悲剧,直至走到生命尽头也依然追求真理。最后他双目失明,但内心却越来越灿烂。他幻想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不由得喊出那一句“你真美啊,请你停留”之后,依照赌约倒地而亡。浮士德肉体虽然死去,但精神却得以复活,天使们高歌着从梅菲斯特手中迎走了他的灵魂:“精神界的这个生灵/已从孽海中超生。/谁肯不倦第奋斗,/我们就使他得救。/上界的爱也向他照临,/翩翩飞舞的仙童/结队对他热烈欢迎。”[8]
复活后的浮士德精神全然摆脱了先前那种虚无的状态,新的精神以其对生命与自由的渴望而建立起坚定的核心价值,并由此包容万物,达到了一种精神的永恒。最终,浮士德完成了由深渊到巅峰的精神飞升。
浮士德这种精神复活的过程是在原先枯朽的旧精神死去之后,历经磨砺的新精神复活并超越了旧精神,从而得到长存的。这种精神复活的过程正是死亡再生原型中英雄人物受难——死亡——再生的模式。
三、阿尼玛
荣格把那些以对异性的个人经验为基础的原型表象都称为阿尼玛斯和阿尼玛。前者是指女性的男性表象,后者是指男性的女性表象。荣格认为,每个男人心中都携带着永恒的女性心象。这不是某个特定的女人的形象,而是一个确切的女性心象。这一心象根本是无意识的,是镂刻在男性有机体组织内的原始起源的遗传要素,是我们祖先有关女性的全部经验的印痕或原型。[9]因此,当人们问一个男人到底迷恋上了一个女人身上的哪一方面时,用荣格的话来回答,他看上的就是那个阿尼玛。阿尼玛不仅被描绘成性的诱惑,而且被认为拥有古老的智慧。比如,在《神曲》中,贝雅特丽齐引领但丁神游天堂,贝雅特丽齐象征着感性和信仰,她就是但丁心中的阿尼玛。浮士德心中也存在着阿尼玛的形象。但这个阿尼玛形象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历经了三个阶段。
少女甘泪卿淳朴善良、单纯无知。她不计后果地与浮士德相爱,结果导致一系列灾难:为了与浮士德约会,她给母亲服食了过量的安眠药,导致母亲死亡;哥哥华伦亭为了她与浮士德决斗,最后丧生;因为不敢面对世间的羞辱,她溺死了与浮士德的私生子,从而被关进死牢。甘泪卿的悲剧源自她的爱情,她使浮士德品尝到爱情的美酒,代表了浮士德的生理本能,也是人类爱情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这个阿尼玛形象被歌德安排在浮士德“通过仪式”的第一个阶段,是因为爱情是人性中最基本、最自然的本性,爱情能够促使人自身能力的激发。
歌德把希腊神话中最美的女人海伦描绘成半宗教半幻想的形象,她半人半神的特殊身份使其具有浪漫主义美感。海伦是浮士德审美的心理具体化,在她身上既体现了希腊古典遗风,又表现出新兴浪漫主义的萌芽,二人的爱情代表了人道精神与浪漫主义理想的平衡,象征着古典与现代的美妙融合。
浮士德在面对最后的考验时,他满足于眼前的假象。正在魔鬼要带走他的灵魂的时候,光明声母派来天使转移魔鬼的注意力,抢走了浮士德的灵魂,飞回天堂。“光明圣母”是浮士德将爱升华到精神献身高度的形象,她最终引导浮士德摆脱了魔鬼的束缚,获得了真正的提升。
《浮士德》中“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前进”指出了阿尼玛的作用。从对甘泪卿的生理之爱上升到对海伦的灵魂之爱,再上升到对圣母的崇拜,这些阿尼玛形象的不断发展促使浮士德的本性发生了变化,最后达到崇拜玛利亚的最高境界,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理想。
通过原型批评方法的分析,我们发现了《浮士德》潜藏的“通过仪式”、死亡再生模式、“阿尼玛”等原型形象。通过这种批评方法的运用,综合又宏观的分析了《浮士德》文本背后蕴涵的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对我们研究《浮士德》又开启了一个全新视角。
[1] 徐贲.美学·艺术·大众文化——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J].文学评论,1995(05).
[2] 坎贝尔.千面英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23.
[3] 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8.
[4] 彭兆荣.文学人类学叙事学的“形式实体”[J].吉首大学学报,2002(02).
[5] [英]E.B.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02。
[6] [德]歌德.浮士德[M].绿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7] [加拿大]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等译.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8] [美]查尔斯·米尔斯·盖雷,编著.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M].北塔,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9] [美]C.S.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54.
王丽捷(1978— ),女,吉林九台人,吉林医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宁爽(1983— ),女,天津人,吉林医药学院外语教研室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