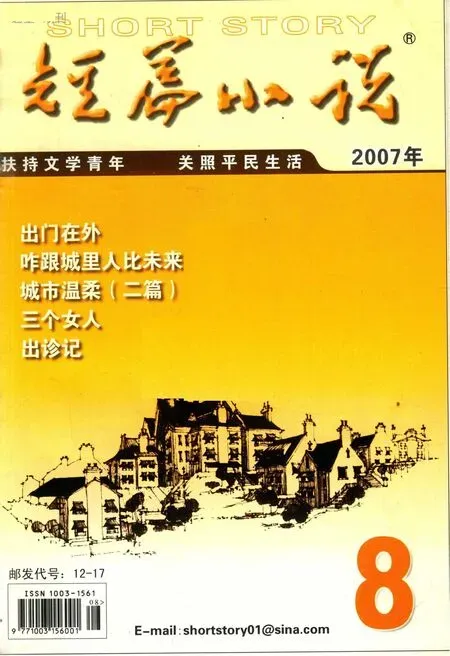简·德万尼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刘浩波
简·德万尼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刘浩波
一、引 言
20世纪初的澳大利亚是父权制观念主导的男权社会,男性具有权威地位,而女性则被边缘化,只具有“他者”的身份,缺失作为“人”的存在。男性为控制女性而创造出一种“理想女性”文本形象,即女性除了甘愿接受社会赋予她们的家庭职责,又需保持不现实的贞洁、禁欲的状态,以自己的人生换取对“爱”的守候。由此出现在男性作者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大都表现为对立的两极,即“天使”与“魔鬼”。“天使”型女性温顺谦恭,是男权社会价值标准虚构出来的理想女性。而“魔鬼”型女性有着独立的意识,拒绝无私奉献,可能对男性的地位造成威胁,因而常常受到妖魔化。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支配着传统的男性叙事,扭曲了女性的真实形象。
男性文本里的女性形象只是他们想象的投射,女性为摆脱男性的控制而拥有独立的人格,就需要通过解构并颠覆“理想女性”文本形象,塑造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女性文本形象。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言,“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
20世纪澳大利亚女性作家简·德万尼的作品饱含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和共产主义思想,一群以多尔西、莉莲、玛丽戈蒂、玛丽金等为代表的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叛逆女性新形象被诉诸笔端。在男权主义者眼里,她们张扬放纵、道德败坏。但透过她们的行为,我们看到的却是洋溢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的女性,她们是一群无畏的叛逆者。简·德万尼的作品反映了殖民时期澳大利亚女性的多样性,女性的心态及欲求,理想与希望。
二、叛逆女性类型及其反叛意识的表现
简·德万尼的文本把外在的宏观世界和内在的心灵世界结合在一起,塑造出的叛逆女性形象是丰满而真实的,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以莉莲、玛丽金为代表的以纵欲滥情来表现人格独立的女性形象,她们有觉醒反抗的一面,行进的道路却是堕落;另一类是以达尔西、玛丽戈蒂为代表的传统女性,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背叛自己的阶级,将自我命运与社会、国家的命运相结合,精明强干的政治女性形象。
第一类是纵欲滥情的女性形象。以玛丽金、莉莲为代表的女性蔑视男性、风流放荡,把追求感官快乐作为人生的目标之一。游戏于男性之间的她们对男性制造出的“理想女性”形象嗤之以鼻,以追求个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为手段,追寻失落已久的自我。面对这种女性,男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表现出某种臣服和妥协。纵欲滥情的女性是时代的产物,当女性无法找到有效的途径来否定社会伦理道德和宣泄自己的反抗意识时,自身的堕落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如简·德万尼小说《可怜人》里女主人公莉莲,她是一个放荡的女人,从十几岁起就跟很多男人有染,婚后仍和情人保持不正当的关系,当地人鄙视她,把她当做耻辱。但简·德万尼却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莉莲,她赞赏莉莲的随心所欲和真实自然,在整部小说里,她更是频繁地提到莉莲的“天真”“清纯”和“内在美”,还把她比作一朵百合。
简·德万尼怀着强烈的女性意识来写这部作品,她把莉莲置于一个弱者的地位,对莉莲受到男性从心灵到肉体上的摧残深恶痛绝。简·德万尼对莉莲的同情和怜悯与其共产主义信仰和女权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她认为,社会罪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性,如果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放荡是不可避免的。在简·德万尼的眼中,导致莉莲现状的责任不在她自己,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是那些鄙视莉莲的人,是这个丑恶的资本主义社会。
从现代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简·德万尼那些描写女性婚外恋、性和心理的作品拥有一种值得肯定的女性主义立场:对一直生活在男权专制文化阴影下的女性的叛逆和放荡,给予一种体贴与宽容。尽管这一类女性表面看起逾越了道德规范,但她们却展示着人性的真实,是人性的自然流露。
第二类是政治女性形象。囿于家庭的女性,除了生儿育女和洗衣做饭外,在政治上是完全边缘化的形象。没有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的女性必然在社会生活中处于被动地位,缺乏对自身命运的掌控能力,只能成为无知、可欺的弱者形象。[5]常见的文学作品里,对自我命运的把握和自我价值的追求是叛逆女性的核心形象,此类女性的主体意识发展仍然处于萌芽阶段。但是女性的价值不应只是存在于其个体自然属性, 更应具有社会层面上的意义。
简·德万尼对传统叛逆女性形象进行解构和重建,但并不否定她们的女性特质。她塑造的达尔西、玛丽戈蒂等政治女性的所作所为常常与社会传统价值观相背离,与大多数人的行为格格不入,觉醒的她们向自身的存在寻求幸福。她们独立、健谈、敢爱敢恨,甚至难以置信的完美。如小说《甜蜜天堂》里的达尔西,她本是一个天真的消极的女人,她不理解丈夫和其他人为何要策划罢工,不愿丈夫卷入,但是随着罢工活动的进展,她逐渐成长为妇女支持罢工团体的领导,加入了这场“不是为了工资,而是为了生存”的政治斗争。这些女性形象似乎传达了简·德万尼希望塑造的政治女性之美,她们具有独立健全的人格形象,温柔而坚强,并不依附于任何男性,也无需任何男人来解放。
这些叛逆女性形象表达了澳大利亚女性渴望达到在意识形态上与男性平权后,对社会前途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力的认识和思考。这些原本的“理想女性”里沉睡的自我意识一旦被唤醒,追求独立人格的渴望就无法抑制。但是她们没有把实现个人价值看成是圆满的结局,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她们的个人命运与某种政治力量或社会变革力量结合在一起,在政治斗争或社会解放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逐渐掌握政治权利。女性命运的探索由此实现了从个体反抗到群体突围的飞跃,传统叛逆女性形象被赋予新的性别身份,拥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三、叛逆女性形象成因分析
所有女性的思想深处都孕育着自由的种子,一旦碰到适合的土壤就会发芽生长。从顺从到反抗,从被动到主动,从被压迫者到解放者,女性形象的衍化实质上反映了一种社会和思想的衍变,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指向性。简·德万尼的作品主要写成于20 世纪上半期,这个时期澳大利亚社会正处于重大发展与变革时期,她笔下的叛逆女性群体可谓是紧扣时代脉搏而衍生出来的一类女性形象,包涵社会文化以及作者本身等各方面的原因。
首先,强烈的女权意识。19世纪末期,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第一次浪潮兴起。此阶段女权运动旨在通过削弱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男性权威来促进女性的进步并进行社会改革,运动的焦点在于女性争取选举权。简·德万尼的女性文本形象反映了此时期女权运动的时代特点。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婚姻不再是两性关系的唯一选择,家庭逐渐被看成是一种约束和压迫的符号而受到批判。简·德万尼从传统男权文化束缚中解放笔下的女性人物,她笔下的女性向往自由、追求人格独立与完整,反抗传统道德约束,具有叛逆精神的种种表现恰好折射了当时澳大利亚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思想、宗教、道德、习俗等各个领域的巨大转变。这些叛逆女性形象负载着简·德万尼对澳大利亚社会未来走向的深切关注和冷静思考,同时也表现了她对澳大利亚白人传统价值观的挑战,即如摩尔所指出的“女性的必然、种族关系的必然、性的必然、社会和生活的必然”,而这些所谓的“必然”,实质上就是男权主义对妇女的束缚和压迫。
其次,作家自身的经历。简·德万尼出生在新西兰一个贫寒的矿工家庭,童年的回忆只是嗜酒如命的父亲和辛苦养家的母亲,这段经历让她对女性的遭遇有了深刻的认识。加入澳大利亚共产党后,出于政治宣传的原因,她采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式进行创作,将浪漫爱情与革命政治相结合,试图在文本中建构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女性形象来唤醒女性对自己现状的认知和承担历史变革的责任。对于简·德万尼来说,文学作品是宣传的工具,她的作品里充斥着激烈和煽动的语言,较之传统爱情文学少了一份伤感和痛楚,多了一种颠覆、叛逆和大胆,因此她的作品经常是超越禁忌的,常常引起争议。她的第一部小说《肉店》就谴责了婚姻中女性的性压抑,大胆地表现了性对于女性的重要性,加之一些不加掩饰的性描写,最终在澳大利亚、德国等多个国家被禁。
四、结 语
毋庸赘述,简·德万尼文本中塑造的一些女性形象出于政治宣传和反男权的需要而沦为一种类型化的符号印象,自身的文学价值多少受到影响。不可否认的是,简·德万尼运用手中的笔颠覆了男性中心的话语表达,新的女性话语权得以表露,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有力地推动了对澳大利亚女性文学主题的探讨。
[1] Jean Devanny.TheButcherShop[M].New York: Macaulay, 1926.
[2] Jean Devanny.PoorSwine[M].London: Duckworth,
1932.
[3] Jean Devanny.SugarHeaven[M].The Vukgar Press,
2002.
[4]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5] 郭秀媛.后殖民姿态下的混杂性书写[J].河北大学学报, 2009 (0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澳大利亚妇女小说研究”(课题编号:W07211062);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资助课题的成果之一;四川省国别与区域重点研究基地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课题“澳大利亚女作家简·德万尼研究”成果之一;西华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重点学科成果(项目编号:XZD1907-09)。
高虹(1981— ),女,四川绵阳人,绵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