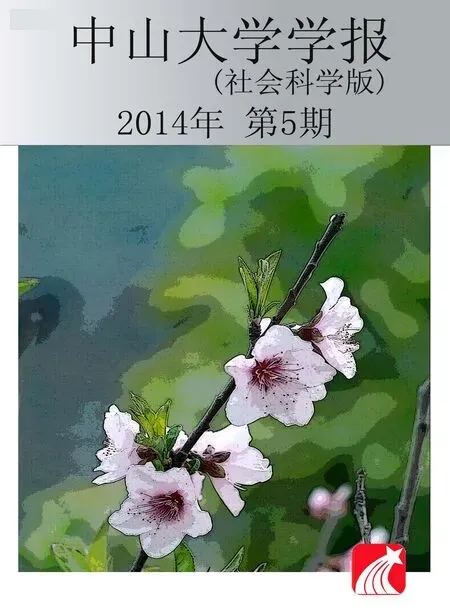从《楞伽经》印心到《金刚经》印心*
冯 焕 珍
一、教下的印心
印心,印即印证、心即人心,指佛教修行者验证自己心行境界的一种行为。此行为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印心的标准,二是被印之心。对佛教来说,最根本的印心标准是释迦牟尼佛觉悟的境界。由于此为佛陀自心所印之境,宗门常常称之为佛心印或如来心印;与此同时,因为佛陀言教是其觉悟宇宙人生实相后的说法与集结,自然也具有与佛心印相同的印心效力,是为佛经常常说的法印或圣谛。被印之心即佛教修行者的心。此心如果被如来心印或法印所印,便能与佛心心相印,是为得佛心印;如果得佛心印者将此心印传与弟子,就叫作传佛心印。
释迦牟尼应世时,上述两种印心的标准就同时在发挥印心的作用。翻开佛经,我们可以看到,佛陀弘扬佛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尚未觉悟或觉悟未臻圆满的弟子进行加持或授记*加持指佛陀以种种力量护佑弟子,令其去除疑惑、烦恼、恐惧、懈怠等不良习气,增强修习佛法的信心、兴趣、毅力、力量;授记指佛陀对弟子将来修行成就的预记。,对圆满觉悟的弟子予以印可,弟子们得到佛陀的印证,则知自己之已学、当学或成就。同时,我们也知道,《阿含经》里常常记载,只要佛弟子依据三法印或四圣谛证知自己已证入圆满的涅槃境界*法印,一般指《阿含经》所说三法印;四圣谛,即佛陀证见的苦、集、灭、道四个真理,由于此真理为佛教中觉悟了的圣人所证见,故称圣谛。,往往会很决断地宣称“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8,[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主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册,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4—1934年,第51页下。,宣布自己获得了涅槃。
因为弟子对释迦牟尼的信仰与恭敬,释尊在世时没人怀疑这两个印心准量,但释尊圆寂后就出现了分歧。就心印说,到底谁真正传持了佛心印?难道只要是佛弟子就传持了佛心印?这当然有问题,因为南传《大般涅槃经》已明确说,佛陀圆寂时尚有未离欲比丘*经文云:“于世尊般涅槃时,彼未离欲之诸比丘,自投地上,如碎岩石,辗转而哭:‘世尊般涅槃何其速!善逝般涅槃何其速!世间眼目隐蔽何其速!’”(元亨寺汉译南传大藏经编译委员会:《汉译南传大藏经》,《长部经典》二,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4年,第113页)。实际上,依佛陀教诫,仍然要看弟子的心行是否与法相契。如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即记载佛临涅槃前对弟子说:
一切诸法皆悉无常,恩爱合会无不别离,汝等不应请我住世。何以故?今者非是劝请我时,向为汝等略说法要,当善奉持,如我无异。*[东晋]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卷上,[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主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第193页上—中。
阿难尊者甚至说:
我等不依于人,而依于法……若有比丘知法者,我等请彼比丘为我等说法;若彼众清净者,我等一切欢喜奉行彼比丘所说;若彼众不清净者,随法所说,我等教作是。*[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經》卷36《梵志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第654页中。
换句话说,佛陀圆寂后,只有法印才是印心的根本准量。
大乘佛经传出后,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这些经典是否佛所说?如果为佛所说,为何佛所说?这个问题,大乘佛经的佛身观给予了大乘信仰者共许的解答。大乘佛经的佛身观主要有两种,即略说为法性身、父母生身的两身说,以及广说为法、报、化的三身说*此说将法性身开为法、报二身,而以父母生身为化身。。不管哪种说法,都认为说《阿含经》的释迦牟尼只是佛的千百亿化身之一,佛的其他化身也能说法,如《大智度论》云:“佛法有五种人说:一者佛自口说,二者佛弟子说,三者仙人说,四者诸天说,五者化人说。”*[印度]龙树著、[姚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2《序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5册,第66页中。此处的佛既包括法、报二身佛,也包括化身释迦牟尼佛,而弟子、仙人、诸天、化人则可以理解为佛的其他化身。依此说,许多佛经由彼等化身演说,并于释迦牟尼圆寂后传出,这并不奇怪。由此,菩萨道信仰者不但可以依释迦牟尼佛印心,也可以依演说佛经的佛弟子、仙人、诸天、化人印心,能印心的佛骤然多了起来。这似乎突出了心印的地位,其实不然,因为大乘佛经尚有“法四依”说。此说认为修行者应当以法为依,所谓“依于义不依语,依于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于法不依人”*[姚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卷下《法供养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册,第556页下。又参《大宝积经》卷82、113,《大般涅槃经》卷6《如来性品》,《佛说大般泥洹经》卷4《四依品》,《大方等大集经》卷5、29,《自在王菩萨经》卷上,《禅法要解》卷下,《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8《大光普照庄严品》等处。。在《大般涅槃经》中,当佛陀说佛弟子可以依四种人时*详见[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6《如来性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册,第396页下。这四种人中,有三种是见道的圣者;而所谓“具烦恼性”者,古德认为指处于十住、十行、十回向三个阶位的地前菩萨。,迦叶菩萨提醒佛陀说,天魔外道可以假冒这四种人破灭佛法*迦叶菩萨说:“如佛所说,是诸比丘当依四法……如是四法,应当证知非四种人”([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6《如来性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册,第401页中—下。),更凸显了法印的根本性与心印的从属性。
剩下的问题就是:大乘佛经的法可依吗?相信只有说《阿含经》的释迦牟尼才是佛的佛教信仰者自然认为不可依,但相信佛有两身或三身的佛教信仰者却认为真实可依。而且,这些经典还阐明了其所说法与《阿含经》的关系。有的经典说,大乘佛经与《阿含经》所说法有了义与不了义(或方便与究竟)的差别*详见[唐]释玄奘译:《解深密经》卷2《无自性相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6册,第697页上—中。;有的经典则说,一切佛经平等不二,都是了义经。此问题非常复杂,非此处所能详论。总体上,我更赞同以诸经义有差别者为方便说,以一切经义平等一味者为究竟说*这并不否定佛经在修证与愿行上有随缘的差别。。如《自在王菩萨经》所云:“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了义经者,一切诸经皆是了义,以依义故,一切法不可说故。菩萨如是名为依了义经。”*[姚秦]鸠摩罗什译:《自在王菩萨经》卷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3册,第927页上。该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不依文解义,能通达经文的真实旨趣,则一切佛经的经义无二无别。其理由经中未说,但龙树菩萨有很透彻的论述:
佛说三种实法印,广说则四种,略说则一种。无常即是苦谛、集谛、道谛,说无我则一切法,说寂灭涅槃即是尽谛。复次,有为法无常,念念生灭故,皆属因缘,无有自在;无有自在故无我;无常、无我、无相故心不著;无相不著故,即是寂灭涅槃。以是故,摩诃衍法中,虽说一切法不生不灭,一相,所谓无相,无相即寂灭涅槃。*[印度]龙树:《大智度论》卷22《序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5册,第223页中。
龙树菩萨的意思是:四圣谛虽然较三法印多了一谛,但苦、集、道三谛的缘起义即“诸行无常”印,四谛的性空义即“诸法无我”印,灭谛即“涅槃寂静”印;实相印不过是从三法印的“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两印和四圣谛的“灭”谛安立的名相,内容也毫无二致。因此,只要真实、彻底通达了经义,以任何一部佛经来印心都没有问题。
禅宗成立前,佛教各家各派都要求佛教修行者在修行路上始终以法印为根本、心印为辅助来印证自己的心行。《正法念处经》云:“如是如是,始发善念,次第乃至一切过尽,得见真谛,圣印印心,彼过相尽。”*[元魏]般若留支译:《正法念处经》卷46《观天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7册,第275页上。佛陀圆寂前,阿难问了四个问题,其中两个是:“如来在世,以佛为师,世尊灭后,以何为师?若佛在世,依佛而住,如来既灭,依何而住?”*[唐]若那跋陀罗译:《大般涅槃经后分》卷上《遗教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册,第901页上,第901页中。佛陀答道:
阿难!尸波罗蜜戒是汝大师,依之修行,能得出世甚深定慧……依四念处严心而住:观身性相同于虚空,名身念处;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名受念处;观心但有名字,名字性离,名心念处;观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名法念处。阿难!一切行者,应当依此四念处住。⑨[唐]若那跋陀罗译:《大般涅槃经后分》卷上《遗教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册,第901页上,第901页中。
“尸波罗蜜戒”即佛教戒律,“四念处”则是证入寂灭涅槃的观修方法,这些都可以说是明确的教证。智者大师也说:“如闻而修,入心成观;观与经合,观则有印;印心作观,非数他宝。”*[隋]释智顗:《摩诃止观》卷7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第98页上。即使是怀则的《天台传佛心印记》,还是通过教理的层层辨析来彰显心印的*参[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主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第934页上—936页下。。
二、宗门的印心
教下依法印心固然稳密,但容易出现两个问题:其一,若无明师指点,学人难以理解经文深义,每以一己知解印心,遂致浅尝辄止、得少为足;其二,如果一心深研经义,往往会陷入知解丛林,甚而迷失佛教本怀,竟成说食数宝之士。
那么,有没有直契如来心印之路呢?禅宗认为本宗所开正是这样一条直截了当之路。据宗门灯录记载,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欲传心印,没有借助语言文字,只是拈花对众微笑。当时,一众悉皆默然,惟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于是佛陀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宋]释普济纂:《五灯会元》卷1,《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80册,第31页上。从此以心传心、心心相印,直到禅宗大播于天下。宗门此说当然不能、也不必诉诸教证来证明,只要师资心心相印即称圆满,此如黄檗禅师所说:“自如来付法迦叶已来,以心印心,心心不异……此一枝法令別行,若能契悟者,便至佛地矣。”*[唐]释希运:《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第382页上。
禅宗的出现给佛教带来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从心印这个角度说,既然禅宗是“传佛心宗”*如释宝臣云:“达磨西来,本自不立文字;《楞伽》东付,以印传佛心宗。”([宋]释宝臣:《注大乘入楞伽经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9册,第433页中—下),禅师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代言人,禅师所说法就与佛法无二无别。譬如,有个叫智彻的僧人听了六祖关于《涅槃经》佛性义的解说,直言其说与佛经大相径庭,六祖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唐]释法海集:《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第359页上。临济义玄禅师更明确说:“道流!约山僧见处,与释迦不别。”*[唐]释慧然集:《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第497页中,第497页中。如此说来,禅师就是佛、法、僧三宝三位一体的化身,只要对禅师信得及,则大事了毕。如大慧宗杲禅师所说:
欲超生死、越苦海,应当竖起精进幢,直下信得及。只这信得及处,便是超生死、越苦海底消息。故释迦老子曰:“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又云:“信能远离生死苦,信能必到如来地。”要识如来地么?亦只是这信得及底……世尊在法华会上只度得一个女子成佛,涅槃会上亦只度得一个广额屠儿成佛。当知此二人成佛亦别无功用,亦只是直下信得及,更无第二念。便坐断报化佛头,径超生死,亦别无道理。*[宋]释宗杲:《示妙圆道人》,[宋]释蕴闻上进:《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3,《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第909页中。
反过来,如果信不及,就不能成就:“如今学者不得,病在甚处?病在不自信处。尔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转,被他万境回换,不得自由。”⑦[唐]释慧然集:《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第497页中,第497页中。到这里,参禅悟道似乎仅仅是弟子对师父有没有信心的问题,至于师父所悟、所传是否究竟圆满的佛心印,乃至是否佛法,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局外人无须、也无权置喙了。
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确如《涅槃经》所说,确有天魔外道诈现禅师像来破灭佛法。只要翻开禅宗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历代都有禅师批判他们眼中不合格的假禅师。例如四祖道信就深怀忧虑地说:
或复有人,未了究竟法,为于名闻利养,教导众生*为于,敦煌写本P2405号《楞伽师资记》作“为相”,误。。不识根缘利钝,似如有异,即皆印可。极为苦哉!苦哉!大祸!或见心路似有明净,即便印可。此人大坏佛法,自诳诳他。*[唐]释净觉:《楞伽师资记》,林世田、刘燕远、申国美编:《敦煌禅宗文献集成》上册P3436号,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第55页。
禅师指出,有的人并未究竟了悟,因为名闻利养所诱,至于不辨弟子根器利钝,见到弟子稍有特异表现,或见其感觉第六意识中稍见光影,就草率印可。他认为这是自欺欺人的行径,对佛法危害极大。六祖慧能对枯木禅也有严厉破斥。当时,有位叫卧轮的禅师影响很大,且有一首代表其禅法思想的偈颂广为流传,所谓“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六祖听到后,明确告诉人们:“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系缚。”并针锋相对地说偈一首:“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唐]释法海集:《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第358页上—中,第353页中。这是说,卧轮禅师根本不知自性清净心的真实面目,也不知菩提就是此心性的作用,本无增减可言,却将菩提视为与心念对立的死灭之境,企图通过断灭念头的有为功夫证达涅槃,必然转加系缚;相反,只有建立起心性自性本来清净、念头即此自性所显菩提的见地,才能明明了了,做到由“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②[唐]释法海集:《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第358页上—中,第353页中。。法眼文益禅师也批评道:“近代之人,多所慢易:丛林虽入,懒慕参求;纵成留心,不择宗匠。邪师过谬,同失指归:未了根尘,辄有邪解;入他魔界,全丧正因。但知急务住持,滥称知识。且贵虚名在世,宁论袭恶于身?不惟聋瞽后人,抑亦凋弊风教。”*[唐]释文益:《宗门十规论》,《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63册,第37页上。他除了喝斥“邪师”,还注意到了学人“不择宗匠”的问题。极力提倡信仰的大慧宗杲禅师,对他眼中的禅病实际上有更为全面、毒辣的喝斥*详见[宋]释蕴闻上进:《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17,《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第884页下—885页上。。
为了避免这种弊端,禅宗大德们还纷纷提出了作为禅师的条件。例如,四祖道信禅师要求:
为人师者,善须识别……故知学者有四种人:有行、有解、有证,上上人;无行、有解、有证,中上人;有行、有解、无证,中下人;有行、无解、无证,下下人也……学用心者,要须心路明净,悟解法相了了分明,然后乃当为人师耳。复须内外相称,理行不相违背。*[唐]释净觉:《楞伽师资记》,《敦煌禅宗文献集成》上册P3436号,第54—55页。
四祖为禅师定出了三个条件:“内外相称,理行不相违背”指真修实证,不停留于口头禅或狂禅,即佛陀所谓“如法而说,如说而行”*关于此义,《大般涅槃经》有全面开展:“善知识者,如法而说,如说而行。云何名为如法而说,如说而行?自不杀生,教人不杀;乃至自行正见,教人正见。若能如是,则得名为真善知识。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义故,名善知识。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闻、智慧,亦能教人信、戒、布施、多闻、智慧。复以是义,名善知识。善知识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乐,常为众生而求于乐。见他有过,不讼其短,口常宣说纯善之事。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25《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册,第510页下—511页上);“心路明净,悟解法相了了分明”即禅门所说“明心见性”,等于教下所谓证见空性,获得根本智;“善须识别”即禅门所说“善辨来机,当机说法”,同于教下所谓圆满差别智。这确实将一个禅师应当具备的见地、修证和行愿都讲得非常全面和透彻。
显然,道信、慧能、义玄、法眼、宗杲等禅师之所以如此自信,敢于说自己与佛无二无别,勇于破斥种种邪师,并为禅师订立标准,除了与佛无二无别的自证经验外,还因为他们都是宗教兼通的大师*南怀瑾云:“每个祖师,从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没有一个人不通教理,经教全通达了,最后摆脱经教而学禅。”(南怀瑾:《如何修证佛法》,《南怀瑾选集》第7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0页),他们本身的见地、修证和行愿与佛经契合无间。
这就涉及到以佛法印印心的问题。禅师要以佛法印来印心,除了避免邪师乱法外,还有如下四个原因:其一,既然禅师传佛心印,而“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唐]释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上之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第400页中。,佛经自然也是禅师之语*[宋]释法云《翻译名义集》卷5:“五祖庄严大师一生训徒,常举维摩曰:‘不着世间如莲华,常善入于空寂行。达诸法相无罣碍,稽首如空无所依。’时有人问:‘此是佛语,欲得和尚自语。’师云:‘佛语即我语,我语即佛语,愿诸智者勿分别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第1141页上),故可以之印心;其二,禅师在堪能传佛心印前有一段修习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需要依法印心,迦叶所以能在灵山会上传佛心印,就与他长期受到佛法熏陶密不可分;其三,祖师传佛心印,如不依佛经印心,难以取信学人、息世讥嫌,是故达摩西来传法即以《楞伽经》印心*此如马祖道一禅师所云:“达磨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又引《楞伽经》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马祖道一禅师广录》,《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69册,第2页中);其四,初心学者未见道前,欲求进修,乃至欲择明师,都必须依佛经印心。此义永明禅师论之最切:“初心始学之者,未自省发已前,若非圣教正宗,凭何修行进道?设不自生妄见,亦乃尽值邪师,故云‘我眼本正,因师故邪’。”*[宋]释延寿:《宗镜录》卷1,《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第419页上。
佛经平等不二,从理论上讲禅宗可以依任何一部佛经来印心;但因实际因缘有别,历史上禅师明确指出的印心佛经只有两部,即《楞伽经》和《金刚经》。
三、《楞伽经》印心
《楞伽经》是菩提达摩祖师用来印心的佛经。首叙此事的《续高僧传》载称:“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552页中。《楞伽经》现存者有三译,分别是刘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四卷《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译十卷《入楞伽经》和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七卷《大乘入楞伽经》,达摩用以印心者为刘宋译本。
考当时中国的佛经已经非常丰富,诸如《阿含》、《华严》、《法华》、《般若》、《涅槃》等经都已传来,达摩为何说“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呢?这当然不能理解为达摩独钟此经,更不能说达摩认为此经最为殊胜。鄙见以为,应当从达摩禅与该经典的关系这个内因与达摩面对的外缘两个方面来寻找个中因由。
要弄清第一个问题,得先确定达摩的著作。达摩传世的著作,据唐代为达摩一系禅师作传记(即《楞伽师资记》)的净觉说,只有《二入四行论》和《楞伽要义》两种,其余皆为他人伪托*净觉说:“此四行是达摩禅师亲说,余则弟子昙林记师言行,集成一卷,名曰《达摩论》也;菩提师又为坐禅众释《楞伽要义》一卷,有十二三纸,亦名《达摩论》也。此两本论文,文理圆满,天下流通。自外更有人伪造《达摩论》三卷,文繁理散,不堪行用。”([唐]释净觉:《楞伽师资记》,《敦煌禅宗文献集成》上册P2045号,第31页)《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册有《楞伽师资记》初步录文。。《楞伽要义》已佚,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二入四行论》却在《续高僧传》和《楞伽师资记》这两部佛教史文献中保存了下来*《续高僧传》所传《四行》,参见[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551页下。。两书见载《二入四行论》在文字上有多少的差别,内容上也有不同*例如“得失从”句之心,敦煌卷子有作“得失从心”(《楞伽师资记》,《敦煌禅宗文献集成》上册,第367、409页),亦有作“得失从缘”(《楞伽师资记》,《敦煌禅宗文献集成》上册,第30、50页),《续高僧传》则作“得失随缘”(《续高僧传》卷1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551页下)。,因此笔者据敦煌写本《楞伽师资记》来考察达摩禅法与《楞伽经》的关系。
达摩禅的内涵,其弟子昙林在《二入四行论》序文中已有很好的概括:“如是安心者,壁观;如是发行者,四行;如是顺物者,防护讥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唐]释净觉:《楞伽师资记》,《敦煌禅宗文献集成》上册P2045号,第29页。其中“顺物”是持守戒律,“方便”是当机对治。前者为佛教共法,无须多说;后者虽然颇有个性,但为禅师机用,乃彻悟后所起之用,亦不必详述。其“四行”指行入,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他说六度万行都可摄入此四行,实际上也如此。从六度来看,报怨行即忍辱行,随缘行囊括了布施、持戒和忍辱三度,无所求行可以摄入禅定度,称法行则属般若行,精进修此四行则属于精进度;他说所有行都要称法而行,实际上是以般若度统摄其余五度。因此,他所谓四行可以说是浓缩了的六度波罗蜜,是大乘菩萨道的共法,亦不必深论。
前述内容都不足证成达摩为何以《楞伽经》印心,能证成者乃其“壁观”一义。“壁观”指理入,包括见地、宗旨与修证方法三个方面。见地上,达摩“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这里的“真性”即佛性或如来藏的异名,意谓一切众生本有自性清净的佛性,只因种种烦恼遮蔽而不能显现。这是典型的如来藏缘起说,与《楞伽经》阐述佛教思想的所依体如出一辙*如《楞伽经》云:“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如大价宝,垢衣所缠。”([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6册,489页上)。宗旨上,达摩所传禅法宗旨,其后学呼为以“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的“南天竺一乘宗”,即后人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楞伽》一经,其后学视为“专唯念惠,不在话言”*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5《法冲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666页中。之经,即以离言绝虑的定慧为宗之经,两者相互应和。修证方法上,达摩提倡“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亦即“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的安心法*释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二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第403页下)。。这种修证方法与《楞伽经》里提持的顿渐相资的瑜伽禅观亦无二致*参[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6册,第485页下—486页上。此题目容后更做探讨。。可以说,正是由于《楞伽经》与达摩禅在见地、宗旨和修证方法上都非常一致,达摩禅师才将该经作为印心经典“传之南北”*[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5《法冲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666页中。。
论及达摩以《楞伽经》印心的外缘,当时的佛教界有两个很突出的特点:首先就是沉溺于义解,禅修风气淡薄。达摩弘化东土之际,略当南朝萧梁与北朝元魏末期,此时佛教界无论南北,佛教义学都极为发达,而栖心禅修之风则较为淡薄。道宣在《续高僧传·义解篇》的《论》中,对南北朝以来这种偏重义学、忽视修证的现象有过扼要的叙述和严厉的批评*参[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548页中—549中。。达摩生当此世,欲传佛心印,自然困难重重,这一点我们可从达摩弟子昙林对其禅法遭遇的叙述窥见一斑:“亡心寂默之士,莫不归信;取相存见之流,乃生讥谤。”*[唐]释净觉:《楞伽师资记》,《敦煌禅宗文献集成》上册P2045号,第29页。灯录甚至说,达摩与慧可师徒都曾多次遭到滞文之徒加害*详参[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3,《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第221页上。。在这么严峻的现实面前,达摩依“髦彦英哲措解无由,愚类庸夫强推邪解”*[唐]释法藏:《入楞伽心玄义》,《大正藏》第39册,第430页中。,同时又“以佛语心为宗”*《马祖道一禅师广录》,《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69册,第2页中。的《楞伽经》付嘱慧可,一方面印证教外别传心印以取信本门弟子,另一方面稍塞依文解义者悠悠之口,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佛教界还有另一个显著特点:虽然不少人也在踏踏实实地修证,但却多在有为的四禅八定中用功,不知如何转入甚至不知尚有无为禅道。如《续高僧传》就记载了二祖慧可禅法遇到如下违缘:
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滞文之徒是非纷举。时有道恒禅师,先有定学,王宗邺下,徒侣千计。承可说法,情事无寄,谓是魔语,乃遣众中通明者来殄可门。既至闻法,泰然心服,悲感盈怀,无心返告。恒又重唤,亦不闻命。相从多使,皆无返者。他日遇恒,恒曰:“我用尔许功夫开汝眼目,何因致此诸使?”答曰:“眼本自正,因师故邪耳。”恒遂深恨,谤恼于可,货财俗府,非理屠害。初无一恨,几其至死,恒众庆快。*[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552页上,第552页中。
慧可承达摩宗旨,以为“万法皆如”,凡夫因“迷本”而不能得见此境;要返本还源,只须“观身与佛不差别”就可“豁然顿觉”[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552页上,第552页中。。因此,他主张依达摩的无得正观来观修。这种禅法在当时的禅学大师道恒听来宛同魔道,故他特派座下通达其禅道的弟子去剿灭慧可禅法。谁料弟子听后不但“泰然心服”、“无心返告”,还反戈一击,指斥道恒所传为邪法。可见,达摩以《楞伽经》印心,对当时的禅道来说更有拨乱反正的意义。诚如南怀瑾先生所说:“当时修道证果的人很多,都是用小乘禅定的路线在修,都是有为法门。虽然方法都对,但欠缺把有为变成无为形而上道的转节。一般大师们,如鸠摩罗什法师,虽然传了佛经,对于形而上道的翻译,也介绍得那么高深,但他修持所走的路线,还是小乘禅观的法门,也就是十念当中,念身的白骨观,或不净观这一类法门。当时,在很难追求形而上道的时候,达摩祖师来了,成为禅宗的开始。”*南怀瑾:《如何修证佛法》,《南怀瑾选集》第7卷,第128—129页。
依《楞伽经》印心的传统,从达摩直到贞观年间的法冲,代代相承,绵绵不绝。此一传统,《楞伽师资记》择要撰述求那跋陀罗、菩提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和神秀七代大德,而《续高僧传·法冲传》则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兹转录于此以见其一斑:
达磨禅师后,有惠可、惠育二人,育师受道,心行口未曾说。可禅师后,粲禅师、惠禅师、盛禅师、那师、端禅师、长藏师、真法师、玉法师。(已上并口说玄理,不出文记。)可师后,善老师(出《抄》四卷)、丰禅师(出《疏》五卷)、明禅师(出《疏》五卷)、胡明师(出《疏》五卷)。远承可师后,大聪师(出《疏》五卷)、道荫师(《抄》四卷)、冲法师(《疏》五卷)、岸法师(《疏》五卷)、宠法师(《疏》八卷)、大明师(《疏》十卷)……那老师后,实禅师、惠禅师、旷法师、弘智师。(名住京师西明,身亡法绝。)明禅师后,伽法师、宝瑜师、宝迎师、道莹师。(并次第传灯,于今扬化。)冲公自从经术,专以《楞伽》命家,前后敷弘将二百遍。*[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666页中。
可见从达摩大师以来,依《楞伽经》修习、印心的“楞伽师”已形成悠久传统,且力量也非常强大。
四、《金刚经》印心
自菩提达摩之后,禅宗的见地与宗旨就没有任何不同,但传授心印的内因与外缘却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内因看,由于慧可、僧璨、道信、慧能等各代祖师都有顿悟自性的真切经验,弘忍更被视为隔世不迷的再来人,因此他们就渐渐将修证方法从达摩传授的瑜伽禅观逐渐转向了般若慧观。早先,二祖慧可虽然已开始提倡“豁然自觉”的顿悟法门*二祖慧可云:“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能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悯此二见之徒辈,申词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552页中。亦参[唐]释净觉:《楞伽师资记》,《敦煌禅宗文献集成》上册P2045号,第32页),但仍旧强调瑜伽禅观功夫,说“十方诸佛,若有一人不因坐禅而成佛者,无有是处”*[唐]释净觉:《楞伽师资记》,《敦煌禅宗文献集成》上册P2045号,第31页。。至三祖僧璨,其禅法已依《维摩诘经》,以不二法门为宗旨,谓“要急相应,唯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30,《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第457页中。,其《信心铭》实际上就是从见地、宗旨和修行方法等各方面再现不二法门的著作。四祖道信依《文殊说般若经》,以一行三昧为宗,认为“亦不念佛,亦不捉心,亦不看心,亦不计心,亦不思惟,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任运;亦不令去,亦不令住,独一清净,究竟处心自明净”*[唐]释净觉:《楞伽师资记》,《敦煌禅宗文献集成》上册P2045号,第36页。。六祖也认为,修道只要有般若的无念行即已足够:“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剎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唐]释法海集:《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第351页上—中。这样的变化自然顺理成章,因真正的般若慧观本来涵摄瑜伽禅观,且达摩拈出的“忘言忘念、无得正观”这个宗旨本身就是般若,只不过达摩认为要令般若现前必须以瑜伽禅观为基础,而从四祖开始则认为无须以此禅观为基础了。
何以如此?从外缘讲,皆因初祖达摩到六祖慧能这一时期,佛教界面临的问题依然如故,或更有过之。史称二祖每每说法结束后,都要对着《楞伽经》哀叹:“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552页中—下。我们看看上文所录楞伽师,几乎每人都有关于《楞伽经》的注疏*当然,这并非说这些楞伽师就是拘执名相之徒。,就知道二祖此言非虚了。不过话说回来,正是由于此际佛教义学极为发达,许多修行者在参禅前已经打下了扎实、深厚的教理基础,禅宗随机解黏去缚的直指法门才能在那时大放异彩。与此同时,就不必再依教理完备、顿渐相资的《楞伽经》,而可改依直显无相实相的《金刚经》来印心了。
《金刚经》前后共有六译,即姚秦鸠摩罗什首译、元魏菩提留支二译、陈真谛三译、隋达摩笈多四译、唐玄奘五译、唐义净六译,前三译皆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次两译名《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后一译名《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禅宗据以印心者乃是首译。禅宗依此经印心,自五祖已然,据《坛经》记载,五祖弘忍“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唐]释法海集:《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第348页上,第350页下,第356页下。。六祖与五祖一脉相承,明确说:
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具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龙下雨于阎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枣叶;若雨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③[唐]释法海集:《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第348页上,第350页下,第356页下。
六祖所说完全没有问题,但我们要清楚,他所谓“闻说《金刚经》”即“心开悟解”者是“大乘人”和“最上乘人”。六祖曾说:“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④[唐]释法海集:《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第348页上,第350页下,第356页下。因此,他所谓大乘人指能够依其所说禅法修行的人。这种人依直显实相无相的《金刚经》印心自然没有问题,如果非此高明流类,岂可效颦?
五、结 语
唐宋之际,佛教兴盛,大师辈出,学人精进,通教者多,此类人的确不少,今天则恐不多见。这倒不能笼统说今人慧根不如唐宋时人,而是因为今人大多没有受过教理熏陶,往往不知《金刚经》所谓“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究何所指,更不用说见到空性以后断除烦恼余习的菩萨十地行了。加上没有具德禅师耳提面命,如果偏执《金刚经》印心,很有可能将第六意识得到的一点轻安视为见道,这就未免冤枉此生了。藕益大师说得好:“真为生死者,放下眼前活计,痛除无始恶习,以心印教,而不为虚言;以教印心,而不为暗证;双超禅教两弊,为智人所可已。”*[明]释智旭:《灵峰藕益大师宗论》卷2,《嘉兴大藏经》第36册,第286页上。窃以为,今时参禅者,若无具德禅师引导,欲避免暗证痴禅、欲达“智人所可”之禅境,较为切实的门径当是回到“藉教悟宗”的达摩禅——从教理的研习入门,以瑜伽禅观的修证为基,依《楞伽经》来印证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