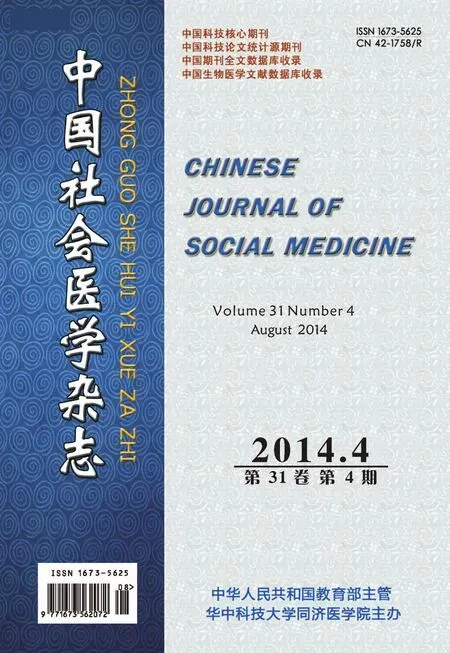我国器官移植协调员作用发挥受限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路绪锋, 张珊
器官移植已成为治疗恶性肿瘤和慢性疾病最终甚至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器官供体短缺依然是限制移植医学的重要因素,为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国家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西班牙等国引入了一种全新模式,即建立一支由受过特殊培训的移植协调员(transplant coordinator)以及内科医师组成的移植协调团队,并明显提高了器官移植率[1]。我国最近几年才引入器官移植协调员(以下称协调员)模式,据报道,在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协调员实际参与协调的几十例都以失败告终,南京等第一批试点城市都面临着没有自愿捐献的尴尬困境[2]。为什么同样的工作模式在国外能大幅提高捐献率,而在我国却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呢?在逐步摆脱对死刑犯器官依赖,广泛推行器官移植捐献的趋势下,器官移植协调员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协调员作用发挥受限的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可行性建议。
1 我国器官移植协调员作用发挥受限的影响因素
作为器官捐献和分配的见证者,协调员的工作包括日常宣传、知识普及、与捐献者家属进行沟通交流、指导捐献者家属填写捐献自愿书、协调与捐献有关的医疗机构及评估小组等相关部门等。正是这些工作内容决定了影响协调员发挥作用的因素,当前我国器官移植协调员作用发挥受限的原因,既有其自身素质等内在因素,也有社会文化环境等外在因素,归结起来主要有4个主要方面。
1.1 协调员的身份未被群众接受
在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后,国外的器官移植协调员作为一个专门职业已经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协调员模式的成功也被众多国家效仿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如乌拉圭在引入移植协调员模式后,有效器官捐赠率从2000年的28.7/100万人上升到2005年的48.1/100万人[3]。而我国的协调员则是一个全新身份,主要由专职协调员和兼职协调员组成,其中专职协调员大都兼有红十字会等机构的正式职务,而兼职协调员主要由重症监护室主任、副主任、护士长担任。由于宣传力度不够,群众普遍不知道协调员的工作性质,在器官买卖现象的影响下,本来作为公益工作者的协调员,可能被误解为从事器官买卖的谋利者,连一些媒体也把协调员称作颇具利益色彩的“劝捐员”。正因为如此,很多协调员会接到一些人要求出卖自身器官的电话,还会遇到捐献者家属提出高额补偿要求的情况,其实这些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对协调员身份以及对器官无偿捐献原则的误读造成的。
1.2 协调员的专业素质不能满足工作需要
在国外,器官移植协调员的主要任务包括:供体资格鉴定、临床评估和选择、家属及司法授权、器官组织的摘取及分配、受体选择[4]。这就要求协调员必须具备全面的综合素质,既要具备医学、伦理学和法学知识,还要接受专业培训,积累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由于我国协调员模式还处于刚起步状态,协调员的综合素质参差不齐,几乎没有协调经验,而健全的培训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目前我国的协调员素质定位是低于国外的:国外的移植协调员承担着脑死亡鉴定、器官评价与保存等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在我国是由专业团队和人员来完成。我国协调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潜在捐献者并与潜在捐献者家属进行沟通和协调,但由于工作经验不足和法律、伦理知识的匮乏,往往导致协调失败。
1.3 传统文化观念是限制协调员作用的重要原因
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孝道,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观念则深深地印刻在人们心中,因此去世后要求“死得全尸”。逝者的亲属也会考虑到舆论压力以及死后火化时器官要完整等社会伦理习俗,坚持完整地为亲人办个风光的葬礼,而我国目前的法律又规定供体生前没有明确捐献意向的必须经亲属签字同意,所以在这种观念的阻碍下,协调员做的大量工作往往都是无用功。另一方面,由于器官捐献的供体是以脑死亡界定的,但是大多数人对“脑死亡”没有清晰的概念,也就谈不上支持脑死亡的规定了,这无疑也是协调员开展协调工作的一大障碍。
1.4 缺乏健全、高效的器官捐献工作系统的支持
协调员要顺利地开展工作,就必须借助健全的工作平台,因为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有力的组织支持以及顺畅的信息沟通渠道。纵观在器官捐献方面取得良好成效的国家,无一不具有健全、高效的器官捐献系统,如西班牙的ONT能够确保移植过程中的所有人员成为一个整体,在国家、地区、医院等不同水平上覆盖所有相关事项及参与的工作人员。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这样的工作系统,也就是说协调员缺少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支撑。在目前的器官捐献模式中,协调员的管理单位红十字会只是作为第三方见证,没有办法介入到实际操作的医疗管理中,也就是说协调员的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取决于卫生主管部门对器官捐献的信息传达和交换。此外,协调工作还会涉及公安、交通、民政等部门,由于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所以仅仅依靠协调员个人的人脉资源和积极性往往收效甚微。
2 促进协调员作用发挥的可行性对策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对协调员作用发挥形成限制的因素主要有4个方面,为了破除这些障碍,笔者提出以下对策。
2.1 加大宣传力度,为协调员开展工作提供舆论支持
一方面,要广泛宣传器官移植协调员的作用职能,使协调工作为群众所理解。协调员必须经过资质认证、持证上岗,并且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协调员的公益性质及其生命接力作用,如通过设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普及宣传,让人们知道协调员的工作性质与职能,消除群众误解。另一方面,要广泛宣传器官捐献的道德魅力,让群众知道器官捐献的意义所在,传统文化资源中“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观念都能为器官捐献提供佐证。相信只要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器官移植协调工作一定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如有研究者在北京、上海和武汉的一个调查显示,66.6%的人认为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捐献自己的器官[5]。此外,要发挥媒体的积极引导作用,树立正面典型,如2012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何玥等,宣传“只需要一颗博爱的心,就能救助一个生命”的理念,让更多的人自觉支持协调员的工作。
2.2 加强正规化建设,使协调员队伍练好基本功
协调员是器官移植的主体角色,是器官捐献能否成功的关键,必须提高协调员的整体素质。因此,器官协调员的选拔过程要严格,同时加强整个队伍的系统化培训,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正规化队伍。结合目前我国协调员的构成情况,可以继续实行专职和兼职并存的模式,同时着眼于未来,使协调员队伍朝着素质多元化发展。既要进行一般性的培训,又要结合协调员的定位突出培训重点。结合我国协调员的定位,即主要负责与潜在捐献对象家属沟通的工作,要重点培训协调员以下能力:一是信息搜集能力,通过多途径搜集相关信息,尽可能发现潜在捐献者,发掘捐献者家属所面临的需求等;二是组织认知能力,能够通过交流,准确辨别直系亲属中最有决策影响力的人,在非直系亲属中辨明能够直接影响直系亲属中决策者的人;三是人际理解能力,必须能够感同身受地体会捐献者家属的感受,并通过语言、动作等准确把握家属的真实想法,采用恰当的行为与家属产生共鸣[6]。
2.3 加快建设器官捐献移植系统,为协调员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在我国当前模式下,隶属红十字会的专职协调员与医院方面在器官捐献试点过程中配合还不到位,信息对接不够顺畅,加之器官移植是一个涉及社会、家庭、司法、医疗等多方面的统筹协调过程,而协调员工作的一个差错就可能导致移植手术机会的丧失,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能在整体上进行统筹和协调移植全过程的运转系统,为协调员提供健全的工作平台。在这方面要注意学习国外可供借鉴的模式,比如澳大利亚的心肺器官联合移植率之所以能位居世界前列,就是因为他们采取了有效的移植协调及器官分配系统,实现了器官分配的最优化[7]。目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正在建立面向协调员队伍的全国捐献信息系统,不同于以往捐献信息依靠手工填报的局面,协调员可以将所有捐献数据录入信息系统,采集捐献过程中涉及的相关信息,如捐献者基本情况、意愿确认、器官分配等,并将整个器官捐献的信息进行全国联网,使我国整个人体器官捐献的动态变化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出来。全国器官捐献信息系统建立后,还应与“分配与共享系统”实现对接,这样才能保证器官流向和使用情况的公开透明,而且不同地方的器官捐献和需求情况在统一调配下,才能实现器官的最优化配置。
2.4 完善法律规范,为协调员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协调员的工作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则很难顺利开展,因为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不仅涉及到捐献者与器官移植接受者的权利和义务,而且涉及到协调员的身份地位和工作职责、权利等能否得到法律支持。虽然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和卫生部共同颁布了针对协调员工作的详细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管理办法(试行)》,对协调员的条件和职责、组织管理工作进行了规定,但是对协调员的合法权益却规定较少。直到2012年天津市颁布的《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才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地位,指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医务人员依法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其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支持和协助,并提供便利条件”,并具体规定了协调员的选定与管理、资格条件、工作职责、权利保障等,为协调员工作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因此,整个国家层面也应加快器官捐献和协调员工作的立法进程,其他地方也应根据自身实际,从立法角度来保护器官捐献协调员开展此项工作的权利。
器官移植协调工作关乎生命的延续,其中协调员承担着为生命接力的角色,所以协调员不仅要全方位提升医学、法律和伦理学素质,还要强化沟通能力和技巧。当然,协调员作用的充分发挥还有赖于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完善捐献系统的支持以及相关法律规范的完善。总之,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任重道远,相信在各方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实现器官捐献率的稳步提升。
[1] FilipponiF,De Simone P,Mosca F.Appraisal of the coordinator-based transplant organizational model[J].Transplant Proc,2005,37(6):2421-2422.
[2] 李静.器官捐献协调员:试点一年零捐献记录[J].瞭望东方周刊,2012-12-10.
[3] MizrajiR,Pérez S,Alvarez I.Activity of transplant coordinationin Uruguay[J].Transplant Proc,2007,39(2):339-340.
[4] Elizalde J,LorenteM.Coordination and donation[J].An Sist Sanit Navar,2006,29(Suppl2):35-44.
[5] 刘亚兰,雷洪,裘法祖.北京上海武汉三城市中青年对器官移植的认识和意愿的调查[J].中华医学杂志,1997,77(1):22-27.
[6] 罗爱静.移植协调员胜任特征分析[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2,22,(11):107-110.
[7] 李恩昌,吉鹏程,韩淑琴,等.多维视角看中国器官捐献的价值导向[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3,30(6):374-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