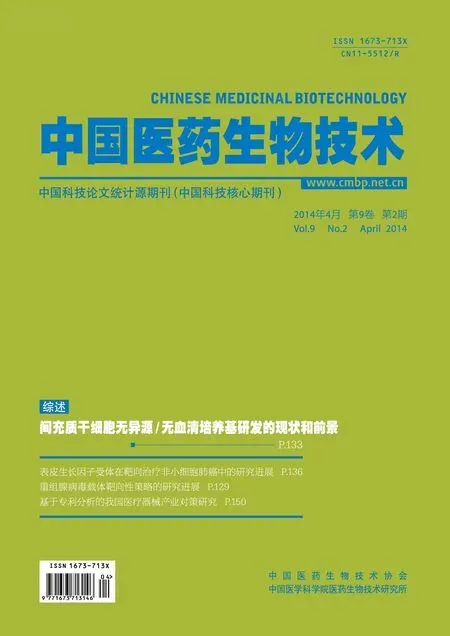H7N9禽流感疫情引发人们的思考
邵惠训
H7N9禽流感疫情引发人们的思考
邵惠训
100012 北京实验动物研究中心,Email:huixunshao@sina.com
2003 – 2004 年,在亚洲广袤地区的家禽中流行了 H5N1 禽流感,并传染给人类,人们仍然记忆犹新。从 2013 年 2 月开始,在中国部分地区又掀起了不祥的波澜,H7N9 和 H10N8 禽流感病毒袭击了人类。H7N9 禽流感曾在禽类发现,但从未传染给人。2013 年春天,该病毒首次袭击了人类。H7N9 病毒对禽类致病力很低,禽作为传染源十分隐蔽。而人类患上 H7N9 禽流感后,易引发多脏器衰竭,病情发展迅速,病死率很高[1-5]。依据呼吸道传染病发病特点分析,今后出现大规模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的可能性很小。散发病例还会发生,疫情已趋于稳定。人类与流感又一回合斗争表明,H7N9 禽流感是一种可控可治的传染病。
1 流感病毒的基因结构与功能
流感病毒由内核、中层蛋白壳和囊膜组成。内核由螺旋状的单股负链 RNA,以及其编码的相应蛋白组成。病毒 RNA 由 8 个基因片段(PB2-PB1-PA-HA-NP-NA-M-NS)连接而成。8 个基因片段分别编码 10 种蛋白,其中 8 种是病毒组成部分,另两种是非结构蛋白。这 10 种蛋白分别为表面蛋白、内部蛋白和非结构蛋白。每一条 RNA 基因都以核糖核蛋白复合体形式存在。每个基因片段两端都有相对保守的非编码序列,每个片段至少有一个开放式读码框架(ORF)。内核是由核蛋白(nucleoprotein,NP)、多聚酶蛋白组成的核衣壳蛋白(ribonucleoprotein,RNP)与 RNA 连接而成。中层蛋白壳含有基质蛋白(matrix,M1)和膜蛋白(membrane protein,M2)。外层为来自宿主细胞的双层类脂囊膜,囊膜上有血凝素(hemagglutinin,HA)和神经氨酸酶(neuraminidase,NA)。HA 有 17 个亚型(HA1-17),NA 有 10 个亚型(NA1-10)。HA 是基因表达产物中最大的I型糖蛋白,是诱生机体保护性免疫的主要蛋白抗原,能刺激机体产生中和抗体。在流感病毒吸附和穿膜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在病毒感染过程中,HA 水解为两条肽链:HA1 和 HA2。HA1 主要刺激机体产生中和抗体。H3N2 流感病毒的 HA 头部有 5 个抗原结合位点和受体结合位点。HA1 基因变异性最大,HA2 基因则相对保守[6]。HA1 具有与宿主细胞受体结合的能力,HA2 参与细胞膜融合。HA 受体能与宿主细胞受体唾液酸(sialic acid,N-乙酰神经氨酸,N-acetylneuraminic acid)结合,使病毒牢牢吸附在宿主细胞表面。不同种类流感病毒的 HA 具有不同唾液酸酶分子结构,结合不同宿主细胞的唾液酸受体。NA 是II型糖蛋白,氨基端插入囊膜内,羧基端游离在囊膜外。NA 能水解宿主细胞表面糖蛋白末端的唾液酸,有利于子代病毒的成熟、释放和扩散。NA 也具有免疫原性,能诱导宿主产生抗体抑制酶。诱导的特异性抗体虽不能给机体提供完全免疫保护,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患者临床症状和降低病死率。NP 具有型特异性,基因片段最为保守,是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CTL)识别的主要位点,具有3 个独立的抗原位点。NP 抗体不能给宿主提供免疫保护。M 是基质蛋白,分别翻译 M1 和 M2。M1 是病毒的主要结构蛋白,是病毒的骨架,维持病毒形态,具有型特异性。M2 是跨膜离子通道蛋白,氨基酸序列保守。RNA 多聚酶(PA、PB1 和 PB2)主要参与病毒 mRNA 合成和病毒基因组 RNA 复制。NS 有两个 ORF,编码非结构蛋白 NS1 和 NS2。NS1 调节 mRNA 的剪切和翻译,对病毒致病力起着重要作用。NS2 是出核转运因子。通过研究病毒非结构蛋白的结构与功能,对了解病毒复制和开发新型抗病毒药物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病原体核蛋白和膜蛋白不同,流感可分为甲、乙和丙三型。甲型流感病毒容易变异,常引起世界性流行。乙型流感病毒比较稳定,能引起地方性或局部地区流行。丙型流感病毒仅引起散发病例。甲型流感是防治重点[7]。
2 流感病毒的遗传变异与传播
流感病毒袭击人体时,病毒首先吸附在人的鼻腔和咽喉内壁细胞。在病毒颗粒和宿主细胞表面都含有受体。病毒和宿主细胞的受体相匹配时,病毒才能吸附在宿主细胞膜上,然后宿主细胞将病毒吞噬,对病毒基因进行加工和改造,形成新的病毒颗粒。禽流感和马流感病毒的受体为唾液酸 α-2,3-半乳糖苷(α-2,3-galactose-sialic acid),人流感病毒的受体为唾液酸 α-2,6-半乳糖苷。猪的呼吸道黏膜细胞表面具有上述两种受体,对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都具有亲和力。猪能感染人、禽、马流感病毒,猪流感病毒又能感染人、禽、马。根据病毒基因进化研究推论,所有哺乳动物的流感病毒均来源于禽流感病毒。猪是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的中间宿主和基因库[8]。水禽是禽流感病毒的天然宿主。禽流感病毒在猪体内适应后获得了感染人的能力。猪可能成为人流感病毒的储存宿主。后来,人们又发现,人的呼吸道黏膜细胞除表达唾液酸 α-2,6-半乳糖苷外,下呼吸道肺泡黏膜细胞也能表达唾液酸 α-2,3-半乳糖苷,为禽流感病毒跨越种系传播给人类提供了分子病毒学依据。在野禽体内,能分离到各种亚型流感病毒的 HA 和 NA。所有人类流感病毒都能引起禽类感染,大部分为隐性感染,但不是所有的禽流感病毒都能引起人类流感。这可能与人体呼吸道黏膜细胞缺乏对禽流感病毒亲和的受体有关。因为人的呼吸道上皮细胞不含有禽流感病毒特异性受体,病毒不被人体细胞识别并结合。能在人群中传播的流感病毒,其基因组都含有人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流感病毒 HA 水解成 HA1 重链和 HA2 轻链,才具有感染性。大多数流感病毒 HA 在禽体内不水解,病毒对禽类不致病。野生水禽的流感病毒能感染家禽和哺乳动物。人流感病毒的 HA 具有高度水解性。人类和禽类流感病毒基因重组后,导致 HA 水解活性改变,对禽类的致病性也发生改变,由不致病到致病,由低致病性到高致病性。流感病毒能在水禽的呼吸道和肠道上皮细胞内复制繁殖,水禽只是隐性感染,自身症状很不明显。水禽通过迁徙到处传播病毒,是流感病毒最大的储存宿主和传播者,构成庞大的流感病毒基因库,是造成人类流感大流行的根源。在禽类不同个体之间,不同品种之间,流感病毒可以相互传播。在同一种群,可同时感染两种或两种以上亚型的流感病毒,造成双重或多重感染,这为流感病毒基因进化重组提供了有利条件。
流感病毒的基因变异有一定规律,并有周期性。流感病毒适应能力很强,基因容易发生变异,编码 HA 的基因片段变异率很高。流感病毒变异有抗原性变异、温度敏感性变异、宿主范围变异和对非特异性抑制物敏感性变异。但在这些变异中,最主要的是抗原性变异。病毒变异的程度并不大,只是 RNA 核苷酸序列发生较小改变时,称为抗原漂移。基因序列变异幅度小,属于量变,只在亚型范围内发生变异。在流感病毒演变过程中,病毒 RNA 核苷酸序列发生了改变,其编码的氨基酸序列随之发生改变。当核苷酸序列的变异达到一定程度,导致病毒抗原决定簇改变,抗原性也发生了变化。抗原性的改变,可帮助病毒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
当病毒变异达到一定程度,可形成新的亚型。RNA 核苷酸序列变化显著,称为抗原转换。病毒基因序列变异幅度大,属于质变,病毒的表面抗原结构一种或两种发生变异,与前次流行株的抗原迥异,形成新的亚型。甲型流感病毒两个不同亚型的基因变异速度是不一致的,H3N2 亚型进化速度快,而 H1N1 的进化速度比较慢。在同一亚型中,HA 的进化速度比 NA 快,PB2 最慢,这与病毒逃避宿主免疫清除而进行的适应性变异紧密相关。1978 年前苏联流行的 H1N1 与香港流感病毒 H3N2 同时感染人,在人体内病毒基因进化重组而成 H3N1,这是在自然条件下发生的变异。此后,从朝鲜饲养的猪体内也分离到 H3N1 病毒[9]。从美国饲养的猪体内分离的 H2N3 病毒,是由禽流感和猪流感病毒重组而成,在 H2 226 位点上含有脱氢亮氨酸,能与哺乳动物细胞上的 α-2,6-半乳糖苷受体结合,此病毒有可能在哺乳动物中传播[10]。抗原漂移与抗原转换往往交替进行。这次 H7N9 新型重组病毒属于抗原转换,在遗传学意义上具备了 H9N2 病毒的特征。H9N2 病毒传播广泛,能使哺乳动物感染,还有传染给人的潜在威胁。人类流感病毒能感染多种动物。在动物体内,人类流感病毒和动物流感病毒的遗传信息进行交换和重组。当两种或两种以上亚型的流感病毒感染同一宿主细胞时,不同种类流感病毒基因片段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病毒亚型。人群对新的病毒缺乏免疫力,从而出现疾病流行。流感流行有明显季节性。对流感进化动力学研究表明,流感季节高峰主要受甲型流感病毒适应性变异的影响[11-12]。
引发这次疫情的 H7N9 禽流感病毒是一种新型的进化重组病毒,主要由 4 个不同来源的流感病毒重组而成。从患者分离的 H7N9 病毒与发病地区活禽市场的鸡分离的 H7N9 病毒基因序列非常接近,同源性达到 99.4%。新病毒 RNA 基因部分来自 H7N3 和 H11N9,另外 6 个基因片段(PB2、PB1、PA、NP、M 和NS)来源于我国家禽携带的 H9N2。这 6 个基因片段也非单一来源,其中一个基因片段可能来源于江苏周边的鸡群,其他 5 个基因片段来源于上海、浙江附近的鸡群。造成 6 个基因片段多样性的原因可能与家禽的贩卖和运输有关[13-15]。也有学者认为,H7 来自浙江的家鸭 H7N3 病毒,N9 来自南韩的野鸟 H7N9 病毒[16]。其 HA 近似于 A/duck/Zhejiang/12/2011 (H7N3) 病毒株,NA 近似于 A/wild bird/Korea/A14/2011 (H7N9) 病毒株,其余 RNA 基因片段近似于 A/Brambling/Beijing/16/2012-like viruses (H9N2) 病毒株。流感病毒的基因重组成为全新的对人类高致病性的 H7N9。新型的病毒受体结合位点获得了部分人类流感病毒的特征。如果 H7N9 禽流感疫情继续扩散和延续,禽流感病毒发生变异并在人间传播的危险将大大增加,应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3 H7N9 禽流感疫情引发的思考
3.1 加强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保护迫在眉睫
我国处在亚洲大陆候鸟迁徙的东线、中线和西线通道上。每年春季,大批候鸟从东南亚途经我国,飞往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和西亚地区生息繁衍。近几十年来,由于各地区经济开发和人为破坏,生态系统逐年恶化,湿地面积不断缩小,物种和遗传多样性以惊人的速度减少,野禽迁徙赖以生存的线路和通道受到侵害。我国应通过立法的方式遏制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行为,恢复湿地和湿地上的植被,进而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保持野禽迁徙通道畅通,还要保护人类本身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的稳定。在候鸟栖息地、繁殖地和迁飞停歇地落实保护管理措施,严防网捕野鸟,严禁下药毒杀等危害候鸟生存的不法行为。尽量减少人类与野禽近距离接触。家禽饲养场应设置防护网,防止野禽入侵。
3.2 改变陋习和不科学的生产、生活习惯和方式
在我国有些地区,家禽、家畜饲养场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饲养家禽、家畜的密度很高,拥挤不堪,动物免疫力低下,加上催熟激素和抗生素滥用,家禽、家畜的生长周期很短,体质下降,容易受到各种病原体侵害,容易患上各种传染性疾病。鸡、鸭、鹅混养和恶劣的运输,也增加了家禽间传染病传播。今后应发展大型的、封闭式的、管理规范的家禽、家畜饲养场,改善动物饲养条件,降低饲养密度,制订严格的管理措施,加强监管,预防各种动物传染病发生。活禽交易市场是传播 H7N9 禽流感的载体,在城市应关闭活禽交易市场,采用现代化销售方式,销售冰鲜鸡。提倡公众购买冰鲜鸡。个人不要宰杀活禽。
有些地区对野生动物乱捕滥杀,枪击、投毒、下夹子时有发生。增加了人和野生动物接触的机会,也增加了动物传染病传给人类的机会。野鸭在禽流感病毒的储存和传播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野鸭对禽流感病毒感染不敏感,在幼龄时期就感染了禽流感病毒,病毒又能在野鸭的肺和肠道细胞内复制繁殖,野鸭长期携带病毒,从粪便大量排出。人流感病毒也能在野鸭上呼吸道黏膜细胞进行复制,野鸭在甲型流感病毒变异中的作用,应引起人们关注。当人们关爱野鸭的同时,也要考虑野鸭对公共卫生带来的威胁。因此,对野鸭的种群和数量应有所控制,不要让所有的水域成为野鸭的栖息场所,尽量减少人类与野鸭近距离接触。宠物(猫和狗)、灵长类和啮鼠类动物也能携带流感病毒,能否传播病毒,有待观察[17-18]。自然界越来越多的报复性行为使人类不得不反思,改变人们不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防止人禽畜共患疾病的传播,善待动物,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
3.3 加强对人流感的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监测
病毒基因变异是生物适应外界环境和维持自身生存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生物进化的体现。流感病毒在宿主体内复制繁殖时,必然遭到宿主免疫系统的抵抗。
各地都要建立流感疫情监测网,对流感疑似病例和突发疫情及时作出流行病学和实验室诊断。及时隔离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及时关闭活禽交易市场,研制快速诊断试剂,并筛选出敏感的抗流感病毒药物,对患者及时进行抗病毒治疗。老年人特别是免疫功能低下的,有免疫性疾病的人群,尽量减少跟活禽接触。对分离到的流感病毒进行基因分析,了解病毒变异情况,及时作出相应防治措施,是否要尽快制备特异性疫苗作出评估[19]。北京疾控系统曾从健康儿童呼吸道分泌物检出 H7N9 病毒,这是个别现象,还是较普遍现象,尚有待观察。H7N9 病毒能在雪貂的呼吸道黏膜细胞内复制,在雪貂的气管、肺部、淋巴结与大脑也出现病毒的 RNA,并通过直接接触使邻笼的雪貂感染,不能排除此病毒通过空气飞沫直接传播的可能性。雪貂感染 H7N9 病毒后,24 h 内出现较高病毒载量排毒,随后出现发热、喷嚏、流涕、倦怠、咳嗽、肺炎等症状。至于在人类之间,H7N9 病毒能否通过空气传播,尚有待观察。
3.4 加强禽流感的监测
人流感的发生与原先在动物中传播的动物流感病毒变异有关。H7N9 和 H10N8 流感患者曾有与动物或动物场所接触史。曾从发病地区的活禽市场的鸡和鸽检出 H7N9 病毒。人类在饲养猪、禽动物过程中,人畜、人禽频繁接触,猪流感和禽流感病毒发生了变异,获得了对人的致病性,获得了在人群中传播的能力,成为人流感病毒。这类事件有可能再次发生,对禽流感病毒袭击人类应保持高度警惕。人在宰杀活禽中很容易受到感染。对暴露于病禽的饲养场工作人员、禽类屠宰者及其家庭成员进行严密监测。一旦出现发烧和呼吸道感染症状或眼部感染症状,应及时报告当地的疾病控制中心。禽流感病毒变异后,可能成为人流感病毒,人体对新的流感病毒缺乏免疫力,可能引起人流感世界性流行。流感病毒能通过空气传播,一旦传染性极强的流感病毒传播开来,其蔓延速度是十分惊人的。目前 H7N9 禽流感病毒尚未具备人传人能力,但禽传人的传播途径十分明确。预防禽流感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放松心情,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保证充足睡眠,提高自身免疫力。根据气候变化及时增减衣服,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和膳食均衡。食用禽、肉、蛋时,要充分加热煮熟。
3.5 加强猪流感的监测
猪流感能传给人类,人流感病毒也能使猪感染[20]。猪在禽流感病毒和人流感病毒基因重组中起中介载体作用[21]。有些饲养场条件很差,饲养密度很高,猪的抵抗力很低,容易罹患各种传染性疾病。有些饲养场将鸡笼建在猪圈上,鸡粪直接落在猪槽内,容易造成禽流感在猪群中传播。如果禽流感病毒和人流感病毒在猪体内发生基因重组,变异成为能在人群中传播的新型流感病毒,这种新型流感病毒具有不同的血凝素表面糖蛋白,人群对这种新病毒缺乏免疫力,危害就很大[22]。1957 年流行的亚洲甲型流感病毒(H2N2)基因的 8 个片段中有 3 个来自鸭流感病毒,而其余 5 个片段则来自H1N1 人流感病毒,猪是否参与了这次基因重组,很值得怀疑。这次 H7N9 禽流感疫情,未发现猪群参与其中,因为在 H7N9 病毒中,没有发现猪的基因成分。以往实验表明,猪能感染 H7N9 病毒,引起猪呼吸道感染和轻度肺炎,但病毒不会在猪与猪之间进行传播。应改善养猪场饲养条件,给猪群一定生长空间,并加强对猪流感监测,预防猪流感传给人类。
3.6 加强流感疫苗研制
流感流行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而且严重影响养禽业的发展。接种流感疫苗能明显降低流感发病率和减轻患者临床症状。由于流感病毒不断发生变异,只有经常掌握流感病毒变异动态,选育出新的流行病毒株,才能及时制备出有特异性预防作用的疫苗。制备出有效、安全、稳定的流感疫苗,对于控制流感流行十分重要[23]。浙江大学李兰娟团队在成功分离出 H7N9 禽流感病毒的基础上,采用反向遗传技术,研制出 H7N9 人用流感疫苗种子株,已经通过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的安全性雪貂评估实验,以及中国食品药品研究院的全面检定。打破和改变了流感疫苗株需由外国引进的历史,为及时应对新型流感疫情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理想的流感疫苗应对各种亚型的甲型流感病毒感染都有良好的免疫效果。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大批量生产。流感病毒主要抗原有 MP、NP、HA 和 NA。HA 和 NA 容易变异,需要每年更换流感疫苗株。而 M2、NP、多聚酶蛋白和 HA 蛋白保守区非常稳定和保守。M2 作为疫苗抗原可预防所有甲型流感病毒的袭击。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M2 蛋白膜外区的基因 M2e 与 HBc 基因连接,然后将这种融合基因导入大肠杆菌内,经细菌培养,大肠杆菌产生 M2e-HBc 融合蛋白。将融合蛋白制成流感通用疫苗,能刺激机体产生广谱的流感抗体,预防各种亚型流感病毒(包括季节性流感和流行型流感病毒)引发的疫病[24-27]。
3.7 对确诊病例及时进行抗流感病毒治疗与危重病例的抢救
达菲(磷酸奥司他韦,oseltamivir)是一种高效口服的流感病毒 NA 抑制剂,一旦确诊 H7N9 禽流感患者,应尽早(发病 3 天内)进行抗病毒治疗。在达菲治疗前和治疗过程中,对病毒载量和耐药基因位点进行密切监测,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提高救治成功率。扎那米韦(zanamivir)通过口腔吸入或滴鼻给药,也要在疾病早期给药[28-29]。H7N9 禽流感对金刚烷(adamantane)有抗药性,用金刚烷治疗,效果不佳。H7N9 禽流感确诊病例均应转入定点诊治医院隔离治疗,危重病例(包括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 病例)应入住 ICU 病房,接受通气支持治疗,降低病死率[30]。
4 结语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人畜禽共患的急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流感病毒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在人类历史上曾引发多次大流行,夺去了大量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沉重的灾难和精神创伤。流感危害养禽业的发展,造成养禽业毁灭性灾害。流感流行有明显季节高峰,秋季和冬季为高发季节。流感病毒的基因变异和进化重组是导致流感流行或暴发的基础。加强流感疫情监测,采取综合性防治措施,制备出有效、安全、稳定的流感疫苗,筛选出敏感的抗流感病毒药物,早期患者进行及时抗病毒治疗,对于控制流感流行和治愈危重病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H7N9 流感新疫苗尚在研制开发中,前景良好。从长远考虑,还是要研制流感通用疫苗,一次疫苗接种,终生获得免疫。
[1] Li Q, Zhou L, Zhou M, et al. Epidemiology of human infections with avian influenza A (H7N9) virus in China. New Eng J Med, 2014, 370(6):520-532.
[2] Ke Y, Wang Y, Zhang W, et al. Deaths associated with avian influenza A (H7N9) virus in China. Ann Intern Med, 2013, 159(2):159-160.
[3] Cao R, Cao B, Hu Y, et al. Human infection with a novel avian-origin influenza A (H7N9) virus. New Eng J Med, 2013, 368(20):1888-1897.
[4] Zhu Y, Qi X, Cui L, et al. Human co-infection with novel avian influenza A H7N9 and influenza A H3N2 viruses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 Lancet, 2013, 381(9883):2134.
[5] Koopmans M, de Jong MD. Avian influenza A H7N9 in Zhejiang, China. Lancet, 2013, 381(9881):1882-1883.
[6] Yan RQ, Du XD. Research progress in genomic structures and proteins of influenza virus. Prog Vet Med, 2004, 25(1):32-35. (in Chinese)
闫若潜, 杜向党. 流感病毒基因组结构及其编码蛋白研究进展. 动物医学进展, 2004, 25(1):32-35.
[7] Shao HX. The evolution of influenza viruses. Health, 2012, 4(Special Issue):1000-1005.
[8] Cong Y, Wang G, Guan Z, et al. Reassortant between human-like H3N2 and avian H5 subtype influenza A viruses in pigs: a potential public health risk. PLoS ONE, 2010, 5(9):e12591.
[9] Shin JY, Song MS, Lee EH, et al.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ovel H3N1 swine influenza viruses from pigs with respiratory diseases in Korea. J Clin Microbiol, 2006, 44(11):3923-3927.
[10] Ma W, Vincent AL, Gramer MR,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H2N3 influenza A viruses from sw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07, 104(52):20949-20954.
[11] Rambaut A, Pybus OG, Nelson MI, et al. The genomic and epidemiological dynamics of human influenza A virus. Nature, 2008, 453(7195):615-619.
[12] Bedford T, Cobey S, Beerli P, et al. Global migration dynamics underlie evolution and persistence of human influenza A (H3N2). PLoS Patho, 2010, 6(5):e1000918.
[13] Kim HR, Park CK, Lee YJ, et al. Low pathogenic H7 subtype avian influenza viruses isolated from domestic ducks in South Korea and the close association with isolates of wild birds. J Gen Virol, 2012, 93(Pt 6):1278-1287.
[14] Kugeyama T, Fujisaki S, Takashita E, et al. Genetic analysis of novel avian A (H7N9) influenza viruses isolated from patients in China, February to April 2013. Euro Surveill, 2013, 18(15):20453.
[15] Van Ranst M, Lemey P. Genesis of avian-origin H7N9 influenza A viruses. Lancet, 2013, 381(9881):1883-1885.
[16] Chen Y, Liang W, Yang S, et al. Human infections with the emerging avian influenza A H7N9 virus from wet market poultry: clinical analy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viral genome. Lancet, 2013, 381(9881):1916-1925.
[17] Amonsin A, Songserm T, Chutinimitkul S, et al. Genetic analysis of influenza A virus (H5N1) derived from domestic cat and dog in Thailand. Arch Virol, 2007, 152(10):1925-1933.
[18] Cardona CJ, Xing Z, Sandrock CE, et al. Avian influenza in birds and mammals. Comp Immunol Microbiol Infect Dis, 2009, 32(4):255-273.
[19] Surveillance Group for New Influenza A (H1N1) Virus Investigation in Italy. Virological surveillance of human cases of influenza A (H1N1)v virus in Italy: preliminary results. Euro Surveill, 2009, 14(24). pii: 19247.
[20] Novel Swine-Origin Influenza A (H1N1) Virus Investigation Team, Dawood FS, Jain S, et al. Emergence of a novel swine-origin influenza A (H1N1) virus in humans. N Engl J Med, 2009, 360(25): 2605-2615.
[21] Lee JH, Pascua PN, Song MS, et al. Isolation and gen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H5N2 influenza viruses from pigs in Korea. J Virol, 2009, 83(9):4205-4215.
[22] Thacker E, Janke B. Swine influenza virus: zoonotic potential and vaccin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control of avian and swine influenzas.J Infect Dis, 2008, 197 Suppl 1:S19-S24.
[23] Nuño M, Chowell G, Gumel AB. Assessing the role of basic control measures, antivirals and vaccine in curtailing pandemic influenza: scenarios for the US, UK and the Netherlands. J R Soc Interface, 2007, 4(14):505-521.
[24] Du L, Zhou Y, Jiang 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al influenza vaccines. Microbes Infect, 2010, 12(4):280-286.
[25] Ebrahimi SM, Tebianian M. Influenza A viruses: why focusing on M2e-based universal vaccines. Virus Genes, 2011, 42(1):1-8.
[26] Lambert LC, Fauci AS. Influenza vaccines for the future. N Engl J Med, 2010, 363(21):2036-2044.
[27] Turiey CB, Rupp RE, Johuson C, et al. Safety and immunogenicity of a recombinant M2e-flagellin influenza vaccine (STF2.4×M2e) in healthy adults. Vaccine, 2011, 29(32):5145-5152.
[28] Schmidt AC. Antiviral therapy for influenza: a clinical and economic comparative review. Drugs, 2004, 64(18):2031-2046.
[29] Stiver G. The treatment of influenza with antiviral drugs. CMAJ, 2003, 168(1):49-56.
[30] Cao HN, Lu HZ, Cao B, et al. Clinical findings in 111 cases of influenza A (H7N9) virus infection. N Engl J Med, 2013, 268(24): 2277-2285.
2013-06-21
10.3969/cmba.j.issn.1673-713X.2014.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