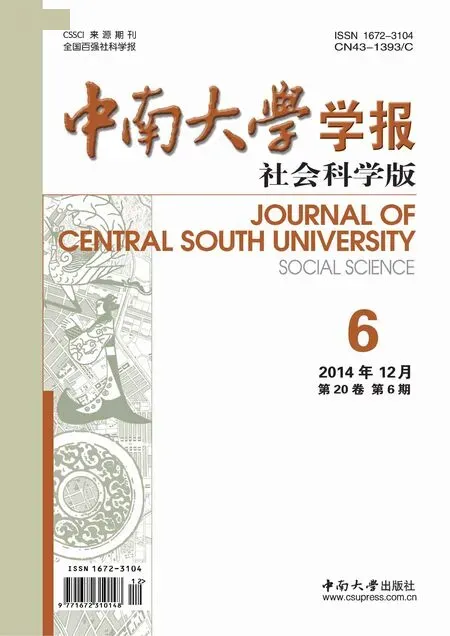试论清代浙西词派的重新分期
刘深
(广西大学行健学院,广西南宁,530005)
试论清代浙西词派的重新分期
刘深
(广西大学行健学院,广西南宁,530005)
在晚清词坛,仍有众多词家遵循浙派词风,浙派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浙派对词坛的影响依然很大。通过考察清代词风的嬗变,应以嘉庆七年为界,将浙西词派分为前后两期。在浙派前期的发展中,康熙十七年和雍正三年是重要的节点,前者标志浙派的形成,后者标志浙派鼎盛期的到来。而在浙派后期的发展过程中,道光十一年与光绪九年均是浙派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前者标志浙派与常派在词学理论上并峙局面的形成,后者标志了浙派在创作上亦进入了衰落期。
晚清;浙派;常派;词史;词风;词派
浙西词派作为清代词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学界对其词史发展形态也早有了论述。如清人蒋敦复就曾提出:“浙派词,竹垞开其端,樊榭振其绪,频伽畅其风,皆奉石帚、玉田为圭臬。”[1](3636)清词研究名家严迪昌在《清词史》中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前期以朱彝尊为旗帜,中期以厉鹗为宗匠,晚期则以吴锡麒为中介环节,而以郭麐为词风嬗变的代表”,并强调“这三个时期恰好都是50年上下为一期,基本上笼盖了浙派词史约经三个甲子的总流程”[2](436)。
受《清词史》的影响,严氏对浙派的词史论述渐成为学界的定论。因此,词学界对于浙派的研究,基本止步于嘉道,然而,这一观点却有其悖谬之处。真实的情况是,浙西词派在嘉道以还仍继续存在并发展着。因此,本文拟对浙派的词史形态作重新的探讨,以更好地揭示浙西词派的发展过程,确定该派词风转变之关捩。
一、重新分期的词史依据
晚清词坛浙派是否存在?这是学界还存在争议的问题。如龙榆生即认为“晚近词坛,悉为常派所笼罩”[3](381)。这显然是文学史本身复杂幽隐所致,正如张宏生所言:“文学史发展的道路往往是有隐有显,有曲有直,有断有连,如果不全面加以考察,就很难如实地反映文学历史的全貌和真相。”([4](19)笔者认为,判断一个流派是否还继续存在,要站在清词史的高度,关键看是否还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以及词学影响,这也是最重要的判断标准。
资料表明,在公认的常派盛行的晚近词坛,浙派仍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词家也甚多。即使至清末民初,浙派推崇的南宋词风依然被不少词家所尊奉。这一现象,有少数学者也注意到了。如严迪昌编有《近代词钞》,客观上修正了他在《清词史》中的观点,在词人小传中把嘉道以来的40余名词人归入浙派范畴。又如陈水云《明清词研究史》《清代词学发展史论》、莫立民《晚清词研究》《近代词史》、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杨柏岭《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等均对晚清浙派词人及词史形态进行了一些研究。可见,学界已有的研究,基本肯定了晚清浙派的存在,“浙词依旧是晚清词坛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5](51),然对具体情形未作明确说明。
当然,最能体现晚清浙派的存在地位及影响的是结社唱和,兹将晚清词坛影响较大的词社活动介绍如下:
(一)吴中唱和
时间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地点在江苏吴县。活动多以戈载为首倡,参与者有吴嘉淦、沈彦曾、朱绶、陈彬华、陈裴之、董国华、董国琛、王嘉禄、潘曾沂、沈传桂等。吴中唱和标举声律,严守律韵,“其论词旨,則首严于律,次辨于韵,然后选字炼句,遣意命言从之”[6],为已趋中衰的浙派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江东词社唱和
时间为道光二十五年(1844)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地点在南京。词社由汤贻汾主持,并负责评阅工作,但不参与具体的唱和活动。江东词社共唱和十五集,其核心是孙麟趾,参与者有秦耀曾、孙若霖、孙廷鐻、戈载、雷葆廉等词人。词社唱和多“咏物”之作,崇尚姜夔、张炎,标榜“清空骚雅”。道光二十七年(1847)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孙麟趾又举“青溪水榭倡和”和“秦淮枯柳倡和”,词风与成员与江东词社基本一致,可视为江东词社唱和之延续。
(三)觅句堂唱和
时间为同治十年(1871)至光绪八年(1882),地点在北京。唱和活动以龙继栋的家即觅句堂为中心,成员有王拯、王汝纯、韦业祥、王鹏运、唐景崧、唐景崇、谢元麒等。唱和以龙继栋为领袖,旨在文酒会友,虽不专于词,而于词为最专。唱和多咏物纪游之作,成员词风不一,如龙继栋词尊浙派词风,而另一重要成员王拯则词尚常州词派,故呈现浙、常融通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觅句堂唱和成员多为广西籍文人,且以词学提倡后进,晚清融通浙、常的临桂词派实由其启迪。
(四)壶园唱和
时间为光绪十三年(1887),地点在苏州,首倡郑文焯,参与者有张祥龄、蒋文鸿、易顺鼎、易顺豫等。唱和诸人“于清真嗜之不深,嗜白石过清真远甚”,故“辄以和白石词以为乐”,“事起四月讫八月而和词竟”,“至于寸律寻声,晨钞冥写,则以大鹤之功为多”[7],可见其宗尚。
(五)咫村词社
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地点在北京。首倡王鹏运,参与者有郑文焯、朱孝臧、张仲炘、裴维侒、王以敏、夏孙桐、易顺鼎、易顺豫、华再云、黄白香、高燮曾等。词社瓣香常派而又发展了浙派注重词的音律之特色,每月祝一词人生日,分咏京华胜迹,为临桂词派形成之重要阶段。
(六)春蛰吟唱和
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地点在北京。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朱孝臧、刘福姚避难于王鹏运寓所。自八月至十一月,王鹏运首倡,三人以词为日课,自写幽忧,加上宋育仁和作,结集为《庚子秋词》,词风慷慨悲凉,寄托遥深,可谓词史。自十二月始,王鹏运与郑文焯、张仲炘、曾习经、刘恩黻、于齐庆、贾璜、吴鸿藻、恩溥、杨福璋、成昌、左绍佐等唱和。至次年辛丑(1901)三月,结集为《春蛰吟》,词作159首。词人怵于危亡,藉词唱和,抒其哀怨,寄托对政局时事之忧虑与感思,隐晦深涩地表达难以言说的激愤之情。值得注意的是,《春蛰吟》中咏物词占65首,沿袭《乐府补题》的方式, 这在形式上继承了浙派推崇咏物词的传统,但在内容上又将常派的比兴寄托的理念融入其中。
(七)舂音词社
地点在上海。民国四年(1915),王蕴章、陈匪石、周庆云结词社,邀朱孝臧为社长,参与者另有庞树柏、吴梅、袁思亮、夏敬观、徐珂、潘飞声、曹元忠、白曾然、叶楚伧、况周颐、郭则沄、邵瑞彭、林葆恒、叶玉森、杨玉衔、林鹍翔、黄孝纾等。词社集会共十七次,填词严于音律,限调限题,作“四声词”,皆寄慨之作。民国七年(1918),社事终止,为民初最著名词社。
从这些唱和当中,可以发现以下信息:
第一,整个嘉、道、咸、同期间,浙派词人占据了唱和的主流地位,其标志即领袖或主倡为浙派词人。浙、常词人相互唱和始于同治十年(1871)至光绪八年(1882)间的觅句堂唱和,而之前的唱和均属浙派内部唱和。觅句堂唱和由浙派词人龙继栋为首倡,然亦有常派词人的加入。这既说明了浙派词人在光绪初年仍主导词坛的潮流,也表明浙、常壁垒开始被打破。
第二,光绪初年以后,浙、常词人之间的唱和开始频繁起来,融通浙、常的词人也越来越多,这表明浙、常合流是当时词坛的潮流。而这一潮流发展的顶点则是民国四年的舂音词社,这标志着浙、常合流的最终形成,此次唱和基本汇聚了当时词坛最有成就的词人。
第三,光绪九年以后,浙派词人失去了首倡席位,而把持这一席位的是常派词人或融通浙、常的词人,这表明,浙派内部已经不能再产生具有领袖性质的词人,词坛的主流地位也由此被常州词派所占据。然而,这并不表明浙派风气的完全消退,如郑文焯首倡的壶园唱和,其内容专以联句和白石词为程课;又如王鹏运在北京还与端木埰、许玉瑑、况周颐进行“薇省同声”唱和,内容“优入南渡诸家之室”[1](4007),显然均是浙派的风气。
新城控股高级副总裁欧阳捷表示,流拍地增多是土地市场回归理性的信号。“过去20多年,地价的不断上涨传导至新房房价,进而影响周边二手房价格,构成了房价不断上涨的逻辑链条。地价不断下行将引导消费者预期,促使房价进一步回归理性。”
第四,融通浙、常的词人往往也是成就最高的词人,为词坛所普遍接受。这说明晚清词的发展趋势是浙、常融合,也说明浙、常两派在晚清时期能力相当,互相影响,地位差堪对等。
综上所述,可知二点:一是晚清词坛仍有不少词人在朱彝尊、厉鹗等人词学基础上继续衍生发展,推崇南宋,坚持浙派词风;二是晚清词坛呈现浙常融合趋势,尤其是晚清四家“跨常迈浙,冶南北宋而一之”的作派,更说明了浙派在晚清词坛的深远影响。因此,“浙派词走到嘉道之际已成强弩之末”的传统说法似须加以厘正[5](46),浙派的发展历程也需重新讨论。
二、重新分期的词风依据
文学史上任一文学流派均要经历由生成、发展、演变以迄衰落的过程,也即说文学流派的演进既表现出连续性,又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历时长久的浙西词派,其阶段性特征有时表现得较为明晰,有时则不大突出。当然,前人也很早就注意到浙派的阶段性问题,亦试图准确地描述浙派分期的时间界限以及词史形态,如似兹《清代词学略述》、王易《词曲史》、龙榆生《中国韵文史》、严迪昌《清词史》等。然而,细考前人的论述,均以词人的构成作为分期的参照系,对浙派的词史分期显得较为简略,时间断限亦不甚明朗,尤其是缺乏对道光之后的浙派成员构成的勾勒,且并未充分反映出词风转变、词史进程等重要的问题。
笔者认为,如以词风嬗变为分期的依据,就可以描述出不同时期词学的特点,很好地揭示浙西词派的阶段性特征。那么,词风嬗变的标志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有四个方面的标志:① 领袖的替现;② 重要词选的刊印;③ 词论主张的补充修正;④ 浙派相对于其他词派地位的升降。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分期时间的界限确定,只能是一种大概的划分。若要想人为地定出一个精确的时间,可以词选的刊印时间为准绳,因为“风气转移,乃在一二选本之力”[3](73)。
根据上述认知,并结合词史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论断:嘉庆初年是浙西词派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清词发展的重要拐点。首先,嘉庆八年(1803),郭麐结集出版《蘅梦词浮眉楼词》,正式登上词坛;嘉庆十一年(1806),王昶去世。这样,郭麐就取代了王昶而成为浙西词人的领袖。其次,嘉庆七年(1802),王昶编纂《国朝词综》四十八卷。严迪昌认为:“如果说朱彝尊的《词综》是标举‘浙派’的宗旨和词统,那么王昶的《国朝词综》则是清代‘浙派’词风集大成、总结性的备览之编,并有‘定于一尊’的倾向。”[2](365)可见,王昶的《国朝词综》宣告了后期浙西词派的到来。第三,浙派以纠明词庸陋鄙俗兴起,推崇“清空醇雅”“以刻削峭洁为贵”,然“不善学之,竞为涩体,务安难字,卒之钞撮堆砌,其音节顿挫之妙荡然”,“人守其说,固结于中而不可解”[1](3528),至嘉庆初年,可谓是弊端渐生。即使对于善学如郭麐这样的浙派词人,对南宋“雅正”词风也逐渐产生了审美疲倦。嘉庆八年(1803),郭麐在《蘅梦词浮眉楼词序》宣称:“自此以往,心息学道,以治幽忧之疾,其无作可也。”[6]那么,他所宣称的“幽忧之疾”又是指什么呢?察其嘉庆十二年撰写的《忏余绮语序》即可知。郭麐在《忏余绮语序》中自责自己在嘉庆八年(1803)至嘉庆十二年(1807)间所作之词存在“多体物补题之作”、“幻情妄想”“绮语”等弊端[8],虽早有“意不复作”之决心,然“结习之难除,悔过之不勇”[9],从郭麐将这些词命名为《忏余绮语》来看,其对浙派词反思的心迹更显得昭然。第四,嘉庆二年张惠言刊印《词选》,标志着常州词派的兴起。张惠言提倡词应“比兴寄托”“意内言外”,“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1](1617)。张氏的词论及《词选》在嘉庆年间即已产生一定的影响。张惠言侄子张曜孙《清淮词·跋》亦曰:“常州词人自先世父、先子《词选》出,而词格为之一变,故嘉庆以后词家,与雍、乾间判若两途也。”[10]另外,浙派词人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九亦曰:“嘉庆间,填词家咸推吾郡张皋文太史惠言。”[1](2824)丁氏诸人所言自然有溢美夸大的成分在内,但毫无疑问可以作为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将对后世词坛产生深远影响的证明。应该指出的是,张惠言编《词选》虽未标举反浙派之帜,但其意图仍是纠弹以姜、张为宗主之风。张惠言的弟子金应珪在《词选后序》中论词坛之弊有云:
近世为词,厥有三蔽:义非宋玉,而独赋蓬发;谏谢淳于,而惟陈履冩。揣摩床第,污秽中冓,是谓淫词,其蔽一也。猛起奋末,分言析字,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此犹巴人振喉以和阳春,黾蜮怒嗌以调疏越,是谓鄙词,其蔽二也。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其蔽三也[1](1619)。
考当时的词坛,“淫词”即沿明词以来的《花间》《草堂》之风,“鄙词”为阳羡词风,“游词”即浙西词风。阳羡词派在乾隆后期即已衰竭,《花》《草》陋习在浙派兴起后也早已得到反拨,因此,在嘉庆词坛,“淫词”“鄙词”均作为不大,影响亦小,唯有“游词”方盛正炙。可见在常州词派创始人的眼中,他们所要批驳的对象自是浙派词风,这也为词坛带来了新的气象。
可见,嘉庆时期的词坛正处于浙、常两派开始升降变化的阶段,浙派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后来的谭献在《复堂日记》中,就很准确地概括出此一时期词坛的特点。谭献云:
填词至嘉庆,俳谐之病已净。即蔓衍阐缓貌似南宋之习,明者亦渐知其非。常州派兴,虽不无皮傅,而比兴渐盛[11](72)。
三、四阶段的新区分及其嬗变
当然,仅将浙西词派分为前后两期仍显得有些粗略。梁启超认为,任何思潮之流转,例分四期,即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13](12)。浙西词派亦是一种文学思潮,故当也可分为此四个阶段,即前期浙派包括启蒙期与全盛期,后期浙派则包括蜕分期与衰落期。
就前期浙派而言,因启蒙期是以朱彝尊的词学活动为中心,全盛期以厉鹗的词学活动为中心,故其启蒙期与全盛期的分界比较明晰。与前期浙派相比,后期浙西词派显得复杂很多,学界也一直未能进行有效的梳理。其原因是常州词派因其词学理论的成就,吸引了学界的注意,使得学界对后期浙派的关注有所缺失。然而,事实上,常派兴起后,更多的只是一种词学理论的倡导,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词人在创作上仍然崇尚浙派。自康熙以来即占据词坛主流地位的浙派,在常派崛起后,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两派势力的消长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后期浙派虽然面临常州词派的强劲挑战,在逐渐丧失其词坛的主流地位,但整个过程是相当的漫长。本文下面将对康熙以来的词坛状况进行剖析,以揭示浙西词派复杂的发展历程。
康熙十七年前后,词坛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吴梅所言“风气为之一变”[14](116)。要之,词坛风气之变,其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词坛上能鼓扬宗风的耆宿如吴伟业、龚鼎孳、王士禄、曹尔堪、陈维崧、纳兰性德等相继凋零,而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应“博学鸿词科”入北京,“于是,一个新的词坛领袖被确认了,一个词派树帜于京师,播扬于南北”[2](246)。第二,明季余习滌除,浙派词风方兴未艾。康熙十七年(1678),朱彝尊、汪森两人共同编刊《词综》,选词宗清空醇雅,以姜夔、张炎为尚,一洗《草堂》之陋,江浙词人纷纷效仿。次年,朱彝尊另一个知音龚翔麟在南京将朱彝尊、李良年、沈皞日、李符、沈岸登、龚翔麟六人词集合刻为《浙西六家词》,并将当时已失传数百年的张炎《山中白云词》八卷附刻于书后,以明浙派词学渊源。北京、南京是南北的文化政治中心,这样,浙派词风流布全国。第三,云间词派、阳羡词派相继式微。这突出表现在其各自词选的编辑方面。康熙十七年,张渊懿、田茂遇辑选《清平初选后集》十卷,这是云间词派的一个总结性的大型选本,考此选纂辑的意向与宗旨,“其为云间一脉的归结之集是十分清楚的”[2](30)。同年,曹亮武主编乡邦词选《荆溪词初集》,该词选是阳羡词派的“一次自我检阅的群体结集,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镌额题碑似的历史性的总结”[2](170)。如此,云间词派与阳羡词派在康熙十七年以后日渐衰歇,而词坛亦逐渐呈“家白石而户玉田”的局面[15](543)。
浙派词发展到厉鹗,即由启蒙期步入了全盛期。首先,厉鹗取代了朱彝尊成为词坛的领袖。雍正三年(1725),厉鹗首次赴扬州马曰琯、马曰璐的“小玲珑山馆”处坐馆。此后三十余年,“大江南北,所至多争设坛坫,皆以先生为主盟,一时往来,通缟纻而联车笠,韩江之雅集,沽上之题襟,虽合群雅之长,而总持风雅,实先生为之倡率也。”[16](703-704)故此期的浙派又有“厉派”之称。其次,厉鹗在浙派发展史上的地位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郭麐在《梦绿庵词序》中所说的:“竹垞开之,樊榭浚而深之。”[8]可以说,“真正能够实现朱彝尊推尊姜夔理念,并开创浙西词派发展局面的是厉鹗”[17](300)。第三,厉鹗通过向南宋史达祖学习,弥补了浙派在初创时的不足和弊端。受厉鹗的影响,兼学史达祖词风即成了词坛风尚,谢章铤曾说:“雍正乾隆间,词学奉樊榭为赤帜,家白石而户梅溪矣。”[2](3458)。第四,从词派的消长来看,浙派基本笼罩了雍、乾词坛,而阳羡词派颓势已极,只“流韵余响还不时振起”[2](371)。值得注意的是,厉鹗并没有编辑重要的词选,然而他也找到了一种有效的传播词学主张的方式,即通过自己的词学创作以及交游唱和等活动,将浙派的词学思想发展到极致,这实际起到了词选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将雍正三年视为全盛期与启蒙期的分界点。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厉鹗于乾隆十七年逝世,吴中词人王昶接替成为浙派的领袖。但这并没有导致浙派发展的新的阶段的到来,其原因是王昶宗法姜张,效仿厉鹗,鼓吹浙派词风,并未对词论进行更新,而词坛的风气及流派的升降亦没有多大变化。然而,其晚年所编纂的《国朝词综》却成了浙派前、后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浙派前、后期的分界也即是全盛期与蜕分期的分界,该部分内容已在上文详细论述,兹不赘言。
要想正确认识后期浙派与整个词坛的关系,首先应该对浙、常两派的势力消长有所了解。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后期浙派是何时让出词坛领袖地位呢?换个角度思考即是词坛何时普遍接受常州词派的理论——词选。
考察词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张惠言的《词选》虽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并未立即被词人奉为圭臬,“终嘉庆一朝常州派未能张帜开风气”[2](472)。从文献来看,嘉庆二年《词选》初刻本,现已不存,今所见者皆为道光十年(1830)张琦重刻本。道光十一年(1831),浙派领袖郭麐去世。道光十二年(1832),周济刊印《宋四家词选》。那么,是否自此常州词派的理论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呢?覆按史实,不难发现,常州词人对这一情况的叙述存在矛盾之处。张琦《重刻词选原序》曰:“同志之乞是刻者踵相接,无以应之,乃校而重刊焉。”[1](1618)由此出发,龙榆生认为,“此选本之在嘉庆道光间,即已普遍流行。”[3](389)“常州词派,至周止庵而确立不摇,衣被词流。”[3](392)而潘曾玮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所纂之《词辨序》记述云:“余向读张氏《词选》,喜其源流正变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尝欲举张氏一书,以正今之学者之失,而世之人,顾弗之好也。”[1](1638)据此,有学者断定,在道光十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常州词派在整个词坛中并没有取得具有主导性的壮观局面,反而颇有岑寂之势[18](130-131)。可见,这种矛盾的叙述导致后世学界对常州词派理论为词坛所普遍接受的时间也形成了不同的理解。放眼词坛,之所以产生这种矛盾的认识,原因自是常州词人在道光十年以后逐渐完成了常州词派理论的建构,词学大兴,而此期间,浙西词人在词的创作上也颇有建树,引人注意。这样,浙、常两派就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对峙局面。兹将两派重要词家列之如下:
浙西词派:
郭麐(1767—1831),著《灵芬馆词话》《词品》等。
冯登府(1783—1841),著《檇李词辑》二卷等。
戈载(1786—1856),著《词林正韵》(道光元年)、《宋七家词选》(道光十年)等。
陶樑(1772—1857),辑《词综补遗》二十卷等。
孙麟趾(1791—1860),有《词迳》、辑《国朝七家词选》一卷(道光三十年)等。
黄燮清(1805—1864),辑《国朝词综续编》二十四卷等。
常州词派:
张琦(1764—1833),重印《词选》。
陆继辂(1772—1832),著《词律评》《词综评》等。
周济(1781—1839),辑《宋词家词选》《词辨》(道光十七年)等。
董毅(1803—1851),辑《续词选》二卷(道光十年)等。
宋翔凤(1776—1860),著《乐府余论》等。
蒋敦复(1808—1867),著《芬陀利室词话》等。
由此可以看出,浙、常两派的重要词论家大多活动于同一时期,其词选及词论著作在各自的地域、流派、词人群体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与浙派相比,常派在理论上成绩斐然,而在创作上却影响甚微。然而,对常派而言,其优势在于词界在理论上给予更多的关注,即使在创作上“顾弗之好也”,也显得声势更为浩大。也正因为常派创作上的缺失,导致大多词人依然遵循浙派的轨迹。这方面,突出的证据就是《词综补遗》《国朝词综续编》等词选的编辑,选入了大量的遵循浙派作风的嘉道咸同时期的词人,常派此时却无相对应的作品。可见,浙西词派在创作上依然保持着主流地位。另外,张琦也说明了“乞是刻者踵相接”者是“同志”,也即是常州词派内部的宗尚了,并不能代表整个词坛的风尚。
既然道光十一年以后,常州词派在理论上已经完成了建构,那么常派的理论为词坛所普遍接受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同治十二年(1873)十二月,潘祖荫在《刊周济宋四家词选序》中说:“近世论词,张氏《词选》称极善。止庵《词辨》,亦惩时俗猖狂雕琢之习。与董晋卿同期复古,意仍张氏……此卷晚出,抉择益精。”[2](1658)至此,常州词派的理论开始得到了词坛普遍的接受与选择。而浙西词派也开始让出词坛的领袖地位。谭献《复堂日记》卷二载,同治四年(1865),“杭州填词为姜、张所缚,偶谈五代北宋,辄以空套抹杀”[11](34),而至光绪二年(1876),“近时颇有人讲南唐北宋,清真、梦窗、中仙之绪既昌,玉田、石帚渐为已陈之刍狗。”[11](72)可见,在光绪初年,常州词派开始取代了浙西词派的主流地位。
考光绪初年清词的发展,有几个重要的现象值得注意:首先,浙西词派一批重要的词家如张炳堃、潘曾莹、刘熙载、杜文澜、陈澧、潘曾绶、丁至和、周星誉等相继去世,继起的词坛领袖有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孝臧、文廷式等,而这些词人,传统观点认为他们词的宗尚渊源是常州词派。其次,光绪九年,丁绍仪《国朝词综补》五十八卷、《续编》十八卷编成。丁氏是编“为续补《国朝词综》所未及”,“爰仿黄氏(燮清)例,一并编列”[19],在创作上对浙派的成就作了一次总结。然而,丁氏词选在编成之后仅得以稿本存世,一直到约光绪二十年(1894)才刷印问世,且数量不多,以至到民国十五年(1926),赵尊岳在访书时即发出“不及卅年,遗书已不易访得”的感慨[19]。丁氏词选亦为时人所不满,即如谭献所责,“阅无锡丁芍仪杏舲《国朝词综补》稿本。扬王昶侍郎之波。集中辈行错落,闻见浅陋。”[11](5)“借丁杏舲选《词综补》四十卷归阅……佳篇不多觏也。”[11](319)可见,此时的浙派词人并未为清词增添多少新的内容了。又次,光绪三年,谭献编刊《箧中词》,目的是“以衍张茗柯、周介存之学”[1](3999),“以比兴为本”[1](4002);光绪八年,谭献编刊《复堂词录》,旨在阐明词可“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1](3987)。从清词史上看,谭献所编辑的词选极具影响力,故夏孙桐赞曰:“先辈甄录今词者。莫善于复堂《箧中词》。”[15](822)谭献的词选使得词坛的创作风气为之顿变,不再遵循浙派的词风。吴梅即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明言“变浙词者,复堂也”[14](138),张扬了谭献变革词坛创作风气的贡献。复次,从常派词家的经历来看,一些著名的词论家学词经历均从浙派开始。这些由浙入常的词人,最著名的有王闿运、谭献、陈廷焯等。词坛的上述诸种现象,充分说明了可以光绪九年丁绍仪编刊词选的事件为标志,将后期浙西词派的蜕分期与衰落期加以分界。
依前所述,光绪九年之后的浙派步入了衰落期。当然,处于衰落期的浙西词派并非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此期的浙西词派呈现两个重大发展趋势。一是仍有众多词人如王允皙、张仲炘、杜贵墀、沈曾植、沈泽棠、蒋玉稜、李慈铭、俞陛云、郭则沄、左又宜等等坚持浙西词风的创作。即使被誉为晚清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亦有部分作品追慕姜张情韵,清空雅正,疏朗俊逸。尤值得注意的是,在柳亚子所撰《玉琤瑽馆词序》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争论:
昔岁在己酉,余与云间高天梅、同邑陈巢南始创南社,驰檄召四方豪俊,以孟冬朔日期会吴中 …… 而檗子实惠然肯来……已归舟,指昌亭,相与上下古今往复辨难,遂及倚声之学。檗子固墨守南宋门户,称词家正宗。而余独猖狂好为大言,妄谓词盛于南唐,逶迤以及北宋,至美成而始衰,至梦窗而流极,稼轩崛起欲挽狂澜而东之,终以时会迁流,不竞所志。檗子闻之,则怫然与余争。寒琼君讐,复互为左右袒,指天画地,声振屋梁[20]。
己酉即宣统元年(1909),此时的词坛当在常州词风的笼罩下。而庞树柏(字檗子)却依然坚持浙派词风,并与常派词人柳亚子怫然争之,辩难不已。而庞树柏的词集,亦得到朱孝臧的青睐,助以删定。这说明即使在衰落期浙派在词坛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也表明了浙派在时人心目中的实际地位和对词坛影响之深远。另一个趋势就是有些词家逐渐不受浙、常两派词风的笼罩,如文廷式、郑文焯、朱孝臧、冒广生等人,走上了融通浙、常两派道路。民国三年(1914)朱孝臧纂辑《宋词三百首》,这标志着词坛浙、常融合的正式完成,他“在选目上给予北宋词、南宋词等同的数量”,“对姜夔、晏几道、柳永等人给予除梦窗、清真以外最高的重视,反映的正是当时浙常合流的情况”[21](232)。次年(1915),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刊《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就此展开,这是传统文学的结穴,亦是新文学的起点。尽管之后仍有一些传统文人坚持词学创作,然而,就浙西词派而言,这已经是余波微响,为研究方便,我们姑且将浙派的衰落期的终点定在民国三年。
四、结语
从晚清词人融通浙、常的情况来看,晚近词坛已经蕴藏着发展的新迹。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迅速到来,新变的苗头未能光大。在民国时期,龙榆生面对词坛凋敝的现状,提出了“重振雅音”的理论,援引如下:
今欲救常州末流之弊,允宜折衷浙、常两派及晚近谭、朱诸家之说,小令并崇温、韦,辅以二主、正中、二晏、永叔;长调则于北宋取耆卿、少游、东坡、清真、方回,南宋取稼轩、白石、梦窗、碧山、玉田。以此十八家者,为倚声家之轨范,又特就各家之源流正变,导学者以从入之途,不侈言尊体以漓真,不专崇技巧以炫俗,庶几涵濡深厚,清气往来,重振雅音,当非难事矣[3](405)。
细考龙氏言论,当可目之为一则简短的师法理论,其要义就在“折衷浙、常两派”。龙榆生对晚近词坛极为熟悉,他所提出的师法理论自是以晚近词坛的创作实践作为基础的,也是他对晚近词坛新生气象的一次理论总结。将龙氏的理论与晚清浙、常融通气象联系在一起,则对晚近词坛的发展脉络就看得更清楚了。在这里,我们不妨大胆猜测,龙榆生应该也曾想仿效朱彝尊、汪森、张惠言、周济等人,倡言师法理论,进而改变词坛风气,构建一个新的流派。然而,时际风会,历史已经进入了白话文的天地,这种融通浙、常的风气只能成为一个新的流派的先声,而这个新的流派却永远不能真正形成了。
[1] 唐圭璋. 词话丛编第四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 严迪昌. 清词史[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 2001.
[3] 龙榆生. 龙榆生论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4] 张宏生. 中国诗学考索[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5] 莫立民. 晚清词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6] 顾广圻. 吴中七家词序. 王嘉禄. 吴中七家词[M]. 清道光二年(1876)刻本.
[7] 易顺鼎. 吴波鸥语序. 近代蜀四家词[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8] 郭麐. 灵芬馆杂著续编[M]. 嘉庆十二年刻本.
[9] 郭麐. 忏余绮语[M]. 光绪刻本.
[10] 汤成烈. 清淮词[M]. 同治元年刻本.
[11] 谭献. 复堂日记[M]. 河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12] 朱惠国. 论晚清词坛“常”“浙”两派的共存与交融,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 2007(9): 116.
[13]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6.
[14] 吴梅. 词学通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15] 施蛰存. 词藉序跋粹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16] 厉鹗. 樊榭山房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7] 张宏生. 清词探微[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8] 迟宝东. 常州词派与晚清词风[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19] 丁绍仪. 清词综补[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0] 庞树柏. 玉琤瑽馆词[M]. 民国五年排印本.
[21] 沙先一, 张晖. 清词的传承与开拓[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On the stages of Ci school of western Zhejiang province
LIU Shen
(College of Xingjian Science and Lib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5, China)
Ci school of western Zhejiang Province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i schools in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Ci school of western Zhejiang Province, questions the view of Yan Di Chang, who believes that Ci school of western Zhejiang Provin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seventh year of Jiaqing.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Ci school of western Zhejiang Province should be sent to seven-year of Jiaqing for the sector, which is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before and after that year.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 school of western Zhejiang Province. The 11th year of Daoguang and nine-year Guangxu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The former marks equal status in Ci theory, while the latter marks the of creation Ci school of western Zhejiang Province having entered a period of decline.
Ci school of western Zhejiang Province; Changzhou Ci school; the late Qing Dynasty; History of Ci; styles of Ci; School of Ci
I222.8
A
1672-3104(2014)06-0277-07
[编辑: 胡兴华]
2014-05-06;
2014-07-3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词自度曲研究”(12CZW039)
刘深(1978-),男,江西永新人,文学博士,广西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词学
——兼论梅里词派及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