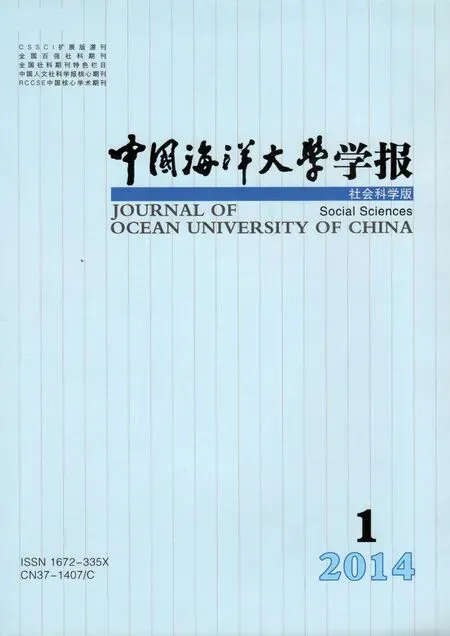美学与政治
——莫言的“黑孩”与福克纳的“班吉”对比研究*
左金梅 高改革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266100)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在其《美学意识形态》一书中对现代美学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并试图“在美学范畴内找到一条通向现代欧洲思想某些中心问题的道路,以便从那个特定的角度出发,弄清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政治、伦理问题。”[1](P1)莫言在其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的自序中也曾说到:“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2]伊格尔顿和莫言的观点揭示了美学与政治间不可分隔的关系,说明了在对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政治因素的影响,对这些因素的艺术化处理体现出了艺术家的独特美学思想。本文将从社会关系、话语权力、意识形态三个角度对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及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班吉身上的美学思想进行分析,从而对政治与美学两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尝试性的阐释。
一、社会关系中的边缘化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56)作为存在于世界上的人类来说,社会属性是其根本属性。没有任何人能够脱离社会关系的束缚而存在于群体之外。《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黑孩与《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同属于社会关系中最底层的人物,这种底层地位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他们的被边缘化处境。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首先提出“边缘人”这一概念,勒温认为社会中的人们可以分为中心人和边缘人。中心人是指那些可以凭借自己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很好处理进而可以使自己融合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群体。而边缘人则泛指那些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黑孩与班吉则正是属于后一群体。
黑孩的被边缘化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家庭的排斥与社会群体的疏远。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透过小石匠的讲述我们得知黑孩的父亲下了关东,三年都没有回家,而他则跟着后娘过日子。经常酗酒的后娘不但未给黑孩任何母性的关爱,而且酗酒后,拧他,咬他,肆意虐待。黑孩在家中受尽冷落,在外面也同样被欺凌。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时期,政治运动正是风起云涌之时,全民皆兵的社会风气无法给黑孩这样的儿童一个无忧无虑的正常童年。十几岁的他便不得不跟随一群大人去修大坝。在被分派任务时,刘副主任对他不屑一顾,讽刺道:“这也算个人?派这么个小瘦猴来,你能拿动锤子吗?”[4](P7)并用力捏着黑孩的脖子摇晃了几下,使黑孩疼痛难忍。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中,黑孩的身心都备受摧残,从开始时的灵性少年变成了后来的“小哑巴”。
《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与黑孩有着同样的经历。由于先天的身体条件缺失,班吉在家里除了姐姐凯丹丝及迪尔西大妈外得不到任何家庭成员的关爱。母亲甚至认为班吉的出生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有时候我想,这准是老天对我的一种惩罚。’”[5](P5)作为班吉的大哥,杰生也丝毫没有对自己的弟弟的处境表示出同情,在母亲去世后,他就把班吉作为一个智障者送到了精神病院。天生的生理缺陷完全阻断了班吉与社会群体进行正常交流。他曾尝试接近小女孩:“她们走过来了。我拉开铁门,她们停了步,把身子转过来。我想说话,我一把抓住了她,想说话,可是她尖声大叫起来,我一个劲儿想说话,想说话,这时明亮的形影开始看不清了,我想爬出来。”[5](P52-53)在这次懵懂的尝试之后,班吉便被做了去势手术。
黑孩与班吉的边缘化也体现在他们与不同人物的社会关系中,与他人之间的碰撞反映了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间的相互矛盾和冲突。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并非某种单调的固态模式,而是不同意识形态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结合体,其“不仅由一般意识形态、局部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等亚结构组成,而且每一个亚结构都可以进一步分成各种不同的层次,它们之间充满了裂缝和冲突。”[6](P129)
在《透明的红萝卜》中,我们通过不同人物间的关系与接触可以发现这种冲突的交错与纠缠。黑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其无疑也是各种矛盾冲突的焦点。这种矛盾与冲突在他与小铁匠及刘副主任间的关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小说中,黑孩与小铁匠间有着某种相似的生活经历。小铁匠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跟随老铁匠学徒三年,最终为了出徒而不惜采取“偷艺”的方式将老铁匠逼上绝路。对于小铁匠来说,掌握了打铁的技巧便拥有了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下去的资本。在老铁匠走后,小铁匠要收黑孩为徒,黑孩虽未对此作出即刻回应,但从其后来的一系列行动中我们可以得知黑孩是心甘情愿的。在小铁匠与小石匠的打斗中出手帮助小铁匠的举动也证明了这点。只要成为小铁匠的徒弟并学会打铁,黑孩也便有了生活的依靠。黑孩与小铁匠代表了处于社会底层人群的意识,即在饥饿与苦难的驱使下人们对于最基本物质生活的追求。
与底层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是代表权威的意识形态.刘副主任作为农村公社的干部,无疑是权力与统治的象征。在他与黑孩的对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两者间巨大的身份差异和意识的冲突。这实际上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与权力者间的对话。在这种强弱悬殊的对话中,弱者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风风火火的革命运动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在农村偏远落后的山区更是如此。在这些角落里,像黑孩这样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们并不罕见。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与现实中,这些人不得不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着不断的挣扎,活下去成为人们唯一的奢求,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似乎与人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在面对刘副主任时,体现在黑孩身上的是一种被压抑的对精神生活及对自由的向往。
《喧哗与骚动》中同样展现了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与矛盾。因为生来便是智障者,康普生太太一直对班吉给家庭带来的灾难耿耿于怀。在康普生太太眼里,自己的贵族血统是不容侵犯与亵渎的,而班吉的出现无疑会给自己的高贵抹上污点。小说中的康普生太太是一位典型的南方淑女,她的身上残存着南方贵族庄园主们曾经引以为傲的荣耀及不可一世。班吉天生的缺陷对康普生太太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班吉出生后,她为维护自己娘家名誉,不顾家人的阻挠而将其原先的名字毛莱改为班吉,因为毛莱是她弟弟的名字,她是无法忍受让一个智障儿来继承自己家族的血统的。所以,她对班吉经常抱怨,一次她不让女儿凯蒂抱班吉,说“他太大了,你抱不动了。你不能再抱他了。这样会影响你的脊背的。咱们这种人家的女子一向是为自己挺直的体态感到骄傲的。”[5](P63)在小说的整个叙述过程中,康普生太太都是以一个试图维护家族荣誉的弱者形象而出现的,她的这种徒劳的挣扎实际上更加凸显了整个康普生家族的没落与衰亡。班吉是她的亲生儿子,无论怎样去拒绝和掩饰,她都不可能逃避这样的事实。她的体弱多病及无止尽的抱怨则更加使得这种遮掩与否认显得苍白无力。康普生太太与班吉在小说中是以母子身份出现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及矛盾冲突实际上集中体现了美国南方贵族庄园主们对自己昔日的辉煌与繁荣在内战后所发生的变化及衰退所产生的担忧及焦虑。战后的美国南方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传统的种植园经济由于废奴制度的诞生而趋于瓦解,在此基础上的农业文化与种族主义文化也受到了北方工业文化的逐渐侵蚀。小说里康普生太太竭力挽留的一丝残存的高贵正是当时南方人内心焦虑及矛盾的集中体现。
小说中关于班吉的另一冲突集中体现在他与自己的哥哥杰生身上。与康普生太太一样,杰生虽是班吉的哥哥,但它却从未给过弟弟任何关爱。在他掌家之后,班吉的存在便成了自己的累赘。他曾多次向自己的母亲抱怨班吉呆在家里只会加重家里的负担,应该把他送到疯人院去。“我说,要是当初一开始就把他送到杰克逊去,我们今天的日子会好过得多。”[5](P218)杰生对班吉的厌恶与排斥实际上集中体现了战后南方社会受到北方工商资本主义经济冲击后,新崛起的实力主义者所推崇的一种价值观念。在杰生眼里,所谓的亲情一旦与利益扯上了关系,便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刚开始让班吉待在家里只是由于听从康普生太太的劝导,等到康普生太太一去世,他便将班吉送到了精神病院。杰生生活中的一切所作所为无不与利益的攫取发生着牵连,而这正是南方种植园经济受到北方资本主义经济侵蚀后的真实反映。
以黑孩和班吉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再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农村与二十世纪初美国南方土地上不同意识形态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在权力领域中则体现在了主人公为争取人性自由所进行的反抗上。
二、话语权的丧失与人性的反抗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米歇尔·福柯曾经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7](P159)虽然福柯这里所讲的“话语”并非单纯指人们平常所提到的语言及说话功能,但语言的诉说权无疑是人类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力之一,对于这一权力的抹杀则象征着对于人类所能享有的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力的抹杀。
《透明的红萝卜》及《喧哗与骚动》两部小说中特殊化艺术处理的最显著特征便是主人公黑孩与班吉的失语化现象。《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从小说开头到结尾除了面对小铁匠重新点燃火苗时兴奋的发出一声“噢”之外,无论是面对菊子姑娘关切的询问,还是用小锤子砸碎食指指甲以及手攥烧红的钢錾,都始终保持了一个沉默者的形象。从小石匠与菊子姑娘的对话中我们得知黑孩不是哑巴,他四五岁时说起话来还可以像“竹筒里晃豌豆”,可是后来话越来越少,动不动就像尊小石像一样发呆。而《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则是一出生便失去了说话的权力,每次自己的回忆被唤醒及遇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只能胡乱哼哼一阵,受到别人欺负的时候也只会敞开嗓子撕心裂肺的大哭。就连在发现自己被“去势”之后,他也只能看着自己的身体哭泣。
语言功能的丧失无疑使黑孩与班吉失去了与其他人进行正常交流的基本工具,这也促成了他们本身的悲剧性与弱势群体地位的形成。《透明的红萝卜》里的小黑孩面对不同人物的询问、关切或是斥责都没有进行任何的言语回应。“孩子不说话,只是把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直盯着队长看。”[4](P3)“小石匠的手指骨节粗大,硬的像小棒槌,敲在光头上很痛,黑孩忍着,一声不吭,只是把嘴角微微吊起来。”[4](P6)《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虽然还能哼哼几声,但他的哼哼在别人的眼中却没有任何意义。“‘听听,你哼哼得多难听。’勒斯特说。‘也真有你的,都三十了,还这副样子。’”[5](P3)“你又是嘟哝,又是哼哼,就不能停一会儿吗,勒斯特说。你吵个没完,害不害臊。”[5](P9)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指出,话语“并非单纯的‘能说’,更意味着有权力说,即有权力通过语言来运用自己的权力。”[8](P76)黑孩与班吉的“失语”则表明了他们在自己所存在的社会中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而该基本权力的遗失也同时否定了他们在生活中对任何形式的权利拟或是幸福的追求。
福柯对话语权的阐释并没有完全否定沉默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他在《性史》一书中曾经提到“沉默并不是话语的绝对终结。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话语与沉默截然分开,然而沉默却是伴随话语而来、相对于话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9]在福柯眼里,当话语所体现的是主流文化,个体的存在融于其中即意味着消逝时,沉默也可以理解为是对社会意识与规范的一种反抗。[10]因此当沉默的主体处于特定的生活环境中时,其沉默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反抗话语。《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正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家里,黑孩经常被后娘吩咐拿着地瓜干到小卖铺里去换酒,而他便成了后娘喝醉酒后的出气虐待的对象。在工地上,黑孩也是这群人里面处于最底层的弱者。徘徊于以刘副主任为代表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农村主流文化之外的他只能以沉默者的姿态来面对一切苦难和欺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与社会背景下,黑孩任何形式的言语反抗都是苍白无力的,而也恰恰是这样的环境和背景,却赋予了沉默者以反抗的力量与高贵。在经受着身体与心灵痛苦磨难的不断冲击,黑孩始终都封锁着自己与外界的交流。他这种坚韧的近乎残忍的沉默给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冲击力与震撼力是巨大的。这种沉默的力量在黑孩赤手捡回灼热的钢錾时表现的最为突出。他一把攥住钢錾,哆嗦着,左手使劲抓着屁股,不慌不忙走回来。黑孩在小铁匠面前蹲下,松开手,抖了两抖,錾子打了两滚儿躺在小铁匠脚前。然后就那么蹲着,仰望着小铁匠的脸。小铁匠浑身哆嗦起来:“别看我,狗小子,别看我。”[4](P35-36)在 小 说里,小 铁匠 是 一 个 铁 石 心 肠 的人,为了生存他可以逼迫自己曾经师从三年的老铁匠走投无路,而面对一个孩子承受痛苦时的坚韧与沉默他却感到了胆怯与恐惧。心灵上在面对菊子姑娘的关爱以及众人的同情与欺辱时,黑孩也全都采取了沉默的方式进行排斥与反抗。在这种情境下,沉默可以说是黑孩拥有的唯一资本与武器,抛弃沉默即意味着对现实苦难的妥协及屈服。他在这个曾被王小波称为“声名狼藉的疯人院”里用仅存的一块破衣烂衫保持着自己作为人的一点点尊严,这是高贵的沉默。
福克纳在为自己的小说《喧哗与骚动》命名时借鉴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里面的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11]这里的喧哗与骚动与小说主人公班吉的喧嚣与叫嚷有很大程度上的关联。据福克纳本人介绍,他创作时原本只打算写一章,即小说的第一部分。由此可见,班吉的意识流部分倾注了作者极大的期望与寄托。而小说里的班吉虽然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但他一切的情感变化却都通过了哭泣与呐喊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在读者眼里,每一次的哭泣与呐喊都充满了绝望与凄凉。小说中班吉的每一次哭泣都是有其触发点的,而引发班吉哭泣的事件几乎大多数都跟自己的姐姐凯丹丝有关。班吉由于天生便是一个傻子,因此他在家里受到了大部分成员的厌恶与排斥,包括自己的妈妈康普生太太和哥哥杰生,只有姐姐凯丹丝与黑人女佣迪尔西大妈真正给予了他关爱与呵护。而姐姐凯丹丝的爱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班吉缺失的母爱,在他的眼中,姐姐凯丹丝或许就是自己的“妈妈”。每次在隐隐约约感觉到姐姐凯丹丝发生变化或将要离开自己时,班吉便会通过哭泣的方式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与反抗。‘我不怕。’凯蒂说。‘我要逃走。’‘哼,你要逃走。’昆丁说。‘我是要逃走,而且永远也不回来。’凯蒂说。我哭了起来。……‘好了,别哭。’她说。‘我不会逃走的。’我就不哭了。[5](P18)姐姐凯丹丝在失身后,班吉同样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他哭泣着推着姐姐进入洗澡间,希望她能洗去不贞,重新做回原来的姐姐。班吉的这些哭泣在表面上看来正如《麦克白》里所说的痴人说梦那样,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哭泣正是班吉在丧失自己的话语权后,选取的另一种形式的反抗。而这种方式的反抗却充满着无奈与悲凉,因为眼泪只能是弱者的护身符,班吉的哭泣也带有深深的悲剧色彩与绝望。
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在丧失自己的话语权后,都选择了进行反抗,而两者所选取的反抗方式不同:一个是高贵的沉默,一个是绝望的哭泣。无论他们所选取的方式怎样,这都是来自人性心灵深处的呐喊,对人性的关注是伟大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也是政治与美学间相结合的基础。作品中主人公的“儿童身份”与他们感官能力的无限延伸促成了传统意识形态结构上的颠倒,束缚中的人性也从而获得了解放。
三、意识形态的颠覆与人性的解放
作品中意识形态结构的颠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儿童对成人传统意识形态观念的鄙弃,另一个则体现在主人公通过无限延伸的感官能力所获取的“能看”及“能说”上。在这里,虚构的美学思想完成了对现实中政治压迫的超越,束缚中的人性也从而获得了解放。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并非毫无根据的幻觉,而是一种坚实的现实,是一种积极的物质力量,它至少必须有足够的认知内容,以此来组织人类的实践生活。[12](P26)这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形成并不是毫无物质基础的,它是整个社会物质结构的产物,它的形成需要以人们的认知过程与生活经验为基础。而对于儿童来说,本身生活经验的不足以及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制约着其个体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形成。成人眼中所关注的世界放于孩子的视角中也失去了其原有的特殊意义及吸引力。
《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只有十来岁左右,他“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有的像青草的汁液,有的像干结的鼻血。裤头的下沿齐着膝盖。孩子的小腿上布满了闪亮的小疤点。”[4](P3)这是一幅典型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小孩的肖像画,我们不得不感叹作者对生活图景细节的捕捉能力之细腻。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多次描写到了黑孩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面对刘副主任的训话,他的眼前浮现的却是在密密麻麻的黄麻地中钻来钻去的薄雾以及瓜地里白皮红瓤的大西瓜。这些惟妙惟肖的描写都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小孩子眼中的世界,充满了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与新鲜感。小黑孩在面对一群修大坝的成年人时始终都有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吸引他注意力的不是“刘太阳”的训斥,也不是妇女们的闲话与家常,而是不断浮现在眼前的一幅幅大自然奇景。“黑孩转过身去,眼睛望着河水,不再看这些女人。河水一块红一块绿,河南岸的柳叶像蜻蜓一样飞舞着。”[4](P14)
福克纳小说中的班吉则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三十多岁的他却只有三岁小孩的智力。在他的脑海中没有思维能力,只有感觉和印象,而且对这些感觉和印象,他也分不清它们的先后顺序。在班吉的世界里,感兴趣的东西只有三样:那片为了给昆丁交学费而卖掉的牧场、姐姐凯丹丝以及炉子里的火光。在自己的牧场被卖掉后,昆丁并没有感到难过,因为在他的世界里,牧场一直都坐落在那里,甚至因为有了来此打球的人们而变得更加有趣。虽然已经三十三岁了,班吉却每天只能跟在一个“黑小子”的身边到处玩耍,吵吵囔囔地看别人在曾经是属于自己的农场里打高尔夫球。班吉虽然在生理上已经是成人,但天生的智力缺陷却也限制了他属于成人个体意识形态的形成。在班吉的世界中,能够引起他兴趣的没有任何成年人世界里所谓的物欲之争,即使在被送进精神病院后,他仍然什么也没有失去,因为在他的眼中,只要睡觉时能够看到炉子里燃烧的火光,那他便拥有了一切。在这两个人物的身上,作者所选取的儿童身份给我们呈现了一幅完全迥异于成年人意识形态世界的社会图景,大人们所关注的传统价值观念放置孩子的眼中失去了其五光十色的外衣,对薄雾河水及牧场炉火的兴趣取代了对利益权欲的衷情,这是对孩子纯真天性的肯定,也是对成年人传统意识形态观念的鄙弃。
传统意识形态结构颠倒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小说中主人公感官能力及想象力的无限延伸性上。伊格尔顿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深受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早期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影响。在对雅克·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基础上,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个体“想象的”与真实世界的关系。[6](P127)通过这种想象关系,主体可以获得不可估量的心理、情感和行动力量。而这种力量一旦被解放,就会冲破理性的束缚而发出自己的声音。阿尔都塞这种想象的情感力量赋予到小说中主人公身上同样展现了其强大的心灵震撼力,在传统意识形态结构的颠覆中,黑孩和班吉也分别成为了自己时代生活中的自由引导者与死亡预言家。
在对小说中的主人公进行艺术创作时,莫言与福克纳都赋予了小黑孩与班吉某种近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集中体现在他们想象力与感官世界的无限延伸性上。《透明的红萝卜》里的小黑孩可以看到或听到一般人所无法感受到的画面或声音,黑孩眼中及耳中出现的已经不是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事物,他的日常感官体验被赋予了某种幻觉或神秘色彩。
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砧子,泛着清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清幽幽蓝幽幽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4](P52)
在这里,普通的一个红萝卜通过作者特殊化的艺术处理后拥有了金子般的光芒,其灵动华美的意象也充分体现了黑孩感官体验的丰富性。《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同样具有某种异于常人的感官能力,他可以闻到树的香味,并能够听到黑夜的声音。“我能听见大伙儿的出气声,能听见黑夜的声音,还有那种我闻得出气味来的东西的声音。”[5](P75)每次死亡降临康普生家族时,班吉都有某种预感。“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听到急匆匆地走开去的脚步声,我闻到了那种气味。”[5](P33)
黑孩与班吉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在现实中几乎没有任何权力去看或者去说。而作者却选取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赋予他们这种权力,即充分打开其感官世界体验,让他们“看”到或“听”到常人所无法理解的一个世界。现实世界中被否定的权力在另一个世界中被升华到一种至高无上的维度,这种颠倒的意识形态结构为处于束缚中的情感力量寻得了一个出口,从而使得压迫下的人性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解放。黑孩眼中的红萝卜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不同的读者都会对其做出不同的阐释。从根本上来说,它的光芒中映射出的是黑孩或“黑孩们”在那个年代对自由的渴望。小说的结尾黑孩钻进了黄麻地,像一条鱼儿游进了大海,这正是获得自由的象征,而班吉对死亡的预言则昭示了战后康普生家族抑或整个南方文化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堕落与颓圮之势。意识形态传统结构的颠倒是对现实生活中政治堕落的嘲讽与反抗,这也是美学赋予艺术作品的一种力量。
结束语
作为构成政治大厦的主要基石,社会关系、社会权力及意识形态自诞生以来便时时刻刻规范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出发,它们同时也是构成人类本身存在所必需的社会因素。莫言与福克纳作品中对这些因素的关注恰恰体现了一个作家对人性最基本生存境遇的关怀与怜悯。从社会关系的边缘化到话语权的丧失,再到人性的反抗以及意识形态的颠覆,黑孩与班吉身上所体现的美学思想为我们展示了一曲处于束缚下的人性寻求自由与解放的悲歌。在伟大的作品里,政治与美学总会以最融洽的姿态对人性做出最深刻的探索,在这一点上,黑孩与班吉恰恰是两个完美的诠释。
[1]特里·伊格尔顿著,王杰,付德根等译.美学意识形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莫言.天堂蒜薹之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莫言.莫言中篇小说选[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5]福克纳著,李文俊译.喧哗与骚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6]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7]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8]杨善华.当代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陆薇.从话语的消失看《喜福会》中主体的重建[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4).
[10]Foucault,Micheal.The history of Sexuality:An Introduction.New York:Vintage Books,1998.
[11]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悲剧卷):下[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12]Eagleton,Terry.Ideology:An Introduction.London New York:Verso,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