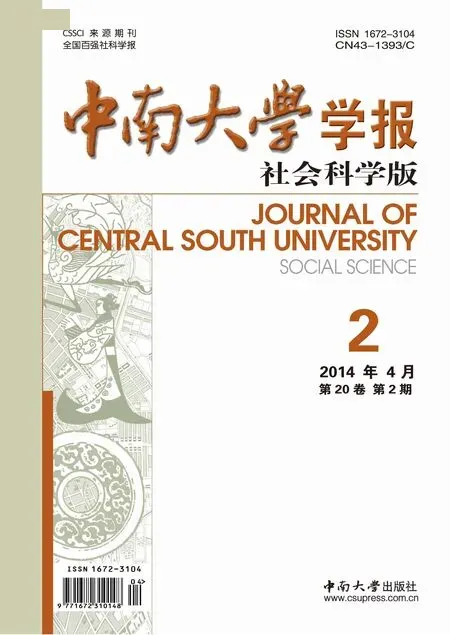郭嵩焘洋务思想对陈宝箴启动湖南维新运动的影响
王俊桥,郝幸艳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30007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关于郭嵩焘与陈宝箴之交谊,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已有总结:“(陈宝箴)与郭公嵩焘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务,负海内重谤,独府君推为孤忠闳识,殆无其比。及巡抚湖南,郭公已前卒,遇设施或抵牾,辄自伤曰:郭公在,不至是也。”[1](2003)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在当时独步一时,被时人赞称“既精且大”。陈宝箴是地方巡抚中少有的开明官僚,深得光绪帝的赏识。郭嵩焘与陈宝箴结下了深厚情谊,研究郭嵩焘对陈宝箴的影响,或许可以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湖南维新运动的启动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年更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18岁就学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订交。1847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53年在籍协助曾国藩创建湘勇、湘军,此后四年他成为湘军中极为重要的决策人物。1858年奉命入职南书房。1859年奉旨随僧格林沁办理天津海防,因反对北塘撤防忤僧王而受排挤。1861年因病回籍休养。1862年奉旨任广东巡抚。1868年又因同僚之间倾轧免官回籍。1875年奉命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公使,1878年又兼任驻法公使,不久被副使刘锡鸿以“汉奸”罪弹劾,并奉召撤回。1879年初,任期未满即卸任东归,愤而托病辞官,从此蛰居乡里,孤愤而终。
郭嵩焘以精透洋务而名垂青史,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性人物李鸿章曾对其如此评价:“生平于洋务最为关心,所论利害皆洞入精微,事后无不应验。前后条列各件,外廷多不尽知,病归后,每与臣书言及中外交涉各端,反复周详,深虑长言,若忧在已,迄今展阅,敬其忠爱之诚,老而弥笃且深,叹不竟其用为可惜也。”[2](10)他深佩郭氏对洋务的执着追求,深叹其没能得到朝廷重用。之后洋务能臣两江总督刘坤一称赞他:“周知中外之情,曲达经权之道,识精力卓,迥出寻常。”[3](580)郭嵩焘在晚年回忆其一生功过是非时,也颇有自负地称道:“吾于洋务,考求其本末与历来办理得失,证之史传,以辨知其异同,自谓有得于心。不独汉唐以来边防夷狄之患,能知其节要,即三代以上规模,亦稍能窥测及之。”[4](760)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可贵之处,就是没有仅仅停留在外交层面,而是把它提升到治国平天下的层面。在其晚年,中法战争爆发前夕,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系统阐发了他的洋务观点,最后得出结论“洋务者,治国平天下之一端也”[5](418),通过举办洋务使国家臻于富强。此时洋务内涵就扩大为“外筹应接之术,内立富强之基。”隐含的深层内涵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洋务思想发轫于鸦片战争时期,在洋务运动中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在其晚年对天下之乱的混沌局面进行探源中得以定型。可以说,洋务与其一生相始终,郭嵩焘崛起于湘军,成名于洋务。
陈宝箴(1831—1900),字相真,号右铭,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人。1852年乡试中举出仕,与左宗棠有着相似的从政经历。陈氏的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分别受到了曾国藩和沈葆桢的赏识。曾国藩赞其为:“海内奇士。”[1](1995)据郭氏称:“沈文肃公巡抚江南,奇其才,事有疑,必咨而后行。曾文正公尤许其有济时之略。”[6](414)后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时与许仙屏号为“江西二雄”。1895年,在湖南巡抚任内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办新政,开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湘学报》,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系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地方督抚中惟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使湖南从以守旧而著称的铁门之城一跃而成当时全国最富有朝气的省份。
陈宝箴与左宗棠的从政经历一样,坎坷多变,有着十六年候补岁月的经历,既无丰厚的家资,又无外力以奥援。在时势造英雄的风云际会的时代,凭借自己卓越才能和坚韧毅力,卒至通达。他以举人之身入幕府,以举办团练起家,崛起于阡陌之中,驰骋于疆场之上,历练于咸丰、同治两朝,通显于光绪朝,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从两人的履历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
其一,相同的理学信仰是他们能相知相交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都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郭氏终生崇奉程朱理学,与曾国藩同为理学经世派代表。而陈氏对理学也有深刻探究,造诣深厚:“大抵躬行实践,各有心得;不同之处,周子主静,程子主敬,用功亦微有不同。……盖就其资禀契悟以几于道,则大贤以下皆有可观,而立言垂教,则惟圣人为能无弊。是在学者之善会而已。”[1](1818)
其二,经世致用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早年都热衷于走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在科举道路上几经挫折与跌宕。郭氏五次参加会试,终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高中进士。而陈氏于两次会试不第后,毅然以举人之身投笔从戎,走上仕途之路。他们在科举之路上都非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仕途生涯也步履维艰、命运多舛。而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剧烈的社会变迁,促使他们从应试转向实用,即经世致用,把读书做学问与匡济时艰、扶危济困结合起来。
其三,相同的幕府生涯锻炼了他们的才干和毅力,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成为他们日后崛起的资本。他们都曾有或长或短的幕府生涯,郭氏在曾国藩幕府以湘军高参的身份,帮助曾国藩创建湘军,筹办钱粮,提出创建水师和征收厘金等战略性建议。这些建议对湘军的发展和壮大,并最终镇压太平军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氏曾在曾国藩幕府有过短暂的停留,因其不满于躬亲文牍,遂离去而返回江西,投入席宝田幕下,参与军务,出谋划策,屡立战功,帮助席宝田成功击败太平天国余部,声明得以鹊起。
其四,共同的相知师友更增加了他们之间的情谊。在他们周围聚集的有洋务派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刘坤一等中兴名臣。两人都视曾国藩为清朝柱石,都以尊师身份相待。曾、郭情谊自不待言。而陈氏也最服膺曾氏,陈氏自谓:“生平未受文正荐达,知己之感,倍深于他人。”[1](1801)曾氏殁后两人都悲苦万分,都表达了深沉的敬仰之情。郭氏谓:“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唐宋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辈惟我最。”[6](264)陈氏谓:“湘乡溘逝,海宇苍茫,有四顾萧然之感。嘉、道以来,疆臣饬吏整军,皆任法而不任人,以驯至大乱莫之救。湘乡起而持之,简擢贤俊,阔疏节目,天下之气为之一振。山摧梁萎,故辙易循,岂但生存华屋,洒邱山泪也!”[1](1628)他们还有交情深厚的在野绅士,如易笏山、王闿运、王先谦、李元度、张力臣、朱香荪、吴南屏、罗研生等。其中,易笏山不仅与陈氏为莫逆之交,他们与罗亨奎有“三君子”的美誉,“以道义经济相切摩。”[1](1995)而且易氏与郭氏交情甚笃,在郭氏的日记中多处可见两人交往谈论国事、学术的记载。如:“笏山来谈,言士君子处今之世,当以挽回气数为己任,而先不能自治其性情,何由起世道人心之沉锢,故必以学问变化其气质,而后能与天地之气运争衡。又言士大夫居乡,大有事业在。…….笏山近日用工,多有独见,令人竦然。”[7](309)他们这一政治结合体虽意见有分歧,学术旨趣有差别,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抱负,共同的事业,使郭陈交谊及其密友圈有着更为深厚的友谊基础。在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难时刻,儒家士大夫共有的 “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这两个素昧平生的有志之士撮合在一起,相知日深,互相提携,志同道合。
正是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一颗思想明星和一颗政治明星在湖南这块以守旧著称于天下的土地上同时冉冉升起,他们相互趋近、相互提携,逐渐驱散了盘旋在湖南上空的愁云惨雾。湖南人从此看到了希望,也使得湖南从守旧闻天下一跃而为中国最富有朝气的省份。
二
郭嵩焘与陈宝箴的人生际遇发生交集而结下深厚情谊是那个时代促成的结果,也是两人政治思想相通,文化思想相近,且彼此欣赏、互相提携而产生思想共鸣的结果。同治六年(1867),郭氏从粤抚卸任返湘,从此开始了8年的退隐生活。而陈氏于同治八年(1869)以知府发湖南候补,这段时期是他们交往的第一阶段。在郭氏日记中首次出现陈氏的记载是在同治十年十月十一日。“邀陈右铭、李次青、易笏山晚酌。”[8](499)此为郭陈交往之始。这一年郭氏53岁,陈氏40岁,但年龄与代沟并没有影响志士同心。郭氏非常欣赏比他小13岁的晚辈,认为其才气、品性、学术各方面都表现绝佳:“予读右铭疏广论,以为兼有南丰、庐陵之胜。右铭十余年踪迹,与其学术志行,略具于斯。其才气诚不可一世,而论事理曲折,心平气夷,虑之周而见之远,又足见其所学与养之邃也。予不足以知文,而要知右铭之文,非众人之所晓。因其文而窥知其所建树,必更有大过人者。”[8](508)相遇伊始,郭氏就能通过其文章学术预见到陈氏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这展示了郭氏过人的识人眼光。从中也可看出陈氏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应是其躬耕苦读的结果。他为陈氏家族在从“棚民”之家到耕读人家再到文化世家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郭陈之间的这段交往一直持续到同治十三年(1874),因海疆多事,郭氏奉诏命入京商议国事而短暂终止。这期间,郭陈还与其他官绅名士交游、会饮、早饭、午酌、晚宴,彼此都加深了了解和认识,为以后结下深厚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郭氏自光绪五年(1879)出使归来后,再无离开湖南,这就开始了他们第二段时期的交往。陈氏于光绪元年以军功被保奏为湖南道员留作补用,代理湖南辰永沅靖兵备道职务,并于光绪二年卸任返回长沙,直至光绪六年(1880)受诏命署理河南河北道而离湘。这段时期他们交往时间仅为1年多,时间虽短,但一起谈时事,论国政,彼此都从对方处获得了有益的见解和启发。郭氏自谓:“自海外归,始相见,甚欢。每过,抵掌谈论,以澄清自期,”且对陈氏的才气和品行更加表现出倾慕之情,“视人世显荣富贵夷然不以屑意,于是益信其才之宏而蓄之远也。”[6](414)时任湖南巡抚也对陈氏器重有加,“一切章奏皆出其手”[9](1687)。郭氏晚年情绪总是郁结不展,陈氏颇能洞察他的心境,知郭氏不能忘救世之心,故劝他借道家的达观作为平衡,在给郭氏回函中劝其“借蒙庄达观之说以养太和,本孔孟救时之心以持正论,并行不悖为宜”[10](230)。当陈宝箴离湘赴任时,郭氏代表湖湘好友为陈氏做了一篇《送陈右铭赴河北道序》。在序中他高度评价了陈的才德,认为陈氏已经具备了郭氏向来所推崇的知、仁、勇三德,他说:“所谓知、仁、勇三者,学素修而行素豫也。聆其言,侃侃然以达。察其行,熙熙然以和。坦乎其心而不怍也,充乎其气而不摄也。”[6](414)对于朝廷对陈氏的任命,郭氏也表达了不满,认为陈氏这样的大才理应留在湖南,“右铭本候补湖南,不留之湖南,而使远适河南,朝廷于此并少权衡。”[10](265)这实则在批评朝廷用人失策,对人才任用向无考览。郭氏确实也有先见之明,陈氏此后杀了个回马枪,因得到权臣荣禄的举荐,得到朝廷重用,升任湖南巡抚,荣膺封疆大吏,主导了湖南的维新运动,使湖南再次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湖南现代化从此开启,而陈氏也因此成为当时耀眼的地方大员,得以青史留名。
陈氏能在当时湖南有声有色地开展维新运动,由此拉开了湖南现代化的序幕。这其中既得到了暂时主政的光绪帝的大力支持,也有当时思想渐趋开化的湖南绅士的多方支援,但同时也应看到陈氏维新思想来源与郭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据陈寅恪先生在《读吴其昌撰á梁启超传ñ书后》一文中说:“咸丰之世,先祖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午宵大火,痛苦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报相倾服,许为孤忠宏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倾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也。到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也。”[11](424)从中既可看出,陈氏变法的初衷和郭陈两人的交情之深厚,又能反映郭氏思想对陈氏的影响之大,陈氏所主导的维新运动的思想可谓渊源有自。在陈三立给其父所做的行状中也提到了郭氏对陈氏的思想影响[1](2003)。可见,郭氏在陈氏心目中地位正如曹操早期重要谋士郭嘉在曹操心中的地位,如郭氏能有幸延寿至 1895年湖南新政之时,必将再如当年以湘军高参的身份为曾国藩效力一样,在维新运动中为陈宝箴充当洋务智囊的角色,共同创造一番宏伟事业,为湖南现代化做出贡献。但命运之神并没有垂青于郭氏,给他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遗憾,这也让后世之人对郭氏的命运常存唏嘘不已之感。
从《散原精舍文集》中也可以看到陈宝箴父子与郭嵩焘关系密切,非同一般。文集目录后有用小字排印的陈寅恪附言,内称其先君三立壮岁时与筠仙(嵩焘)往复商榷诗文。文集中又记述了陈三立所撰《船山师友录叙》。文称:“船山遗书‘久而后显,越二百有余岁,乡人湘阴郭侍郎嵩焘,始尊信而笃好之,以为斯文之传,莫大乎是。”[11](64)这句话虽因述及船山思想而涉及到郭氏,但从中亦可反映对其推崇之情。文集中的《郭侍郎荔湾话别图跋》,这本是为他在离开粤东前与友人王少鹤、丁禹生(日昌)、陈兰甫(澧)等十余人,同游潘氏海山仙馆名园所写的纪游小文,但也指出了郭氏“痛言古今之变,得失之宜……立自强之基,振兴变革”的胸襟怀抱。郭氏与陈氏父子畅谈洋务的具体实情可见于郭氏的日记与往来的书信中,郭氏在光绪十年给陈氏所写信中就交流了对洋务和当时时局的看法。当时中法战争即将爆发,郭氏严厉批评了言官一味言战的态度:“猖狂恣睢、暗无天日。”并说:“自通商以来,研求古今得失以知洋务本末,能规见其大,原不易言。至于粗暗洋情,所在多有,独京师无之,是何也?富贵利达之念胜有所甚蔽焉,至言要义不能入也。意旨之所尚,厚赏之招靡,然以求得所欲,而据以为真言敢谏,岂复有人心廉耻之存哉!此所尤危惧者也。”[5](410)郭氏在光绪十一年的日记中提到了与陈三立的交谈:“卞公闻之李香缘,以陈伯严(陈三立)优于文,谋致之幕府。伯严以其先施也,往见之。出而见语,所言虚浮无实,无适听者,于洋务尤远。彼此言论不能相入,而可以共事乎?因悟国家遇有事变,聚讼盈廷,无与辨其是非,相率为冥行而已。明者视之,真不直一噱。故曰:‘谈言微中,可以解纷。虚浮无实之言盈天下,能辨知者谁哉?”[12](104)卞公是当时湖南巡抚卞宝第,他想聘请三立入幕,但看到巡抚对洋务的无知,且显露出虚浮无实的态度,便没有应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郭氏与陈氏父子在洋务思想上具有相通之处。不仅如此,他们还一起讨论当时棘手的伊犁问题。郭氏记述道: “陈右铭见示毛实君孝廉至伯严书,论俄事利病,与鄙人持论正同。”[10](266)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深沉的忧患意识成为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重要因素。
郭、陈两人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西冲突、古今嬗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中西、古今之间探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以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这应该是两人结下深情厚谊的根本原因。而政治思想的相通、文化思想的相近更强化了他们之间的情谊,成为他们自由沟通、倾心交流的润滑剂。郭氏殁后,陈氏在给其的挽联中写道:“由清秘起家,岭南开府,海外乘槎,模范共推山斗重;以贰卿退老,著作等身,尘凡脱舃,乡邦怅阻岳云封。”[1](1980)既有深深的哀悼之情,也有崇高的敬仰之意。足见,两人交谊之深厚。
三
郭陈交谊甚笃,彼此给对方产生了深远影响。郭氏于1891年病逝,陈氏于1895年任湖南巡抚,其主政时的思想来源与郭氏有着很大的关联。笔者认为陈氏是郭氏洋务思想遗产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人生如戏,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和活动舞台,湖南就是郭陈两人共同的舞台。陈宝箴在这大舞台上扮演了主要角色。
一是郭氏教育思想的完善者。郭氏晚年投入很大的精力来办教育,力纠长沙三书院的陋习,求为征实致用之学,并恢复湘水校经堂,创办思贤讲舍,认为学校教育能引导人心风俗,对人心风俗的整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西方富强的根源就是求实务精,这些都得益于学校教育的兴盛,并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弊端进行了揭露。这些思想在陈氏推进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执行。陈氏在《致用精舍学规》中阐发了对教育的认识,可以发现与郭氏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指出:“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1](1236)他对三代教育的推崇及对书院教育沦落为科举附庸也进行了揭露,他说:“三代之所以造士者,至矣。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由明德而亲民,体用备焉。士无等差,而皆教之,穷理尽性,修己治人。晚周学校仅存虚名,先王良法美意荡焉。汉唐以来,体用遂分为二,国家学校之外,广建书院,纳群髦于经籍,因明制而加详焉。降及末流,考所为教,率不出制艺试帖,盖利禄之锢,蔽乎人心久矣。”[1](1872)所以,他推行教育新政的一大举措就是变革书院士习和开启民智,即要通过改革科举取士制度,以造就新型人才。正是在科举一日不废,人才无一日之兴的思想指导下,陈氏与学政江标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厘定书院章程,增加算学、物理、化学、商务等新型科目,创办时务学堂和《湘学报》,使学子们达到“请求新学、考古之外,兼可知今”的实用目的。可以说,郭氏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在陈氏推行的新政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二是郭氏吏治思想的执行者。陈氏在新政中以大无畏的勇气和锐意进取的革新意识整顿湖南官场,一改“官僚朋比,声气把持,几无复是非邪正之辨”的混乱局面,这种举措也得益于郭氏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郭氏认为吏治的好坏与否直接影响到天下的安危和民瘼福祉的改善,吏治与人心风俗有着很大关系。他早在咸丰八年就指出官僚朋比与吏道废弛的关系:“天下事任劳者必任怨。数十年来,吏道废弛,贤者无一二,不肖者朋比固结,举世皆然。”[7](109)晚年他还一直在呼吁清廷重视对吏治的整顿,日记中多处记载了重视吏治的表述:“吏治不修,民俗凋敝,所至皆畏途也。”[10](326)“天下治乱之原,全在吏治,而其根本则在朝廷。有一分实用,即有一分效验,非可以文饰为也。”[10](291)“吏治不修,不在州县而在大吏,其源尤在当国之大臣”。[10](261)这些表述清晰表明了整顿吏治关键在于朝廷是否有决心,大臣是否有作为,这种认识对陈氏影响甚大。两人经常在一起评论湖南吏治的状况,“陈右铭过谈,论及湖南吏治,以侯补府李芗垣(有棻)为最,兼提调厘金、发审两局事,所见甚卓,不止为良吏而已”[10](274)。光绪六年,两人在一次交谈中,涉及到吏治的看法,认为湖南处于危乱之势与吏治偷敝有着极大的关系,这使得陈氏在新政中把整顿刀锋指向了无人敢触动的吏治之网。陈氏认为盗贼日多,将会导致湖南之乱,他说“近今盗贼之烦,刑罚之失,无能窥求大体,而各挟其趋避之私,规己自大之见,而一行之以悻忌,皆导乱之徵也。至今不知悔祸,酿乱将不可支”[10](279)。郭氏对陈氏的忧虑给予了解答,他说:“吾谓万事原本皆在吏治。吾楚十馀年来,吏治偷敝,至不可问,虽有贤者发扬蹈厉,提而振之,犹惧不可堪也,岂夫瞻顾因循所能施其挽救之功者?并心一力,相奖为昏,岂惟酿乱而已,直是奖进而扬引之,此有心者所为慨叹而流涕也。”[10](279)对于郭氏开出的解决方案,陈氏表示认可,并引起了陈氏的强烈共鸣,即谓:“相与徵引实事数端,相对欷歔而已。”[10](280)可以说,陈氏整顿吏治决心之坚定、力度之强大和范围之广泛都与郭氏的引导有着很大关系。陈氏整顿吏治风暴引起了湖南官场大震荡,震惊朝野,群吏凛然。此后,湖南各级官吏大都能安分守己,恪尽职守,保证了政令得以畅通,为新政的顺利开展铺平了坚实的道路。
三是郭氏富强观念的实践者。郭嵩焘的富强观是建立在对西方富强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的基础之上,认为西方富强的根基不外乎矿务和汽轮舟车等实业的大力举办。他指出西方之富裕在于民众,不在国家,而中国之富裕在官府,不在百姓。他总结出只有在政教修明,风俗敦厚,百姓丰衣足食且趋功避私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磐固的基业,富强指日可待。他认为西方富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尽可能多地去广开利源,而不是简单去节约,让民众富裕才是真正的富裕,国家才能强大。郭嵩焘在几次归隐期间,经常和好友一起调查研究湖南省情,对湖南的矿产分布有着更多的了解。他认为:“湘水以西,由湘潭、湘乡以达衡、宝,径西至沅、靖;湘水以东,由澧、攸以达郴、桂,煤铁各矿,无地无之。”[5](476)这么多的矿产资源为何不能利用呢?他认为这些都是自然之利,普通百姓都可以去经营,不必全部由官府来开采。若如此,就是强夺生民之业,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滋生腐败,更重要的是百姓不能因此而得利。自身利益在得不到维护的情况下就会发生民变,导致秩序不稳,统治就会发生危机,更谈不上富强之业了。他不仅反对官办,也对官督商办表示不满,认为民办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另外,他还曾主张在湖南开办轮船公司,以兴舟车之利。但囿于“绅士相与阻难”的强大压力而作罢。不仅绅士如此,而且出现了近十年来“阻难专在官”的怪象,由此可以看出湖南风气之保守,洋务运动面临的阻难之大。由于陈氏与郭氏交情深厚,深得郭氏的思想精髓,“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1](2000)。郭氏的富强基业在陈氏主导的新政中渐渐得以实现。陈氏和郭氏一样,都曾对湖南的地形、地貌和矿产资源有过考察,意识到湖南山多田少,物产也不丰富,山石层峦叠嶂,但有五金之矿,可以让民众开采。在郭氏思想的熏陶下,他上任伊始就向朝廷奏请在湖南设立矿务总局。他在奏折中说:“当此时局艰难,度支日绌,凡有可以稍裨国计民生者,分应殚竭愚忱,尽其力之所能及;矿产为自然之利,正宜设法经理,少佐赈需;且行之目前,既可以工代赈,如渐办有成效,尤可次第推广,以为练兵制械之资,冀辅库藏之所不逮。”[13](129)可见陈氏卓越的才干、宽广的视野和强烈的家国情怀。所不同是陈氏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比郭氏更灵活,更实在,更符合当时的国情。即采用官办、民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多种形式开采矿藏。
发展湖南近代交通运输业,尤其是航运业一直郭氏生前的梦想。因为他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当年他以中国首任公使的身份乘坐小火轮船回到阔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时,遭到了湖南绅士的强烈围攻。面对官员的冷遇和绅士的仇视,郭氏的悲伤和落寞可想而知。湖南近代航运业从梦想到实现经历了一番挫折是不言而喻的。当时一个很大阻力就是遭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拒绝。后来在陈氏与湖南名士的多方努力下,张之洞才最终同意,但已经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了。湖南内河航运业的开发对湖南经济现代化的启动产生了积极影响。至此,陈氏完成了郭氏生前的梦想。除此之外,陈氏还大力支持近代企业的兴办,抵制洋货,与洋商争利,之后,铁路、发电、通讯、机械制造等新兴产业在湖南得以建立。这些都是郭氏所一直倡导的富强之基。
四
陈氏所主导的新政赋予了戊戌变法运动实质性内涵,也使得只维持了103天的维新运动并没有落入空想,还是有所成就的,在昙花一现中也结出了一个果子。郭氏晚年的洋务宣传虽在普通民众之间应者寥寥,但他能引起思想知音陈氏的强烈共鸣,郭氏洋务思想间接地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也是郭氏对湖南新政的历史性贡献。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列宁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14](26)。用这句话来证明郭、陈二人在近代中国发展中的作用恰如其分。郭氏是当时的思想家,陈氏是当时的政治活动家,他们都是爱国者,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而不断去探索救国救民之真理,不断与封建保守派作殊死搏斗与抗争,不断去支持新事物的发展。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理应受到世人的敬重。他们在当时遇到的挫折是个人的挫折,折射出近代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挫折,但正如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清政府在庚子之变后,不得已开始了为期 10年的“清末新政”,全国范围内的革新举措实际上就是郭氏洋务思想在当时得到了具体落实和实施,也是陈氏主导的湖南新政在当时的延续和发展。清政府虽顺应了历史潮流,但为时已晚,且不够真诚,历史不再给它任何延续朝命的机会,辛亥首义敲响了清廷灭亡的丧钟。
[1]汪叔子, 张求会.陈宝箴集(下)[M].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沈云龙.玉池老人自叙[C]//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十一辑,台北: 文海出版社印行, 1970.
[3]刘坤一.刘坤一遗集(二)[M].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4]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C]//郭嵩焘全集(十五).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 2012.
[5]郭嵩焘.致李鸿章[C]//郭嵩焘全集·书信(十三).长沙: 岳麓书社出版社, 2012.
[6]郭嵩焘.送陈右铭廉访序[C]//郭嵩焘全集·诗文集(十四).长沙: 岳麓书社出版社, 2012.
[7]郭嵩焘.郭嵩焘全集·日记一(八)[M].长沙: 岳麓书社出版社, 2012.
[8]郭嵩焘.郭嵩焘全集·日记二(九)[M].长沙: 岳麓书社出版社, 2012.
[9]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 4)党人传·陈宝箴[C]//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45册).台北: 文海出版社1970.
[10]郭嵩焘.郭嵩焘全集·日记四》(十一)[M].长沙: 岳麓书社出版社, 2012.
[11]王元化.王元化文集[M].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12]郭嵩焘.郭嵩焘全集·日记五(十二)[M].长沙: 岳麓书社出版社, 2012.
[13]陈宝箴.陈宝箴开办湘省矿务疏[J].湖南历史资料 1958(4):171.
[14]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C]//列宁选集(第1 卷), 北京: 人民才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