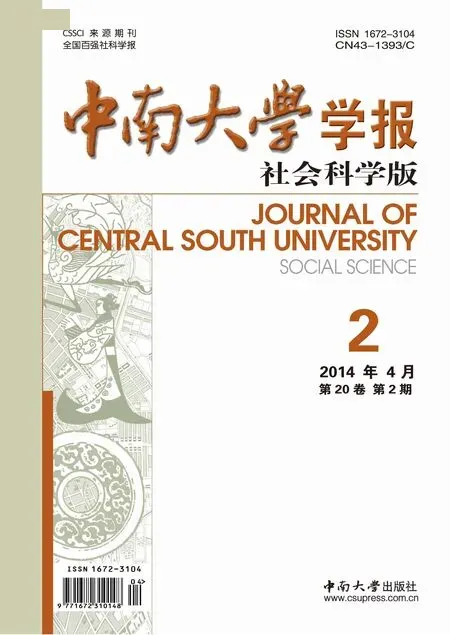字素分析法在民国新生词中的应用举隅
——兼论表音字素义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
李娜,林鹤鸣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23)
字素分析法在民国新生词中的应用举隅
——兼论表音字素义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
李娜,林鹤鸣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23)
一般认为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在对民国时期新生单音节词的字素义的分析中,发现字素义与词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运用字素分析法,对单音节词构成部件的意义进行分解,可以挖掘新造字、新生词意义的产生机制和规律;由此现象入手,进而扩展到形声兼会意字中音义关系的系统性和能产性,从而提出音义关系的系统性,不仅是词汇系统性的表现,也是生成新词的基本依据。根据音义关系的系统性原则,可以对当代汉语中新生词的字形和意义进行规范化整理;也有利于生成新的规范汉字、新的规范词。此外,字素分析法的运用也为分析单音节词的内部结构、发现词义生成的规律拓展了思路。
字素;音义关系;系统性;单音节词;形旁;声旁
世界历史上曾拥有重要地位的古老文字中,唯有汉字仍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曾在古埃及历史上活跃了3 000多年的圣书字早已作古;苏美尔楔形文字最终也没有作为意音文字存在下去,而是变成拼音文字;中美玛雅人的图像文字随其国家的灭亡也消失殆尽;古拉丁文、古希腊文,全世界也都只有少数专家才懂得;古代印度的梵文书面语也已经成为历史语言,而其口语形式则分化为千余种地方方言。惟有汉字是当今世界仅有的仍在通行使用的古老文字。汉字以其生动而形象的造字心理机制传载着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从不同侧面再现了上古初民们的心态观念和悠远的记忆,汉字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证实了华夏民族超凡的智慧。
一、字素的概念
杨端志先生在《汉语的词义探析》一书中说:
一般认为,单音词由单音词素构成,不存在词素义组合问题。但是,如果要作一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合成词的词素义在合成词词义中的地位,跟单音词的记录符号——文字中有意义的部件所表达的字素义在单音词词义中的地位相当。尽管字在词之后产生,但在现在的研究中,由于表意汉字与词义有关,因此也不妨将词义和字的部件义作一比较。合成词的词素义、文字中的有意义的部件表达的字素义,都是词的本义义素成分。文字有意义的部件反映的文字的意义又叫造意,就是造字之意。关于汉字的造意和实义,王宁先生有过一段很中肯的论述:“造意是指字的造形意图,实义则是由造意中反映出的词义。造意以实义为依据的,但有时它仅是实义的具体化、形象化,而并非实义本身,造意只能说字,实义才真正在语言中被使用过,才能成为词的本义。”[1]
也就是说,单音词的词义要素是汉字中有意义的组成部件——字素的意义。字素从字的构成而言,是能够切分到的最小的有独立意义的组成部件。在汉语系统中,一个字基本上就是一个词,字素义就是词的词义要素。因此字素的意义对单音词的意义影响很大,是单音词词义的基础,是单音词词义的有形成分。一部分字素的意义或字素意义之和就是单音词的词义。汉字也正是具有形体表意的功能,才得以传承几千载而未湮灭。
二、民国新生词字素分析
民国时期,尽管历史比较短,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新生单音节词。这些单音词,有的是新生的汉字,如“绱”“蹓”“甭”等;有的是在原有汉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意义,即所谓“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新生的词,如表示“停留”义的“歹”,表示“眼皮微合”义的“眯”,表示“踢”义的“踡”①。在《汉语大词典》中,我们搜索出始用于民国时期的单音节新生词77个②。通过对这些新生词意义与其字素义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基本字素义与词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新生汉字词
在这77个新生词中,有11个词的词形是新生的,如蹓、甭、猹等。它们的字素义是新词意义的核心。如:
【蹓1】1.滑行。碧野《没有花的春天》第十三章:“猴子们目标小,身子轻便,一爬两蹓就下去了!”
【蹓】 又作“遛”,是一个形声字。从足留声,表示与行走有关,本义是慢慢走、散步。“足”是象形字,其甲骨文字形、、,象脚趾头和脚面、脚掌的样子;金文字形,小篆字形,都是甲骨文字形的递变,本义是脚,足字加以象踝骨。秦汉以前,“足”和“趾”都表示“脚”,“脚”表示小腿。魏晋以后,三者都表示脚,但在书面语中,多用“足”;《说文解字》:“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留”是会意字,从田,从卯,“卯”甲骨文字形、,金文字形,作偏旁也写作,本义是漏水的明沟,后加“田”作“留”,“留”古文字形为或,从“田”(此田非指田地之田,而指阴沟、暗沟),引申为停留,留下。《说文解字》:“留,止也。”从以上对“蹓”的组成部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蹓”的意义与“足”有关,“滑行”的动作是由“足”来进行的,而“留”也不仅是“蹓”的声旁,也与它的意义有关,“足”慢慢地行动,不停止,即为“蹓”。所以“蹓”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
【甭】1[bén]方言。“不用”两字的合音。不要;用不着;不必。刘半农《扬鞭集·面包与盐》诗:“咱们做的是活,谁不做,谁甭活。”
【甭】是由“不”和“用”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这个“合字”是“不用”两字的合音,即将两个字组合到一起组成一个词,新字意义就是其组合字素意义之和。
猹1[cháˊㄔㄚ]獾类野兽。鲁迅《呐喊·故乡》:“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
【猹】是一个形声字,从“犭”“查”声。由字素“犭”(表示动物的类属的字)与字素“查”组合而成,两者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很明确。个人的观点是,“犭”表明此物为一种动物,“查”是被用来表明此词读音的,正如鲁迅《书信集·致舒新城》总共所说:“‘猹’字是我据乡下人所说的声音,生造出来的,读如‘查’。但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动物,因为这乃是闰土所说,别人不知其详。现在想起来,也许是獾罢。”[2]可见“查”是说明此字的声音与其有关,而在意义上没有什么联系的。因为“查”本义是“木筏”。所以这是一个根据形旁表意、声旁表音方法创造出来的典型的形声字。
(二)新生词义词
民国新生单音节词中,绝大多数都是发新芽的原有词,在《汉语大词典》的民国新生单音词中有将近85%是用这种方式创造出来的。它们的字素义与新生义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如:
髚1[qiào《篇海类编》苦吊切]翘起。胡祖德《沪谚外编·山歌·待客》:“喜鹊叫,客人到,有啥耽来微微笑,无啥耽来嘴唇髚。”
【髚】是由字素“高”与字素“亢”组合而成的一个动词。“高”是个象形字,甲骨文、金文字形都是的样子,象楼台重叠之形,后隶变做“高”;《说文解字》:“高,崇也,像台观高之形。”“亢”也是一个象形字,其小篆字形,从大(人)省,象人的颈脉形,本义是“人颈的前部,喉咙”。“高”“亢”两个字素组合在一起是“高高的喉咙”或者是“喉咙高高的”意思,这个形象就是“翘起”意思的形象化说明。因此,从字素的意义与词义上来看,二者之间可以说是以特征说明动作。
乜1[miē《广韵》弥也切,上马,明。《字汇》弥耶切]1. 眼睛略微张开。巴人《有张好嘴子的女人》:“房东太太乜着眼,仿佛胡大嫂子的脸孔是个大太阳,叫它张不开。”
【乜】是由两个变形的“乙”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乙”是一个象形字,甲骨文字形是“”,本义是“象植物屈曲生长的样子”;篆文作“”,象燕高飞时只见其略形,亦极言其小。“乜”是一个同体会意字,两个“乙”组合而成,在意义上形成一定的联系:眼睛略微张开,好像两棵屈曲盘旋着生长的植物似的,绵连在一起,彼此之间缝隙很小;好像高飞的燕子,身影越来越小……
哗2 [huāㄏㄨㄚ]“哗2”的繁体字。1.象声词。张天翼《脊背与奶子》三:“任三对手心吐几口唾沫,拿起筋条。哗!——一下抽在她脊背上。”
【哗】是由“口”“华”组合而成的形声字。“口”是个象形字,甲骨文字形,象人的口形,本义是口腔器官,嘴。《说文解字》:“口,人所以言食也。”。“华”是个会意字,从芔,从芌(xū)。“华”古陶器作,命簋作,上面是“垂”字,象花叶下垂的样子,像全枝之花,因此本义是花,隶变作“华”;《说文解字》:“华,荣也。”由“荣”引申出“多、盛、大”的意思。“哗”所拟的声音一般较大、较响,这一意义也是源于其声旁“华”的意义。因此“华”在“哗”中,不仅仅是声符,也表示一定的意义:即声音很响或很大的意思。“哗”字也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
眯4[mīㄇㄧ]亦作“瞇2”。1.眼皮微合。曹禺《日出》第一幕:“他的眼睛眯得小小的,鼻子像个狮子狗。”
【眯】是一个由“目”“米”组合而成的形声字。“目”是象形字,甲骨文字形和金文字形均为、,小篆字形,中间两划是的变体,均象眼睛形,外边轮廓象眼眶,里面象瞳孔,《说文解字》:“目,人眼,象形。”“米”是象形字,甲骨文和金文字形为,纵画不连,象米粒琐碎纵横之状,本义是谷物和其他植物子实去壳后的子实;《说文解字》:“米,粟实也。象禾实之形。”由此分析可以看出,在“眯”的意义中,“目”表明“眯”的意义与眼睛有关,是眼睛的动作;而“米”不仅表音,而且还表示眼睛“眯”动作的幅度与“米”的大小相关,即眼睛微合,留下了大约米粒大小的空间,很小。所以这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
踡2[juǎnㄐㄩㄢˇ]1. 方言。踢。《中国地方戏曲集成·安徽卷〈三踡寒桥·许亲〉》:“小奴才不认为娘,三脚将我踡下寒桥。”
【踡】是由“足”与“卷”组合而成的形声字,从足,卷声。“卷”“踡”同“蜷”,像虫子一样卷缩着身体成一团,这里强调“足”的动作性,动作由脚发出来。“卷”本为名词,古指书的卷轴,同时也带有一种形象性,就是将东西像卷轴一样卷起。在这里字素“卷”是表音的,同时也表示脚的动作有“卷”的弧度,带有一定的形象性,因而,我们认为“卷”在“踡”中也有一定的意义表现。“踡”也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
(三)民国新生单音词的特点
1. 形声兼会意字居多
由以上解析,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的新造字中会意字很少,基本上都是形声字,不过尤以形声兼会意的居多。在我们搜索出来的77个民国新造字中,只有19个形声字的声旁不表意,有54个字是形声兼会意字。可见,民国时期的单音节新生词中,运用字素组合表义不仅是创造新意的主要方式,声符也是凸显词义特征的主要承载者。
2. 形旁取诸身的居多
从构字的形旁看,也表现出极强的集中性:口字旁的字最多,有35个,占全部形声字总数的一半还多;其余39个形声字分别由“土2、糸1、犬1、金1、页1、禾1、人5、巾1、目4、火1、舌1、足3、羽2、木2、疒3、竹1、革1、耒1、食1、艹1、氵1、穴1、匚1、高1、艹1”25个偏旁分别承担着;在这39个字中,又以“亻”字旁的字最多,有5个;其次是“目”字旁的形声字有4个;再次是“足”字旁、“疒”字旁的形声字,各有3个。“口”“亻”“目”“足”“疒”都是与人的身体有关的偏旁。与身体有关的形旁在民国时期仍然有着较大的创造力,这说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认识理念始终是人们对新事物赋名的首要原则。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时候,无论人类进化到什么程度,无论思想走多远,人们对自身的认识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认识,而对自身的了解,也就自然成为赋名于新事物的首选了。
3. 形旁标属类,声旁标词义
“口”“足”“目”是动物体的动作器官,而“木”“竹”“革”“耒”“食”“巾”“金”“犬”等均是说明事物类属的类属名词。这些形旁在新生词的词性上,从某种程度也可以说起了一定的决定性的作用。“口”是身体的器官,因此与“口”这一器官有关联的也取形于口,如“喉”“咙”“咽”等;与这一器官有关的动作也多取形于“口”,如“叹”“吐”“吞”“叫”“叼”等;“口”是发声的共鸣腔,是发声器官,所以拟声词或与声音有关的词、与言语气息有关的词大多取形于口,如“嘭”“叭”“嗒”“吧”“啊”“哪”等。因此在“口”部字中动词、叹词、象声词很多。同理“足”是运动器官、“目”是视觉器官,因此除了与“足”“目”有关的身体器官等名词取形于“足”“目”(如“踝”“趾”“蹄”“眼”“睛”“瞳”“眶”等)以外,与“足”“目”有关的动作动词也大多取形于“足”“目”(如“跺”“趴”“跑”“跳”“踱”“盯”“瞥”“眯”“瞎”“盲”等)。而其余从事物名称的词则多数仍是以新的事物名称所属的名词为主。如从“木”为形旁的字“树”“林”“枫”“枝”“根”“桦”“杨”“板”“棒”“案”等等均是名词。再如从“竹”的“竿”“笔”“筋”“策”“笋”“笋”等均是名词;从“革”的“鞍”“鞯”“靴”“鞭”“鞠”等都是名词。所以我们认为,在形声字中,形旁所起的作用是标注词语所属的类别;而对于词的核心意义,声旁则作用更大,它有标明词义的区别性作用。
我们先看看几个声旁的表意性体现在哪里,如:
盯2[dīnɡㄉㄧㄥ]1. 注视;目光集中地看着一处。茅盾《第一个半天的工作》:“他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只管盯住了黄女士身上身下打量。”
仃1[dīnɡㄉㄧㄥ][《广韵》当经切,平青,端。]见“仃伶”。【仃伶】孤独。郭沫若《卓文君》第一景:“安得那月里姮娥,前来慰我仃伶!”
再如:
癌1[áiㄞˊ]病名。恶性肿瘤。如胃癌、肝癌、食道癌、皮肤癌等。也叫癌瘤或癌肿。鲁迅《书信集·致许钦文》:“(内子)本是去检查的,因为胃病;现在颇有胃癌嫌疑。”
疤[bā《集韵》邦加切,平麻,帮。]1.疤痕。老舍《骆驼祥子》四:“﹝祥子﹞摸了摸脸上那块平滑的疤,摸了摸袋中的钱,又看了一眼角楼上的阳光,他硬把病忘了。”
三、表音字素义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
索绪尔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见解:“我们的记忆常保存着各种的句段,有的复杂些,有的不很复杂,不管是什么种类或长度如何,使用时就利,联想集合参加进来,以便决定我们的选择。当一个法国人说marchons!‘我们罢!’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想到各种联想的集合,它们的交叉点就是marchons!个句段。它一方面出现在marche!‘你步行吧!’,marchez!‘你们步行吧!’这列里,决定选择的正是marchons!同这些形式的对立:另一方面,malrchons里起montons!‘我们上去吧!’,man罗ons!‘我们吃吧!’等等的系列,通过同样序从中选出。说话人在每一个系列里都知道应该变化什么才能得出适合于他所单位的差别。若要改变所要表达的观念,那就需要另外的对立来表现另外值;比方说marchez‘你们步行吧!’或者montons里‘我们上去吧!’。”由此可见,“念唤起的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整个潜在系统,有了这个系统,人们才能获得构符号所必需的对立。”这一原则大到句子,小到音位要素,“只要具有一个价值,不受这一确定和选择程序的支配”[3]。
这段话实际上揭示了语言输出过程中相似规律所起的重要作用:任何一个语言单位的输出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相似于说话者存贮在大脑中的其他语言单位[4]。语言符号的相似性是客观物质世界的相似性在我们大脑中的反映,两者均存于大脑的长时记忆中,随时听候提取和使用。长时记忆中贮存的知识单元我们称之为相似块,“人们大脑中存贮的相似块不是静止的,它一方面和感觉器官输入的信息互联系、相互作用,又能和其他相似块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就如频谱分析仪中相干、相关作用一样,也会结成一个新的相干、相关的新的相似块来”[5]。
单音节新生词的新字形或新意义产生与出现是随着人们对社会认识、理解的拓宽与加深而来的。这些新生词的字形依托于何者,词义源于何处,对此周光庆谈到:“当人们基于社会文化生活的需要而意欲认知、解释、表述以前未曾认知、解释、表述过的‘新现事物’或‘未知事物’时,他们自然地也是必然地会凭借已有的经验、知识及其语言表征(语词),在联想的激发和引导下,将原已认知、解释和表述过相关事物与之关联起来,并置起来,予以比较、类推,参照已知事物经验解释未知事物,参照已知事物的名称命名未知事物,从而顺利地实现对于未知事物的认识、解释和表述,并且由此而将已知事物与相关的未知事物系列化而使之具有某种系统性,将已知事物的名称语词与未知事物的名称语词同源系统化而使之具有同源系统性,体现出民族人的认知活动、命名活动、文化活动的次序性、连续性和规律性。”[6]
我们常说音义之间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这也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属性。也许在言语产生之初二者之间存在着任意性。不过,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对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入,新事物、新思想不断涌现,这种“约定俗成”也逐渐生成一定的“约定”,那就是音义的结合逐渐由偶然性进入到必然性。汉字是表意文字,这种表意性不仅体现在形声字的形旁,也体现在声旁中。也就是说,声旁自身也是具有表意作用的汉字。我们所分析的民国时期77个新生词,都是合体字,因此我们采用字素分析法,对这些合体字的构成部件进行分解,从其组成字素的意义入手,对其意义与声音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和了解。
如以字素“巴”作为声符的词,其意义都与“巴”的意义密切相关:
“巴”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大蛇,《说文·巴部》:“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由“巴”的形象特点取义,成为以“巴”为声旁的形声字的很多意义来源,即许多从“巴”的字都突出了“弯曲、屈曲”的意义。如:有的是突出象蛇的牙齿一样,即象“巴”虫的牙齿一样,向内生,捕获住猎物后不易脱出的特点:如“把”是握、执的意思(《战国策·燕策三》:“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就是用手紧紧握住,不使之脱手之义;农具“耙”与“杷”分别是碎土平地的农具(清郝懿行《证俗文》卷三:“《农政全书》,耙制有方耙,有人字耙,如犂,亦用牛驾。但横阔多齿,犂后用之。盖犂以起土,惟深爲功,耙以破块,惟细爲功。”)和聚拢、耙梳谷物或整地的农具(《急就篇》卷三:“捃获秉把插捌杷。”颜师古注:“无齿爲捌,有齿爲杷,皆所以推引聚禾谷也。”)都是有齿的农具,是利用齿来发挥作用的;有的是取其身形弯曲之特点的;如“弝”是指弓背中央手执处(汉焦赣《易林·干之明夷》:“弓矢俱张,弝弹折弦。”);“钯”是古代的一种兵器,也是弯形的(明何良臣《阵纪·束伍》:“授器之要,因其短长编列之,宜随其地势,每以枪筅弓弩标铳爲长兵,刀鎌钗钯牌斧爲短器。”);“跁”指小儿匍匐,后通作“爬”,就是取如同“巴”蜿蜒屈曲行进之义(清郝懿行《证俗文》卷十七:“江淮之间谓小儿匍匐曰跁。”);“爬”是指人或动物用四肢伏地慢行(明吴宽《是日往观果刻本乃复次韵》:“浓书銕把纯绵裹,深刻蟹上潮泥爬。”);“疤”即疤痕,也常常是弯曲的形状,而且还好似“巴”一般圆圆隆起的(老舍《骆驼祥子》四:“﹝祥子﹞摸了摸脸上那块平滑的疤,摸了摸袋中的钱,又看了一眼角楼上的阳光,他硬把病忘了。”);再如辔首垂下部,即辔革,看似如“巴”形,所以写作“靶”(《文选·左思〈吴都赋〉》:“回靶乎行邪睨,观鱼乎三江。”李周翰注:“靶,马辔也。);“蚆”是一种软体动物,即贝,古时以贝壳作货币,故亦指货币(清姚鼐《硕士约过舍久俟不至留书与之》诗:“秀句成见寄,岂不珍朋蚆。”),就是取“巴”软件的特点;“芭”即芭蕉,取“巴”指“大”义(唐张希复段成式《赠诸上人联句》:“乘兴书芭叶,闲来入豆房。”);“笆”是用竹或荆条编成的障隔,取“巴”“长、软”的特点(唐柳宗元《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诗:“引泉开故窦,护药插新笆。”);此外“爸”即父亲(《广雅·释亲》:“爸,父也。”章炳麟《新方言·释亲属》:“今通谓父爲爸。古无轻脣,鱼模转麻,故父爲爸。”),也是指举斧以率耕者之中最有权势的那个人,就是一家之长“爸爸”,此义也是训自“巴”的“大”义。
再如:
“尧”《说文·土部》:“尧,高也。”段玉裁注:“尧,本谓高。陶唐氏以爲号……尧之言至高也。”,所以从“尧”得声的形声字有的有“高、大、多”义,如“峣”形容高的样子;“顤”形容头高长的样子(《说文·页部》:“顤,高长头。”);“饶”形容食物很多,富裕,丰足(《左传·成公六年》:“夫山、泽、林、盬,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娆”是形容女人很多,所以带来许多的烦扰(《淮南子·原道训》:“其魂不躁,其神不娆。”高诱注:“娆,烦娆也。”);“膮”是指猪肉羹,肉多所以(《仪礼·公食大夫礼》:“膷以东,臐、膮、牛炙。”郑玄注:“膷、臐、膮,今时臛也。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皆香美之名也。”);言语很多而显得杂乱,即争辩、喧嚣之事,所以写作“譊”(《文子·上礼》:“世俗之学,擢德攓性,内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譊名声之世,此至人所不爲也。”);人要求很多,即贪求不止写作“侥”(《魏书·清河王怿传》:“昔新垣奸,不登于明堂;五利侥,终婴于显戮。”);“獟”指健捷勇悍,即强大、力量大(《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去病﹞诛獟駻,获首虏八千余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人。”《汉书·霍去病传》作“獟悍”。颜师古注:“獟,健行轻貌也,字或作趬。悍,勇也。”);好马、良马写作“骁”;好箭、响箭写作“髐”(《汉书·匈奴传上》:“冒顿乃作鸣镝”颜师古注:“应劭曰:‘髐箭也。’镝音嫡。髐音呼交反。”)。“荛”指柴草(《管子·轻重甲》:“千乘之国,不能无薪而炊。今北泽烧莫之续,则是农夫得居装而卖其薪荛。”尹知章注:“大曰薪,小曰荛。”);“蛲”蛲虫,动物体内的一种寄生虫(《淮南子·原道训》:“泽及蚑蛲。”);“铙”是古代军中用以止鼓退军的乐器,青铜制,体短而阔,有中空的短柄,插入木柄后可执,原无舌,以槌击之而鸣(《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铙止鼓。”郑玄注:“铙,如铃,无舌,有秉,执而鸣之,以止击鼓。”贾公彦疏:“进军之时击鼓,退军之时鸣铙。”),这几个字都有“小”的意思,其“小”的意义也是源自于共同的声旁“尧”字,是由其“高、大”之义反义引申而来的。“硗”指土质坚硬瘠薄(《国语·楚语上》:“瘠硗之地,于是乎爲之。”韦昭注:“硗,确也。”);“墝”也是指瘠薄的田地(《荀子·儒效》:“相高下,视墝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杨倞注:“墝,薄田也。”)这里的“贫瘠”之义也是由“尧”的“多”之义反义引申而来的。由“高”义引申出“向上”的意义,如“翘”即举起(《庄子·马蹄》:“齕草饮水,翘足而陆。”);“跷”指举足,抬腿(《广韵·平宵》:“跷,揭足。”);“趬”也是翘的意思,即举起(《西游记》第三三回:“﹝孙悟空﹞说了誓,将身一纵,把尾子趬了一趬,跳在南天门前,谢了哪咤太子麾旗相助之功。”);“晓”即太阳升起了,所以特指天亮、明亮(《说文·日部》:“晓,明也。从日,尧声。”段玉裁注:“俗云天晓是也。”)。由“向上”的意义反向引申出“向下”的意义,如“浇”即以水灌溉(唐王建《原上新居》诗之九:“扫渠忧竹旱,浇地引兰生。”)。由“向上、向下”之义又引申出“上上下下、绕”的意义,如“绕”指丝线上上下下转个不停,即缠绕、缭绕(《山海经·海外西经》:“﹝穷山﹞其丘方,四蛇相绕。”);“桡”指弯曲(《易·大过》:“栋桡,凶。”陆德明释文:“桡,曲折也。”);“遶”指围绕、环绕(三国魏曹植《杂诗》之三:“飞鸟遶树翔,噭噭鸣索羣。”);“襓”指剑套(《礼记·少仪》:“劒则啓椟,盖袭之,加夫襓与剑焉。”郑玄注:“夫襓,劒衣也,加劒于衣上,夫或爲烦,皆发声。”孔颖达疏:“云‘夫襓,劒衣也’者,熊氏云:‘依《广雅》“夫襓,木劒衣。”谓以木爲劒衣者,若今刀榼。’”),包裹在剑的外面,就像缠绕着一样;“穘”指缩耗,因变形而不平,弯弯曲曲,拱拱翘翘的(《周礼·考工记·轮人》:“是故以火养其阴,而齐诸其阳,则毂虽敝,不藃。”);“墝”指土地不平,就是有高有低(汉刘向《说苑·建本》:“丰墙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壤必先矣。”《集韵·去效》:“墝,土不平。”);手挥动,摇动写作“挠”(《庄子·天地》:“手挠顾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陆德明释文:“司马云:动也。一云:谓指麾四方也。”);内心忐忑不安恐惧,戒惧写作“哓”(明方孝孺《送凌君入太学序》:“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后可以当大任;有轻贵富之心,然后可以成大功……浦江凌允恭哓然有志操,以郡诸生选入成均。”)或“憢”(《集韵·平萧》:“憢,《说文》:‘惧也。’引《诗》‘唯予音之哓哓。’或从言从心。”)。
声音和意义是存在于同一个词的统一体中,彼此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7]。雷缙碚认为,“新词的产生以及旧词获得新义往往有待于新概念的产生。新概念的产生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认识新事物形成新概念,二是对旧有概念的再认识,在此主要是对旧概念的分析和概括,从而形成新的概念,三是概念的抽象化。”“如我们面对一新事物,以至在我们的头脑里形成了一个新概念而需对其命名时,我们不可能摆脱旧概念的影响而给与一个所谓的‘全新的’名。我们往往是将此新概念与我们所已有的旧概念相比较,或比其相似性,或比其相关性,从而予以命名,得到新词。记录新概念的新词与记录旧概念的旧词在语音上往往相同或相近,这样便可以产生‘相似’类的同源词和‘相关’类的同源词。”[8]“新词产生的主要途径是词义的引申分化。新词在语音方面有两种情况,一是语音不变,在一个词内增加新的义项;一是语音稍变,由一个词派生出新词,成为派生词。同一语根的派生词——即同根词——往往音相同相近,意义相同相关。在同词族中,派生词的音和义是从其语根的早已约定俗成而结合在一起的音和义发展而来的,因此带有了历史的可以追索的必然性。”[9]因此,我们认为,词的发展是以声音为纽带,以声音来系联一组组意义上相近或相关的词语,从而使得词语表现出一定的系统性。
现代思维科学研究成果表明,人们在认识新事物时,最容易产生类比联想,即根据新事物的性质、情状、功能等某一方面的特征,去和以往认识的事物进行类比,并在心理上给予认同。作为思维的工具的语言,作为反映客观世界的符号系统,就要将这这种类比联想反映或表现在语言活动中,赋予这些具有相同特征的事物一个有着相同、相似或相近、相关关系的立意名称,并将这一名称以共同的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10]。
因此,我们对先人造词的过程梳理出这样一条思维顺序:当我们要对一个事物或行为、现象等命名时,首先从外部形象特点上或者是可感知的最突出的特点上来寻找命名的依据或依托,然后从头脑中已有的概念中进行搜索,而这一搜索是首先由声音开始的,然后再付诸于形象(即字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许多声符相同的字意义上有许多的共通之处,而它们所属的形旁却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是因为,先在声旁上取得了彼此意义上的联系,然后依部分类,将其归属到其所属的各个大的类别上来。即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一听到声音,就知道所说何意。因此,声符信息对词义的判定有着决定性作用。
王力先生曾说:“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都是容易体会到的,唯有词汇的系统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因为词汇里面一个个的词好像是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11]对单音节词进行字素分析,探寻其中字素义与词义的关系,既有利于阐释词义的源流,也便于我们发现汉语造字的一些规律。
注释:
① 这些增加新意的汉字,有的语音没有发生变化,如“踡”,有的语音发生了变化,如“歹”表新意的时候,读作“dāi”,“眯”表新意的时候读作“mī”。语音的变化由于不涉及到字素的意义,因此在这里不展开讨论。
② 这77个新生单音词分别是乜1、歹3、髚1、甭1、壓2、猹1、鉨1、咚、哪1、哪2、嘞2、顎、嘩2、嚓1、嘭、唷、哼2、和3、吭3、唉2、份2、噘、唸2、幛、呱2、嚯2、嚜3、唼3、呲1、噲3、咧3、吧2、啊1、啊2、啊3、啊5、眯4、燴、緔、舔、蹓1、翌1、盯2、嚇2、仔3、榫1、翹2、癌1、仃1、佈、踡2、篢3、癟3、鞢2、朳(木换做耒)、唣、跕4、忡(心换做土)、糈(米换做食)、唵2、嗒3、睄1、啵1、蒙2、睔2、淜2、橧1、窨2、匨2、咯2、疤、咩、唔3、唔4、啛2、嚕2、侷。
[1] 杨端志. 汉语的词义探析[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79.
[2] 鲁迅. 鲁迅全集(第1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62.
[3]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79-181.
[4] 龚玉苗. 隐喻和明喻异质论的认知解释——以相似性特征为研究视角[J]. 外语教学, 2013(1): 37.
[5] 张光鉴. 相似论[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2: 5.
[6] 周光庆. 汉字的系统性与词汇的系统性[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7, 26(2): 57.
[7] 杨光荣.《说文段注》校改中的形、音、义观念[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5): 30.
[8] 雷缙碚. 从概念形成的角度分析同源词的词义联系[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 19(4): 42.
[9] 陆宗达, 王宁. 训诂与训诂学[M]. 太原: 山西教育育出版社, 1996: 64.
[10] 潘明霞. 汉英“以物喻身”复合词认知考察[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3(4): 33.
[11] 王力. 汉语史稿[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545.
Examples of application of grapheme analysis method in new charaters creat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On the function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nd and the meanings in development of the language
LI Na, LIN Hem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116023, China)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nd and meaning is arbitrary, while it is an established relationship. When we analyie the single-syllable words which were created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apheme, meaning and the word’s meaning. Using the grapheme analysis method, we can explore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rules of the new words and new words, meaning .From these phenomena, we extend to the Syste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s of words, which can produce much more new words, which shows that the systemic systemically makes the vocabulary systemically and it is also the basic foundation to build new words. Depending on the systemic, we can clean up the new character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ore specificatly, and new standar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new words can alse be created. In addition, the grapheme analysis method can broaden the thought of analyzing the monosyllabic words and their generate rules.
graphe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nd and the meanings; systematic significance; One-syllable word; pictograph; Phonetic element
H109.4
A
1672-3104(2014)02-0254-07
[编辑: 汪晓]
2013-11-21;
2014-03-1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汉语词汇通史研究”(10AYY004);辽宁省社科规划项目“民国白话教科书与汉语词汇系统的构建研究”(L13BYY01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汉语发展演变数据平台建设与研究”(13&ZD133)
李娜(1974-),女,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民国词汇研究;林鹤鸣(1990-),女,辽宁营口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