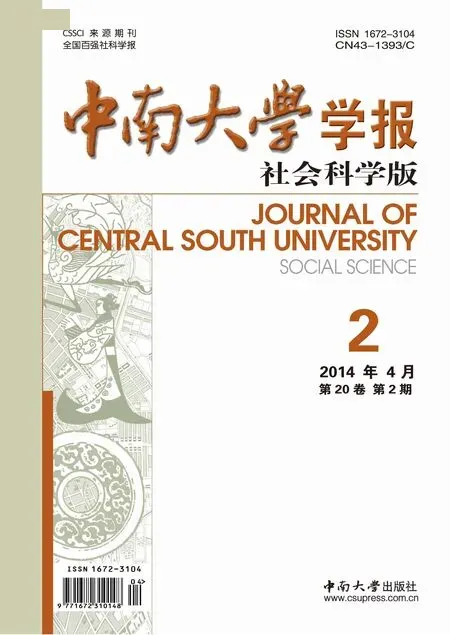两宋词论尊雅观中的情志纠偏
祝云珠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宋代词论尊雅观是包括借诗而言词的词体雅化,即词体诗化理论和就词而言词的词体雅化(词体“本色论”)理论。诗化之雅论包括“以诗为词”“自是一家”“诗词同源”等等观点,本色之雅论则包括“别是一家”“骚雅”“清空”等观点。尊雅观在词体创作层面要求音协律合,字琢句炼,才高意新,创作者人品高洁;在词体风格论层面,以“雅”为审美要求,强调意高趣雅;在思想层面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以道、释为辅。其中,在两宋词论尊雅观的创作层面中,“缘情”与“言志”问题是个备受关注而争论不休的问题,根据笔者对两宋词论尊雅观的分析,发现“情志”是其核心矛盾,在“情”与“志”的矛盾冲突和渗透中,“情”不断被倡雅词论者引入新的因素从而被赋予新的内涵,到了南宋,“情”与“志”终于达到了理论上的和谐。
在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131)这里帝命夔去“教胄子”,“诗言志”是从思想情感上影响和规范人,并进行伦理教化。《毛诗序》吸收先秦的诗乐理论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2](269)在“诗言志”的基础上,肯定了诗歌的抒情功能。而陆机的《文赋》正式标举“诗缘情”等等。概言之,“情”与“志”是两个含义各有侧重的概念,“情”一般指未经规范的个体情感,是自然性个体意识的体现。“志”主要指经过道德规范的主体情感,是一种社会性群体意识的表现;“志”的内容往往与社会政治、功名抱负相关,而情多指儿女私情、个体闲情。情与志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而在词论尊雅观中,情志问题尤为突出,在北宋词论尊“雅”观中,倡雅词论者重在纠“情”之偏执即通过引入“情性”“情致”“气象”“气格”等来纠正唐五代以来的淫靡艳情。
一、北宋:重在纠“情”之偏
从中唐的刘禹锡提出以雅易俗的主张到五代欧阳炯的《花间集序》提倡“清雅”,皆孕育着文人对词的“雅化”要求。然而,这种雏形期的尊雅观却树立了词“缘情”的思想倾向。其中刘禹锡的《竹枝词序》提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焉。”[3](56)实际是不满民间词的不谐音律,但赞同民间词的“含思宛转”与“淇澳之艳”,即是认同词的缠绵动人的情感。而《花间集序》所描绘的:“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4](1)这些“诗客”们处于美酒佳人的温柔之地,所歌之词必然是以男女情事为主,从而奠定了词“缘情”的基调,而这一时期的“情”大多是男女之情。
宋初,由于受唐五代绮靡词风的影响,词体多描写艳情。“诗言志”“词缘情”“诗庄词媚”的观念深入时人心中,其创作中的情感表现为“情其性”即赤裸而无节制地表现艳情。而北宋尊雅词论者提倡闲雅、清淡的词风,一扫绮靡、浮艳的词体风气,其理论核心是旨在纠“情”之偏执。这一时期,诗化之雅论者与本色之雅论者纠淫靡之情的措施各异。
(一)引“情性”、“志”“气”入词
北宋前期,词论者就抒情主体的情感而言,已经开始注重词作中主体情性的抒发,尤其是注重表现主体的人生感怀,虽然仍是私密化而非社会性的情感,但“情”之范围得到扩大,不再囿于男女艳情。“情”的层次得到提升,不再是由感官刺激而发的情爱感受而是阅历社会后的深层次人生感悟即是诗化之雅论者提倡的引“情性”入词。如陈世脩《阳春集序》:
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日月浸久,录而成编,观其思深辞丽,韵律调新,真清奇飘逸之才也。噫,公以远图长策翊李氏,卒令有江介地,而居鼎辅之任,磊磊乎才业何其壮也?及乎国已宁,家已成,又能不矜不伐,以清商自娱,为之歌诗以吟咏情性,飘飘乎才思何其清也。核是之美,萃之于身,何其贤也[5](188)。
序中虽指出冯延巳的词具有“俾歌者依丝竹而歌之”“娱宾遣兴”的娱乐功能,但亦注意到冯词“吟咏情性”且有“思深辞丽”的审美特点。“吟咏情性”一词是《毛诗序》对诗歌特征和功能的认识,但毛序又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具有浓厚的儒家诗学色彩。以诗学之“吟咏情性”论词,陈氏可谓导夫先路。陈氏所提倡之“情性”是在“国已宁,家已成,又能不矜不伐,以清商自娱”的背景下而发,创作者是权臣与雅士相兼的身份,蕴含着此“情”是作者历经社会政治生活后的文人情怀。而潘阆更是提倡词作当抒发一种无拘无束、自然自在的雅士情怀,其《逍遥词附记》写道:
茂秀茂秀,颇有吟性,若或忘倦,必取大名,老夫之言又非佞也。闻诵诗云:‘入郭无人识,归山有鹤迎。’又云:‘犬睡长廊静,僧归片石闲。’虽无妙用,亦可播于人口耶。然诗家之流,古自尤少,间代而出,或谓比肩。当其用意欲深,放情须远,变风雅之道,岂可容易而闻之哉!其所要《酒泉子》曲子十一首,并写封在宅内也。若或水榭高歌,松轩静唱,盘泊之意,缥缈之情,亦尽见于兹矣。其间作用,理且一焉。即勿以礼翰不谨而为笑耶。阆顿首[6](12)。
《附记》将诗学理论用于词的创作和品评。“颇有吟性”是肯定茂秀具有诗人的情性,且这种情性“当其用意欲深,放情须远”,同时对词作者的创作心态提出要求“盘泊之意,缥缈之情”,是强调一种不拘形迹、自在无拘的创作心境。结尾处潘阆指出词作与诗“其间作用,理且一焉”,词与诗的功能是相通的,促使词体由“酒席文学”向“言志文学”过渡,潘阆的词学见解对苏门的“诗化之雅”论不无启发作用。结合《附记》和《酒泉子》词作不难看出,潘阆提倡的“情性”是一种自在不拘、渴望归隐的情感,这已完全摆脱了“花间”樊篱。如果说陈世脩的《阳春集序》中的“性情”是初步由男女私情走向士大夫的个人感怀的话,《附记》中的“性情”则已完全是一种自由洒脱的诗人情怀,这时的“情”逐渐向“志”靠拢。
以诗论词、以诗衡词大帷幕的拉开,当推苏轼。他在《与蔡景繁书》中云:“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语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晚即面呈。”[7](1662)赵令畤《侯鲭录》卷七记载:“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5](179)这些论断皆拿诗来做为参照,在与诗的比较中得出词的优劣。苏轼又大力提倡“以诗入词”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主张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注入词中,即引“志”入词,改变了五代词所缘之相思眷恋的狭隘之情。他的词学观念得到苏门学士的认同,张耒论词,尤重情性,“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至道也”[5](205)。张耒明确拈出“情性”二字,把情性的自然流露看成词创作的根本动因,只要真情弥漫,词就“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本于《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与韩愈《答李翊书》所主张的“气盛言宜”说略同机杼。张耒论词把儒家的诗教、文统融入其中,提倡真性情。
首次举起词体雅化旗帜反对词体艳情的是苏门词人。“以诗为词”“自是一家”的提出,最初是反对风靡北宋的柳永之俗词、艳曲,标志着词体雅化意识的自觉。苏轼以“志”“气”统“情”,词体内部也被输入雅的因素,如苏轼之词注重陶写情性,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注入词中,其《卜算子·缺月挂疏桐》,黄庭坚评论说:“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5](197)这首词作于乌台诗案后,抒写词人“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独、高洁情志。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描写威武雄壮的狩猎场面,并由此激发起为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他那首响彻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词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浩大的气象和雄奇的景物是唐末宋初词中所少有的。词人写景时,把大江、浪涛写得惊心动魄、有声有色;写人时,英雄豪杰形象尽现,突出了赤壁古战场的英雄精神,词人那种无比阔大的襟怀、豪迈雄阔的抱负、英雄报国无门的感慨,都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对词的意境是很大的开拓。理论上,从苏轼对待秦观词的态度也能体现其对词体气格的要求,如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
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苏子盼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阵子》语也[8](182)。
苏轼之所以常戏少游之词是因为其词气格不高,鄙俗、狭窄。他批评柳永艳俗、鄙下之词,而赞扬柳永的具有“唐人高处”之词,亦是苏轼引志、气入词,提高词格之词学思想的体现。而黄裳《演山居士新词序》更是把歌词主要当作自持情性、写志立言之工具。他说:“风、雅、颂诗之体,赋、比、兴诗之用,古之诗人,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含思则有赋,触类则有比,对景则有兴,以言乎德则有风,以言乎政则有雅,以言乎功则有颂。……故予之词清淡而正,悦人之听者鲜。”[5](201)引志入词,提倡清淡、雅正的词风,等等。
北宋诗化之雅论者提倡“以诗为词”“诗词同源”等等,其核心是引“志”入词,强调“以志统情”,并非不能抒情,他们主张抒发符合自然、天理的人之“性情”即“性其情”。词论者提升词体气格,其宗旨是为了借助诗体达到雅化并推尊词体的目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词论者太过于重视词体的“言志”功能,而忽略了其协律等艺术形式方面的内容,有着消解词体本色的趋向。而北宋本色之雅论者则采取不同的举措来解决时下流行歌词的淫靡言情。
(二)倡富贵气象,主情致
苏门词人自觉地推尊词体,并亦开始思索词体本位的问题,如李之仪与晁补之提倡“闲雅”,注重词体“本色”。李之仪在《跋吴思道小词》提出词体“自有一种风格”[5](200),并称晏殊、欧阳修、宋祁词“风流闲雅”,晁补之《评本朝乐府》提出“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而称晏殊之词“风调闲雅”[5](181)。其实,这种闲雅的词风是建立在创作主体的“富贵气象”之上的。
“气象”原用于指自然景象、社会风貌等等,至唐被大量用来评品诗歌,如皎然《诗式》:“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9](2)严羽的《沧浪诗话》:“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10](151)“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10](158)并认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等等[10](7),这里“气象”当指作品的整体精神风貌。而晏殊却提出了“富贵气象”说,据吴处厚《青箱杂记》记载:
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11](46)
在《韵语阳秋》也记载了有关晏殊诗“富贵”者:“元献诗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此自然有富贵气。”[12](490)晏殊不仅提倡“富贵气象”,诗歌也具有“富贵气象”,而其词集《珠玉词》,名为“珠玉”取其“珠圆玉润”之意,观其集名及集中之词,的确是富贵不俗、闲雅有余,正是“富贵气象”的典型。晏殊与欧阳修等生活在太平盛世,生活富贵优游,他们把这些生活与他们的文人雅士的情趣、修养反映在词作中就形成了“闲雅”之风。李清照的《词论》评价秦观的词“终乏富贵态”[5](53)。其实李清照这种批评与苏轼评秦观词“以气格为病”皆是批评秦观词写儿女艳情与风格柔弱。而把“富贵气象”引入词中,使词不再卑弱淫艳,这时词之情感不再囿于脂粉猥俗的艳情,而更重视超然物质之外的高雅意趣。“气象”与“气格”皆是重视其间的“气”,文人佳作素以“积气”、“养气”著称,这种“气”其实是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的大感慨充盈在作品中而成,其力度大于“情”而与“志”相近。
从李之仪的“自有一种风格”到李清照的“别是一家”皆是重视词体本色的表现,他们对待“词情”是怎样的呢?李之仪的《跋吴思道小词》虽然肯定“以《花间》所集为准”,然而提倡“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提倡有“韵”之词。李之仪并不反对花间传统的“词情”,但这种情感应当“宛转䌷绎,能到人所不到处”[5](204)。不再是简单的艳情。如前所论李清照的《词论》引入“富贵气象”提升词体气格,她所倡之“情致”,当是有气格之情致。这种“情致”的力度是大于“情”而小于“志”,是一种有韵而蕴气之“情”。总之,北宋本色之雅论者并不反对男女情感的描写,但已超出了腻脂淫艳之气。
由于北宋诗人身处太平时期,加之唐五代淫靡诗风的影响,歌酒欢娱、男女情爱在词作中多有体现,所以北宋倡雅词论者在对待“情志”问题时,多纠“情”之偏执。南宋内忧外患、国势衰萎,爱国之情、豪壮之志渗透词体,使南宋倡雅词论者在协调“情志”问题时,不仅纠“情”之偏执,而且纠“志”之偏执,使词体内部矛盾达到和谐,从而呈现词作外在表现的雅正。
二、南宋:“情”“志”之偏兼纠
词论者在理论上不断提出雅化、推尊词体,但在创作实践中还是有大量艳情词作的出现,所以南宋倡雅词论者继续纠词作中“情”之偏执。这一时期词论者重在引入“礼”来节制“情”。
(一)以“礼”节“情”
南宋倡雅词论者提倡词之情应“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云:“发乎情,民之性也。”“发乎情,止乎礼义。”肯定抒情的合理性,但又提出情感须“无邪”、“止乎礼义”。以“礼”节“情”,诗教思想被意图雅化、推尊词体的论者运用到了词学理论中。
由于唐五代及宋初,艳词盛行,诸多词人一味沉溺于男欢女爱的艳情描写,绮靡香浓。针对词坛绮靡之风,论者多从儒家“温柔敦厚”的伦理原则出发,批评缘情淫艳之曲,要求词须约情合中,有节制、有规范。论者以儒家诗教来矫正艳词、重振雅词,在南宋表现得较为突出。如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序》开头即提出《诗经》的“止乎礼义”,批评唐宋以来的艳词“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5](249),显然是以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为标准,并且认为艳词溺于情而伤风教,不能持人向善。胡寅《酒边词序》进一步强调词要继承《离骚》《楚辞》为代表的“变风变雅之怨而迫,哀而伤者”,他认为词与诗皆能发乎情,批判词“曲尽人情”却不能“止乎礼义”。曾丰评黄公度词:
夫颂类选有道德者为之,发乎情性,归乎礼仪,故商周之乐感人深。歌则杂出于无赖不羁之士,率情性而发耳。礼仪之归欤否也不计也。故汉之乐感人浅。本朝太平二百年,乐章名家纷如也。文忠劳公,文章妙天下,长短句特绪馀耳,犹有与道德合者。……考功(黄公度)所立不在文字,余于乐章窥之,文字之中所立寓焉。……凡感发而输写,大抵清而不激,和而不流,要其情性则适,揆之礼义而安。非能为词也,道德之美,腴于根而盎于华,不能不为词也[5](217)。
由此可见,南宋词体雅化理论是不排斥词的抒情性的,但抒情要合乎道德规范,其实宋代词论家所谈之“礼”已经转化为天理、人理。“在汉人那里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具有外向性,要求‘情’合于外在的礼;而宋人则糅合儒、释、道诸家学说共同的扬性抑情的成分,提出‘吟咏情性之正’的抒情主张,既不违背人之常情,又将情纳于‘理’、‘道’的规范,其内涵是‘正心’、‘诚意’、‘思无邪’,重在心性修养。”[13](136)因而,受理学影响较深的南宋尊“雅”词论者提倡以理节情、以理统情。
王炎曰:“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惟婉转妩媚为善。……不溺于情欲,不荡而无法,可以言曲矣。”[5](225)既肯定词的“曲尽人情”,又认为情不能任意放纵流宕,要有节制。林景熙评胡汲古词“清而腆,丽而则,逸而敛,婉而庄 ……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亦出于诗人礼义之正。”[5](240)林正大自称其词“婉而成章,乐而不淫”[5](235),类似之说,不胜枚举。以礼节情,抒情委婉是儒家诗教在尊“雅”观中情感表达方面的映射。以诗教之“礼”节情,这是它与北宋的诗化之雅与本色之雅的“纠情之偏”的最大不同:诗化之雅的“性情”、“气格”和本色之雅的“情致”、“气象”是在力度上对“情”的丰盈、补充,而“礼”则是对“情”之低靡、柔弱的格调的禁制。
(二)以“本”救“志”
词至南宋,“言志”入词走向极端,尤其是辛派末流流于叫嚣。词论者为维护词体本质特征,开始纠“志”之偏即是以“本”救“志”,而不使词中之“志”太过。“志”之偏执的外在表现为词风的粗狂。南宋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评时人与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就用了“粗豪”这一贬语。此后,与辛弃疾同时代的王炎在为自己的《双溪诗馀》作序时,亦对时风有所贬抑,“今之为长短句者,字字言闺阃事,故语懦而意卑。或者欲为豪壮语矫之,夫古律诗且不以豪壮语为贵,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惟婉转妩媚为善,豪壮语何贵焉?”[6](170)他认为“语懦而意卑”和一味“豪壮”都是在“情”与“志”两个向度上的过分偏执,而词“曲尽人情”、“婉转妩媚”方为本色。宁宗嘉定三年(1210),詹傅为郭应祥《笑笑词》作序,提到“近世词人,如康伯可,非不足取,然其失也诙谐。如辛稼轩,非不可喜,然其失也粗豪”。张炎也是坚持词之本色,反对粗豪之词,如他论词时提到:“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5](232)等等。为了维护词体本色之雅,张炎、沈义父等尊“雅”词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和主张。他们精研词法、妙解音律,注重章法、意境、旨趣。如沈义父撰《乐府指迷》中论作词之法:“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不失柔婉。”[8](227)此论中之“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不失柔婉”,“意”当是“志”之意,此处是为了避免“言志”走向极端,风格流于“狂怪”,而失词之本色。
张炎的《词源》是宋代词学的总结,仍然强调“节情”,如张炎强调“为风月所使”“为情所役”之词非雅词。其《词源》卷下说:“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14](29)张炎已由宋初的“缘情”说上升到“言志”说,但情、志兼具,所言之情要合法度,不能“为情所役”。此论可上溯到《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注:“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谓诗歌情感之“中和”,认为诗歌表达情感时要适度、中正,不可过激、失度,要符合传统诗教之“温柔敦厚”。张炎把传统诗论观引入词论中:“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14](23)肯定词之“吟咏情性”,但应“乐而不淫”有节制、合规范,“约情和中”方不失为“汉、魏乐府之遗意”,等等。至此,“情”与“志”达到和谐,才能最终出现“骚雅”之词。当然,由于《词源》完成于元代,可以说,至宋元之际,在理论上,词论完成了“情”与“志”的和谐,但词人在实际创作中却仍不免有“怨而迫、哀而伤”者也。
总之,词论尊“雅”观中的“情”与“志”之间的关系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情与志的和谐发展。既言志,也要抒发适度的情感。即“志之所之,不为情所役”;其次,情与志的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已经得到了转化,化成了一种缠绵悱恻、挥之不去的沉郁,持久而幽深。前者在宋代词论尊“雅”观中表现较为突出。后者在清代的词论尊“雅”观中表现较为突出,如陈廷焯提倡的“沉郁顿挫”及况周颐提倡的“重、拙、大”等等。
[1]孔颖达.尚书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C].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0.
[2]孔颖达.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C].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0.
[3]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词[M].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4]李一氓.花间集校[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5]张惠民等编.宋代词学资料汇编[M].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6]金启华等编.唐宋词集序跋汇编[M].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7]孔凡礼校点.苏轼文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8]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 中华书局1986.
[9]皎然.诗式丛书集成本, [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0.
[10]严羽著, 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11]吴处厚撰, 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97.
[12]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3]邓莹辉.两宋理学美学与文学研究[M].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4]张炎著, 夏承焘校注.词源[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