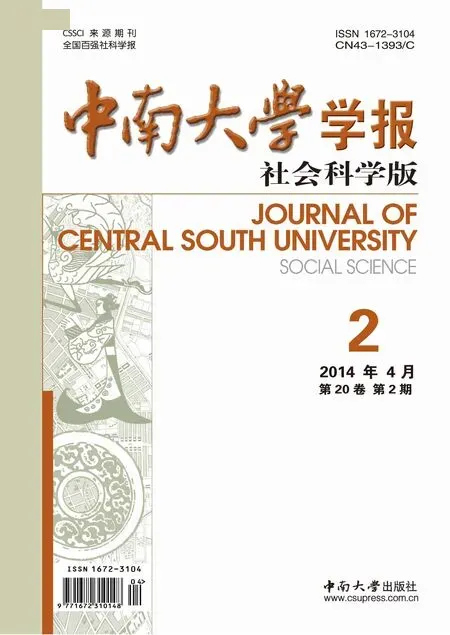受贿罪之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的量化研究
林竹静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上海,200042;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上海,201199)
一、量化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的必要性
在受贿罪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似乎很少会像计算受贿金额那样,去深究受贿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利用了职务便利,到底为他人谋取了何种利益或多少利益。作为侵害公权力行为在受贿罪罪状规定中的最直接表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似乎只是一个判断犯罪成立与否的构成要件要素,而无进一步对其进行量化的必要与可能。显然,这种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的量化不足将使我们只能得到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的定性结论,却无法根据不同侵害公权力行为的严重性程度在量刑上做出有效区分。在某些原本处于犯罪“临界状态”的侵害公权力行为中,这种因为缺乏对侵害公权力行为有效量化所导致的刑罚偏差——要么作无罪认定,要么视同一般受贿罪定罪量刑——就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们先来对比两起因在侵害公权力行为的定性上存在认识差异导致情节类似而判罚迥异的案例。
(一)侵害公权力行为处于犯罪“临界状态”的案例
【案例一】被告人李某,原系某市财政局局长。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在担任某市财政局局长期间,于1993年1月至1999年2月,先后19次收受某县、区财政局局长等人行送的“礼金”“红包”,共计人民币91 000元。李某的辩护人提出,李某收受上述款项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构成受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有关人员送钱的目的是希望李某在工作中给予支持和关照,但无具体的请托事项,公诉机关也没有向法庭出示李某为单位谋取利益的具体证据,因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上述构成受贿罪的指控不能成立。[1]
【案例二】被告人丁某,原系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以下简称“兰大二院”)原党委书记兼基建领导小组副组长。检察机关指控:丁某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收受负责承建兰大二院医疗综合大楼土建工程及该院家属楼工程的建筑公司经理张某人民币50万元。2006年,丁某被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从轻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一审宣判后,丁某不服,向省高院提起上诉。理由是自己收受50万元是单纯的受贿行为,不论是在主观思想还是在客观行为上,均没有为对方谋取利益。即使不廉洁,也没有在公务活动中不廉洁,其行为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受贿行为,违反了党纪、政纪,但不应以受贿罪论处。而省高院经审理查明后认为,丁某明知他人送财物的目的与自己的职务行为有关而予以接受,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廉洁性,构成受贿罪。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
(二)从案例反观对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进行量化的必要性
考察上述两个案例,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即其中的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均明显低于一般受贿案件中所表现的侵害公权力行为的严重性程度,甚至可以说,都处于构成犯罪的“临界状态”。在上述“财政局李某受贿案”和“兰大二院丁某受贿案”中,从犯罪定性的角度看,之所以存在单纯利用职务便利是否构成犯罪的争议,其症结在于理论和实务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存在不同理解。单纯利用职务受贿不构成犯罪的观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纪要》(《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笔者按)规定,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省高院将与职务行为有关的收受财物行为仍定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有扩大解释之嫌,有可能彻底颠覆‘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要件,这恐怕与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也是相悖的。”[3]而认为单纯利用职务便利受贿应构成犯罪的观点则主张,“只要在客观上完成符合受贿罪数额标准的受财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已经承诺、实施或兑现为行为人的利益,即使没有牟利的对应性供述,财产流转的客观事实与贿赂意图的主观故意内容将原本存在错位的受贿罪受财物与谋利要件有效联结,能够追溯性地印证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概括故意。”[4]但是无论如何,“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显然在行为严重性程度上要低于典型意义上作为实行行为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我们知道,在受贿罪中,刑法所要保护的对象并非公私财产所有权,而是国家公权力。因此,如果缺乏对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的有效量化,仅依靠受贿数额显然无法完成对受贿罪罪量的准确评价。这一点在上述侵害公权力行为呈非典型状态的受贿案件中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类案件中,虽然其侵害公权力行为的严重性程度要明显低于一般受贿罪中所表现的典型严重性程度,但由于立法和司法解释上均没有对侵害公权力行为做出过合适的类型区分和严重性程度量化,因此,司法者就只能在侵害公权力行为构成犯罪与否上作择一的定性选择。就这样,在这类存在非典型侵害公权力行为的案例中,我们就更清晰地看到由于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量化不足所导致的刑罚偏差——要么无罪,要么十年。
二、量化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的可能性
(一)对犯罪行为进行量化的理论前提
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样的道理,犯罪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虽然说,我们都认同“制度和整个人类社会只能由人的行为所形成而别无其他,因此可以用个人行为的术语来分析,也可以根据个人行为的原则来解释。”①甚至于“社会学家所研究的制度、组织和社会,可以通过研究个别人物的行为而毫无遗漏地加以认识。”②也就是说,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早已毋庸赘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些学者看来,“直至当代,关于社会行为的研究都仅仅集中于定性分析,缺乏、甚至没有定量分析,它从根本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发展。”[5]果真如此,横亘于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巨大难题。既然我们迄今尚未攻克对社会行为(上位概念)进行定量研究的理论堡垒,那接下来又该如何展开对犯罪行为(下位概念)的量化分析?
如果我们把“量化”简单理解为精确的“数量化”,把对社会行为的定量研究按照自然科学中的数量化标准去要求,以犯罪数额的量化标准来要求犯罪行为,那么对犯罪行为的量化将始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犯罪行为的量化之所以比犯罪数额的量化要粗糙,是由于对行为的量化涉及一些很难在量上进行数值确定的事物。人的行为、心理活动极为复杂,很难分离出对人的行为有影响的独立变量,而且,人的态度、意向是潜在的主观因素,在量的规定性上通常是非数值性的,因此,无法用完全精确的、定量的方法进行研究。虽然说对犯罪行为的精确“数量化”实难测定,但“量化”毕竟不等同于“数量化”。退一步而言,所谓精确或者不够精确,其标准也只是一个相对值。早在两千年前,哲学家庄子就曾说,“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③。现代物理学、微积分学和科学哲学更告诉我们,微观物质世界具有无穷小的可分性,只要可能,对物质不论做多少次分割,都会得到一个非零的量。既然物质可以分到无穷小的量,那么这也意味着所谓的再精确的数量化也根本不可能绝对精确地计算出无穷小的数量值。既然自然科学的量化都已承认“测不准”,我们对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犯罪行为严重性程度量化研究,就更无需要求精确数量化。
(二)犯罪行为严重性程度量化的刑法表现
在当前的刑法规定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关于犯罪行为严重性程度的量化是被涵括进情节、后果等规定中一并加以考量的。刑法分则各项具体罪状表述中的“情节严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后果特别严重”等规定,其中都含有对犯罪行为严重性程度的粗略量化。只不过,相比于犯罪数额规定的客观明确,情节或后果的严重与否更多的只能依靠司法者的主观判断和自由裁量。可既然“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显然,如果我们不在刑法条文或司法解释中对情节严重与否的具体量化标准做出明确规定,仅把量化犯罪行为严重性程度的重任寄托在司法者的酌情判断上,那么,这种对犯罪行为严重性程度的量化效果只能是聊胜于无的。
通过刑法条文或司法解释的方式确定情节(或后果)严重与否的法定标准,可以有效避免上述酌定标准所产生的宽严失距问题。其具体的规定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刑法条文中以法定情节的方式加以规定。在刑法分则的四百余项罪名中,直接通过刑法条文对不同的侵害行为严重性程度进行明确量化规定的只占少数。如在刑法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中,该条第1款规定了构成犯罪的一般情节,所配置的法定刑区间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第二款规定了八项加重处罚情形,配置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又如在刑法第 263条抢劫罪中,该条第1款规定了构成犯罪的一般情节,所配置的法定刑区间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的八项加重处罚的情形,配置的法定刑区间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更常见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司法解释对包括侵害行为严重性程度在内的情节(或后果)标准做出明确规定。如在2004年“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中,对刑法第215条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中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标准分别做出明确规定。在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条中,对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和第339条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中的后果严重、后果特别严重的具体标准分别做出明确规定。然而,在受贿罪中,除了索贿情节从重处罚的规定外,刑法和司法解释再无任何关于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的法定情节标准设置,这就直接导致了侵害公权力行为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因为缺乏明确的适用标准在量刑中只能发挥若有似无的作用。
三、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的量化
要对受贿罪中针对公权力所实施的侵害行为严重性程度进行量化,我们首先要将司法实践中表现形式各异的具体侵害行为加以类型化。通过对现行刑法受贿罪罪状规定的文本考察,我们发现,有关侵害公权力行为的严重性程度,除了刑法第386条“索贿的从重处罚”这一法定加重情节规定外,作为侵害公权力行为的具体条文表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再无任何明确量化区分。为使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在受贿罪的量刑中真正发挥作用,我们将以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为标准,对司法实践中不同表现形式的具体侵害行为加以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法定情节”的形式对其加以明确。
(一)四类应通过法定情节明确的侵害公权力行为类型
1.“利用职务便利状态”④与“利用职务便利行为”
在受贿犯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人“以权换钱”的筹码,只有具有一定职务,手中握有职权的人,才有资本接受或者索取贿赂。而行贿人之所以愿意给予财物实施贿赂,也正是看上了受贿人手中握有的职权,意识到受贿人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取利益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也就是说,对于受贿人而言,其“招权纳贿”很多时候未必都典型地表现为“拿人钱财,为人谋利”,通过职务行为的实际履行来达成与行贿人之间的“银货两讫”。由于公权力的稀缺性,处于“卖方市场”地位的公权力拥有者只要稍加展示其所拥有的“职务便利”,尚无须待其将该职务便利付诸行动,恐怕就早已是“贿客盈门”。而这种“利用职务便利状态”时所表现出的对公权力的行为危害,就其严重性程度而言,自然要小于付诸行动、造成实害的“利用职务便利行为”。
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到受贿罪中对“利用职务便利状态”与“利用职务便利行为”的区别规定。例如,美国《联邦贿赂法》对贿赂犯罪做了区分轻、重罪的不同规定。在轻型受贿罪中,只要证明公务员为了或者因为其“公务员”地位在法定外接受了“有价之物”,即可构成犯罪,而在重型受贿罪中,则要求收受贿赂与具体的履行职务行为相对应,两者的法定刑也差别悬殊。同样,《澳大利亚刑法典》在第141节和第142节中分别规定了联邦公职人员“受贿罪”和“收受腐败利益罪”,对前者规定的最高法定刑是10年,而对后者只有5年。[6]《菲律宾刑法典》在第210条和第211条分别做了“直接受贿罪”和“间接受贿罪”的规定,对前者配置“较重监禁的中间刑至最高刑”,对后者配置“矫正监禁的中间刑至最高刑”。[7]《波兰刑法典》在第 228条的第 1款、第 3款和第4款对“利用职务便利状态受贿,未实际上为他人谋取利益”和“利用职务便利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做了区分量刑,对前者配置的法定最高刑为 6个月至8年,而后者为1至10年的有期徒刑。[8]《斐济群岛刑法典》在第106条和第107条做了“公务腐败罪”与“公职人员勒索罪”的区分,对前者的法定最高刑为7年,后者则为3年。[9]因此,在借鉴上述国家受贿罪区分立法的基础上,按照“利用职务便利状态”和“利用职务便利行为”这两种严重性程度不同的公权力侵害行为作“罪状——法定刑”区别规定,就显得很有必要。
2.“违背职务的利用”和“不违背职务的利用”
实际上,关于在受贿行为中区分背职与否的规定在我国古代法律中早已有之,即认为在贿赂罪的定罪量刑中应具体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受有事人财,而曲法科断者,为枉法赃;另一种是虽受有事人财,判断不为曲法者,为不枉法赃。前者受财枉法,后者受财不枉法,虽然都是犯赃罪,不枉法赃较枉法赃罪要轻,因而两者要区别对待。1957年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22稿第205条、第206条曾也分别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而没有枉法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或者要求其他不正当利益而枉法的,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样明显体现了不枉法受贿的处罚要轻于枉法受贿。但后来,立法者却又认为“这样划分意义不大,而且容易给人造成似乎受贿本身并不枉法的模糊概念,因此予以删除合并。”[10]因此,在之后的1979年刑法典和1997年刑法典中,均没有再将背职与否作为设置法定刑的依据。笔者认为,无论是刑法典的繁简还是具体罪名的增删,对其合理性与否的评判都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法治重启,在受贿罪的罪名设置上“宜粗不宜细”符合当时的司法实践需要,但是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仍只片面强调受贿数额而忽视公权力要素在受贿罪罪量计算中应然作用的发挥,就既不符合当前社会发展对立法精细化的总体要求,也与国际上根据公务人员是否违背职责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将受贿罪区分为违背职责的受贿罪与不违背职责的受贿罪这一立法通例相脱节。
例如,《德国刑法典》第331条规定的“接受利益罪”,实际上是指公务人员接受他人利益后,在其职务活动范围内,也就是通过不违背职务上的义务的行为给予回报的受贿罪,故法定刑较轻,最高为3年徒刑;而第332条规定的“索贿罪”,就是指公务员接受他人利益后,以侵害或可能侵害其职务义务,也就是通过违背职务上的义务的行为给予回报的受贿罪,故法定刑较重,最高为5年徒刑。[11]《日本刑法典》第197条规定的“受贿罪”,也是指公务人员在其职务活动范围内受贿,故法定刑较轻,最高为3年徒刑;而第197条第3款规定的“枉法受贿罪”,就是指公务员在职务活动中作出不正当行为的受贿,故法定刑较重,最高为15年徒刑。[12]《意大利刑法典》在第318条“因职务行为受贿”和第319条“因违反职责义务的行为受贿”分别规定了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和2年至5年有期徒刑两种轻重不等的法定刑区间。[13]《奥地利刑法典》在第204条公务受贿罪第1款和第2款中分别规定了背职受贿罪与不背职受贿罪,前者的最高法定刑是3年,后者则为1年。[14]《葡萄牙刑法典》在第372条“受贿实施不法行为罪”、第373条“受贿实施合法行为罪”分别规定了最高8年和最高2年的不同法定刑。[15]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第121条“不违背职务的受贿罪”、第122条“违背职务的受贿罪”规定前者的法定刑最高为7年,而后者则可判至无期徒刑。[16]此外,包括俄罗斯、西班牙、波兰、匈牙利、芬兰、瑞士、埃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冰岛、越南、马其顿、汤加、科索沃等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对违背职务受贿与不违背职务受贿在立法上明确了轻重不等的法定刑配置。
3.“履职当时无受贿故意”与“履职当时有受贿故意”
在受贿罪中,权钱交易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也就是说,受贿人之所以愿意冒着触犯刑法的风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无非是见财起意,看在财物的份上。然而,也可能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如受贿人在履行职务当时并无收受贿赂的主观故意,当其职务行为客观上为行贿人带来利益时,出于感激之情,行贿人行送财物,受贿人也予以笑纳。这显然与通常情况下“履职当时有受贿故意”的一般受贿行为存在很大区别。那这种“履职当时无受贿故意”而事后受贿的行为,又该如何评价呢?笔者认为:既然受贿罪所保护的犯罪客体系公权力的不可交易性,而公权力既是一项可体现为具体职务和职权的真实存在,又体现为国家权力和政府威信的抽象存在。那么,对公权力的侵害行为就既包含行为对具体职务与职权不可交易性的真实侵害,也包含行为对公民与政府之间信赖关系的抽象侵害。而后者当然包括对过去、现在、未来的职务行为的信赖。因此,即便是国家工作人员就已经实施的、在履职当时无受财故意的职务行为收受贿赂,该行为也必定是对公民与国家政府之间信赖利益的伤害。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事后受贿的行为与上述“利用职务便利状态”单纯收受贿赂的行为一样,都构成受贿罪。当然,体现在罪量和相应的刑量配置上,事后受贿和一般受贿是存在差别的。
新近,在不少国家关于受贿罪的刑事立法中,都有了针对一般受贿和事后受贿的分别规定,并为两者配置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例如:2006年修订的《意大利刑法典》在第318条第1款就一般的“因职务行为受贿”配置以“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后,在第2款规定“如果公务员因已经履行的职务行为而收受上述报酬的,处以 1年以下有期徒刑。”[13]2006年修订的《罗马尼亚共和国刑法典》在第308条对受贿犯罪作出一般配置以“三年以上十五年以下严格监禁”的法定刑规定后,在第310条“收受不当利益罪”中规定“公务员在完成职务行为或完成与其职务有关的行为后,直接或间接收受金钱或其他利益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严格监禁。”[17]2005年《塞尔维亚共和国刑法典》在第367条第1款背职受贿(处2年以上12年以下监禁)、第2款不背职受贿(处2年以上8年以下监禁)和第3款特殊公职人员受贿(处3年以上8年以下监禁)规定的基础上,在该条第4款规定“公职人员在实施或不实施本条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公职行为后,就该行为而索取或收受礼物或其他财产利益的,处三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监禁。”[18]2008年《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刑法典》在第261条第1款背职受贿(处1年以上8年以下监禁)、第2款不背职受贿(处1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的基础上,在该条第3款规定,“公职人员在实施或不实施本条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职务行为后,就该行为而索取或接受非法报酬、礼物或其他财产利益的,处罚金,或者三年以下监禁。”[19]从上述国家刑法典对一般受贿行为与事后受贿行为的“罪状——法定刑”区别规定中可见,相关国家均对“履职当时无受贿故意”的事后受贿行为配置了比“履职当时有受贿故意”的一般受贿行为相对更轻的法定刑。
4.“职内受贿并渎职”和“职外受贿职内渎职”
“职内受贿并渎职”,即受贿人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而收受行为人的财物,这是受贿犯罪的常态。“贿随权集”,行贿人之所以给受贿人行送财物,正是看中了受贿人在任职期间手中握有的,可以为其带来利益的公权力。而受贿人也正是意识到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才会在任职期间将公权力 “待价而沽”,大肆收受贿赂。然而,既然有权钱交易的典型,也就有权钱交易的例外。在实践中,还存在这样两种“职外受贿”的情况:行贿人通过“期货投资”的方式,在行贿人任职前通过行送财物结交“感情”,在受贿人任职后再图回报;或者受贿人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离职后再收受行贿人财物。对此类“职外受贿”,也有一些国家通过区分立法,明确了各自不同的法定刑。
例如,《日本刑法典》第197条第2款规定,即将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在其将要担任的职务上,接受请托,接受、索要或约定贿赂的,在成为公务员或仲裁员的场合,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97条之3第3项规定,曾任公务员和仲裁人员在任职的时候接受请托,曾为职务上的不正当或没有实施正当行为方面,收受、索要或约定贿赂的时候,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20]《韩国刑法典》中规定“曾任公务员、仲裁人者在任职期间接受请托,实施违背职务之不正行为后,收受、索取或者约定贿赂的,处五年以下劳役或者十年以下停止资格。”[21]《泰国刑法典》在第148条、第149条一般受贿罪(处五年至二十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最高处死刑)的基础上,在第150条规定,“公务员在没有被任命公务员前要求、受贿或者同意收受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在当公务员时因而执行或者不执行其职务的,处五年至二十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两千至四万铢罚金。”(基于1959年刑法修正案第4、5、6条修改。)[22]此外,美国、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喀麦隆、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等国也有关于事后受贿相比一般受贿减轻处罚的规定。由于“职后受贿”可以当然涵盖入“事后受贿”的时间段中,也可视为对“职后受贿”做出了明确的减轻法定刑规定。
(二)侵害公权力行为类型区分与法定化的标准说明
除了上述严重性程度差异较明显的四类侵害公权力行为类型外,根据不同标准的行为类型区分,我们还可以把受贿罪中的侵害公权力行为分为“作为形式的侵害公权力行为”与“不作为形式的侵害公权力行为”,“指向某项特定公权力的侵害行为”与“概括故意的侵害公权力行为”等。应该说,基于不同的认识角度,对行为的类型区分是无穷尽的。那么,笔者又何以选择上述四类侵害公权力行为类型并主张通过“法定情节”的方式加以明确,理由何在?
为方便说明,我们将受贿罪中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的量化值简称为“行为量”。与此同时,我们再引入“行为值”概念。所谓“行为值”,是指侵害行为在抽象“静止状态”下所呈现出的严重性程度。例如,表现为客观危害,“违背职务的利用”就要比“不违背职务的利用”在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的“行为值”上要高。同样,表现为主观恶性,“履职当时有受贿故意”也要比“履职当时无受贿故意”在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的“行为值”上要高。然而,和任何社会行为一样,犯罪行为的发生也必定发生在一定的时空背景内,要完整地对其进行分析,我们必须测量它的动态。《汉书·韩安国传》上说:“冲风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可见,“行为量”的大小不仅由“行为值”决定,还与行为与对象之间的“时空距离”有关。行为与对象的时空距离越大,相同的抽象“行为值”所表现出的实际“行为量”越小。例如,同样“行为值”的侵害公权力行为,由于“职内受贿并渎职”时侵害行为与对象之间的“时空距离”要小于“职外受贿职内渎职”时,因而,最终体现在“行为量”即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上,“职内受贿并渎职”要高于“职外受贿职内渎职”。
再回过头来看上述四类侵害公权力行为的类型区分。其中,前三类就是按照“行为值”大小所做的侵害公权力严重性程度量化区分,第四类则是以侵害行为与对象之间“时空距离”为标准所进行的区分。应该说,在由“行为值”与“时空距离”共同构成的“行为量”——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的量化过程中,可作出的行为类型区分远不止上述四种。例如,上述“作为形式的侵害公权力行为”与“不作为形式的侵害公权力行为”也可视作不同“行为值”的侵害公权力行为类型区分。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无论在客观危害还是主观恶性上,作为形式的犯罪都要比不作为形式的犯罪更为严重。但是,这种“行为量”上的区分度尚无以法定情节的方式加以立法(或司法解释)确认的必要,司法者完全可以通过自由裁量,以“酌定情节”的方式,将两者不同的“行为量”在量刑上表现出来。通过对各国刑法受贿罪罪状规定的考察,笔者也没有发现将侵害公权力行为方式的作为与否作为法定情节规定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在对不同的侵害公权力行为进行“罪状——法定刑”设置的时候,除了重点关注侵害行为类型区分的明确性外,同时还要对类型区分的必要性加以考虑。
四、侵害公权力行为量化的立法价值与应用
为了对受贿罪中侵害公权力行为的严重性程度进行合理量化,笔者对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刑法典或单行刑法中的受贿罪规定进行了文本考察,上述“四类应通过法定情节明确的侵害公权力行为”正是基于这一考察所做的行为类型区分。同时,通过对受贿罪规定的域外考察,笔者发现,较之日本等一些国家在受贿罪立法上的周延细密、“不厌其烦”,我国在受贿罪刑事立法上就多少显得过于“微言大义”了。当前,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受贿罪刑事立法,通过更加精确的罪状设置来保障定罪量刑的准确性已成共识。在此过程中,对侵害公权力行为的量化将充分显示其立法价值。
(一)侵害公权力行为量化与“罪刑系列”立法
“罪刑系列是犯罪形式多样化的立法反映”,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罪刑系列”的立法形态一般都存在于多发性犯罪中。由于这类犯罪发案率高,犯罪经验相应较丰富,犯罪人有较大可能通过处理犯罪信息来改变“传统的”与法律直接“对号”的行为方式,规避法律制裁的多种犯罪形式便继而出现。[23]当单一的刑法规定不足以有效规制形式多样的犯罪形态时,“罪刑系列”的立法状态就应运而生。包括美国模范刑法典中的盗窃罪规定,日本刑法中的受贿罪规定等等,均属于“罪刑系列”的立法模式。[24,25]
在日本刑法关于受贿罪的“罪刑系列”立法中,单纯受贿罪、普通受贿罪、枉法受贿罪即是按照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所作的犯罪形态区分。在单纯受贿罪中,受贿人侵害公权力的行为表现为“利用职务便利状态”,行为危害性程度最低,因此,法定刑规定也最轻;在普通受贿罪中,受贿人侵害公权力的行为表现为“利用职务便利行为”,但该公权力行为的履行并不违背职务规定本身,因此,在同等受贿数额的情况下,法定刑较重;在枉法受贿罪中,受贿人侵害公权力的行为表现为“违背职务的利用公权力”,因此,在同等受贿数额的情况下,法定刑规定最重。同样,事前受贿罪与事后受贿罪的规定也有效区分了受贿人在履职当时是否存在受贿故意(体现为“行为值”)以及侵害公权力行为与受贿行为之间的关联性程度(体现为“时空距离”),因此,对事前受贿罪与事后受贿罪配置区别于普通受贿罪的法定刑,也正是“罪刑系列”立法形式的具体体现。
(二)侵害公权力行为量化的立法假设与司法应用
在受贿罪中,侵害公权力行为量化的出发点是案例,落脚点则是刑罚。要使侵害公权力行为量化研究能够真正对现实司法有所助益,关键还在于如何通过立法上更为精确合理的罪状设置,使受贿罪中不同程度的侵害公权力行为能够与不同轻重等级的法定刑区间达成最大限度的罪刑均衡。按照现行《刑法》第385条第1款对受贿罪一般犯罪形态的概括表述,受贿行为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仅凭这样“粗线条”的罪状表述,要实现不同程度侵害公权力行为与不同法定刑之间的罪刑均衡显无可能。那么,如何利用上述侵害公权力行为的量化成果来完善受贿罪的罪状设置呢?
要使对侵害公权力行为的量化能够最终落实到精确量刑上,我们首先要设置一个“基准罪”。所谓“基准罪”并非是特指某一个具体犯罪,而是指从司法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受贿罪的一般犯罪形态。以现行《刑法》第385条第1款为我国受贿罪“罪刑系列”立法的最初模版,笔者拟将受贿罪的“基准罪”设置为:“国家工作人员在任职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如果以上述对侵害公权力行为的量化结果来对这一“基准罪”作分解,这一“基准罪”行为特征是:首先,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便利行为,但其对公权力的利用尚在职务权限之内;其次,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在行使公权力的同时存在受贿故意;再次,行为人侵害公权力行为和受贿行为均发生在任职期间。应该说,这种形态的受贿行为是实践中最常见的,以此为“基准罪”,辅之以包括受贿数额、公权力自身重要性程度等罪量评价要素的共同作用,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基准刑”区间。而当侵害公权力行为的具体形态偏移出“基准罪”的界域,如表现在客观方面,侵害公权力行为仅达到“利用公权力状态”的程度,或者侵害公权力行为达到了“违背职务的利用”的程度;或者表现在主观方面,当行为人行使公权力当时无受贿故意,甚或表现在侵害公权力行为与受贿行为的关联性程度上,当行为人并非是在任职内侵害公权力并收受贿赂,而是在任职前或任职后收受贿赂,那么,与侵害公权力行为“基准罪”的修正量一致,在刑罚设置上,也应该对“基准刑”做相应的轻重调节。
五、结语
在对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的量化上,虽然说,立法愈精细愈有利防范量刑偏差,但凡事“过犹不及”,我们必须清楚,量化毕竟并不等同于数量化。同时,警惕维纳(Wiener N)的告诫:“任何想把精确的公式应用于这些不准确定义的量的企图,都是胡闹和时间的浪费。”[26]既然我们不可能奢望通过精确数量化的方式对不同严重性程度的侵害公权力行为进行量化排序,那么,除了对上述在严重性程度上区分度高的侵害公权力行为类型做“罪状—法定刑”的明确规定外,我们也应该容许不同类型的侵害公权力行为在严重性程度上的灰色地带存在,这些就只能通过罪状上的“(酌定)情节”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加以补强。
注释:
① G·霍曼斯:《基本的社会过程》,载J.斯美舍尔编:《社会学》,第32页,转引自《社会行为的定量分析》,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4期。
② G.霍曼斯:《评论》,载《社会学调查》第34卷,第231页,转引自《社会行为的定量分析》,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 4期。
③ 《庄子·天下篇》
④ 按照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受贿罪的构罪要求,要成立犯罪,在客观方面仅具备“利用职务便利状态”尚未足够,还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为他人谋取利益”做了包括“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扩大解释。基于这一解释,“为他人谋取利益”就不再只是一个与“收受贿赂”相对应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实体行为,也可能只是一个与行贿人支付的“预付款”相对应的“期权”。
[1]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宁刑初字第 110号刑事判决书[C]//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第2辑).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2: 255.
[2]兰大二院原党委书记受贿获刑 10年, 终审维持原判[EB/OL]http://www.china.com.cn/law/txt/2007-07/19/content_8545961.h tm, 2013−6−23
[3]于志刚.新型受贿犯罪争议问题研究[M].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1: 369−370.
[4]薛进展, 张铭训.“贿赂犯罪慎改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9): 49−57.
[5]蒋影明.社会行为的定量分析[J].江海学刊, 1994(4): 45−50.
[6]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M].张旭, 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10−113.
[7]菲律宾刑法典[M].陈志军译.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 76−77.
[8]波兰刑法典[M].陈志军译.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85−86.
[9]大洋洲十国刑法典[M].于志刚, 等译.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9: 234−286.
[10]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58.
[11]德国刑法典[M].庄敬华, 等译.[M].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 167−169.
[12]黎宏.日本刑法精义[M].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508−511.
[13]最新意大利刑法典[M].黄风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115−117.
[14]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M].徐久生译.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 105−106.
[15]葡萄牙刑法典[M].陈志军译.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163−164.
[16]杨景镇.海峡两岸贿赂罪立法比较研究——兼谈大陆贿赂罪立法的完善[J].中国刑事法杂志, 1994(3): 92−95.
[17]罗马尼亚共和国刑法典[M].王秀梅, 等译.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 92−94.
[18]塞尔维亚共和国刑法典[M].王立志译.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1: 161−162.
[19]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刑法典[M].王立志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2: 127−128.
[20]黎宏.日本刑法精义[M].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508−511.
[21][韩]李在祥.韩国刑法总论[M].[韩]韩相敦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2]泰国刑法典[M].吴光侠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34−36.
[23]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1): 346.
[24]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M].刘仁文.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5: 150.
[25]黎宏.日本刑法精义[M].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508−511.
[26]嘎日达.关于社会科学中量化研究的深层思考[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6(3): 8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