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深度的刻写与镜像的自我表达
龚奎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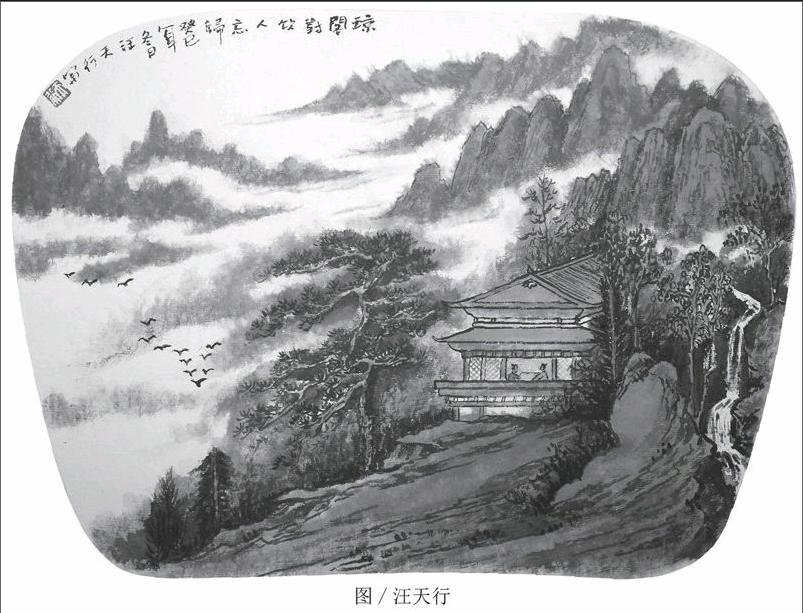
目前江西诗坛主要是靠60后、70后中青年诗人在支撑,能够接上诗歌棒的80后、90后新锐者不多,导致有点代际断层现象,值得警惕,这可能与人口基数较少有关,也可能与“孔雀东南飞”相关,还可能与经济欠发达有关,更主要的还是与诗歌氛围及媒介缺失有关。
江西没有真正能够坚持持久的诗歌刊物,无论是官刊亦或是民刊。所以江西诗坛需要有杞人忧天的眼光,需要有补充新鲜血液的胸怀,尤其需要有刊物对诗歌及诗人的刊载与传播。如今,《创作评谭》在过去一直关注江西诗歌的基础上,辟出专栏“诗江西”,以扶持江西的诗歌发展,我感到非常兴奋,希望这种坚持能够一直伴随江西诗坛的成长!
颜溶、三子、林莉、汪泽、傅菲等都是江西非常有实力的代表性诗人,他们的所思所行也暗含着江西诗坛发展的未来方向。五位诗人的本次作品与以往江西诗坛重乡土路径的风格有点不一样,开始转向关注日常生活,以人文关怀的眼光、敏感的艺术直觉和个体化经验,介入时代与物质碰撞的生活低处及经验世界和历史想象,挖掘物质与技术双重压抑下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灵魂真空和欲望诉求,进而建构自由的诗意栖居地和审美空间,获得主体镜像的自我认同。我认为这是江西诗歌走出地域局限向全国诗坛整体迈进并取得实效的重要一步。
诗歌要感人,首先要引人思考触及灵魂,打动读者内心深处最柔软最隐秘的内核,这就需要诗人在创作中融入悲悯气质和博爱情怀,颜溶的诗歌就是如此,其诗《修女特蕾莎》、《仰望》、《熟睡的女人》就涌动着爱、悲悯与感恩。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真正的诗人永远怀有人类的悲悯与关怀。他应该是高尚的,即使他在这个被时代命名的高尚者中间永远缺席。”因为人性的残忍、因为独裁的贪婪、因为权力者的攀比,天灾人祸无时不在大地上吐露自己邪恶的信子,于是,战争、饥饿、疾病、灾难、旋涡、暗礁、阴霾、蛆、炎症肆虐着千疮百孔的大地。
如果说《修女特蕾莎》是诗人仰望的目标,那么《仰望》则是自我的救赎,浑浊的时光、腐烂的星光、善恶的交叉、膨胀的欲望、吸吮贪婪的苍蝇不仅建构起生存的阴暗,更提供了人性贪婪的暗示,腐蚀着秩序的法理性,理想与道德“正慢慢沦陷”,诗人在这种人生的困境中非常警醒,极力建构起精神保护的屏障,自觉地抵抗“被同化”的悲剧命运。
与上述两首的沉重不同,《熟睡的女人》则用口语化的语言营造一种温情而唯美的意境,诗人落笔在生活的细部去咀嚼生命的大爱,直面人生的意义与亲情的温馨,同样是写女人,但这个“熟睡的女人”无疑是诗人自我镜像的呈现,因为两者之间在血缘的牵连下已经心灵相通,成为“我”呵护及思念的想象性所在。
当下的中国,已经彻底地进入了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转型期,现代化机械复制时代的莅临一方面推动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暗伤与苦痛。
三子的《逍遥记》《美人记》诗意浓郁,诗境清新,语言简洁,其抒情方式安静、从容坦率而又细腻婉约,把个体经验转化为独具生命诗意与人文情怀的哲思,这种诗意哲思随着“我”的时空变化和人生轨迹获得升华,使得其书写极富现场感和存在感。《逍遥记》书写“我”对未来、对信念、对美丽新世界的渴望与追求。“我”乡土养育的,血管里流淌着泥土的芳香,因为“我的春衫是虫子的蜕壳做的/轻巧的鞋子,是去年的草编的/甚至,包括我的身子,身子里的每一根骨头/都是用江南最粘密的土,捏的”,这种隐喻化的语言也正表明了“我”所存在的家园与精神的根,但“我就要到远方去”,“把江山、清风/连同多余的皮囊舍在身后”,诗人通过“我要到更远的远方去”句式的反复来强化这种孤绝与悲壮,尽管要“趟过渐涨的河水/翻过丘陵,这就到一次次谈论过的远方去”,但不改自己的志向,目标依然直指前方,这是难能可贵的。虽然诗人没有说明“去”往何方,也许为了寻找爱情,也许为了寻找更好的栖居地,也许为了寻找诗意的故乡,也许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也许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远方”已经成为了一个理想的词,与现实无关,与经验无关。
于是“我”轻装上阵,辞别万物:“告诉连绵的细雨”,“碰见摇尾巴的狗,说一声告辞”,“看到田野里站着的一头牛,道声再见”,幽默的语言、物化的意象、可爱的精灵、使得诗歌充满情趣,显得轻灵飘逸,也呈现出幽隐的透明与志趣。《美人记》语言也较为精致纯正,全诗诗意饱满。诗人以白描写意和影像透视的言说方式抒怀美丽的精致与个体的艳羡,一辈子的光阴浓缩在短短的诗行,不可企及的伤感也在“我”的遥远祝福和欲望化注视中弥漫,如同烟雾。
林莉的《嘉峪关》厚重沉郁,呈现出铿锵大气与家国情怀的气象。诗人走着托物言志、直抒胸臆、以小见大、以古写今的路子,通过敏锐地观察、想象嘉峪关的古与今,还原历史的厚度与现实的广度,以慷慨激昂的姿态实现自我对自然的力量、历史的关怀和人类文明史的现实处境的思考、认知和感悟,“抚摸着这些厚实的墙砖,随风/逐一走上寂然无语的箭楼、敌楼、角楼、阁楼”,感怀历史,想象当年的英勇多姿,多少勇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祖国的边疆,“尘沙阵阵,西去千千里,仍是我的汉唐疆!”换取国家的幸福安宁。但她的经验没有局限在嘉峪关这一“小”部,而是通过“小”部细节的不断膨胀与影像化透视呈现生命的大气,文化的怀柔远比武器的坚硬要更重要,“驼铃声中,我目送一队队驮伏着中华文明的商旅远行/越过极边,继续向西,向西……/日暮后,我偶尔会念想起我的中原故土/泪湿双眸,似听到妻儿的呼唤:胡不归兮,我的夫君,我的父亲!”人性的力量与文化的光芒照亮着大地的幽暗与沉重,那种悲壮情怀驻守在诗人内心,并通过夫妻的时空对话呈现出来,极其震撼。同时,诗人在文化地理时空的聚合与流变下,借助古代边塞雄浑的礼赞来呈现当下的发展:“如今的嘉峪关市,大漠边缘的一颗明珠/生命和希望的绿洲因为召唤而一刻不停地奔涌着时尚的潮流”,边疆的和平推动了祖国的发展,唯有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永远和平。最后一节“嘉峪关/谁是谁的关隘,谁又是/谁的城堡”是全诗之眼,诗意厚实,哲思幽深,具有相当的高度,诗人在语言追问的基础上注入思想的力量,探求真理的锋芒。但是,她的开头两句“一座关城,吾国脊梁不可缺少的一块骨节/一座关城,坚守吾族完整意志的巨灵”的说白与全诗的大气形成反差,降低了全诗的格调,确是可有可无。
别林斯基认为:“诗歌是生活的全部,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生活本身。”但问题在于如何把生活的哲思、深度和广度呈现出来,这是考验一个优秀诗人的分水岭。诗人汪铎深入生活的细处、事物的内部,关注爱、自然、生命、死亡等话题,介入和体验社会真实状态,直陈现代人生活中的孤独、寂寞、苦痛与阴暗,探索人类灵魂与精神的困境,进而思考人类生存世界的主体秩序,追问痛苦之由、生之意义和死亡之谜。《蟋蟀》、《这些鸟》、《月光下的河流》、《南山》、《祭奠》、《接站人》等诗语言干净,诗意单纯,诗思流畅,矛盾、孤寂、纠结、忧郁和焦虑加深了诗歌张力的深邃,显现出悲悯的气质和博爱的情怀。蟋蟀、鸟、河流、南山、野萝卜花、接站人无疑是自我心灵镜像的外化投影,更是主体分裂成无数个体在自我认知世界的折射,意象的反复出现不断深化自我的困境体验,获得自我的镜像认同。“一条河流需要忍受怎样的屈辱/才能拥有如此圣洁的光辉/一条河流需要经历多少次苦难/才能获得今晚短暂的安宁”(《月光下的河流》),诗人用两个排比句式以直抵灵魂的力量,呈现人类的生存困境与坎坷命运。“一匹马醉死在归家的路上/一个人耗尽光阴没有找到故乡”(《南山》),则表达出现代人对心灵家园的迷失与寻找。而《祭奠》以“故事化”写法将生活中的细节抽象化,富于暗示性,把野胡萝卜花包围城防堤、城防堤包围城市进行拟像仿真和戏谑,建构起野胡萝卜花花圈祭奠城市的狂欢图景,产生戏剧化效果,形成否定之否定的诗歌张力,从而达到标题所标识的反讽效果。生的悲悯、存在的悖谬、死亡的追问与思考在极度荒诞化的黑色幽默中显得格外沉重,“每一年,我们都要被野胡萝卜花/隆重地,祭奠一次”,诗人汪铎批判物质现代化视阈下的生存困境,直抵人类生命的本质。这一点在与《等待戈多》类似的诗歌文本《接站人》中同样呈现,没有结局、没有终点的等待不正是我们生存状态的复现么?
傅菲在哲理小诗《蔷薇组诗》中发扬绵长、炽热、天然的抒情优势,提炼现实的诗意,真诚地呈现出自己对个体生命与周遭世界的感受与思考,不仅语言飘逸,而且意蕴醇厚。尤其是诗人一直以蔷薇物象作为意象载体,传递主体“我”与客体“你”“他”的心情状态和心理思绪,深沉地表达生活的感悟和生命的滋味,使得诗歌开合自如,凝重而富有画面感、细腻更具哲理性。那淡淡的忧伤、惆怅与忏悔在冷抒情的冷艳中异常尖锐,强烈的痛感油然而生,刺向人性的虚空,如“用剩余的三公斤泪水,每日取一滴/浇灌泥垛上的蔷薇”(《蔷薇》),“回望你的双眼/恰似一个坟墓毗邻另一个坟墓”(《蔷薇小令》),“带来尘埃 爱 深呼吸/最后带来凋谢 不留匆匆一瞥”(《蔷薇的悲伤》),“目睹蔷薇盛开的人远去他乡/闪光之后扔下一片漆黑/像不散的亡灵,缠绕指尖”(《滚过蔷薇的闪电》),“生活就是一堵满是弹孔的墙,我扶墙而歌”(《不是每个人这么幸运,遇见蔷薇》),诗人以不露声色的冷色调和深沉刻骨的悲剧感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真相,探寻个体心灵的悸动和苦涩内心的挣扎,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对存在与死亡的深度思考。同时,诗人在《手捧蔷薇的人》、《十二株蔷薇》等诗中传递个人生命的体验以及对生命和自然所发生的温暖,如“列车离开麻石站台之前,我留最后一刻钟给你/不要相拥,不要细语道别。我只想回眸时/看你手捧蔷薇,面带微笑,犹如初见”(《手捧蔷薇的人》),“不是爱,但温暖,偶尔痛/我喜欢你种下的蔷薇……晚安”(《喜欢你种下的蔷薇……》),生活的驳杂消解了诗意的温暖与情爱的温馨,但痛并快乐着,自然的原色、生命的温馨与心灵的相通在蔷薇花的暖色调中依然显得精神饱满。
总之,颜溶、三子、林莉、汪泽、傅菲等诗人以各自的意象载体切入,呈现自我镜像的主体认同,探寻诗歌隐喻层面上的生命本真、存在意义和人类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