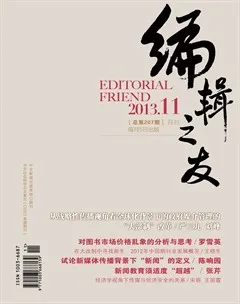机关报和都市报对网络语言的态度和接纳方式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语言也蓬勃发展,并自成一体。网络语言不仅关乎网络,同时深刻影响着媒体和社会的语言风格。从目前情况看,媒体对网络语言认可程度不同,最有代表性的是机关报和都市报。它们对待网络语言态度不同,接纳方式也有差异。文章分析了这两种报纸对网络语言的接纳表现及其原因,指出媒体应理性对待网络语言,这有利于网络语言的良性发展,也有利于媒介语言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
媒介融合 报纸媒介 网络语言 态度 差异
覃芹,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
本文系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纸质媒体的转型与升级”(2011WB026)阶段性成果之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语言也蓬勃发展,并自成一体。网络语言不仅关乎网络,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媒体的语言风格,带来了媒介语言的大融合。但从目前情况看,不同媒体对网络语言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即便是同一种媒介,由于其社会功能不同,对待网络语言的态度也有差异。最具代表性的是机关报(主要是党委机关报)和都市报。
一、机关报和都市报对网络语言的接纳差异体现
作为网络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网络语言已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语言创造思路与语言结构组合模式。与传统语言相比,网络语言具有鲜明的内容个性化、形式不规范等特征。一般的网络语言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即网络新词、网络流行语、网络热词。其中网络新词是网络上由网民新创的词,如high、mm、菜鸟、粉丝等;网络流行语是创造于网络并能流行的网络新词,如晕倒、酱紫、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等;网络热词则是与一定社会事件与社会现象相联系的使用频率较高的网络语,如躲猫猫、俯卧撑、欺实马、我爸是李刚等等。
由于机关报和都市报的社会功能不同,它们对网络语言的态度也明显不同。机关报对网络语言基本以排斥为主。这种排斥的程度由“给力”一词2010年11月10日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引起一片哗然可见一斑。反常即新闻,网络热词“给力”登上《人民日报》被视为新闻,说明其反常性,也可见机关报对网络语言的采纳行为很罕见。笔者对《人民日报》等重要机关报进行抽样,很难见到对网络语言的积极采用,只有在开放意识浓厚的广东,常能见到机关报对网络语言的接纳,如《他们不是来打酱油的》(《南方日报》2008年8月5日)、《热烈祝贺“官二代”笔试夺魁》(《南方日报》2011年8月11日)。一些中性的网络语言也会偶尔出现在机关报中,如《透析“宅男宅女”现象,谁之过?》(《福建日报》2008年7月28日)。但那些标新立异和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的网络语言还是难以被机关报认可接纳。
不同的是,都市类报纸对网络语言的接纳则比较积极。都市报接纳网络语言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新闻标题或新闻内容上直接采用网络语言,如《史上最牛书记》(《郑州晚报》2007年12月11日)、《学生中毒属“群体性癔病”是“欺实马”?》(《燕赵晚报》2010年5月4日)、《“不差钱”副处长的灰色账单》(《北京晨报》2009年12月7日)、《消费者退药遭遇“躲猫猫”》(《燕赵晚报》2010年3月24日)、《中国电影很傻很天真》(《潇湘晨报》2008年2月26日)等等。
另一种是直接设置一些栏目或者专版来接纳网络语言。如《楚天都市报》的 “网事周刊·顶热帖”和 “网事周刊·晒生活”系列,以及《南方都市报》的“网络天下”专版等等。这种做法实际上等同于对网络语言大开绿灯,全面接纳。在这些栏目和专版的具体内容上,都市类报纸为增强娱乐效果和表达力度以及拉近与网民的心理接近度,往往直接把一些幽默性的网络段子等以集纳的形式予以刊载。《楚天都市报》(2011年10月17日)的“网事周刊·晒生活”就把有趣的网易微博刊登其上,并把一些具有艺术意蕴或者幽默效果的网名网语一起刊登出来,如把@瘟酒吧、@半熟正太、@韬光养肥、@yoda等网名与其幽默的网络段子一起刊载。
都市报纸对于网络语言的接纳能起到吸引受众阅读兴趣的作用,也拉近了报纸与受众的感情距离。总而言之,都市报纸对网络语言采取了欣然接受的态度并尽力采用一些相协调的编辑手段来利用网络语言,以丰富报纸的内容与增加栏目的多样性。
两者对比可见,都市报纸对网络语言的接纳积极主动并有创新意识,而机关报在采编上则对网络语言较为排斥。
二、两种属性报纸对网络语言接纳差异的原因
形成机关报和都市报对网络语言接纳态度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的属性和社会功能的不同。机关报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舆论阵地,其政治属性强,主要是直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而都市报是市场化报纸,市场属性强,主要传播日常生活信息和市场信息。前者受到政治话语的强力制约,后者受市场因素的强烈引导。属性和功能的不同,带来了他们社会定位和语言风格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对网络语言的认识态度和接纳方式不同。
具体来说,机关报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的宣传舆论工具,它“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与政策”。[1]所以,机关报是党和国家政策政令的传播者与解释者,强调的是政治功能而不是经济效益。机关报被赋予了“主流媒体、权威报道”的身份性质。机关报语言因此更多是一种政治语言而不是新闻语言,它不能过于诙谐,要遵守语言的约定俗成,其语言风格的要求是严肃、权威、正统。如福柯所言,机关报话语在运行中“必须将论述(话语)看做一系列的事件,看做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它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反过来控制论述(话语)本身”。[2]于是,机关报在这种背景下经过长期锤炼形成了其严肃端正的语言风格以及遣词造句特点方面的稳定模式。同时,作为主流媒体,机关报是彰显主流文化的重要媒介,这就要求机关报不能随意改变其语言符号的严肃性与约定俗成的规则。对此,孔子曾提出“正名以正政”的观点,因为“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3]从这一角度来看,机关报对网络语言采取不认同的态度也是必然。一定程度上来说,网络语言的风格与机关报语言风格是背道而驰的,网络语言的反传统与标新立异是一种典型的亚文化体现,而亚文化被定义为对主流文化的一种柔性抵抗,这种特征导致了机关报对网络语言持不认同态度。
作为大众化的平民报纸,都市报的主要受众是普通民众,这种属性规定其必须适应市场,追求经济收益。在经营上,靠市场化求生存,其盈利与否在于有无自愿购买的受众和受众的数量。这种市场属性决定了都市报必须走平民化的语言路线:一切喜闻乐见的大众语言都是其接纳对象,从网络中兴起的网民语言自然也不例外。都市报对网络语言的接纳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现实因素:第一、网络语言的制造者同时也是商业报纸潜在的受众;第二、网络语言本身具有的个性化、幽默睿智以及形象的刻画力彰显了这种语言本身的价值,接纳网络语言意味着增加受众对报纸内容的认可度。
三、对机关报和都市报接纳网络语言态度差异的评析
从大部分的相关研究和专家意见来看,对网络语言的态度贬大于褒,有些地方还通过了限制网络语言“滥用”的法规,如2006年上海市通过了《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明确规定公文和教科书“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词语”,新闻报道除需要外也不得使用。这种否定网络语言的法规,在于网络语言的标新立异及不遵守传统词汇生成规则的做法破坏了语言的纯洁性和正常规则。
笔者认为,对于网络语言应有全面理性的评价,网络语言具备诸多可取之处。
1. 网络语言体现了网络时代的创新特质。网络堪称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发明,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而网络语言则是网络时代的重要内容,任何忽略这种重要内容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对现实的逃避。
2. 不能过于强调网络语言破坏了语言的纯洁与规则。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W.Labov)认为,语言本无所谓好坏、完善或不完善,对语言好坏等方面的定性主要决定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或社会集团所处的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等因素。从语言的内涵来看,语言从来就不是纯洁的,等级与特权一直占据着中国语言史,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成功便成仁”等,而网络语言主要体现了网民对个性、自由、快乐、民主的追求。从语言的规则来看,语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社会变迁中,新的语言产生与旧的语言消失一直是一个动态的存在,语言的重要特点就是其约定俗成性,网络语言在网络上具有良好的约定俗成性而被网民广泛使用,虽破坏了传统的词汇生成组合规则,但并不影响网民之间约定俗成的共享使用。
3. 网络语言的“草根性”正是其价值体现之一。语言本来来自于劳动,来自于草根。语言的发展方向也是由草根性的民众牵引,而不是由专家和上层创造,网络语言不能因其草根性被轻视。目前中国网民有5亿之众,5亿人说的话绝不是胡言乱语。在90多年前的白话文运动中,针对一些正统人士反对白话文,鲁迅先生说:“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4]要学学鲁迅先生,重视新生的网络语言。
在都市报对网络语言全面主动接纳的背景下,机关报有必要考虑及时接受网络语言的先进成分和先进理念。过分排斥网络语言,无法保证机关报与时俱进,无法显示机关报的时代特征。机关报尤其是党委机关报,属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其影响力,就须用民众话语和包括网民在内的广大民众对话沟通。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才能将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得深入人心,使“机关报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最大限度地重叠与共鸣。[5]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已然告诉我们,语言的有效性取决于双方对话的形成,只有交际才能赋予语言真正的生命,而符号只是一种物质载体,意义只存在于人们的交际对话之中。
同时,还要认识到,语言的变化虽受政治和文化环境制约,但在科技力量强大的今天,技术的力量不可小觑。网络促生网络语言并引起媒介乃至社会语言的变化就是例证。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网络语言的影响会更加深入。正如喻国明教授所言:现在是技术拖着制度走,因为技术是社会最活跃、最本质的因素。[6]因此,不管是机关报还是商业报,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不主动跟着网络走也会被网络拖着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
当然,网络语言的确存在不规范、随意和不严谨等问题,这需要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地锤炼和改进。都市报等媒体对于网络语言不能盲目地接纳使用,应有所取有所不取。
参考文献:
[1]毛泽东.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56.
[2] 高宣扬. 福柯的生存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2.
[3] 戴望. 诸子集成(第五册)管子校正[M]. 北京:中华书局,1954:302.
[4] 鲁迅. 热风.现在的屠杀者[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0.
[5] 周跃敏. 以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拓宽党报功能[J]. 中国记者,2009(12).
[6] 贾乐蓉. 中俄转型与中俄大众传媒转型[J]. 国际新闻界,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