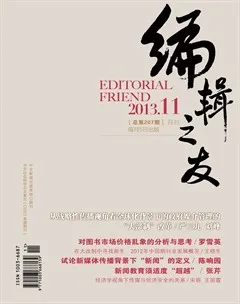论现代作家编辑活动的意义
中国现代作家几乎都参加过各种形式的编辑活动,他们通过刊物和丛书的编辑来散播和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构建新文学的批判体系,培养作家队伍。他们的编辑活动是现代文学运行发展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形式。由此可以看出,编辑活动对现代文学的萌发和运行所起到的非常现实的作用,这也是现代作家编辑活动最为重要的意义。
现代作家 编辑活动 文学理想
尹变英,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现代作家几乎都有过不同规模的编辑活动。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周作人、郑振铎、王统照、徐志摩、老舍、沈从文、施蛰存、戴望舒、林语堂、胡风、丁玲等等,非常长的一串名字。编辑活动也往往是他们文学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兴起和人们对新的传媒形式的重视,致力于现代文学建设和现代思想传播的现代作家们必然将编辑活动当做自己文学活动的基础。现代作家的编辑活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期刊的编辑与丛书的编辑。现代作家的编辑活动,是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种重要的运行方式,其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作家因实现文学甚至社会理想而从事编辑活动,又因编辑活动本身而创作大量的作品。从编辑活动中发现和培养新生力量是现代文学能够延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编辑活动也是连接新老作家的重要纽带和构建现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渠道。在现代文学从各种思潮中探索发展道路的众声喧哗的语境中,编辑活动和由此而来的刊物与丛书,是现代文学最为鲜活的成果。
一、实现文学理想
这些作家不仅仅是文学编辑,还是刊物的创作主力军和引导者,这和后来的编辑有所不同。他们总是要用自己的创作来支持刊物的品格和发展,以自身的创作来带动刊物的进步。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这未必是最科学的方法,但对于当时文学和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而言,无疑是最快捷有效的方式。从鲁迅、周作人创办《新生》,到丁玲、沈从文、胡也频编辑《红黑》的失败,再到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和孙伏园促成《语丝》的诞生,每一份刊物都承载着编辑者的文学理想。陈独秀的编辑思想,无疑是现代作家编辑刊物的目标所在:“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的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种‘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于要办的事。”[1]
现代文学的母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最重要的摇篮就是《新青年》。《新青年》是典型的同人刊物,现代文学最早的创作者、批评者都是该刊物的编辑。致力于“文学革命”的《新青年》4至6卷也是现代文学的缔造者们轮流编辑的时期。有了《新青年》,才有了文学革命,才有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可见新文学的诞生发展与出版传媒的关系极为密切。“双簧戏”更是体现了《新青年》编辑者超前的创新意识,显示了重要的市场传播意义,典型地体现了“对期刊既存文化氛围的突破和对新的文化氛围的营造”的功能。[2]
沈雁冰从《小说月报》12卷起对其改革,其编辑定位是相当宏阔高远的。《<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显示了沈雁冰等文学研究会作家致力于革新整个中国文坛的目的:“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以“中国文学”为对象,呈现出面向整个新文学发展的理想。所列栏目也体现了这种宏大的关注:评论、研究、译丛、创作、特载、杂载,关涉到了批评、译介、创作、文坛消息等新文学发展的各方面。同时也提出了新文学发展的方向:“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纳入了世界文学的视野,提出中国的新文学要“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之地”。在对待各种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时也显示了极大的宽容性:“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提倡写实主义,“而同时非写实主义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3]《小说月报》的编辑方针和思路成为新文学发展的导向,承载着当时大部分致力于新文学建设者的梦想。
这种文学理想在《小说月报》终刊于战火之后依然在延续。1934年,郑振铎、冰心、巴金等创刊编辑《文学季刊》,其发刊词仍表达了对《小说月报》所提出的新文学理想:“(一)继续十五年来未竟全功的对于传统文学与非人文学的攻击与摧毁工作;(二)尽力于新文学的作风与技术上的改进与发展;(三)试要阐明我们文学的前途是怎样的进展和向什么方向而进展。”[4]如《小说月报》所提倡,其不限于某个派别或思潮的介绍发展,而以整个新文学的发展为目标。其所刊载的内容也一样包括了创作、译介、批评和传统文学的研究整理。
周作人、鲁迅等编辑的《语丝》是失去《新青年》这块文学阵地后,他们为自己办的一个刊物,“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语丝>发刊词》将其文学理想表述得非常清晰:“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5]最大程度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自由的理想。刊物围绕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等社会事件,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这种思想的自由追求。而《语丝》的编辑,也典型地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通过编辑活动,实现其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编辑活动无疑成了现代知识分子最有力的阵地和战场。
相对于《新青年》《小说月报》这种着眼于整个新文学建设的理想而言,创造社的刊物更具个性色彩。创造社创办之初,郭沫若就提出过要办一种同人刊物。他的想法与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时的意义不同,是要倡导个性化的文学理想。创造社是一个追随时代脉搏而动的团体,其不同时期的刊物也表达了不同的文学理想。1922年的《创造》季刊强调“自我表现”。1923年的《创造日》宣言为:“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6]延续着“唯真唯美”的文学观。1926年的《创造》月刊起了变化,《卷头语》指出:“我们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7]刊物的社会关注加强,文学的战斗色彩已非常明显,《创造》月刊也就成了倡导革命文学的阵地。其第2卷第1期的《编辑后记》更是直接指出:“本志以后不再以纯文艺的杂志自称,却以战斗的阵营自负。”[8]郭沫若、郁达夫们编辑的这些刊物,是其实现文学理想的渠道和阵地。创造社的刊物,特别是《创造周报》,热衷于文学批评,往往引发各种各样的文学论争,如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与鲁迅的论争,都是其执着于自己的文学理想的表现。
胡风所编辑的《七月》,代表了抗日背景下现代作家所树立的战斗的、文学的理想。胡风《七月》创刊号代致辞《愿和读者一同成长》说:“中国的革命文学是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五四”运动)一同产生,一同受难,一同成长的……在今天,抗日的民族战争已在走向全面展开的局势。如果这个战争不能不深刻地向前发展,如果这个战争的最后胜利不能不从抖去阻塞民族活力的死的渣滓,启发隐藏在民众里的伟大力量而得到,那么,这个战争就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它对于意识战线所提出的任务也是不小的……我们认为: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工作者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文艺作家不但能够从民众里面找到真实的理解者,同时还能够源源地发现在实际斗争里成长的新的同道和伙友。”[9]
二、构建现代文学批评
现代作家作为编辑者也成了现代文学批评体系的构建者。他们所写的序跋都是对青年作家的批评和引导。鲁迅等人编辑的《新文学大系》导言是对自己编选原则的说明和对所编选作品的批评。对乡土派小说的最初界定就源于鲁迅的导言。鲁迅编辑《奴隶丛书》时对萧军、萧红、叶紫等人的肯定,是最早对抗日文学主张的肯定。茅盾,胡风等人的编辑工作也有此种性质。《小说月报》设立批评专栏,创造社刊物热衷于文学批评,对社团内的作家,如郭沫若、郁达夫等进行批评,对文学研究会作家,如冰心、王统照、许地山及鲁迅都展开了批评。这些批评文章,都是现代文学批评体系建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新文学大系》导言更能体现编辑思想的文学批评意义。编选本身就是一种批评,每一种编选标准的提出,也即相关领域研究基础理论的提出。郁达夫的话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这一集里所选的,都是我所佩服的人,而他们的文字,当然又都是我所喜欢的文字,——不喜欢的就不选了——本来是可以不必再有所评述,来搅乱视听的,因为文字具在,读者读了自然会知道它们的好坏。但是向来的选家习惯,似乎都要有些眉批和脚注,才算称职,我在这里,也只能加上些蛇足,以符旧例。”[10]诗集编辑者朱自清的批判,无疑成了现代白话诗研究的理论基础,他对于所选诗人诗作的批判,也成了研究这些诗人诗作的基本定论,如对颇为难解的李金发诗,朱自清说:“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11]这段话在任何研究李金发诗歌和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时,都是重要参照。朱自清所提出的诗坛3个派别“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也成为研究现代白话诗的基本分类。周作人和郁达夫的散文一集和二集的导言,都追述了散文发展的历史和特色,更是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理论基础。而导言集中呈现出来的文学批评思想涉及现代文学各方面,不仅仅是文体批判,更是现代文学思想的展示。5191c129571d8e6bbb1275af38c57d51
鲁迅在编辑“奴隶丛书”时所写的序言,丰富了左翼文学批评。鲁迅《叶紫作〈丰收〉序》云:“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的经历,在辗转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文学是战斗的!”将作家的生活经历与文学视野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左翼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命题:“文学是战斗的!”鲁迅《八月的乡村》序云:“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致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由此将左翼文学批评中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极细腻地体现了出来。鲁迅《生死场》序云:“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12]将左翼文学批评重视文学的风骨和力度的特点提炼了出来。
胡风编辑“七月丛书”时为路翎所作《财主底儿女们》序云:“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点的现代中国底动态。然而,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底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搏斗的经验。真实性愈高的精神状态(即使是,或者说尤其是向着未来的精神状态),它底产生和成长就愈是和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人生纠结得深。那么,整个现在中国历史能够颤动在这部史诗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就并不是不能理解的了。”[13]这正是胡风文艺思想中“主观战斗精神”理论的最好阐释,这一文艺理论观念也是现代文学批评史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创造社同人更是在《创造季刊》里开设了“曼衍言”,刊载编辑者郭沫若和成仿吾谈论文艺理论、创作感受的零言屑语,这些言论不出现在期刊目录当中,编辑者补白之用,方式灵活。这种看似零散的言论往往是编辑者灵光的闪现,如“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情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叫喊,那便是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14]这是对创造社以自我为中心,直露、真挚大胆的创作最好的阐释。编辑者的这种独特的创作小议,成了文学批评的特别形式。
三、培养青年作家
现代作家在从事编辑活动时,一个共同点是对新人的发现和大力培养。鲁迅对很多青年作家的发现和培养、茅盾对左翼作家的发现和培养、胡风对七月派新人的培养、沈从文对京派青年作家的培养,都体现了作家编辑活动的价值。沈从文曾写了大量的废邮存底,体现了他对文学爱好者和初学者的热情鼓励和引导。由刊物而培养的青年作家和编辑刊物的作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古代文人间的师友关系,刊物也就成为他们交流的最好平台。
鲁迅把刊物的编辑作为对青年们的召唤:“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15]他所编辑的《语丝》《奔流》《莽原》《艺苑朝华》《朝花》《萌芽》等培养了柔石、白莽、韦素园、李霁野、许钦文等青年作家。从刊物的名目上,也可看出鲁迅对于青年怀着多么强烈的期望。其编辑态度是:“留心发现投稿者中间可造之才,不惜奖掖备至,稍可录用,无不从宽。”[16]鲁迅编辑“奴隶丛书”,是对叶紫、萧军、萧红等青年作家的推崇。应美国人伊罗生之约,鲁迅和茅盾编选了一本小说选《草鞋脚》,其中入选的,一大部分都是青年作家,如吴组缃、艾芜、沙汀、邱东平、楼适夷、欧阳山、草明女士,还有不知名的文学青年涟清、张瓴等,显示了鲁迅与茅盾对青年作家的赏识和爱护。如鲁迅在《<草鞋脚>小引》中所言:“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17]
茅盾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时,说他编辑的《小说月报》就是要发现那些“青年的‘尝试者’”,正是他们“把‘文坛’装点得颇为热闹了”。[18]10年后总结这段文学史时,他还是要把那些不知名的青年作家的作品编选入册,肯定了那些“无名作家”的价值。叶圣陶在编辑《小说月报》时发现了巴金和丁玲,发表了他们的处女作。丁玲和巴金都说过,如果没有叶圣陶,他们或许就不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了。而巴金又是发现曹禺、何其芳、刘白羽、萧乾、芦焚、臧克家等青年作家的编辑。胡风在编辑《七月》《希望》等刊物时,也发现和培养了阿垅、鲁藜、绿原、牛汉等青年作家。沈从文在编辑《大公报·文艺》时,经常为青年作家改稿子,写信谈创作经验。这是现代文学发展借由刊物而实现的承接链条。
现代作家几乎每个人都与编辑活动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其编辑活动带动了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在文学史和编辑出版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陈独秀. 随感录75·新出版物[J]. 新青年,1920,7(2).
[2] 黎海英. 对现代期刊编辑创新意识的理性审视[J]. 学术论坛,2007(7).
[3] 沈雁冰. 《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J]. 小说月报,1921,12(1).
[4] 本刊. 发刊词[J]. 文学季刊,1934(1).
[5] 鲁迅. 发刊词[J]. 语丝,1924(1).
[6] 本刊. 《创造日》宣言[J]. 创造日,1923(1).
[7] 本刊. 卷头语[J]. 创造(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1922,1(1).
[8] 本刊. 编辑后记[J]. 创造(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1922,2(1).
[9] [13] 胡风. 胡风全集(第3卷)[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499,263.
[10] 郁达夫. 导言[M]//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影印本).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13.
[11] 朱自清. 导言[M]//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7-8.
[12] 鲁迅. 题记[M]//鲁迅全集(第6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4,292,414.
[14] 郭沫若.“曼衍言”[J]. 创造季刊,1922,1(1).
[15] 鲁迅. 题记[M]//鲁迅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
[16] 许广平. 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38.
[17] 鲁迅.《草鞋脚》小引[M]//鲁迅全集(第6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
[18] 茅盾. 导言[M]//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 影印本).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