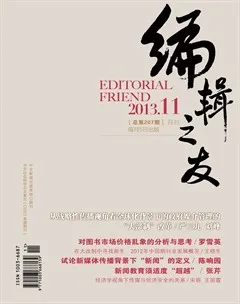论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编辑群体的职业素养观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知识激烈碰撞、文化风起云涌的时代,是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和国家民族首次面临危机的时期。与此相适应,随着知识传播的需要,编辑群体开始出现并呈现为近代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因此对编辑本身的关注应成为对近代文化进行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那个时代,为各类知识传播服务的先进知识分子编辑们,以他们的天职思考着自身的角色定位和职业要求,构成了此时编辑群体的自我认识,展示着其时编辑群体特有的职业精神,标志着中国编辑队伍职业意识的初步形成。
近代先进知识分子 编辑群体 职业素养
李彬,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副编审,博士。
本文所谓的先进知识分子编辑群体,特指那些勇于担当时代责任而不随波逐流的报刊出版职业工作者,这些人构成了近代文化传承和参与文化碰撞的重要力量,有别于那些纯粹为谋生的“小报”编辑。后者的“不思进取”也是前者办报过程中坚决反对的。其职业因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而具有特殊值得纪念的地方;其职业精神就是这一群体共同展现的职业意识、职业素养和职业操守。
一、坚守宗旨、救国新民的价值取向
对于近代中国的衰弱,先进的知识分子有着切肤之痛,其普遍认为,“中国之弱,由于民愚,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1]因此,作为编辑的知识分子,首先把办报刊的宗旨定为开民智、新国民以图救国,他们将这样的宗旨在办报刊的过程中一以贯之。
同治年间,作为民间的且为传教士在华出版机构做编译的王韬,留心于普法战争的报道,收集了很多战事记录而汇编成册,名为《普法战纪》,目的在于惊醒国人,不要因当前的劣势而沮丧,而要抓住时机,养精蓄锐,一雪国耻,充分表达了其爱国主义思想。他还给当时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写信,建议福建设立肄习舟师馆和翻译西书馆,收集翻译各国各专业的典籍为我所用,以备不时之需,体现了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2]王韬面对列强在华报刊对中国事务的指手画脚,十分愤懑,主张国人应编辑自己的西文报刊进行反击。他认为,要学习西方、了解西方且反击西方,非编辑报刊不可,“汇观各处日报而撷取要略译以华文,寄呈总理衙门”,让朝廷在应对外国时胸有成竹。移居香港期间,王韬于1874年主办《循环日报》,宣布该报的宗旨是:“日报立言,义节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诹远以师长。”[3]该报设有“中外新闻”栏目,几乎每天都发表时评文章,很多文章都由王韬亲自撰写。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严重,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公车上书”不达,“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于是先办《万国公报》,于1895年8月17日创刊,“遍送士夫党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11月中旬,强学会成立,其又称译书局,或强学书局。“先以报事为主”,改《万国公报》为《中外纪闻》,于12月16日出版,双日刊,有阁抄﹑新闻及“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诸栏,译印后有附论,专论不多。后强学会被封,《中外纪闻》随之停刊,梁启超感慨颇多,但也认为,除言论外,也没有其他途径为国效力了。此后,梁启超更加倾力办报刊,以实现己之抱负。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在冯镜如等的支持下,于1898年12月创办《清议报》,他在阐述办刊宗旨时说:“一倡民权,始终抱定此议,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曰衍哲理,读东西读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中国,虽不敢自谓有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三曰明政局,戊戌之政变,己亥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曰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说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一悟。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矣。”[4]1902年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说:“吾济业报馆,请与诸君纵论报事。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5]
1907年,梁启超在给朋友的信中论及《政论》月刊的编辑内容时说:“弟所欲作之文,一为世界大势与中国前途,一为宪政之运用,一为货币政策(此大意如此,命题或尚有斟酌),颇欲对于政府举措,常为批评训导,如此乃尽我辈之责任。”[6]
1897年,严复在天津开办《国闻报》,论其宗旨时说:“《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为一国自立之国,则以通下情为要义,塞其下情,则有利而不知兴,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国必弱。为各国并立之国,则以通外情为要务,昧于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龠而以为日圆,若是者国必危。”[7]
1897年4月,受维新思潮的影响,唐才常任主笔的湖南第一份近代报刊《湘学新报》(后改为《湘学报》,实为期刊)创刊,其目的在于介绍新学、开民智、育人材、图富强。设有“掌故”“史学”“舆地”“算学”“商学”“交涉”等栏目。先进的知识分子,如唐才常、梁启超、李善兰等都是其作者。唐才常在《湘学新报例言》中阐明创刊初衷:“民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术恶乎振,振于师。顾安所得天下之老师宿儒,悉以明体达用之新法谕之,则报馆其师范嚆矢也。故周知时事,察验新理,目营四海,目属九州,舍此别无良法。”[8]谭嗣同在1898年3月18日《湘报》第11期发表了《湘报后叙》,借周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话,阐述了《湘报》的宗旨在于“助人日新”,以新民而新国,是孔子所谓“日新之谓盛德”。
章太炎在主编《民报》时,提出该报要坚持的六大主义,即颠覆恶劣的政府,建设共和政体,维护世界和平,土地国有,主张中日国民联合,要求列强赞成中国的革命事业。《民报》更是在《复报》刊登的广告上,宣扬其宗旨为“发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民生主义,而主张我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9]
张元济任职商务印书馆时,曾主持出版了很多西方的学术和文化著作,其目的在于传播西学以提振中国的民族精神,以匡救时弊,改良社会,“吾之意在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与吾国民质、俗尚、宗教、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之精神耳”“一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10]
蔡元培于1902年与张元济创办《开先报》,取“开路先锋”之意,“以有裨实际为宗旨,凡放言琐事均不录”,期望凭借办报对社会实际有所裨益,无非想开风气之先,传知识、变风尚、革政治、新社会。“五四”前夕的1918年10月20日,蔡元培在《在<国民杂志>社成立会上的演说词》中对该杂志社的成立宗旨进行了阐表:“诸君为此,志在拯救国家于危亡,深堪嘉尚。……若乃杂志之发行,实在提倡实业,发展学术,增进道德,诚足以抒救国之热忱矣。”[11]
1902年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一人身兼数职,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大公报序》,阐明该报的宗旨是“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12]主张变法图强,反对封建专制,吁求民族独立,抗击外来侵略。
这种救国新民的情怀在近代先进的编辑群体中是普遍的,就连似乎以娱乐为目的的《月月小说》杂志的曾任主编吴趼人也说:“余向以滑稽自喜,年来更从事小说,盖改良社会之心,无一息敢自已焉。”视编辑小说刊物的宗旨为改良社会、教化人民。这种影响在读者处也得到了印证。曹聚仁曾对梁启超在东京办的《新民丛报》回忆说:“《新民丛报》虽是在日本东京刊行,而散播之广,乃及穷乡僻壤,清光绪年间,我们家乡去杭州四百里,邮递经月才到,先父的思想文笔,也曾受梁氏的影响;远至重庆、成都,也让《新民丛报》飞越三峡而入,改变了士大夫的视听。”[13]
可以说,对那时的报刊业人来说,救国和新民的时代职责与学问是一致的,历史大环境为其提出历史任务,把他们推上历史舞台,他们所用以表演的,就是他们的笔墨和版面。
二、克勤敬业、孜孜以求的职业修养
较早从事编译工作的王韬,对编辑人才的标准有自己的看法,此看法来自他所任职的传教士出版机构墨海学馆:“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14]而对中国报刊的发展,他认为那种不是通才、见识不广、不识大体的人,或那种挟私讦人、只顾自己泄私愤、品格低下的人,都不应被录用。
梁启超先后主持过很多报刊的工作,对报刊从业人的素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要使报馆成为具有舆论理论的实体,对于报刊业人来说,应持五本,修八德。
所谓五本,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这实际构成了报刊业人的基本道德规范。报刊人要懂得常识,即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规律、原理和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要谙熟于心,如此“持论乃有凭借”,不然经不起他人的反驳,不能传播真理和知识,报刊也就失去了地位及影响社会的力量。真诚,即“以国家利害为鹄,而不以私人利害为鹄”,应以公心办报刊,从低层次讲,不应以此谋取私人利益,甚至要牺牲己之利益,抛弃己之得失;同样,真诚办报刊,不能利用报刊为己造势,不能“构煽舆论”,成为私人或利益集团的舆论工具。直道,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坚持真理,不惧权贵,不依附权势,不欺负弱小。所谓“柔而不茹,刚而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精神”,不能因遭遇权贵的弹压,就噤若寒蝉,更不能逢迎权贵的喜好。如此看,梁启超对报刊人的精神气质的要求颇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节所在。公心,即不以自己的好恶判断是非,要不偏不倚,即使报刊为哪个党派所办,也不应迎合党派的言论,而反对其他的言论,也不能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一味迎合非正当要求而一概反对政府。节制,即要倡导真理、理性,而不能煽动和调拨情绪,不能“迎合佻浅之性,故作偏执之论”。[15]
所谓八德,即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可以说是业人的八种基本业务素质。忠告,即对政府或国民的不合乎正义、正道的言行加以规劝,不仅不能袒护和默许,且不能似乎事不关己那样地看热闹,嘲讽挖苦,应立足自己的职责苦口婆心地忠告,做到仁至义尽。向导,即引导社会正气,传播自然和社会的真知,循序渐进地影响国民和社会。浸润,即业人应有坐冷板凳的心理素质,要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要对受众有信心,对自己工作的社会效果有信心,“月月而浸润之”,慢慢改造民心,改变社会风气,改革人们的生活方式,提升社会的整体素质。强聒,在心理取向上则与浸润相反,即“旦旦而聒之”,每天想着自己的职责,以强力的意志和无坚不摧的精神办刊,引导舆论,改造社会,对社会的不公和错误认识要敢于碰硬并奋起揭露和批判。见大,即作为一个报刊业者,面对种种社会弊端和令人不满的现实怎么办?答案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能因这些问题而丧失对改造社会的信心,不能只顾及一事一时。面对外界干扰更要专心致志,分清轻重缓急,要看到未来之“大”,要坚守自己的理想,循序渐进终能达致千里。能够见大,自然知道主从,心中有主,方可淡定而更专业,这就是“主一”,即业者要坚持己之人生信念和报刊宗旨,“一以贯之,彻于终始”。没有宗旨,有可能是胡言乱语,形不成合力,也会使读者无所适从,对社会的影响就会大打折扣。旁通,是一个好的编辑和业人的基础素质,其要求是掌握丰富的知识,各种资料齐备,就像人的粮食。各种资料“所凭借以广其益而眇其思”,如此,“进可以获攻错,而退可助张目”。下逮,即要求编辑和业人要充分了解读者,知道读者的需求和知识水平,所刊能够为读者喜闻乐见,能够为其接受,起到最终影响其心智和道德的目的,那种奢谈学理、自我炫耀渊博的做法,只会使自己和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这种不顾读者实际和社会现实的做法是办刊人的大忌。[16]由于当时的编辑大多为学有专长的大师,这种专业的素养是先进知识分子编辑群体都应具备的。如王国维,不仅具有渊博的知识,而且对古往今来的器物和书籍烂熟于心,能够出入书本知识和生活知识,具有较高水平的考证能力和近代科学知识常识。由于王国维的素质高于常人,曾被聘为《教育世界》《国学丛刊》《学术丛编》多家报刊的主编或主笔,他还对当时在学术界的中西之争、新旧之争、有用无用之争等提出了见解,认为学问没有这些区别,中西、新旧的学问都是同生共长的,可相得益彰,好的学问不存在是否有用的问题。这样的观念不仅在其学问中得到体现,且落实到编辑活动中,使之成为学术大师与编辑家结合的典范。
《时报》早期接受康有为、梁启超指导,梁启超对其中的《纪事》栏目提出过详细要求。他认为,此栏目第一要博,访事员(记者——本文注)应遍设要埠,及时采访,“使读者不出户而知天下”;第二要快,记者采访的内容要及时见报;第三要准,记者和编辑不要道听途说,未经实证的消息不要刊登,刊登有误的要及时更正;第四要直,即要忠实事实,不能掐头去尾、断章取义、隐讳甚至歪曲事实,只要关乎国计民生,“必忠实报闻”;第五要正,对于私人攻讦、排挤他人、借机报复的言论要严禁刊出,“概严屏绝”。[17]梁启超认为,记者编辑做到这几条,才能实现本栏目的宗旨,这同样是栏目对记者和编辑提出的职业素养要求。
严复对编辑的素质也提出了要求。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主持的《国闻报》发表《说难》指出:报馆的文章就像酒店的厨师和妓院的女人,具有同样的习气,“此三事者,托业不同,而终于无以善其后则同”。意即报馆发表此类文章,没有什么立场,处处都想讨好以满足自己的生存。报馆刊登一些应付口味的文章,无关痛痒,于国家和国民的发展都无益,有的报馆报道事实不准,反而误导舆论。“或洋洋数千言,而茫然不见其命意之所在”。表面上是对刊载文章的批评,实则是对报刊编辑的批评和讽刺,他认为,对于报刊或编辑来说,应“就吾见闻,敬告天下,平心出之,正志以待之,如此而已矣”。[18]
章太炎曾作《敬告同职业者》文:“报章之作,所以上通国政,旁达民情,有所弹正,比于工商能言……是故,不侮鳏寡,不畏强御,是新闻记者之职也。”[19]
近代大编辑家张元济对编辑人才的要求相当严格。他在负责商务印书馆期间,所聘编辑多为学有专长的青年才俊,如蔡元培、夏曾佑、高梦旦等均曾留学国外。且张元济坚持编辑岗位要给专业人士,而不是用来照顾亲属的饭碗,体现了他对编辑工作的专业精神和敬业精神。
蔡元培于1918年在《国民杂志》创刊时,对编辑提出了希望:“爱国不可不有热诚,而救国之计划,则必持以冷静之头脑,必灼见于事实之不诬而始下判断,则正确之谓也。”[20]意即爱国和工作不可没有热情,作为我辈救国途径的办刊却不可专凭热情,还需理性头脑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三、独立办刊、不畏强权的浩然气节
民族的灾难和国际国内的危机,使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编辑群体普遍怀有某种敢于担当的气概,此气概反映在办报刊上,就是独立办刊,不畏强权,坚守办刊的自由精神和浩然正气。
王韬是最早提出办报自由的人,提出报人要“指陈时事,无所忌讳”。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中提出了报刊应坚持的“直道”信仰,提倡“柔而不茹,刚而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精神”,如此舆论才可以发生。不能因遭遇权贵的弹压,就噤若寒蝉,更不能逢迎权贵的喜好。梁启超倡导以儒家之诚来办刊:“诚者何?曰:以国家利害为鹄,而不以私人利害为鹄是已。”[21]梁启超认为,监督政府和引导民智是报刊的天职:“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躬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22]
谭嗣同的《湘报后叙》提出了报刊应成为“民史”“民口”的观点。报纸要成为“民史”,就是说报纸所记载的应是“民之生业”“民之教法”和“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而不是专图“一己之私”的封建王朝起居注的“官书”。同时,报纸还要成为反映民意、为民呼吁的“民口”。[23]为此,报刊应坚持己见,直笔而言,才对得起民众。
近代社会动荡,在外国媒体挤压的背景下,经济凋敝,越是这种情况下,能够坚持报刊人的社会效益操守,越显得难能可贵。由于经费紧张,有的报刊因得到了资助而逐渐丧失了报刊的自由,从而使报刊受制于人,逐渐脱离办刊宗旨。对此,梁启超在《时事新报五千号纪念辞》中说:“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论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势力奋斗,于是吾侪相与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24]由此看出,在时局维艰、经费紧张的情形下,梁启超尚能鼓励同仁保持独立办刊的自由,的确值得敬佩。
1926年,《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的文章,倡言“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原则,坚守报刊的社会效益优先。以“不卖”为何:“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做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人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25]
四、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开放情怀
报刊编辑体例、报刊语言和风格等的业务创新,是近代报刊的鲜明一面,反映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编辑群体的开放眼光和务实态度。
首先表现为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如梁启超认为“凡真善良之报,能使人读其报,而全世界之智识,无一不具备焉”(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饮冰室合集》第11册。),基于此种认识,梁启超在办《清议报》时,大胆在编辑体例上进行创新,“多设门类,间册论载”。其认为,尤其丛报,各学科的知识,如政治、理财、法律、哲学、教育、宗教、格致、农工商、军事、文学、艺术等都应刊载。因此,他对欧美的丛报倍加推崇,对那种热衷于刊载警察小偷故事、家长里短新闻、风花雪月情事的报刊十分不屑,认为报刊应负有改造社会与国民的责任,不能囿于传统的内容转递。所以,他一生所办报刊除传播新知识、新道德的内容外,时事评论内容占有很大的篇幅。他认为,西洋的很多报刊都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能够左右政治,启迪民智,中国的报刊应学习之。
其次是报刊编辑业务(技术)的创新。近代是白话文兴起的时期,白话文的出现打破了文人对知识话语权的垄断,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白话文得到普及,其间报刊和编辑起到了重要作用。黄遵宪就认为“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26]主张改变文体以适应普及文化的需要,和以新式语言为大众接受的素质教育的工具,梁启超对此十分支持,并在创作和办刊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体。这种文体平易流畅并杂有俚语,不似旧式的文言文,“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27]此文体因在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运用较多,加上《新民丛报》的巨大影响而得到广泛认知,被称为“新民文体”,成为近代报刊文风发展的里程碑。
对版式和编排格式的创新,近代报刊也多有表现。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对编辑业务有过很多创新和改革。他把该报的版式改为新式版面布局,使报纸两面都印制内容,每面分为四栏,每栏再分两小栏,从而方便读者阅读,这种版式为许多新式报刊效仿。对于内容的分门别类的编排,梁启超也有己之想法,他在《<时报>发刊例》中说“本报编排,务求秩序”,报纸的内容,如评论、电报、谕旨等“皆有一定之位置”,每期都在同样位置安排,不同国家的新闻,也以国别为目做出安排;不同的字号按照内容的重要性而不同适用,不同的标点符号用在该用的地方,标题和正文内容使用不同的字号和符号。严复于1897年在天津创设《国闻报》,其编辑体例以“略仿英国《泰晤士报》之例”。1903年6月,《苏报》开始编辑改良,先后刊载《本报大改良》《本报大注意》《本报大沙汰》《本报大感情》《本报重改良》等改良按语:“本报发行之趣意,谅为阅者诸公所谬许,今后特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夹印二号字样,以发明本报之特色,而冀速感阅者之神经。”使重要的时论内容以重要字号出现,目的在于吸引读者的注意。在《本报重改良》中,该报重提改良的重要性:“本报自五月初六改良以来,仍有未臻完善之处,无以副读者诸君之望,心窃慊然。兹于本日闰月一日起,重加一次改良。”《苏报》则重新划分了栏目,增加了新内容,使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为邹容《革命军》的作序得以发表。[28]由此看来,《苏报》的版式改良和其内容的革命精神是一致的,其以报刊影响革命、匡救时弊的宗旨,在报纸改良的用心良苦上可见一斑。
装订的创新也是一个方面。随着外国出版和印刷技术的传入,“洋装”被引入书籍和期刊的装订,平装、精装相继出现,封面的设计越来越考究。1900年12月,郑贯公等在日本创办宣传革命的杂志《开智录》,“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种用洋装形式出版的中文书刊”。[29]此后的宣传革命的新式书刊大都采用此类方式装订出版。
报刊的内容如何,其彰显的社会效益就如何。近代报刊种类繁多,专业复杂,但很多报刊的内容多是家长里短、风月场闻、警察小偷、权贵往来。以当时报刊业比较兴盛的上海、广州和香港为例,其内容也多“沪滨冠盖”“瀛眷南来”“祝融肆虐”“图窃不成”“惊散鸳鸯”“甘为情死”等。这些内容在当时的以救国为宗旨的知识分子看来,不痛不痒,于事无补。梁启超在戊戌时期办的《中外纪闻》、流亡日本办的《新民丛报》等都开有时评栏目,发挥报刊的议政和新民的作用。初期主张君主立宪的《时报》接受康有为、梁启超指导时期,梁启超对《时报》的“论说”栏目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以公为主,不对任何政党偏私;二是以要为主,要讨论关系国家和社会的大问题;三是以周为主,对大问题要讲明白,力求让国民理解;四是以适为主,无论怎样的理论都要适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否则社会效果适得其反。可见,梁启超对栏目的定位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栏目要生存、要持续有生命力,应明确自己的定位,要主题鲜明,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体现出栏目的专业性的特点来。梁启超还认识到“著书须问将以供何等人之读”的问题,特别强调在编辑史书方面,要注意让人民来读的理念,要让人民知道除君主还有国家,除个人还有群体,除旧事还有新事,除事实还有理想。
结 语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出现,致使话语权下移。近代报刊的出现,体现了中国出版史上的官家出版到民间出版的过渡阶段。深刻的民族危机,使得近代知识分子编辑群体普遍怀有救国的焦躁情绪,这也反映了对报刊编辑素养的要求具有时代的特色。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48.
[2] 王韬. 上丁中丞书[M]// 园尺牍. 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531-532.
[4] 梁启超.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M]//饮冰室合集(第11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9.
[5] 梁启超. 敬告我同业诸君[M]//梁启超全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70.
[6] 欧阳哲生,丁文江,赵丰田.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 北京:中华书局,2010:247.
[7] 严复. 国闻报缘起[M]//严复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6:1-4.
[8] 杨建辉.《湘报》研究[D]. 湖南师范大学,2007:6.
[9] 汤志钧. 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M]//中国近代编辑家评(1版).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75.
[10] 汪家熔. 张元济主持的古籍影印工作[M]// 出版史料:第5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
[11] 陈独秀.《国民杂志》社成立会上的演说词[J]. 国民杂志,1919(1).
[12] 陈建云. 中外新闻学名著导读[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44.
[13] 曹聚仁. 文坛五十年[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5:31.
[14] 王韬. 论日报渐行于中土[M]// 园文录外编.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99.
[15] [16] [21] [24] 梁启超. 国风报叙例[M]//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
[17] [28] 李明山. 中国近代编辑家评传[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38.
[18] 严复. 诗文(下)[M]//严复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6:492.
[19] 章太炎. 敬告同职业者[N]. 大共和日报,1912-01-07.
[20] 蔡元培. 国民杂志[J], 1919(1).
[22] 梁启超. 敬告我同业诸君[M]// 梁启超全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70.
[23] 陈建云. 中外新闻学名著导读[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40.
[25] 张季鸾. 本社同人之志趣[N]. 大公报,1926-09-01.
[26] 黄遵宪. 日本国志[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811.
[27]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86.
[29] 姚福申. 中国编辑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280.
[30]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