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木匙的舅公
第代着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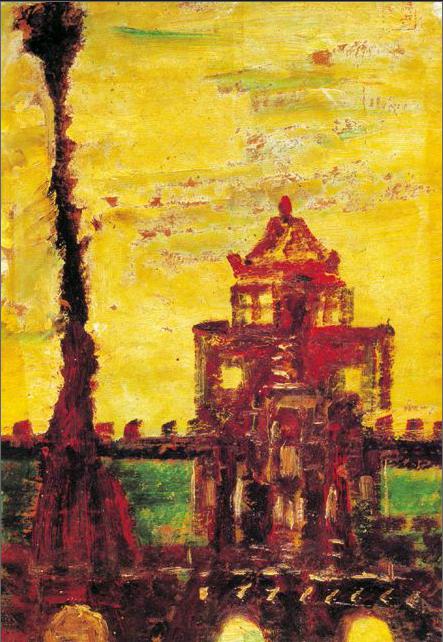

许多年后,当他拱出泥土,钻出地道,面对一支乌
黑的枪口,一定想起了最先抵上他脑门的左轮手枪。
是这支枪口改变了他的命运——尽管他带着一只木
匙,也没能抗拒命运的力量。
据说,舅公十七岁那年,他爸爸在给土匪抬滑竿时,摔坏了压寨夫人,被后来死于非命的土匪点了天灯。到了夏天,舅公的母亲死于一场由小贩带进山来的瘟疫。小贩以贩卖斑带、顶针和铜器为生,他背着背夹,走村串寨,身后跟着大群蓝翅膀的漂亮蝴蝶,像一条奔腾的钢蓝色河流。小贩离开不久,一场瘟疫席卷了暗藏在大山深处的村寨。人们认为,死于瘟疫的人,都曾看见过由蝴蝶组成的■景观,他们的灵魂受到蛊惑,忍不住跟上蝴蝶的步伐,往远处飞翔。
舅公的母亲去世之后,他在老家梨树湾举目无亲。秋天,他到阿尾寨投奔他姐姐。阿尾寨地处乌江河谷东岸,一条官道穿寨而过,成为从湘西翻越武陵山脉的重要捷径。顺着大路,阿尾寨行走着很多外乡人,流寇,贩夫,走卒,马倌,土匪,银匠,偷牛贼,刀斧手,以及不明身份的人。陌生人南来北往,携带的东西舅公闻所未闻,大开眼界,比如,洋油,洋碱,花布,头绳,用洋玻璃做罩子的灯盏。有一次,他用两只锦鸡从一个过路人手里换到半盒洋火,快捷的取火方式令他姐姐高兴了很久。
舅公初到阿尾寨时,除了一张嘴,一身破衣裳,专注而好奇的眼神,还带来一只漂亮的木匙。木匙用黄杨木做成,是他爸爸用一只缺柄的铜茶罐从一个过路木匠手里换到的。木匙经过吃百家饭的木匠使用,有了一层灿烂的金黄色光芒,像打磨过的铜器闪闪发亮。在我们老家,一个男人拥有一只木匙,说明他可以随时讨到饭食。跟传言差不多,木匙像一块路标,把舅公引领到各种各样的饭桌边,不等主人亮出筷子,舅公迅速取出木匙,从别人的碗里舀到一点点食物。
十七岁的舅公无所事事,东游西逛,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同各种过路人打交道上。秋天,田里黄熟的谷物把金黄色引向山冈,树木的落叶像鸟群在空中缓缓飞翔。舅公用一捧板栗从一个耍猴戏的男人手里换到一块吸铁石。吸铁石真不错,舅公幻想用吸铁石把别人装满饭食的鼎罐吸到家里。舅公揣着吸铁石往回走,在路上,他看见山垭口源源不断地出现一些土黄色人影,他们像奔走的蝗虫,混乱,嘈杂,密集。舅公站在路上看了一小会儿,快步跑回家,发现他姐姐家的院坝里也聚集起大批穿土黄色军装的人。人们在竹林下烧了一堆火,一个脸上留有疤痕的男人正在火苗上烧烤一只画眉。
后来舅公才知道,衣着土黄色军装的军人是被解放军击溃的“国军”,他们隶属钟彬所辖的第十四兵团,不久前在川湘边界被解放军狠狠揍了一顿,准备退到白马山布防。看着眼前烧烤的画眉,舅公惊讶得目瞪口呆。按照我们老家的说法,每个人都有灵魂。人的灵魂寄居在不同的鸟身上,比如,喜鹊,斑鸠,麻雀,老鹰,灰鸽。人的灵魂一旦由某种鸟所驮负,鸟就会成为他的守护神。鸟死了,人的灵魂也死了。据换给舅公木匙的木匠说,驮负舅公灵魂的不是别的鸟,正是画眉。一直以来,舅公对他的守护神敬畏有加,当他看见烧烤画眉的家伙准备吃掉他的灵魂,想也没想,握着吸铁石冲了上去。很快,一支黑洞洞的枪口抵上了舅公的脑门。他看见,枪管乌黑发亮,崭新的烤漆上满是阳光的斑点。这个场景一直潜藏在舅公的记忆深处。许多年后,当他拱出泥土,钻出地道,面对一支乌黑的枪口,一定想起了最先抵上他脑门的左轮手枪。是这支枪口改变了他的命运——尽管他带着一只木匙,也没能抗拒命运的力量。
舅公被“国军”士兵打倒在地。我的外婆——舅公的姐姐——在一旁痛哭,试图把她弟弟从枪口下解救出来。可花了很长时间,她也没能挤到人群中心,只能听到从空中飘落的怒吼,谩骂,恫吓,解释。舅公挥舞着手里的吸铁石,那是一件不错的武器,它让扑上来的几个“国军”士兵受到了轻微的伤害。人们把他摔倒在地,按住手脚,舅公身上的力气很快被大地吸收,再也没有力气挣扎。脸上有疤痕的男人继续把枪口抵在他脑门上,腾出左手,像珠宝商检查一颗有瑕疵的钻石,把舅公的破烂衣裳仔细检视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危险,放松下来说,狗日的,你想干啥子?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舅公说,龟儿子,你们好歹毒,即使是巫师,也不能吃掉我的灵魂。在舅公的骂声中,“国军”们听清楚了,他不想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明白过来的“国军”们发出阵阵谩骂和嘲笑。脸上有疤痕的男人把左轮手枪收进枪套——他的身份在后来的传说中,被人们确定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国军”连长,连长做了一个让舅公死心塌地的举动——他遣散周围的“国军”士兵,把舅公从地上扶起来,接着取出一只装有大群画眉的笼子,将它们一一放生。
我曾深度怀疑过这一细节。在我看过的影视作品和书籍中,“国军”的低级官员僵化而麻木,很少有顺应潮流之举。一个刚吃了败仗的“国军”连长居然相信群山深处残存的习俗,我只能把它视为为了让舅公的人生转折多少合乎逻辑,而由历代讲述者逐渐丰富的一道伏笔。自此,舅公认为连长有起死回生之术,自愿在“民国”倒台前夕成为“国军”的一员。事实上,当溃败的“国军”从阿尾寨退走,追随连长的舅公连一套军装也没有,他从连长手里得到一顶军帽,像傻瓜爬上一艘行将翻覆的大船,跟随“国军”到白马山布防。是时,他姐姐刚生下我母亲,来不及阻止他的疯狂举动,带木匙的舅公就再次离开了家乡。
阳光落在白马山陡峭的山冈和坡土上,密布的战壕像编织的蛛网往远处蔓延。大批新鲜的带有潮湿地气的泥土被翻到坚硬的表面,一阵新耕地的气味随着秋风往远处弥漫。舅公在行军灶前吃过早饭,收好木匙,躺在一块大青石上玩耍他的吸铁石。他仍然只戴着一顶军帽,身上破烂的黑色衣裳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被抓来的民夫。正当他把吸铁石吸到身边的一把军用铁锹上,连长走过来,拍了拍他肩膀。舅公从青石上坐起身,看见连长身后跟着两个军人。一个戴一副眼镜,面孔白净清瘦,样子不够成熟,仿佛是被人从他母亲子宫里硬拽出来的;另一个五大三粗,一脸横肉,瞎掉的右眼戴着一只黑色眼罩,一看就是个不好惹的角色。过了一段时间,舅公才弄清楚他们的来路。瘦个子是“国军”从昆明征来的工程师,学建筑出身,“国军”本来想让他帮助设计战壕,可一直忙着败退,他没有施展本领的机会。叫独眼龙的大个子则是“国军”捡到的流落土匪,溃退途中,连长顺手给他扣了一顶军帽,独眼龙从此加入“国军”序列。舅公从两个陌生人身上收回目光,听见连长说,你们三个,工程师,独眼龙,还有带木匙的家伙,你们没受过训练,打仗派不上用场。你们看,在我们侧面的大山里面,有一条小路直通贵州洪度,上峰担心共军派部队抄我们后路。你们有两个本地人,熟悉地形;有个工程师,能够画图。现在上峰命令你们,到山上潜伏,发现敌情及时通报。你们准备一下,一会儿我送你们上去。
在老家人后来的讲述中,准备过程被渲染得绘声绘色。人们极尽想象,把从影视上看来的“国军”装备全部用到了带木匙的舅公身上,以显示此次行动非同小可。军用铁锹,尖嘴镐,帐篷,洋火,手电筒,洋油,干粮,被褥,水壶,大衣,炸药,以及两支可有可无的中正式步枪。人们把能够想到的东西都加到带木匙的舅公身上,他显然背不动,又给他加了几个帮手,才在连长的带领下,往远山进发。很快,小小的队伍被大片林莽吞噬了。阳光落到林外。阴暗潮湿的林间回荡着风声。偶尔露出林梢的高岩亮出一块瀑布,像一面白色的三角旗在蓝天下飞扬。舅公跟着护送队伍走了一程又一程,脚下落叶沤烂的腐殖土绵延不尽,踩上去像云朵一样疲软乏力。遇到陡峭的山坡,他们要用军用铁锹挖出下脚的洼坑,才能把物资送到山顶。
舅公跟着队伍走了三天。他们曾露宿过两次。一次是在林中的河道上,一次是在山岩的下面。到了第三天中午,当他们再次看到远处的山峰和蓝天,就到达了目的地的高处——一个连接两面山峰的宽大垭口。垭口乔木稀落,草丛茂盛,视线良好。正面,一条废弃的小路像游动的小蛇若隐若现,小路消失的前方,遥远的群山一望无际,像传说中的马匹一路狂奔。连长把潜伏的三个人安顿好,带着护送的“国军”士兵返回战场。临上路前,连长反复告诫,没有命令不得撤退,擅自撤退者一律格杀勿论。许多年后,在老家人的叙述中,这两句话被反复提及,以证明舅公秉持了军人的良好纪律——尽管他的军旅生涯不伦不类。没被提及的,则是连长放飞画眉产生的心理暗示。舅公如此死心塌地,我长大成人后认为,他一直追随的并不是连长,而是寄居在画眉身上的灵魂。
三个人在垭口上驻扎下来。他们挖了浅浅的壕沟,搭了帐篷,甚至还垒了一眼土灶。开始,山野空旷而宁静,秋风带着啸声穿过垭口,送来了林中觅食的鸟鸣。在秋天细密频繁的林莽声响中,空中满是野果子——核桃,板栗,还有无数色泽各异的浆果——成熟的味道。他们没有经历正规的军事训练,但求生的欲望把三个人团结起来,有了周密的安排。他们留一个人看守从垭口下面蜿蜒出去的小路。小路游过发黄的草地,进入森林,汇入远处的陡峭河谷。解放军攻上来的猜测令他们脊背发麻,胆颤心惊。他们总感觉树林里藏有无数黑洞洞的枪口,等到某个命中注定的时辰,才张开嘴巴向他们一齐怒吼。战争的恐惧使三个蹩脚的“国军”士兵不敢懈怠,即使晚上,他们也会留一个人蹲在浅浅的战壕里,对着密不透风的暗夜出神。白天的情况要好一些,阳光的降临松弛掉他们紧绷的神经,除了看守小路的人,另外两个人进入森林,捡回野果和干柴,空中很快升起板栗烧熟后的清香。多数时候,他们躺在视野良好的垭口上,闻着秋草的芬芳,以讲述各自的身世打发时间。舅公讲到了瘟疫,画眉,木匙,吸铁石。随着时间进程,工程师对舅公的吸铁石产生了兴趣,他说,兄弟,把吸铁石给我看看。舅公正坐在草地上用木匙从军用铝盒里舀饭食,他把木匙对着阳光,举起来看了看说,我不是一个喜欢说谎的人,我用驮负在画眉身上的自己的灵魂起誓,不会把吸铁石给别人。工程师说,我在想,如果解放军打上来,我们三个弟兄怎样才能保全性命,需要用到你的吸铁石,我问你,你要命,还是要吸铁石?独眼龙说,给他,要不然,解放军冲上来你一个人去挡枪子。舅公一脸惶惑地摸出了吸铁石。
在传说中,舅公曾有片刻犹豫,他不想把属于自己的贵重物品交出去。到最后,大约是生存欲望占了上风,他把吸铁石郑重地交给了工程师。我猜想,舅公也有可能是想看看工程师会什么妖法,能够用一块吸铁石在枪林弹雨中挽救三个人的性命。工程师把吸铁石握在手里掂了掂,用铁锹试了试它的磁性,从身上掏出一个简陋的金属器物,对舅公和独眼龙说,你们看,这是我做的指南针,你们知道指南针吗?就是用来指引方向的机器。我的指南针坏掉了,需要一块吸铁石的帮助才能正常运转。独眼龙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准备逃跑?工程师说,不。他展开一张书籍大的纸张继续说,假如解放军攻上来,我们怎么办?舅公说,去给连长报信。工程师说,傻子,你跑得过子弹吗?还没等你跑下垭口,就死掉了。独眼龙问,那怎么办?工程师说,我这样想,趁解放军还没来,我们在垭口下面修一条地道,解放军进攻时,我们就藏进地道活命。独眼龙说,假如解放军把我们堵在地道里,只有像地老鼠一样被他们逮住。工程师说,不会,你们看,地道里面像迷宫,外面有很多出口,我们可以在里面储存食物,坚持几个月没问题。由于地道结构复杂,我们得有指南针的帮助,才能完成修建任务。舅公和独眼龙把头俯在白纸上,他们看见,密密麻麻的线条像无数铁丝虫在纸上蜿蜒,一会儿像蛛网一样整齐,一会儿又像一团毫无头绪的乱麻。
工程师修好指南针的那天早晨,晨光带来了远处隐约的枪炮声。舅公所处的垭口跟白马山主战场同样位于群山高处,虽然相距数十公里,仍然能清晰地听见白马山方向的枪声,炮声,军号声……枪炮声真密啊,它们超过了舅公所听过的鞭炮声,仿佛谁不小心点燃了天上绵延的霹雳,声音密集而尖厉。骤然响起的枪炮声加快了他们修建地道的速度,三个人挥舞起铁锹、尖嘴镐,在工程师指挥下,从一丛隐蔽的红籽树下动手,很快挖出一个洞子。洞子慢慢往地下延伸,产生的泥土他们用编织的箢篼运出来,按照工程师的要求,整齐地筑成一条环形战壕。战壕根据设计,以垭口的草地为中心,逐渐向两面山脊辐射,形成交通壕,散兵坑,屯积物品的暗堡。随着洞子深入地下,枪炮声听不见了,宁静的空气给了他们三个人充分的安全感,也促使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往地下掘进。两天后,即便躺在垭口上的草丛里,也听不见白马山方向的声音,他们不知道战场上交战的双方谁输谁赢——有可能“国军”击溃了解放军,解放军正积蓄力量准备卷土重来;也有可能解放军击溃了“国军”,“国军”正伺机反扑。对未来缺乏判断的三个人只好把命运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加快了地道的掘进速度。他们甚至做出长远打算,把食物储存到冬天使用。秋天,则以树林里的野果充饥。
秋天过去了。
冬天过去了。
春天伴随着鸟鸣,从树梢的新绿一点点地泛滥开来,阳光越来越温暖。草地上升腾起阵阵湿气,有了植物缓慢生长的馨香芬芳。经过秋冬三个人的快速挖掘,地道已经有了相当规模。除了最先开挖的主道,又产生了三条支道,支道上又各有数量不等的起迷惑作用的次道。按照老家人的说法,舅公从一个地道口进去,十多分钟之后,又从两百米开外的地道口钻出地面,非凡的成就感给他注入了强大动力,他甚至从工程师那里学会了在地下利用简陋的指南针辨别方向,从而把地道引向最初预设的地方。我对老家代代相传的口述史充满怀疑,当我以后来者的身份对舅公整个人生进行考察后,我相信,是死亡的威胁迫使舅公迅速成为一个挖掘地道的高手,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疯狂地爱上了这一工作。
春天的到来没有减缓地道的掘进速度。山野是宁静的,风声,鸟鸣,以及远处沟谷的水声,似乎白马山的交战双方已陷入一种沉默的对峙状态。宁静强化了三个人对未来的担忧,随着技巧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工序越来越熟悉,他们每天开挖的地道越来越多,剖面越来越整洁漂亮,连用运出的泥土修筑的战壕,也像蚁巢一样光洁精美。在这期间,工程师和舅公在独眼龙的帮助下,学会了用中正式步枪到树林里狩猎。他们打到过野猪,麂子,荒狗,獾子;舅公还用老家下绳扣的办法,捉到过兔子和松鸡。跟舅公高涨的情绪相反,工程师越来越忧郁。独眼龙提出,利用工程师手里的指南针,另外找一条路回家。听到独眼龙的建议,工程师哭了。他的眼睛仿佛是用劣质材料做的口袋,毫无征兆地漏水。哭了一小会儿,工程师说,你以为我不想离开这里吗?连长说过,没有命令,不准撤退,假如我们当了逃兵,不仅要遭枪毙,家人也要倒霉。舅公说,反正是死,这里还安全些。独眼龙说,我们绕过白马山。工程师说,到处是退下来的“国军”,你绕得过去吗?独眼龙不说话了。
逃跑的念头被否决之后,三个人精诚团结,继续进行地道的挖掘。他们更加科学地分配劳动力,一个人狩猎,一个人挖掘地道,一个人放哨兼负责准备吃食。合理的分工带来了安全感,也带来了地道的匀速推进。可惜好景不长,当地下出现第五条支道,地面上的战壕也贯通了出口时,打猎的独眼龙从树林里带回了一捆通心草。通心草是一种柔软微甘的植物,寄生在低矮的灌木或草地上。舅公说,独眼龙,你拿的啥子东西?独眼龙说,我拿的通心草。如果我们吃了通心草的汁液,它能帮助我们打开天目,看到千里之外驰骋的马匹。我们不是想看到远处的解放军吗?吃了这个东西,不用等他们走到跟前,我们也能发现。舅公说,你让我吃一点,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独眼龙说,不急,你去地道里把工程师叫上来,大家一起吃。
吃了通心草的汁液,舅公和工程师很快在明亮的阳光下睡了过去。舅公不是个爱做梦的人,但他服用了通心草,脑袋里不断出现奇妙的幻景。他先梦见一群女人。她们真漂亮啊!每个人长着一对小翅膀,趴在同伴的肩膀上,用妩媚的眼睛向舅公■。后来,他又梦见了一群奔驰的马匹,一群羊,以及一个带木匙的银匠。过了好一会儿,令人不安的梦境慢慢消退,空荡荡的意识让他有机会好好睡了一觉。舅公再次醒来时,发现独眼龙不见了,只有工程师独自一人歪睡在草地上,像一具战场上被人遗弃的僵尸,脸色灰白,模样丑陋。舅公拍了拍工程师说,你醒醒,独眼龙不见了。工程师醒过来,睁开眼睛说,可耻的家伙,他给我们吃了催眠的东西,丢下我们跑了。工程师又哭了。舅公说,我做了很多梦,你呢?工程师说,我也做了很多梦,先梦见一队队乌龟和挤满了人的沼泽,沼泽很大,人们站在稀泥里大声唱歌,乌龟跟随歌声的节奏翩翩起舞。后来,我又梦见发蓝的树根抓住了我的脚踝骨,让我动弹不得。我像被人捆住一样在树林里挣扎了很久,看见自己身上长出菌子,又长出大片闪烁蓝光的花朵。
舅公和工程师做梦之后,工程师的身体像一道被水流冲刷的堤岸,一天天垮下去。终于,到了山顶的树木露出秋天的征兆,工程师猝死在地道里。那时,他们已经在地道里修建了永久性居所,地道冬暖夏凉,工程师却死于一场没有来由的短时间出现的寒潮。据说,临死前,他拉着舅公的手说,我要死了,这场战争只能靠你了。舅公决定不辱使命。还有一种说法是,工程师并非死于寒潮,而是死于内心无法支撑的煎熬。他死时,地道里飞出一只形体巨大的蓝翅膀蝴蝶,光彩夺目,像个天使。老一辈的人说,那只蝴蝶是工程师灵魂的化身,蝴蝶驮负着他的灵魂,飞越了早已安静下来的战场。在战事惨烈的白马山地区,凡是战后活下来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奇怪景象。
现在,整个林莽覆盖的群山之上,只有舅公一个人坚守。他把工程师埋在垭口下的一小块洼地里,用石头做了标记,让坟头慢慢长出杂草,开出花朵。他则像一只疯狂的地老鼠,起早贪黑地掘进地道。饿了,用木匙吃一点煮熟的食物,或者用野果充饥。经过长期摸索与积累,舅公已精于计算。他不仅有计划地安排出打猎和寻找食物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他能以一个训练有素的工程师的精准,修建那座迷宫般的地道网,使它成为一座美轮美奂的地下宫殿。许多年后,我满怀戳破谎言的心情到达舅公坚守的地区,看到了地面上绵延数里的纵横交错的战壕,设计精巧的居所,盘桓于地表之下的复杂地道。它们数量如此庞大,几乎掏空了呈放射状的宽大垭口。
事情出现转机,是在人们的口述中显得比较模糊的一个年份。两个川东地质大队的勘探队员背着背包,握着地质锤,沿人迹罕至的白马山寻找铜矿。武陵山脉的地质结构表明,那一带应该有铜矿,或者铁矿。两个地质队员信心百倍地带着睡袋,干粮,指南针,在山上转了五天。当第六天他们翻过一个宽大垭口,眼前的景象把他们惊呆了。泥土新鲜的战壕密布在垭口正面,地上的灰烬和遗弃的食物表明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站在垭口上出神时,有人朝他们放了一枪,子弹尖锐的啸声还没消失,一个沙哑的声音在林莽里响起,他说,共军进攻了,共军进攻了……循声望去,两个地质队员发现,一个长发飘飘的“野人”提着一支步枪,在一丛红籽树间转眼消失,像一道不真实的幻影。此时,群山之外,到处都在演习抓美蒋特务,两个地质队员吓得掉头就跑,他们一口气跑下白马山,把这一重要军情汇报上去。
那道山垭口很快就被大批民兵包围起来。他们不时听到树林里响起一声冷枪,以及共军进攻的报警信号,却很难看到人影。人们不知道,在他们站立的地方,隐藏着一座庞大的地下迷宫。通过喊话,人们终于搞清楚了,向他们放冷枪的,是带木匙的舅公——一个连“国军”军装都没穿过的半吊子“国军”士兵。可搞清楚身份也没能让事情进展顺利,舅公拒不投降,精良的地道使活捉他的想法化为泡影。民兵们冷静下来,顺着他的身份,理清了舅公解放前的关系,很容易找到了当初派他出来放风的“国军”连长。“国军”连长在白马山战役开战当天,就很明智地带着他的部队下山投诚,解放后担任了邻县的文史馆馆员。衣着中山装的连长渐渐发福,除了脸上那道疤痕,已看不出军人迹象。当他百感交集地站在山垭口上时,一时哽咽莫名。过了一会儿,他才亮开嗓子喊,你是哪个?工程师,独眼龙,还是带木匙的家伙?舅公在树林里回答,工程师死了,独眼龙跑了,我是那个带木匙的人。连长说,你出来吧。舅公说,我不能擅自撤退。连长急了,他说,狗日的,大家都撤退十多年了,你龟儿子在深山老林里发啥子神经?你好生看一下,老子就是让你不要撤退的连长,现在,我命令你,缴枪投降,撤出阵地。
这个细节在老家人的无数次转述中,被赋予了很多搞笑成分,形成无数大同小异的民间版本。有说舅公高呼口号的,有说舅公跟人抱头痛哭的,有说舅公语无伦次的……但是,所有民间叙述版本的结局都一样——舅公带着木匙,直接从山上去了猫耳岭劳改农场。这里要作一点说明,按照政策,“国军”俘虏可以宽大处理,而潜伏特务只有劳改一途。以舅公的身份而论,他算不上正规“国军”士兵,顶多算个被“国军”连长的“起死回生术”诱骗到战场上的流民。可他接下来十多年的坚守和经营,以及死心塌地的效忠,无论如何都像个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潜伏特务。此后发生的事情,有效证明了老家关于木匙的说法——一个男人拥有一只漂亮的木匙,即使不种田也可以获得食物——带木匙的舅公正是这样,他即将去的猫耳岭劳改农场,由政府负责提供食物。
猫耳岭劳改农场是一个茶场,以生产高级绿茶闻名。监狱在山下,山上则是盘旋而上的层层茶田,看上去美丽而富饶。据说,舅公到达猫耳岭后,性格发生了根本变化。他性情孤僻,不跟人交往,说话常常词语含混,听上去像莫名嘀咕。除了交际障碍,他还得了嗜睡症。用木匙吃着饭,木匙还在嘴巴里,他就睡着了;上山去放羊,还没到达放羊地点,他又睡到半路上;让他种茶,他把头搁在锄头把上,像一只一动不动的黑色鼎罐,睡得又香又甜。劳改农场极尽人道,给他看了无数次医生,吃了各种各样的药,没有效果,人们对改造好舅公几乎不抱希望。
糊里糊涂地睡了两年,眼看舅公这一辈子快要睡过去了,形势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出于对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城乡广泛开展了修建战备洞运动。猫耳岭农场也不例外,受命在茶山修建战备洞。这项看似无关紧要的工作,再一次让舅公起死回生。从挖洞第一天开始,舅公就像换了个人。他把木匙揣在身上,精神抖擞,没日没夜地在山上挖洞。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惊讶地发现,舅公完全是一个打洞的天才,不仅速度快,效果好,根本无须再给他增派第二个人手。同时,舅公思维缜密,挖出的洞子精准无误,连通风、逃生,以及其他战备所需的功能,都一一考虑周全。犯人们怀疑,舅公的前世是一只地老鼠,或者穿山甲转世。一个月之后,劳改农场放心地把这项工作交给舅公,任由他独自一人在人们看不见的地下忙活。
老家的人们在月夜或者柴火边,讲到这个情节时,一致认定,是修地道产生的强大惯性,使舅公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只能沿地下运行。舅公正是带着这略显荒诞的悲凉,在猫耳岭的茶山下挖了两年。两年时间,他很少在犯人们的视线里出现,偶尔现身一下,多半也是为了应付点名,或者对付必要的饮食。两年后的春天,金黄色的油菜花沿着监狱的高墙向远山铺过去,像一块明黄的飞毯,一直镶接到远方安静的村落。背着步枪的哨兵踩着阳光勾勒出的弧线,穿过墙顶的通道,警惕地注视着墙内的动静。上午温暖的阳光引发了哨兵身上的倦意,正当他伸出胳膊,张开嘴巴准备打呵欠时,地坝里的一声响动,令他把后半个呵欠重新吞回到肚子里。顺着传出响声的方向,哨兵发现平整的地坝瞬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塌陷。他端着步枪跑下高墙,快速冲到地坝的塌陷处。哨兵惊讶地发现,舅公像一只穿山甲拱开泥土,钻出了地道。
炫目的阳光下面,舅公看见哨兵手里乌黑的枪口闪闪发亮。此时,他一定想起了许多年前,那柄“国军”连长顶在他脑门上的左轮手枪。彼时,他的灵魂正跟着画眉死去,或者,跟着活着的画眉飞翔。老家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什么要把战备洞修成地道,进而挖进监狱?监狱方面的结论只有一个——带木匙的舅公准备制造大规模的越狱暴动。这个说法似乎最符合逻辑,因为面对荒唐的结局,舅公很难自圆其说。
动机水落石出,事情变得简单了。经过问讯和审判,舅公由有期徒刑改为死刑。行刑那天,是春末。下午,一声清脆的枪声之后,舅公近四十年的人生被浓缩成一盒骨灰,由政府送回到他的老家。他的老家梨树湾已没有亲人。骨灰又辗转到阿尾寨他姐姐家。我外婆早已谢世,人们又尽心尽意地沿着我母亲出嫁的路线,把舅公的骨灰送到我的老家风吹岭。母亲接过她毫无记忆的舅舅的骨灰,像接过一个传说,连同那柄木匙,一起埋到了风吹岭的高处——那里终年吹着大风,像一群人在山上耳语。许多年后,舅公的坟堆长出花朵,不时有蓝翅膀的蝴蝶在上面飞翔。
选自《安徽文学》2013年第10期
原刊责编 张 琳
本刊责编 鄢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