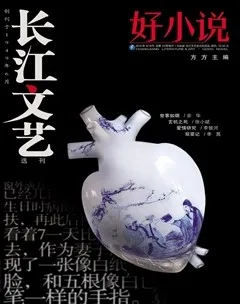池莉 :写出比生活更精彩的小说
池莉,著名作家,武汉市文联主席,代表作品有《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生活秀》等。
池莉是一位写实高手。
在情感实录已经铺天盖地的时候,她的《云破处》、《来来往往》和《小姐你早》,却依然以锐利的目光,把世间儿女情长剖析得鞭辟入里;
当城市文化聚汇成一股热潮,城市名片满天飞的时候,她的《生活秀》不声不响捧红了武汉女人和鸭脖子;
当教育成为街头巷尾绕不开的话题时,她的《来吧孩子》和《立》,又让多少父亲母亲和孩子肩负着中国式教育的沉重大山时,看到脚下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
情感、市井与未来,生活钻石最闪耀的几个棱面,在平凡人生的舞台上,折射一幕幕精彩的大戏。
但是池莉并不满足,一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
“新写实”是曾经评论家赋予池莉的一个文学标签,而她现在面临的新的现实是,哪怕再如何写实,作品往往也不可能比生活更“新”。每天成千上万比特的数据,在网络上堆砌而成的世界,比文字构筑的天地更新、更快、更庞杂也更为汹涌浩瀚。
在无数“记事”的网友面前,驾驭文字野马的池莉,忽然发现想象的草原已经被各种微博、段子和新闻事件挤满。
这是写实的文学在今天面临的困境,生活比文学更文学,生活比写实更写实。
这或许也是严肃的文学在今天遭遇边缘化的一个潜在因素。对于作家而言,人们的阅读趣味和习惯发生转变只是挑战之一,更大的挑战是:如何不被生活抛弃?
池莉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尽管她现在深居简出,尽管她现在有音乐为伴,但是写作——挖掘超越生活的精彩——仍然是最让她心旌激荡的冒险。
7月上旬,即将推出新作《石头书》的池莉,在武汉接受了笔者专访。这次采访被池莉笑称为“史上最热的采访”,这种热度,大概不仅仅来自气温,也来自话题所碰撞出的阵阵火花……
一
梁文道曾经有部时评集,书名叫做《常识》。常识是今天人们最缺乏的东西之一,就像人们越来越不知道,自己该有怎样的活法。生活的迷惘来自常识的混乱,因为曾经很多被视为常识的东西,今天都被奇奇怪怪的现实所颠覆。所以才有了池莉的《石头书》。
“石头书”的缘起,在于池莉为各种杂志撰写的一批专栏文章,它们都与常识有关。在确定书名的时候,池莉从书桌上一块镇纸石获得灵感。石头代表着古老、恒久和坚固,这些品质恰恰是常识应该具备的。
范宁(以下简称“范”):您的新书《石头书》读起来像一部杂文。
池莉(以下简称“池”):其实应该叫做长篇思想随笔,全书就是一个主题:常识。书里所写算是一种常识性的哲学,生活哲学。石头是最自然、最古老、最基础也是最恒定的,就像常识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一样。
范:为什么忽然关注起常识来了?
池:从很多年前开始,涉及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就没能获得重建或者修正。今天我们社会一个重大的文化缺失,是极其多的逻辑混乱和各种不靠谱的事情。且不要说更高级的思辨,就是生活层面,从行政管理到经商做企业到大学生读书,丧失常识的事情比比皆是。比如现在一些城市街头,洒水车都开始唱起红歌来了,有些老人对以前的音乐习以为常,都不知道洒水车靠近,结果浑身被淋得透湿。这样的决策判断究竟从何而来?还有一些执法语言,它本该是法律权威的体现,但是却使用一些网络语言,显得很不严肃。
执法语言应该具有权威性,应该严肃;洒水车本身的音乐已经约定俗成,轻易改变却没有让大众习惯,在我看来都属于常识问题。常识缺乏导致生活的混乱,工作理念、家庭观念等整个体系随之混乱。由此而生的笑话层出不穷,一地碎片。所以我才打算写这本书,希望自己梳理并找回生活中基本的常识。
以后我还可能写《石头书》的分支,继续思考生活里常识的缺失。我不会写得太艰涩、哲学化,就是活生生发现常识在生活中的缺失。
范:所以您是一位很关注社会的作家?
池:我觉得如果是写历史小说——其实历史小说也不例外,其实作家都是非常关注社会的。不同的是,有些作家会把写作思考与现实联系起来,有些则可能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我就是一个很自然关注现实的作家,并非常希望用写作参与现实。
但是我现在写作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我的小说里不会出现太多的社会热点现象,因为这些碎片不构成小说。以前我写《生活秀》的时候,生活还没有现在这样戏剧化。那时候吉庆街上还没有几个人,我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可以把某种人的精神在这条街上展示出来。但现在生活本身超过了小说,你怎么想象都赶不上它的戏剧性。作为小说家,我认为这些生活碎片就不再是我要写的了,我应该转向,笔锋应该转向更具有审美、更能建立想象的东西。
二
对于社会现状的认识变化,促使池莉开始转型。也许读者会不由担心,他们不会在以后的作品中,看到那个冷眼旁观男欢女爱、男痴女怨的池莉。不过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对于创作的紧张感,促使池莉向生活的深处探索,她说,在那些不经意的地方忽然找回生活的诗意,这种感觉比以前更好。
范:您现在是在筹备新的长篇吗?会是怎样一部长篇?
池:具体内容现在先不说,因为写作量还不是很大,但是我觉得内容找得很好,我自己很感兴趣。就像足球运动员的临门一脚一样,那一脚有没有踢中部位,这个球能不能射进去,球员自己会有感觉。我就感觉自己这一脚是踢对了。
范:那么这个长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
池:这个时间非常久了,至少五六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否定了自己很多次,重新写,一再变换,现在的样子可能都不是最初的那个了。但这都不重要,我现在写东西特别不着急,就想能够表达我刚才说的——找到超过生活审美。
我们中国作家有一个特点,我们都是从生活中写出来的。以前别人说我是“新写实”的代表作家之一,因为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新的春天刚到来,相对于“假大空”的时代,屏蔽的现实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满怀激情地把现实故事照实写出来就好。但是这个会变的。现在写作有个误区要突破,就是老是跟着现实跑。有些人热衷于写一些现实的泡沫和碎片,但是这种方式已经不适应今天的情况了。
小说不需要写这些碎片,没人看。小说必须保持小说的纯粹性,保持它的审美性,能激起内心更深的振动。现在很多作品振动不了人,因为大家知道的甚至比你还多,所以作家必须一再地更新自己,一定要真正地把握住小说的那种审美和震撼,就像骑马师一样,要勒住缰绳,不能被马带着走。
范:我想大家还是很想知道您正在创作的新作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否给我们透露更多呢?
池:我的上一部长篇小说叫做《所以》,所以下一部就是《因为》。《所以》写的是女性,《因为》就是写男性,以及这个男性眼中的女性。男人的社会活动更多,变化更大。我写着写着发现他又跟着现实跑了,他做的事说的话,就像现在社会上可以看到的新闻一样,这让我不得不重新来。尽管像我们这样的作家,完全有能力把这个现实性的东西写得很俏皮,但是那不对,毫无意思,触发不了一个读者内心深处最深刻的激动。我就要找这样的激动,现在这样的激动太难找了,不过我相信一定存在,可以找到的。这就是作家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是我这个作家存在的意义。我有没有可能找到它?一定有。我如果激动不了别人,我宁可不写小说,或者不出书。
范:为什么这么执著呢?
池: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太难被激动了,现实发生的事情太离奇了,超过了故事,所以作家不能一味写故事。
《因为》里面这个男人被我写得死去活来很多次,我还是觉得不对,因为社会上浮在表面的东西太多了。我刚刚以为某个情节能够达到审美的要求,但写了没多久,就发现社会上的东西比我写的还要离奇,所以我一次又一次改,最后我发现,我错了,实际上还是被带着跑。
所以我必须坚持小说最能感动人的,那种深刻的,像刀子一样的力量。只要有人,这种力量一定会存在,就看小说家驾驭得够不够。这对我来说是更严峻的挑战,也许我写不出来,但我只有这么做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的灵感和力气都有了;如果还那么随波逐流地写,写着写着就无趣了。这种感觉挺像国足,踢着踢着就怎么踢都不行了。
采访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池莉忽然宕开一笔,说起自己的看球经历。从球迷岁月说到南非世界杯,然后居然又折回到文学上来——
池:很多年轻男孩看足球,根本瞧不起女人,认为女人不会看足球,更何况我这个年纪的女人。但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在看足球了。最开始电视只有这么大(池莉比划了一下)。在我们医院,那时候电视上都还是雪花的时候,我就在看足球。应该是二十出头吧。我还在现场看山东对武汉,就在新华路老体育馆,那时候现场根本都没女的,而我就是从那时候一直看到南非世界杯。
范:南非世界杯之行一定很难让人忘怀吧?
池:到南非之后,我要求去索维托,可导游不让去,说那里都是黑人,非常危险,不能去。我说我无论如何要去,冒着天大的风险也要去。
有两个人是我去南非的目的,一个是图图大主教,一个是曼德拉,他们都曾经住在索维托。图图大主教现在还住在索维托,他对面就是曼德拉的家。
结果去索维托的一路真是太好了。一路上我们看到非常贫穷的景象,满眼都是矮房子,但是一路上看到的那些黑人小孩都在踢球,我情不自禁下车去跟他们玩球,非常开心(当国足惨败的时候,我就想起索维托,那么穷,可球踢得那么好,黑人那么穷,却依然温和)。
后来我发现,索维托是我们翻译的中文名称,我在当地看到一个路标,上面写着“so we to go”,意译过来就是“我们去向(哪里)”,就是黑人长期那种歌吟般的询问,非常好的英文名,充满了对自己命运的诘问,这就是个很哲学的命题啊!
漫长的种族隔离和做黑奴时候内心的痛苦,成了这个地方的地区名称。如果只看中文的翻译和简单介绍,我们永远都不知道里面饱含着某种震撼人心的东西,只有去了实地才知道。所以文字永远有它切入人心的力量,通过新闻,通过简单的组合的文字是无法传递的。索维托给我的整个感觉就是震撼,从地区名称到孩子,到图图大主教。
所以我意识到,世界再现代,信息量再大,总有让人心里震动的人性。只要它还存在,只要是人,人心是永远会不满的。我坚信物质代替不了精神的需求,也代替不了我们对什么事情都想弄明白、弄清晰的需求。中国作家有更大空间,就看我们怎么做。
三
2012年12月15日,池莉坐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古典雍容的大礼堂,看到滚动屏上显示的该校著名校友:克林顿、布莱尔、安南、曼德拉和索罗斯,还有26位国家首脑人物,以及15位诺贝尔奖得主,数不清的精英……
她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内心陡起狂喜波澜。但这种狂喜不是为了这所风云学校的风云人物,而是为了女儿亦池。那一天,是亦池从这所学校硕士毕业的日子。此前,亦池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这两所学校都是英国顶尖高校,与牛津、剑桥齐名。不过池莉很明白,再多的风云人物,女儿也不会是风云人物;再好的学校,大多数学生也只是普通人。
范:为什么在《来吧孩子》之后又要写《立》?
池:《立》是不同的阶段,亦池大学毕业后又考研,到研究生毕业时,我得出结论,这孩子的后五年成熟得非常快,真的可以站起来了。
我有办法让孩子立起来,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不要跟着社会潮流跑就行了。中国人真的好怕寂寞,所以很容易流行一种东西,形成一个潮流,事实上被裹挟其中的人真的是很受罪的。
《立》所说的主要是孩子自身的东西超过一切。有些记者问我的时候说:你当然好了,有你修桥铺路,孩子当然能够考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事实上不是这样,试想,如果我是中国家长,或许就会站在这个学校的起点上要求我的孩子,在那样的标准下,我的孩子还是很失败的,我会想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用啊。一旦考上,家长的要求就会变,他会根据平台变化,这样还算是成功吗?
但是我并不像别的家长一样,我说这孩子是这个学校最普通的学生,智力中等,没有过人之处。她的优点是愿意自食其力,懂得勤俭节约。我在《立》里都没有写到过,亦池到现在都攒着买东西时候送的购物袋,她认为这就是一件东西,不能随便糟蹋了,直到用坏了为止。
不过,她又不是那种特别抠门的人,小里小气,土里吧唧的。她最成功的地方是从来不恶,不具备挑战性,多了一些善和宽容。
范:这里面其实写的还是您的教育理念?
池:以前我看到很多学校高三班的教室里会悬挂横幅:“多考一分,干掉千人”,全都是这样的口号,让孩子们长大之后真的一点都不懂善意。父母也会说孩子不孝顺,但是他们不想想,为什么孩子会变成这样?
不与人为恶,挺好。亦池钢琴到九级,但她从来不参加任何竞赛,从来不挑战。但是因此她获得更多,人人都喜欢她,因为她无害嘛,所以别人愿意把机会给她,认为她是不会欺负人的。我发现这样很好啊,一点竞争心都没有的,最后是什么都不缺,能走得更久。
这个对一般家长也许很难做到。其实真不要有挑战性。为什么一定要有挑战性?从来都是想要干掉别人,为什么从来不去想和别人合作?为什么今天连婴儿奶粉都敢下毒?就是为了要赢,要挣钱,要把别人的利润变成自己的,最后玉石俱焚。所以我提倡的“立”就是不要挑战。
范:这个我很能理解。现在大家觉得只有挑战才能立足,恰恰不挑战反而能立得更好。
池:老实人不吃亏,不傻,不是没有学识没有见识的。立就是不挑战主义。做好自己就行了。
四
写微博、种菜、听音乐,这几年池莉深居简出,很多读者都不知道她在做什么。新书里的一张照片上,池莉一身简单打扮,拿着农具站在菜地里,和韩少功一样,她也过了一段农家生活。她笑着回忆起几年前这段经历,用了句网络流行语评价自己:“都市里的田园生活真的只是传说啊!”
范:我还经常看您的微博,写微博的时候会被碎片化影响吗?
池:一个人一天面对那么多陌生人,一开始可能会兴奋,但时间长了,就会觉得被大量东西占领了,时间、心情都没有了。所以最开始我很抵触。去南非看球的时候,认识了几个小记者,做网站的,他们跟着我玩,都挺开心的,每次我建议哪里去玩,跟着我就收获最大。他们几个是管微博的,所以开个微博,“友情出演”。
开了微博后,我对它也是有看法的。微博成了新闻直播,这个作用肯定是最大的。它有大量的泡沫,但是新闻直播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它可以第一时间最直接地反映现实。这让我比较看重。它可能会促进媒体的变化。
和你们年轻人不同,我不玩微博,我仅仅只是把我要写的写上去,两年多才300多条,不算多吧?但是因为有550万人在看,不更新很多人就在期待,我还是多少有了责任感。
我的微博上很少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和任何人互动,但是会浏览一下大家在说什么。很多年轻人和我性格接近的,比较偏静的,会习惯我的微博,我也不舍得抛弃他们。有些人不想炒新闻,就是想知道一点书讯啊,或者我怎么调剂生活,大是大非面前我保持怎样的姿态等。很多年轻人会坚持看。
我不会被别人所左右,我也不发火,就是简单的聊天。现在网站编辑也成了我的朋友,还有几百万人很沉静地跟着,中间确实有些人内心很孤独。
范:看您的新书,您之前还种过地?
池:这两三年抛荒了,发现种不下去,呵呵。
我在武汉的家里,后院有两分地。我种菜不是想过田园生活,仅仅是比较感性地觉得养花种菜蛮好玩的,然后有很安全的食品(自己种的菜真的好好吃)。
这只是初期感性的想法,我内心深处实际上想:中国人有一个情结,特别想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在上面工作、劳动,“属于我”,我觉得这种象征意义对我特别重要——辛苦一辈子,终于有一块地是属于我的,我可以耕种、享受、收获,这种感觉特别好。
范:所以种地的感觉特别好?
池:人就是这样,一旦获得这种感觉,现实马上不一样了。第一,这块地其实并不是真正属于我的——这房子只有50年的所有权啊!
第二,我发现,用一个简单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一个理念,却麻烦了太多的人。种子要靠农科院的朋友,还有纯有机的肥料、农具,一切的一切都麻烦好多朋友。农具是别人回乡下找铁匠新打的,或者是拿自己家的;还有朋友把乡下的大水缸开着卡车运过来,就为了接雨水!兴师动众,场面之大!还有农大的科学家,院士,替我操心,“你今天的豇豆生了病虫害,要怎么怎么做……”太大材小用了。人家是院士啊,来帮我操心这些,我觉得太过意不去了!在现代都市种菜就是一个传说,实在麻烦太多的人。但不麻烦他们,我都种不出东西——最开始买的种子就是假的!
实际上是一个专家组在研究我种菜这件事。这个事情持续了三年,我坚持不下去了。这个成本太高了,人家多忙啊!
范:投入很大,收获应该也很高啊!
池:收获还是很大的,豇豆茄子辣椒西红柿,随着季节种,有这么大一个科技团队,能长得不好吗?吃不完就给邻居,邻居都说味道好。但最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是什么人,住在什么地方,就做什么事情,就做符合那个地方的事情,不过体验一下也挺好的。
我真的是热爱土地,难道你不觉得我像个农民吗?我真的很农民的。我觉得我好会种地,有知青的经历,17岁到乡下,也种菜。
范:听说您还是音乐上的发烧友?
池:我谈不上那种特别高级的发烧友。在中国,一说你喜欢音乐,就涉及“发烧”,器械啦,自己去买喇叭功放啦,流派啦,古典的当代的啦,我特怕中国的方式。
我从来不敢标榜自己多喜欢音乐,只是十几年来就在武胜路买CD,后来去北京。就是喜欢听音乐,很纯粹地喜欢。我不太苛刻地挑音乐器械,只认准一条,买最好的,以前用的是波士牌,最近可能会换麦景图。
我会去换最好的最新的音乐器材,但一定是要原装的。从最初到现在都记不住换了多少。最早买国产器材,还要到中南商场门口,找熟人帮忙才买得到,那时我还没有孩子呢。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套一套地换,会跟进这个市场。
我还会去试听。北京国贸的CD试听间,只有我一个人,前不久听了两个半小时。那间CD行一老一少两个服务员就一直陪着我一个人,他们反而很激动,说上了一天班,这两个半小时算是做了事情。
早年很穷,稍微有一点钱的时候我就会去注意音乐CD。我选的CD基本都是进口的,北京那家CD行里,我发现过一套钢琴家鲁宾斯坦的专辑,2003年引进的,到现在没卖出去,我欣喜若狂,全套都买下来了,没有人能够替代他的指头砸在琴键上的声音。我出国都会去逛碟店,买碟子回来。
南非世界杯上的夏奇拉,能歌能舞,那种嗓子的变调是不可想象的音乐,好的音乐没有止境。我就觉得现在自己太穷了,否则可以买更多的好音乐回来听。
我们总说音乐太高雅了,其实不是,是整个社会缺乏普及和熏陶,随便乱放一些没名堂的歌。音乐作为我们基本感情的抒发在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好像放什么无所谓一样。其实听到那些好的音乐真的会上瘾。
范:以前我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您还说自己在剪片子呢。难道最近还在参与一些影视方面的制作吗?
池:上次剪片子是改编我的一个戏,剪辑得很糟糕,所以我就帮帮忙。原来我倒是想过拍纪录片,后来放弃了,我就特想拍出租车司机。结果和一个司机聊来聊去,他反问我:“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啊?你说你是医生,怎么喜欢这些东西?”我在外面面对陌生人从来不说我是作家,因为我以前也确实是医生,一旦暴露身份,你就听不到真话,别人也不会跟你说了。
五
关于池莉住在哪里,坊间总有很多说法,或者住在上海,或者并无定所。池莉告诉我,她更多时间还是在武汉,而且武汉之好,别的地方都找不到的。
范:您觉得自己算是“宅女”吗?因为现在其实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了。
池:我不算“宅”,出去走动的时间不算少。写作长篇小说《所以》的时候,我在上海闭关3个月。我挺像一个背着行囊到处流浪的人。只要住处干净和安静就行。
我有位武汉的朋友,曾经邀请我参观他的住宅。偌大一栋房子,几乎所有装修都是他本人亲力亲为,相当精致。我很惊叹但并不羡慕,因为我对装修不感兴趣。我家最大的是书房,大约五六十平米,但实际上家里到处都是书,我不怎么打理房间,够住就好,房间大了难做清洁。
现在年轻人很多被房子压着,可以理解他们的压力。如果要结婚,买一套房子倒无可厚非。对于家庭而言,房子很重要,却不是第一标准。我当年结婚的时候住房才15平米呢。结婚的第一标准一定是爱情而不是房子。
范:现在来看,武汉在您心目中是什么地位?
池:武汉有别的大城市一样的毛病。建筑太多,道路拥挤,空气很差,大城市不宜居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但是武汉有其可爱之处。
武汉有足够的淡水,所以生活很滋润。我出差北京,几乎一到那里就觉得皮肤干燥,也倍加想念武汉。武汉四季分明,植物长得很好,花开得很好,连蔬菜也比别处好吃。我喜欢从我住处附近的农民手上买青菜,买禽畜,我在我家附近发展了很多“据点”。平时和他们相处也很好,需要时一个电话,他们骑着自行车就送来了。
武汉人的直爽个性让这座城市充满“处江湖之远”的人情味,有人气,有人情,有山水,这就是座不错的城市。
责任编辑 向 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