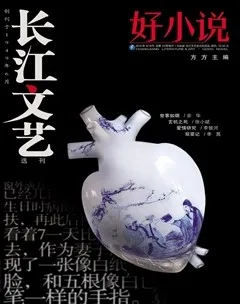宁静里的时间之花
自时间的消逝和剥落里,取得最终的灿烂和成熟。
——郑 敏
作为中国现代诗派“九叶”诗人中唯一健在的郑敏,她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诗路跋涉中留下了一串让人沉思的脚印。从她的第一首诗《晚会》到近期的《最后的诞生》,从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到《郑敏文集》,这棵历经风刀霜剑的诗坛常青树蓊郁丰茂。她一以贯之地坚持新诗现代化的有益探索,追求雕塑般沉思的诗歌品质。这是一个有着“成熟的寂寞”的女性,而随着时间到来的智慧使得她的诗歌独树一帜。
“也许最美总是沉默”
1920年7月18日(阴历六月初三)郑敏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官僚家庭。从儿时起郑敏就对自己每天出入的东华门和北池子大街附近的闷葫芦罐胡同(后更名为蒙福禄馆胡同)备感兴趣。新月诗人朱湘曾经在散文《胡同》中专门提到了闷葫芦罐胡同。郑敏祖父王又典福建长乐人,光绪十一年举人。其为前清颇有诗名的碧栖词人,著有《碧栖诗词》。郑敏的生父王子沅早年留学于法国和比利时,回国后在外交部任职并曾出任悉尼公使。然而他却因为情感上遭遇重创而精神消沉,再加上肺结核的病扰,最终越来越陷入对人生追问的他辞去公职,成为一位不问世事念经诵佛的居士和素食主义者。由于生活无着,郑敏的父亲只得外出四处借粮借钱。但不善言辞的他尽管早出晚归,往往每次都是空手而返。而有意思的是他在山中看见古寺和僧人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自己出行的目的。在与僧人的谈经论法和山中溪水淙淙、鸟声啁啾里饥饿似乎已经离他远去。王子沅四十多岁即去世。小小的郑敏此后对生命哲学的探索多少还是受到了父亲的性格和命运的一些影响。郑敏的生母林耽宜,为王子沅的第二夫人。她读过私塾,贤惠聪敏,经常喜欢用闽调吟诵古诗。她对郑敏的影响很大,只可惜三十多岁就守寡,含辛茹苦拉扯六个子女。由于无力照顾,郑敏等兄弟姐妹六人曾一段时间暂居在外祖父家。郑敏的二姐王勘很早过世,郑敏也在两岁的时候突然患上脑膜炎并差一点死去。经过多方救治以及外祖父四处寻找民间偏方,郑敏才逃过一劫。病情好转的郑敏需要一个较好的环境休养身体,于是她被过继给了姨妈林妍宜。由于养父姓郑,这个王家小姑娘也自然改姓郑了。郑敏的养父郑礼明与生父王子沅两家是世交并且都曾留学法国,后来还结拜为把兄弟。郑礼明曾经在留学法国时与一法国女子结婚。回国后,这位法国妻子因为不能适应中国的生活习惯最终离郑礼明而去。受国外文化思潮的影响,郑礼明为人处世遵循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宽松自由的家庭环境使得郑敏小小年纪就养成了多思独立的个性。正如她自己所说,从1939年踏入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园一直到今天,她之所以能够坚持探索的道路就在于独立思考的本能。
由于郑礼明总工程师的身份以及他和留学回国的朋友一起经营着一个煤矿,年幼的郑敏和养父来到了位于河南六河沟的煤矿。当时全家暂时居住在半山坡的一个房子里。人生地疏的郑敏在寂寞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种寂寞和多思更使得她在清晨或黄昏像是一个雕塑一样静默地坐在那里。只有园子里的蟋蟀和蝈蝈的叫声陪伴着她。从那时起郑敏就养成了静心观察事物以及体察内心感受的习惯。儿时,她唯一的乐园就是煤矿附近的东山。那里四处是荒坟,年幼的郑敏不敢轻易外出走动。草木鸟虫的自然声响以及无声的日升日落陪伴着郑敏。每天郑敏在矮墙前看山坡下唯一的一条大马路上矿工们上班下班的人流。突发矿难的尸体和哭声使得郑敏对人世无常有了过早成熟的理解。然而当时最吸引郑敏目光的是每天经过的一对梳着麻花辫子、穿着长裙短袄的姑娘。她们举止温文尔雅,每次分手时还彼此鞠躬告别。后来郑敏听说其中的一个姑娘得了肺病死去。此后,在这条喧闹的马路上只剩下一个姑娘,形单影只。无比孤独的郑敏更是对这个姑娘无比同情,心有戚戚。父亲希望郑敏学自然科学,在她五岁以后就教她数学。可是郑敏对数学没有半点兴趣。看到每天晚上郑敏在院子里呆呆地仰望星空,于是父亲又开始教授她天文知识。可是郑敏感兴趣的却是翻看父亲所谓的闲书。四大古典名著以及《小说月报》成了郑敏的启蒙读物。父亲也只好改弦更张,每晚让来自北京的保姆给郑敏讲一些民间奇闻。闲时,他也亲自给郑敏讲《西游记》的故事。因为工作忙碌,父亲又给郑敏从矿上请了一位家庭老师。这位老师家学渊源,写得一手好字。可是郑敏似乎对背诵古文也不太感兴趣,只对屋外的大自然充满了无尽的好奇心。
“上天仍赐给你季节的沛霖”
1930年春天,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10岁的郑敏随母亲又回到了北平。
郑敏插班在培元小学读四年级。当时校舍以及师资环境都极差,老师动不动就对学生打板子甚至还罚跪羞辱。郑敏对这种教学方式以及师生的冷嘲热讽很不适应并且还时常生病,功课跟不上了。生母和养母对此都很着急,利用暑假时间她们请老师给郑敏补习功课。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起床,然后坐洋包车上学。年幼的郑敏对每天挥汗如雨的车夫产生了同情,后来还专门写诗以作纪念,“二十年代的北平,每个破晓 / 衰老的人力车夫的咳嗽 / 在人生的尽头,呼出白色寒气飘绕 / 我在车子里,幼小的心灵满载忧愁”。1931年郑敏转学到贝满女子中学附属小学读书,学习成绩有很大提升。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父亲不得不辞去六河沟煤矿公司的工作,先后在蚌埠和淮南的煤矿任职,后来又调南京任度量衡局局长。
举家迁往南京后,郑敏跳级考入了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读初三时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章骏仪对郑敏的文学影响非常大。在她的引导下,郑敏大量阅读《古诗十九首》以及李商隐、李清照和李煜的诗,并且还阅读了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以及《简·爱》等西方著作。受此影响,郑敏和同学创办了读书会。每周六,七个女孩子在巨大的法国梧桐下一起讨论中外文学作品。在南京女中读高中期间,时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的大哥王勉使郑敏进一步接触到了新文学。郑敏几乎对各种文学流派都能够接受,她不仅喜欢鲁迅、周作人和梁实秋,而且也喜欢徐志摩、戴望舒、陈梦家的诗作。尤其是对废名的禅宗意蕴的小说她更是情有独钟。这似乎又再次体现了生父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抗战全面爆发后,郑敏不得不休学,跟随父亲辗转到庐山避难。1938年全家坐船经三峡到达陪都重庆。郑敏在张伯苓创办的南渝中学读书。
1939年考大学前夕,郑敏得了一场重病,但最终还是考取了西南联大外文系。
9月,郑敏独自一人从重庆出发,经贵州终于抵达昆明。在报到时郑敏临时决定改修哲学系。这一决定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在校期间她不仅系统接触到中西哲学,而且她几乎天天到国文系和外文系去蹭课,比如闻一多的“楚辞”研究,沈从文的“中国小说史”。这些简陋的铁皮屋顶的教室却给了郑敏一生以巨大的影响,“我也从白衣青裙的校服 / 走出,穿过昆明的街巷 / 奔向那一排排的铁皮之屋 / 来到智慧之堂,心灵之乡”。尤其是冯至对里尔克等德语诗歌以及十四行诗的研究,使得郑敏真正开始了解西方诗歌并付诸写作实践。通过外文系的卞之琳,郑敏又接触到了17世纪的玄学诗以及艾略特、奥登等英美现代主义诗歌。郑敏一有了诗歌灵感,就记录在随身携带的一个淡蓝色封皮的小本子上。积淀了两年多的时间,在一次冯至的德文课后,郑敏红着脸将自己的手抄诗集递给了这位诗人老师。第二天课后,冯至归还诗稿时肯定了郑敏的诗歌,“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是一条寂寞的道路。”
晚年的郑敏每当回忆起西南联大岁月的时候仍然无比激动。日常交往中的冯至不善言辞,郑敏每次去找冯至先生,两人阅读的时间多于交谈。但在当时,郑敏觉得两个人默默坐着的感觉也很好。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以及冯至的诗集《十四行集》,使得郑敏逐渐找到了一条自己一生将坚持的诗歌道路。尽管战火频仍,昆明在郑敏的青春岁月里仍是“迷人”的。这也开启了郑敏诗歌和哲学的大门。大哥王勉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到昆明工作,他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了郑敏很多的照顾。王勉曾经担任过国民党远征军的美军翻译,期间他与西南联大的冯至和闻一多等人都有着深入的文学交往。大学期间的一个暑假,郑敏和一个女生到云南呈贡去旅游,结果半路上钱花光了。无奈之下,她们想到了老师沈从文。于是她们一路来到湘西凤凰,可惜老师不在。张兆和想办法凑了钱,她们才得以乘火车返回昆明。
在古希腊的神柱上铭刻着一句话——“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对郑敏的诗歌写作有着灯塔一样的烛照。“诗歌与哲学是近邻”,郑敏如是说。作为诗人哲学家,在长久的向天空的守望中,她一生都专注在哲学诗化的沉思里,“唯有坐在像里尔克那样的心灵里,你才会透过那无限沉静的注视与倾听”。一次,郑敏走在黄昏的田野上,金黄色的光辉在夕阳下跃动、闪耀。背景是静穆而孤独的稻束,“金黄的稻束站在 / 割过的秋天的田里 / 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收割过后的田野空旷寂寥。疲倦的稻束静默地伫立在空荡荡的田野上,风此刻也停止了它的呼吸。收获过后的人们四散离去。而此时,稻束与孕育了无数儿女的善良、疲惫、满足、欣慰的沉默的母亲一样,获得了同等的哲学内涵。郑敏如一只美丽而勤勉的河蚌,在无尽的诗思的潮汐和咸涩而坚韧的等待中,静静地打磨和照料着闪光而圆润的珠贝。正如诗人公刘所评价她的那样,“如果现实可以比作一个能够目测的坐标,那么,女诗人郑敏大概是九叶中距离最为遥远的星座。她有一部分诗作,写到很美,仿佛一口布满青苔的古井:幽深、清澈而甘冽,还寒气逼人,云天的影子隐约可见,却又不甚了然。”
1943年夏天,郑敏从西南联大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她的学位论文是《柏拉图的诗学》。大学毕业后,郑敏在重庆北碚的一所护士学校教授英文和语文,后来到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做翻译。当时工作比较清闲,一天工作四小时,主要是翻译英文报纸。在空闲时间里郑敏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她的诗歌也开始在《大公报》等报刊发表。当时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青年诗人李瑛第一次读到郑敏的诗歌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个极富热情而又极富理智的人,因富于热情始有人道的浪漫的神秘倾向,因重于理智与现实,始产生了自然主义的作品”。
“奥菲亚斯拿着他的弦琴”
1948年,郑敏申请赴美留学,她最终获得了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布朗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为了凑足女儿的路费,父亲毅然卖掉了房产。郑敏在父母送别的泪水中乘船前往大洋彼岸。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郑敏都是在颠簸不定的船上度过。大海起初的新鲜很快被单调和枯燥所替代,只有每天的日出和日落能够给远离父母的她以慰藉和安宁。郑敏到美后,在英语系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郑敏不得不勤工俭学,在餐馆、商店、珠宝首饰厂以及电容器厂打工。后来搬到青年会,这样可以节省住宿费和餐费。1949年5月,远在温州的■为郑敏写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郑敏静夜里的祈祷》,“她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历史性的宁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一幅画面,一个雕像”。1949年夏天,郑敏突然收到了从国内寄来的自己的首部诗集《诗集 一九四二 —— 一九四七》。该诗集收入巴金先生主编的《文学丛刊》。郑敏抚摸着散发着铅字芳香的诗集几乎夜不能寐,她触摸到了诗歌和汉语以及祖国的体温。在美期间,郑敏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了深入系统的研读,并以17世纪的玄学诗人多恩作为硕士论文。由于经济拮据,她不得不经常加班打零工,未能及时提交论文。1951年秋天,郑敏到伊利诺州立大学申请了博士预科。这一年,郑敏相遇并结识了西南联大的校友童诗白。两人一见钟情,文学、音乐和哲学成了他们共同的话题。童诗白与郑敏同岁,2月14日出生于沈阳的一个教育世家。童诗白的祖父曾任沈阳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父亲■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8年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童■先后在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和南京工学院等高校任教,被誉为“中国建筑四杰”之一。童诗白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电机系,1948年秋天进入伊利诺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童诗白后来成为中国电子学学科和课程建设的主要奠基人。因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断交,在美的华人留学生被禁止离境。由于童诗白曾经参加了华罗庚等组织的“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而受到美当局注意,更是被阻挠回国。主管留学生的院长汉密尔顿找他谈话时说:“敌对国家公民擅自离开美国将受到罚款和监禁等严厉的处分,你看美国培养你们那么多年,你回去帮共产党打我们美国人,说不定你一个人的作用要顶一个师,顶成千上万士兵呢?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在这儿待着吧!”回国无望,童诗白只得在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任教。1951年春天,郑敏突然接到了童诗白的求爱信。当年冬天,郑敏和童诗白在伊利诺州立大学的礼堂举行了简朴而圣洁的婚礼。婚后,郑敏来到纽约与丈夫居住。她继续撰写自己的硕士论文,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声乐(1小时要交纳学费10美金),并经常光顾画廊和美术馆以及音乐会。郑敏的硕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并获得了导师时威伯斯特的极力称赞。1952年一个清风徐徐的晚上,郑敏和丈夫在路易斯露天体育场现场聆听了世界四大小提琴家之一的爱尔曼演奏的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郑敏夫妇完全被天籁一样的音乐折服了。
日内瓦会议后,经过中美双方多次谈判,留学人员终于可以回国了。
1955年6月,郑敏夫妇从旧金山乘船出发离开美国,经香港到达深圳。此后,童诗白到清华大学机电系任教,郑敏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组(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1956年,郑敏的女儿童蔚出生。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热潮的到来,郑敏也开始到革命大学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毛泽东思想。郑敏和同时代人一样,不断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和政治会议,进行精神洗礼。大跃进期间,郑敏下放到山西临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由于体力严重透支以及长时间饥饿,郑敏浑身浮肿,身上按下去就是一个深窝。郑敏整个人完全变了形,虚脱得卧床不起。随着1960年阶级斗争的激化,知识分子面临的政治形势更为严峻。一次郑敏无意间问了一个人一句“好久没有看见苏联的专家了”而受到单位领导的严厉批评。经过党组讨论,领导认为郑敏不适合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1960年郑敏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在1961年的“四清”运动中,郑敏到山西贫苦的农村插队一年。她和当地农民同住在一个冰冷的土炕上。这也使得她对中国乡村的生活真相有了深入的了解。1962年,三年大饥荒过后,儿子童朗出生。
1955年郑敏回国后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然而,郑敏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写作在建国后政治化热潮中遭到了集体噤声的命运。郑敏从1949年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的30年停止了诗歌写作。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觉得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可能再进行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和实验了。有意思的是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冲进她的住处进行破“四旧”的革命,红卫兵看了郑敏在40年代的《诗集:一九四二 —— 一九四七》时就偷偷告诉她非常喜欢这本诗集。甚至当时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头头也来问郑敏:“你真的下决心以后不写诗了吗?”当时的郑敏“脑子还停留在很僵化的左倾的激进的思维状态”,她甚至幻想如果可以牺牲自己的诗歌生命而换得中国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那也是可以的,所以郑敏对红卫兵们说:“可以不写。”可怕的诗歌冬眠期到来了!郑敏对汉语诗歌受到的伤害感到无比悲痛——“如果20世纪中国诗坛上有什么纯种中华诗歌的话,那就是这一批‘文化大革命’诗歌及此前在大跃进年代的全民撰写的大跃进民歌,一时间这两种纯种国产诗歌真是铺天盖地的红海洋,……它们都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在一场乌托邦之梦中的呓语,当时人们是如何充满了天真的自欺的热望,向往一个地上的天国,纯洁无瑕。……天国之梦中的豪言壮语与事后跌得遍体鳞伤的真实情况之间是多么奇异的联系!又是何等无情的讽刺!大跃进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纷纷落在大地上的并非事先允诺的果实,而是死亡,梦幻者的尸体。”“文革”中郑敏夫妇没有受到多大冲击,而大哥王勉则因为曾经在国民政府远征军中任职以及“因言获罪”被定性为极右派分子,他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竟然达17年之久。在红色运动的潮流里,郑敏在一个个压抑的暗夜里不断反思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一只只红色火焰上空的火烈鸟正是这一代人灵魂的象征,“我们都是火烈鸟 / 终生踩着赤色的火焰 / 穿过地狱,烧断了天桥 / 没有发出失去身份的呻吟”。
“诗啊,我又找到了你!”
“文革”结束后,诗人才又重新找回了失踪已久的诗神缪斯。直到1979年春天,一只搁放的生尘的诗笔才重又焕发了生机。
北岛和芒克等人创办的《今天》以及新诗潮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而郑敏等老诗人也再次焕发了诗歌的青春。1979年,除了已经逝世的穆旦,郑敏、袁可嘉、辛笛、陈敬容、曹辛之、杜运燮、唐祈和■等八人终于历经坎坷在北京相遇。这是“九叶”诗人平生的第一次集体聚会,也是郑敏第一次见到唐祈、陈敬容和曹辛之。而这距离他们四十年代的书信和诗歌交往已经过去了30多年——沉默而无情的30年。当从曹辛之家里出来后,坐在公交车上的郑敏心情如潮汐般起伏不定。此次受到各位诗友的鼓励,郑敏感觉仿佛又回到了缪斯的怀抱,“幸亏我的诗神能走出朱丽叶的尸棺”。在颠簸的汽车上,诗神重又回到郑敏身边。她在汽车上完成了搁笔30年后的第一首诗《诗啊,我又找到了你!》——“绿了,绿了,柳丝在颤抖 / 是早春透明的薄翅,掠过枝头。/ 为什么人们看不见她,/ 这轻盈的精灵,你在哪儿?在哪儿? / ‘在这儿,就在你心头,’她轻声回答。/ ……让我的心变绿吧,我又找到了你, / 哪里有绿色的春天,/ 哪儿就有你,/ 就在我的心里,你永远在我的心里,/ ……有你在我身边,我将幸福地前去”。郑敏认为这首诗是自己的“再生之诗”。1981年7月,由曹辛之设计封面的《九叶集》终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次迟到的结集。自此,“九叶诗派”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进入了新诗史。诗集出版后影响很大,尤其是受到了青年诗人的青睐。青年诗人林莽在王府井书店看到《九叶集》时无比激动,一下子买了好几本分别送给诗人和朋友。而远在兰州的唐祈不仅在课堂上给学生教授包括“九叶”在内的新诗流派,而且还将郑敏等人的诗介绍给了当时的青年诗人北岛。北岛看过这些诗后大为震惊,“我们想做的事,40年代的诗人已经开始在做了。”北岛也自此通过唐祈和吴思敬等人结识了郑敏。1981年的春天,郑敏先生家的园子里开满了二月兰。一天清晨,北岛、芒克、江河、多多、顾城、杨炼、林莽、严力、一平和田小青等一行十几人,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前往郑敏先生的寓所。这些渴望诗神眷顾的年轻诗人简直是行进在朝圣的路上。到了郑敏家里后,年轻诗人们热烈地与她谈论现代诗歌流派以及当下诗歌的现象和发展前景。
回国近30年之后,郑敏才第二次走出国门。在八九十年代到美国、瑞典、挪威、丹麦等地讲学过程中,郑敏对西方的结构主义诗学有了深入的认识。她这一时期对汉语诗歌的语言、新诗传统和文化以及西方和本土化解构文化思潮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诗学意义。晚年的郑敏每次与青年诗人聊天时都对汉语诗歌的命运充满了忧虑。她的语言良知在当下中国诗坛具有启示录般的意义,“最近当我合上又一本铅印的诗选集时,我默想:不能再这样写下去了。我们已经走进一条窄胡同,我们需要退出来,重新打开诗的视野。”
儿子童朗在美国教书,只有女儿童蔚陪伴在她身边。每当想起远隔重洋的儿子,看似平静的郑敏实则内心波涛涌动。在一个秋雨飘洒的夜晚,郑敏遥想远方的儿子,写下这样的诗句,“外面秋雨下湿了黑夜 / 你不再听见落叶叩阶 / 雨,天上的,人间的,一样压抑 / 悲痛只能小声低语”。1989年的冬天空前寒冷,而外孙子林轩(小名豆豆)的出生给郑敏夫妇带来了欣喜和天伦之乐。然而紧接着郑敏接到的则是一个又一个噩耗。1989年陈敬容辞世。悲伤不已的郑敏只能通过诗歌来追念这位一生命运多舛的诗友,“秋天的林径是透明的 / 金黄的叶子织成阳光的绸帐 / 你已经走完秋天的林径 / 穿过阳光的惆怅,等在那一头 / 你穿着落叶斑斓的衣裳 // 爱是不会死亡的”。1990年1月20日,九叶诗人之一的唐祈突然去世。闻此消息郑敏难以置信且情难自抑。尤其是唐祈因为医疗事故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郑敏的一系列思考和疑问。接连数日,诗人彻夜难眠。只有诗歌能够表达她此刻的心情,一连气她写成了19首诗。这组诗名为《诗人与死》(最初名为《诗人之死》)的十四行组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这也是郑敏新时期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收获。该组诗既表达了对好友唐祈以及同是右派的莫桂新之死的深沉追念,也是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以及在生命哲学的高度追问生与死的诸多难解的存在命题,“是谁,是谁 / 是谁的有力的手指 / 折断这冬日的水仙 / 让白色的汁液溢出 // 翠绿的,葱白的茎条?/ 是谁,是谁 / 是谁的有力的拳头 / 把这典雅的古瓶砸碎 // 让生命的汁液 / 喷出他的胸膛 / 水仙枯萎”。
郑敏先生清华大学清荷园的寓所里,至今仍摆放着一架白色的钢琴。很多个安静的清晨,她弹奏舒缓的钢琴曲,丈夫童诗白在旁边拉小提琴。我曾经在翻看郑敏先生的相册时目睹了这一充满诗意的美妙场景。而这种美好的日子已经结束了。2005年7月24日7点40分,童诗白因胆总管疾病导致心肺功能衰竭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85岁。两人一起携手走过了54个春秋,耄耋情深非常人能够想象。童诗白辞世给郑敏以极大的打击。她长时间地精神抑郁、神情恍惚。生命最终会凋落的,正如郑敏的诗“玫瑰告别了晚秋的花枝”。童诗白逝世一个月后,也就是8月24日黎明时刻,郑敏在梦中与丈夫相遇。郑敏醒来时更感痛苦,梦中的情景历历在目,然而两人却永远阴阳两隔了。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当年苏轼挽悼亡妻王弗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丈夫的死使郑敏真正觉悟了生死。尽管两个人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相濡以沫,但人生的相聚最终是偶然的,只有分离才是永久的。从梦中醒来的郑敏已经泪水洇湿了枕头。在凄然莫名中郑敏写下“黎明前我忽然被歌声唤醒/ 是你,亲爱的 / 穿过黑暗来寻找我 / 你还没有走远 / 飘过树梢 / 顺着小溪 / 你的手指轻弹我的窗门 // 当两个灵魂相抱时 / 天地为之融化/你回来了,短短的离别……”。
这是一个一生承受了无限寂寞在诗路上朝圣和跋涉的诗人。她的诗歌不仅呈现了叶芝一样的随时间而到来的智慧,而且她的对语言和社会的双重良知,使得她成为中国诗坛不多见的“有机知识分子”。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郑敏文集》。这是对郑敏先生写作和研究的一个总结。然而诗人仍然在路上,继续倾听诗神的神秘之声的召唤。深秋有如初春!这是一朵宁静的时光里寂然开放的花朵。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