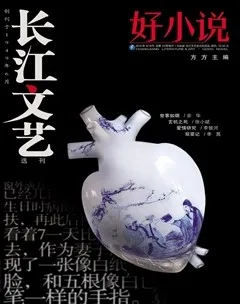诗与神秘
在一切文学类型中,诗似乎最有神秘性。首先,“诗”这个字,《说文》中有“诗者,从言寺声”,有作者引申出:诗歌,寺庙里的语言。“寺庙”二字,透露出诗歌起源的神秘性。事实上,无论说是起源于劳动还是宗教祭祀,在社会学上我们都不能说清诗歌的源头。
而在文学写作的过程上,诗歌的写作也是奥秘。一首好诗是怎样诞生的,恐怕作者也说不清楚。如果能说清楚的话,诗人就可以像ATM一样了,当感觉、想象与经验都有了,就敲敲脑袋上的按钮,笔端立马吐出诗人想要的东西。在写作上,将诗歌弄得最神秘的是象征主义诗人。这方面鼻祖式的人物,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有一首宣言式的作品《应和》:“自然是座庙宇,那里活的柱子/有时说出了模模糊糊的话音/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森林用熟识的目光将他注视//如同悠长的回声遥遥地回合/在一个混沌深邃的统一体中/广大浩漫好像黑夜连着光明——/芳香、颜色和声音在相互应和/……”波德莱尔的意思是:世界在说话,我们要听得懂它的声音。万物都以象征的方式在表现自己,我们要看得懂。为此,作为命名者的诗人要寻求适当的意象来表现世界,这种意象化的努力在英国诗人T.S.艾略特那里就是寻找“客观对应物”(那些与“自然”在“互相应和”的“芳香、颜色和声音”,在这种感觉化的语言中,世界呈现出来)。
象征主义诗人将诗歌写作弄得相当神秘,他们的中国传人李金发就曾经让1920年代的新诗读者十分纠结,他一句“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就够你捉摸半天。而最神秘的,还数法国天才诗人兰波,他将波德莱尔的“诗人是观察者”的说法发展到“诗人应该是通灵者”,他习惯于“那神圣的神经错乱”。他在《语言的炼金术》中说:“我已习惯于天真的幻觉,在有工厂的地方,我很清楚地看见一座清真寺。”兰波渴望的诗人形象是:“在无法言喻的痛苦和折磨下,他要保持全部信念,全部超越于人的力量,他要成为一切人中伟大的病人,伟大的罪人,伟大的被诅咒的人——同时却也是最精深的博学之士——因为他进入了未知的领域。”
兰波作为诗人的感觉和想象极为奇特,让无数写诗者企慕。在当代中国,饱读古典经书和西方现代文学、哲学的诗人海子对大多数现代诗人、哲学家都看不上眼,却对兰波青睐有加,他曾在一张纸上写道:“要和兰波赛一赛……”熟悉海子的人知道海子为什么有这句夙愿,因为他俩都是一般人所认为的某种“天才”诗人,他们在想象力上是绝顶高手。《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的作者燎原和海子生前好友、诗人西川都提到一件事:海子短暂的一生有两次进藏,回程曾在四川逗留。蜀地诗人甚多,高手如云,大家对这个安徽小个子不甚尊重。有一次众人比赛想象力,主题为“天堂”。应该说,这个题目堪称绝妙。在千奇百怪的关于“天堂”的想象中,海子的诗句是:“我看见天堂的黑暗/就是一万年抱在一起……”据西川说,海子后来骄傲地回忆:我把他们全灭了。
我相信海子的出众是因为他进入了类似于兰波所说的“未知的领域”。西川回忆海子生前爱读的书不是当时流行的西方哲学、文艺思潮,虽然这些书他也读,但他更流连于人类古文明的经典,像《圣经》、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婆罗门教的《奥义书》和《摩奴法典》之类。他的文化根基和诗歌想象力与众不同,这也让他耗费一生建构的宏大的诗歌宫殿——七部长诗《太阳·七部书》赏识者寥寥无几。如果说,兰波自诩为一位“通灵者”,海子可能是当代中国诗人中少有的一位进入了宗教领域、亲近“神灵”的写作者。他在东西方宗教之中游走,获取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想象资源,但也付出了代价。海子生前常佩戴上有耶稣的十字架。海子在诗歌中也常常称呼耶稣为“圣之羔羊”。但是,在今天海子的墓碑两边的石墙上,你可以看到一块不小的佛像。我在一次参观海子墓地时,海子的母亲曾对我说,这是海子千里迢迢从西藏不辞劳苦背回来的。当这位苍老的母亲说起此事,有轻轻的叹息:“这小鬼(指海子、也指逝去的人)不该做这事啊……”她在指责海子不该将佛像带回,似乎是此举严重干犯神灵。
事实上,海子的自杀,有人就认为与他练气功走火入魔有关。1989年3月26日,时为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的海子在山海关附近的一段慢车道上卧轨自杀。这个25岁的年轻人短暂的一生创作了200多万字令人惊叹的诗歌、诗剧等作品,死的时候随身携带着四部书,其中一部是《新旧约全书》。从他的结局看,他并没有进入上帝之城,与其说他自杀,不同说是被撒旦强行掳走的。24年过去了,海子的死因到底是什么无人能知,但海子诗歌的影响,却在日益深远。作为诗人的海子,他的“生”(作品的成就),他的死,也许,也在于他的生命进入了某种神秘的领域。
海子的死不能不让人想起当代另一位优秀诗人骆一禾。1979年,比海子大三岁的骆一禾进入北大中文系(海子是法律系),1984年获学士学位,毕业分配到北京出版社《十月》文学编辑部任编辑,后主持《十月之诗》栏目。他1989年5月31日因脑血管突发大面积出血去世,年仅28岁。骆一禾生前留下近两万行诗作(其中包括长诗《世界的血》、《大海》等)及数万字的诗论、小说。骆一禾在写作上其实和海子一样,有天才之禀赋和广博的文化视野、出众的想象力。海子死后,骆一禾付出了大量的劳力整理海子长诗,以至于在七十天之后,他也与世长辞。“当一个扼断了自己的歌喉,另一个也已经不能倾听”,当代中国这绝无仅有的两位诗人,如此紧密地生命相连,他们的生涯也成为中国文坛少有的美丽而哀伤的神话。
天才短命,天才诗人的一生,常常如彗星陨落。天才、诗歌与死亡,之间有什么神秘的联系?西川在《生命的故事》一文中记述了他生命中四位杰出的诗友在1989至1992年间的相继离去,在海子和骆一禾之后,是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诗人戈麦。戈麦于1991年9月24日自沉于北京西郊的万泉河。戈麦死后,他的朋友们出版他的遗稿,诗集即名为“彗星”,书的末页说到戈麦所创造的世界,“是对所有以往诗歌的一个有力的挑战。他的设想和雄心使他预先进入了天国的瑰丽之境”。事实上,海子、骆一禾和戈麦,都是彗星式的诗人,像人们说戈麦的那样,他们“天才的想象力”对世界是“强暴”式的爆发与照亮。“海子只生活了25年,他的文学创作大概只持续了7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像一颗年轻的星宿,争分夺秒地燃烧,然后突然爆炸。”他们的死是因为爆发而耗尽了自己吗?还是他们的诗歌写作方式使他们进入了一种领域,其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他们吸引至死亡?海子自己在长诗《土地》中写道:“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这仿佛是他对自己将死的预言及死后的安慰。
当代诗坛,因向“神秘”致敬、直接由“神秘”诞生的经典之作,是西川1987年前后完成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听凭那神秘的力量/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像今夜,在哈尔盖/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地方,在这青藏高原上的/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马群忘记了飞翔/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我成为某个人,某间/点着油灯的陋室/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这首诗也许透露了好诗产生的一个奥秘:对存在、永恒、生命满怀敬畏,谦卑地沉浸其中,敬虔领受。
责任编辑 申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