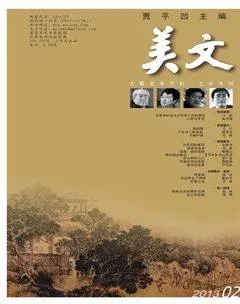在山野的日月

在山野睡觉
我在野外队时,多数情况下,晚上,我睡觉香甜。虽然在活动板房那窄小的钢丝床上,夏天暑热,蚊虫成群叮咬,我照睡我的;冬天鼓荡大风,我冰冻的身子,也能在梦乡里取暖——只是早上起来,鞋子穿不到脚上,脸盆也不听话了,端不起来,都给冻住了,冻住到地板上了。
那阵子,我人年轻,瞌睡也多,说睡就能睡着。要是在井场劳累一天,刚钻进被窝,就失去意识了,似乎到另一个不受苦的世界去了。我得承认,也不是每次都说睡就睡,睡不着也是经常的。通常是快过年了,我想家,我就睡不着了。还有就是野外队上谁的媳妇来探亲了,我也会失眠好长时间。我都二十出头了,还没有谈过对象呢。
在野外队,出去,满眼睛荒凉,见到个人都困难,得受着。上班,搬铁疙瘩,一身土,一身油,也得受着。吃饭,清汤寡水,还吃不饱,还是得受着。想起来,只有睡觉最安慰人了。睡着了,啥都被隔离在了梦境外边,如果做个好梦,醒来,我也当真的一样,要高兴一阵子呢。
所以,我不应该失眠,可是为想家失眠,为女人失眠,我管不住自己。失眠就失眠吧,我不会整夜都失眠的,难受一阵子,瞌睡浓烈起来,我还是可以睡得深沉。
我最难忘的,是在山里的井场上睡觉。
野外队上班,三班倒,上夜班是经常的。一个班,如果一直站在井口,一直劳动,后半夜,浑身乏困。有时,我竟然一边机械地操作着,一边就睡着了,竟然能两不误!这很是让我自己吃惊,而我真的做到了。我缠旋绳,拆装吊卡,摆动油管,这些动作,我都在完成,同时呢,我的脑子,空空的,我睡过去了。这是多么神奇的能力,我能在睡眠中,实现对身体的控制和把握。不过,这样的睡,是片断的,不连续的,就是,感到似乎睡着了,却随时又能醒来,就这么反复着,错乱着。反正,肯定睡了,我能体验到睡眠给我的身体带来的那种充实,虽然短暂,但我获得了这样的充实。这样睡眠,是极其危险的,回想起来,我要庆幸,我竟然没有发生一次伤胳膊伤腿的意外。
有的夜班,工作量提前完成了,就停下了。不能早早回到野外队的营地去,要等到下班,值班车才来。于是,探照灯照射出来的一个个笨拙的身影,移动着,朝着不同的方向,寻找可以安顿身子的角落。井场上分布着油污和水渍,不能睡。山洼里可以睡,半山坡的塄坎下头可以睡,找到一棵树,树下面可以睡。起先,我胆子小,不敢走远,我在探照灯下面睡过,蚊虫如雨,得不停摆手,睡安稳是不可能的。慢慢的,我不害怕了,也走远,走到僻背处睡。这些地方,热天还可以,晴天还可以。这些地方,睡下去,身子和泥土,和青草接触,被山风吹着,看天上繁茂的星星,听虫子激烈的鸣叫,渐渐闭上眼睛,人进入虚拟状态,在我来说,也是一种享受。
井场是不断变换的,再变换,都在山里,不是山顶,就是山沟,睡觉的选择,也跟着变换。有一段,井场跟前,有一个半人高的土窑,不知做什么用途的,人能进去,不能坐,只能睡下,我也睡过。睡在里面,我没有担心土窑坍塌,却产生了被埋葬的感觉。这个土窑,一起找地方睡的,都愿意睡在这里,谁占上了,就归谁。有的井场,施工周期长,便派人看护,便拉来一间值班房。这样,在冬天,一个班的人,睡一地,都睡在值班房的地上。地面小,交织着,人挤人,而且,都往火炉子跟前靠,都想多乘点暖和。一次,我的棉工衣让火引着了,烟起来,把我没呛醒,把别人呛醒了,浇了一缸子水才浇灭。
天冷了,或者遇上阴雨天,外面就不能睡了。又没有值班房,瞌睡在身子里起伏,却发愁没有地方躺下。不过,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我有办法。井场上,有一间工具房,有一间库房,都是铁的,顶子,四边,底下,都是铁。我在这两间铁房子里,都睡过。工具房里一张桌子,也是铁的,而且,还是铁板的桌面。一次,我就在这张铁桌子上睡了一觉,时间很短,反正我睡着了,而且,竟然遗精了。我没有做梦,即使做梦了,也没有梦见电影明星,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生理反应呢,我挺奇怪的。在铁桌子上睡觉,是要下决心的。刚挨上铁桌子,是巨大的冰凉,针一般的冰凉,穿透我的棉工衣,刺激着我的皮肤,骨头,甚至血液。我挪动着,强制着,来适应铁桌子的冰凉,终于,我睡着了,在冷库睡觉一样,终于,我睡着了。可是,很快的,我又醒来了。铁桌子生发着不断的冰冷,我暖和不了铁桌子。我有限的热量,无法抵抗铁桌子的坚决的冰冷。看来,铁桌子是不适合睡觉的。库房不像工具房,地板是一层铁板,库房的下面,铺着一根一根钢管,只是,钢管和钢管之间,有一人宽的间隙,横着睡,竖着睡,都不得劲。我把一卷散开的棕绳放到两根钢管中间,棕绳有锅盖那么大,中空,身子蜷起来,睡进去,刚好盛下。在棕绳上睡,虽然有悬空的感觉,但是,我一下子踏实了,很快,我就迷糊起来,自己把自己抱得紧紧的,身子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总体来看,还是很舒服的。
我最佩服自己的,就数在通井机上睡觉了。冬天,通井机是不能熄火的,不然,水箱油箱就冻住了。通井机像拖拉机,又像坦克,操作室躺进去一个人,还是富余的。可是,活塞在运动中,发出的声音,平时,在山背后听,都觉得刺耳,更别说在跟前了,更别说在操作室里了,更别说躺在里面了。我竟然如此顽强,我就躺在里面,打算睡觉。刚躺下,那剧烈的声音,全往耳朵里钻,不光耳朵,还往身上的毛孔里钻,往身上有缝隙的地方钻,我硬忍住,忍不住也忍,似乎我要验证自己抵抗噪音的能力似的。除了噪音,身子下的铁板,还在振颤、抖动,这样,我的身子就放不平稳,就随着铁板一起振颤和抖动, 这我同样忍着,同样忍不住也忍。最难受的是,通井机的噪音和振颤和抖动,传导进耳朵,我老是觉得痒,我得不时用指头捅几下。鼻孔也痒,头皮也痒,浑身都痒。这些,都是在躺下的初期,才感受明确,躺久了,就习惯了,就觉不来了。似乎没有噪音,似乎没有振颤和抖动。必须提到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由于通井机在发功,操作室里是温暖的,身子下面的铁板,也烫烫的,热炕一样。咋说也比外面强,外面,是零下十多度,外面待不住,就是给我长一身羊皮,也待不住。
回到野外队,天大亮了。按说,我应该美美睡一觉,可是,人就这么贱,现成的床,绵软的被窝,我的瞌睡也没有睡光,我却不愿意睡了。土路上走,走半个钟头,到镇子上逛去。不打算买啥,就是看人。镇子上,也没有多少人,但总归能看到人,有走路的,有和我一样逛的。镇子上唯一的商店,我一定会进去,有个营业员,女的,长辫子,红脸蛋,看一眼,我都感到愉快。经常的,我有意无意在她面前逗留,有时不好意思了,我就买一盒牙膏,不过,这样就可以和她说上几句话。
路上的信
过去,互相不在跟前,又没有手机、电脑,而固定电话也少,还要专门到邮局去打,于是,人们传递信息,安顿事情,主要靠写信。我到了野外队,大山深处,山塬起伏,如食肉动物的身体,却也是禁锢的,被压抑的,我也和世界隔绝了,被遗弃了,虽然天地是如此阔大,虽然四季是如此鲜明。在这一时期,我给家里写了许多信,搬动铁疙瘩的间隙,激荡而粗糙的劳动之余,要说什么能让我舒缓下来,就是写信了。
是的,是写信。在纸上落下一个个文字,我的酸楚和温暖,一起涌来,似乎在提示我,一身油污的我,在井架下挥洒汗水的我,并不是野蛮人。石油是重工业,入侵了农耕的山野,我还没有完全成为机械的一部分,在和大地的冲突中,内心的柔软,还保持了弹性,在符号化的外表之下,作为一个人的欲念,还没有消失,还存活着,残喘着。
野外队的人,文化程度低,也要写信,哪怕一张纸上,就写了几个字,就说这个月给家里的钱寄出去了,就问老人身子好着吗,也是一个个重要的叮咛和问候。野外队的人,成家了的,没有成家的,都是单身,为一碗饭,在山里挣扎,拿命挣扎。家乡都在远方,在农村,一年到头,只有一次探亲假,牵挂多,担忧多,写信是必需的。随便一个老工人的枕头下,都会压着几封家乡的来信。有的怕别人看,还把信锁到箱子里。
我出门早,十七岁就离开父母,到了矿区,到了陌生的天空下。在家里时,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失败,我沉闷,烦躁,盼着摆脱家庭,走出去,去远远的地方,一个人独立生活,证明自己还不是废物,还有些用途。可当我真的离开家乡,对父母的思念,却日益强烈。尤其是在野外队,生活单调,要我贡献的,就是我的力气,越是这样,越感到家里的好,给家里写信,也频繁起来。而信的内容,却从未提到艰苦,提到山里的荒凉。我在信里说,我顿顿都能吃上肉菜,实际上我经常啃干馒头;我在信里说,我每天都能洗澡,实际上我就是拿脸盆打来水,在睡觉前擦擦身;我在信里说,野外队发下来的工服,穿不完,实际上,一年一身单的,一身棉的,早就被油污浸透了,磨破了。我希望让父母知道,我是有出息的,我不但长大了,而且是成功的。可是,父母不可抗拒地老了,病也多了起来,我却难得回去,到不了跟前,我只能一封封写信,给父母精神上的问候,也要求弟妹好好念书,听话,不要惹父母生气。
我的父母都不识字,收到信,叫弟妹念给听。又把给我说的话,叫弟妹记下来,也是叮咛了又叮咛:穿暖和,吃饱。别和野外队的领导顶嘴,别和人打架。家里都好,不用操心。说的不外就这些。我探亲回去,在家里的抽屉里,翻出了我写的信,都保存着。妹妹说,有信来,父母高兴,听一遍不够,有时,要念几遍。平日里,也常提着我的小名问,有信来吗?听见外头邮递员的自行车的铃铛声,也赶紧安顿出去看看,是不是有信来了。我在家里,读自己写的信,情绪再一次波动,产生恍然的错觉。远方和家乡这两个阻隔的时空,似乎重合了,似乎保存了些值得珍惜的抽象的物质,却又以书信的形式具体地呈现了出来。
一封信寄出去,一条看不见的路,有起点,有目的地,是能够确认的。可是,一封信要抵达信皮上的地址,却费尽周折。在路上走,快也得一礼拜,慢,则超过十天。即使这样,我也对邮局充满感情。野外队每搬迁到一个地方,我都要打听最近的乡镇在哪里,邮局在什么方位。经常的,走路走一个钟头,才走到镇上,找见邮局是容易的,街上就几间老式的砖房,一定有一间是邮局。里头窄小,站不下几个人。我加入进来了,感觉自己和外面的联系,和家乡的联系,没有中断。感觉这里的空间,很大,装进来的东西很多,送出去的东西也很多。我去邮局的次数多,发出一封信,过些天,又来,又发出一封信。看着我写的信,躺在一堆信中间,那么安静,可我知道,到了时间,我的信会被装进邮包,会走路,一路代替我回家。有时,野外队的营地在深山里,离镇子太远,写好了信,只能找人捎出去发。顺利了,会有外出的人,也有十几天把信压在手里的状况发生,这让我无奈又焦虑。
野外队经常搬迁,安营扎寨的地点,多僻背,收信也是很困难的。邮局的人,不送信过来。如果能确定在一个地方留居的时间长,可以安顿家里,来信写这个地方。隔上些日子,自己去邮局,窗台上一堆信,在里面找,就真找到了自己的一封。我在野外队时,多数情况下,都让家里把信寄到矿区机关,这样寄来的信,是不会落空的,但也有不足,只有野外队有人去,才能把信拿回来。十天八天拿回来是经常,一个月拿回来一次也有过。我去过矿区机关,那里有一个收发室,里头有一个柜子,组装成一个一个格子,每一个格子上都贴着纸条,写着不同的野外队的番号,里头填塞进去了报纸,信件。有的空了,是被拿走了,有的满满的,都没有空间了,说明这个野外队长时间没有来人取。我只要去矿区,一定要去收发室看看,看着我的信,拿着别人的信,都觉得高兴。有时,野外队离矿区机关也遥远,要几百里远,比发信的地点都远,一封信来到我的手里,也得费尽周折。
野外队生活寂寞,成天面对荒凉的大山,看见一个人都不容易,写信,也是一种排遣寂寞的方式。写信能安定内心,也缓解了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收到家里来信,夜深了,还来回读着,也是幸福的。家里的来信,都是弟妹的笔迹,却是父母的口气,说的是琐碎的家常,对我都是重要的,对我都是安慰。想到以前父母对我指望大,我也有雄心,却落了个在野外队受苦,我心里也不好受,是对不住父母的不好受,是对不住自己的不好受。那些年,一封又一封信,强化了我对家里对父母的情感,也让我没有沉沦,没有丧失面对艰难的勇气。野外队不是人待的,常常有人这么说。可是,我坚持下来了,我在坚持中迎来了离开野外队的机会。当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我能想象出父母知道后的宽慰,也能听见父母发出的轻轻的叹息声。
喝酒,难得喝出香来
早先,我喝酒没量。平日想不起喝酒,也轻易不碰酒。野外队日子难熬,下的苦大,出死力气,回到营地,喝些酒,按说是正常的,染上酒瘾,也是正常的,可是,这都不绝对,我在野外队六个年头,虽然有过几次喝酒的经历,和酒的关系却并不密切。
我第一次喝酒,不在野外队,在家里。我妈说过一句话,说喝酒图个香。我信,也认为这是一个境界。我呢,就达到过一次,就这么一次。
那时,我还小,在上学,平日爱疯跑,错过饭点,回去只能吃剩饭。不是黑面蒸馍,就是黄面饼子,或者就是糊糊面。锅里热着,拿出来,就着咸菜吃,就是一顿饭。一次我回去,发现蒸馍是白面的,还给我留了一盘白菜炒粉条。这样的饭菜,一年吃不了几次,我心里高兴,而大人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吃了几口,觉着应该再享受一些,就偷偷从桌子旁的架板上,取下一个暗红色的瓶子,还取了一个小酒盅。瓶子原来是装咳嗽糖浆的,现在里头是一毛钱一两的散酒。我爸带我给我爷上坟,就拿这个瓶子,烧了烧纸,把大部分酒泼倒烧纸的灰烬上,祭奠的仪式才能结束。酒瓶子拿回来,放到架板上,平日里,没有人动,我爸不喝酒,一家人,都不喝酒。假如平日里动酒瓶子,一定是谁扭伤了腿脚,得倒些酒在碗里,点纸引着,拿手快速蘸,从蓝色的火焰里带出滚烫的酒来,在受伤的部位上来回抹,能活血化淤。那天,我有冒险的刺激,也有尝试新事物的害怕,我吃几口菜,抿一口酒,酒是辣的,可是,酒更是香的,那天,我就喝了一杯酒,却真正喝出了酒的香。这以后,我喝酒,各种场合,各种酒,再也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野外队喝酒,逢年过节才喝。这样的日子,通常要组织会餐,以班为单位,从炊事班端回来四凉四热八个菜,还领回来两瓶子酒,六七个人,围坐一起,吃喝得高兴。这样的场合,我会喝两三杯。这是我那些年喝酒的极限,过了这个数字,我就得睡到床上去了。在野外队,吃饭只能图吃饱,随心意吃,办不到,会餐时桌子上丰盛,我的注意力不在酒上。会餐一次,每个班,总会醉倒几个,也有喝多了满院子串的,也有话多而且大声的。我在野外队也喝醉过,只有一回。那是一年春节,我请假不准,不能回家过年,我情绪波动,内心烦乱。大山里,除了山还是山,腊月天,满目萧条,看不到生机。大年三十那晚,留下的十多人,一起在队部吃饭,我喝醉了,吐了。我有意这样的,这样,我就不想家了,不难受了。第二天一早,我又爬到大卡车的车槽子里,一路颠簸,去山背后劳动。回想起来,我在野外队,就醉过这一回。
我那阵子,人生没有定型,前途却看不出来。夏天夜短,难熬,冬天夜长,更难熬。繁重的体力活,天天重复,压歪了我的肩膀,我应该消沉,应该自我放弃,才显得合情理,我却没有。我在不正常的环境里,过的是正常人的日子。我庆幸我没有变成傻子,没有发疯,我感谢我自己心态。也不是天天忧愁,感叹,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其中也是有舒心,有快乐的。照通常状况,无聊了,心慌心乱了,喝酒麻醉自己,也是无奈而有效的选择,我却没有,我就没有这样想过。后来,我练出了发呆的本领,不上班,或者下了夜班,没有瞌睡,我一个人,在单人床上坐着,能坐一上午,能坐一下午。晚上,不到睡觉时间,我靠在被窝上,眼睛看一个地方,也能姿势不变,看到想睡觉了,才睡觉。
只要有人群,就有各种人,自然也会有能喝酒的,喜欢喝酒的。和我一个野外队的工人里,有两三个,会在悠闲时,买一瓶酒,叫几个人一起喝。没有菜,也没有条件弄菜,几乎都是干喝。连酒杯子也没有,拿酒瓶盖盖,倒上酒,倒换着喝。或者,酒瓶子传递着,你一口他一口喝。年轻的,负担轻,会善待自己,会顺便买回来沙丁鱼罐头,桔子罐头,来当下酒菜,这就够排场了,和如今下馆子一样了。这就既有了喝酒的意思,也有了改善生活的意思。这样的情景,在野外队,也是不常见的。那时,挣钱少,用途大,轻易不敢有额外的开销。所以,后来遇见外面的人,说,你们野外队的人,喝酒厉害,一个人能放倒一桌子人,我不承认。我就说我就是野外队的人,酒不怕我,我怕酒。在野外队那些年,的确的,我没喝多少酒。那时,难得进城,去一次,吃了饭再回。在饭馆里,看到有的人在招呼人,坐一圈人,中间只有一个菜,盘子早空了,不加菜,只是一下下端酒杯子。我就奇怪,多要些菜,多吃些菜,才是享受,菜钱再贵,总没有酒钱贵。我要上一个菜,要上一盘炒面,吃着过瘾。我一口酒都不会喝的,头晕的感觉,跟重感冒差不多,跟中暑差不多,我不找罪受。
我前头说的酒,都是白酒。在陇东,人们把白酒叫辣酒。辣对人的刺激,是剧烈的,迅速的。辣酒就是这样。我在野外队,没买过白酒,只买过红酒。也是招呼人,我才买红酒,买罐头。野外队的食堂,我不赞美,到现在也是。开饭了,供应的,只有两种菜,一种是肉菜,肉菜找出来肉困难,一种是素菜,没有油水,白菜的话一定团成了一团。这要放现在,我吃不下去,可是,我那时十八九岁,能吃,而且还吃得欢喜,吃不够。碗递进去,还眼巴巴地,希望给多打些进去。来了人,就不能让吃食堂的饭了,何况,一年里,来人也就一次两次,都是老乡或者同学,我要热情。那是商品短缺的年代,我也只能再买一瓶杏子罐头,加上桔子罐头,沙丁鱼罐头,就三瓶罐头。馒头得在食堂买。所谓红酒,可不是干红,进入九十年代后,我才知道有干红这种酒。我说的红酒,实际上是葡萄汁,也含了一点酒精,是甜的,是便宜的。当然和白酒比,价高一些。红酒在嘴里,在肚子里,都平和。任谁喝上些,都能接受。我这样招呼人,都知道,这在野外队,是最高规格了。
那时,在野外队,我没见过,也没喝过啤酒。山里头,还没有啤酒卖。后来随野外队搬迁去毛乌素沙漠施工,路过银川,在街上看别人喝,图新鲜,我喝过一回,只喝了一口,就不愿再喝了。我竟然还怀疑,我喝的啤酒,是不是放坏了,变质了。
我还喝过黄酒,是在华池的元城乡林场的一户人家喝的。那一次,我彻底喝醉了,在人家炕上,睡到半夜才醒来,被架子车拉着送回野外队的营地。野外队经常搬迁,有时就离村镇近,不上班了,可以去转悠。不过,我性格内向,和当地人不打交道。一天,我去邮局发信,说起林场也有和我一个姓的,就认识了,约我去家里坐坐。我这个姓少,在外面遇见了,觉得亲切,我赶紧答应了。去时,还提了两包点心。对方也客气,还准备了一桌子饭菜,还端上来了黄酒。这黄酒,是当地人用黄米自酿的。每家都有一口大缸,装满黄酒,平时偶尔喝,过年天天喝。须加热喝,味酸,喝不惯的,加红糖喝,喝惯了的,就要这个酸劲。这酒后劲大,我并不知道。黄酒是盛在碗里喝的,看去跟中药一样。主人五十来岁,儿子年龄和我相仿,不停和我碰碗,我也不时表示感谢。一口一口喝着,开头,没有明显感觉,只是出汗多,身子热,还夸赞黄酒地道。喝光一碗,我有反应了,言语间还在抱歉,就软了下去,啥都不知道了。这次喝黄酒,我教训深刻,提醒自己以后要注意。过些天,在集市上遇见一家子,还关心地问我,我有些不好意思。
有一年,我所在的野外队搬迁到了一个叫太阳坡的山头上,营地离子午岭近,意外而欣喜的是,旁边还有一个采油站,上班的有姑娘。在野外队,见个姑娘,可是不容易的,有事没事,眼睛老往采油站瞅。姑娘们不认生,常结伴来营地要水喝,一来二去,我认识了两个。熟悉了,心里怀着企图,一次便邀请吃饭,竟然答应了。也是吃罐头,喝红酒,其中一个,或者无论哪个,只要愿意,我都想深入交往。我没有勇气,暗示的话也说不出来,吃毕,姑娘走了。没几天,野外队再次搬迁,我白白丧失了机会。不过,两个姑娘在我的野营房里,坐我床上,和我一起吃了一次饭,很是让我愉快,相伴的,也是我这以后经常失神失眠的一个原因。
后来,安定下来了,生活周正了,倒端起酒杯子了。我真正开始喝酒,是工作变动,到了矿区的后勤之后。上班固定,下班也固定,交往扩大,熟人增多,聚会频繁起来。起先,我喝几杯就醉,后来,喝十几杯也不醉,再后来,我一次能喝二两。几乎每个月,都要喝上几次酒。最集中的,是在1995年前后,我认识的一个,在马岭川,一周来庆阳三次,都是下午来。来了,我两个,到桥头一家清汤羊肉馆,要两个菜,一瓶九块钱的彭阳春酒,就要喝光才罢休。两个大玻璃杯,一人一半均分,我性子急,三五口喝光,然后便埋头吃清汤羊肉,吃了回家就睡。这样持续了一年,把酒量练下了。
人说饱暖思淫欲,同样的,饱暖也会思饮酒。随着收入增加,生活改善,人们喝酒,也显示日子过得顺心。我呢,隔三差五,总得喝一场酒,觉得没有亏待自己。虽然喝多了难受,喝多了后悔,可是,要是许多天没有参加酒局,倒会觉得失落,人不叫我,我就叫人。喝酒成了生活里的一项离不开的内容。我不知道别人喝酒,能喝出什么品味,我喝酒,已经把脂肪肝喝出来了。现在,我在控制喝酒,也常常逃避喝酒。几个经常在一起的朋友,一边关心我的身体,一边都对我有意见了。
我离开野外队后喝酒的故事,这里只简单说几句,就不再展开了,以后我找机会另说。
我在野外队,都能做到不喝酒,少喝酒,现在,我也得有这个毅力。喝酒把多少时间都浪费了,通过喝酒和人亲近关系,也是临时的,短暂的。要是怀念酒的好,我忘不了小时候在家里的那一次喝酒,虽然只喝了一杯,那个香,还真切的存在于我的记忆里。那一次喝酒,就是为了喝酒,那一次喝酒,我的味蕾苏醒了,为酒绽放了一回。
等车的苦乐
那些年,道路简易,汽车也少,路上走一天,能遇见马车,毛驴车,难得遇见汽车。在陇东的深山里,进去一辆汽车,不要说狗咬不断,听见声音,大人出来看,娃娃后面追,车轮子卷起来的土尘上了脸面,也觉得新鲜。
我在野外队时,出去,为找车愁,回,又为等车愁。等车最愁,没指望地愁着,却又不灰心不死心地等着。
如果营地离村镇近,来回困不住。可是,石油偏偏就生在僻背处,没有人烟处,营地也就天高地远。在大山里,孤岛一般,要和外面发生一次联系,非常艰难。最长的一次,我半年没有出去,身上都生霉斑了。
那阵子,我也就二十出头,苦累能受,心慌难熬。成天见到的,都是一个野外队的几十个男人,一个女人也见不上,工闲下来,总想到镇子上转转,到县城走走。去了,总归看见了活动的鲜艳的女人,看一看,眼睛点了眼药一样,眼睛是难受的也是舒服的。虽然回到野外队上,也有更大的失落,但这样的失落,起码是吃不上肉却闻见了肉香的失落。可是,单人床上睡一天,把头睡肿都可以,要出去一趟,却常常不能如愿。
由于营地和工地之间的距离远,野外队雇了一辆大卡车,叫配属车,主要运送上下班人员。也会出去,拉上队长,到矿区机关开会,拉上成本员,到矿区机关算账。这样的时候,我一定会翻身跳进车槽子里,跟着出去。和我一样的,都攀着车帮,满脸尽是欢喜。通常,大卡车经过县城时,放下我们,说上一个时间,返回时,再来拉上。这样,我就可以在县城逗留近一个白天。我不能说自己是为了看街上的女人才来到县城的,对着季节了,我也买桃吃,我还到县城北边的新华书店,买过一本介绍计划生育的书,那里头的一些话,那里头的一些插图,曾让我稀奇又遐想不已。
班车是有的,却只在县城有车站。有时,忍不住了,有急事情了,离开野外队,脚走着走半晌,走到路边,估摸时间,等班车,也是能等上的。这叫过路车,停不停,随司机的愿意。我出钱,又不要票,司机是愿意的。这样坐班车,错过了时间段,就走不成了。脚走着原走回去。在五蛟时,在打扮梁时,我就这么坐车。过路的班车,一来一往,就这么一趟。在城壕时,福气大,我出去,有车坐,要回来,也有车坐。坐的不是班车,是油罐车。原来,城壕也偏远,也没有车,后来,新油区投产了,却还没有连上输送石油的管线,油井里出来的石油,就得用车拉。将近一年时间里,城壕的路上,来回跑的,全是拉油的罐车。罐车是东风牌的,灰白色,四吨装,是新的。开罐车的,全是年轻人,从驾校才出来,胆子却大,脚踩着油门不知道松开。城壕的路是土路,还坑坑洼洼,还经常有大石头在路中间,也没有影响车速。辗死鸡,压死狗,那是经常的。脑子正常的不正常的人,看见油罐车,都躲得远远的。还别说,伤人死人的事故,真没有发生过。有过一次意外,那是一辆油罐车在行进中,引擎盖突然松开,挡在了挡风玻璃前,司机反应不及,把路边一棵洋槐树撞断了。还有一次,却是爆胎,油罐车一头扎进了河坝里,车头缩进去了一截子。万幸的是,这两次,都没有出人命,司机只受了点轻伤。
我最恨这些司机了,要说原因,不是开车,不是。也不是他们戴墨镜,留长发,不是。我恨他们,是因为,山里头的姑娘,长得好看的,甚至,长得一般的,全被他们勾引跑了。或者干脆就主动投入了他们的怀抱。这些姑娘,有矿区的,也有当地农家的。本来就少,对野外队的,看不上眼,可坐在油罐车的驾驶楼里,就像坐进了花轿里,而且还被颠簸着,心思早乱了。我要是开油罐车,我也有这样的福气,我要是姑娘,我也这样选择。谁不愿意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谁不愿意在车上风光呀。那些年,坐汽车,可是很稀罕的。
野外队的,要坐油罐车,除非和司机是朋友,不然,挡车车不停,白吃一嘴土。可是,司机的头脑是灵活的,野外队的也愿意付出,这样一来,可以另说了。于是,交上两块钱,就能坐进驾驶楼了。这是司机的外快,司机的油水,一月下来的收入,比工资还高。我交了钱,一路和司机寒暄。也跟别人学,拿出纸烟,一次叼两根,点着了,自己嘴上留一根,另一根,递给司机。那时,都这样给正开车的司机敬烟。还有一些农民,没有钱,拿鸡蛋顶,拿苹果顶,也是可以的。那一年,油罐车成了山里人的主要交通工具。到现在,都几十年了,我听说,这一路还没有通班车。不过,倒是有了私人中巴跑运输。道路也改善了,不是土路了,铺了油路了。
回老家探亲,到矿区机关参加学习班,出去,周转几回,上车下车,才到地方。回野外队,也一样,甚至更不容易。有时,还得打听清楚,也许离开时营地在山脚下,这些天不在,却搬到另一座山的山背后去了,不掌握情况,就可能把单位丢失了,又得费周折重新寻找。
野外队在元城时,出去了要回去,最耽误时间,最遭罪。如果在冬天,又刮着风,那简直跟死了一回一样,而且是有知觉的死,是半死不活的死。
通常的,从庆阳到悦乐,有车坐,再步行,到五里地外的一个岔路口,就在这里等车。这个岔路口,地势高,一边是土崖,三面敞开,土崖下是一条土路,扭曲着延伸进了元城方向的沟里,土崖对面,要远一些,是柔远河的河道。这个岔路口,容易生风,人站在路口,衣服就舞动起来,挣脱着,要离开人的身体。在这里,一整天,都有三两个人在等车。有时,天快黑了,也有人在等车。我也多次加入到等车人中间,有时,还会相互说些话,通报一些各自知道的信息,自然是啥时候有车来,会不会有车来。
在这里等车,是盲目的,能不能等上车,也是不确定的。到元城的班车,上午有一班,下午有一班,都是过路车。班车经过这里的时间,上午应该在十点左右,下午应该在四点左右。在这个时间段,运气好,等上了,让人欢喜不已。可是,多数情况下,班车不见来,比预期的时间过去了三四个钟头也不见来,等车人的神情,便不仅仅是焦急了,甚至,不仅仅是痛苦了。想发火,没地方发,想骂人,又不知道骂谁。实在等不来车,只好原路走回到悦乐去,在那里找个车马店住下,第二天再来等。
交九天,又下过一场雪,等车,对身心都是煎熬。耳朵冷,头皮麻,都不算啥;手生疼生疼的,搓一搓,哈哈气,也能缓解;脚受冻,最难忍受。我是野外队的,脚上穿的是发下的大头翻毛皮鞋,冷气照样可以穿透。开始,只是觉得冰凉,从脚尖开始冰凉,从脚心开始冰凉,再把这冰凉,弥漫到脚踝和脚背时,冰凉加重了。加重了的冰凉,生出了刺,生出了针,不仅仅冰凉脚的表层,而是往深处扎,往血管里扎,往骨髓里扎。这样持续着,脚变得麻木了,脚结冰了一样。脚也变重了,说是石头的脚,生铁的脚也成立。分明又是自己的脚,是自己身体的组成部分。脚刚开始感到冰凉时,还可以用力跺脚,通过和地面撞击,产生一些热量。等到脚麻木了,脚不听指挥了,笨拙了,调动意志再用力跺脚是可以的,但随即袭来的疼痛,似乎要骨折,似乎要粉碎,似乎要失去脚,失去脚的支撑,是万万不可以的。但静止不动,脚上的冰凉,脚上的麻木,会传染一样,又要往上走,往腿关节走,往胯骨走,便只好缓慢地、轻微地踩着小步,一点一点移动,一点一点把沉睡在冰凉和麻木里的脚唤醒。
在土崖的崖根下,散布着一团一团的乌黑,那是冬天等车的人,点柴禾取暖留下的残迹。有一堆火,人围着,不至于冻僵冻硬。可是,山里光秃秃的,能生火的材料,无非是蒿草、树上掉下来的枯枝、地里挖来的玉米根。这些,被之前的人消耗得几乎没有了。要找,就得再往远走,连被风吹来的烂纸片,谁扔掉的橡胶鞋,也拿来点着。只要是能燃烧的,都点着,哪怕是河滩里发大水时冲下来的棺材板,也点着。有一团火光,有呛人的黑烟飘散,等车的人,会从心理上缩短时间的漫长,也认命般觉得等车就得这样等。这时候,假如看见班车过来,等车的人,本来还想着把火堆挑拨旺,立刻丢手,换个人似的窜起来,不断招手,站路中间招手,似乎过来的不是班车,是诺亚方舟。和我在城壕遇到的一样,也会有矿区的车辆到元城,只是没那么多,偶尔会有一辆车过来,有车槽加长的日野牌卡车,有给油井压裂的压裂车,有背着铁架子拉油管的解放牌卡车。只要是车,等车的人都赶紧招手。有的车看着减速了,到了人跟前,却轰一下油门,快速开过去了。等车的人是有办法的,招手时,手里拿一张钱,使劲抖动,让司机看见。有的车真就停下了,等车的人疯了一般攀爬上去。压裂车的车身,都是些铁管铁箱,人找个缝隙,抓牢,哪怕身子斜着,一条腿悬空,也不在乎,也不害怕。这些车的司机,有的心善,给钱不要,白拉,有的要钱,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好人。
1986年,我终于调出野外队了,谢天谢地,我不用再搬铁疙瘩了,也不用在野地里等车了。我在野外队的最后一年,是在元城度过的。那一天,接收我的单位,派了一辆大卡车,来到元城,来拉我,拉我的行李。我所有的家当,就是一口木箱子,是我参加工作时,我爸给我做的。里头最值钱的物品,是我积攒下来的十几本书。那一天,春光美好,我身心美好。在路上,只要遇见等车的人,只要顺路,我都让司机拉上。一路上,上人,下人,都高高兴兴的。快到庆阳了,车槽子里,还有十几个人,他们的终点是庆阳。他们的神情,和我一样喜悦。应该是,我比他们,更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