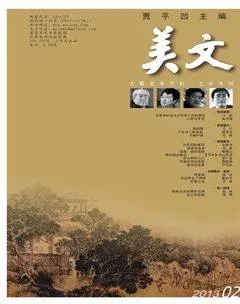拥有历史图景的视界

初闻范老,与自己阅读沈从文的体验有关。当时隐约知道他是国画大师,不过对他的生平事迹未做进一步的考究。如今,范老古稀之年仍热情地出现在公众面前,或以国画、书法与诗词之美好,或以艺术、人生与爱国之觉悟,或以古典、自然与儒学之对话,谆谆告诫于我们。更难能可贵的是,范老还通过画展、文化演讲以及画作等途径,担任起了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使者。为此,范老不但先后得到法国领导人萨科齐、奥朗德等的高度赞赏,还和戴高乐将军的爱子菲利普·戴高乐有过书信往来。早在2011年12月7日的《新华副刊》上,我就看到了范曾先生所作戴高乐将军像那张珍贵的画。我清楚地记得,范老在《准将的肩章》文末特别附录了书信全文。
《准将的肩章》把我们引入了1940年代硝烟弥漫的欧洲战场——那片看似熟悉的历史场景中,把我们的目光定格在那位“心中只有‘法兰西’三字,而置自己生死于度外的伟大人物”,“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准将军衔”的戴高乐身上。“战争是离不开火焰的,烈火中可以飞出凤凰,也会烧焦了乌鸦”,我们从五个场景中不仅看到了戴高乐将军对自由法兰西民族尊严的维护,还体味了他“澹泊寡欲、不务浮名”所彰显的人性的光洁。特别是戴高乐故去十八年前的那封信函的内容,让我想起了茨威格在《世间最美丽的坟墓——记1928年的一次俄国旅行》一文中描述过自己瞻仰托尔斯泰墓时的感受:“保护列夫·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唯有人们的敬意”,“逼人的朴素禁锢住任何一种观赏的闲情,并且不容许你大声说话。”托尔斯泰墓如此,范老眼中的戴高乐墓地亦如此。
这些天,由冯小刚导演、刘震云编剧的《一九四二》正在热映。我觉得,影片也好,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也罢,在讲到“人与世界的和解”这一主题的背后,有着自觉的世界历史图景的视界。当时间定格在1942年,不仅仅有河南省的大饥荒,也有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等事件,尽管其间少不了刘震云一贯的调侃或者揶揄。而我感触很深的是,我们的历史课堂教育改革迫在眉睫。哈耶克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在认知自然的同时,我们要拥有历史图景的视界。虽然我们的历史传统还音调未定,但对历史的细部、尤其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遇的耻辱要有个清醒的认识:如何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在思想层面的转折——从匍匐的奴隶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中国人。这也是澳洲学者费约翰《唤醒中国》那本思辨性著作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只有这样,知耻后勇的我们才会更明白维护民族尊严的可贵。
末尾,借用范老二十一年前赠送给萧瀚的一首七绝作结:“画到烟霞迷惘处,人间碧落两勾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