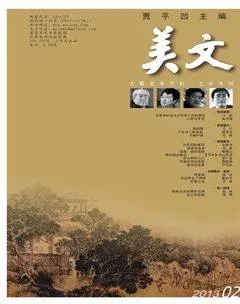我的朋友鲁迅

先生那些话
在这里,我想回忆一下鲁迅先生说过的一些话。
“老版,你猜孔圣人要是今天还在世的话,他是亲日派还是反日派?”
这是最近先生和我闲聊时谈起的话题,非常有趣。
“大概,有时候亲日,有时候反日吧?”
听了我的话,他哈哈地笑出声来。
“老版,你要是想了解什么是自由人的话,只要了解下皇帝的生活就行了。那真是完全的自由啊!”
“老版,今天发生了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以前在商务印书馆的外文书部征订了一本德文书,昨天接到通知说预订的书到了,让我准备好四元五角钱过去取书。我想着这大概是运费吧?加上书的价格怎么说也得五六十元钱。于是,我刚才带上钱去书馆了。店员拿来我预订的书,问我要四元五角钱。我问他是什么钱,他告诉我是收的书钱。我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说这书都应该卖四十元以上啊。于是我提出让他查一下看有没有弄错,没想到他还是告诉我说没有错,四元五角钱就够了。我又对他强调了7bf9f7d5ddb4b701da7f416fd8c0c02061d964f4662f2b4dcb4d9cbaa594f9d1一遍,说他绝对弄错了。这本书售价四十马克,换成人民币的话至少也得四五十块钱,希望他再查一下。结果那个店员啊,居然让我别闹事,想要的话就留下四元五角,把书带走,不想要就赶紧出门。我很无奈,这本书我确实需要,事情到了这地步,也只好息事宁人了,于是就付了四元五角钱,带着书回来了。商务印书馆肯定是亏了啊,毫无疑问。”
“类似这样的事情随处可见。邮局、火车站、轮船公司、商店、宾馆等,哪儿都能看到。我也曾经看到过好几次。”
“老版,你也认识的那位爱罗先珂先生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他说‘日本人非常顺从,严格遵守上级说的话,官员说的尤其如此。因此日本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被统治的国家。然而中国人则完全是反过来的。中国人对于别人说的话总是习惯性地持怀疑态度,特别是人们总认为官员说的话不可信。因此在中国推行政治政策是最难的’。”
我点头称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打个比方,长官对警官说这个人是坏人。如果是日本人的话,不会管这人到底是不是罪犯,只要被批准逮捕的,就一定是坏人了。警官的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哦不,也许应该说警官根本没有想要动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眼前的对象。他只是听了长官的话,就认定这个人是坏人。对于长官的话他全盘相信,没有丝毫怀疑。但是在中国,事情却恰恰相反。即便长官说这是个坏人,十恶不赦的坏人,警官也绝不会轻易相信的。即便接收了长官的命令,把对象当成罪犯来处理,他也一定会动用自己的意识,去考虑一些其他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一定会有自己的见解。比如说,这个人为什么是罪犯?为什么十恶不赦?怎么看都不像是罪犯啊,不觉得是坏人什么的。”
“这是日本容易统一,而中国很难统一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老版,在日本,小孩子出生后立刻就喂乳汁给他喝吗?”
我回答:“不是的,也许每个地方的习惯不一样。但是据我所知,小孩子出生后,先是给他们喂‘五香’,然后才是喂奶喝。”
“啊!原来是这样。我虽不知道什么是‘五香’,不过听起来这种风俗和我老家那儿倒是很像。在绍兴,小孩子出生后,在给他喂奶之前,大人们会先拿五种东西放到他嘴边给他舔一下。第一种是醋,第二种是盐,第三种是黄连,第四种是钩藤,第五种是砂糖。按照上面说的顺序依次给他尝醋的酸味、盐的咸味、黄连的苦味、钩藤代表了人生的荆棘(野蔷薇)——苦痛,最后才给他尝到人生的甜味。”
“从这个你就能看出来中国人教育孩子的顺序了。把人生的甜味放到最后让孩子品尝,这大概和日本人的做法不一样吧?”
这些虽然讲的都是很普通的习惯或风俗问题,却蕴含着许多让人深思的东西。
“老版,你觉得胡××有没有去南京?”
“唔,不清楚。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没想过这个问题。”
“那么,胡是亲日派,还是反日派?”
“说不准。大概有时候亲日,有时候反日吧。”
“那就跟赌博差不多吧。他来了后中国人民很担心。吸满了血的南京虫子昏昏欲睡,再也吸不动更多的血了。所以暂时让人放心了。然而新来的南京虫子还没有吸血,肚子空空的。这只虫子什么时候跳出来吸掉最后一口血就坏事了。哈哈哈……”
这比喻真是绝了!难道不是吗?
“老版,即便都是吸血动物,我最讨厌蚊子了,嗡嗡嗡的,吵死了,吸饱了血,肚子鼓鼓的,也不怎么动,只会慢慢地转来转去。那样子,真让人感到滑稽可笑。”
我记得大概是先生病后三个月,正值天气非常凉爽的时候,有一天先生从门外进来,很大声地喊了句“老版”。因为太突然了,我都吓了一跳。这是先生生病后第一次来我书店。
“老版,我感觉今天身体还不错,就出来走走。几天前从南京来了个客人,是我的学生,特意跑来见我,非常担心我的病情。今天我又收到他从南京寄来的信。”
说着把信读给我听,上面这样写道:
距离当初先生的逮捕状出来后,已经有十年了。如今先生病了,我想命令已经撤销了吧。我过去就一直仰慕先生高洁的品性,怕做了肯定会受到先生责罚。首先请先生予以谅解。
于是我问他:“先生,你怎么回信的呢?”
“我觉得很悲哀,简短地回了一行字。是这样写的: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我命不久矣,所谓的逮捕状留着也无妨。”
说完这番话,我清楚地看到先生脸上神采奕奕。
“老版,你看报纸了吗?上面说×××五十六岁寿辰收到礼金十多万元。大概没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吧。真是悲哀!在过去,中国人习惯十年庆祝一次生日,例如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从来没有像这个男的一样,过五十六岁寿辰。所以,这男的应该是每年都庆祝生日吧,然后大概每一次都收这么多礼金。每年生日收十万礼金,真是太难以接受了。在过去,受贿什么的都是偷偷摸摸的,现如今贿赂竟然差不多公开化了。”
我至今仍然记得,说这话的时候,先生的脸色是多么黯淡。
还记得有一次去探望生病休养的先生时,他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老版,《海上述林》还没到吗?都已经十月份了,这帮人都在搞什么啊?明明说好五月份出版的,这态度简直就是马马虎虎嘛!我之前写了封信过去骂他们,‘翻译的人突然死了,作家高尔基最近也死了,但是你们出版社还没完成校稿。你们是打算等读者也死掉吗?’但是没有人回我。”
先生这样抱怨着,可惜的是,他只看过上卷,还没来得及看下卷就与世长辞了。怎能不叫人惋惜!不过下卷已经开始印刷了,我想最近一定会问世的吧。
先生是一个眼里容不得半点马虎的人,若是和谁约了见面的时间,一定会准时赴约。有时候对方迟到个半小时,先生总会说“马马虎虎的人真让人没办法”。
还记得有一个人曾经向先生借了一本私藏的外文书,后来还回来的时候,书不仅变得皱巴巴的,连书里边的插图也变得脏兮兮的了。那时看到先生脸上难过的表情,连我都为那个还书的人感到抱歉了。先生说他难过并不是因为书被弄脏了,而是对不断把书弄脏的人的心灵的肮脏感到悲哀。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我都会对他涌起一股钦佩之情。
“老版,你听说过‘黄河之水天上来’吗?因为古人治理黄河靠的不是疏通河床,而是把两岸的堤坝修建得越来越高。随着河床被淤泥堆积得越来越高,两岸的堤坝也渐渐变得越来越高。一旦发洪水了,高筑的堤坝决堤了,水就像瀑布一样倾泻而出。这应该就是所谓的‘黄河之水天上来’了。这样看来,中国确实有必要改革治水方式啊!”

先生说的很多话,简直就是金玉良言。可惜我记性不好,平日里又比较懒惰,没有把那些话一句句都记下来。真让人遗憾!
“老版,你知道吗?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先生曾经这样对我说过。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非分明,绝不含糊。在政治、病痛、反对者的三重压迫下,仍能不屈不挠坚持战斗,我想先生留下的足迹绝不会被荒草掩盖。
而沿着先生留下的足迹,踏出一条光明大道不正是后来者该有的责任吗?
——《作家》一九三六年
附注:该文原题《忆鲁迅先生》,登载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号《作家》报。另外《忆鲁迅先生》前半部分为《文艺春秋》同年十二月登载的《临终的鲁迅先生》的中文译文,该部分为没有重复的后半部分。
先生和版画
被称为东亚唯一一个世界级大文豪——周树人即鲁迅先生,在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上可谓是不遗余力。
鲁迅先生收藏的汉代石刻数量非常多,单单上海的藏品就装了满满一大箱,留在北平住处的则更多了。他本想全部整理后拍成照片的,无奈数量实在太多,即便是拍照收集起来也很困难,一时半会儿也弄不完,这事情就一直拖了下来。如今也不知道这些藏品怎么样了,然而毫无疑问,这些藏品在石刻领域里都极其珍贵。我想其中肯定有很多极具参考价值的,因此才更觉得这些东西就放在那儿蒙灰实在太可惜了。
此外,先生对新兴版画(也许这样称呼不太准确,与中国历史悠久的古老版画相对,我把当下正流行的德国和苏联等国的版画称作新兴版画)也很感兴趣,特意大费周章从遥远的德国、法国、英国、苏联、日本(先生对日本的浮世绘感兴趣)等国家收集了许多作品。其中数德国和苏联的藏品最多,兴许是这两个国家的作品最容易收集吧。此外我还注意到德国一派的作品风格多属豪放,而苏联一派则纤细,线条优美,不同于前者给人的厚实感。我想这种差异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先生性格的两面性。
每次一有新的版画到,先生总会拿给我看。而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对版画燃起了兴趣。有一天我对先生说:“先生,我想把您收藏的版画拿给其他人瞧瞧,能把它们借给我吗?我想开一个版画展览会。”话音刚落,先生就欣然答应了,让我给点儿时间他好好选几幅,然后拿相框裱起来。我和他一拍即合,着手准备举办一个小型的世界版画展览会。
正好那阵子我在北四川路上的狄思威街角处租了上海供销合作社的二楼用来进行日语的夜校培训,于是就用这个教室做展览会会场。先生准备了德国和苏联的大大小小的版画作品共七十幅,全部用框裱好并编上号,下面用该国语言及中文标明作品对应的国家名字和作者名字,并制成目录印刷成册。展览会预期举办两天,安排在星期五和星期六。
据说在中国这是第一次有人举办版画展览会。在当时的上海,一共才四所美术学校。
终于等到展览会开幕的那一天,日本方面对这次活动评价很高,反之中国方面前来参观的人却相对较少。这其中肯定有宣传不到位的原因,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大概是由于许多人连版画是什么都不太清楚。不过不管怎样展览会总算成功了。
事实上,不论是先生还是我都认为版画需要的工具很简单,一把刀加上一张木板片就够了。只要有纸和墨,就会产生一种艺术。在中国,这种艺术比油画和水彩画更为普及。自古以来,也许应该说中国人骨子里就具备了鉴赏水墨画的能力,因此有人认为这种黑与白的版画同样会受到国人的追捧。可以说第一次版画展览会也是这种观点的表现。为期两日的展览会共吸引了四百多人前来参观,不管怎样都算得上是成功的。如果把这次展览会视作一颗在中国艺术界的湖面里引起波纹的石子的话,那更称得上是取得巨大的成功了。只不过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先生决定复制一部名为《水泥》的小说中的一组插画,特意找了商务印书馆定做了珂罗版两百册,放到我店里销售。然而几乎没什么中国人来买,买的全是日本人。先生看到这种销售情形多少有点儿沮丧,不过他仍然继续从世界各地搜集着版画作品。
在先生的影响下,渐渐地我对版画也产生了兴趣,打算举办第二次版画展览会。他自然对我的提议十分赞成,这次摆出的作品我们决定以法国小说中的插画为主。
那时候日语学习会已经移到其他地方去上了(之前长春路上的美国小学旧址),不能再用那个教室做会场了,于是我就把会场设到了老鞄子路上的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馆二楼。和先前一样,先生仍然给每一幅作品都编了号并写上国家名字和作者名字,按照这些编号及名字制成目录。在紧张的筹备后,展览会终于开幕了。然而不知道是换了场地还是有别的其他原因,前来参观的人出乎意料的少。总体而言,这次展览是失败了。
版画展览会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在中国人之间产生多么大的反响,甚至没有出现一个中国人立志从事版画创作。目睹此景的鲁迅先生十分惋惜中国的版画事业即将面临绝迹的命运,于是他联系了住在北平的郑振铎先生。两人决定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尽力保存该项世界瞩目的古老艺术。于是在克服了一系列财力物力以及其他各种困难后,他们终于完成了一部六册、集合了大约四百种优秀作品的版画集——《北平笺谱》。
在《北平笺谱》出版前夕,公开接受预约订购申请时,整个大上海据说一共只订购出了两部。由此可以想象出,版画在中国人当中是如何乏人问津了。
因为该笺谱只限量发行一百部,我当时以书店的名义订购了三十部进行出售,其余的则由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分摊掉了。郑先生的那部分不知道是不是留在北平卖出去了,鲁迅先生拿到的那部分则基本上都送给了英国、美国、法国、苏联、日本等国家的图书馆或者外国朋友了。而我拿的这部分则眨眼之间就被日本客人抢购一空,后来几笔订单都因为没货只能婉拒掉,这时候中国人里面也开始陆续有人找我订购了。因为很多人表示无论如何都想得到一本,于是我向先生请求再发行一百部。即便是再版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因为版本作者人数较多,所以比较gTM3QOnCDo952jqX5wm9Ph54hNyVIT3D/Fi22CLO3M4=麻烦),还好最后终于完成了。我尽力争取还是只拿到了四十部,也是一会儿工夫就卖完了。如今市面上《北平笺谱》已经算得上是珍品了,可谓一本难求。
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在东京成城学园当手工老师的内山嘉吉君来到上海旅游(他后来凭借雕刻作品两次入选二科会),他在上海期间与鲁迅先生往来密切。
他无意间说起愿意帮忙教一些有关版画入门方面的知识,这次聊天很快取得了效果。在鲁迅先生的热忱努力下,最终定下来由内山嘉吉君为美术学校十三名在校生进行授课讲习。由于内山完全不会说中文,鲁迅先生就临时当起了翻译。演讲的会场用的是日语学习会的教室,至于版画工具几乎什么都没有,只能把用过的铅笔头削尖装上转轴代替真的刻刀。短短几天的讲习结束了,姑且不论炎炎夏日坐在连一把电扇都没有的教室里,又闷又热、汗流浃背有多难熬,单单是这十三名学生的这份求知的热情和老师们的热诚之心都无疑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刻上了重重的一笔。从这一点看,这次讲习虽然简陋,却是极具意义的一次大运动。
正是通过这次讲习,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新兴版画家。自此以后,新兴版画家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将自己的足迹印在了中国大地上。
鲁迅先生为了给这帮学生制作参考资料,计划制作一本苏联版画作品选集,命名为《引玉集》。在日本进行珂罗版印刷,做工十分考究。首次出版发行了三百册,不到一个月就卖完了。
中国的这股版画热潮主要集中在北平、上海和广东三个地区。其中又以广东最为火热,画作风格多数模仿苏联流派的纤细特点。上海地区的作品则是继承了德国流派的粗犷,而北平地区似乎仍然更偏爱纤细的画风。而此时国民政府却突然宣称要将这些新兴版画家一网打尽,好像是把这些版画家都当成是共产党了。总之这次暴行使得十三名画家里有十个人最后行踪不明。恐怕这些人到今天为止仍然下落不明吧。
每次一回想起这些事,我就有一种责任感,禁不住热泪盈眶。
鲁迅先生为了鼓励这些新兴版画家,自己出钱给首次出版的一百册版画选集撰写了序文,排版并制作成书。这样就有了第一集《木刻纪要》。
我计划举办第三次版画展览会。《木刻纪要》出版后,版画这种日文说法统一改成中文说法“木刻画”。新出版的个人作品集或是同人作品集统统都用上了木刻画这样的字眼。
终于迎来了第三次展览会,这次的举办地点定在了施高塔路千爱里四十五号,展览会也已经改名叫木刻画展览会了。此次展览会得到了鲁迅先生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前来参观的人非常多。甚至展会上还来了三组中国小学生,由学校老师带着前来参观。不用说也看得出来,中国的木刻画业开始蓬勃发展了。
木刻画热潮迅速弥漫开了。没多久,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内部就举行了一次木刻画家作品展览会,先生和我都去参观了。学生们热情地把我们围在中间问我们的意见。我为了便于参考,把这次展览会上除去非卖品的所有作品都买了下来。
虽然这些作品多少还透着少许幼稚,然而却很容易看出来这些作品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绝非随着性子玩玩而已。不同于被称为“闲人的艺术”的日本木刻画,中国的木刻画带有非常浓厚的实用色彩。我和先生看到作品整体的风格倾向,都感到非常高兴。
然而,如果说风景木刻画还算可圈可点的话,人物木刻画就比较拙劣了。说起人物画,传统的中国画很少有写实的,肉体描写更是几乎没有,这或许导致了展览会上的人物木刻画基本没什么看头,里面的人物看上去跟机器人差不多。
年轻人似乎喜欢刻画一些举行工厂大罢工、高唱革命歌曲的团体人物像。只不过这些画大都没有张力,让人感觉不到热情。很明显能看出,这些人在素描方面的不足,为此先生总是特别指出这点,提醒年轻人注意,不过始终没引起多大的变化。当然这种改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广东地区一些人的个人作品集渐渐出版了。上海地区的木刻画则由当地特色的小报作了插画。紧接着漫画杂志、图表以及杂志插画都被木刻画占领了。一些主流报纸、小说、诗歌等单行本的插画也几乎都开始大量使用起木刻画了。刘砚和罗清桢等人还特意到日本研究木刻画。他们制作了《罪与罚》中的插画并出版了单行本。而《引玉集》由于希望其再版的读者众多,再版后我的店里一直在销售。
这时候鲁迅先生已经卧病在床了,病情时好时坏。他会经常过来店里坐坐,即使在病中他对木刻画的热情也丝毫未减。他打算复刻德国老画家科尔维斯基的木刻画作品,对出版相关事宜一直亲力亲为,耗费了许多心血。从原文的翻译到纸张的选择再到题字、序文等 ,都坚持一个人完成。
不知何时,苏联大使馆注意到了木刻画的流行。从国内运来了数百种大小的木刻画,并由苏联大使馆主办,在北平、汉口、南京、上海、广东等地举行了木刻画展览会。中国的木刻画事业也迎来了最高潮。
鲁迅先生也接到了使馆方的邀请。他不顾自己有病在身,仍然前去参观,每次参观回来,心情总是大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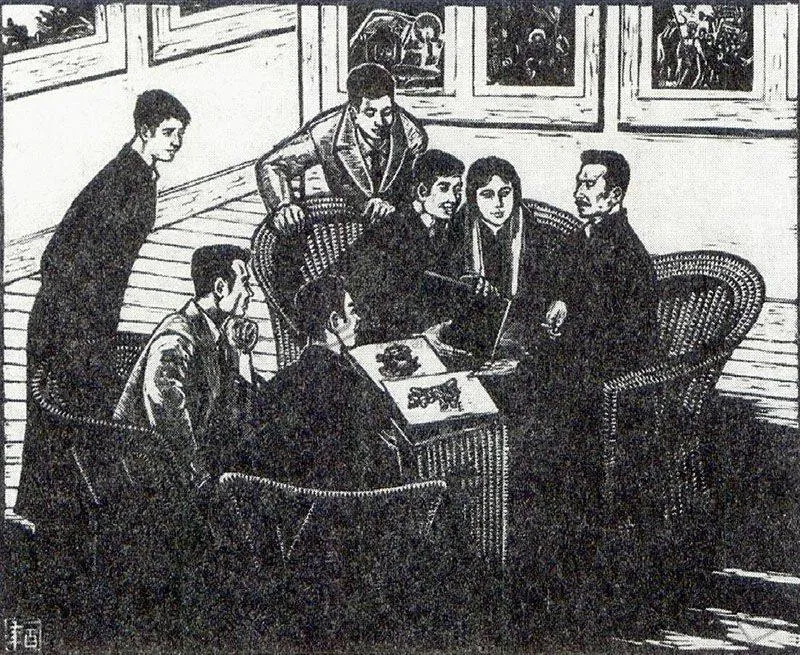
“老版,我去看了。真的很不错哟。素描什么的都非常好,人物刻画得很仔细,血管什么的都清晰可见,让人感觉跟活人一样有力。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我看到很多作品都想买下来,可是一幅画就要五十元、一百元,我的钱包实在是负荷不了呀!只定了四五幅,等送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签收下。”
后来先生又和我聊了会儿就回家了,之后一直没见有人送画过来,挺奇怪的。一直等到各地展览会都结束了,画才送到。
如今在对舶来品征收重税的苏联,用材便宜的小小木刻画能这么火热也不足为奇了,我仿佛从这种现实中看到了中国的明天。中国人自古就赏玩水墨画。到底是先欣赏再作画,还是先有画才出现鉴赏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黑白水墨画使中国人享誉世界。而这也让我相信,我对于同属黑白艺术的木刻画持有的希望绝不会只是一个梦而已,而是一点点变得愈加清晰。
其间科尔维斯基的木刻画集成功问世了。只不过还未来得及销售就被一些木刻画爱好者分购一空,我只抢到了三十部放在店里销售。木刻画集的广告是先生亲笔写下广告语的作品,而该广告图从一开始就被人订下了,我一拿到手就立刻给对方了。
新兴木刻画就像一滴活水,给枯寂沉闷的中国艺术界带去了新的生机和色彩。
先生去世前几天,在法租界的仙桥青年会馆又举办了一次木刻画展览会。先生大概是感动于年轻人的蓬勃朝气,于是不顾重病在身坚持前去参观了。这次的木刻画与以往的作品相比,可谓是面目一新。先生和几名木刻画家一起在会场里微笑着合影留念。只是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会是先生生前最后一张相片。十月十九日凌晨,先生最终还是离我们而去了,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悲痛的海洋里。
如今在中国极其兴盛的木刻画事业,离不开当初鲁迅先生的悉心播种及灌溉,正是先生的热情培育才有了木刻画事业的茁壮成长。先生既是先知者,又是一位考古学家。在鼓励新兴木刻画的同时,仍然不忘尽心尽力保护旧木刻画,真不愧是一位温故知新的智者啊。
——《上海漫语》一九三八年
先生趣话
我想到关于鲁迅先生的一则旧事。
一直以来他都称呼我为“老版、老版”,不论什么时候总能听见先生叫我“老版!”
有一天,他冲我说:“老版!有些事情虽然听上去说的是中国某些地方,其实有很多也正是全部中国人有的情况。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可不少哟。比如说山西,有人把山西人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因为山西人和‘犹太人’一样对赚钱有着执着的热情。北平和天津这些地方的钱庄几乎全部是山西人开的。欧洲人和日本人常说中国人喜欢把银币熔了制成银块,不断熔化冷却后最终做成更大的银块。好像全中国到处都滚动着这些大银块似的,其实这里说的事情正是山西人对金钱财富执着追求的结果,山西人喜欢把银子熔化后做成大的银块。有些银块做得太大了,成了怎么都搬不动的千斤银锭时,据说有人用家乡话说了句‘没奈何’,于是渐渐地就成为约定俗成的说法了。
“再比如某人家生了男孩,家里马上会买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做童养媳用来守护这个初生的男婴,这种做法据说在山西的风俗中是最多的。”
确实是这样呢。过去说起中国的事情,那些只见过满洲一角的人都会立刻说中国怎样、中国人怎样云云。于是生活在内地的人们一直被那些并不正确的所谓“见闻”抹黑了。这对于那些对中国持有好感的人而言,是多么大的误导啊。单凭“没奈何”这个事情就足以说明,我们的脑海里会记住那些完全没有根据的话。即便是如今,一些相当危险的话也是肆无忌惮地向我们涌来。
对于那些无凭无据、居心叵测的传闻和言语,我们必须擦亮自己的眼睛,做到明辨是非。
不管怎么说,一定不能忘记中国人的生活里必然包括了现象和本质两个方面。
我脑海里时常想起此前鲁迅先生经常说的一段话,那就是中国的事情是复数而非单数,不能只看各种表面现象。如果单单靠表面现象就做出判断的话,往往看不到现象背后深藏的内因,而只能单单停留在眼前看到的表象上。现在想来,先生的话确实很有道理。
——《上海漫语》一九三八年
徐福的故事
我总会时不时地想起先生。先生高兴的样子、悲伤的样子、天真的样子、忧郁的样子、苦闷的样子不断变换着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时隐时现。
这十年间我见识的很多张脸孔给我留下的印象似乎都是瞬间性的,当时记得很清楚,过后回想起来却变得模糊,唯独先生的容貌不论在脑海里出现了几十遍还是几百遍都依然清晰,未有丝毫改变。
假如我现在能把脑海中先生的整个相貌,包括从一根头发到一颗痣都全部画下来,那一定就是先生本来的样子。
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人很难再有了。过去我时不时地会听到四五个人谈论先生。无论是谁都高赞先生的伟大,称他为“世界的鲁迅先生”。类似这样的话基本都差不多,只不过谈话到最后总会把世界的鲁迅先生归结为中国的或者中国某个地方的,甚至是渺小的个人。这时我便会更真切而深刻地感到先生的伟大,同时也感觉到我等普通人在先生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只能是望其项背罢了。
有一天和先生闲聊时讲到了徐福东渡的故事。先生说:“老版你知道吗?这个徐福根本没有炼成什么长生不老的药。但是他深知不能直接上奏皇上说这世上根本没什么长生不老药,否则肯定会掉脑袋,于是为了避免杀身之祸,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告诉皇上去东海的蓬莱岛可以得到长生仙药,说得诚恳无比,最终骗过了皇上。于是他带着数千童男童女出海了,其实就是逃跑。他根本没想过要再回去。如果他直接说没有仙药的话,必死无疑。于是他想到编个蓬莱有仙药的谎话,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这都是事先就计划好的。中国很早以前开始就有许多人致力于炼制长生不老药和炼金术,只不过到最后都失败了。徐福也不过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罢了,哈哈哈……”
这个说法真有意思。徐福的故事真相如果是这样的话,倒显得合情合理了,一点儿没有什么牵强附会或讲不通的地方。听了先生的这个解释,我恍然大悟。虽然先生不在了,但是他的那些话仍然活在我的心中,而且透着革命的精神。
——《大鲁迅全集月报》一九三七年
鲁迅与萧伯纳
这是发生在大文豪萧伯纳抵达上海三天前的事情。当时,我接到改造社的密电,大概意思是:“请让萧伯纳与鲁迅进行会谈,因此现特派木村毅先生前往。”看到这封电报,我明白了改造社的意图,他们已经和萧伯纳交涉好了,现在让我与鲁迅先生沟通,然后促成这两位文豪的对话交流。于是,我将电报给先生看了,并得到了他的应允。但先生立刻又问道:“我见了萧伯纳做什么呢?我并不打算见他。”我回答说:“你既然说了可以见面,那见见也行嘛!”不管怎么说,他已经接受了这个请求,所以我也就放心了。我算了一下木村先生到达的时间,发现他和萧伯纳同一天到达。虽然两人坐的都是欧洲邮船,但我还是去船运公司咨询了一下,得知木村先生的船艇比萧伯纳先生的提前三十分钟到达税官栈桥。他们大概是八点和八点三十分这两个时间点到吧!于是,当天早上我让先生待在家里,独自一人前往海关码头迎接木村先生。一到那儿,眼前一片人山人海,大家都是为了迎接萧伯纳而来的吧!几乎都是文学界的人,甚至还有几个团体高举着用英语书写的旗帜以示热烈欢迎,但不知道具体写的内容是什么。有一个学生发现我站在那儿,立刻大声喊叫:“内山来了,内山来了。”于是,众人将我团团围住,异口同声地问:“鲁迅来不来?鲁迅也一起来吗?”总之,全是有关“鲁迅如何”的问题。然而,我只能佯装糊涂。
“不晓得,不晓得。”我一口咬定说不知道,就这样穿过人群。这时,《每日新闻》的吉冈先生向我打招呼:“喂!老板。”我回答道:“啊!真够呛啊!围观的观众如此之多。”吉冈先生紧接着问:“老板您也是来一睹萧伯纳风采吗?”我说:“不是的,实际上我是来迎接改造社的木村先生的。”那个敏感的吉冈先生不会遗漏一丝疑问,所以他接着问:“木村先生来此有何贵干呢?”我略作暧昧地回答道:“木村先生也是来迎接萧伯纳的。”于是,吉冈说:“如果木村先生来了,请您介绍他给我认识啊!拜托了!”我答应了他的请求。然后,他就这样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在八点的船艇到达之前,我见过他两三次,每次他都会说:“拜托了,老板!”
七点四十五分,海关的挂钟“咣”地敲了一下。先前的那些学生来到我跟前说:“内山先生,把鲁迅先生叫来好吗?”然而,还有十五分钟木村先生的船就要到了,我无法抽开身来。于是,我回答说:“八点钟到的那趟船里有我的客人,我回去后再问问鲁迅先生。”大家都高兴地回答:“好好好好。”“灾难”终于暂时平息了。不久,“咣咣咣……”八点钟的钟声敲响了。我眺望河流下游,日本邮船公司的金陵丸(船名)终于出现了,它在晨风中吐着黑烟,渐渐向码头靠近。本想去码头迎接,但因为今天不允许,所以只好在行李检查处的出口等着。但是,所有的乘客全部都出来了,还是未见木村先生的身影,我大失所望。我想,可能是我看漏了吧!可是,这不可能啊!我清清楚楚地看着每一位出来的人,确实没有木村先生。于是,我想起当天的渡轮是从长崎进港的,木村先生在神户坐不到渡轮,应该是在长崎乘坐的吧!无可奈何,我只好打道回府。就在这时,吉冈先生来了。
他双眼充满血丝,失落地问我:“老板,您见到萧伯纳了吗?”我随意地回答道:“没有。”但是,他不甘心地说:“从今天清晨四点开始,一直都在等他,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他。您见到了他,请一定要告诉我。拜托了!”说完,他再次消失在人群中。我看到新闻记者一无所获的样子,感觉他们的苦痛甚是悲壮。决定先回家,不能再这样混混沌沌了。我的车经过外白渡桥向西拐时,看见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前面挤满了人。
回到家中,一边泡着“初雁”,一边“哎呀!哎呀”地叹气。就在这时电话“丁零、丁零”地响了。
“您好,请问内山先生在吗?”电话那端问道。
“是,我就是内山,请问您是?”我回答道。
“我是木村,因为萧伯纳说要来礼查饭店吃午饭,所以我就直接来到饭店了。能请您立刻过来一趟吗?”既然他都这么说了,那我暂且将责问的事情放在一边吧!“好的,我马上就过去。”说完,我挂断了电话。因为离吃午餐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坐一号电车出门了。
一到那儿,我看见木村在礼查饭店前等着。我说起早上所发生的事情,并问及原因。木村解释说:“乘船时,我和上海旅行社的老板Y先生同一个房间。Y先生说他可以带我来这儿。”我追问道:“可我在检查处的出口并没有看见你啊!”他回答道:“实际上,通过Y先生的关系,我和他从别的出口出来的。”“啊?”我很是惊讶,甚至有点气愤。木村先生建议说:“我们自己也在这儿吃饭,等待着萧伯纳先生的到来吧!”我想,无论如何要让木村先生先见鲁迅先生一面,尽量让俩人一起来这儿。于是,我强硬地带着踌躇不决的木村先生来到我家,并在礼查饭店告别了Y先生。
回到家中,我们吃了两三个点心,从木村先生那儿听了改造社的许多计划。令我惊讶的是,改造社事先并没有与萧伯纳联系沟通。木村先生仅仅是拿着一张介绍信,是一位在伦敦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M先生写的。就是说,改造社为这件事支付了巨额的旅费,还特意派木村先生来上海。我对改造社的胆量感到惊讶和震撼。我说:“去见见鲁迅先生吧!”就在这时,一辆轿车停在了门前。一位身材高大、陌生的中国青年手持信件问我:“内山先生在不在?”我停下脚步,回答说:“我就是内山。”于是,那位年轻人说:“这是蔡元培先生写给您的信件。”他将手中的信件递给我。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将另一张纸转交给鲁迅先生。于是,我让信差稍等片刻,拿着信件向对面的住宅走去。先生看完信件说:“蔡老板通知说,萧伯纳马上就来了,他正在家中等着,请咱们坐车过去。那咱们就去吧!”邀请我陪同他前往。我就将木村先生的事情跟他说了。他说:“因为对方是私人家庭,我自己先去打听一下萧伯纳的情况,然后再联系你们。请你们暂时先在这儿等一会儿。”鲁迅先生便和来迎接的人一同出去了。下午两点,先生打来电话说,请木村先生立刻过去。木村先生欢欣鼓舞,直接奔赴目的地——宋庆龄女士家。萧伯纳和鲁迅先生的见面会就这样促成了。后来,据先生说:
萧伯纳的船刚刚驶进港口,宋女士就立刻停下汽艇上船迎接。因为宋女士和萧伯纳是旧识,所以萧伯纳很快就被宋女士邀请上岸了。然而,因为之后船务公司的船还要去迎接乘客,所以萧伯纳没有在海关码头上岸,也没有去礼查饭店吃午餐,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按照蔡元培先生的计划,邀请了萧伯纳先生去世界文化协会小厅参加欢迎会。会上有人说:“我翻译了您的书,送给您一本。”萧先生说:“即使拿了书也没有办法看啊!倒不如您送我钱吧!”他还是收下了书。当有人问到妇女问题时,他巧妙地回答:“夫人在世期间是不能说的。”让对方扑了个空。还有人问及有关中国政治的高见时,他再次精辟地说:“我杀了约十万人后再讨论吧!”他精锐的利剑完美地击中了对方的心脏。虽然大家都说萧伯纳先生是讽刺家,直到真正见了他,才明白他绝不是讽刺家。他将最多的内容浓缩成最短的语言来表现。而且,他的话语都是精心提炼的金子,令人心中油然升起一股赞叹之情。
我拥有一张特别的照片,照片上高大的萧伯纳先生站在正中间,蔡先生和鲁迅先生并列在其左右。但是,鲁迅先生先去世了,蔡元培先生也长眠了,唯独萧伯纳先生还健在。不知是上帝的捉弄,还是佛的因果报应?最年轻的鲁迅先生却最先去世了,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每当我细数这些事情的时候,先生生前的姿态历历在目。
每天早晨,先生从大陆新村的家里出来,他一步一步坚定的脚印,是特征性的、代表性的东西。他每天去狄思威路的图书室以及里面的读书办公室。在那儿,或者读书,或者写文章,或者整理书籍。午餐的时候回家一趟,下午两三点到我的书店来。每次来,肯定都有谁在等待着他,所以,他一坐下来便开始闲谈交流。聊得起劲时,他颤动着双肩高兴地笑起来,看起来是多么愉快啊!
有时我也去他的图书室看看,每次去的时候,他的图书室都是干净整洁的。杂志是杂志,中文、日文也都分科别类,他还将过期刊物整理好用纸包裹着,并在上面整齐地写着杂志名、发行年月、编号,将其按顺序排列。当然,全集和单行本也都是这样的。此外,中文、日文以及其他外文都是分别装在不同的箱子里。其整齐干净的程度,是其他的图书室无法达到的。花多长时间整理好的呢?真是不可思议啊!看看先生的文章,也是非常工整明了,我甚是惊讶。先生的图书室和他的文章一样整洁干净。此外,先生刚出版新刊时的原稿也是一样的整齐。原稿虽是原稿,却和已经出版的书籍一样成型了。我对此感到惊讶不已。
最近,出版社发行了近藤春雄编写的一本书,名叫《现代中国的作家和作品》。其中有一篇文章是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在鲁迅先生两周年祭日时发表的演讲,他将先生的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政治的卓识;二、斗争的精神;三、牺牲的精神。我认为,必须还要加上整理的精神,以及先生的民族魂。“事情如果发展到那种地步,就是感情的问题了。同样是丧失财产,但比起被强盗偷去,还是被放荡子浪费的好;同样是被虐杀,但我希望被同国人杀害。”(这是先生与野口米次郎对话的最后一句)如果加上这个,那应该是五个特点吧!
——《桃园》一九四九年
理所当然的事
中国人对比自己生活水平低的人,总是毫无理由地认为应该帮一把。也不光是对比自己生活水平低的人,对一些自己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也总想着从自己的一份里拿出一部分分给没有的人。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会心里不安。同理,接受的一方也不应该拒绝,好像拒绝了心里也会不踏实(可能有一些夸大)。这种时候,就根本不是什么面子之类的原因了,而只是出于一种非这样做不可的不成文的规定,觉得必须得帮对方一把。
有人给鲁迅先生寄来了一百块稿费。正好赶上先生来我店里,我就把稿费的事情对他说了。先生听后对我说道:“那今天就把那一百块给我吧,正好我有点儿用。”我听后马上把钱给他了。
我俩刚闲聊了一会儿,有个女人过来找先生。先生转过去听了会那个女人说话,就把我刚给他的一百块钱给了那个女人。那女人只说了一声谢谢,拿着一百块钱就匆匆回家去了。
要知道,在鲁迅先生的生活里,一百块钱绝不是一笔小数目。我忍不住问先生:“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先生说道:“那个女人的丈夫,因为一个朋友的谗言,前段时间被关进苏州监狱了。这个女人正好从事解放运动。几天前从监狱方面传来消息,说是只要带三百块钱过去就把人给放了。她自己和朋友只拿得出两百块,另外一百块怎么也拿不出来,所以让我借一百块钱给她,于是我就把钱给她了。”
那个女人可能被骗了,我想要不要提醒先生一下呢?最后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先生那人到底和他是什么关系。先生对我说道:“那个女人和她丈夫都是我在北平时候的学生。我也知道她是被人骗了,中国监狱的那些狱警很多都不是好东西,编编谎话欺骗这些可怜人的不在少数。这个女人应该也是被这些流氓给骗了,但是这会儿我不能告诉她这些。她拿钱走的时候应该心里充满了希望吧,算啦。”
我一时还真的体会不到先生说的这些,不过要是换了我站在先生的立场上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拿钱出来的。而且我会明明白白告诉那个女人她被骗了,劝她别去。听了我的想法,先生说道:“老版,你可以把立场再换一换呢。如果你是那个女人,而我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劝你不要去,你肯定会迫于无奈答应下来,但是心里边一定很绝望吧?”
先生的话让我脸红起来。紧接着他又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是不应该拒绝的。这种时候,如果你手上有,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要借给她。这是一种习惯。”
我问先生这种只要有就不会拒绝,是不是为了“面子”?先生笑道:“不不,不是为了面子什么的。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条件,对于有的人来说,只要一无所有、生活困难的人有需求,能帮忙的话帮一把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哈哈哈。”我听后,再一次感觉惭愧起来。
“只要一无所有、生活困难的人有需求,能帮忙的话帮一把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多么透彻的一句话啊!然而这句话不是光靠嘴上说的,是要落到实际行动中去的。也就是有人说的把它当成一种习惯去付出。每次我劝自己别想了,过后又总会忍不住去想这句话。就凭这一件事,我也不会浅薄地卖弄自己是个中国通。
——《上海漫语》一九三八年
有关诗歌的谈话
N氏(即野口米次郎):中国的将来会变成怎样呢?
L氏(即鲁迅):中国怕是将来会变成阿拉伯那样的沙漠,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我必须战斗。
N氏:中日两国会友好共存吗?
L氏:日本亲华人士如果能更多地发挥个人力量的话,应该可以吧。
N氏:如果当今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最终还是不能拥有安定百姓的能力的话,进而变成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一样,连国防和政治都被外国人侵占了,到时候怎么办?
L氏:事情如果发展到那种地步,就是感情的问题了。同样是丧失财产,但比起被强盗偷去,还是被放荡子浪费的好;同样是被虐杀,但我希望被同国人杀害。
一九三五年秋日的某一天,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两个诗人曾经对话过。当时我只是茫然地听着。以上是这段谈话内容的如实记录。
——《上海漫语》一九三八年

人品有价
有一句话叫做:“天地是大剧场,剧场是小天地。”这似乎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想法。如今东亚的舞台上出现了一个红毛洋鬼子(称呼西洋人的说法),还有一个黑头发的亚细亚人带着四五个朋友吵吵嚷嚷地出现了。他刚看见红毛洋鬼子,就转过头对身后的朋友说该洋鬼子居心叵测,务必提防着点儿,然后又气势汹汹地说为了世界和平应该打倒红毛洋鬼子。听了他的这番话,同伴们也都怒气冲冲地表示要给那个鬼子一点颜色看看。
当那个红毛洋鬼子边挥着手杖边走路的时候,无论是走在前面骂骂咧咧的那个还是跟在后面怒气冲冲的同伴们,都学着红毛洋鬼子挥动手杖的样子走了起来。洋鬼子停下来抽烟,后面的人也跟着停下来抽烟。总之一切都模仿那个洋鬼子。旁边的人看到了都觉得很有意思,笑了起来。唯独邬其山叹了口气,无奈地抚了抚额头,小声抱怨道:“真可笑啊!”
邬其山曾经有一次回了趟阔别三十年的帝都东京。从中央停车场下来打量着眼前这座气势恢宏的大楼时情不自禁地喊了声“美国”。很显然在他的心里素未谋面的美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吧。看到东京人走路很快的样子,他觉得像短腿的美国人走路。看到街上妆容新奇的女人们,他又想这难道是戴着黑色假发的矮个儿美国街头女演员吗?据说最近几年日本很流行以前中国上上下下都爱玩的麻将,所谓的麻将俱乐部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邬其山觉得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日本人在此前的中日甲午、日俄战争中曾经那么看不起中国,觉得中国文化如同路边的野草一般蛮荒,但最近却开始流行起中国常见的麻将来,这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难道说日本又重新开始关注起中国了?所以最先从娱乐上着手引进中国的东西?邬其山也差点先入为主下结论了。后来想了想,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调查后他发现这现象背后另有文章。原来,这麻将并非是从中国传来的,而是从美国传进来的。日本流行的麻将其实是美国制造的。虽说日本急于吸取美国的长处,所谓的新建筑、新经营全部都是美国式的,然而绕开离日本极近的麻将产地——中国,特意舍近求远从远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引进麻将,多少有点儿让人匪夷所思。邬其山心想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吧。然而几经询问,回答都只有一个:麻将现在在美国很流行。没想到日本人醉心于美国文化居然到了这个地步,邬其山不由感叹这些人已经病入膏肓了。
读到这,也就不觉得邬其山一下车站便误把东京当成美国这件事,有什么滑稽和不可思议的地方了吧?
啊!糟了!我本该说中国见闻的,没想到不知不觉间讲成日本和美国了,赶紧绕回来。
3GTRwe1SwfNXohERPLHQ0m5xtOplzIb3IxXemRkyYfM=我注意到中国的小贩们很精明,连哪些东西卖得便宜了都要一笔笔记录下来。在我眼中这些小贩的做法很奇怪,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心态,中国才发展得很滞后吧。有一次闲聊的时候我近乎失礼地直说,在中国买东西,如果买得少就便宜,买得多就很贵了。听了我的话,鲁迅先生便给我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有一户人家的阿妈(女佣)每天都去小菜场买菜。有一天正碰上她有事情,于是就事先付给了油店老板四角洋钱,然后把油瓶放在那儿,嘱咐完打了油送到哪里去之后就去办她自己的事情去了。这个阿妈之前每次都用一个威士忌的空瓶花四角洋钱打满满一瓶油回来。那天她办完事回到家后发现油店照例送来了满瓶的油,她也就放心了。
后来有一次她又有事情在身,于是就像之前一样留了四角洋钱和一个空瓶子,拜托油店的伙计打了油送到家里去后就走了。晚上回到家后,女主人拿出油瓶对她说道:“今天的油比往常的要少。”阿妈一看,果然平日里用来装油的威士忌瓶子这次只有八九分满。
于是女主人拿了油去油店评理,说之前一直都是满瓶的油,为什么今天的油只有八九分满呢。结果油店的伙计回答说不可能少,四角洋钱就只有这么多。女主人指责他胡说,之前送过来的油难道不是满瓶的吗。小伙计死不承认,一口咬定说没有这回事。于是女主人也只好作罢,安安静静地回家去了。
多有意思,之前用四角洋钱打来了满瓶的油,后来瓶子还是那个瓶子,里面的油却再也没有装满过。原来阿妈常去买油的那个油店,第一次阿妈有事拜托油店的人把油送到家里去,油店的伙计不确定到底应该送到阿妈家还是谁的家里,就当作是送到阿妈家去的,灌了满满的一瓶。但是等到伙计抱着油瓶送过去了,才发现送的地方不是阿妈家,而是非常气派的大户人家。眼前的景象自然而然地印在了小伙计的脑海里。等到下次阿妈再拜托他送油过去的时候,小伙计脑中浮现的就不是阿妈的身影了,而换成了大户人家的女主人。这时候伙计打油的手自然而然就在瓶子八分左右满的时候停住了。而这样做的小伙计压根就没感觉到女主人说的油少了的地方是哪里,于是不慌不忙地说就只有这么多。即便被女主人再次责问为什么不是满瓶的时候,小伙计仍然坚持说只有这么多。
有趣!实在是有趣!不记得谁说过,商品的价格包括了原料的原价和加工费以及商人的利润。如果这个定理在全世界都行得通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批发商也就不搞什么批发了。实际上在有些商人看来,商品的价格包括原料的价格、加工费、商人利润,还有客人的人品价格,非常麻烦。无论是否有人一口断定这是封建的、亚洲式的残余,有些人习惯出售五成商品来做生意,有些人用六成做生意。这真的是落后的吗?我看不一定,有时候会不会是一种进步呢?
——《活中国的姿态》一九三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