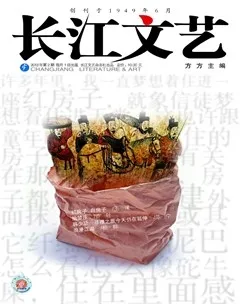“羊群啃食石头上的阳光”
作为一个文学编辑,我很长时间没有专心读诗。过去刊物不太重视诗歌栏目,有一个也是点缀一下,少了这种文体好像是不像话。读者也不太认真地读。常常只是几个作者在那里较劲谁好谁不好,编辑多半是照顾关系谁上谁不上,读者置若罔闻,作者读者和编者都觉得没劲。起了变化,在我们这本杂志,是2012年改版之后,有了一个“诗空间”栏目。
前些时,诗歌编辑佳燕同学给我留言,说:这一期有你喜欢的小引哦!我马上更正,我不是喜欢小引,我是喜欢《西北偏北》,因为我只读过他这首诗,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我记错了,我曾经读过张子选的《西北偏西》,有一天想起要再看看,记错了题目,到网上一搜,才读到了小引的《西北偏北》,啊呀,好喜欢。对于我这样一个常年读稿干一行恨一行的人来说,喜欢,太难得了。只有当这点喜悦一闪而过的时候 ,我才觉得“只有文学值得奋斗”①。
数年前,偶然读到张子选的诗,大惊之下,心生感慨,原来还有这么美的当代诗歌,还好,我没有错过它们,心中也不免有一丝惆怅,我还错过了多少美好的诗句呢?有人在评介张子选的时候说:“面对张子选,中国诗歌界就是一个瞎子。”是的,我当瞎子已经很久了,我愿意从此开始,睁开眼睛。
我是编辑却不爱和作者面对面,钱钟书说得好,你吃一个鸡蛋吃得香,又何必要认得那只生蛋的鸡?但是你喜欢一首诗,了解一下写诗的人,也是有趣的事。刚好手边有个介绍,就抄下来吧:小引,原名王朝晖,43岁,理工科出身,曾是摇滚青年,现在是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师。据说喜欢行走(这个词有点恶俗)。行走了万水千山,笔下自然有了山水气。不过,他就是行走在菜市场,写的诗也引人入胜。这次栏目主持人选了他的8首诗,有《山顶之歌》,也有《下雪的中午在菜市场想起你》,希望读者喜欢。还有更多的诗,在行走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写,他一边写我们一边看,相看两不厌,彼此都不寂寞。
有些年头了,写作是一件苦事,没名没利的,后来写作变得有利可图了,但诗人写诗还是很寂寞的干活。最近有个喜欢搞鸿篇巨制的诗作者号称自己写诗能挣大钱,看上去着实行迹可疑,居心叵测。我近乎本能地质疑。也有人说,吃饱了没事干,才写诗,才读诗。不对,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常是人在极度苦闷压抑中才会写出美丽诗篇。在这些诗篇里,我们能感受到诗人对汉语抱有极大的敬意。他们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像是生活在偏僻之所的织绣工人,孜孜不倦地编织花样:云纹水纹龟背纹,龙纹凤纹串枝莲……这种努力,除了给我们这些读者感情上的冲击,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的一个男同学,看到他妹妹的牛仔裤上整了两个洞,很不高兴,说道:“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如今我看到有些人糟蹋汉语的时候(这种人真不少)心情也大致如此。在这里,我要引用韩少功的话,他说出了我心中所想,这也是我今天要写这篇读后感最初的原因:“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心里只有语言,精神唯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②
①白先勇主编的《现代文学》编辑部散伙多年之后,有一次和朋友谈起当年把文学当饭吃、埋头苦干的种种事情,这个朋友感叹:“只有文学值得奋斗。”我年少轻狂时也这么想,现在偶尔会想起来,偶尔说起,朋友中没一个相信。他们笑我,我自己也笑了。不过如果我很老了,还能这样想,那说明我的选择很值得。很少人能像张承志那样,写下《心灵史》的时候就宣告这会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没有之一。人们多是年少时“为赋新词强说愁”,老了“却道天凉好个秋”。我也说不准。
②这段话引自韩少功的文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