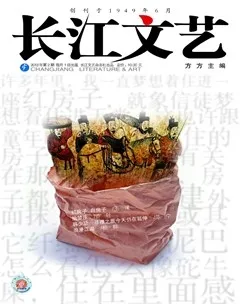在一个理想落空的时代谈谈诗歌
“商业化”背景下的诗歌状况
最近一段时间,我选择性地读了新诗开创以来的一些诗作,发现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写作脱离了新诗开端的婴儿期,打开了较以往更为明晰的诗歌前景。地下刊物《今天》的诗人们和第三代的诗人们为诗歌开阔了一大片天地。这也是当下的诗歌写作在语言与思想上有了更多空间的一个前提。今天,包括在诗歌行为上也延续了以地下刊物、民刊性质的刊物为主的传播途径。而现在,还有了网络传播方式。
诗歌的批判性和自由度因“89事件”戛然而止。上世纪90年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引导人们在地位、身份、阶层、价值认识上直接以金钱为衡量标准,但却没有公平的竞争。权力的无限延伸,使大量获取金钱的途径成为肮脏的交易之路,社会价值取向越来越失衡,精神价值被现实边缘化了。看上去,诗人在精神和理想的层面上被悬空,无法重拾80年代对诗歌的热望,但这样的境遇同时使那些严肃的诗人们沉入到更深更独自的思考和写作中,他们的努力使一种更加内在的表达在诗人身上和诗歌创作中被引申出来。这种转化和改变就在诗人与受众之间拉开了距离,也促成了那些成熟的具有持久创造力和宽阔视野的诗人们与诗歌的内在融合,因此淘汰了大量寄生性的诗人与读者。
新世纪前后,在对这种处境的反省中,人们开始试图用各种方式重建失去的理想与自由,诗人们的写作对现实的介入和重审成为精神建构的方式之一。这种方式不仅仅是社会事件化的,还细节到更日常的生存状况之中,更多的是一种从个体处境出发的人性和诗性在现实和写作上的展开。诗歌的各种流派、团体、读本、交流活动也在有限的范围内热闹起来。
这几年,关于诗歌,不断地传来各类担忧的声音,关于“商业化”、“娱乐化”、“消费时代”、“多媒体时代”、“全球化”等等造成的“诗歌的边缘化”的困惑。首先,在这一切的前提下还有我们不能言说的大背景,我们所能拥有的是极其有限的自由和一个人关上门有所选择的内心自由。应对时代环境的恶劣,诗人们在力所能及之处都在尽着自己的努力。
在中国,“商业化”是由它自然生成的部分和被迫的部分混杂在一起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而实现理想首先要有挣钱和生存的能力。而我们的年轻人因为生存更累,大量的就业危机,大量地沦为房奴、车奴、卡奴等各种奴,大量的生存空间被剥夺,太多的青春年华和精力都应付了这所谓的“时代洪流”。在我看来,接近理想或部分理想的实现才能算是一个时代是否重要的标准,而这是一个理想落空的时代,所谓“商业化”仅仅是想实现理想的手段,在中国它不是一个公平的手段,而且往往错位成目的。
从商业化的另一方面来看,因为人们永远无法抛弃价值,无法不留取自身精神需求,为了赋予商品以价值,就开始赋予其文化意义,就会借助于甚至窃取诗意、哲学乃至宗教。商品仿佛具有了生命,在忙碌的生存状况下给人以安慰使欲望得到满足,但这种精神与心理满足也是临时的,获得的愉悦和个人自由也是暂时的,很快会消失。消费主义深谙人类精神层面的饥渴,那么它一定分散了一部分诗意。
信息时代的各种快餐文化更多是一种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等种种速生速死的文化。“每个人都可以做15分钟的名人”是提供一种人之存在的新方式和思路,是一种观念艺术,一种预言。它是比喻性的,和根本的救赎无关。而真正的诗歌应具有长久的活力,只要它面向真理,就结盟永恒。诗的这个核心从来没有变过,尽管诗歌的语言方式和传播方式不断在改变。
既然任何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现实背景都是不稳定的,那么诗人和诗歌的地位更不可能不变,诗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有着很大的灵活度。
“被要求的诗歌”
加缪说,“真正的艺术家看重一切,他们逼迫自己去理解,而不仅仅满足当个评判”。
让我们回头看一眼30年以前的新诗与背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诗歌的革命,“新诗”诞生并无可阻挡地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主体。开启新诗写作的诗人们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和实践,推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转型。30年代有以诗歌为战斗武器的诗人群体,有“热情关注时代,企图用诗来唤起民众,使现实主义诗歌有更广阔的发展”的诗歌同仁,有以描写中国农民苦难命运为己任的像臧克家这样的诗人,诗歌的脉动一直朝向传达时代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以“诗建设”、“诗战线”为名的杂志,主张“投入战争,把新的血的战争的现实写入诗里”。1942年,24岁的诗人穆旦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以翻译官的身份参加“远征军”进入抗日战场,经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于成堆的白骨之上幸存,后来留下《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等著名诗篇。
自1949年到70年代后期,文学被逼上了专制之路,公开的写作完全受集团利益的控制。新诗提倡者之一、写过诗篇《女神》的郭沫若写下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这样的效忠口号,据说作者还是真情实感的。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文化旗帜。可见,在那个时代,文化的命运何其不堪。
文革后期,文学与诗歌开始复苏。经过文革期压抑已久的蓄备,出现了以知青为主的经历了十年浩劫、又私下读到“黄、白皮书”的一代青年诗人,内心充满恐惧、激愤、迷茫和失落,也有着对现实的反思和理性思考,同时还受到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感染,随着地下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刊,在全国范围内涌起了崭新的诗歌热潮,被称为“第二个新文化运动”。
这仅仅是一个大概的历程,我们知道复杂性只有深入单个诗人的个人经历才能呈现。现在的问题是,有多少作品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文学价值?有多少作品为后代诗人的写作提供了动力以及审美的活力?又有多少作品仅仅是一个时代口号式的呼吁以及对意识形态话语的依附(包括直接的反映意识形态)?“新诗”一路走来不是在正常秩序下展开的。在一次次秩序剧烈地动荡和瓦解中,诗歌的第一反应就是试图带动时代,而瓦解之惨烈使得身在其中的诗人们没有空间和时间来从文学的角度上对诗歌与时代关系进行冷处理。如此迅疾、灾变而复杂的题材没有盛放它的恰当容器,就像颠沛流离的悲愤灵魂没等到可以投胎的肉身。也许这就是所有灾变情况下诗歌的状况。我们也同时看到坚持下来的诗人,因他们自身经历里埋藏着巨大的伤口,保留着伤痛的感受,这感受和思考就进入了经验,参与了多年后的诗歌创作。诗歌有它自身的均衡活力,瓦解的暴力有多大,重构的能量就有多大。现实世界不能重构,但诗歌可以。
信息时代的今天,传播途径已经完全改变,诗歌引导或吸引“大众”完全是一种幻觉,也不再可能,曾经在这方面的辉煌成为记忆。我一直赞同诗人更应该以个人身份参与意识形态的公共话语。
诗歌有权要求一切,它却不是现实中的武器,它阻挡不了坦克已是常识。也许它曾经鼓舞过某个时代,却有失审美。加缪说得好,“我们需要锻造一种灾难时代的艺术,以全新的面貌获得再生,与历史生涯中死亡的本能作斗争”。自《今天》一代到90年代之间的诗歌写作出现过二元对立的阶段,要求诗歌工具化和追求纯诗类写作的二元对立,这种现象慢慢消解的过程也意味着上代诗人为后来的写作者■了更为明晰的路。
诗歌被它自身要求,被它自身对“真”的识别和承担人性的不幸与光明的诗性所要求,它与每一个明辨时代黑暗、面向真理和自由、以书写来保留生存与死亡尊严的写作者的人性来协商。此时,我想起经历了纳粹集中营的策兰,在他那里,集体与个人极度的苦难沉淀于内心作为不可磨灭的经验隐入文学,他的诗歌与他的经历不可分割,成为具有生命力的一体。所以他的诗即便离开他当时的时代,依然是伟大的文学。
本栏目文章选自深圳第六届“诗歌人间”研讨会
责任编辑 吴佳燕